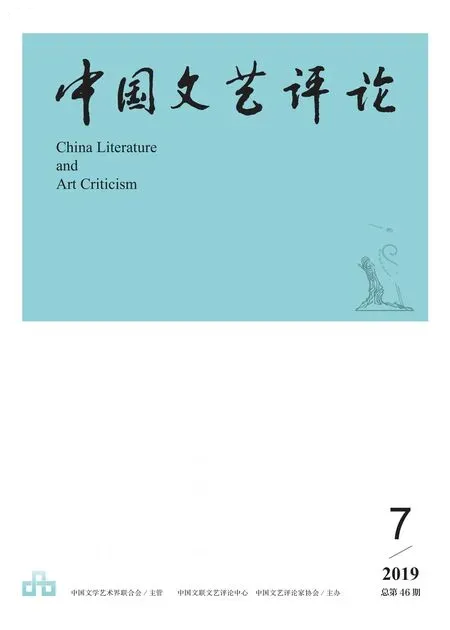心灵探索与精神抵达
——《酗酒者莫非》舞台艺术的美学阐释
张 荔
作为2017年林兆华国际邀请展原创剧目,波兰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执导的舞台剧《酗酒者莫非》2017年6月在天津大剧院首演。之后的两年里,作品先后在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地演出,所到之处备受关注。该剧高品质的舞台呈现,被普遍认为是“一部整体而言殊为可喜甚至难得的戏剧作品”。借助《酗酒者莫非》,史铁生的文学精神获得了超越本民族的世界性表达,其心魂漂泊与精神漫游具有了国际化表情;史铁生用文字营造的“写作之夜”戏剧性地转化为陆帕的“戏剧之夜”和舞台上的戏剧诗。
一、跨文化改编:是对话,也是融合
沉重的肉身、心魂的漂泊以及对生命困境的审视与精神探索,是史铁生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刻性所在,也是其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的魅人之处。一以贯之的追问与思辨贯穿史铁生创作始终,让他成为了“中国当代最具有自发的哲学气质的小说家”。正因此,排演史铁生的作品自然有其不寻常的难度;而对于来自异域的导演艺术家,更具挑战性。陆帕曾经多次感慨:“这部作品确实是一个挑战,但是我喜欢这样。其实我非常希望能够与史铁生对话,而不是仅仅依照他的剧本做戏剧。”
改编即对话。陆帕与史铁生的对话,有赖于对该剧主人公酗酒者莫非形象的塑造,或说有赖于王学兵扮演的酗酒者莫非。莫非是舞台的灵魂,是陆帕舞台叙事不俗的起点。在舞台叙事中,史铁生原作中的莫非与作家史铁生生命原型叠加,人物关系设置和性格塑造等显然融入了陆帕的生命感受、文化视域、文化精神和艺术探索。
该剧舞台叙事主体是史铁生小说《关于一部以电影为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下称《设想》)。在小说的戏剧改编中,陆帕将主人公酗酒者A改为酗酒者莫非,而莫非是史铁生《宿命》中的主人公。剧目排练后期宣传海报上的绿丝带——莫比乌斯环,正是源于《宿命》中的故事。其间暗含命运即圈套。在莫比乌斯环里摇着轮椅奋力前行的“莫非”,无论如何努力、怎样挣扎,也只能在既定的命运中循环往复。直面生命困境,对人内心的洞察与探索,令史铁生的文学表达知性、内倾。这些不仅体现于为人熟知的篇什,在小说《设想》中也有充分显现,只是,《设想》发表以来并未引起关注,仿佛一枚蒙尘的珍珠;正是陆帕的舞台创作,让它令人刮目。《设想》在碎片化叙事中,以酗酒者超时空的心灵独白解构当代人的精神困境,探寻生命的意义及对人的终极追问。

图1 《酗酒者莫非》海报
不仅《设想》和《宿命》,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合欢树》也都被陆帕编织在舞台叙事中,彼此勾连共同构建了莫非的世界。由小说中的A到舞台上的莫非,其间自然有导演作为改编者的创作意图。在陆帕看来,莫非的世界,因为有作家史铁生生命的遭际和精神生活为依托,已经不再仅仅属于酗酒者,而是众多处于醉与醒之间、在灵与肉挣扎中孤绝者的精神世界。对于导演陆帕而言,最富创造机心的,除了意味深长的酗酒者莫非的命名与塑造,更有在《设计》叙事主干上挖掘出的莫比乌斯环,以及在史铁生《设想》原作基础上进行的有效删减和慎重添加。
尽管史铁生在《设计》原作中再三强调,剧名不要改动,更不要更换。但陆帕还是把剧的名字改成了《酗酒者莫非》,而且把史铁生作品中酗酒者看到的一群少年宫的女学生,改为三个古希腊神话中代表“真善美”的“帕里忒斯”(女神),并将之在被颠覆的语境中浴火重生,成为世俗眼中的“问题”少女,而其实她们是三个广场大妈。即三个广场大妈在酗酒者莫非眼里幻化成了女神。这个片段是全剧唯一不用屏幕做舞台背景的一场戏。仿佛是被放大的“戏中戏”或者是电影本身,充满了魔幻色彩。其间,无论是酒的迷醉还是激情狂舞,无不是世俗人生中人们逃避生存困境和内心苦难的方式。尽管如此,人们依旧告别不了生活、亲人友人和爱情带来的苦痛,依旧孤独。酗酒,是莫非在孤独中的狂欢。而集体狂欢,不过是众人孤独中的沉醉。
莫比乌斯环这个全剧“主脑”的构思与立意、“帕里忒斯”(女神)以及宗教音乐和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加入等,充分显示了西方异质文化对东方文学的解读与重构。其中不仅有西方视域下的文化转移,也有一厢情愿的发展和再创造,但不能不承认确实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更具有世界性。
在这部戏的改编与创作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添加了史铁生原作中没有的、来自奥兰的女记者桑德拉,以及由此衍生的莫非与桑德拉之间的情感交集。在排练场陆帕说:“没有桑德拉,我就无法和莫非交流。”桑德拉代表了与史铁生不同种族的西方人,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陆帕本人。来自东西方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两个陌生人,身处困境与孤寂中的对话,延展和深化了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际遇:愈孤独愈渴望与他人沟通,愈身处困厄愈渴望挣脱。不论史铁生、陆帕还是众多文学艺术家,在直面困境时,往往把人的生存关系放在首位。在史铁生看来,“人是生存在关系之中的,意义产生于关系之中,世界是呈现于关系之中的。”与史铁生暗合,陆帕增加女记者桑德拉恰恰是为了建立一种关系,并将哲思潜藏于独特的关系之中。
该剧舞台叙事中《我与地坛》的加入,可谓陆帕改编遒劲的一笔;母亲与我、母亲与父亲、我与父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是这部剧最深奥难解的部分。陆帕将《设想》中父母关系与《我与地坛》中我和母亲的关系发生关联,并顺理成章推论出《我与地坛》中我与母亲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设想》中父亲与母亲虚伪的爱、甚至无爱。莫非不愿意和母亲独处、对母亲有敌意,也许是陆帕有意埋伏的思想密码。这些密码与深度是理解莫非苦难的根源,也与我们民族乃至人类的悲剧关联密切。盲目崇拜、强权、妄自尊大、奴性、虚伪等人的劣根性是父亲的,也是人类在欲望驱使下的通病;更有甚者,父亲一直在演戏,或者说在精神分裂的状态下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觉。而“一个时代之精神生活的分裂,和一个人之精神生活的激烈变化,其形式是一样的”。至此,陆帕导演的思想能力露出了冰山一角。
不得不承认,经由改编最终呈现在舞台上的酗酒者,已经不仅仅是小说文本中的莫非,他是史铁生、是陆帕,也是你、我。如此改编是陆帕与史铁生精神对话的结果,是他们的灵魂跨越了文化与时空,在戏剧舞台上的遥相呼应。在宏大的文化视域中,深度逼视人、人内在的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使这部剧的格局得以扩大、格调得以提升,具有了人类意识和终极情怀。陆帕及其团队的创作,充分验证了上乘的改编一定尊重原作,并在契合经典文本精神的前提下,与原作者深度对话,这是两者间的会意与神交;而且,一定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再创造。
二、循环往复的环形结构:人类境遇的隐喻
陆帕的戏令人回味,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对精神的深入探索;同时又极懂剧场艺术真谛、讲究戏剧结构。《酗酒者莫非》讲述的是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孤独者的宿命与救赎。陆帕认为,“史铁生是借用酒鬼批判社会中的幻想和虚假,这些虚假基于我们不太愿意去面对周围的真实”。在他看来,莫非喝酒,是为了找到爱,只有爱能救他。寻找、挣扎,在宿命中循环往复,是莫非抑或史铁生的生命状态,也很难说不是陆帕和你我的;这种生命观和美学意趣决定了这部剧的结构样式——内向化、铸灵性和追溯式结构。莫非“死后七天被发现”,这句统领全剧的导语,预示着全剧都是莫非死后的灵魂诉说。
内倾化、铸灵性及追溯式结构,是具体化了的舞台叙事策略,而戏剧的深层意味又隐藏在舞台叙事伦理的更深处,隐含在人物与人物之间、叙述者与人物、叙述者与观众和时代之间等各种关系的互动中。舞台演出中的故事经由陆帕重新结构之后,史铁生作品的意义得以衍生和扩张。莫非死后游魂和生前醉语,伴随主人公意识的流动自然拼贴,这显然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戏剧架构。但是,貌似随意流动的主人公内心生活的碎片,绝非没有章法;相反,该剧的结构暗合史铁生的创作思想和圆形思维。在史铁生看来,“过去和未来无穷地相连、组合、演变……那就是梦想,就是人的独特。”而“人与世界相处的形式是无穷多的,就像一个小圆由一个大圆包含着,大圆又由更大圆包含着,以至无穷”。于是,在“写作之夜”的时间之流中,史铁生的心魂自由自在地漂泊和找寻。线性的时间被颠覆,人与事交叉混淆、荒诞不经;在循环往复中被孤苦和死亡困扰。写作是史铁生对宿命达成的和解,也是自我拯救和超越……而这一切显然已经被陆帕悉心勘察到,并以“很陆帕”的方式布局在舞台演绎的分秒之间。因此,《酗酒者莫非》的舞台文本,打破了线性时间逻辑,实在的物理性时空被虚幻的心理时空所取代;舞台叙事呈多层级、多维度的圆形结构。
这部剧的圆形结构首先体现在全剧的架构——死去七天的莫非面对自己过往的真实生活,却无法进入。在真实与虚幻的撕扯中,莫非过往的现实人生和精神生活形成了两个圆形的环。与此同时,剧中的圆形结构还呈现在情节、片段前后呼应中构成的一个个小圆环,比如第二幕和第三幕母亲的戏、第一幕和第三幕桑德拉的戏、第一幕的梦和第三幕的幻觉等相互呼应、映照,同时又自成一体。这些小圆环并置于全剧,构成了整部剧莫非命运轮回中的莫比乌斯环。具体体现在剧中多处圆形或环形舞台行动的调度图谱。比如,影像中的自行车、汽车和行人的行动线,以及重头戏中演员舞台行动的调度。以后者为例,在莫非幻想中寻找杨花儿的片段里,杨花儿在屏幕深处出现,伴随镜头缓缓推进,杨花儿置身屏幕下方,当走到屏幕边门时,影像转换为杨花儿演员的实相,她推门进入舞台真境。之后,在莫非的幻想和诉说中,杨花儿从左向右款款前行,绕到屏幕后侧时屏幕上杨花儿的影像替代了实相,之后再次从侧门进入舞台,如此,杨花儿围绕屏幕的行动路线刚好是一个圆形。圆形的循环恰如杨花儿在莫非心海中的状态,反复萦绕挥之不去;又如他们之间的关系,绵绵无绝期。
少年莫非与母亲的片段里,莫非舞台行动的调度也是圆形。母亲试图安慰孤独的莫非,“人可不是为孤独而生”“想去就去吧”;残疾绝望中的莫非,内心抵触着外界、母亲甚至自己,决绝地说,“我可以不去”,而身体却不由自主地转动轮椅,一圈、两圈、三圈,圈越转越小,内心的局促不安越发强烈,他竭尽全力掀翻了家里的桌子,绝望中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号叫……残疾,就是命运和莫非开的玩笑,让他困厄、窒息、生不如死。在陆帕看来,“残疾与酗酒,某种程度上是同等的,每个人内心都有残疾,精神上的残疾让人与社会隔离。史铁生是借酗酒者说自己的话,我们通常不重视酒鬼的醉话,认为是一大堆无意义的话,但恰恰在醉酒状态下的人才会有恍然大悟的感受。我做这个戏,目的是让每个观众能够通过这个作品,看见内心没有意识到的黑暗空间,更了解自己隐藏的内心世界,把被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最令人回味的是,全剧的尾声,屏幕中健硕的少年莫非骑着自行车,一圈又一圈地转,转出两个圆形组成的横8字型,走过两个相连的圆环路线后,停留……静默中发生了惊天大逆转:自行车轮子没有碰到那个给他带来厄运的茄子;而且,井盖是盖着的,对面驶来的汽车根本没有和莫非发生任何关系,至此,大幕落下……如此开放式的戏剧结局,再次紧扣莫比乌斯环的总体意象,为全剧点染了诡异、荒诞的味道。剧中的莫比乌斯环影射了莫非的命运,也隐喻了具有普遍性的人的际遇,是人类的共同境遇。莫非只能如此。至此,陆帕对全剧及酗酒者冠名为“莫非”的创作理趣和机心再次彰显。
三、诗化象征:心魂之思与想象之舞
《酗酒者莫非》的艺术品质,除了有赖于高超得当的文本改编和戏剧结构外,更与影像技术关系密切。大屏幕影像和舞台表演在互文中相互辉映。舞台上植入影像是近年舞台呈现的趋势。陆帕作品也不乏类似创作,只是这次难度和力度都非同寻常。剧中的影像与表演水乳交融,共同营造了一个象征无处不在的艺术有机体。陆帕的神思妙悟,诗化了史铁生的心魂之思。
1. 屏幕:象征性空间语汇
作为剧场艺术,在实现文学叙事向舞台叙事的转化中,“空间的表达”尤其关键。所谓“空间的表达”即:如何将戏剧“空间”在一定演出“时间”里生动地建立起来,将空间的艺术跟时间艺术有机勾连,从而构建舞台上富于美学意味的个性化时空表达。具体体现在舞台创作上,往往是个性化舞台形象和视听语汇的构建。在这部剧中,屏幕中的影像与剧中其他视听语汇共同打造了这部剧个性化的整体舞台形象。
屏幕中的影像在剧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角色在真实舞台与虚幻屏幕之间游走,凸显了史铁生原著对世界真实性的质疑及其诸多哲思。同时,屏幕及其影像还承载了多种功能——是活动的布景,也参与叙事和表演。就视觉语汇而言,影像不仅提供剧情发展的环境,同时是一种有意味的意义符号,暗示剧的深层意蕴,从而与其他舞台元素共同打造了该剧的诗剧风格。
屏幕,作为《酗酒者莫非》的整体性象征形象,是史铁生小说《设想》文学文本提供的。史铁生在小说开篇写道:“每个人都是孤零零地在舞台上演戏,周围的人群全是电影……”应该说,在文学文本引领下,以电影屏幕为舞台背景,构建这部戏的整体性象征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不断勘探和挖掘史铁生文本及其精神诉求,从中自然生成想象瑰丽的诗意具象,且将之恰当而微妙地埋伏于演出之中,为表演效力。自然,史铁生作品的心理复调、情感丰沛等,为陆帕及其团队提供了施展空间,但也构成了挑战。
在宏观上,在演出的视觉语汇中,舞台中央核心演出区的大屏幕如同电影银幕,依剧情发展随时变化视觉语汇。屏幕上主体视觉语汇是空旷的广场和远处的高楼,偶尔过路的车和行人,更多的场次里屏幕上是颓败的广场和斑驳的墙面。舞台两侧建筑工地脚手架和垃圾堆,公园的长椅、简陋的家具,舞台前台口和大屏幕的边框被刺眼的红线勾勒。后台则比一般舞台剧开阔得多,巨大的弧形幕布对整个舞台呈包围之势。这就是莫非的生活场景,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存场域。生机活力与腐烂垃圾并置,自由被规约捆束;各色人等在浩大的宇宙中行色匆匆,渺小而可怜。屏幕上开出的两扇“门”、一个窗,以及投影技术的娴熟应用,使得人物进出幕布的那一刻,幻想的虚幻与实有的现实自然连接。人物知觉的外部世界与潜意识内心世界的秘密通道被打通,舞台时空也因此自由开放,莫非的精神漫游,变得可触碰、可感知,灵动自如。以第一幕开场为例,孤苦无依的莫非游魂般逡巡于灰色、昏暗的胡同间,他混沌、疏离、没有着落,用力叩击紧闭的铁门,门内却无一人应和,只有大铁门无比沉闷的回响。影像中的莫非越来越局促、胡同越来越狭窄。舞台上是莫非“我死了七天才被发现……”的现场表演,配以影像幻觉中视像的冲击,主人公的生存困境和内心情境透过慢镜头的影像,清晰可感,令人玩味。
剧开场的影像中胡同空无一人,只有莫非的心魂游弋。伴随剧情的发展、莫非生存际遇和内心生活的演变,屏幕上的胡同语汇也不断变异。当莫非想念杨花儿、赞美真爱——“爱就是不演戏,杨花儿就不演戏”,随即寻找杨花儿的幻觉出现,胡同影像再次出现,而且加入了人像——胡同里那些面孔怪诞、眼神怪异,人们三三两两或漠然或令人毛骨悚然地死死盯视莫非,在双方眼神对峙中,这些人聚拢成人墙,将莫非隔绝在人之外……在剧中,如此象征性视觉语汇层出不穷。其中胡同和墙的视觉语汇极具冲击力。胡同、墙是现代人彼此隔绝、内心孤寂的视觉化,是典型的诗意语汇,让人仿佛阅读一首首高冷的现代诗,又如同品味一幅幅超现实主义画卷。值得注意的是,在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中循环反复出现的核心意象与陆帕舞台上的影像遥相呼应。小说中游走的是千年行魂,是约束人自由的森严壁垒、裸体之衣等。小说里的“墙”和剧中一样,也是“鬼打墙”的意象,是人与人、心与心之间的隔绝和梦魇,是自闭和循环怪圈中心魂的游荡……史铁生文本中的内心意象被陆帕自觉不自觉地幻化为舞台形象。
作为“有意味”的舞台布景,屏幕及其间的活动影像构成了这部剧表演赖以存在的视觉空间,也是精神载体。同时,它又始终指向表演,成为表演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具有符号意义,意韵幽深、富于活力的部分。
2. 影像:有意味的形式
在该剧中,作为特殊的“舞台形象”,影像承担了多种使命。最显而易见的是,影像的表演成为组织舞台事件、配合舞台行动的手段,特别是有效调控了戏的速度和节奏。可以设想,在这部近乎意识流的剧中,大段人物内心独白构成的内向化叙事,如果段落与段落之间、幕与幕之间抽去影像的调节,势必影响观看效果。在演出中陆帕将台词做了减法,大胆删减后的台词洗练、蕴藉;而以影像贯穿全剧,且铺排有板有眼,颇具章法。
在这部剧中,影像的使用及功能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影像构成人物舞台动作的背景、支点和参照,与剧情交融。在剧中大量使用城市广场、摩天大楼、汽车、自行车和路人的背景影像,再如公园和长椅、枝桠旁逸斜出的茂密树林。在第一幕中,影像作为叙事背景,帮助演员实现了表演时间和空间、室内与室外、现实与梦境的自由穿梭,戏剧的现场感和电影的镜头语言交织为一体,奠定了这部剧的舞台基调。第二幕,轮椅上莫非在小公园的影像有力衬托了主人公的生活际遇和内心情境。孤独、孱弱的莫非与公园旁逸斜出、茂密而杂芜的环境形成对照,更显莫非的渺小渺茫,公园的硕大而荒芜。不能不令人思量史铁生的“地坛”“合欢树”和命运对其极大的不公与其对自由美好的憧憬。类似的段落在剧中比比皆是。正由于影像的合力,文学文本获得重新剪裁与编排,很多舞台瞬间被影像放大、定格,为剧情营构诗意。
第二种:在剧的关节处和重头戏中,活动影像营造了氛围,同时也扩展了人物内心空间,为点染主题效力。以桑德拉与莫非在公园二度相遇片段为例。莫非迷醉在公园长椅上,伴随他的愁苦心境,身后屏幕的影像中逐渐出现了漩涡,继之巨大的塌陷,随之而来的是硕大无边的坑洞。漩涡——塌陷——坑洞,影像的视觉冲击,伴以台上演员的即兴表演,莫非的内在心像被凸显、放大。孤独就是人内心的塌陷、内在的坑洞,越绝望无援,内心的塌陷和坑洞越大,如临深渊。此时再次出现的桑德兰恰似莫非的救命稻草。再如“回到过去”的片段,年少的莫表情冷淡,不停眨眼睛的巨幅影像,以及穿越未来中莫非的迷醉、洪水滔天、来自地狱中三个裸女的重头戏,作为剧的高潮,莫非内心独白部分的影像,伴随他情绪的变化,形成一种咄咄逼人的舞台气势和象征氛围,点明并深化了主题。在这些戏眼处,影像非但没有抢戏,而是令演员的现场表演在影像的助力下更具感染力。
第三种:在影像的交融和衬托下,大量活动影像与演员表演的对接了无痕迹,凸显了该剧虚实相间的艺术创造力。以剧中耗子的影像和莫非前后呼应的对话为例。在第一幕“夜梦在家”片段中,屏幕下方呈现一只耗子的影像,耗子由右向左爬行,爬至屏幕左下角的“门”边变幻成一个人形,这个人形演员与耗子影像自然衔接由门入场,进入表演区;下场也以同样的方式展现。再如,莫非的过去——莫,出场前,他在屏幕深处的影像缓缓前行,从虚幻的屏幕一路走来,开门后,真实的莫走出来,坐到莫非所在长椅的一端,与莫非攀谈。从虚幻的影像到真实的表演,亦虚亦实,梦幻中恍若置身魔幻世界。在重叠复调的舞台叙事中,莫非内心幻化的影像与生活真实的现场表演、生命的真实与虚幻、醉与醒、梦与真相互交织和渗透。舞台如此,生活亦然。
3. 灯光:明暗之间的间离与唤醒
“在一出戏的演出要素中,再没有什么比灯光更有效地传达其情绪和情感了。”在这部剧中,灯光还别具功能,是表演的组成部分,也是象征性视觉语汇的一部分。
当莫非被隔绝、孤苦压迫时,场灯伺机大亮,此时置身剧场幽暗中的观众被明亮的场灯照亮、间离出剧情,在惊醒中无法继续沉醉,不自觉地卷入思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内心不也同样被各种有形无形的墙、各种怪诞、匪夷所思的人和事包围和挤压吗,我们不也同样在热闹中孤寂、在繁华处寂寥吗。就这样,几次剧情灼心处,场灯随之亮起,令人警醒和陷入深思。与亮场灯相映成趣的是,三次惊心动魄、戛然而止的黑场——在全剧接近尾声时,三次急促惊悚极其刺耳的音响、伴以黑屏、黑场。
当莫非死后,重返人间,寻找亲人和爱人,他终于对着妈妈大声喊出心中的积郁——“请不要在没有爱情的时候生下我”——演员王学兵的情绪在不断堆积中推进,最后如火山喷发。与此同时,瞬间黑屏黑场。第二次是与杨花儿相遇,杨花儿述说了内心的凄苦:“没法爱,也没法不爱”;“你在下沉,我也在下沉”……第三次,莫非倒地,而对面驶来的车绕道而行,没有撞到他。如此三个回合的黑屏黑场,加之重金属爆破音,观众在惊奇中惊醒。三个关节点点醒的正是关乎人及人类的终极思考:我们是从哪里来——莫非生命只能在无爱、虚伪的爱甚至仇恨中诞生吗;我们要到哪里去——莫非只有无休止地下沉,在命运的怪圈里循环往复吗……灯光语汇独特的空间叙事,无疑是该剧内向化叙事的外化形式,为舞台叙事助力。
4. 心灵独语:叙事时空的自由穿梭
剧中大量象征语汇隐晦深奥,并非所有观众都能心领神会。很多片段、诸多台词由于阅历、修养等不同,理解的程度自然有别。比如剧中莫非与杨花儿探讨昆虫的“床戏”,台词蕴藉诗意、画面唯美。醉酒的莫非困顿绝望,和同样疲倦、无助的杨花儿同置一床,但是,他俩的身体却隔离着。此刻,爱已尽,爱情变成了自救和救赎的渴望。这个片段语义隐晦、多解。影射着人在轮回中恐惧、绝望的宿命。爱与被爱,渴望而不可得,沉沦于宿命的怪圈,谁也无法拯救谁,甚至无法自救;人人都如同被套入莫比乌斯环中的莫非,身心残缺,挣脱无力。
与这段“床戏”相似,莫非与母亲的两场戏,没有温情脉脉的暖色,同样是漠然、隔绝。不懂怜惜母亲的莫非在抱怨,而怜爱儿子的母亲,同样不知道怎样尊重儿子、不懂如何释放自己的母爱。当儿子终于被母亲感动拥她入怀,母亲的双手却不知所措,局促中展开双手,竟然没有一个母亲对儿子应有的爱抚。这两场戏的表演都是虚实交织,屏幕上的影像放大了人物神态,与台上的即时表演相得益彰。
爱与梦幻是史铁生文学文本的叙事密码,也是陆帕舞台叙事的关键词。对杨花儿的爱情、对母亲以及妹妹等亲人的伦常之爱,是莫非的困境,也是连接他梦想和希冀的纽带,但这些几乎不是陆帕所要表达的最终意图。他舞台叙事的全部激情,并非为了人世间各种实在之爱和实有困境,而是在探讨人的困境何以产生,又将如何摆脱,或怎样与之达成和解。陆帕似乎更关心——在心魂的漂泊和精神游荡中,人如何能活得有尊严、爱得有意义;人何以进入天堂,而不是堕入心的地狱——心狱。因此,在戏的高潮“走进未来”,陆帕运用了夸张而极具冲击力的视听语汇:酗酒者莫非癫狂的醉态和诳语,配以音乐,在时空穿越中,展示人的命运和人类未来。
莫非心灵的独语作为叙事方式,在表演与影像诗意的象征中颠覆了时空的拘囿,突破了传统戏剧的情节链,在貌似无序却有机关联的情节碎片的拼缀中,陆帕带领观众沉入了莫非的精神谷底,也引领观众审视和观照自我内心。在虚实辉映中,达成了对史铁生灵魂写作的自觉膺服。
这部剧中影像的长度和剧的长度一致,相当于拍了一部同等时长的电影,是陆帕戏剧中技术难度最高的一部。他“以欧洲当代文学剧场的理念方法,创造出了影像和心理时空的奇妙结合……体现了当代剧场对戏剧文学本体的尊崇和回归”。贯穿全剧始终的影像,以及剧中象征语汇的舞台呈现为全剧镀上了诗的意趣和象征色彩;连同其他视听语汇独具匠心的悉心营造,不仅有助剧的内在蕴涵进入了精神层面, 更使艺术想象、创作构思与舞台实现了理性的超越;在特定舞台语汇里,令观众收心内视,感悟其间无处不在的哲理与诗意。
近年我国引进的陆帕作品多高冷、沉静,在京津沪为核心的戏剧界不断引发热议。百家争鸣之中,无法否认他是一位天赋极高、艺术品味不俗、追求个性的导演艺术家。包括《酗酒者莫非》在内,他的舞台创作以其高超的思想阐释力及舞台艺术的创造力,在当代中国剧坛产生强烈反响。作为跨文化联合创作,陆帕对史铁生作品的舞台演绎并没有呈现出水土不服;但一定有诸多“很陆帕”的元素在排演中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等被消弭在舞台上。联合创作消耗导演等主创自身能量也不可避免。不过,当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时,演出激发的情思及其在观众内心的持续发酵,无疑是演出成功的反响。这部剧对中国当代戏剧界的价值与影响,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毋庸置疑的是,《酗酒者莫非》高品质、跨文化的创作,在当代中国演剧史上一定会留下其独特的印记;特别是,该剧创作中中外戏剧家在人文精神、现实表达、美学实践上的深度交流与相互碰撞,无疑有益于对戏剧本体的认识和戏剧文化生态良性发展,进而,为我国戏剧健康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