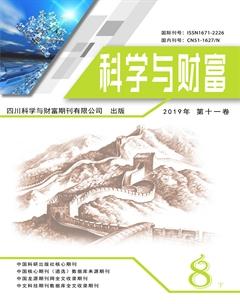浅析网络钓鱼中的犯罪认定
摘 要:随着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中国已然迈进了互联网信息时代,而以网络平台为依托的互联网社会也逐渐成型。纷繁无形的光纤将天南海北的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在享受其带来的十足便利的同时,虚拟的网民身份,复杂的计算机程序等,也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致使类似臧进泉案的网络盗窃的新型违法犯罪活动随之蔓延。而针对这一新型犯罪方式如何定性,理论界和实务界有一定争议,下面笔者将以最高院的指导案例臧进泉等诈骗盗窃案为例。通过其中争议的焦点,来阐述笔者对这类利用新型犯罪手法犯罪的定性分析。
关键词:网络钓鱼;臧进泉案;盗窃罪;处分意识;因果关系;期待可能性
一.案情简介
2010年5月开始,臧进泉、郑必玲、刘涛等人流窜在江苏多地网吧,以在淘宝网开设虚假店铺的方式,欺骗买家将货款汇入其在支付宝所设立的私人账户中,以此来进行网络钓鱼。在郑必玲骗取被害人金某货款195元,并得知其网银账户余额为30余万元后,臧进泉遂以尚未看到金某付款195元成功的记录为由,诱导被害人金小丽点击一个表面上标注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元而实际却植入了支付人民币305000元的计算机程序的虚假链接来确认之前的交易行为,在被害人金小丽点击确认支付后,其账户余额30.5万元随即进入到臧进泉注册的账户中。针对前述骗取货款的犯罪方式构成诈骗罪是得到学界与实务界的普遍认可的,但是利用一元的虚假链接的犯罪事实是构成诈骗罪还是盗窃罪,理论界与实务界掀起了一番讨论热潮。下面笔者将针对此案来简要说明笔者对于此类案件关于诈骗罪和盗窃罪的划分标准。
二.对网络钓鱼中的犯罪行为的定性分析
(一)被害人是否具有处分意识
盗窃罪中财物占有的转移是违背被害人意愿的。所以,如果被害人自愿处分财物,则不可能成立盗窃罪。一般认为,处分行为的成立,不仅要在客观方面有处分财产的事实,主观方面还必须具有处分财产的意思。而在本案中金某虽然有处分人民币一元的行为,但是对于剩下的304999元财产的非法转移,并不是处分,只是简单的交付行为,因为她并没有自愿交付30.5萬元的主观意愿。
在具有十足特殊性的网络空间,其犯罪手段复杂多样,为了更好地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理应采用刑法学界通说的观点,处分意识必要说。因为首先诈骗罪中的交付关键在于“基于错误认识而产生处分意识,并以此来处分财物”,所以,诈骗罪中需要有错误认识和因错误认识而产生的处分意识。其次,在盗窃罪间接正犯的案件中,若被利用者为不知情人,假如仅因客观的处分行为认定其未处分,而忽略处分意识,那么,就难以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间接正犯的界限区分开来。据此,把是否具有“处分意识”来作为网络钓鱼案件中诈骗罪和盗窃罪的一个判断标准,是十分合理的。即被害人金某具有处分意识则为诈骗罪,不具有,则为盗窃罪。而在本案中,被害人金某不仅要在客观方面有处分财产的事实,更要在主观方面具有处分财产的意思。就被害人金某而言,其点击一元支付虚假链接,只是以处分1元钱的意思来确认之前195元的交易,但对自己合法占的304999的转移毫不知情,其也并未同意或授权臧进泉转移自己占有的304999万元。所以,在被害人对自己行为直接后果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害人金某并没有自愿交付其304999元存款的意思,更谈不上被害人自己主动将自己的合法所有的304999元进行转移。因此,本案中被害人金小丽欠缺处分意思,其行为不构成处分行为,财物的转移违背被害人的意愿。
(二)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
在本案中,臧进泉的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的因果关系属于介入受害人行为的类型。关于其一系列的犯罪行为不能单独地割裂来看,应该做出整体地评价。臧进泉,既伙同郑碧玲骗取其衣服的货款195元,又在明知点击一元的虚假链接会导致被害人损失巨额财产的情况下,继续诱导被害人金某点击一元支付的虚假链接来确认之前的交易的等等一连串的欺骗行为都是在为后面的窃取行为做铺垫。被害人金某成为臧进泉所利用的“无意识的工具”,在自己的意志不自由的时作出的不自主行为导致了巨额存款被非法转移的危害结果。而被告人臧进泉通过一系列行为已经完全对被害人金某具备了压制性的意思支配能力。即金某受到臧进泉的欺骗行为影响,认为只有点击1元支付链接才可最终获得购买物品,可见,臧进泉对被害人金某点击虚假链接转移财物的行为起到了支配性作用,被害人金某并不能具有控制能力,可以认定为臧进泉前行为的一个延续,因此,被害人金某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而臧进泉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可以将其认定为 “利用他人自害行为”的间接正犯形式的盗窃罪。
(三)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
正如前文所言,臧进泉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受害人金某的行为介入而中断。如果受害人金某是处于可以自由选择和控制的状态下,那么,受害人金某的行为与臧进泉所做的前行为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则受害人金某应该对自己所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具有期待可能性,即只有金某能预料到自己点击一元的链接会导致自己的30.5万元被转移到他人的账户中的结果,才可说金某对自己的行为具有期待可能性。随即建立起被害人金某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被害人金某在此情况下应当承担责任;但是在本案中,根据具体案情可得知,被害人金某在财产被转移后,接收到信息时方才知道其损失了巨额财产,所以,被害人金某并不能预测到其行为带来的结果,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其行为也就与危害结果没有建立因果关系。
三.总结
由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使得利用互联网犯罪的新兴犯罪手段,不能单纯地仅适用现实中的判断标准,更应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其犯罪行为作出应有的评价。而本文仅以臧进泉案为例,以期为实践中复杂多变的网络钓鱼案件提供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徐光华.刑法解释视域下的“自愿处分”——以常见疑难盗窃与诈骗案件的区分为视角[J].政治与法律,2010(08):49-58.
[2]张明楷. 论盗窃故意的认识内容[J]. 法学, 2004(11):62-72.
[3]王立志.认定诈骗罪必需“处分意识”——以“不知情交付”类型的欺诈性取财案件为例[J].政法论坛,2015,33(01):119-131.
作者简介:
单江沛,女,汉,河北衡水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