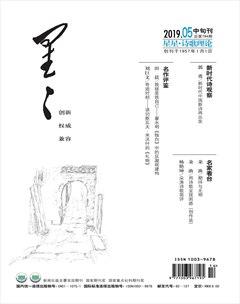树桩上的雪
王之峰 王克金
向东虽然被冠以“乡土诗人”,但他的诗早已从农耕文明的乡村语境,拓展到世界视野的人文语义场。他张扬生命主体,观照、审视生存境遇,不断扩展自己的感知边界。他写树、写草、写花、写石、写鸟、写人等等,无一不触及到生命。他完全是站在原乡的背景上叙写生命。农耕只是这类生命存在的方式,也许更原始化。他们每时每刻离不开土地,他们的衣食来源完全依赖于土地,他们的命运更是与土地凝结为一体。为了说明这类生命与土地的密切性,我们姑且称这类生命为“泥土生命”。下面的几个阐述涉及生命部分基本上是在“泥土生命”的角度下展开的。
那些改变了历史的尘埃
陈超说过:“记住,个人是最多的,比整体多出一个”。陈超作为先锋诗歌研究者,说出这句话,是在自省个体生命的个人生命荷载对文学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作为同道,向东尊重生命,对原乡生命与生存双向观照。他聚焦故土人物,用诗人之灵深访那些“改变了历史的尘埃”。
长期以来,诗人与故乡在内心相互依存、唤醒、碰撞,在俯仰省察中获具自身痛感,迹写举轻若重的悲悯。诗人受感于自己的家公文奎、二爷文孝及其真刀真枪和鬼子拼过命的抗日民兵队长青山、“子弟兵的母亲”司玉荣、不争个人名利,埋地雷炸鬼子的刘申、吹唢呐的赵福安、庄稼人刘臣等这些人物在舍生取义时的凌然与忘我,在民族性上,大写他们“活出了令人仰慕的背影和脊梁”,活出“直立的资本”。这些人“或用骨头照亮道路,或用胸脯温暖大地”。向东对这些人心感事知,完成了有精神重力和灵魂维度的人物塑型,让他们鲜活地矗立在历史语境。
“燕山啊/我灵魂的父王命运的主/满载石头和呼吸的古船”(《燕山》),在诗人向东笔下,八百里燕山的石头里有太阳,上庄的土里有神。这些都仿佛是生活启示录,他抓住原型意象蜕变。李白写下“燕山雪花大如席”。在燕山深处上庄,在河北兴隆,西大梁上,向东的先人披覆李白之雪,“黄土炕上生儿子,黄土坑里埋祖宗”。《新房子》一诗,向东不是在直陈一个物质的在,而是仰望生命的诞生。诗人不过是在借助乡土物象和语境,抒写生命,唏嘘存在。
鄉土“物象”,一旦有了像“文物一样的历史内涵”,就承载了精神意象的全部。这些意象如麦田里的白骨引发生与死的历史想象。当一棵大树成为一个村庄的象征,也是大树成为生命的象征,当一棵树成了人的象征,也是能构架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互关系的象征。
老家,老屋,青瓦檐下/格子窗前/老枣树躬身站在那里/你说那是你的/老母亲//另一棵老枣树/在老屋土院的外边/碾道的南边,老井的北边/老母亲见谁问谁/那是谁啊
——(《老枣树》)
通灵历来存在于人与物之间,它是两个或多个“生命”之中的某个瞬间约定。上述诗句看似人物叙事,实则是意象言说。老枣树是一个隐喻。在老枣树、老母亲、另一棵老枣树三者之间,不同的生命形式在诗人的精神情感世界是一体的。
面对必然的死亡,向东关注众生死亡之后的灵魂归属。风土中,客死他乡的人都抱有一颗“痴心”望归的灵魂,这是千百年来民族故土的向心力使然。诗《小石门悬棺》《客家》《慰魂节》都逼近了一种凄楚、酸辛的生命状态。对于客死他乡的人,冥冥之中安排了一个希望和归期,一句“时候到了”,便是对悲壮、惨烈的慰藉。那些从中原迁徙过去的“客家人”一代代客居,一代代死去,却“归心不死”,“把骨殖埋三年挖出来入瓮/摆在大道边/等着回去//虽然知道等着也是白等/还是等等/再等等”(《客家》)。诗中的“等”字,直指悲辛的极限。
困惑与忧患的新视野
当人们谈及忧患,多在家国,而诗人向东却聚焦在人类整正,用个体生命去丈量人类集体的命运。他不再是一腔热血地写,而是在个人化历史想象中脱胎换骨地、充满忧患地叙述。诗人沉思的参考系不是一家、一族、一国,而是地球与世界。诗人的美学原则是现代的,人文理念是人道。在隐喻的遮蔽和象征的澄明之间,诗人是无为无不为的。
向东的组诗《记忆的权利》关乎民族气节,历史与正义,表现了勇敢无畏的牺牲精神。诗人的道义是在战争的污血上让审判和救赎同时发生。这一组抗战题材的诗,将正义的剑从纪念碑里拔出。
这就是记忆
是一种权利
也是庄严的法则和启示
人无分长幼
栽下头颅长出壮士
地无分南北
种下落日收获晨曦
——《胜利的记忆》
诗在理性认定,感性表述之外,也还原了家乡人的慷慨与悲歌。我们不答应“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我们《守望长城》,我们《保卫长城》,我们浴血《喜峰口》的抗战,我们前仆后继才有了《纪念碑》上《胜利的记忆》。这个记忆就是“为了抵抗命运……/可以放弃脑袋/但不能把沙子揉进眼里”(《胜利的记忆》)。
优秀诗人的视野宽阔在未来。诗人向东的良知在于,他能在个体与整体之间觉悟、举证、演绎、归纳出整体世界的可能边界,去责任、担当人类的共同命运。每个人尊严、自由、和平的天赋权力都应该得到享用。在地球的边缘,他调整自己的姿态和视角,见证历史,辉耀情怀。《告别》里的伊扎克·拉宾,《柏林墙的影子》里的平民,诗人马哈墓地的灯光,贝尔格莱德的“花房”(铁托墓)的蜜蜂和花朵,都是对人类“一边梦想一边作战”的反思。写到这里,想起波兰诗人米沃什这句话:“如果不是我,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诗人向东在穿行于鸽子、橄榄枝、炮火和地雷的呼吸中,祈祷太阳清晨升起,光明充满大地,生命之火永不熄灭!
经典,语言言说和诗艺言说
诗就是诗!诗,思、言合一,但思与言之后,必是言之有物的审美实体,能显示独自的生命体征。向东的诗在真上求朴,在朴上生拙,于浑朴中见旷邈、显幽邃。这是读《沉默集》的感觉。其诗,及物、有效,远看有块垒的墨色,近看有一吻江山的梨花。
诗人向东用语言在从事另一种生活,他厚养于方言母语最初的精神哺乳期,而他也生活在别处。
有时大老鹰是静止的
是天的补丁
似乎没有它
天就有漏洞
——《大老鹰》
诗不仅独特而新奇,在钝化感受力的同时,要在语言场中达到炼字炼意炉火纯青。然而,在语言之外,试想除了女娲能补天,还有谁能?燕山上空的“大老鹰”,是诗人自己的心理响应。向东心有一片草原,他向往自由。他的《牧马人》中的“牧马人”,就是白云下牧游的诗人自己。醉卧花丛,在马头琴和古老的长调里望着天空的空,恍若虫儿成草、草儿成虫、虫草成龙,渐次进入自由的,萬物有灵的,相互替换、相互转世的沉醉。
向东用语言托起了生命与实在。语言自觉是诗意成熟的标志,简约并不简单的语言,犹如每一个透明的黑夜都经历了时间一样,能激活语言自身的生命性。向东的诗语是减法,是琢磨、消除、剥离,有语言生命本体的光泽和鲜润,能抵达无限的“没有面颊的笑容”《半坡村》,同时见证语言自身有效的表达和审美的愉悦释放。时空张力和生命角力,陡然让语言楔入历史语境,言约意丰,言近旨远,复现“历史与生命的辙印”。诗人也让生命律动在语言中:
天/可以没有横梁没有支柱/但一棵树不能没有年轮//冬天来临/阳光冰冷/一场雪压实另一场雪/年轮不见了/只见树桩上的突兀的白/苍白的白,白发的/白!白骨的/白!空白的/白!//孤零零/一顶白帽子悬在空中/
——《树桩上的雪》
语言个性、卓越,现纯然之态。语言个性就是生命个性,节制、冷静,不倾诉而呈现,如高空坠物,气场强大。每一个“白”字都有不同的生命语意在栖居。
诗来自神秘,也走向神秘。诗若是无点滴神秘,在诗的意味上,则难于成立。真正的为诗者不会否认这一点。《2010年7月17日深夜与大解在草原说草》一诗中,诗人的生命陷入了无限的惆怅,因为他看到了“风把草原吹过来”,而不是把一棵草吹过来。道家洞悉整体,但也分一二。诗在哲学的关照和映射下,给出神秘中的在。草原是抽象性,但也及物及心及境。一种彼此依赖的在,克制的在,此消彼长的在,形而上的在,汇成一体。对生命、生存的多重观照,在自我意识的深层,成了深海里倒立的钢钉。这不是视通万里,神与物游,仅仅是一次阳光下的呼吸。蝉完成了诗人的隐喻,但通往渺远的哲思,却没有戛然而止。
向东《沉默集》中的每一个词就像他写到的白洋淀的柳树,都曾拴过乘风破浪的船。古川俊太郎说:“推敲沉默/没有抵达语言的途径/推敲语言/抵达这样的沉默”。向东推崇并暗地里借用这样的话,自有他的道理!
附:刘向东的诗(二首)
守望长城
我和老屋,在长城边上
这里居留着最后的太阳
这里有无人清扫的月光
许多死去了的都还活着
不少活着的懒得再活
我和老屋,在长城边上
我们把自古英雄守望——
他们无处告别
也就无从离去
他们拥有江山
却又两手空空
他们为长城而死
对坟墓从不适应
他们因长城而活
生命有永恒的特征
我和老屋,在长城边上
一切皆我亲眼所见——
亡灵和石头一起养神
以沉默预言战争
他们出入残损的古砖
在鸡叫之前散步
他们从不与我交谈
只听我不能说出的话
我和老屋,在长城边上
看长城是活的如一只尺蠖
要么前进,要么后退
忙着把山河岁月丈量
我和老屋,在长城边上
高高的向日葵贴紧城墙
死亡在它的思念之中
它在思念中继续生长
小石门悬棺
悬棺何止江南有
雁门关外,小石门前
悬着悬念
悬着
心
你们从哪儿来啊
我不问
你们到哪儿去啊
我不问
开凿栈道的老石匠
宁武关年轻的士兵
灵魂回家了
骨头在等
等来一个悬空寺
悬着悬念
悬着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