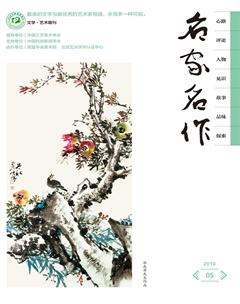《青春之歌》:作为政治修辞的情爱叙事
狄丰琳
[摘 要] 《青春之歌》虽以情爱叙事贯穿全篇,但在“十七年”的特殊时代语境下,非但没有受到太多指责,反而跻身红色经典行列。究其原因在于,围绕林道静展开的情爱叙事,早已超越两性范畴,而依据意识形态的演进逻辑构筑起繁复庞杂的政治寓言。情爱的角逐,事实上暗示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方向以及革命政权的最终归属。
[关 键 词]《青春之歌》; 政治修辞; 情爱叙事;意识形态
1958年初,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短短的一年半,作品销量就达130万册,成为仅次于《林海雪原》的畅销书。更值得骄傲的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文艺献礼,《青春之歌》在1959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由著名导演崔嵬执导,产生巨大而持久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先后以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出现的《青春之歌》相当有力地推动了“十七年”期间的社会主义文艺建设,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数代人的精神形态和价值指向,堪称红色经典中的“经典”。
一、幸免于难的情爱叙事
与同时代其他经典作品相比,《青春之歌》有不少独异之处。首先是作家杨沫的女性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女性解放成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命题,女性广泛地参与到了劳动生产、政治活动中来,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在文艺领域,女作家的比例并不算高。究其原因,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知识分子少,受教育程度低有关,更与女性在过往历史中长期缺乏文化教育、艺术训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是阳刚雄健的,主流文学亦多是关乎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至于细腻温婉、偏重日常生活和自我情感的女性书写,则在审美层面受到了严格限制。在“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口号的感召下,女性不断追求着外在于自我生命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目标,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性别意识已遭严重磨蚀。某种意义上,只有背离自己的性别基点,自觉借用男性的喉管发声,女性方可获准进入男权意识主宰社会主流的文学场域。但即使是在如此严格的条件限定下,性别意识看似非常鲜明的《青春之歌》还是得到了革命话语的认可,并且迅速跻身经典行列,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从故事情节来看,《青春之歌》属于少女成长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三位男性的情感纠葛。在爱情稀缺、情爱叙事几成禁忌的时代里,这是很抢眼,也很扎眼的。因为立足个体生命的两性情爱常常与群体性的政治革命发生抵触,是否留恋于个人的情爱生活,就成了区别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重要标识。理想的革命者应当毅然决然地斩断儿女情长,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所以在革命叙事中掺入爱情书写,哪怕仅仅是一些片段、细节,也会承担很大的风险。譬如《林海雪原》,其在以少剑波与卫生员白茹的情感火花吸引大批读者的同时,也招来了诸多责难。“为什么他这样偏爱白茹?因为在他们的爱情中更加突出了少剑波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灵魂。白茹在‘林海雪原中的作用,就是为了给少剑波个人英雄主义锦上添花。”照此来看,以情爱贯穿全篇的《青春之歌》就更难逃劫难了。
确实,出版前后及改编电影过程中,《青春之歌》遭遇了不少坎坷,批评的声音时有出现。1959年4月,作品问世不久,就有署名“刘茵”的文章指责,卢嘉川在宣传革命思想、从事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竟然对林道静这位美丽、热情、活泼的有夫之妇产生感情,这是有违道德伦理的,是不利于革命者英雄形象塑造的;与此同时,林道静也常常沉浸在个人的情感世界中,而没有倾心于党的伟大事业,这不禁让人怀疑她参加革命的真实动机,是出于马克思主义信仰,还是对卢嘉川的个人的爱。
只是让人深感意外的是,在众多批评者中,如刘茵那样着力攻击作品情爱叙事的并不多见。更多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林道静的政治身份,即社会主义文学是否可以书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就如欧阳凡海,作为《青春之歌》的审稿人之一,他认为作品最致命的是主人公身份不符合工农兵文学的叙事规范,“以小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为书中最主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而对其中的恋爱描写,仅是表示无须“花费很多心血来布置”。欧阳凡海在文学批评上有着极为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是“左联”老作家,1937年到延安后曾担任鲁艺文学研究室主任,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別是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常熟悉。但在面对《青春之歌》的男女情爱时,他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青春之歌》的情爱叙事并没有太过“犯忌”,甚或还与革命主题保持着某种同质同构的关系。
二、情爱叙事中的政治寓言
与家庭出身有直接关联,或者说血统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标识。主人公林道静从一开始就具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双重属性。其父林伯唐是典型的官僚地主,城里有公馆、乡下有田产,还挂着大学校长、慈幼院院长的名号,其母秀妮则是佃农家的女儿,在委身林家后备受虐待,年纪轻轻就被逼死。在这个冷酷残暴的剥削阶级家庭里,林道静既没有享受荣华富贵,也没有得到父母亲人的关爱,反倒受尽屈辱压迫,打小就与穷苦人家的野孩子混杂在一起。哪怕此后读书上学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继母徐凤英还是把她当作一棵摇钱树,要许配给特务头子胡梦安。
受限于特殊的家庭环境、教育经历与命运遭际,林道静在政治道路的选择上困难重重。一方面因于家庭中的身份与地位,她同情弱者、关心底层民众,有着反封建、反压迫的革命要求,但另一方面又受家庭教养、新式教育的影响,有狂热、幻想、软弱、个人英雄主义等资产阶级的精神气质。依据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论述,知识分子应当划归为小资产阶级,介于剥削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他们既对社会现实不满,有一些革命的意愿,但又习惯安于现状,不敢贸然参加革命,经常处在迷茫、徘徊、踌躇不前的状态。这种摇摆不定的“中间状态”,使知识分子成为各方力量都努力争取的对象,“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如何通过理论教育和斗争实践,将知识分子推入到革命轨道,促其在政治上、思想上、情感上实现彻底的转变,是无产阶级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而《青春之歌》的情爱叙事就是在这一政治主题下展开的。从余永泽到卢嘉川,再到江华,林道静每一次的情爱选择都预示着她蜕变求新后的政治转向。
首先出场的是余永泽。林道静离家出走后,在北戴河频遭挫折,以致要蹈海自尽。回乡度假的北大学生余永泽这时英雄救美,两人自此相识相恋。与余永泽结合,林道静绝不仅仅是为报救命之恩。传统的道德伦理并不足以左右她的情爱,真正打动她的,还是余永澤的博学多才、浪漫多情和对女性解放的支持。这对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青年男女,拥有共同的理想,那就是争取个人的自由和家庭幸福。如果置放在“五四”时代,这样的追求会有相当的进步意义,是破除封建樊篱、反抗社会压迫的利器;但及至20世纪30年代,伴随民族危机的加剧,其所立足的个体本位已与阶级斗争、民族救亡发生严重抵触。投射在家庭生活中,林道静渐渐察觉到了余永泽自私平庸的一面,对他整日埋首故纸堆,对国家大事、民众疾苦不闻不问的做法深表不满;与此同时,她也努力走出家庭,要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寻找生命的激情。但林道静并没有因为情感上的分裂、思想上的冲突而有离开余永泽的念头,直到革命者卢嘉川进入她的生活。
在一次进步青年聚会上,林道静结识了北大学生运动领袖卢嘉川,从他那儿明白了没有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就没有个人解放的道理。经卢嘉川推荐,林道静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她的青春激情被宏伟瑰丽的共产主义理想点燃,她已经意识到自己与余永泽的分歧实际上是政治立场的根本冲突。伴随政治信仰的改变,卢嘉川逐渐占据了林道静的情感世界。虽然双方始终没有明确关系,但事实上已成为精神上的恋人。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对于这样一位优秀的“导师加恋人”,作品为何要给他安排死亡结局呢?作为着力塑造的中心人物之一,卢嘉川是马克思主义的虔诚信徒,在革命思想传播中又发挥了积极作用,林道静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才转向革命正途的。他的提前退场,似乎有违革命叙事的惯常模式。一般来讲,为突显正义必胜的历史方向,展现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历程,作品要尽可能避免主要英雄人物的牺牲。虽历经磨难,他还是要九死一生,以见证那插上敌人城头的红旗。但如结合意识形态的演进逻辑,我们却会发现,卢嘉川的退场是必然的。唯有如此,林道静才有机会重新选择爱情,才可能将情感空间留给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方向的江华同志。
三、政治与情爱的共同归宿
卢嘉川牺牲后,林道静在革命斗争中更多接受江华的指导。江华也是北京大学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后又担任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但不同于卢嘉川的革命知识分子身份,江华工人出身,在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和学联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马克思主义在他那里已不再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与卢嘉川相比,江华显然代表着革命发展的更高阶段,但在感情上他还是很难接近林道静。林道静长久沉浸在对卢嘉川的怀想中,不愿再去接受其他人。这给江华造成很大压力。卢嘉川虽已离世,但在林道静心中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一个比余永泽强大百倍的“情敌”。唯有击倒他,才有可能俘获林道静的爱情。江华积极开展了自己的计划。在一次谈话中,他接连向林道静提问,“你知道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吗?”“你认为中国的革命将要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发展下去呢?”虽然平日里读书不少,还学习了辩证三原则、资本主义范畴、共产主义理想等理论知识,但面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林道静紧张局促,无力应答。林道静的尴尬,完全可以视作江华对卢嘉川的成功挑战。在一系列以“中国革命”为起头的问题追问下,林道静和他的精神导师卢嘉川暴露了自己的致命软肋:理论与实践脱节,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革命斗争经验严重匮乏。以后的日子里,江华时常向林道静抛出类似的问题,然后再和她一道分析解决。经过江华的“补课”,林道静获得了新一轮的精神成长,也逐渐走出了卢嘉川的巨大投影。她开始发自肺腑地认同、倾慕江华这位成熟的革命领导者。
《青春之歌》在细腻的情爱叙事背后隐伏着巨大的政治寓言。主人公林道静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女性个体,不如说是抽象的政治象征符号。在作品起始,当她一身素衣出现在拥挤嘈杂的火车车厢时,就已经成为围观者的欲望对象或试图捕获的猎物。白色的衣装和随身携带的雅致乐器,都极具象征性地显露了林道静涉世不深、思想单纯、易为人染指的特性。围绕在她身边的男性,就是各方政治势力的代表。“骑士兼诗人”的余永泽,走上了资产阶级道路。他追随胡适,一心向学,希望通过个人奋斗而在学术道路上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导师兼恋人”的卢嘉川则是革命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启蒙者。他有充沛的革命热情、虔诚的政治信仰、良好的理论素养,但知识分子身份还是严重阻隔了他与广大民众的血肉联系。即便曾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完成基本的理论传播、结束自己的阶段性使命后,革命知识分子还是要将领导权交付于更富斗争经验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亦即真正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江华。为强化这一意识形态逻辑,林道静最终将自己完全托付给了江华,爱情选择与政治归宿得到了完美统一。在江华的教导下,林道静对革命的认知实现了从启蒙到实践的飞跃,进而完成了从知识分子到革命者的身份蜕变,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帮助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完成自我改造,成为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这正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行进方式。以林道静为中心展开的情爱叙事,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两性范畴,而在政治层面上标示着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方向以及领导权的最终归属。
参考文献:
[1]田禾.女英雄还是装饰品[N].北京日报,1961-06-10.
[2]欧阳凡海.对于《青春之歌》的初稿意见[J].新文学史料,2007(1).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6]张闻天.张闻天文集(第3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