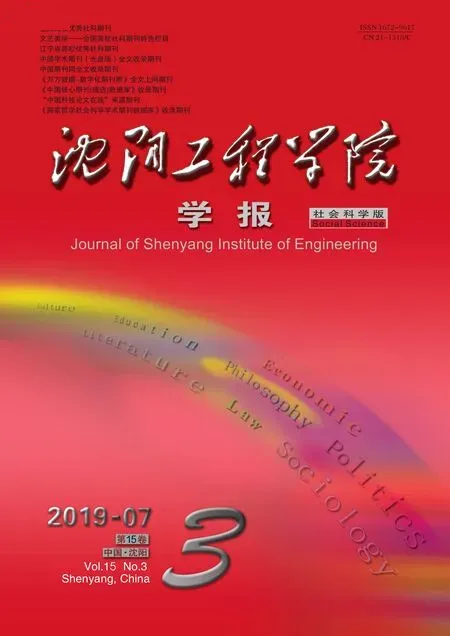《古诗十九首》中动物意象的情感意蕴
杨红丽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363000)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诗歌长河中最早成熟的文人五言诗,代表了汉代文人诗的最高成就,最早见于梁代萧统编撰的《文选》。自其诞生之日起,“十九首”就以其情感之真,艺术之美而获历代文人骚客的赞誉。钟嵘《诗品》卷上称它:“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称它是“五言之冠冕”。意象是诗人表情达意的寄托,《古诗十九首》享誉如此之高,其充满艺术感染力的意象功不可没。早在明代,学者胡应麟就已经意识到《古诗十九首》意象之精妙,他在《诗薮》中曰:“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1]25时代的不幸加之人生的无常,文人选择用内蕴丰富的意象来表达复杂而深刻的生命情感。正如清人陈祚明所述:“‘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2]81《古诗十九首》中的动物意象丰富独特,体现了当时文人的情感意蕴和生命态度。
一、《古诗十九首》中的动物种类
《古诗十九首》中所出现的动物种类,黄文熙《论〈古诗十九首〉对〈诗〉、〈骚〉意象的因革》一文中统计为9 种。笔者则认为《古诗十九首》中出现的动物有11 种,按动物类别可分为马、鸟和昆虫3类,这3 类11 种动物分布于《古诗十九首》中的7 篇13处,列表统计如下:

表1 《古诗十九首》中出现的动物列表
诗中出现了马、鸟、昆虫三类动物,马:胡马、驽马;鸟:越鸟、双鸿鹄、玄鸟、双飞燕、晨风、鸳鸯;昆虫:蟋蟀(促织)、秋蝉、蝼蛄。其中马2 种,鸟6 种,昆虫3种,共3类11种。
《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末,在当时,《诗经》被宗为经,《楚辞》是最流行的诗歌,诗人作诗多受这两组作品的影响。《古诗十九首》中的动物来源及意蕴对《诗经》和《楚辞》均有明显的继承,但又因注入了当时文人的生命情感而大放异彩。
二、《古诗十九首》中动物意象的情感意蕴
即事感怀,是中国古代诗歌最基本的题材之一。即因为一件事而引发诗人的感慨,这件事可以是历史中的大事,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可以是心事,往往表现为思亲、怀乡、念友等[3]13。《古诗十九首》产生于衰败没落之世,政局动荡,外戚与宦官争权,文人仕进无门,情感郁积又无处申诉,便把内心的苦闷倾注于文字。《十九首》中出现了11种动物意象,这11 种意象根据其情感的特征又可分为四类:一是表现诗人对生命短促认识的“蟋蟀”“秋蝉”“蝼蛄”;二是表达乱离间理想难即的“晨风”“驽马”;三是表现夫妻之间生别离相思悱恻的“鸳鸯”“胡马”“越鸟”;四是反映诗人于落败之世渴求知音的“鸿鹄”“玄鸟”“双飞燕”。
1.时序压迫之悲
时代悲剧与命运的不幸,让诗人唱出对生命时序充满压迫感的悲歌。“蟋蟀”“秋蝉”“蝼蛄”多为生命短促的小虫:“蟪蛄”寒蝉也,古人有“蟪蛄不知春秋”之说;蟋蟀成虫的寿命大概也只有两三个月;“蝼蛄”,昼伏夜出,于夜晚鸣叫,闻其声,易让人产生一日的光阴将尽的紧迫感。诗人抓住这些昆虫的生命特征,表达了人生苦短的悲叹。
《十九首》中的“蟋蟀”与“促织”实为同一意象。“蟋蟀”意象见于“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明月皎夜光》)和“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东城高且长》)两篇。“促织”是蟋蟀的别名,一作“趣织”。“趣”是“促”的古字。《春秋考异邮》曰:“立秋趣织鸣,女功急趣之。”宋均曰:“立秋女功急,故趣之。”[4]633在古代,人民按照季节的变化进行劳作,蟋蟀的鸣声标志着秋天的到来,暗示妇女们制作寒衣的时节已到,所以民间把这个虫叫做“促织”。至于《明月皎夜光》篇用的“促织”而非“蟋蟀”。朱自清给出的说法是:“也许含有别人忙于工作,自己却偃蹇无成的意思。”[5]65《诗经·豳风·七月》中第五章写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宇”,即屋檐。蟋蟀本居土穴,随着气候的变化由田野迁入室内。“东壁”向阳,蟋蟀就暖,“鸣东壁”,也就是“在宇”的意思,“促织鸣东壁”表明气候已经渐渐进入深秋,其与本诗随后出现的“白露”“秋蝉”“玄鸟”意象相呼应,均含时序变迁之义,但具体情感所指又有微妙的变化。“白露”无生命特征,单纯给人时光流逝之感,“树间秋蝉”的鸣声有生机没落之象,“玄鸟”于“秋蝉鸣树”之际往南飞,驱寒就暖,会令诗人联想到友人飞黄腾达之后“弃我如遗迹”的现实处境。意象的错综,统一于诗人感于时序变化之悲、友人功成名就之后视己如飘尘的世态炎凉的情感中,达到了情与景水乳浑融的境界。
《东城高且长》篇中的“蟋蟀伤局促”,承“岁暮一何速”生发,又《唐风·蟋蟀》共三章,每一章都是以“蟋蟀在堂”起兴,通过“岁聿其莫”“岁聿其逝”“役车其休”的变化来发出光阴易逝的感叹。“局促”,不开展也,与“蟋蟀在堂”义同。深秋渐寒,蟋蟀就暖,待到“蟋蟀在堂”的时节,蟋蟀的生命也就慢慢接近尾声。所以“蟋蟀伤局促”隐喻了作者对人生苦短的悲叹,为下文劝勉世人及时行乐埋下伏笔。《古诗十九首》中的“蟋蟀”意象与《诗经》一脉相承,其叫声急促且多鸣于夜深人静时,出门在外的游子尤能从中读出孤寂、悲怆的意味。后代诗人内心有郁疾时,或以“蟋蟀”起兴,或借“蟋蟀”抒哀情。如唐戍昱的《客堂秋夕》:“虫声竟夜引乡泪,蟋蟀何自知人(一作知人自)愁。”
“秋蝉”,生命周期短,鸣声凄长而厉。以“秋蝉”意象入诗,最早见于《古诗十九首》:中“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秋蝉”的鸣叫暗示又是一年秋风起,但诗人依然不知何去何从,看到昔日好友振翅高飞而弃自己如尘埃,顿时看破人间世态,苍凉感油然而生。后世诗歌“秋蝉”意象的文化意蕴也多沿用于此,如唐张乔的《蝉》:“先秋蝉一悲,长是客行时。”又唐张籍的《思远人》:“杨柳别离处,秋蝉今复鸣。”诗中的“秋蝉”意象总给人淡淡忧愁之感。
“蝼蛄”,夜喜就灯光飞鸣,声如蚯蚓。由于其长得丑陋,历代文人多以之喻力量微弱或地位低微、无足轻重的人。司马迁在《史记》中言:“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6]2183“蝼蛄”这一意象在《十九首》见于《凛凛岁云暮》篇,“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本篇通过对虚幻梦境的描述,表达思妇思君不得见之苦。诗人先从冬天凄凉的景物落笔,抓住“蝼蛄”夜晚鸣叫的习性,以其“悲鸣”起兴,奠定了全诗惆怅不得排解的沉郁基调,为下文由相思入梦到梦醒不见君恍惚悲恸情感的层层展开做了铺垫。情动于其中,定会托于一物,《古诗十九首》作者以此意象入诗,与他们出身低微,时局动乱及复杂的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2.理想难即之痛
因受儒学熏陶,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一直以来修身齐家的信念与汲汲于功名的人生追求是文人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激化,到了东汉末年,时局的动荡与人们生命意识的觉醒,虚伪矫饰已失去条件,士人开始大胆表达自己及时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愿望。《古诗十九首》中的“何不策高足,先据要道津”“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等均表达了诗人及时建功的思想。但囿于时代的原因,《古诗十九首》中文人的寻梦之路充满了清影难即的艰辛与无奈。于是他们借“晨风”“驽马”意象表达人生理想难以实现的痛苦。
“晨风”亦作“鷐风”,鸟名,即鹯。“晨风”作为意象入诗最早见于《诗经·秦风·晨风》“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晨风”是健飞的鸟,“钦钦”忧而不忘貌。晨风这种健飞的鸟在秋高气爽正好高飞远举的时节却被滞留于茂密的丛林,当然不免于“忧心钦钦”。“晨风”意象在《古诗十九首》中出现了两次,或直言衰败之世理想实现路途的艰辛,如《东城高且长》篇:“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诗人从洛阳的繁华大都东城落笔,但是诗人并没有顺接洛阳繁华大气象畅抒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相反,诗人笔锋一转,看到的却是郊外“回风动地”的萧条,可见其内心对本欲大展雄才的洛阳感到万分的失望。或以思妇的视角,通过描写闺中少妇碍于各种现实因素,终不得实现与丈夫团聚的理想的悲痛心情来寄寓诗人自身实现理想过程的孤独、失落以及无可奈何。如《凛凛岁云暮》篇“亮无晨风翼,焉能凌空飞”,此诗中的“晨风”意象与《东城高且长》篇意同,表健飞的鸟。诗歌由寒冷时节蝼蛄的悲鸣起兴,思妇开始担心外出的游子没有衣服御寒,紧接着自怜自叹,埋怨游子久久不归。由于思念过甚,游子于漫漫长夜中进入了怀人的梦,良人念旧情,“携手同车归”,梦很美,也很短,醒来后的现实落差,让这位处于深闺的女子想要“飞”到良人的身边。但无奈,自己并没有“晨风翼”,所以只能“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晨风翼”,即健飞的羽翼,是思妇借以飞到心上人身边的一种载体,但可惜,或囿于自身或缘于现实,无论是诗人还是闺中思妇他们都没有这可以实现理想的羽翼。梦境难即,幻灭感油然而生。
“驽马”指“迟钝的马”。《周礼·夏官司马》:“马量三物,一曰戎马,二曰田马,三曰驽马。”[7]1149又《周礼·夏官司马》:“圉人,良马匹一人,驽马丽一人。”[7]1093由句中“驽马”与“良马”相对亦可知“驽马”应为一种劣马,“驽马”意象出现在《青青陵上柏》篇“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作者先以“陵上柏”永恒不变之色、“磵中石”永恒不变之形与人生的短促作比,发出人不如物的感慨,劝勉世人及时行乐。纵然知道所驭之马是驽钝的,但仍策其游戏繁华大都,与下文“冠带自相索”形成对比,深切地感受到诗人“聊厚不为薄”式聊以自慰的无奈。隐约流露了作者感于时势维艰、理想难即的苦闷。
3.相思别离之苦
相思别离可谓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个母题,其源流可以追溯到《诗经》,《关雎》篇描述了一男子对佳人由春心萌动、求之不得到终成眷属的过程;《蒹葭》篇则描述了男子追求佳人“道阻且长”的曲折过程。《古诗十九首》中表相思之苦的意象有“鸳鸯”“胡马”“越鸟”。
“鸳鸯”,鸟名,似野鸭,体形较小,栖息于内陆湖泊和溪流边,旧传雌雄偶居不离,古称“匹鸟”(毛传:鸳鸯,匹鸟也)。故后人多以鸳鸯来比喻成双配对的事物,或喻夫妻,如汉司马相如《琴歌》之一:“室迩人遐独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8]104或象征吉祥美好,如《诗经·小雅·鸳鸯》篇中:“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诗人以鸳鸯起兴,借用鸳鸯具有象征美好爱情的意蕴,用以表达对他人的美好祝愿。此外,“鸳鸯”亦或单纯指饰物上的图案,暗喻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古诗十九首》中《客从远方来》篇的“鸳鸯”意象正沿此义,“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中鸳鸯的意象表面上是指饰物上的图案,但细究其细节,在乱离的时代,游子在相去万里的情况下依然“故人心尚尔”遣客送端绮,给远在他方的妻子送去宽慰。思妇以游子送回来的布匹裁作有鸳鸯图案“合欢被”,流露了思妇思君的细腻情思,表明二人纵然在动乱的年代依然忠于爱情。虽然诗中没有提及分离的原因但其背后还是能隐约感受到时代动荡带来的忧伤。后人对“鸳鸯”意象的运用一般也是由鸳鸯成双成对的栖息习惯生发,或喻忠贞美好的爱情,或喻志同道合的兄弟,如唐代温庭筠《偶游》:“與君便是鸳鸯侶,休向人间觅往还。”自此以后,“鸳鸯”意象便成为中国古典诗词领域用之不竭的一寸芳土。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胡马”总是与“越鸟”并举,表达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但是在《古诗十九首》中诗人主要用其表达思妇与丈夫生别离的相思之痛。游子以“胡马”和“越鸟”为喻体,慨叹不能忘记故乡的思想可追溯到屈原的《九章·哀邶》:“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守丘。”《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篇“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中“胡马”即北方的马,“越鸟”即来自南方的鸟,“依北风”与“巢南枝”是动物恋故土的本能表现,思妇借此与游子作比,言动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由此而引出系列情思。诗歌在开头就点明生别离的主题,而且别离的空间距离是渐行渐远,无限向远处延伸的。会面的困难又是如此的困难重重,思妇继而希望游子能与“胡马”和“越鸟”一样具有恋故土的本能早日归家,但是复杂而残酷的现实始终使游子久久不归。于是思妇开始劝勉自己:“日夜的念想只会催人老去,思恋的人也不会就此回来,且转眼间年岁已晚。或许他日还能相见,还是好好吃饭,保重身体为好。”相思之情极为缠绵,纵使知道游子归家的现实阻力很大,此生相见的机会很渺茫,但是诗中主人公依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心怀期望,寄希望于未来。
4.知音难觅之哀
东汉末年是一个底层知识分子希望幻灭的时代,无论是仕途还是精神层面,他们都无比希望得到他人的理解与赏识,以此来聊慰内心的焦虑与寂寞。《古诗十九首》中的诗人借“鸿鹄”“玄鸟”“双飞燕”三个动物意象,寄托了诗人希望与知音惺惺相惜冲破黑暗现实的愿望。
“鸿鹄”,因善高飞,常比喻志向远大的人。因此有词曰“鸿鹄之志”。《吕氏春秋·士容》:“夫骥骜之气,鸿鹄之志,有谕乎人心者诚也。”[9]328又《管子·戒》:“今夫鸿鹄,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时。”[10]95《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在运用“鸿鹄”这一意象时,“不失其时”的原始意义是蕴含其中的。《古诗十九首》的文人多生不逢时,满腹经纶而无人赏识。《西北有高楼》篇作者用“鸿鹄”这一意象表达了知音难觅的痛苦,作者听曲感心,他人悠扬的曲音与自己抑郁于心的情感互通,由感慨“失其时”而产生“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携同知音冲破黑暗而获自由的美好遐想。所以诗中“鸿鹄”意象当是喻楼上的弹者与伫立于楼下的聆听者,诗人发出“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的呼唤,既包含了诗人对知音的渴求又寄寓了诗人冲破黑暗现实、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古诗十九首》中的“玄鸟”与“双飞燕”是同一种意象,但“玄鸟”侧重表南飞之义,暗表时序。“双飞燕”侧重“双”字,有男女相思之义。“玄鸟”最早见于《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郑玄笺:“玄鸟,鳦也。”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禽二·燕》:“燕子,篆文象形。乙者,其鸣自呼也。玄,其色也。”[11]1094“玄鸟”见于《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篇中:“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玄鸟”是候鸟,仲秋时节会飞往南方。将“秋蝉”与“玄鸟”对举,一方面表明时节变化,另一方面以“玄鸟”的去寒就暖暗示昔日友人离自己而去的炎凉世态。“双飞燕”指雌雄并飞的两只燕子,《东城高且长》篇中的“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与《西北有高楼》篇的“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义近,均为诗人听曲感心,希望于乱世中能与知音共筑爱巢以摆脱黑暗的现实。
三、动物情感意蕴中士人的人生态度
《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东汉初,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以察举、征辟的方式招揽文士,这种制度为德才兼备的文士开辟了建功立业的阳光大道。但到了东汉后期,政治制度随朝代的衰落而腐化,士族豪门把持官场人员的任用,以察举、征辟来选拔人才的初衷成为泡影,正如汉桓帝时《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12]295知识分子开始被边缘化,加之两次的“党锢之祸”,大批文士被杀害,使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仕途的不济与人生的无常。陆时雍说:“情动于中,郁勃莫己,而势又不能自达,故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13]1411-1431时序变换的压迫促使文人选择具生命式微感的“蟋蟀、秋蝉、蝼蛄”入诗,“秋蝉鸣树间”暗示时序已晚,表达自己仍无人赏识的焦虑;“蟋蟀伤局促”和“蝼蛄夕悲鸣”字里行间均流露出诗人对时光流逝“徒伤悲”的无奈。这三种动物实为文人生命的自拟,他们以两种不同人生态度来应对生命的无常,他们或及时行乐:“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或希冀于微黯之世建功立业:“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但是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刘毅《清罢中正除九品疏》)的时代,扬名后世并非易事,所以他们就把理想难即的痛苦寄寓于“郁于北林”的“晨风”和满腹无奈的“驽马”。“晨风怀苦心”“亮无晨风翼”“驱车策驽马”均表达了士不遇的悲痛。生于乱离而不甘沉沦,追求理想而无人赏识,《古诗十九首》的文人是焦虑且孤独的。理想的落空使他们通过渴求知音和恋慕故土以求得内心的依靠感与安全感。“鸳鸯”“越鸟”“胡马”成为士人表达相思别离之苦的意象。“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均表达了诗人希望于微黯之世携同知音摆脱黑暗的社会现实的美好幻想。
面对无常的人生,及时行乐、同时梦想建功立业是《古诗十九首》文人徘徊在现实与理想的人生态度。时序压迫与仕途不济并没有使文人消极堕落,他们在认清残酷的现实之后依然选择热爱生活,纵使理想飘渺,他们也会于携同知音共筑良巢的美好幻想中得到宽慰。文人把至真至醇的生命情感融入极具生命活力的动物意象,铸造了中国诗歌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