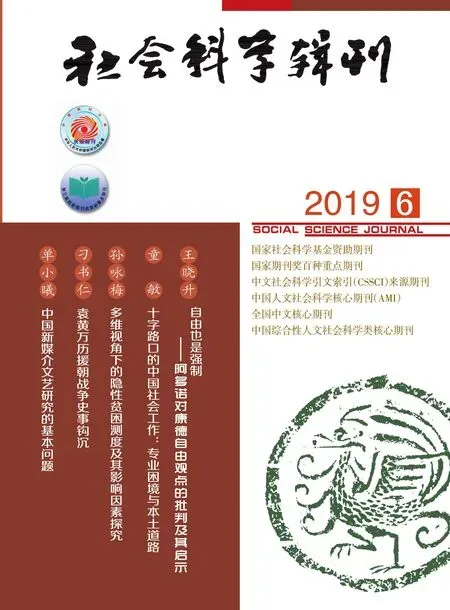北宋黄河、汴河基层管理机构及其治水实践
——兼论缘河地方政府的协同管理机制
王 战 扬
北宋中央水政职掌机构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宋初水政职权由三司修造案掌管,后由三司河渠司继之,嘉祐三年(1058〕都水监建立以后,河渠司遭到废除,水政权力独立于三司之外;熙宁年间,司农寺与都水监协同治理农田水利;元丰改制以后,水部开始同都水监共同职掌水政。因此在加强辨识北宋不同时期中央水政职掌机构演变情况的同时,还应深入考究其基层管理机构的置废、职掌及实践。以往的成果侧重于对河患治理及漕运经济的讨论,而对与之相关的基层河道管理机构的研究较为薄弱。笔者希冀通过对北宋黄河、汴河基层河道管理机构的考察,能够加深对北宋基层水政运行机制及水利社会问题的认识。
一、北宋基层河道管理机构置废考
北宋基层河道管理机构隶属于中央水政管理机构,其级别最高者是外都水监,外监之下设修河司,修河司之下设河埽司,埽所隶属于河埽司,埽所之下又设铺屋,形成层级的隶属关系和管理组织。汴河沿岸则设堤岸司与导洛通汴司。北宋基层河道管理机构的置废受朝中政局影响颇深,这也成为北宋王朝在河患治理中走向被动的重要因素。
(一〕黄河沿岸外都水监、修河司、河埽司、埽所、铺屋的置废
北宋中期黄河河患日趋严峻,嘉祐三年(1058〕十一月二十二日,“诏置都水监,罢三司河渠司”〔1〕。宋廷在中央建立了由都水监独掌水政职权的管理机构,且从其名称来看,水政权力已不再依附于三司。外都水监是隶属于中央水政部门都水监的基层常驻机构:“轮遣丞一人出外治河埽之事,或一岁再岁而罢,其间有谙知水政,或至三年者。置局于澶州,号曰外监。”〔2〕由史料可知,外都水监的治所在澶州(今河南濮阳),为加强治理河患,朝廷轮番差遣都水监丞外出掌管黄河河埽之事,其任职一般为一年或两年,对于谙熟水利的官员,有任职三年的情况。事实上,文献记载中对外都水监的最初设置时间并不明确。笔者认为外都水监应是在中央都水监丞被频繁差遣到基层处置河患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最早的相关史料记载见于熙宁四年(1071),程昉成为首任“外都水监丞”〔3〕。元丰改制期间,又置“南、北外都水丞各一人”〔4〕,“南北外都水丞依旧澶州置司”〔5〕。元祐年间,南、北外都水监受朝廷政局及黄河河患因素的影响屡置屡罢:
五年,诏南、北外都水丞并以三年为任。七年,方议回河东流,乃诏河北、京西漕臣及开封府界提点,各兼南、北外都水事;绍圣元年罢。元符三年,诏罢北外都水丞,以河事委之漕臣;三年,复置。重和元年,工部尚书王诏言,乞选差曾任水官谙练者为南、北两外丞,从之。宣和三年,诏罢南、北外都水丞司,依元丰法,通差文武官一员。……绍兴九年,复置南、北外都水丞各一员,南丞于应天府,北丞于东京置司。十年,诏都水事归于工部,不复置官。〔6〕
哲宗朝是继仁宗朝以后黄河泛滥的又一严重时期,关于黄河东流或改道北流的问题在朝中形成河议政局。为加强治理黄河河患,朝廷规定南、北外都水丞三年为一任,改变了以往一年或两年的任期标准,但是受朝廷政局影响,保守派势力反对回河,主张黄河北流,变法派势力主张黄河回故道东流。进入南宋以后,绍兴九年(1139),宋廷又置南、北外都水丞,其治所分别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和东京(今河南开封),次年工部则取代了都水监,外监也被一并废除。
比外都水监低一级的河道管理机构是修河司,全称“都大提举修河司”,简称“都大司”,先后隶属于河渠司和都水监。关于修河司的记载,最早见于嘉祐元年(1056〕〔7〕,河渠司罢除之后,隶属于都水监,是地方基层修河机构。哲宗元祐年间,与外监一样,修河司也屡屡置废不定,有时仅相隔数月。元祐五年(1090〕十月二日,因黄河回河失败,修河司被彻底废除。〔8〕修河司设置在黄河沿岸,“须是已有兴修去处,始立提举修河司总领其事”〔9〕。神宗元丰三年(1080〕八月,黄河南岸分别在“怀、卫、西京、河阴、酸枣、白马”六处设都大提举修河司;黄河北岸分别在“澶、濮、金堤东流南、北两岸”四处设都大提举修河司,共十处治所。〔10〕修河司有一支庞大的队伍组织,有“官吏几百余人,诸州催促物料使臣四五十员”〔11〕,负责黄河的修治及管理等任务,其下设河埽司。
宋初已有河埽之建置,如淳化二年(991〕三月,诏:“长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经度行视河堤,勿致坏隳,违者当寘于法。”〔12〕可见,宋太宗淳化年间已建置有河埽,设有主埽使臣,负责巡视河堤,维护河堤安全,并制有法律,管理严格。宋代河埽司的正称见于哲宗元祐五年(1090〕十一月。〔13〕关于河埽司的官员组成及选官之制记载如下:河埽司有“大小使臣一百六十余员,并委监丞已上奏举,其所举未必习知水事”〔14〕。针对这一问题,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十一日,知都水监主簿公事李士良提出:“欲乞今后河埽罢举官之制,并委审官西院、三班院选差。”〔15〕河埽司在嘉祐三年(1058〕之后隶属于都水监。〔16〕关于河埽司的职掌,概括来讲主要有三点:第一,巡视河堤,保证安全。〔17〕该职能上文已经论及,此不赘述。第二,筹备埽料,修治河埽。如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自曹村决溢后,诸埽物料遂无生计准备,乞支见钱二十万缗,趁时市稍草封桩,如来年河埽无事,自可兑充次年”〔18〕。第三,合调兵夫,指挥工役。如元祐七年(1092〕八月,“所有本路沟河夫数,并于管下以远州县均差趱那,近里州县夫应副河埽役使”〔19〕。又如元符二年(1099〕,“请自今河埽岁调春夫,并依旧条差拨正夫赴役”〔20〕。以上表明,河埽司是黄河河道修治工程的重要管理机构,治河劳役的派遣由其负责。
北宋朝廷在黄河中下游沿岸建置有大量的水利工程——埽,埽皆有具体的名称,大多以河道所经之乡村名作为埽名,一地两埽者称上下埽,多埽者常以第一第二第三等顺序排列。如元祐五年(1090),北京(今河北大名〕留守司上奏请求“于内黄第一埽第三铺地分荒字号坊内,修打遮栏槐花村一带披摊出岸漫水小堰一道,至阚村物料场西佥合”〔21〕。
在河埽处设置驻所,即埽所,有主埽使臣驻扎管理,其“差出埽兵”〔22〕负责日常埽岸的巡察维护。从史料中亦可以得知,每个埽所之下又设有铺屋,形成了系统的层级管理模式,是河道管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的表现。〔23〕需要指出的是,北宋在汴河虽无有埽所的建置,但却有铺的设置,且与黄河沿岸相比更为灵活,皆随水情需要临时设置,水退或留或撤。〔24〕再如天圣四年(1026)六月,诏:“凡汴水涨一丈,即命殿前马军司禁卒缘岸列铺巡护,以防决溢,及五昼夜即赐以缗钱。”〔25〕黄河埽所负责巡察的埽兵一般为厢兵,而巡护汴河的铺屋之兵一般为禁兵,二者的差异体现汴河铺屋的不常设性,常在水情危急时刻设铺救援。
(二〕汴河堤岸司及导洛通汴司的置废
关于汴河堤岸司的最早记载见于熙宁六年(1073〕十月戊戌〔26〕,说明其在此之前即已设置,但具体始设时间不详。元丰三年(1080〕五月甲申,导洛通汴工程完成以后,“诏改都大提举导洛通汴司为都提举汴河堤岸司”〔27〕。即朝廷将都大提举导洛通汴司废除,其职责归于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掌管。
很显然,此时其管辖的范围包括竣工后的导洛通汴工程。元丰八年(1085〕五月庚子,“诏提举汴河堤岸司隶都水监”〔28〕。此前朝廷一直“专置堤岸司”〔29〕管理汴河事宜,至此开始正式隶属于都水监。而朝廷对其在汴河的管理职责也有所缩减和限制。如元丰八年(1085〕九月乙未,“汴河堤岸司所管房廊、水磨、茶场”〔30〕,“并拨隶户部左曹”,“所有水磨、茶场,乞令左曹疾速措置经久利害以闻”〔31〕。此后汴河堤岸司专门管理汴河河道相关事宜为其主要职责。如绍圣四年(1097〕十二月壬寅,“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一丈五尺为堤面,官私不得侵占。承告侵占京城内堤岸者,检定送开封府,其赏钱乞先以杂收钱代支,却于犯人理还。京城内汴河堤岸人户,辄有侵占者,许人经都提举汴河堤岸司告”〔32〕。即随着汴京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汴河两岸市民侵堤问题日益凸显,朝廷对汴河堤面的宽度作出规定,堤面一丈五尺之内不准官私侵占,汴河堤岸司对其负有重要管理责任。其后汴河堤岸司经历短暂罢除后复置,元符元年(1098〕四月辛丑,工部言:“请复置都提举汴河堤岸司,乞应缘河事经画奏请等事。”〔33〕进入南宋以后与都水监一并被朝廷废除。
元丰二年(1079〕三月庚寅,“诏入内东头供奉官宋用臣都大提举导洛通汴”〔34〕,宋用臣即主政导洛通汴司。元丰二年(1079〕六月甲寅,提举导洛通汴司言:“清汴成,四月甲子起役,六月戊申毕工,凡四十五日。”〔35〕其后朝廷又下诏,令宋用臣继续留任导洛通汴司一年,继续管理导洛通汴的具体事宜:“诏应导洛通汴事,令宋用臣管勾一年,如洛水通快,委范子渊闭黄水口,其沿汴淤田,既非浊水,可并闭塞,并水东下,接应江、淮漕运。”〔36〕不久汴口的黄河水得以闭断,导洛通汴工程步入正常运转。元丰三年(1080)五月甲申,“诏改都大提举导洛通汴司为都提举汴河堤岸司”〔37〕。导洛通汴司被朝廷废除,汴河管理职责归属于堤岸司,统归中央水政部门都水监管辖。
二、北宋基层河道管理机构长官的治水实践
北宋基层河道管理机构的长官群体在河道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出身不尽相同,仕途各有差异,在基层担任水官期间的水利治绩,是值得考察的重要问题,经笔者统计,北宋共有20 名曾担任过基层河道管理机构长官的水官,见下表:

表1 北宋基层河道管理机构长官统计表
以上统计表中,仁宗时期的水官以李仲昌为代表,神宗时期以程昉、范子渊、宋用臣为代表,哲宗时期以吴安持、李伟、曾孝广、范子奇为代表,其余水官虽在黄河、汴河的治理中也各有地位,但并无特别的治水实践,因此笔者将以上述各时期代表性人物为中心展开探讨。
熙宁初,为河北屯田都监。河决枣强,酾二股河导之使东,为锯牙,下以竹落塞决口。加带御器械。河决商胡北流,与御河合为一。及二股东流,御河遂浅淀。昉以开浚功,迁宫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于洺州。兼外都水丞,诏相度兴修水利。河决大名第五埽,昉议塞之,因疏塘水溉深州田。又导葫芦河,自乐寿之东至沧州二百里。塞孟家口,开乾宁军直河,作桥于真定之中渡。又自卫州王供埽导沙河入御河,以广运路。累迁达州团练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46〕
程昉能得到朝廷重用,成为熙丰变法时期水利治理的风云人物,与神宗、王安石君臣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王安石言:“拔程昉于近习以治河,昉果可以治河,乃天锡陛下聪明旷绝也。”〔47〕程昉曾主持诸多水利工程的修治,权势显赫一时,“始,安石欲兴水利,骤用昉,昉挟安石势而慢韩琦,后安石觉其虚诞,亦疏之”〔48〕。时间一久,程昉的治水实效也受到御史盛陶等人的弹劾:
昉挟第五埽之功,专为己力。假朝廷威福,恐动州县。所开共城河,颇废人户水硙,久无成功。又议开沁河,因察访官按行,始知不便。漳河、滹沱之役,水占邢、洺、赵、深、祁五州之田,王广廉、孔嗣宗、钱勰、赵子几皆尝论奏其奸欺之状,则多置挞口,指决河所侵便为淤田。其事权之盛,则举官废吏,惟其所欲。悖慢豪横,则受圣旨者三,受提点刑狱司牒者十二,故有违拒。小人误当赏擢,骄暴自肆。愿遣官代还,仍行究治。〔49〕
从史料中可知,程昉假借权势,在治水实践中有诸多不当之举,但与前文李仲昌重酿河患相比,程昉仍具备一定的治水之才,其水利治绩值得肯定,后来程昉之所以受到朝廷疏远,在其为人,而不在其治水本身。程昉乃宦官出身,其参与河道治理反映出中央集权对基层水政权力的渗透与控制。
神宗时期另一位水官范子渊在黄河、汴河的治理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曾参与诸多水利工程的修治,尤其以利用浚川杷疏浚黄河、汴河最为朝廷所重视。熙宁七年(1074〕四月庚午,“子渊以事至京师,安石问子渊,浚川杷法甚善,何故顷言其不可用?子渊即对曰:‘此诚善法,但当时同官议不合耳。’ 安石大悦,遂专置浚川司,命子渊领之”〔50〕。可见范子渊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与信任,也与王安石的支持是息息相关的,起初范子渊利用浚川杷疏导淤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甲戌,范子渊被朝廷“赏开清水镇直河及用浚川杷导河之劳”〔51〕,又如熙宁十年(1077〕三月甲戌,都大提举疏浚黄河,范子渊言:“近闻朝廷以浚川杷于汴河试验有效,乞候七八月间水湍急,用疏导汴流。”〔52〕范子渊对浚川杷的利用,是对传统机械化清淤排污技术的一次重要尝试,但是时人却并不认为浚川杷对疏浚河道淤塞有显著的效果:“天下指笑以为儿戏,安石独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渊行其法。子渊奏用杷之功,水悉归故道,退出民田数万顷。诏大名核实,彦博言:‘河非杷可濬,虽甚愚之人,皆知无益。’”〔53〕此条史料反映出范子渊利用浚川杷疏浚河道实际上收效不佳,当河道中水深湍急时,浚川杷难以触底,水浅干涸时却又难以起到清淤排污的作用,因此被认为形同儿戏。与范子渊相比,宋用臣的治水实践相对实际很多,其主要治水功绩是“导洛通汴,凡大工役,悉董其事”〔54〕。元丰二年(1079〕三月庚寅,“诏入内东头供奉官宋用臣都大提举导洛通汴”〔55〕。元丰二年(1079〕六月甲寅,提举导洛通汴司言:“清汴成,四月甲子起役,六月戊申毕工,凡四十五日。自任村沙谷至河阴瓦亭子,并汜水关北通黄河接运河,长五十一里,河两岸为堤,总长一百三里,河所占官私地二十九顷。已引洛水入新口斗门、通流入汴,候水调勾,可塞汴口,乞徙汴口官吏、河清指挥于新开洛口。”〔56〕在导洛通汴以前,汴河主要引黄入汴作为水源补给,以保障漕运航道的畅通,但是因黄河水中含有大量泥沙,因此极易造成河道淤塞,宋廷每年都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实施清汴工作,导洛通汴工程的修建,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汴河淤堵的问题。但是因洛水夏秋涨落不定,“夏秋以来,盖亦屡雨,而河未尝涨;亦有经旬不雨,而水未尝干”〔57〕,因此严重影响汴河的漕运航行,“洛水入汴至淮,河道甚有阔处,水行散漫,故多浅涩”〔58〕,“致重船留阻”〔59〕。政和元年(1111〕六月四日,诏:“汴河水大段浅涩,有妨纲运。令蓝从熙差人前去洛口调节水势,须管常及一丈,不得有妨漕运。”〔60〕洛水水量有限,难以与黄河入汴之水量相比,但是其泥沙含量却远远低于黄河,因此导洛通汴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哲宗时期是黄河泛滥的又一高峰期,为加强治理黄河河患,针对黄河北流与东流的问题,朝中形成河议政局。在基层水官中,吴安持、李伟主张黄河回故道东流:“欲因涨水,回大河于孙村口,使还故道。”〔61〕指出:
今来大河已是分流,即更不消开陶。因昨来一决之后,东流自是顺快,渲刷渐成港道,见今已为两股,约夺大河三分已来。今若得夫二万,于九月便兴工,至十月寒冻时已毕,因而引导河势,岂止为二股通行而已,亦将遂为回夺大河之计。今来既因擗拶东流,修全锯牙,当迤逦增进,一埽取一埽之利,比至来年春夏之交,遂可复全故道。〔62〕
由史料可知,回河之役需征发民夫二万,于九月开工,十月完成。因其役使民力之众,工期之仓促,成为反对者争辩的口实:“河事必兴,工作不息,河北生灵困弊,无有休已矣。”〔63〕基层水官中,“范子奇争言河不可回”〔64〕,“(曾〕孝广尝为南外都水丞,迁都水监丞,不主东流之议”〔65〕。反对回河者指出:“今黄河北流如旧,涨水既退,东流淤填,遂成道路。”〔66〕“黄河涨水,于孙村出岸东流,本非东决,而吴安持、李伟等附会大臣,欺罔朝听,欲因此塞断北流,东复故道,差官调夫,于今年春首兴起大役。”〔67〕反对回河者要求“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晓然知圣意所在”〔68〕。其后黄河复决北流,回河无望,朝中争论自然平息。北宋后期回河之争中的两股势力各以爱惜民力与维护边防为由,展开激烈的辩论,实则是政党之争,对中央治水决策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宋廷对河道本身的水利勘测已处于次要的地位,在河患治理的实践中笼罩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北宋缘黄河、汴河地方政府的协同管理机制
北宋缘黄河、汴河地方政府与基层治水机构之间存在着协同管理机制,其主要表现为协同检视、筹备治河物料,在河患时期协同抢险救灾,协同巡查河堤等。缘河地方政府与基层河道管理机构在协同治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具体的运作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多的矛盾及问题,因此制度本身及非制度性因素在河道协同管理之中皆潜移默化地对其治水实效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第一,协同检视、筹备治河物料。转运司在地方财政的调配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协同检视、筹备治河物料是其主要职责之一。元丰元年(1078〕六月己酉,“开浚沟河,令都水监遣官同转运司检视工料”〔69〕。都水监与转运司共同检验查看储备的治河物料,有助于保障治河工役的顺利开展。在治河工程中,除对已有储备治河物料加强管理以外,对物料的筹措也十分必要。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癸亥,京西转运司言:“每岁于京西河阳差刈芟梢草夫,纳免夫钱应副洛口买梢草。”〔70〕梢草是修治埽岸的重要原料之一,转运司负责筹措免夫钱,用以购买梢草,筹备物料,是开展治河工役的必要前提及准备。又如:“六年八月,河决于澶州之王楚埽,凡三十步。八年,始诏河北转运司计塞河之备。”〔71〕除与路级机构转运司协同以外,在河道的开浚中,治水机构亦需“与县官同定紧慢功料,据合差夫数,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开淘”〔72〕。因此县级官吏也与专门治水机构存在协同筹备物料的职责。
第二,协同抢险救灾、治理河患。北宋时期黄河泛滥频繁,河患对州县百姓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州县长官积极参与抢险救灾、治理河患是当务之急,其与专门治水机构在抢险救灾中形成协同机制。如元丰三年(1080〕四月丁巳,“先是,河决曹村,水至郓州城下,明年山水暴至,漂坏城北庐舍。知州贾昌衡、李肃之相继议筑遥堤以捍水患”〔73〕。又如元符二年(1099〕八月甲戌,诏:“大河水势十分北流,将河事付转运司,责州县共力救护北流堤岸。”〔74〕可见在河患时期,转运司与州县形成层级的救护职责。在河道抢险救灾的工程中,转运司总理其事,州县则负责调集役夫,即“逐州长吏、令佐督役”〔75〕,与治水机构共同致力于河道的修治任务。又如:“臣愚欲望朝廷罢李伟小人职事,悉减修河司官,放罢见役开减水河兵夫,只委都水使者与本路监司并州县官吏将见修护急切埽岸,合役人夫,一面循理施行。”〔76〕都水使者与路级监司及州县官吏协同修治埽岸,并商议征发劳役问题。下面一则史料也反映了在水情危急时刻地方政府与治水机构的协同运作机制。熙宁七年(1074〕四月癸未,诏:“应黄河夏秋水涨,堤岸危急,须藉民夫救护处,去所隶州五十里以上者,本埽申所屡县辍令佐一员部急夫入役,及申外丞司并本属州催促应副,仍令通判提举。如不至急,妄追集民夫,并科违制,仍委按察官觉察之。”〔77〕朝廷规定在黄河水情危急的情况下,沿岸埽所需及时申报所属州县,州县接到奏报以后,派遣一名专员负责调发役夫抢险救灾。但是若不至危急,州县长官妄自纠集民夫,则要受到朝廷惩处。但在水情危急时刻若救助不及时,也要受到朝廷惩处。元丰五年(1082〕二月,诏:“‘前知澶州韩瓙,都水监丞张次山、苏液,北外都水丞陈德甫,判都水监张唐民,主簿李士良,都水监勾当,公事钱曜、张元卿罚铜有差;大、小吴埽使臣各追一官勒停;澶州通判、幕职官,临河、濮阳县令佐并冲替;本路监司劾罪。’ 以去岁河决,不能救护提举也。”〔78〕从史料中可知,因黄河决口,澶州知州等地方政府及治水机构都水监等众官吏未能及时救护,受到朝廷罚铜、贬官的责任追究。
第三,协同巡查河堤、日常维护堤防。宋廷对河道巡查管理有明确的制度规定:“诏缘河官吏虽秩满须水落受代,知州、通判每月一巡堤,县令、佐官迭巡,转运使勿委以他职。”〔79〕即在黄河汛期,缘河官吏虽已满任职年限,也需等水落方可离任交接,知州、通判每月巡查河堤一次,县令及佐官也需轮流巡河,转运使不可在汛期被委任其他职务,以免黄河发生意外决口,不能及时应对。元丰四年(1081〕四月,北外都水丞陈德甫言:“‘昨被旨令知深州孙民先及河北转运司那官一员,与臣同自卫州王供埽至海口案视大河故道。缘臣本以孙民先常有奏议,复修大禹旧迹,故请案视。今民先物故,臣未敢往。’ 诏转运司官同相视。”〔80〕史料反映了朝廷批准北外都水丞陈德甫与地方知州、转运使共同案视卫州王供埽至海口故道之事。缘河州县官吏又有植树造林,固护堤防的责任。史载:“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81〕即缘河州县在河堤植树造林,加强绿化,并时常巡查,是堤防日常维护的重要方面。
第四,协同管理中出现的矛盾及问题。在河道的协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非制度性因素导致的配合不力,如官吏之间的私人矛盾、办事态度、办事效率等;二是制度性因素导致的权力归属失衡,如官吏权责不明、侵夺权力等。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两个因素经常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最终导致协同运作之中出现严重的矛盾及问题。熙宁五年(1072〕四月辛未,“转运使既不肯应副买梢草,又以为无地安置物料,都水监李立之又多端沮其所须物料,差兵士,前后申请至于六七,仅能差得”〔82〕。转运使有向都水监筹备所需治河物料的职责,但此时转运使却不肯负责购买物料,并以无地安置为借口。都水监李立之多次埋怨其所急需之物料未能齐备,前后差派兵卒申请六七次,才筹备到所需治河物料。到北宋后期,在河道的协同管理中,转运司与都水监的治水职权出现权责不明的问题。如御史中丞刘挚言:“大河职事,河北转运司言之,别属转运司,都水言之,则属都水矣。”〔83〕又如户部侍郎苏辙言:
昔嘉祐中,京师频岁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置监以来,比之旧案,所补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职事。转运司之领河事也,凡郡之诸埽,埽之吏兵储蓄,无事则分,有事则合。水之所向,诸埽趋之。吏兵得以并功,储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敛伤财之患,事定之后,徐补其阙,两无所妨。自有监丞,据法责成,缓急之际,诸埽所有不相为用,而转运司始不胜其弊矣。近岁尝诏罢外监丞,识者韪之;既而复故,物论所惜。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一也……凡事之类此者多矣,臣不能遍举也。故愿明诏有司,罢外水监丞,而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之转运司。〔84〕
即苏辙认为,都水监自设置以来与原修造案相比于事无补,且河北外都水监侵夺转运司职事,对转运司的治河职权造成不便,且对户部财政构成危害。因此苏辙请求废除外都水监,将河北河事归属转运司管理。苏辙作为中央财政机构户部长官,提出废除外都水监,将河事归之转运司的做法,实际上反映了苏辙欲扩大户部财权对地方水政权力控制力度的构想,从制度设计上来讲,此时户部与北宋前期三司相比,已失去对地方水政权力的直接管辖权。实际上,户部、转运司之财权对地方水政权力的控制与侵夺,是专门治水机构与地方政府在协同运作中出现矛盾及问题的主要因素,以致于北宋后期出现转运使兼都水使者的现象。元四年(1089〕八月己酉,“河北路转运使兼都水使者谢卿材为河东路转运使,直龙图阁范子奇为集贤殿修撰、充河北路都转运使兼外都水使者”〔85〕。又如同年十月戊午,“河北都转运使兼外都水使者、集贤殿修撰范子奇依旧直龙图阁、权河东路转运使”〔86〕。转运使兼都水使者之制的出现,皆是财权力图控制水政权力的重要表现。
结 语
北宋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基层河道管理机构,在黄河沿岸其级别由高到低分别为外都水监、修河司、河埽司、埽所、铺屋,形成层级的隶属关系及管理组织;在汴河沿岸设有堤岸司、导洛通汴司,皆隶属于中央水政机构都水监。黄、汴二河基层管理机构的置废及其长官的治水实践受朝中政局影响颇深,变法派及反变法势力对黄河北流与回故道的激烈争论,成为北宋河道治理陷入被动及实效不佳的重要因素。北宋基层河道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协同治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协同检视、筹备治河物料;协同抢险救灾、治理河患;协同巡查河堤、日常维护堤防等。北宋基层河道协同管理机制,一是有助于增强专门治水机构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关系;二是有助于地方政府利用自身优势,集中力量投入基层河道治理任务之中,避免了基层河道管理部门孤军奋战的劣势。
但是在北宋基层河道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协同管理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及问题,其中制度性因素及非制度性因素导致的转运司、州县与治水机构之间配合不力,并出现转运司与外都水监之间水政权力归属失衡的问题,且在北宋后期出现转运使兼都水使者的现象。户部侍郎苏辙甚至要求废除都水监,将地方河事归属转运司,反映了户部、转运司之财权对水政权力的控制与争夺,是财权力图控制水政权力的重要表现。北宋王朝在发展的过程中,水利治理与漕粮运输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宋政府通过在黄河、汴河沿岸设置基层河道管理机构,对其加强了管制:一是有助于减轻黄河频繁泛滥对农业生产及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二是有助于保障汴河漕运航道的畅通;三是有助于维护黄、汴二河沿岸区域的水利治安。北宋基层河道管理机构及其长官在任期间虽取得了一定的治水实效,但由于受朝廷政局变化等因素的作用,北宋政府始终未能彻底消除河患对其王朝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