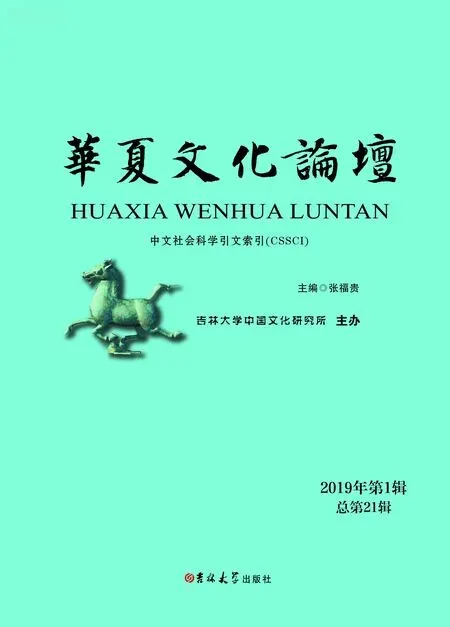先秦汉语“唯”的词性及其发展演变
——语法化的逆过程
徐正考 张 欢
【内容提要】“唯”的词性在先秦时期经历了逆语法化,演变过程为“语气助词〉范围副词〉谓词”。殷商时期,“唯”是表达强调语气的语气助词。西周春秋时期,“惠”消失;“是”取代了“唯”的语法功能;话题句兴起、语气词出现,这些动因促使“唯”发生了逆语法化,而被重新分析为了副词和谓词词性。战国时期,词双音节化进一步巩固了“唯”的逆语法化进程。
语法化的单项性的反例是指“逆语法化”或者“非语法化”现象,即语法化的单向性假设路径(实义词>语法词>缩合形式>屈折词缀)的逆过程,由屈折变化标记逆变为缩合形式,缩合形式演化为具有独立形式的语法词,具有语法意义的情态动词升格为普通的动词的过程。其具体路径可概括为“附着成分>缩合形式>语法词>词汇词(自由词素)”。逆语法化现象并不是广泛存在的,鲍尔·J. 霍博尔、伊丽莎白·克劳丝·特拉格特(2008)曾论述道:“语法化的单向演变是一种总体趋势;而单向性反例是偶然出现的、零星的,并未以重要方式构成模式。”对于逆语法化典型例证的探究有利于发现逆语法化现象发生的一般动因和机制。“唯”词义和词性的演变是逆语法化现象的典型例证,“唯”在先秦时期经历了由语气助词>范围副词>应诺之词(谓词性)的语法化逆过程,即由附着成分变成语法词再到实词的过程。
一、“唯”的词性——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
关于先秦时期“唯”的词性,学界众说纷纭。归结起来大致有“介词说”“副词说”“系词说”“词性多样说”“语气助词说”等五种。
“介词说”以管夑初(1953)、陈梦家(1988)为代表,采用殷商甲骨文作为语料。管夑初(1953)提出:“先秦时期‘唯宾动'‘唯宾是动'格式中,宾语位于动词前,“唯”是介词,标记宾语。”陈梦家(1988)认为:“‘唯'位于时间词前,‘唯'是介词,标记时间。”
“副词说”以何乐士(1994)、张玉金(1994)、陈双新(1996)为代表。何乐士(1994)采用《左传》作为语料,认为:“‘唯'是范围副词,表示仅限。”张玉金(1994)采用甲骨文语料,指出:“‘唯'是语气副词。”陈双新(1996)采用先秦历时语料,认为:“‘唯'是表强调副词兼有系词意义。”
“系词说”以周法高(1961)、谢纪锋(1983)为代表,均以《诗经》作为语料。周法高(1961)认为:“唯、伊、繄、即、乃,全部都是系词。”谢纪峰(1983)认为:“处于主语和谓语之间的‘维'要看作系词。”
“词性多样说”,以裘燮君(1991)、黄易青(2016)为代表。裘燮君(1991)认为:“‘唯'在殷商卜辞中作提示性的肯定助词,在两周传世文献中,发展为介词、连词、语气词等用法,在先秦早期文献中,‘维'可用作一般性的指示代词,第三人称代词和特指代词。”黄易青(2016)认为:“‘唯'的词性可为代词、副词、系词、连词等。”持此学说的学者,其使用的语料均为单一的传世文献。因而,不能全面地反映语言的真实面貌。
“语气助词说”,由王力(1980)提出,其后张书锋(1988)、赵诚(1998)、黄德宽(1988)、唐钰明(1990)、姜宝昌(1990)、杨伯峻、何乐士(1992)、陈永正(1992)、沈培(1992)、洪波(2000)、冯胜利、汪维辉(2003)、杨逢彬(2003)、武振玉(2006)等也持相同看法。持此学说的学者在对“唯”的词性判定标准上较为一致,“唯”是表示提示强调作用的语气助词,用于强调、标记其后焦点信息成分,且“唯”不是语气副词,因其位置灵活,不符合副词基本语法特征。
以上几种说法各有其合理性,之所以会各执一词,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其论证过程大多采用传世文献或出土文献进行专书或者断代研究而得出结论,未能在综合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基础上对“唯”进行历时演变研究,因而也就不可能较为全面地揭示“唯”在各个时代的不同面貌与性质。通过多角度、多种文献的历时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唯”在殷商、西周时期是语气助词,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发展出范围副词、谓词(应诺之词)的用法,也就是说“唯”在先秦时期词性经历了逆语法化。
二、“唯”的发展演变——逆语法化历程
殷商甲骨文中“唯”仅是表达强调、肯定语气的助词。西周春秋时期,“惠”消失,“唯”使用范围扩大;“唯宾动”格式锐减,“唯宾是动”格式确立,“是”取代了“唯”的功能;话题句兴起、语气词出现,替代了“唯”构成的语言组织形式,这些动因促使“唯”发生了逆语法化,而重新分析为副词、应诺之词(谓词性)。战国时期,词的双音节化趋势进一步巩固了“唯”的逆语法化进程。下面对“唯”的逆语法化的历程进行具体梳理。
(一)殷商时期
殷商卜辞中的“唯”是语气助词,位置十分灵活,可位于主语、谓语、宾语、状语前,对其后成分起提示强调作用。大多位于句首,有时位于句中,位于句首的“唯”是句子发出的第一个信息,往往赋予句子某种语气。例如:
(1)丁丑王卜曰:“唯余其亡延”。(《合》24980)
(2)勿唯王往。(《合》7352)
(3)癸未卜,宾贞:“兹雹唯降祸”。(《合》11423)
(4)唯我咎。(《合》6091)
(5)其唯小臣临令,王弗每。(《合》36418)
(6)唯八月有事。(《合》21586)
通过以上例句可以看出,语气助词“唯”句法位置多样,可以位于主语前如上例中(1)(2);可以位于谓语前如上例中(3);可以位于宾语前如上例中(4)(5);可以位于状语前如上例中(6),灵活的句法位置使“唯”常被分析为其他词性。陈双新(1996)认为“唯”是语气副词,其后向熹(1998)、张玉金(2001)赞同此观点。均依据语气助词用于句末,语气副词用于谓词之前的句法位置标准。这种单一的标准没有从根本上区分语气助词和语气副词。对于语气副词,各家定义并不一致,但具有两条公认的标准。在功能上,语气副词作为副词,在句中作状语或者补语,对形容词谓语或者动词谓语起修饰或者限制的作用。甲骨文中的“唯”可以位于任何一个句法成分前面,位置非常灵活,可以位于主语、谓语、宾语、状语等成分前,这与副词的功能标准相冲突。在意义上,语气副词表示说话人的主观情感和主观认识,这种主观性成分也作用于句子层面,由语气副词构成的句子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而甲骨文中由“唯”构成的句子有时推测客观的事实,表示非主体的活动,不具有主观性,如例(2)(4)句义只是在进行客观的说明。再如,甲骨文中“唯”的对贞形式用表示客观可能性的否定副词“不”“弗”而不用表示主观意愿的“勿”“弜”。这都可以说明“唯”所在句子表达客观的意义,并不是表达主观情感的语气副词。从“唯”和否定副词的位置看,语气副词排列顺序应该在否定副词之前,而甲骨文中“唯”位于否定副词之后,如“勿唯王比望乘”“王不唯有不若”。因此,“唯”不符合语气副词的语法特征。
管夑初(1953)认为“唯”为介词,其后陈梦家(1988)、黄德宽(1988)也认同此看法。其原因归结为两点:第一,“唯宾动”格式中“唯”为介词,用于介引宾语。第二,认为位于时间名词前的“唯”是介词,用于介引时间。然而卜辞中“唯”并不是宾语前置的标志,在某些情况下“唯”后动宾之宾语不前置,语序仍为“唯动宾”。
(7)勿唯王往伐邛方。(《合》614)
(8)勿唯王比望乘。(《合》7531)
(9)勿唯正邛方。(《合》6316)
(10)父乙不唯伐崇?父乙唯伐崇?(《合》903正)
(11)贞:不唯帝害我年?(《合》10124正)
上例均为“唯动宾”。当主语位于“唯”之后,语序不发生变化,此时“唯”用于强调主语。有时即使“唯”位于主语后,谓语和宾语也不发生倒装,如“王唯有不若?王不唯有不若?”(《合》376正)“贞:邛方不唯有福。”(《合》150)因此,“唯”并不是用于介引宾语的介词。
赵诚(2009)认为:“‘唯'放在时间词前,相当于“于”“在”的意思,好像是一个介词。”这是“惠”“唯”用法混淆导致的结果,在卜辞中表示时间远近时用“惠”和“于”对举,近称用“惠”,远称用“于”。如“辛丑卜:惠今逐狼?”(《花》108·2)与“辛丑卜:于翌逐狼!”(《花》108·3)如果卜辞中“唯”用为介词,也必然会出现“唯”“于”对举的情况,但在卜辞中并没有出现表示近称的“唯”,因而“唯”并不是介词。在卜辞中,“唯”“惠”用法相当,但“唯”的用法比“惠”灵活,使用范围更加广泛,把“惠”的用法等同于“唯”的用法是不准确的。
因此,“唯”在甲骨卜辞中,既不是语气副词也不是介词,而是一个用来强调其后成分的语气助词。
(二)西周春秋时期
这个时期“唯”除继承了殷商甲骨文时期的用法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惠”渐渐消失,“唯”替代了“惠”的语法功能。二、“唯宾动”格式在西周时期锐减,“宾是动”“唯宾是动”格式开始出现,“唯”提宾标志功能逐渐被“是”取代。“唯”语法功能减弱,使其语义向“是”靠近。三、主题句兴起,语气词开始出现。以上新兴语法现象,使语气助词“唯”开始重新分析演变为其他词性。
1.“惠”消失
黄德宽(1988)指出:“在五期甲骨文中‘惠'已渐趋消失,‘惠'‘唯'使用界限趋于模糊,‘唯'有合并‘惠'的趋势。”“惠”的消失使其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都由“唯”承担。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用于对举近称时间的“惠”由“唯”取代,并且“唯”逐渐取代了用于远称时间介词“于”的位置,导致西周金文中“于”不单独放在时间词前。“唯”用于句首表示对时间的强调,固定为基本格式“唯+年+月+其他”。
(12)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5,2751中方鼎,西早)
(13)唯十又二月初吉,伯吉父作毅尊鼎。(5,2656伯吉父鼎,西早)
(14)唯三年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8,4318三年师兑簋,西晚)
用在时间词前面的“唯”表示对时间的提示强调,与介词“于”有本质的区别。甲骨文中介词“于”介绍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构成介宾结构后作状语和补语。而“唯”只能位于句首,表示提示,所在结构只能作状语。因此,在时间词前的“唯”不是介词而是语气助词。
然而“唯”取代了“惠”的句法位置和意义,并且占用了介词“于”的位置,会使“唯”的用法增多,分布范围扩大。但与此同时,语言的明晰性与语境的作用要求各种用意合方式表达的语义关系,都要用明确的语法关系词来表示,而“唯”灵活而大范围的使用不能满足语言精确表达的需要。因此,在春秋时期大量的连词“则”“如”“故”兴起,这些新词的产生避免了歧义,同时提高语言的表达效率,并且占用了“唯”原有的信息组织形式,使“唯”渐渐冗余而重新分析为其他词性。
2.“唯宾是动”格式确立
“唯宾是动”是“唯宾动”和“宾是动”不同历史层面组合而来,其语义是排除其他可能,使宾语成为唯一选择。许嘉璐(1983)认为:“《尚书》《诗经》是‘(唯)宾是动'句式初始面貌,流行于西周末年。”黄德宽(1988)认为:“‘唯宾动'格式在西周中期消失,‘(唯)宾是动'西周中期产生。”唐钰明(1990)认为:“‘宾是动'在甲骨和金文中都未见,在西周春秋之交出现。”战国晚期中山王 鼎中出现“唯宾是动”格式“唯傅姆氏(是)从。”可见“唯宾是动”格式至迟在西周晚期已产生,至战国晚期发展成熟。
甲骨文中“唯宾动”格式极为普遍,而西周金文中却只能找到两个典型事例,“唯丁公报。”(8,4300作册令簋,西早);“乌乎!唯考 叉(守)。”(沈子簋·昭王器,西早)。而“宾是动”格式极为普遍。
(15)子子孙孙其万年永是宝用。(晋侯蹩马方壶,西中晚)
(16)其万年令冬(终)难老,子子孙孙是永宝。(曼季良父壶,西晚)
(17)子孙是尚,子孙之宝,用孝用享。(丰伯车父簋,西晚)
(18)天命是扬。(蔡侯钟,春秋)
(19)万民是赦。(秦公簋,春秋)
在《诗经》《尚书》中也是同样的情况,“宾是动”“唯宾是动”出现频率较高,“唯宾动”格式出现频率低。此时“唯”要带宾语,要用助词“所”搭配组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商颂·玄鸟》)这类“唯宾动”格式,“唯”好像是一个用于复指的代词,但此时的“唯”仍带有强烈的强调意味,用来提示宾语。
西周春秋时期,“宾是动”格式中“是”的出现替代了“唯”提宾标志的功能,如
唐钰明:《甲骨文“唯宾动”式及其蜕变》,《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小雅·大东》)“惟慢游是好,敖虐是作,罔昼夜。”(《尚书·皋陶谟》)此时“唯”不再是提示宾语的标志,渐渐成为一个冗余成分,失去了原本的句法位置。而“唯宾是动”格式出现使“唯”获得新的句法位置,避免了“唯宾动”格式“唯”词性不明确而带来的歧义。如,处于同一时代《小雅·巧言》和《郭店·缁衣》中,“匪其止共,维王之邛。”和“《小雅》云:‘非其止也,共唯王恭。'”二者用不同的句法结构“唯宾是(之)动”“唯宾动”表达同一内容,句中“是(之)”的存在,避免了歧义,补充了音节,让失去提宾标志功能的“唯”获得了新的句法位置。但此时的“唯”语法功能消失,“唯”作为语气助词,意义不够确切,这也就使“唯”渐渐成为句中的冗余成分,而语言的明晰性要求组成部分有明确的句法位置。“唯”作为有粘附性语气助词,在“唯宾是动”格式中,为了满足语言韵律和词汇双音节化的需求,和其后宾语经常黏连在一起组成双音节结构,“唯”渐渐地有了限制宾语的意思,用于确定宾语的唯一性,也就是说“唯”此时开始重新分析为范围副词,发生了逆语法化。
《诗经》《尚书》中的“唯”有时误析为系词和连词词性,这是由语气助词“唯”内在特征决定的,其一,语气助词黏附性极强,黏附于其他语言成分,十分容易派生出新的语法意义;其二,语气助词经常处于某固定位置容易产生新的句法意义,使词性发生变化;其三,“唯”在音律上和后面的组成部分构成一个韵律单位,用法和语义易受后面组成成分的影响。杨树达(1965)、裘燮君(1991)、陈双新(1996)、黄易青(2016)等认为《诗经》《尚书》中“唯”产生了系词的词性。这是语气助词“唯”的提宾标志功能弱化而向代词“是”发展所表现出的语法特征,符合“距离象似原则”。在“唯是”结构中,语气助词“唯”和代词“是”经常组合起来位于句首,用以强调后面的主语或者宾语,如“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由于指示代词“是”后面全部接名词或者名词性短语,这样使“是”有了判断词的意味,而经常与其黏连在一起的语气助词“唯”也渐渐与判断词的语义相似。尽管如此,此时的“唯”仍为语气助词表示强调。在“时唯”“实唯”“是唯”结构中,《郑笺》:“‘实'与‘是'通,‘是'与‘之'‘时'通,故‘实'与‘之'‘时'古音亦近。”“时唯”“实唯”“是唯”语音相通,意义相同。如,“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商颂·长发》)“非予罪,时惟天命。”(《尚书·多士》)此时的“唯”位于更靠近主语和宾语的位置,其系词的意味比“唯是”时期更为强烈,但句子中“实”用于复指,“唯”仍为表示强调语气的语气助词,而不是判断词。
黄易青(2016)等认为《诗经》中“唯以”和“是以”都是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如“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周南·卷耳》)“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小雅·蓼萧》)“唯以”“是以”在句法中并不对等,如“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不惟逸豫,惟以乱民。”(《尚书·说命中》)“唯”在句中形似起到了“是”的复指作用,但实际起到复指作用的是“以”后省略的宾语“之”。“唯”在句子中还是一个语气助词,而不是复指代词。“是以”连用表示“因此”的意思,而“唯以”不成词,“唯”仅用于强调其后的成分。
3.话题句产生
早期的汉语语言结构简单,句子之间的语义关系靠意合的方式体现,“唯”作为语气助词建立了一个效率极高的信息表达系统。春秋时期社会进一步发展,对语言的明晰性有了更高的要求,词的双音节化加快,使句法的形态更加的严密。“唯”原为一个高效率的句法组织形式,但其不能满足句法发展的需要,由“唯”构成的语言组织形式随着“唯”词性的转变和使用频率的降低而逐渐衰落。其后,汉语利用新的句法手段建立了新的信息结构,话题句应运而生。话题句的兴起和语气词的出现,使“唯”的词性发生转变。
梅广(2015)在探讨话题句产生的过程时提出:“‘唯'是上古汉语前期的系词,具有标示语句信息焦点等各种用法。上古汉语话题句的产生和系词‘唯'的衰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对“唯”的词性判断上认为“唯”是系词,并认为上古汉语系词经历了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一观点否定了汉语中第一个系词“是”的地位。但同意其“话题句的产生和‘唯'的使用范围的缩小有重要关系”这一观点。因为“上古汉语前期没有话题句,话题句是上古汉语中期以后出现的。”殷商卜辞中没有话题句,西周文献包括《尚书》和金文都没有话题句。殷商卜辞和西周金文中没有构成话题句的两个形式要件“者”“也”,这两个词语使用最早见于《诗经》,时间应为西周晚期。语气词“者”“也”的出现是话题句兴起的标志;“唯”作为信息焦点衰落的标志;“唯”词性转变的标志。
据张玉金(2015)调查,出土文献中语气词“也”在春秋时期才产生,而最早产生的语气词“哉”在西周时期才出现。这刚好和语气助词“唯”使用频率降低的时间相吻合。
下表(2)中,考察了七部传世文献中“者”“也”“唯”的使用数量、使用频率及使用趋势,具体数据如下:

表2-1 先秦文献“者”“也”“唯”出现频率统计(次)

图2-1 “唯”“者”“也”文献中频率百分比折线图
上图(图2-1)中,《尚书》《诗经》中“者”“也”渐渐出现并逐渐增多,到了《左传》中,“者”“也”的使用频率已经远远超过了“唯”,而“唯”的使用频率呈锐减趋势。可以推测“唯”作为一种信息表达手段,其句法功能和形式逐渐被更加高效的话题句所取代。话题句的产生使“唯”的语法功能衰退,词汇意义逐渐增强,是“唯”词性转变的重要动因。
“唯”使用频率降低,但句子仍需表达各种情感,而话题句有时不能满足表情达意的需要,语气词作为一种新兴词类越发丰富,“哉”始见于西周早期金文中如“敬享哉!”(11,6014何尊),“哉”是专职表感叹的语气词,在西周、春秋的语料中都可以见到,据武振玉(2006)统计西周金文中“哉”出现18次。“哉”等语气词的出现和提示宾语“唯”的消失、起提示强调作用的“唯”数量的减少有密切关系。此后,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更多的语气词如“与”“乎”“焉”“也”等等。
话题句和语气词的出现使“唯”的句法功能变得冗余。“唯”在语言演变的过程中其原有的语法功能消失,但它的语言形式继续存在,为“唯”向其他方面转化或者获得新的功能创造条件。这也是“唯”的词性进一步逆语法化为副词、谓词重要的动因。
(三)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唯宾是动”已经成为一种固定格式;话题句成为一种常用的语言形式;语气词成为表达中不可或缺的手段,使“唯”的使用范围缩小并发生了词性转移,此时“唯”可作范围副词、谓词(应诺之词)等 。
“唯……为”“唯恐”结构在《诗经》《尚书》中均未出现,在《左传》中用例较少,而在其他战国文献中使用频率较高,此时的“唯”已明确有了范围副词的词性。“唯……为”用于表示强调,“唯”用于主语前,表示唯一性,动词“为”表示论断和确认。如“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诬乎?”(《左传·定公六年》) “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庄子·外篇·天运》)“唯恐”是动词性结构,是词双音节化的产物,用于动词或者小句前表示对于某一件事情的唯一忧虑。在战国时期典籍中出现频率很高,如“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论语·公冶长》)“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庄子·外篇·天地》)此时的“唯”是范围副词,用来表示仅限。
“唯”可作应诺之词(谓词词性),独立成句,表示对对方询问的肯定,最早见于《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唯”由表示“强调、肯定”作用的语气助词,逆语法化为表示“肯定”的谓词性实词,符合“语法—语义相宜性”原则。词汇单位语法化过程中,它的初始意义和语法化之后的意义具有一定程度和谐一致的关系。“唯(语气)”与“唯(谓词)”具有相同的语义基础,都有肯定强调的意义,符合语义相宜性。语法位置具有话语意义和情感语气的功能,“唯(语气)”在句子中经常位于句首,句首是统摄句子的位置,为整个句子的内容和情感奠定了基础。句首位置为“唯”谓词性用法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位置。“语法—语义相宜性”促使“唯(语气)”进一步逆语法化为“唯(谓词)”。此时的“唯(谓词)”出现在互动对话语境中,表示一种价值的肯定判断,具有很强的个人主观色彩。如“老子曰:‘子自楚之所来乎?'南荣趎曰:‘唯。'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庄子·杂篇·庚桑楚》,句中的“唯”用于问话的肯定回答。
战国时期,“唯”作为语气助词基本完成了逆语法化的过程,有了副词、谓词词性。
三、结论
早期汉语结构简单,句子之间的语义关系主要靠意合的方式体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一步发展,对语言的明晰性有了更高的要求,使句法的形态更加的严密。“唯”原为一个高效率的句法组织形式,随着“惠”的消失;“唯宾是动”格式确立;话题句的兴起,语气词的出现,其形式逐渐不能满足语言发展的需要。其后,“唯”的词性发生了逆语法化,从语气助词发展为范围副词,最后发展为谓词性成分。语法功能逐渐减弱,而词汇意义逐渐加强。
语法化的单向性发展是语言演变的普遍规律,而逆语法化现象是较为罕见的。先秦汉语“唯”词性、词义的发展是一个较为完整的逆语法化过程,经历了由附着成分到语法词再到词汇词的过程。此前,李宗江(2004)、张谊生(2011)、吴福祥(2017)对汉语中的若干逆语法化现象进行了探讨,并总结出了一些逆语法化的规律,“唯”的逆语法化发展演变规律可以为“语气助词>范围副词>谓词”这一逆语法化路径提供解释。首先,逆语法化的发生是需要特定的句法环境和句法位置的。第二,句首和谓头是句子中较为敏感的位置,处于此处的词语较为容易发生逆语法化。第三,语言结构类型发生转变时,往往伴随着逆语法化的发生。第四,逆语法化现象发生的开端,往往从表达信息冗余开始。
上古汉语的语气助词丰富,“盖”“抑”“越”“允”“夫”等语气助词都经历了逆语法化的过程,有的转化为介词,有的转化为副词或连词,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逆语法化,这是汉语句法结构演变带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