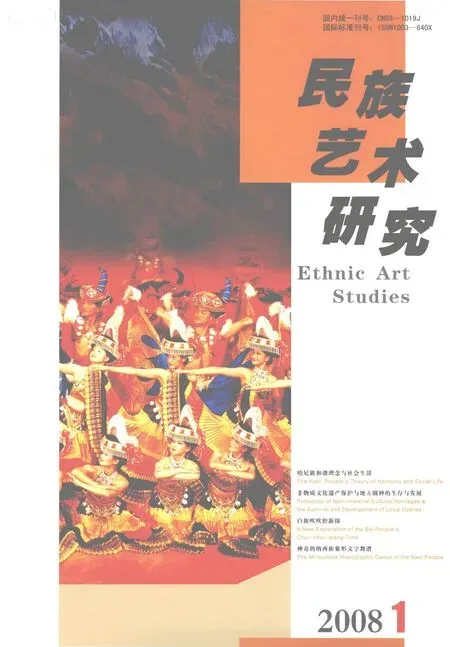有关中国电影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丁亚平
近年来,中国电影史学的研究形成一股热潮,出现了若干代表性的学者与成果。我从事电影史研究,也不揣浅陋先后出过一些著述。时光荏苒,我一个人写的《中国电影通史》(两卷本,120万字,中国电影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联合出版)面世已经两年多了。此书的完成和出版虽不能说是无憾,但亦是尽心之作。电影史研究,想要“言之有物”,就要去除先验性的幻象和框范;而进行中国电影通史的研究,面对新的问题,发现新的史料,探求新的答案,呈现于具体实践,无疑有着相应的路径、原则和方法论意识。对此进行梳理、反思和总结,是有意义的。
一、传承、创新和通史路径
学者之所以称学者,实在传承,在找寻学术路径与发挥个人原力。1963年,中国电影学术界有了第一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其中的三位作者中的两位,李少白和邢祖文先生,是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的前辈老师,也是电影学界最重要的老一辈电影史学家。他们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作为一种学术风格、一种电影史学派和元素的显著标签,为他们,也为影视研究所赢得了无数声誉。
《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时,被命名为“初稿”。这部上、下两册的电影史著作,梳理、研究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凸显了当时要求与特色。它距离写作的对象比较近,又有官方支持、策划与组织,所以在史料、观点主流化、电影史模式、范式的开创性上都占了先机。《中国电影发展史》无疑是渊博的,材料丰富,具有范式建立和拓荒的性质。后来的电影史著作,包括港台出的几本,各有所长,各有所失,却几乎可以说都是从程季华主编的这本中国电影通史著作里派生出来的。这部电影通史的政治性与电影史结构及观点选择,显然有它其时书写的理由。这项具有开创性的电影历史叙事既包含了政治对学术的介入,也包含将电影史视为有意义的方式加以建构的努力。共和国的电影历史叙事模式,在与时代语境的映射中孕育开启。 1981年,这部电影史著作未加修订,继续以“初稿”形式重印出版。这种出版方式并没有导致书的传播受到阻滞。相反,此著作在新时期的作用和影响非同寻常,声名远播。但是,毋庸讳言,左翼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史述的主要素材,认定它在电影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其他电影的活动重要得多,具有狭隘性。以新的眼光考察历史,需要超越。[注]重写电影史,相对于在实际的电影史研究和写作中提出的消解、解构和“颠覆”,还是提“重思”与“重述”更好,更有代际意义上的微妙的张力。李少白老师自己比较了不起的在于,他一直想解构《中国电影发展史》。比如,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想写一部《中国电影艺术史》。李少白联手邢祖文申请了院级和国家级的项目,组了课题写作的班子,积极规划着之后的研究论域与方向。这个难度不消说是非常大的。因为,完全跳脱发展史的史学范式和治史观念,去另辟蹊径,确实是一项重任。但李少白有其高瞻远瞩解构的强烈愿望。也就是,他不想把电影史写成电影政治史。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他希望电影史不能简单地为政治服务,希望尊重历史,回归学术研究。丁亚平,郝蕊:《创新的是电影史学发展的终极源泉》,《电影研究》第4辑,中国电影出版社,2018年版。
一种学术传统和学术文化是宝贵的,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而在这种传承中,也需要学人内心中能够有我们时代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断地萌动出崭新而又与众不同的素质和构想来。每一个时代的电影史寻求改变,把过去和当前结合起来,站在当下回顾、重审以前的电影历史,无论是文本、个案研究,还是做更全面的历史考量,融入作者新的眼光、历史分寸感和基本的立场是必需的。如果说电影史研究寓蕴范式、学派,那在不同的语境下一种范式或学派有什么样的活力和创造力,有哪些代表性的成果,这应该是电影史研究者要考察、思考和自觉的。
传承、创新和守护传统,是学科发展的灵魂,是电影学术、电影史学观念方法的核心内容,也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呈现。在近十几年来电影史学研究的热潮中,门类史、微观史得到拓展和深化,而通史研究,也被前所未有地激活。怎样将新的电影史写作作为一种进一步提高理论反思能力的宝贵实践,是许多学者思考的中心问题。通史写作,过去一直是电影史学研究中的弱项,在有的人眼中可能这无足轻重,没有什么价值。如何改变这样的认知与现状,需要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也需要刮风下雨、雷打不动,以足够的自我坚守与坚持进行漫长的研究和写作。其中的关键是,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对于电影史著述而言,更崇尚的是行动。中国电影通史,现在已出版的、已完成待出版的,和正在编写中的,有好几种。我想,在电影史研究和写作中,保持“滴水穿石”的韧性和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而在具体工作中,则不必担心在什么伸脚挂手上面做错,电影史的意识、撰写的标准是不是过严,更加大胆的电影史书写体例及新意的捕捉,为多少已成为几十年“固体”的电影通史这个难题开了一扇能吹进新风的窗子。
电影通史是什么?电影通史将时间向度作为自己的主要维度,试图解释电影长时段发展所发生的变革,但又并不限于此。“电影所能获得的艺术效果部分依赖于电影的技术状况。技术的发展在许多情况下是受经济条件制约的。而经济决定的影响则产生于社会语境之中。”[注][美]罗伯特·C ·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李迅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年版,第5页、第21页。在关联与制约中探索影响电影史发生与演变的生成机制及其因果链条,是其重要任务。李少白在谈道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方法时认为,电影史“兼有电影和历史的双重品格。作为电影学的历史方面,它研究构成整个历史现象中电影现象的变化过程。作为电影的历史部分,它研究电影历史现象的更替、变迁”[注]李少白:《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文艺研究》1990年第4期。。不少研究者认为,研究电影历史必须跳出以往研究影片历史和作者历史的范畴,将电影置于历史之中作更为开放的研究,既融入更具主体性意义的“电影”探析,又同时可为社会发展史、意识形态史、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等“起到注脚的作用”[注]郦苏元:《关于中国电影史写作走向的思考》,《当代电影》2005年第5期。。
无疑,电影通史是在丰富的影像和文献之上进行的更全面的对电影的历史考察和梳理,它是基于电影实践的过去和现在之间不断的对话。为获得一个可以观照不同电影史的公共视野,它使电影史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和补充。电影史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从电影作品入手,通过分析比较的方法,密切联系与作品和电影人相关的社会背景,叙述电影史上发生的以前的中国电影和电影人的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从当时的政治、哲学、文学等思潮中寻绎电影艺术风格演变的历史依据,理解并说明今天中国的电影传统是如何从过去到当下被逐渐建构起来的。
由电影史学实践出发,研究者的价值和意义被彰显。过去以《中国电影通史》为题的较具规模的由个人撰写的电影史著作一直没有,2016年这本《中国电影通史》出版,它的研究和写作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开拓性性质。作为全新的通史著述,所做的研究是积累性的。从搜集资料,写专题论文,追踪一百多年来中国电影发展的脉络,到最后成书,体现了这种特点。该书对1896年以来中国电影不同阶段的发展进行属于自己的梳理、分析和阐释,其中有电影作品、电影人研究,也有电影历史风貌、重大事件的回顾与阐述,同时又不缺乏对一个历史时期电影生态、文化生态横断面的分析、把握与深入剖析。中国电影通史这样的较大体量的著作,努力破解当下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困局,它比其他专史要求涉猎的内容更广、更丰富,史料更翔实,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全面了解中国电影的工具性的图书,它于有的读者而言,轻松就能做到一书在手,随时备查。
电影通史与过去的电影史著作特别是不无童稚化的电影史讲义与教程一类的书有着重要区别。与现实的电影经验相比,电影通史以宏观的视野、学术的品格和客观踏实的精神回归理性、科学、专业,不掺杂任何功利性,融入了有效的反思;电影通史因为距离的关系,“不受对象、权力和威势影响,更多关注电影发生发展中的精神逻辑,显示出其存在的意义”。[注]丁亚平:《中国电影通史》(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适应一时的口味,或者继续沿袭主流电影史学,或者将冷饭一炒再炒,不符合史学研究者心中的理想和原则,这样的电影史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
二、中国电影史“纵深线”的复杂性和通史写作的限度性
我在一种可称为“纵深线”时间的维度中融入思想与精神,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对电影历史“纵深线”的原型图式、多维走向及其交叉重叠与潮汐起落进行探究、梳理和把握,并在自体反思和理论场域中出新。这跟电影史学发展中的跨学科趋向有关,也跟我们的重新思考的创新意识、史学思维和方法论有关。其史学意识和思维,体现了电影通史研究的自觉,较之以前的研究,它可能更为重视历史主义的理论原则、观念、研究范式、方法、模型和视角。研究和写作中国电影通史,力图重视电影研究“纵深线”的形成和历史学的实证性,这之中也会面临许多问题。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作为中国电影通史的“纵深线”,其内容中较为容易产生质疑的可能是如何以及怎样涉指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两者是构成中国电影史非常重要的部分,不知该作何考量。笔者的意见和处理是:《中国电影通史》这样的书虽因篇幅所限,未能全面囊括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在内的中国电影,但是在梳理和研究中仍然要注意找寻、捕捉电影史上不同时期中国电影整体发展中的“纵深线”和共同建构的脉络,在贯通大陆、香港和台湾一百多年来电影发展历史及其把握与阐释上体现独特的创新性。对于中国电影或中华电影来说,以前三足鼎立,现在是一个融合的市场。在此之前的三足鼎立的电影,笔者在写作中贯之以大陆电影为主,港台电影为辅的观照与研究原则,即:以中国大陆电影梳理、论述为主,港台部分适当涉及,一些“纵深线”上的部分重要的电影史事、人物被梳理和展现。在大的历史节点和具体电影发展上,对涉及到的台湾电影、香港电影进行重点的评析,如:早期电影互动和发展、20世纪40年代上海电影人南下香港、50年代在香港的朱石麟和费穆等人的电影创作及香港的巴金电影改编、香港电影文化流变等都要有论述,着意将中国电影史放在大的“纵深线”时空跨度上进行表述。至于近40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需要尽可能详细地梳理和总结大陆和港台电影发展的历史脉络、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的电影市场逐步打破封闭的态势,内地和香港及国外合拍片成为制片业的重要选择方向,且从以协拍为主,转向以大陆为主(以我为主)的拍摄原则。开始,中国内地制片厂协助欧美等国拍摄了《太阳帝国》和《末代皇帝》等影片,此后更多的是与香港合作。自此,电影工作人员逐步走向高度交融。与张鑫炎合作《少林寺》、与李翰祥合作《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内地协拍)等,带动了港台与大陆合拍的热潮。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陆续走红国际影坛,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奖项,出现“台湾的资金,香港的技术,大陆的人才”相组合的新关系。1993年合拍片热达到高峰,创纪录拍摄56部。进入21世纪后,也即在形成中国电影的融合市场中的原三足鼎立电影,已经作为中国电影的整体,极大地推动了华语电影繁荣与兴盛的走向,产生了广泛的传播力。由此,中国电影的“纵深线”越来越交融在一起。
不管是香港电影也好,台湾电影也好,在中国这个范围之内出现的电影,我们认为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电影;在这些“纵深线”范围之内活动的电影人和他们的创作,我们都可归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电影家和电影现象。电影通史涉及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的内容,虽可能较简明与综合,但却一定要注意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讨论其为何如此发生,而不像传统的一些电影史或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专题史学著作那样,探讨单一维度的香港电影、台湾电影发生什么和怎样发生。
还有一个问题,是近40年来的中国电影史,所涉内容很多,加以主要指向当代中国电影的评价与判断,材料庞杂,认识、视角各有不同,电影随着当代历史客观环境的变动承载不同的定义和理解,然而倘若从“纵深线”举重若轻地进行新的发掘、整理、解读,并将其放在更宏观的历史语境里观察,以使中国电影通史成为一部总体性的电影史,则自然难度下降,殊非易事之电影史,同样可以予不可能以可能。
中国电影为40年来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的注解。自从电影的生产制作、发行和放映各个环节连体形成产业经济形态之后,中国电影在呈显庞大的产业规模的同时,展现出爆发式增长和跨越式发展的景观。2010年内地电影年度票房迈入100亿元,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突破600亿大关,以609.76亿元完美收官,比上年559.11亿元增长9.06%。
电影产业持续走在快速发展的轨道上。2012年内地电影市场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2018年一季度一度超过北美市场,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银幕总数已达到60079块。截至2019年2月22日,中国内地电影市场该月已突破100亿元,这是继2018年2月后,内地总票房第二次突破百亿大关,并把时间缩短到22天,比2018年提前了6天。在世界电影史上,单一市场月破百亿元的票房的纪录由中国创造。中国电影观众的观影年龄层广泛,电影市场体量不断扩大,在增强中国电影的产业和文化影响力的同时,作为全球电影贸易大国之一的地位得以上升。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依赖于国产电影创新的内生增长动力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升。中国如何迈向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中国电影无疑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基点和转折关头,尽管对电影改革的实际运作与走向的看法有很大差异,但不管怎样,许多重要的经验值得总结,国产电影有着怎么样的未来走向,电影创作如何在改革开放演进过程中被进一步唤醒、改变和塑造,成为值得关注的当代电影史的重要问题。[注]参见丁亚平:《中国电影:如何走向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艺术评论》2018年第10期。
通史研究无疑需要尽力集大成而致中和,在这方面做积极的宏观认知、梳理和归纳,值得认真去考量。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 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中国电影与社会经济的融合紧密。电影作品的内涵及艺术风格映寓着特定的时代遭逢和美学选择。
在中国电影史上,社会派、人文派、商业派、浪漫派构成电影史“纵深线”上的多样性美感与话语形态。社会派直面现实,最受观众喜爱和富有参与性,和现实主义的真实美感形态结合,匡正时弊,给人愉快和省思,有益于社会发展,构成电影的主流。人文派重视艺术的风格化建构,影片在真实性、思想的深刻性和结构的完整性诸方面较其他形态的电影尤显突出。商业派变异多端,欢快喧闹。浪漫派则热烈灿灿,是典型性的“逆出之类”。这样的四种形态有时也会被打散和重组,而且对它们的概括可能有人不完全认同,但他们其实反映了中国电影,以至华语电影发展的基本状况。社会派和商业派在显在的层面掌握话语权和文化优势;而人文派捕摄神韵而又婉曲、多义,成功地表现了“关心人”的主题,于隐在的层面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范式的意义;浪漫派显现出某种希望的活力与主体性张力,但属于少数派,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和90年代以来电影商业化兴起、发展的结果。
中国的电影历来和不同时期的政治以至国家意志的发展相勾连。“十七年”时期,20世纪80年代,一些电影,特别是秉持社会和人文选择取向的影片上映后往往会遭到批评,而且批判相当凶猛,硬被安上“丑化党的领导”“歪曲现实”等帽子,“上纲”很高,让人胆寒。与之成为对照的是,香港电影导演的作品,大都是职业化的电影,是在片场和影院工作的结果,通常会回避谈论意识形态和政治。作为好的导演,除了扎硬寨、打硬仗,不屑于走捷径、抄近道,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回避跟老板和观众谈政治和意识形态。香港以至台湾影人的电影属于商业派和人文派的居多,与这种职业生态相联系。而商业与人文并非总处于互相支持的兼容关系之中,而是有时处于“纵深线”互相抵牾的悖论性的关系中。
人文或艺术电影大都受限观赏性较差的基本条件,创作并不顺利,影响力不大,这是人文电影最大的危机,而且这也是范式电影、艺术电影以至基本电影的危机,这比中国电影独霸中国内地庞大的市场或者在国际电影节比赛丢几个大奖都更为严重。可见电影的发展,与不同的时代与生态环境,和特定电影人及其各别作品的具体形态相联系。复杂、多维的电影实践、活跃态势与多样性趋向,包括审查制度以及中国影院电影的宣传和商业的双重属性等,反衬出电影史学具有的限度性。
进行通史的写作,在对中国电影做了“纵深线”发生史的周翔描述的同时,能否在结构上以及论述内容中加强对中国电影史发展中多维度的重要文本以及重要导演风格形成、特征以及启承和影像的基本逻辑关系提供明确的分析线索?在通史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人们究竟希望中国电影通史这样的书,融入怎么样的最新学术成果和打开怎么样的全新研究视野呢?我想,前提当然是尽量显现电影历史和“纵深线”的复杂性、当代性,呈献一种新的看待电影史的面貌。中国电影通史著作,记载、分析、研究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特点与客观规律,重点反映电影“纵深线”的复杂交错与承续的生态格局及历史流变。电影因时代的不同,其面目、特点与影响也不同。我格外重视去思考的是:怎样在追踪、梳理百余年的中国电影历史的过程中,找到我们研判中国电影问题所用的艺术的、文化的、学术的范式标准和框架?能否在电影史的总体性探索与“纵深线”描绘过程中超越狭隘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和道德话语?如何写出一部有自己特点的电影史,以丰富人们对中国电影的认识?这些是一个电影史研究者不能不去努力的目标和方向。笔者研究中国电影通史,将中国电影历史发展视为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存在,但相关电影史的综合梳理,仍然是以代表性的电影人和影片为坐标,围绕电影史“纵深线”上的电影人、影片,包括中国电影史发展中的重要文本以及重要导演风格形成、特征进行论述。
作为一部电影史著作而非专题理论研究,所处理和使用的术语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约定俗成的为大家共同接受与认同的概念,如“抗战”电影、“文革”电影、主流电影、商业电影,但在做这样处理的同时,电影史家关注的重点,应该是用新的分析法而不是旧的叙事法来撰写历史,采纳什么样的概念和认识能对电影史的研究工作有更细致、精准及脉络化的理解。另一类术语和概念则可能更具有电影史的阐释力,隐藏着一种当代史的视角。好的或比较好的理论视角、概括与术语,应该具有相当高的建构性。电影史是活的学术研究,不用死的框框框住它,把电影当成一个开放的系统来研究,研究视野更为开阔,方法和方向更为清晰,这是重要的。
三、第三重空间:走向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电影史作者不是一个自在逍遥的历时性旅行者,也不是简单地去独辟门径,一味驰马试剑。电影史的真实与叙事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经验论视域下的电影史料及其运用在日趋开放的数字化语境下改变了它的意义。电影史的重写与“修正”提供了不同的可能蕴含以偏概全的视野和角度。通史叙事的面相,存在于超乎其上的第三重空间中。电影通史的研究基于作者自己的客观审视和主观阐释所得,将“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主体性建构与“为什么发生”结合,在走向历史和逻辑的综合中力图对电影史及其生生不息的发展进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扫描和深入的阐释,在主客观统一的范式中彰显开放、完整的电影历史研究方法的效能,以此进一步凸显电影通史写作的严整性和独特性。
有关通史的研究,无论是偏重于社会学方法还是倚重风格分析,是编年史抑或国别史,有时都需要融入“跨界”的视角、新的话语体系,突破观念的藩篱,以深入描绘电影历史发展的丰富面貌。如海外学者米莲姆·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汤姆·甘宁的吸引力电影等,和电影历史现象和相关电影实践并非总处于互相支持的兼容关系之中,但他们所采用的仍然是富有启示的有趣方法,是域外史学开出的花朵。再如“大电影”的概念,是笔者和影视研究所部分学者进行理论研究的个人成果,它并不是官方概念(在这方面绝无有关“大电影”的“官方文件”)。在电影史研究中使用的“大电影”概念和结构分析,不是指“影院电影”“大银幕电影”,而是指数字化转型和网络化新语境下电影形态、电影叙事、电影本体和电影业态及生态的改变,涉及影响日趋重要的技术、影像本体、传播的多重维度。[注]此可详见丁亚平《新语境下“大电影”的建构与发展》,《文艺研究》2012年第11期。参见丁亚平主编:《大电影制造:异彩纷呈的热播影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丁亚平主编:《大电影制造:热门影视的光影世界》,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丁亚平等著:《大电影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丁亚平主编:《大电影转向:热播影视的发展趋势》(上、下),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丁亚平主编:《大电影的拓展: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策略分析》,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丁亚平主编:《大电影的互动: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策略可行性研究2》,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丁亚平主编:《全球化与大电影: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策略可行性研究3》,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这样的新的术语、视角和场域,包括前面论及的“纵深线”等,如潮水般涌来,一起推着我们往既定的大道上走。不消说,其中当然蕴含对中国电影下一步的创新路径和发展空间等的前瞻探讨。
通史的写作和探讨,和那些先于我们存在的秩序相遇,可以打开观照方式和视野,扩充心量,却又不能不带有“自我”气质和自传性质。
但是,通史写作,史料筑基。一部电影史著作,重返历史的现场,史料的发掘是基础,尽力搜集资料,认识并把握其中呈现的确切性、可信性与问题,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发掘力分辨力,是研究与写作的前提。为使研究内容更为生动翔实和可靠,电影通史写作和论述有时也可以尽可能比较充分、大量地引述电影人的访谈内容,通过多处使用一些重要的中国电影人的访谈或自述等口述史材料,使感性的东西融入理性分析和历史的探索中。[注]以我的《中国电影通史》为例,电影人口述涉及和包括第四代的谢飞(下册第83、94、122、160页)、黄健中(下册第95页)、张暖忻(下册第108、109页)、杨延晋(下册第96-97页)、黄蜀芹(下册第142页)、郑洞天(下册第83、150页),以及常彦(下册第92页)、马德波(下册第89页);第五代的张艺谋(下册第139?141、145、146、148、152页)、陈凯歌(下册第140、145页)、田壮壮(下册第151、152、153页)、张军钊(下册第141页)、霍建起(下册第82页)等。兹不赘述。
电影通史这样的著作,努力去总结电影历史经验,揭示电影发展规律,但所体现出来的选择与笔墨仍各有不同,对百余年中国电影的梳理取舍仍比较大。笔者对此是怎么考虑的呢?(一)电影史,即使是以“通史”名之,要包罗一切电影现象和作品,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二)还是需要承认中国电影历史发展中存在着矛盾和复杂性,慎重选择和处理有关论述对象是必要的。(三)一部内容丰富、生动的电影史(特别是电影通史),对其中出现的“执拗的低音”(日本学者丸山真男语)不能无视而不去做必要的叙述与呈显。写中国电影史,要能干净独立,贯穿秉笔直书的勇气和传统,以学者鲜明的治史立场进行分析。选择让电影史的本质更真实的方式去把握,而不是其他。
电影史写作的个性化,其实也是不同的电影史作者个体/主体不同的选择和做法的呈现。一部中国电影通史,面对多品种多样式的电影,往往会聚焦考察和重点梳理影史上有代表性的电影作品,以剧情故事片为主,兼及纪录电影、动画电影。但是,电影史作者有其个性诉求,可以选择追求自己理想的写作方式与编辑体例。虽然,笔者认为一部电影史不可能把什么都悉数包罗,而且,能把复杂的电影发展历史化为扼要且稳当的表述,也是格外考验史识和学力的。
电影史对电影发生发展的历史需要做全面的审视与扫描。徜徉其中,一方面作者希望在具备知识分子特质的导演身上看到对社会与现实有思考有担当有深度的电影,并将之突显地呈现出来,放到比较重要的影史位置上;另一方面,作者也希望中国电影通史这样的著作能展现当代中国电影的“众生相”,从全面的角度进行历史的梳理与分析。如“文革”电影虽然相对于“十七年”时期电影(尤其是故事片)产量很少,但“文革”时期电影表现出高度的集体意识和快速走向极端的革命实践的热情,为电影艺术画了一幅特殊而谵妄的“画像”,不能视而不见。“文革”时期的中国电影,江青的作用,“样板戏”的影响,以至那一时期拍摄没有停止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简报》[注]《中国电影通史》限于篇幅原因,对新闻纪录片、科教片较少论及,但对重要的电影现象,有所论述。如“文革”后的1977年10月18日,文化部(当时电影主管机构)发出《关于停映有“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形象的新闻纪录片和他们指使拍摄的部分科教片、艺术片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要求相关新闻纪录片一律停映(下册第72-73页)。至于“文革”时期,有关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简报》,本著作并非“完全没有涉及”,在第六章第一节第三部分(该部分的标题为“同一种红色的新闻纪录电影和洋为中用的《红色娘子军》”),标题所标明的“红色的新闻纪录电影”即指《新闻简报》,该段落(下册第13页)对《新闻简报》进行了简明叙述。此外,下册“文革”时期的外国导演纪录片,介绍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但没有涉及当时由周恩来总理邀请尤里斯·伊文思及其伴侣马斯林·罗丽丹女士在中国耗时3年创作完成达12小时12部的系列纪录电影《愚公移山》,这是重要遗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这部纪录电影是在世界电影史上都很重的一笔,在中国电影历史中不该被遗漏。,作为当时最及时的“革命现场”,电影通史著作对此不能没有涉及。再如中国独立电影,这些影片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环境中因为不可能申请到“龙标”——即放映许可证,观众面受限,影响力不大,但因此就不该纳入通史研究的范围内了吗?尤其是数字电影时代以来,中国独立电影的创作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电影史的构成部分。又如关于“献礼片”“英模片”和《建国大业》等主旋律电影作品的论列和分析,也出于同样的考虑,这样的影片,同样具有明显的历史价值。
在中国,“独立史官”的历史传统,对后来影响非常大。不从政治的角度书写中国电影史,有其史学合理性。作为学术研究,我们不想把电影史写成电影政治史,希望电影史不去简单地为政治服务,希望尊重历史。过去,政治对中国电影历史书写的影响和改变,是比较明显的,这种做法让人感觉好像电影史就是为某个人写的,感觉中国电影只是因为出现了左翼电影,因为延安和解放区电影,才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当然是一种有偏差的历史认知,是需要解构的电影史。
各个时期中国电影发展都包括电影在这一时期独立的工业、风格和主题关怀的系统发展的描述,而这些不同时期的特征常常是共存和重叠的,但这不能否定就其主要特点进行概括的意义。
对于一部电影史著作而非电影理论或批评论著说来,重返历史现场是史论写作必要的前提,电影史研究需要看到它特定历史时期的特点,要准确把握,进行宏观跟微观结合的研究,这样结论才可能比较扎实,是历史主义的。所以尽力了解、搜集资料,努力思考、融合,以扎实材料支持这样的历史梳理与分析,做到笔者一直主张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注]首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完整的方法论,历史主义本身就是方法论,是很重要的史论研究的观察视角,建立论述的框架,所以这是不能割裂的。在电影史研究中,历史和逻辑,从来都是既不可或缺、又彼此互动的。也正因为这样, 这两者之间其实也并非总是那么界线分明。其次,当你把议题或论述对象放到历史语境中去,确实有如何禀有主动精神,怎么去论述并给出自己的判断、评价、观点的问题,这对你的研究的方向、深度、整体的格局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所以还要有逻辑的建立、自己的阐释。这里有梳理、接续、拓阔,也可以有扭转、矫正与塑形。再次,对于一部新的电影史说来,这之中其实还有一个中介层,就是如何把它做一个必要的论述和表达,把你的观点做一个专业化程度高、又区别于他人的史学和理论论述结合的新的个性表达。每个人的研究个性、风格、观点跟思想依赖于这样的表达、论述的个性角度形式,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方法论,其中必然会包含自己的知识、学科背景、历史思维,等等。(丁亚平,郝蕊:《创新的是电影史学发展的终极源泉》,《电影研究》第4辑,中国电影出版社,2018年版。),是必要的。在我看来,这也是电影史写作跟电影理论、电影批评的区别之一。我们做电影研究和史著写作,考虑应尽可能地让它重回历史本来的形态中,努力梳理、把握它和特定历史相应的社会、政治、文化、艺术的复杂关系,而在中国出版一部内容、篇幅较大的电影史著作[注]笔者《中国电影通史》的写作,最初没有列入自己个人的学术写作计划,而是来自中国电影出版社的约稿。,一方面不会简单地寻求“发球得分”,另方面恐也难以太过形而上地要求,就像要求拔起自己的头发让自己的身体脱离地球一样。中国电影通史这样的书著写作,有其学科建设价值与中国电影的文化传播意义。在电影史的写作中,史料或文献需要集中而又具有覆盖力,要顾及它的微观、中观、全貌、“纵深线”和历史演进的脉络,所以写完、出版后即使发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我们专诚不二、潜移影史的自然结果。
电影通史写作坚持历史的维度,形成开放的研究和体验、激发问题意识,以至对于整个新电影史范式的反思和论述,都包含在我们与我们这个时代之间的情感的、精神的联系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观察之中。作为电影史学的新的建构,多少年后回过头来看,近年兴起的中国电影通史写作,也许会是一个新的起点。电影史研究者的主张与其说是尝试提出“新”的研究方向,不如说是追蹑电影历史发生与发展的轨迹。理智清明,心与天游,方法活泼,穷变化以洞彻事理,创新性地去进行历史叙事、呈现其具有的特色、时代意义,更为重要。潜入历史和学术的汪洋,“板凳坐得十年冷”,更能帮助我们以更开阔的胸襟走好自己的路,进而更清楚自身与他人的特色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