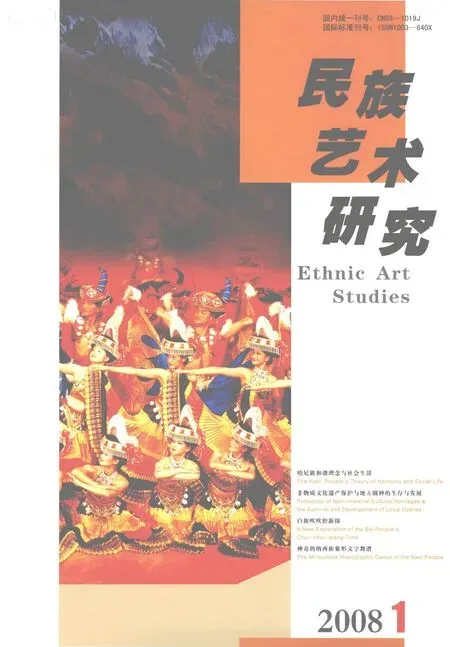中国艺术理论之源:《二十四史》“艺术列传”
李倍雷
《后汉书》最早提到“艺术”的概念,《魏书》为“术艺”作传,此后《晋书》《北史》《周书》《隋书》始为“艺术”而传。因为“艺”与“术”都是作为技术、技巧、技能层面的含义且是并列关系,故此“术艺”与“艺术”同义。同时《二十四史》中的“艺术”概念与内涵本身也在不断地变迁,唐代以后《二十四史》中“艺术列传”不再出现,“艺术”分散在“文艺列传”或回到“方技列传”中去,但有意思的是《清史稿》再度恢复了“艺术列传”,且在《四库全书》“经”“史”“子”“集”都有《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的内容,这是由于不同时代官修中对“艺术”作为纳入文化架构整体中考察、认知和与主体文化体系建构的不同态度,从而采取的对庞大的“艺术”容量进行“分解”与“重组”所形成的变迁结果。这方面已有学者做了很好的讨论,如文韬《雅俗与正变之间的“艺术”范畴——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中的术语考察》。《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所包含的复杂而丰富的内容,昭显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更是当下我们建构中国艺术理论之“源”。
我们这里提出两个问题并以此来探讨艺术理论的源流问题:一是《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的“艺术”与西方的“Art”二者之间的源流问题;二是艺术本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源流问题。以下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探讨艺术的“源”“流”问题。
一、诘问“艺术”与“Art”谁为源与流
中国的“艺术”与西方的“Art”在19世纪的汇合中,必然有一个源流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清末民初一大批学者也在思考与面临着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云:“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注](南朝·宋)范晔、(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5页。同时《后汉书·卷二十六·伏湛传》也提到了“艺术”的概念,其云:“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蓺术。”[注](南朝·宋)范晔、(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98页。这是中国古籍文献中最早提到“艺术”这个概念的。自此以后《魏书》《晋书》《北史》《周书》等都设有“艺术列传”,尽管“艺术”这个小道致远恐泥,但还是正式进入中国古代的正史之中,“艺术”终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专门一类,并源远流长。19世纪中国的“艺术”与西方的“Art”在碰撞与交流的过程中,使中国的“艺术”内涵发生重大的变故,以至于人们似乎忘记了在中国传统中还有一个“艺术”的概念以及自身的内涵与内容。甚至还有人以为“艺术”就是西方的“Art”翻译而来的,即使知道中国传统中还有一个“艺术”概念,也不是作为“源”来认知的。
“艺术”与“Art”二者之间的这个“源”“流”问题若不弄清楚,中国艺术学的理论体系与话语建设工作就难以深入,甚至无法建构出中国艺术学的理论体系与话语。纵观当下的“艺术学理论”或者说从事“艺术史”“艺术理论”研究的学者,只要一提到“艺术学”这个学科或艺术的概念就言指康拉德·费德勒(Konrad Feidler,1841—1895)、马克斯·德索瓦尔(Max Dessoir,1867—1947)、恩斯特·格罗塞 (Ernst Grosse,1862-1927)等人,言必《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德索瓦尔)、《艺术的起源》(格罗塞),却忽视中国自己文化中《二十四史》中的“艺术列传”,很多情况下把西方的“Art”作为我们艺术理论的逻辑起点。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定向思维模式?因为在一些人的认知中,费德勒是西方第一个意识到美学与艺术是不同的人,他注意到了绘画、雕塑视觉性的特殊意义与抽象的美学相区别,因此费德勒被称为“艺术学之父”。随后又认定是德索瓦尔建立的艺术学,因由他撰写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严格地区分了美学与艺术学的关系,第一次将艺术学作为学科对待。同时,只要一提到“艺术起源”的问题,言必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一书。我们不是说西方这些美学家所探讨的“Art”问题不重要,只是这些是西方有关艺术或艺术学的问题,是西方艺术理论的逻辑起点,但不是中国艺术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清末民初,中西文化与艺术的碰撞与交流,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很自然地将“Art”概念引进与中国传统“艺术”概念进行对接,且清末民初很多学者在梳理“艺术”概念时也在思考“艺术”内涵的所指。尽管《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的内涵与《四库全书》中“经”“史”“子”“集”在对艺术的文化分层上存在不同看法或者有的甚至没有被包含在“艺术列传”中,但也是属于“同源异流”的问题。同时,“中华民国”的学者们还接受了“Fine art”的概念和观念,康有为、蔡元培、鲁迅、刘师培等人即是如此,终归把“艺术”归类到了西方“Art”的概念与内涵中。
鲁迅曾说:“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此之所用,译自英之爱忒(art or fine art)。爱忒云者,原出希腊,其谊为艺,是有九神,先民所祈,以冀工巧之具足,亦犹华土工师,无不有崇祀拜祷矣。顾在今兹,则词中函有美丽之意,凡是者不当以美术称……言美术之目的者,为说至繁,而要以与人享乐为臬极,惟于利用有无,有所牴午。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系。诚言目的,此其正解。然主用者则以为美术必有利于世,傥其不尔,即不足存。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注]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这就是把中国传统“艺术”观念靠向了“Art”或“Fine art”观念。“艺术”在经历民国时期学者们的重新认定后,“艺术”或“美术”的内涵逐渐指向绘画、雕塑、文学、音乐(蔡元培的观点即是如此)。1949年以后“艺术学”作为“文学”下的一级学科纳入正式的中国教育体系,艺术学所包含的二级学科有“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戏剧”“影视”“工艺美术”(“设计”)等。当2011年“艺术学”从“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13大门类学科,便形成了5个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戏剧戏曲影视学、设计学。这个划分基本上沿袭了以经由民国时期对“艺术”或“美术”进行改造之后所承载的内容,而划分的学科以及对于其内容的定位。当然,也就不难发现参照标准是“Art”或“Fine art”。上述两个方面艺术(美术)学科几乎都没有考虑到《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的“艺术”概念和内容,如果单就“美术”的概念和内容来看,也就是西方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意大利著名的建筑家、画家、雕刻家传》又称《意大利艺苑名人传》框定的三位一体的“建筑”“雕塑”和“绘画”所涵盖的内容。目前艺术院校的美术学教学大纲的课程设置以及教育部学科规划也是以绘画、雕塑为主,亦有一些美术学院增加了“建筑系”,把建筑学纳入美术学的范畴。从“艺术学”的范畴来看,也不是《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的全部。李贤将《后汉书·伏湛传》中“艺术”的阐释为:“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注](南朝·宋)范晔、(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98页。这无疑是中国最早对“艺”与“术”两个集合名词内涵的解释,即使到了清代《清史稿》“复出”的“艺术列传”大抵也是依照这个路径进行的调整,《清史稿·卷五百二十·艺术列传》云:“自司马迁传扁鹊、仓公及日者、龟策,史家因之,或曰方技,或曰艺术。大抵所收多医、卜、阴阳、术数之流,间及工巧。夫艺之所赅,博矣众矣,古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士所常肄,而百工所执,皆艺事也。近代方志,于书画、技击、工巧并入此类,实有合于故意。”[注](清)赵尔巽等:《清史稿》(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548页。《四库全书》对“艺术类”做了较大的调整,原有“艺术列传”中一些内容分别调整到“经”“史”“子”“集”中去了。但在《子部》的“艺术类”中除了绘画、书法、琴律等外,依然保留了奕棋、投壶、射、五木等内容。也就是说,中国传统“艺术”内涵与内容极为宽广且丰富。但是,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艺术”在与西方的“Art”碰撞与交流过程中,主动把“艺术”靠近“Art”,使原有丰富而宽广的“艺术”内涵变得紧缩起来,尤其是接受了“Fine art”后,时至今日的“美术”概念仅仅包含“绘画”“雕塑”,偶有把“建筑”涵盖进来。这实际上是把西方的“Art”作为“源”,而中国的“艺术”则被作为“流”。
有关“艺术”与“Art”二者谁为“源”谁为“流”的问题,我曾在《〈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是建构中国艺术理论学术话语的基础》一文中提出,我认为构建中国艺术学的理论之“源”是《二十四史》“艺术列传”及其中国古籍文献有关的艺术观念和内涵,而西方的“Art”则应该是“流”。[注]李倍雷:《〈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是建构中国艺术理论学术话语的基础》,《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8年第6期。
二、有关艺术学理论源与流的诘问
上面我们从中西方之间的“艺术”与“Art”关系探讨了“源”与“流”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探讨艺术本元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源”“流”问题。诸如艺术学与美学、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考古学等以及与其他人文学科所形成的交叉学科“艺术美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艺术考古学”“民俗艺术学”“民族艺术学”“艺术管理学”“艺术经济学”等,到底谁是“源”,谁是“流”的问题。
当下艺术学的理论研究包括美术学的理论研究,受到其他人文学科影响较大,或者说其他人文学科介入艺术学领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研究趋势与研究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介入推动了艺术学的理论研究,也拓展了艺术学的理论研究空间以及提供了理论研究的方法与经验,以至于形成了上述的交叉学科。现在也流行一种说法,叫“跨界”或“跨界研究”,指的就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而一提到“跨界”研究,在艺术学理论内部产生了一个误解,以为“艺术学理论”就是不同门类艺术之间的跨界研究。这种认识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弄懂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性质、特征、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等所造成的。“艺术学理论”是一个一级学科,它的学科性质就是在其他门类艺术理论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综合地、宏观地和整体地探讨与研究艺术的普遍规律、艺术共性、艺术普遍性和艺术原理等。正如张道一先生所说:“在艺术的各部门,即音乐、美术、戏剧(戏曲)、电影(电视)、舞蹈等分别研究的基础上,须着手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探讨其共性,由个别上升到一般,使之进入人文科学。”[注]张道一:《应该建立“艺术学”》,《张道一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跨界”的问题。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还有“隔行不隔理”,艺术学理论探讨的就是“隔行不隔理”的这个“理”。艺术学理论这个学科本身就要求研究者具备贯通所有艺术门类的研究能力,如果缺乏这种能力就不要轻易去碰它,同时也说明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不是所有人都承担得起的。这个逻辑后面就是要求研究者守候着艺术本身,贯通艺术本身,在艺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所有艺术门类及其艺术形态。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讲,“艺术”(“艺术学”)就是艺术学的理论之“源”。
艺术学的理论本元问题其实不是一个问题的问题。但问题在于一些研究者尤其是缺乏艺术背景的年轻研究者,在进入艺术学的理论研究领域中往往借用自己过去非艺术学科背景的优势,做了真正的“跨界”行为,跨到艺术学的理论研究领域来。在缺乏艺术学知识结构情况下,仅仅套用了“艺术”的概念进行了跨界,表面上看还形成了交叉学科,如艺术美学、艺术哲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伦理学、艺术考古学、艺术经济学、艺术管理学等等,颇为壮观,也很热闹,然而真正与“艺术”相关的研究成果,或者说靠谱点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多是用“艺术”这个概念进行简单地学科嫁接或拼凑。其实,只要留心观察这些“成果”,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嫁接术”还可以把“艺术”的概念,不断地与其他任何学科进行更换成所谓的交叉学科。我们认为这种更换概念的游戏不是艺术学的理论研究,更有甚者把“艺术”作为“流”而不是“源”,反而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作为“源”而不是作为“流”。这种现象并非个别还比较普遍。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艺术”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不像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图案、戏曲等那么具体地有一个明确的对象。这就造成了可以获得一个天马行空地玩起形而上的概念游戏的“时机”,任意贴上“艺术”的标签,窃以为艺术学的“理论”研究就是逻辑推论、假设、论证、文献,从理论到理论不断地“转译”在各种概念中穿梭而行,完全不顾“艺术”这个对象,也不顾艺术事实,其结果必然将自己的知识背景或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作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源”。
脱离艺术或者背离艺术大谈艺术理论,从而还把艺术学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流”而不是“源”,形成源流不清或源流部分的混乱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当下一些“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偏离了艺术学的方向,背离了艺术实践产生的所谓“艺术理论”的根本原理。这是我们应该诘问与反思的问题。
脱离了艺术的所谓理论是无源之水,乃至“流”都算不上。艺术理论来源于艺术实践,这是谁都应该明白的道理。倘若所研究的艺术学的理论“源”“流”不分,或根本不想分清源流而是为了“分地盘、分蛋糕”,置艺术本身而不顾,就会出现如“艺术学的中国经验:2018年艺术学与美学全国论坛”议题上所说的现象:“艺术学理论陷入自我循环”(实际就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游戏);“艺术学理论与真实的艺术经验脱节,不能为具体的门类艺术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三、中国艺术学的理论之源
紧接着上面我们“诘问”的第一个源流问题,我们再回过头来认识中国艺术学的理论之源。同样,上面我们也提到了“艺术”这个概念来源于《二十四史》,下面我们首先来看《二十四史》对“艺术”的阐释与限定的范畴。
《魏书·术艺列传》序云:“该小道必有可观,况往圣标历数之术,先王垂卜筮之典,论察有法,占候相传,触类长之,其流遂广。工艺纷纶,理非抑止,今列于篇,亦所以广闻见也。”[注](北齐)魏收:《魏书》(六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43页。这里《魏书》讲述为何要为“术艺”单独列传,“术”与“艺”尽管在孔子那里就认为是“小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注]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0页。但是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魏书》首先依然将“术艺”列纪于传。《魏书·术艺列传》并对“术艺”作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史臣曰:阴阳卜祝之事,圣哲之教存焉。虽不可以专,亦不可得而废也。徇于是者不能无非,厚于利者必有其害。诗书礼乐,所失也鲜,故先王重其德;方术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轻其艺。夫能通方术而不诡于俗,习伎巧而必蹈于礼者,几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贤,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张渊、王早、殷绍、耿玄、刘灵助皆术艺之士也。观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虚,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状。周澹、李脩、徐謇、王显、崔彧方药特妙,各一时之美也。蒋少游以剞劂见知,没其学思,艺成为下,其近是乎?”[注](北齐)魏收:《魏书》(六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72页。“诗书礼乐”“方术伎巧”“占候卜筮”皆作为“术艺”范畴予以列传。
又《晋书·艺术列传》序云:
艺术之兴,由来尚矣。先王以是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曰神与智,藏往知来;幽赞冥符,弼成人事;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所谓神道设教,率由于此。然而诡托近于妖妄,迂诞难可根源,法术纷以多端,变态谅非一绪,真虽存矣,伪亦凭焉。圣人不语怪力乱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梦以垂文,子长继作,援龟策以立传,自兹厥后,史不绝书。汉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谶术,遂使文成、五利,逞诡诈而取宠荣,尹敏、桓谭,由忤时而婴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虑之一失者乎!详观众术,抑惟小道,弃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经。载籍既务在博闻,笔削则理宜详备,晋谓之《乘》,义在于斯。今录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纪者,以为《艺术传》,式备前史云。[注](唐)房玄龄:《晋书》(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67页。
又《周书·艺术列传》云:
太祖受命之始,属天下分崩,于时戎马交驰,而学术之士盖寡,故曲艺末技,咸见引纳。至若冀隽、蒋升、赵文深之徒,虽才愧昔人,而名著当世。及克定鄢、郢,俊异毕集。乐茂雅、萧吉以阴阳显,庾季才以天官称,史元华相术擅奇,许奭、姚僧垣方药特妙,斯皆一时之美也。茂雅、元华、许奭,史失其传。季才、萧吉,官成于隋。自余纪于此篇,以备遗阙云尔。[注](唐)令狐德棻等:《周书》(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837页。
《北史·艺术列传》也有相同的阐述,不再赘述。宋人郑樵在《通志·艺文略第七·艺术类》收集了历代“艺术”类别:“射”“骑”“画录”“画图”“投壶”“奕碁”“博塞”“象经”“樗蒲”“弹碁”“打马”“双陆”“打球”“彩选”“叶子格”“杂戏格”。[注](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07-1737页。其中关于“艺术”概念称谓有所不同,如“伎术”“伎艺”。但宋代的《通志》将“乐”独立列出,按照“曲”“律”两大部进行分类,并没有放入“艺术类”。而清朝所编《四库全书》“艺术类”则延续《二十四史》“艺术列传”与上述提及的“艺术类”的含义延伸与演变,对“艺术”的容量与内涵做了说明与调整,其“小序”云:
古言六书,后明八法,于是字学、书品为二事。左图右史,画亦古义,丹青金碧,渐别为赏鉴一途;衣裳制而纂组巧,饮食造而陆海陈,踵事增华,势有驯致。然均与文史相出入,要为艺事之首也。琴本雅音,旧列乐部,后世俗工拔捩,率造新声,非复《清庙》《生民》之奏,是特一技耳。摹印本六体之一,自汉白玄朱,务矜镌刻,与《小学》远矣。射义投壶,载于《戴记》,诸家所述,亦事异礼经。均退列艺术,于义差允。至于谱博弈、谕歌舞,名品纷繁,事皆琐屑,亦并为一类,统曰杂技焉。[注](清)纪昀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78页。
同时,我们注意到了“艺术类存目”中有“琴谱正传六卷”“琴谱大全十卷”“文会堂琴谱六卷”“理性元雅六卷”等多部“琴乐”的存目,另还有弈棋存目“弈史一卷”“弈律一卷”“秋仙遗谱十二卷”“射书四卷”“射义新书二卷”,以及“壶谱一卷”“壶史三卷”“五木经一卷”“丸经二卷”“双陆谱一卷”[注](清)纪昀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19-1524页。等有关存目,显然艺术类容量增加,内容广泛。在这里我只想提及一下中国的“围棋”。围棋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属于“艺术”的范畴,结果被西化以后归类到体育里去了,实为荒谬之极。围棋是一种智力活动,包含了极高的文化内涵,是从太极阴阳的变易中演化出来的艺术活动,要有极高智慧和文化修炼才能达到的“弈境”。黑、白二字体现的就是中国文化最高的哲学理念——道,围棋是对《易》的阐释与演示,它与中国传统绘画所说的“夫画者,以水墨为上”是同一个道理。水墨何为上,就在于黑、白水墨的世界昭显的是天地之易变,也涵盖了“墨分五彩”的艺术理念。绘画如此,围棋亦是如此,昭显的是天地之易变。又“文以气为主”、绘画以“气韵生动”为第一要义,中国艺术讲究的是“气”,气聚则生,气散则死。而围棋讲究的也是“气”,无气则死,有气则活,活则生动,山水无气则死或板,故“气韵”要求一定“生动”,动才是活。“气”在宋代成为一个阐释“道”甚至等同于“道”的最高概念,北宋张载(1020-1077)为该方面的代表。张载认为“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正蒙·太和》) 也就是说“气”是宇宙之本体,万物皆始于气,所以“气”在中国各种艺术形态中是同一个道理,故为“同一”。事实上中国文化最高端的思想是同一的,万物于归一。这个“一”可以理解为“道”,只是往下分述或展开时出现的是不同的形式或形态,颇似“理一而分殊”。亦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样,“琴、棋、书、画”便是“一”的“分殊”形式。但是在“琴、棋、书、画”中,至今我们依然把“围棋”拒之在艺术之外,从不把围棋作为艺术的范畴进行研究与探讨,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意味。这只是一例。《二十四史》“艺术列传”中还有很多“艺术”的形态和内容,至今都因为“Art”而拒斥在“艺术”之外,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
我曾在《〈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是建构中国艺术理论学术话语的基础》的文章中指出:“《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是中国艺术理论建构的基础与参照系统。《后汉书》最早提出‘艺术’的概念,自此以后《魏书》《晋书》《北史》《周书》《隋书》为‘术艺’‘艺术’作‘列传’,同时《二十四史》的‘艺术列传’也在不断地变迁,唐代以后《二十四史》中‘艺术列传’几乎没有出现,而是分散在‘文艺’或回到‘方技’中代替了‘艺术列传’。如果我们把《清史稿》列入讨论,在《清史稿》中又恢复了‘艺术列传’。《二十四史》‘艺术列传’包含着经历了概念和内涵的变迁的比较复杂的内容,在彰显中国传统艺术本质特征的同时,亦承载着当今中国艺术理论的源头。”[注]李倍雷:《〈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是建构中国艺术理论学术话语的基础》,《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8年第6期。这基本上是我的一个观点。
结 语
毫无疑问《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等古籍艺术文献是中国艺术学的理论之“源”,尤其是在国际文化视野下更应该意识到这个立本之“源”。在中西艺术交流的汇流中,中国《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的艺术概念和内涵是“源”,而西方的“Art”则是“流”。甚至我认为在使用“艺术”的概念时要与《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的内涵一致,因为中国的“艺术”都是从《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的路径演化而来的,而在指外来的艺术概念,尤其是西方的艺术概念时就用“Art”较好,没有必要把“艺术”与“Art”进行对译,毕竟二者在能指与所指两个方面还是存在很大区别,在阐释与研究中国艺术学的理论时用“艺术”,提及西方的艺术时用“Art”,以区别二者“能指”与“所指”的不同,避免造成语义转换的麻烦,更避免用西方“Art”的概念、内涵和理论体系架构中国“艺术”的概念、内涵和理论体系,否则就会建构成为西方“Art”结构意义路径上和西方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艺术理论”。当今我们要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基础上,要为中国艺术立命,为中国艺术理论立心。
在我们探讨与研究“艺术学理论”时,需要以艺术本元为理论之源,尤其是艺术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跨界)研究时,落脚点一定要站在艺术学的学科位置上,而不是站在其他学科的位置上。要清楚我们在艺术学与其他人文社科的交叉研究中,实际上就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或方法研究艺术学而不是相反。从这层意义上讲,艺术或艺术学是“源”,而其他人文学科则是“流”,否则就会产生“张冠李戴”的误读,不但偏离艺术领域研究本身,而且根本无法解决真正的艺术问题和艺术现象,更不要说用所谓的艺术理论去指导艺术的实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