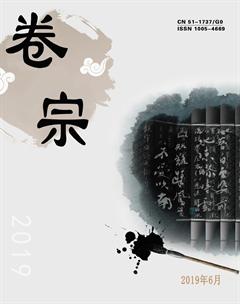庄子“小大之辩”浅析
摘 要:事物在有限的比较对象中可以体现出绝对的大小,但在自然界的无限事物中“小”和“大”只是一种相对的存在,只有打破大小的界限,模糊对大小的认识,忘记自己形体的存在,顺应天地自然之道,形体不动而能游乎上下之间,才能达到逍遥的境界,获得绝对的自由和解脱。
关键词:庄子;小大之辩;逍遥
1 小、大的绝对性
自然界首先展现给人的是大小不一的事物,从客观角度来讲,只要是客观存在的有限物体,总会有大小之别,即大小之绝对性。在这里,我们探讨的“小”和“大”即这种自然界呈现给我们的“小大不一”,即事物本身在体积或面积等外在的大小。
庄子极力推崇大的事物,向往和追求无限之美、“大美”,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其大蔽数千牛,契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仭而后有枝”的栎社树的美,以及对大坤大鹏的羡慕,对大海神树的神往等。
庄子喜欢用大的形象来比喻自己的思想,将大的事物和小的事物放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效果。他习惯于用这种对比手法刻画一种恢宏浩渺的壮美境界,在感官上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从而引发人们对无限之美、“大美”的向往和追求。如《逍遥游》中,庄子塑造了鲲、鹏蜩与学鸠等一系列“极大”和“极小”事物。把大鹏和蜩与学鸠放在同一个时空背景下对照,由此而生发的壮大愈加淋漓尽致。通过这样强烈的对比,庄子提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观点。普通人的寿命就像朝菌和蟪蛄一样,稍纵即逝,在冥灵和大椿树面前,我们更是渺小的不值一提,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更显人类在视野和思想上的卑微渺小,这一点是最为悲哀的。普通人由于受制于自身的先天条件,只能像蜩与学鸠一样满足于“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的卑小境界,而无法突破自身的限制,达到像大鹏那样“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的高远境界。
庄子从“体积”、“力量”、“空间”和“时间”这四个方面来论述小大之别。在这里他极力推崇“大”与“久”的事物,因为大与久是力量、时间和空间的保证,而宇宙是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庄子站在宇宙这一宏大的视角上来考察世间万物,其中含义之深刻不言自明。庄子站在宇宙意识这一理论制高点上鸟瞰整个世界,把大的空间纳到小的空间之中,并从小的空间中领略大的空间,通过一系列的对比和思考,他一方面认识到了人类自身的渺小与局限,另一方面,更是表达了一种突破自身条件束缚的渴望,和对行动自由、搏击九天、达到至大至美的境界的向往与追求。这种大的精神境界,不受客观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是一种超越肉体的的无限性追求。
现实是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无法突破,无法跳出,但我们可以在思想上达到无限与玄远的境界,在心灵上突破出去,让灵魂挣脱现实的桎梏。庄子认为“小”与“大”的区别,在于事物能否突破自身及外在环境的限制,达到一种“逍遥”的境界。
2 小、大的相对性
大与小是相对而生的一对范畴,任何意义上的“大”与“小”都只是相对的,当我们改变参照物时,所有的大与小便不复存在,仅仅从外形来判断大小是不准确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人衡量自然的尺度不是固定不变的,总是会受到自身或环境的影响而做出改变,因此所有的“小”与“大”都是相对的。
所谓小者,是相对于大者而言的。如《秋水》篇中,“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径流之大,两涘渚涯之间,不辩牛马”,这样的景色,是何其奔腾壮阔!以至于河伯在看到自己的领地之后“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但当河伯看到北海若时,“始旋其面目”,望洋而兴叹:“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一个是“不辨牛马”的宽广,一个是“不见水端”的广阔,孰大孰小,相形之下,不言自明。庄子通过这种小大的对比,极力论证万物大小、是非的无限相对性,人的认识的局限性,宇宙天地的无限广大性,以及人生贵贱、荣辱的极端无常性。
“河伯曰:‘然则吾则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是故大知观于远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这一番问答,从事物的“大”、“小”这一性质入手,来说明所谓极小之物,不足以谓之小,极大之物,亦不足以称之大,参照物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事物的大小和境界。河伯以自己的支流为参照,自我感觉世上没有比自己更广阔的事物了,而没有认识到自己所选择的参照对象的局限性,一味骄傲自满,最终贻笑于大方之家。
人作为认识活动的主体,生活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相应地也会受到自身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养生主》中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追求無限的知识,本身就是一个由小到大、不断丰富与认识的过程。追求给予我们的并不是自身所达到的“大”,而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与不足,对自己的“小”有了新的认识。“大”“小”不过是相对的概念,世间万物没有绝对的大,也没有绝对的小,而相对永远是一个无穷的概念。在这种概念的支配下,如果强行对大小做出分辨的话,恐怕惠施的话最为恰当不过:“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3 结语:道通为一,无小无大
世间自然万物都是“道”的产物,在本质上没有大小好坏优劣之分,每一个生命体都有其存在的道理,自然都赋予了它们与众不同的外形和能力。这种自然赋予的东西,在形体上是无法摆脱和超越的。“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摆脱和超越的过程和结果是痛苦且不合理的,违背自然运行的规律无法达到逍遥的境界,只会束缚自己的行动自由,阻碍自身的发展。为了追求超越天然上的某一种“突破”而去改变自己的形态,永远不能达到逍遥的境界,世间万物虽有外形上的小大之别,但只要能满足于自然赋予自己的一切,超越形体,亦能在精神上达到逍遥的境界。
在相对性上讲,事物的体积是没有穷尽的,所以也就没有必然上的“小”,也没有必然上的“大”。天地万物绝对的大和绝对的小是不存在的,从绝对的观念看,大与小是有区别的;从相对的观念看,大与小是相同的,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眼界与胸襟,不局限于小,也要顺乎“道”,不拘泥于大。世间万物,在量上没有穷尽,在时间上也没有休止,因此在根本上也就没有了“过去”和“未来”这种概念,生、死也没有了界限,所有的事物都顺乎自然,在动态的外在世界中保持一种内在的“不变”。打破大小的界限,在根本上模糊对大小的认识,忘记自己以及万物的存在,顺应天地自然之道,无欲无求地遨游于无穷的时间和空间中,洞悉世间的一切而不被世间万物所局限和主宰,这时所有的局限都不复存在,形体不动而能游乎上下之间,在精神上获得绝对的解脱和自由。
《庄子·列御寇》中记载:“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哉!何以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生、死乃至今生、来世都已经无法奈何庄子了,于他而言,形体的存在与覆灭已无任何意义,在精神上,他已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不论往世来生,皆“无所待”,安于生死,脱尘天外,任命逍遥。
参考文献
[1]郭庆藩 撰 王孝鱼 点校.庄子集释[M].中华书局,2016.
[2]郭象 注 成玄英 疏.庄子注疏[M].中华书局,2011.
[3]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作者简介
巩在兴(1994-),男,汉族,山东临沂人,青岛大学,2017级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