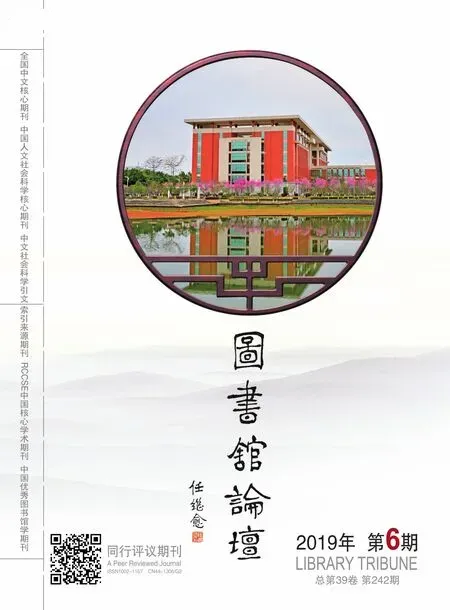民国时期的书籍贸易考察(1912-1931)
耿 达
书籍贸易是近代中国国际贸易的组成部分,虽然所占份额不大,但对中国文化思想界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与理论指导作用。古代中国一直处于文化“高位”,属于书籍“输出大国”,儒家经典著作被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所积极引进,汉唐时期就形成了以儒学、礼制、汉字、律令为主要内容的“汉字文化圈”。而西汉末年开始的“援佛入儒”和明清时期的“耶稣入华”,大量佛教书籍和西方传教士书籍涌入,是中国传统文化引进外来文化的两次高潮,给中国带来了新知识,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发展。1840年以降,随着以坚船利炮作为后盾的西方文化连续强烈冲击,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主动广泛深入地去了解、学习西方,先后经历梁启超所谓的由“器物”到“政体”到“文化”观念的转变[1]。民国时期西方的学术、思想、政治、法律等等各种文化相继全面涌入“相激相荡”[2]。学习西方乃至以西方文化为蓝本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新文化知识分子孜孜不倦的追求。在这一时期主动引进西方书籍,传播西方文化思想成为一股强劲的思潮。学界对书籍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且以中日之间的书籍贸易考察为主,而对民国时期书籍贸易的研究还相当匮乏,系统研究基本阙如。本文以《中国旧海关史料》为核心资料,对民国时期书籍进出口贸易的数额、流向、国别进行考察,试图分析书籍进出口贸易背后的历史意义。
1 书籍进出口贸易的总体考察
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辑出版的《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系统性的详细记录了近代中国贸易发展的状况,包括贸易品的种类、数量、价值、贸易国别、船只进出各港的数量、吨位统计等等,并且各通商海关都有年度贸易报告。《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为研究近代中国贸易提供了详细而精准的资料。本文所考察的书籍国际贸易,在海关贸易记载中主要是以“books,printed”指称,即印本书籍[3]37。1931年前海关贸易以关平银两作为统计值,1932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进行币制改革,进出口贸易之间的货币换算相当复杂且每年都有波动,海关进口贸易主要以金为统计单位,而出口贸易又主要以国币为统计单位,造成数据计量单位的换算难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犯中国东北,以书籍为媒介大肆传播日本文化,进行殖民教育,因此1931年后的书籍贸易呈现出另一番情形。本文主要分析1912-1931年民国上半期的书籍进出口贸易情况。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笔者逐年整理统计1912-1931年20年间中国书籍进出口贸易的整体情况(见表1)。
在书籍进口贸易方面,1912-1931年中国书籍进口贸易的净数额大致呈逐年增长趋势。1912年外洋进口的书籍净数额为38 万多两,后缓慢发展并时有回落;1918年后,进口增速开始加快;1921年发展到86 万多两,是1912年的2.2 倍;1925年后进口增速持续增加,到1931年达到200 多万两,是1912年的5.3 倍、1921年的2.4 倍。根据1912年到1931年中国书籍进口发展趋势(见图1),可大致把民国上半期书籍进口贸易划分为两个阶段:1912-1921年为一个阶段,1922-1931年为一个阶段。两个阶段恰好都是十年,发展趋势也恰好吻合:都是在经历四五年的曲折缓慢发展后迎来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其中,1918-1921年、1927-1931年能够快速增长的缘由有所不同:前一阶段处于欧战(1914-1918)结束后的经济复苏期和新文化运动(1915-1923)高潮期。国际上,“举欧战以还,因而发生之所有状况论之,则本年实为世界各国重整经济之期,故战前原状,间有多少之恢复,胥由此际得之,第处于过渡时代”[3]25。海洋运输开始正常有序,进口来自欧洲的书籍量大幅增加;国内方面,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派”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主张“全盘西化”,大力引进西方文化思想,承载西方文化和知识的书籍得到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大力提倡。鲁迅主张“拿来主义”,更极端者提出要多读西书而不读中文书。后一阶段处于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时期,且中外关系相对前一阶段较为平稳,特别是中美之间关于教育文化方面的交流更频繁,来自美国的书籍数额占这一时期最大的进口额。

表1 1912-1931年通商海关书籍进出口贸易净数额统计 (单位:关平银)

图1 1912-1931年中国书籍进口趋势图
当时进口书籍的主要通商海关有上海、大连、天津、广州、厦门、南京、汉口等,关口呈沿海沿江分布,这七大海关是中国各区域的交通枢纽和经济文化中心(见表2)。

表2 1923-1931年主要关口书籍进口贸易统计 (单位:关平银)
1923年上海书籍进口额占全年全国海关书籍进口总额51%,充分说明上海在全国中的文化和经济中心地位。上海自开埠通商后迅速崛起,到民国时期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与纽约、伦敦、巴黎等一起构成世界经济文化中心。1931年主要通商海关中书籍进口的比例为上海42%、大连26%、天津6%、广州5%,南京、汉口、厦门各占1%(见图2)。上海牢牢占据着中国贸易地位的头牌,但贸易份额有所下降,大连书籍进口贸易发展迅速,逐年增长。南京和汉口作为黄金水道长江上的两大城市,书籍进口份额变动不大,但价值数额增幅较大。

图2 1931年中国主要关口书籍进口比例
广东作为中国对外通商贸易的桥头堡,是最先与西方国家进行对外贸易的地区。根据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出版的《统计月刊》显示,当时广东省的通商海关多达8 个:广州、汕头、九龙、拱北、江门、三水、琼州和北海,是单个省辖区中最多的[4]。1931年广东省各通商海关的书籍进口总额达335110 圆,大约是1923年的4 倍。其中广州作为广东省的省府所在地和最大对外贸易港口,一直占据广东省书籍进口贸易的最大份额,1923年占广东省37.8%,1931年上升到50.4%(参见表3)。
在书籍出口方面,1912-1931年的20年间,书籍出口走势大致与进口书籍走势相同(见图3)。1912年书籍出口价值为223512 两;1913年、1914年书籍出口呈直线增长,但1916年后急剧下降,1917-1919年处于低潮期,原因系正处于欧战最惨烈阶段,与欧洲贸易处于停滞状态等;随后因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1920-1923年快速回升;1924-1926年不断回落,主因是军阀割据,战乱不断,阻碍了对外贸易发展;1927

表3 1923-1931年广东省洋印本书籍进口值统计(单位:国币)

图3 1912-1931年中国书籍出口趋势图
注:根据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1935年编《统计月刊》整理。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书籍出口贸易开始繁荣发展,到1929年书籍出口价值达到834276 两,为20年内的最高值,是1912年书籍出口数量的3 倍、书籍出口价值的3.7 倍。
从价值上看,中国书籍的出口远远少于对外文书籍的进口。20年间,中国书籍的出口总额为1034 万余两,而中国对外文书籍的进口总额达到1628 万余两,出口书籍价值占进口书籍价值的63.52%。并且每年的书籍贸易都处于入超状态,20年书籍贸易的入超总额达593 万余两,相当于1912年书籍出口价值的2.66 倍。在书籍出口和进口环比上涨的情况下,出口价值始终低于进口价值,而且入超额环比也同时上涨,在1931年入超额达到128 万余两,为历年最高。这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总趋势是一致的。从1871-1931年,中国国货出口额虽然也呈增长态势,但无法与洋货进口的迅猛增长速度相提并论,除1871-1873年保持着微弱的出超额,1881年以后一直处于入超地位,且1911年后入超额越拉越大(见表4)。这种发展情势恰如民国时期的陈重民所说:“我国进口贸易常呈逐年发展之趋势,盖进口货值(金银不在内)在光绪十二年(1886)以前,每年至多不过八九千万两,辛丑合约成立以前,至多亦不过二万数千万两,辛丑以后,内地风气渐开,交通日便,洋商深入内地,争相推广销路,洋货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而进口货值逐陡形增多。民国成立后增加尤巨,虽民国三年至民国七年间,受欧战影响,稍形停滞,然世界和平后,旋即恢复增加之步骤。”[5]因此,通过1912-1931年间的书籍国际贸易的整体观察,可以发现中国一直是入超状态,在整个国际文化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对西方书籍的需求不断扩大却表明进口书籍、引进新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世界、改造中国的一种必要途径,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一种知识储备。

表4 1871-193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净值[6](单位:百万元)
2 书籍进出口贸易的国别考察
通过书籍进出口贸易的国别考察,是了解当时世界上知识的分布、中国的价值取向及其国际地位的一张极好的“文化地图”。笔者选取了与中国有书籍贸易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有些国家和地区虽然也与中国有书籍交易,但贸易价值数额太少,对于考察当时中国的书籍贸易没有多大影响,故不计。
中国内地民国时期书籍进口贸易的来源国家和地区主要有亚洲地区的新加坡、日本、朝鲜、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欧洲地区的英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比利时;美洲地区的加拿大和美国。其中,香港和澳门作为中国固有的领土,在近代以来分别沦为英国和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地,承担着贸易中转站的媒介作用,香港的地位尤为突出。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后,香港成为英国进行贸易的驻地,并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香港在近代中国内地书籍进口贸易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到民国时期基本维持在书籍进口贸易的第四位。
从表5 和图4 来看,民国时期中国内地书籍进口的主要来源地区是西欧、日本和美国,其中尤以日本、美国、英国最为突出。从1912年到1931年这20年间,日本、美国、英国、中国香港基本维持在前四位,除1913年的英国,1921年、1923年和1924年的美国短暂的位列第一外,日本一直独占鳌头。20年间中国进口日本书籍的总额达680 万余两,是美国(386 万两)的1.8 倍,英国(253 万两)的2.6 倍。

表5 民国时期通商海关由外洋进口书籍之来源统计(1912-1931)(单位:关平银)

图4 1912-1931年中国内地图书进口主要来源国家和地区趋势图
日本、美国、英国在中国书籍进口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反映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国对日本、美国、英国的重视。英国、美国是20 世纪上半叶的文化经济大国,领导国际文化贸易发展,在中国有着极大的势力范围和贸易份额;民国建立后,英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成为中国学习借鉴的典范,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英美各种思想文化被介绍到国内,英美文化一时成为国民追求的时尚潮流。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有着地缘上和文化交流上的优势,且在中国势力越来越膨胀。中国书籍进口来源地区的具体贸易份额1913年为英国23%、日本21%、美国17%,1923年为美国34%、日本26%、英国20%;1928年为日本54%、美国16%、英国12%。日、美、英三国占据中国书籍进口贸易的绝对优势地位,且这三国占比和越来越大,一度超过80%。
在中国书籍进口贸易的国家中,俄国地位变化值得关注。俄国1912-1915年一度在中国书籍进口贸易中进入前五位,份额维持在10%左右,但是在1918-1920年、1927-1931年又两度急剧萎缩,份额跌破1%。两度急剧萎缩的主要原因是战乱,刚刚结束一战后俄国就陷入了国内战争,爆发了十月革命;而1927年以后,日本逐渐把俄国势力排挤出中国东北,俄国失去了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相对优势。
中国书籍进口贸易的主要来源国家是以英国、美国和日本等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体现了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断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情境。那么,中国书籍出口贸易主要是流向哪些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何种景象?
1912-1931年,中国内地书籍贸易出口的国家及地区主要分布在东亚,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朝鲜、俄国(太平洋各港);东南亚,包括安南(越南)、暹罗(泰国)、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爪哇)、印度、菲律宾;西欧,包括英国、德国、法国;北美,包括加拿大、美国。20年间,向世界各地输出书籍的总额前十位分别为中国香港5032226 两、新加坡2449792 两、日本770492 两、爪哇446552 两、美国370602 两、朝鲜266849 两、暹罗249991 两、安南165966两、中国澳门165636 两、俄国(太平洋各港)95641 两(具体见表6),其中多为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书籍出口的国家及地区多为华人华侨聚集地。

表6 民国时期通商海关书籍出洋的国家和地区来源统计(1912-1931)(单位:关平银)
在全球书籍贸易中,选取民国时期在中国对外关系和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日本、朝鲜、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七个国家作为进出口贸易的比较分析,见表7。中国的书籍贸易在对这七国中都处于入超地位,入超贸易额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朝鲜的入超额最少,但也达到了20876两。这进一步说明,民国时期,中国在对外书籍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对欧美的文化需求远远大于欧美对中国的文化需求,日本、美国、英国对中国文化影响较大。

表7 1912-1931年中国书籍进出口贸易主要国家对比分析 (单位:关平银)
3 结论与探讨
书籍是文化的最集中体现,书籍是文字、造纸和印刷术这三大发明的综合成果,自古以来就是知识的最佳载体。书籍作为贸易对象,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性:消费时间长、受惠面广,对学术、思想具有深层次的影响,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命运。书籍的国际贸易,实质上是知识在国家间的流转。“书籍贸易之类文化事业,虽然不像政治、军事事件那样扣人心弦,也不像交通、产业等经济事业引人注目,但却是社会变迁的基础”[7]。书籍贸易的起伏是知识流的大小、流向的主要标志。古代中国是东亚乃至世界的文化中心,很长时间一直作为文化输出的大国,经史子集等古典书籍源源不断的流向朝鲜、日本和东南亚诸国。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步步溃败,“千年未有之变局”使晚清中国不得不面向西方,文化优势的心理防线也一步一步被冲垮。于是民国肇始,中国开始主动地全面向西方学习,政治、经济、文化都以西方为模板。到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论”更是甚嚣尘上。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成为近代中国现代转型发展的必要课程。
随着近代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知识、信息和娱乐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文化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作为国际文化贸易的重要构成部分,书籍是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消费品,它能够提供信息和娱乐,进而形成群体认同并影响文化行为。书籍贸易具有普通商品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双重属性,书籍在产业化和世界范围内销售的过程,被不断复制并附加了新的价值。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国书籍进出口贸易的考察,可以勾勒出这一时期国际书籍贸易的基本特征和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基本情况。
首先,国际书籍贸易市场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发展速度来看,民国时期中国书籍引进和输出发展的不平衡,且贸易逆差呈不断扩大趋势。根据统计,中国书籍进口价值额从1912年的388751两发展到1931年的2047212 两,20年间增长了5.3 倍,而中国书籍出口价值额从1912年的223512 两发展到1931年的766608 两,20年间只增长了3.4 倍,书籍贸易逆差1912年为165239 两,1931年扩大到1280604 两,20年间增长了7.8 倍。巨大贸易逆差的背后,不仅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书籍贸易存在着经济赤字,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国书籍贸易输出与引进两者之间存在着的“文化赤字”。经济赤字体现的是贸易的弱势地位,而“文化赤字”体现的则是文化屈从态势。二是书籍贸易区域结构处于明显失衡状态,书籍的引进和输出对象呈现过度集中化现象。民国时期中国书籍贸易引进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其中以美国、英国和日本三国的书籍贸易引进最多,长期占所有引进书籍贸易的一半以上。而书籍贸易输出却主要集中在亚洲几个国家和地区,1912-1931年的20年间,向世界各地输出书籍的总额前十位分别为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爪哇、美国、朝鲜、暹罗、安南、中国澳门、俄国。可见,民国时期中国内地主要向西方国家和地区引进书籍,而书籍的输出则主要局限于东亚东南亚一带的汉字文化圈内,在西方主流文化市场的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三是书籍贸易的引进和输出在题材上有很大区别。民国时期中国书籍贸易的引进题材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地理、自然、哲学等各个领域,无论是畅销书还是专业性书籍都有较大的增长,相较而言民国时期中国书籍贸易输出的内容和题材就略显单一,主要是以经史子集为主的传统文化典籍。国际书籍贸易的竞争力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国际书籍贸易的不平衡性问题的背后,深刻地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文化输出的弱势地位。
其次,国际书籍贸易背后显现了知识流向和文化传播的图景。文化具有独特的渗透力,书籍传达着观念、价值和生活方式,是极具个性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书籍是人类知识交换和国家文化沟通的一种有效工具,书籍贸易的价值超过了其商业价值,与其他货物贸易相比,它会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输入国的文化消费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书籍的流向反映了20 世纪上半叶世界上知识的分布状态。整体上,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个知识洼地,而以美国、英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成为知识高地,中国向其进口书籍来引进新知。民国时期书籍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尤其是促进了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快速传播。1912年至1931年中国书籍贸易进出口的情形和当时外文书籍翻译的情况都共同显示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文化传播对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日本的法律书籍对民国时期中国现代法律的构建发挥了关键作用。“民国仅仅继承了大清帝国为数有限的法律文献,而西洋法律书籍又无法读懂,这便很自然的转而求助日本人大部分用汉字写成的西洋法律著作。很多人东渡日本研习法律,因而中国的法律学校不久就被从日本学成归来的中国人所把持。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为例,它是一所拥有700 名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律学学生的学校。今年(1923年,作者注)5月,该校校长讲,学校所用教材的70%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有60%的教员是留日学生。”[8]而美国的现代教育思想和管理制度对民国时期中国的学校教育有着重要影响。罗家伦指出:“近二十年来有一件可伤心的现象,就是美国的普通教科书,充满了中国的学府,教授讲的美国教科书、学生读的美国教科书、学者书架上能常发现的也大都是美国教科书。”[9]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类的书籍非常受欢迎,但是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更多的是稗贩外来学说。正如当时郑天心慨叹所言:“在社会科学界里要得一本敢依正义与事实来写的一本书简直找不到。中国社会科学固然还脱不了稗贩西洋的学说,然而近来稗贩的种数也够多了。”[10]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知识界,主要是奉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为圭臬,“在此学术荒芜的中国,新知识的来源,总不外乎东西两洋。即如最近喧传一时极度时髦的计划经济论,就多半是从这两地的出版品中转译过来的。其来自西洋的,称为计划经济;其来自东洋的,叫做统制经济”[11]。民国时期日本长期位列中国国际书籍进口的第一名,说明当时中国对日本的文化模式有着急切的需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一心以日本为范本筹谋传统中国的现代化。梁启超在《读日本书目志数后》认识到:“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书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12]虽“东学不如西学”,但为“力省效速”,“译西书不如译东书”。梁启超认为:“日本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初具矣,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13]日本成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窗口和最便捷的通道。与晚清时期知识引进出自“富国强兵”的目的不同,民国时期知识引进更加注重对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学习和借鉴。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在引进新知、学习西学中经历了如下转变:“在知识层面,从最初对科学技术类的注重和单纯引进,发展为对社会科学、哲学类以致文学艺术类的翻译和大力阐扬;在思想层面,从最初的通经致用、中体西用过渡到中西融合、中西汇通。”[14]
最后,国际书籍贸易也展现了近代中国不断探求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书籍贸易承载了一个社会的理想寄托,不论是国家权力机构还是精英知识阶层,都力图通过这种形式塑造理想的社会与未来民众[15]。为促进书籍贸易和推广现代教育,1910年上海书业商会呈请税务处,请求凡出口进口书籍无论在中国或外国印刷,一概免税,后由税务处核准:“以后中国旧书籍图画出口,应按值百抽五征收税项,其余一切新书新图,无论运至外国,或由此口运至彼口,一概免税。”[16]书籍贸易进出口税费的调整直接促进了民国时期国际书籍贸易的发展。然而,在根本上,民国时期国际书籍贸易发展的基本动力是近代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对现代知识体系的价值认可与强烈需求,其发展又得益于三种进步力量的良好互动:一是近代新的国民教育体系提供了时代的大平台;二是由知识分子群体组成的强有力的翻译编辑队伍的推动;三是新兴出版业的热心投入。近代中国在现代化的转型道路上已经步入了全面学习、整体变革的阶段,这种新的趋向不仅对现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显示中国知识分子日益了解到要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不能全靠军事和技术的知识,还须具有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综合知识[17]。张灏指出,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中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造成了特别的影响:一是构成20 世纪文化发展基础建构的启端,二是加快了公共舆论的展开[18]。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书籍贸易所引进的书籍类型与知识体系也不断发生变化,但是传输健全合理的知识体系、培养科学精神,始终是民国时期书籍国际贸易的使命。书籍贸易所承载的文化知识传播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性传播媒介”,它带来了文化知识的引进,成为促进文化发展的“基础建构”力量。这时期最为显著的事例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大量关于“科学”与“民主”书籍的引进和翻译,促进了这一时期各种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发展转型。“输入文明”“启迪民智”是民国时期书籍贸易的时代使命,书籍贸易发展所带来的现代知识体系对于涵化与培育新文化、新市民、新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