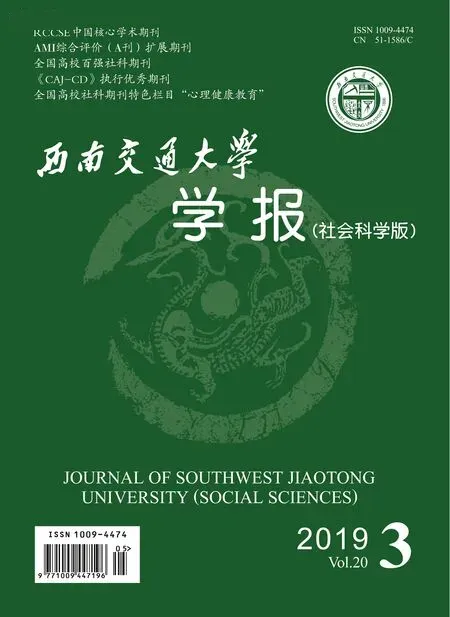吴世尚《楚辞注疏》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成就
(南通大学 楚辞研究中心,江苏 南通 226019)
吴世尚是清初著名楚辞学家,其《楚辞注疏》是一本颇为重要的清代楚辞学注本。但是,目前学术界只有王泗原、毛庆、竹治贞夫等学者曾引用过其部分观点,而对吴世尚本人及其《楚辞注疏》均尚未作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依据目前所见的有关资料,试图对吴世尚《楚辞注疏》的注疏方法与学术成就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吴世尚,安徽贵池开元乡人,字群玉,后改字为六书。其生卒年,据清人章永祚《南湖集钞》记载:“康熙己未春……曹勺子在馆,亦善余,顾群玉曰:‘此子年十龄……’”,“今白头相对,年俱七十矣”①。由此可以推知,吴世尚应当生于康熙庚戌年(1670),卒于乾隆己未年(1739)之后。吴世尚幼而颖异,曾拜有明逸民曹勺子为师,“年十龄,遍诵五经,凌凌露爽”①。清人章永祚亦言其“弱冠问字于余,则已举所谓十三经者,无不熟复贯通”①,后“迨群玉补博士弟子员,而勺子已殁。癸酉乡围,群玉垂得复失,归而益肆力于古”①。
吴世尚“博雅而刚介不阿”〔1〕,“名其居曰易老庄山房”〔1〕,以手抄书成帙,昼夜蒲编,“尝手录十三经,又聚砚田所得,购廿一史,坐而诵之。其学无所不窥,旁及圭臬,虫篆之类,靡不通晓,所著书甚多”①,以至“指腕力弱。行年五十,不得已以左手作字,矻矻不少休”①。晚年,吴世尚开始授徒四方,曾在章永祚家塾训课,“儿曹、白头,师弟相对一堂。授受渊源,延于两世”①。古稀之年,又“近故居,筑书屋三楹,授徒课子。工既疏竣,得诗三十首”①。
吴世尚“食饩郡庠,未贡而卒”〔1〕,一生著述颇丰,自言:“余生平鲜他好,所沉酣者,五经四书而外,左、老、庄、骚其最也”①。据《贵池县志·艺文志》记载,吴世尚留有多部著作:“《易经注解》见旧志续编,《老子宗旨》见通志,《春秋义疏四十卷》见本集,《庄子解》、《楚辞注疏》均见旧志续编”〔1〕。此外,吴世尚还更定了朱子《周易大全》,并著有“《周易本义启蒙通刊》十四卷附《周易经》二卷”〔2〕。
其中《楚辞注疏》成书于雍正丁未(1727)冬十月庚子,最早由清雍正尚论堂刊刻发行。吴世尚在撰作此书时,自言“楚辞传本字句不同”〔3〕,故此书“止以朱子集注本为定”〔3〕。但实际上吴世尚并不拘囿于朱熹的观点,云:“朱子提挈纲维,开示蕴奥,而于波澜意度处,尚多略而未畅”〔3〕。因此,吴世尚在注疏楚辞时,怀有“补前贤所未备”〔3〕的目的,着力于对楚辞文本义理、结构章法及创作特色进行分析,最终形成了其独特的楚辞注疏方法。
一、儒道并采——评析文本义理
清初社会趋于安定,“统治者开始大力提倡性理之学,以图恢复、弘扬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4〕,忠孝节义观念再次兴起。一些诞生于新朝的学者致力于以儒家的中正至孝之道来著书立言,企图淡化民族矛盾。同样,楚辞研究也受到了这一学风的影响,如李光地有《离骚经九歌解义》,方苞有《离骚正义》。
吴世尚也将儒家义理与楚辞文本相结合,认为楚辞的“核心还是在于君臣大义”〔5〕。同时,吴世尚还明显受到了钱澄之“庄屈无二道”〔6〕观念的影响,不仅以儒论骚,而且以庄解骚,令人耳目一新。
(一)以儒论骚,钩玄提要
1.探析作者归属
吴世尚认为楚辞是对儒家经学的传承,云:“《诗》《骚》一乎?曰若父与子”〔3〕,“天下有大戒二,离骚兼之矣”〔3〕。关于《大招》的作者归属,历来存有疑惑。
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认为《大招》的语言风格“平淡醇古”,与宋玉大、小言赋中的景差语言风格相似,由此判断《大招》为景差的作品。朱子云:“今以宋玉大、小赋考之,则凡差语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闲退,不为词人墨客浮夸艳逸之态,然后知此篇,决为差作无疑也。”〔7〕林云铭《楚辞灯》则认为《大招》“乃尊君之词也”,云:“篇中段段细叙,皆是对怀王语”〔8〕,“至末六段说出亲亲仁民,用贤退不肖,朝诸侯,继三代”〔8〕,“此皆帝王之事”〔8〕。
吴世尚继承了林云铭的观点,并从儒家“父子君臣”大义的角度对朱子之说进行了辩驳,判定《大招》的作者为屈原,角度十分新颖。其云:“林西仲以为招怀王,尤属细心巨眼,而其文亦另是一格,故说者相传以为景差也。”〔3〕吴氏认为《大招》的文风平淡醇古,正说明屈原“以臣招其君,立言自有体要”〔3〕,故而“语语典实,绝无荒谬怪癖之谈”〔3〕。言下之意,此为屈原招其君无疑。
此外,吴世尚还进一步引用儒家“中庸”之道中的“治国”主张对此观点进行论述,认为《大招》末尾陈述“始以保身,次以亲亲,次以敬大臣,次以子庶民,次以柔远人,次以怀诸侯”〔3〕及其所说“正始昆,赏罚当,尚贤士,国家为,尚三王”〔3〕,正是对应了《中庸》里治理国家的九经,即:“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9〕吴世尚认为:此则“固人君之所事事”〔3〕,“非人君不敢当”〔3〕,即《大招》应是招怀王之魂。
由此,吴世尚最终肯定《大招》的作者是屈原,而非景差。后世徐仁甫也认同《大招》为屈原招楚王魂魄之作,曰:“末段谓赏罚当,尚贤士,禁苛暴,曲终奏雅,必有所制”〔10〕,“则非招君王之魂不可”〔10〕。
2.探讨篇名题义
吴世尚以儒学义理来解读楚辞,还反映在对楚辞篇名题义的解读中。如《天问》一章,王逸认为“天问”意为“天尊不可问”,乃是屈原被流放以后仰观庙堂壁画之作,云:“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诡谲,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疲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11〕后世学者大多认为注《天问》者,莫古于王逸《楚辞章句》,且汉鲁灵光殿石壁及文翁礼殿图皆有先贤画像。因此,王逸之说广为流传。
吴世尚对王逸之说明确表示反对,并以儒家“中庸”之道为根据对《天问》的篇名题义重新进行了梳理。吴世尚认为《天问》体现了屈原的良苦用心,此篇“是则命问而实自答矣”〔3〕,“其名天问者,言天下事,原有不可究问者也”〔3〕,而“非倒其文而问天也,亦非天尊不可问也,更非见庙宇图画,呵而问之,以泄愤懑也”〔3〕。
吴世尚从儒家学说的角度入手,援引《论语·述而》中“子不语怪力乱神”一说,将《天问》解释为“是则命问而实自答”〔3〕。吴世尚认为屈原创作的《天问》,奇特诡谲,篇中多用“曰谁,曰何,曰孰,曰安,曰焉,曰胡”〔3〕之词,乃是意指此“诸云云者,是皆所谓怪力乱神,圣人之所不语者也”〔3〕。言下之意是屈子既为圣贤,就不会轻易谈论神怪之事,而是讲究中庸之道,以人道为修行准则。而《天问》中离奇诡怪、荒诞不经的语言,正表现了屈原对古今以来“传道之言”的质疑。因此,《天问》一篇表面上是屈原在发问,而实际上是自答之语。由此,吴世尚认定《天问》乃是屈原被楚王放逐以后,思考“天地之内,古今以来,有多少可知不可知,可信不可信”〔3〕之事所作,故而“其名天问者,言天下事,原有不可究问者也”〔3〕。
应该说,吴世尚的观点颇有见地,也符合《天问》的大旨。清代学者戴震的观点就与吴世尚颇有相似之处,他说:“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人之智所能测者,设难以疑之”〔12〕。郭沫若在《屈原天问的释文》一书中也认为《天问》表现的是屈原对天地传道之事的怀疑,云:“屈原把自己对于自然和历史的批判,采取了问难的方式提出。他是受着强烈的创造欲所驱遣,存心作出一首奇特的诗”〔13〕。此外,日本学者西村时彦《屈原赋二卷》对吴世尚的观点也较为认可,曰:“是亦一说也”〔14〕。
3.探索主旨大义
再如《渔父》,吴世尚也认为此篇表现出了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云:“所以既赋《离骚》,又作《天问》,而《九歌》《九章》《远游》《招魂》诸篇,一而再,再而三,虽其缠绵悱恻,实皆本于忠君爱国之心”〔3〕。
《渔父》是屈原的绝命之词,对于此篇的章旨,后世学者常持有不同的观点。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渔父怜悯屈原的忠贞爱国,因此以全身远害之道前来相劝,云:“江汉之间,多高蹈之士,隐于耕钓,若接舆、庄周之流,皆以全身远害为道。渔父盖其类也,悯原之忠贞将及于祸,而欲以其道易之”〔15〕。林云铭《楚辞灯》则认为渔父与屈原之间的对话实际上表现出了渔父对屈原言行的不以为然,指出:“篇中有‘葬于江鱼腹中’之语,意已决矣”〔8〕,“是渔父以不入耳之谈来相劝勉也。及自言其志,而渔父亦以为不然,长歌而去。此时,举世总无一可语之人,虽欲不自沉,不可得矣。此通篇之大旨也”〔8〕。
对于林云铭的观点,吴世尚并不赞同,认为“是亦乌足与论文章之妙哉”〔3〕。然而,对于王夫之的看法,吴世尚则表现出了明显的继承性,并援引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对其作了非常独到的补充和说明。吴世尚认为渔父以“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及至“鼓枻而去”来劝谏屈原,并非是“以为此皆不入耳之言,来相劝勉”〔3〕,其实是因为他深知世人皆崇尚投机取巧,所以对屈原因忠君爱国而被流放表示深深的同情,劝谏屈原应当避祸远害,保全自身,云:“然而曰‘何世俗之工巧’、‘遭谗人之嫉妒’、‘虚惑误又以欺’、‘敖朕词而不听’,则小人之闻而侧目,捃摭而媒蘖其短者,固不知其几矣。此渔父之所为深惜,而欲其稍自沉晦,以全真而保天年也”〔3〕。此外,吴世尚还指出渔父实际上是屈原的知音,十分赞同屈原秉持的君臣大义。渔父和屈原的对话,道尽了屈原一生的无可奈何之处。因此当屈原“自度性不可易,俗不可混,道不可枉”〔3〕,最终只能选择以死自誓,“宁赴湘流而死,不从世俗而生”〔3〕时,渔父鼓枻而去,“亦未尝不心许其是”〔3〕。他认为:“屈原,一国无知己,惟詹尹、渔父庶几其有同心。故一生不可奈何之处,惟于此二人发之,而二人之惓惓于三闾,亦不啻空谷跫然之音也。”〔3〕
应该说,吴世尚从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角度出发,对《渔父》的主旨大义进行探析,对前人的观点进行辩驳和补充,颇具参考和借鉴意义。
(二)以庄解骚,剖析奥义
“庄骚”并称,始于韩愈。庄子和屈原颇多相似之处。陈子龙《谭子庄骚二学序》言:“二子所著之书,用心恢奇,呈辞荒诞,其宕逸变幻,亦有相类。”〔16〕吴世尚亦同时注有《庄子解》,并常常试图将庄文和楚辞进行比较,以阐明楚辞篇章的文本义理。
如《招魂》一文变幻离奇,对于此篇主旨大义,后世学者多有不同的理解。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招魂》是宋玉所作,目的是招其师屈原的魂魄,云:“《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7〕,“荆楚之俗,乃或以施之生人,故宋玉哀悯屈原无罪放逐,恐其魂魄离散而不复还,遂因国俗,托帝命,假巫语以招之”〔7〕。黄文焕《楚辞听直·凡例》则认为《招魂》为屈原所作,云:“太史公曰‘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而又似亦原之自作。则存《招魂》,亦并存原耳”〔17〕。黄文焕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后世“林西仲、蒋涑塍皆祖其说”〔18〕。林云铭在《楚辞灯》中补充道:“世俗《招魂》,皆出他人之口,不知古人以文滑稽,无所不可。且有生而自祭者,则原被放之后,愁苦无可宣泄,借题寄意,亦不嫌其为自招也。”〔8〕
吴世尚继承了林云铭的观点,认为林云铭辨别《招魂》为屈原自招其魂,“理信而词可征”〔3〕,并引用《庄子·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对其进行了精妙的解读。吴世尚指出《招魂》一篇“变幻离奇,有镜中之镜,影外之影”〔3〕,与《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有异曲同工之妙。关于“庄周梦蝶”,吴世尚在其《庄子解》中云:“庄周梦为蝴蝶,蝴蝶复为庄周。周与蝴蝶两无所在,如影与形,谓之二,固不可。谓之一,亦不可”②。吴世尚用“庄周”和“蝴蝶”来代表“屈原”与“魂魄”,认为屈原与魂魄交织繁密的关系正好可以通过庄周与蝴蝶的“如影与形”来体现,云:“奚为通篇纯是自诳之语?《庄子》有之矣。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此即《招魂》之机轴也。盖既以魂为非我而招之,而魂亦绝不知有我之为我此”〔3〕。
由此,吴世尚最终肯定《招魂》一篇实际上是屈原自招其魂之作,是屈原“不得已而算出一法,托己言于人言,借正面作反面”〔3〕,“撰为巫阳招魂一篇文字”〔3〕。吴世尚的这一观点十分新颖,颇能揭示《招魂》的主旨义理。毛庆在《楚辞著作提要》中评价他:“发现庄周梦蝶与屈子《招魂》在内在精神方面有相通之处,可谓有见解。”〔5〕
二、时文之法——评点结构章法
“时文”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北宋科举业,盛名曰时文,而文之不以应科举者,乃自目为古文”〔19〕。明清时期,“时文”特指八股文。八股文在内容上讲求“代圣贤立言”〔20〕,形式上讲究起承转合,相对成文,故又称八比文、制义、四书文。清初朴学兴起,辞赋注家讲究笃守师法,常以八股文的程式技巧来解读古文,如林云铭《楚辞灯》、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等。
吴世尚早年参加过科举考试,对时文的章法颇为熟悉。受林云铭《楚辞灯》的影响,吴世尚也竭力运用时文之法来梳理楚辞篇章的层次结构。洪湛侯在《楚辞要籍解题》中评价他虽是“以分析时文的方法来论析作品”〔21〕,但也因此得以“将文义阐述的较为明晰”〔21〕。
(一)起承转合,注重章法
1.承上起下,衔接紧凑
对楚辞文脉的解读,“早在宋代便已萌芽”〔22〕,到清代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清代林云铭以时文之法解读楚辞的组织脉络,有开创之功。吴世尚继承了林云铭的做法,注重梳理楚辞中的过渡句式和非过渡句式,以指明上下文之间的线索脉络和承接关系。
第一,重视提炼楚辞篇章中的过渡句。吴世尚在注疏楚辞时,既重视篇章中局部内容的承上起下,也重视文章整体的承接和传递,并每每使用“此段以上……此段以下……”“收上文……起下文……”等句型加以总结概括。如《招魂》中“室中之观,多珍怪些;兰膏明烛,华容备些”,吴世尚认为这两句有贯通文章局部文意的作用,注曰:“二句承上起下之词”〔3〕,前者乃承接上段言室内珍宝极多,后者乃引出下段对美人的描写。又如《哀郢》:“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吴世尚则将其置于全文中来分析,认为这两句有串联全文的功能,言“此二句尚承上文,指百姓而言。以下乃原自言也”〔3〕。
第二,重视那些虽不具有过渡性质,但与上下文承递有重要关联的句子,如“承上”句和“起下”句。吴世尚在注解具有承接上文文意功能的句子时,常常会用“此承”“此总承”“承上而言”等句式加以论述;而在注解具有承接下文文意功能的句子时,则往往会用“此起下文”“此以下”等句式。
(1)承上。《楚辞注疏》中的承上可以分为两部分:承接本篇章中的内容;承接其他篇章中的内容。如《天问》“簒就前续,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吴世尚注曰:“此承上文变化而言”〔3〕。又如《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吴世尚注曰:“此承上篇(《湘君》)‘夕弭节兮北渚’而言。湘君自江皋而至北渚,则湘夫人亦必与之俱来,而降于北渚也”〔3〕。
(2)起下。“起下”可以分为“开头处总领全文”和“中间承接下文”两种。如《大司命》首句“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令飘风兮先驱,使冻雨兮洒尘”,吴世尚认为此处有总领全文的作用,注云:“此以下,皆为大司命语少司命之词也”〔3〕。又如《远游》“欲度世以忘归兮,意姿睢以抯挢。内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娱以淫乐”,吴世尚仅注明此句与下文的关系,云:“此起下文临睨旧乡之意”〔3〕。
“清代八股文在抓住题目中心之后,即按八股程序,起、承、转、合构成全文”〔23〕,吴世尚在注楚辞时,极力运用时文之法梳理楚辞文脉。虽稍显拘谨,但也足以“使读者一气贯注,不复隔阂”〔3〕,为后世学者研究楚辞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方向。
2.统一章法,相对成文
明清时文讲究股与股之间前后承接、两两相对,即“柱分两义,总须使但看一比则偏,合看两比则全”〔24〕。如《九歌》一章,吴世尚即运用这种分股成对的技巧,来分析《九歌》内部篇章的相互关系,认为“《湘君》《湘夫人》及大、少《司命》,虽各有乐章,而意相承顾”〔3〕。
《湘君》《湘夫人》上下两篇,前后相承,互为对应。“湘君,尧女娥皇”〔3〕,湘夫人为“尧女女英”〔3〕,二者既是舜的妃子,也都是湘水之神。《湘君》《湘夫人》不仅在内容上都表现出了湘水之神来与不来、犹豫不决的场景,而且叙述结构相同,文意上前后相接,《湘夫人》中“数句大指与前篇同”〔3〕。如吴世尚在《湘君》第一句“君不行兮夷犹”后注云:“通篇总止写此一句之意”〔3〕,也在《湘夫人》开首“目渺渺兮愁予”后注云:“通篇总止写此一句”〔3〕,结构上两两相对。又如《湘君》中有“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湘夫人》中有“帝子降兮北渚”,吴世尚认为前者乃是湘君鉴我心诚而前来享祀的意思,云:“此则言湘君鉴余忱,而有以歆余祀”〔3〕;后者乃是承接上文,表湘夫人随湘君前来之意,云:“此承上篇‘夕弭节兮北渚’而言。湘君自江皋而至北渚,则湘夫人亦必与之俱来,而降于北渚也”〔3〕。
“二司命”也是如此,前后文意两两相承。由此,吴世尚又将这种分股的结构技法扩大到了《九歌》的整体研究之中,云:“《九歌》首二章莁(当作‘筮’)日斋沐,末章成礼传葩,乃一篇大章法也。其间有二篇相承,而为章法者,则首二章与《湘君》《湘夫人》及大、少《司命》也。至各篇自为章法,则固人之所能知矣”〔3〕。
吴世尚认为《东皇太一》《云中君》二章不仅前后相承,而且与《礼魂》相呼应,前者为迎神之曲,后者为送神之曲。《东皇太一》与《云中君》开首“吉日兮良辰”与“浴兰汤兮沐芳”,有祭祀之前“莁(当作‘筮’)日斋沐”的意思,言:“凡祭祀,必先筮日也”〔3〕,“兰汤沐浴,香洁之至也”〔3〕。而《礼魂》中“成礼兮会鼓,传葩兮代舞”,则是祭祀之后送神的乐曲,云:“祀礼既成,则急击鼓而送神也。葩,巫所持之香草也。舞节既毕,则流传香葩而为后用也”〔3〕。
《九歌》为祭祀之歌,各篇所祭祀的神明并不相同。吴世尚从《九歌》整体着手,以“二《湘》”“二《司命》”为切入点,将“时文”中分股成比的程式技巧运用到了整个《九歌》的研究之中,最终整理出了《九歌》一章前后“两两相对的总体结构,析出其统一章法。这对楚辞之艺术研究是一大贡献”〔5〕。
(二)分段析篇,划分层次
1.《离骚》层次的划分
楚辞中“最难读者莫如《离骚》一篇”〔25〕,而“《离骚》的难点在篇章层次”〔26〕。清初学者朱冀认为:“读《离骚》须分段看,又须通长看;不分段看,则章法不清,不通长看,则血脉不贯。”〔27〕吴世尚也认为理清《离骚》的层次结构,有助于把握文章的脉络文理,云:“《离骚》用意精深,立体高浑,文理血脉最难寻觅。故先逐句悉其训诂,乃逐节清其义理,庶几上下有接续,前后有贯通”〔3〕。
《楚辞疏目例》中,吴世尚自言《离骚》分为两段,云:“《离骚》前半、后半”〔3〕。但在实际的文本注疏中,吴世尚则将《离骚》先分为四十三节,再逐层梳理,最终理出了其中过渡段性质的文字。吴世尚认为“‘跪敷衽以陈辞’至‘索琼茅以筳篿’一大段文字”〔3〕当为“白日梦”中之语,因而《离骚》全文共分为三段,即:入梦之前愤懑忧郁至自陈重华、白日梦中上下三次求女、梦醒之后占卜梦境和求教巫咸。毛庆在《〈离骚〉的层次划分及结构的奥秘》一文中简单的认为“吴世尚《楚辞注疏》分两大段”〔28〕,可谓失察。
《离骚》第一节“帝高阳之苗裔兮”至二十五节“沾余襟之浪浪”为《离骚》第一段,吴世尚认为此段表明了屈原的愤郁之情,为下文“就重华而陈辞”作了铺垫。此时屈原的情感虽然越来越深,但总是清醒的。
第二十六节“跪敷衽以陈辞兮”至三十三节“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离骚》第二段。其中“‘耿吾既得此中正’,乃入梦之始”〔3〕,“‘焉能忍与此终古’,乃出梦之终”〔3〕。吴世尚认为此段文字是屈原自陈重华时无意识状态下的“白日梦”境之语,“原跪而陈词重华,冥冥相告,而原遂若梦非梦,似醒非醒,此一刻之间之事也……此正是‘白日梦’境”〔3〕。
第三十四节“索琼茅以筳篿兮”至最后为第三段。吴世尚认为此处乃是屈原出梦以后占卜“白日梦”境和求教巫咸,云:“占上文之梦寐也。屈原志在悟君兴国,而重华示以远引深藏,非其素愿,故欲占之”〔3〕。
吴世尚以屈原的心理变化为依据,将《离骚》分为三段,一反前人如王夫之、朱冀等多将“女媭之婵媛兮”一句视为《离骚》分层标志的做法,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人龚景瀚《离骚笺》中段落结构的划分方法就与吴世尚相同,先是“把《离骚》的叙述区分为现实界与梦幻界,并把后者进一步分成两个部分”〔29〕。由此,龚景瀚最终将《离骚》分为三段,即:帝高阳之苗裔兮——沾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陈辞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索琼茅以筳篿兮——篇末。
2.《哀郢》段落的梳理
又如《哀郢》一篇,由于历来楚辞学者对其作意的不同理解和对“乱曰”部分的不同处理,导致其结构层次有着不同的划分方法。黄文焕《楚辞听直》将《哀郢》分为三段,而林云铭《楚辞灯》、高秋月《楚辞约注》、马茂元《楚辞注释》虽将《哀郢》分为四段,但实际上都受到了黄文焕的影响。
吴世尚以“时文”的程式技巧将《哀郢》细分为六段,颇为独特。吴世尚先是于《哀郢》“解题”之处对全文的结构进行概括:“故屈原始出国门而轸怀,则哀见君而不得。中登大坟而远望,则哀州土之平乐。上不得为,上为德;下不得为,下为民。一反何时,首丘何日”〔3〕,接着在文章内容注解之后附上夹评,最终将《哀郢》分为六段,胪列于下:
“皇天之不纯命兮”至“哀见君而不再得”为第一段。吴世尚点评为:“原以怀王十六年被放,十八年复召用之,至此则原必又放而不用矣。放逐之时,随众远去,故自哀其欲见君而不能再得也”〔3〕,“此上三节则先述其去国离家之时日也”〔3〕。
“望长楸而太息兮”至“思蹇产而不释”为第二段。吴世尚点评为:“此三节,则追思其去都已远,终日郁郁于舟中,不能为情之甚也”〔3〕。
“将运舟而下浮兮”至“悲江介之遗风”为第三段。吴世尚点评为:“此上三节则言其西去郢而东至鄂,中道登高四望,则故都信为乐土,不能忘也”〔3〕。
“当陵阳之焉至兮”至“蹇侘傺而含戚”为第四段。吴世尚点评为:“此上三节,既伤怀襄之不能复兴,又伤己身之不能复用。中心闭结,怅然住立,而无以自适也”〔3〕。
“外承欢之汋约兮”至“美超远而踰迈”为第五段。吴世尚点评为:“此上三节,则又推原君之所以不能复郢,己之所以不能复用者,总由于小人之善为邪佞,肆为谮毁,能使人君堕其术中而不自觉。以故终其身,甘于远君子、近小人,而谗邪得志,谀佞满朝,且美其有能有为,而任用不二”〔3〕。
“乱曰”为第六段,吴世尚点评为:“狐死正丘首,不忘其所自生也。忘谓忘其故都。正指郢也”〔3〕。
吴世尚围绕文章的统一脉络,推定《哀郢》是作于“顷襄王之世,而追思怀王之事”〔3〕,将其划分为六段。虽与历代楚辞注家作家均不尽相同,但在学理上颇具说服力。赵逵夫在《历代赋评注》中对《哀郢》的结构处理与吴世尚相同,云:“《哀郢》不计乱辞,可分为五层,每层三节。前三层为回忆,第四层抒发作者当时的心情,第五层为对造成国家、个人悲剧之原因的思考。乱辞在情致、结构两方面总括全诗,为第六层”〔30〕。
三、诗艺品鉴——评议创作特色
学者梅琼林认为在当代,“与楚辞学的其它研究方法相比,艺术审美研究方法所追求的终极目的,已不再是以经史传统为依据的考据训诂”〔31〕,可以说,“当代心理学介入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现当代乃至古典文学研究,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32〕,“从文学的角度看,创作心理更是楚辞心理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32〕。其实,早在《楚辞注疏》中,吴世尚就已经开始尝试对楚辞篇章的创作心理和创作思路进行解读。这在历代注家中独树一帜,比世界公认的心理学奠基人、奥地利学者弗洛伊德要早180多年,也给后世学者深入研究楚辞作品开辟了先河。
(一)涵泳创作心理
1.《离骚》中的“白日梦”境
《离骚》中“见帝”和“求女”两处文字离奇怪诞,后世有很多异说歧解。清人王邦采认为:“《离骚》之尤难读者,在中间见帝、求女两段,必得其解,方不失之背谬侮亵,不流于奇幻,不入于淫靡”〔25〕。吴世尚《楚辞注疏》从屈原的创作心理着手,提出了“白日梦”的概念。毛庆认为此是“该著最大的特点”〔5〕。
吴世尚认为《离骚》中的“见帝”和“求女”这一大段文字都是屈原的“白日梦”中之语,云:自“跪敷衽以陈辞兮”到“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皆原跪而陈词重华,冥冥相告。而原遂若梦非梦,似醒非醒,此一刻之间之事也……此正是‘白日梦’境。”〔3〕这种“白日梦”并不同于普通的梦境,吴世尚认为其具有“似梦非梦,似醒不醒”〔3〕的特点,只因“元是白日事”〔3〕,故屈原明明说梦而又“说不出梦字来”〔3〕。屈原一直“所用者义,所服者善,未有可侮之处”〔3〕,而遇“时命之穷,进退维谷”〔3〕,因此脑海中思绪杂乱无章,“尘世仙乡,片晷千年,尺宅万里,实情虚境,意外心中,无限忧悲,一时都尽”〔3〕,并最终体现在“见帝”和“求女”的创作中。“见帝”和“求女”两处文字在艺术章法上就表现为“忽朝忽暮,倏东倏西,如断如续,无绪无踪,惝恍迷离,不可方物”〔3〕,“如万千乱丝,毫无端绪;如百十里黑洞,杳无萤光”〔3〕,这正是屈原梦愈深而情愈乱的体现,吴世尚云:“须知此是梦幻境,故引用许多不经之说”〔3〕。
“白日梦”概念的提出,对后世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人龚景瀚《离骚笺》就继承了吴世尚“白日梦”的说法,将《离骚》分为现实和梦幻两个部分。又如陈本礼《屈辞精义·离骚》,也将“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蜷局顾而不行”形容为“无如旧乡在目,使我魂销故国,依然梦醒如初矣”〔18〕,并“将屈辞中一切天马行空,上天下地之幻游,皆形容为梦”〔22〕。再如,日本学者竹治贞夫在《作为梦幻的叙事诗的〈离骚〉》中指出《离骚》是“梦幻式的叙事诗”〔33〕,其表现手法是“叙事诗式的,因而构成了囊括现实世界与梦幻世界的宏大的传奇故事”〔29〕。这也“显然借鉴了清人吴世尚以《离骚》为‘千古第一写梦极笔也’,‘须知此是梦幻事,故引用许多神怪不经之说’的见解”〔33〕。
2.《天问》里的“畏秦入楚”
《天问》一章,吴世尚也力图从心理角度来探索其“微情大义”,自云:“沉潜玩味,餐梦不忘”〔3〕,“庶几质之三闾之初心,或亦可无遗憾”〔3〕。吴世尚通过对《天问》一文的详细解读,最终指出了屈原创作《天问》时的“畏秦”心理,颇为独特。
《天问》一文以“问”为主,讲古论今,涉及天文地理,阴阳变化,表现形式非常特殊。对于《天问》的创作动机,楚辞注家往往各持己见,王逸最早有“抒愤说”,云:“以泄愤懑,舒泻愁思”〔11〕。后世学者有“讽谏说”、“究理说”等观点,但这些看法又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王逸的“抒愤说”。如王夫之“首揭讽谏之说”〔13〕,在《楚辞通释》中云:“黩武忌谏,耽乐淫色,疑贤信奸,为废兴存亡之本。原讽谏楚王之心,于此而至”〔15〕,又云:“抑非徒泄愤舒愁已也”〔15〕。又如“究理说”的代表人物李陈玉,在《楚辞笺注》中云:“天道多不可解。善未必蒙福,恶未必获罪……故著《天问》以自解”〔13〕,又说:“发愤而为此也”〔13〕。吴世尚并不赞同“抒愤说”,认为“非见庙宇图画……以泄愤懑也”〔3〕。

吴世尚力图从心理角度着手把握《天问》的创作动机,分析极为细致。这也说明吴世尚在长期的读骚过程中,对于心理分析已经有了系统的把握,而这在我国古代楚辞注家中是极为少见的。朱碧莲在《还芝斋读楚辞》中也赞同吴世尚提出的“于宗国也,恐再罹吴光入郢之祸”的观点,认为这样解读是对的,云:“楚国从灵王、平王至昭王,经历了一个由衰而兴的过程,这个历史的教训应引以为鉴。他常望怀王学习昭王,能善自振作,‘悟过改新’,弃旧图新;而自己则要以子文‘毁家纾难’的精神来为国为君效忠。这恐怕就是篇末点题的深意吧。”〔34〕
(二)揭橥构思技巧
1.《九辩》中的“交映”之策
关于《九辩》,朱子曰:“《九辩》者,屈原弟子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悯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云”〔7〕。吴世尚继承了朱熹的观点,并从构思方法着手,揣摩出了其中的“交映”之法,为楚辞的文本研究带来了新的视域。
“交映”一词,唐人芮挺章的《〈国秀集〉序》将其解释为:“诗缘情而绮靡,是彩色相宜,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35〕《九辩》共分为九个部分,吴世尚在《九辩》前三篇中对“交映”之法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指出《九辩》虽然通篇只写“秋”字,但“秋”字正与“屈原”相互映衬,云:“世道衰微,灵均坎壈,止以一秋字尽之”〔3〕。
《九辩》第一篇“悲哉秋之为气也”至“蹇淹留而无成”,吴世尚认为此篇虽是以写“秋”为主,但又以“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及“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等句来暗示屈原因被疏远流放而产生的悲愤情感,“秋”与“屈原”交相掩映,互为一体,云:“此篇总止写一秋字,而以原之情事,掩映其中,虽不明言原。而句句是秋,已句句是原矣”〔3〕。又如《九辩》第二篇“悲忧穷戚兮独处廓”至“心怦怦兮谅直”,此辩宋玉句句写屈原被放逐而不得见君的愁苦烦闷,并未提及“秋”。吴世尚则认为屈原的情感与“秋”的肃杀悲凉之意相同,云:“屈原怀忠履洁,而遭放逐,正所谓秋之时也”〔3〕,“此篇总止写一屈原,更无一语及秋,然而句句是原,句句是秋”〔3〕。再如《九辩》第三篇,既有“秋”又有“屈原”。吴世尚则先将其分为三个部分:“皇天平分四时兮”至“余萎约而悲愁”为第一节,“秋既先戒以白露兮”至“恨其失而无当”为第二节,“揽騑辔而下节兮”至“布列星而极明”为第三节,吴氏认为“屈原”与“秋”相互交织,正体现了“交映”之法的妙处:“此篇乃合秋与屈原而言之,而前两节先句句言秋,惟各节末句乃及于原。后一节先句句言原,唯末二句乃及于秋,则交映之妙也”〔3〕。
由此,吴世尚最终提出“秋”与“屈原”互为衬映,“秋者,气之收。天地闭,贤人隐”〔3〕,《九辩》中“纯以秋为言也”〔3〕,正是“宋玉哀悯其师,而作《九辩》以悲之”〔3〕的体现。可以说,吴世尚从创作构思的角度来考证宋玉的创作意图,颇具说服力。
2.《招隐士》里的“拟骚”之法

首先,《招隐士》在情感基调上受到了《离骚》的影响。从“情致缠绵”来看,《招隐士》继承了《离骚》中的比兴手法,使情感更加缠绵悱恻,寄托幽深。吴世尚认为《招隐士》写的是屈原被流放后的真实处境,隐士就是屈原,云:“屈原,放臣也。不曰放臣,而曰隐士,逐于江南也。不曰逐于江南,而曰游于山中,弃于荒远而不令其归也。不曰吾弃之而不令其归,而曰彼自攀援桂枝,淹留而不归”〔3〕。从“音节幽悲”来看,《招隐士》借鉴了《离骚》中的联绵词,在文中运用了大量的双声、叠韵和叠字,使得音节句调更加凄切婉转,如“恍惚”“连蜷”“啾啾”“萋萋”。
其次,《招隐士》在句式停顿上参考了《九歌》。吴世尚认为《九歌》是“最为按脉切理之作”〔3〕,《九歌》中长句、短句交替,每两句有一韵,且两句都用“兮”字,都用于句中,如《大司命》中“令飘风兮先驱,使冻雨兮洒尘”。《招隐士》的句式大多也是如此,如“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再次,《招隐士》章法结构上与“二招”相仿。吴世尚认为“二招”立足于“魂魄归来”,在文中极力描写四方上下环境的险恶,强调对魂魄的惊吓,云:“二篇之许多奇险谲诡,不过是‘归来’二字之一楔子耳”〔3〕。而《招隐士》全篇也是以“魂魄归来”为中心,重视铺排和罗列,利用“虎豹”“崭岩”等意象着力描写山野的幽深险恶,用“恫恍惚”“憭兮栗”等词突出表现人物的恐惧心理,并引用王逸的观点加以论述,云:“王逸曰:‘从此以上,皆陈山林倾危,草木茂盛,麋鹿所居,虎兕所聚,不宜育道德,养情性,欲使屈原还归郢也’”〔3〕。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招隐士》的“拟骚”之法虽无太多新意,但是吴世尚从艺术构思的角度出发揭橥其创作过程,也颇有参考价值。
总之,吴世尚以独特的研究方法,即“儒道并采”、“时文分析”和“诗艺品鉴”的方法对楚辞的文本义理、结构章法、创作特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因此,吴世尚不仅是清初也是整个楚辞学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
注释:
①见章永祚撰、刘世珩辑《南湖集钞》卷八、卷八、卷四、卷八、卷四、卷四、卷四、卷四、卷四,刘氏唐石簃刻本,1920年。
②见吴世尚撰、刘世珩辑《庄子解》卷一,刘氏唐石簃刻本,19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