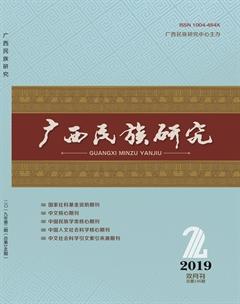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变迁与有效治理


【摘 要】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具有独特性,长期以来存在“乡规民约治理模式”“政、教、礼、法互嵌模式”“行政治理模式”等历史治理模式。“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为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思维,实现了民族地区行政治理从“力治”“柔治”等单主体治理到“共治”的多主体治理的跨越式转变。“共治”体系的核心思想是人民本位、以人为本的治理,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提升人民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谋求“共治”体系下的有效治理,实化“共治”中的“自治”、强化“一核多元”原则、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细化地方性法规是其必然进路。
【关键词】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有效治理;“善治”
【作 者】漆彦忠,许昌学院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许昌,461000。
【中图分类号】C95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2-0047-010
一、引 言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决胜阶段,党和国家对社会治理总体目标的基本表述与路径指引。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同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設定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共建共治共享”的根本在于完全摆正政府、社会、居民三者的关系,扭转其长期以来作为“管理人”“旁观人”和“局外人”的身份,均以“共建人”“共治人”“共享人”的身份参与当前社会治理,形成“联动式治理”[1]的基本模式。“共建共治共享”三位一体,[2]以共同参与为核心原则,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共同目标,是现代治理理念的集中体现。
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治理机制的特殊性,即一般性国家治理机制在民族地区有特别的体现方式。如杨军指出西部民族地区传统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逻辑顺序和国家社会治理“法理情”的逻辑顺序有别,情理法存在冲突。[3]二是治理环境的特殊性,即与一般社会治理环境相比存在更多的限制条件。如青觉、闫力认为,民族自治地方民族成分多元、文化多样、传统各异、社会发展程度不一以及周边环境复杂,进而使得其社会治理难度加大。[4]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特点,民族问题异常复杂、多样。“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民族地区如何结合其特殊性而创设更为适合的治理路径,对于完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和实践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治理模式变迁的角度对“共治”体系下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策略作探讨。
二、理论框架
(一)治理理论与社会治理
治理理论(Governance Theory)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在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性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合组织中兴起,目前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热门话题。国外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治理正日益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描述概念。[5]治理理论是在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反思中产生的,现已逐渐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和实践追求。它在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角色的定位,以及如何通过相关制度和机制实现三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等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研究上和实践中的成效。
国外理论对于治理的本质及其基本规定性做了相关解释。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CGG)认为:“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6]2-3。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 J·N·Rosenau)则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这些管理机制“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7]29。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则总结出治理的四个特征:一是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二是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三是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四是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这些关于治理的本质属性的揭示,对当前我国治理现代化构建有重要启示意义。
国内学者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特征,对社会治理进行了深入阐述。所谓的社会治理,其实是治理社会,就是特定的治理主体对社会实施的管理。[8]具体到我国的政策法律环境和治理实践,社会治理则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的,充分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治理主体参与的,对社会公共事务实施的管理活动,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9]。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对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方略做出明确指示,即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10]总体格局下运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十九大报告沿袭了这一精神,由此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
(二)共建共治共享理论
随着社会治理理论的深入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以来逐渐形成了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话语,是一种可持续的治理方式,[11]88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为此,学者们就“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
首先,学者们就“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内涵进行了多维解释。马海韵认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深层和长远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中国政治民主的表现方式之一和实现路径之一;拓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在全球治理理论体系中的中国特色”[12],较为全面地解读了“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论的政治意蕴。颜克高和任彬彬则对“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价值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新的治理格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治理创新的政治价值、“社会”作为国家发展的子领域独立于政府之外成为“共治”治理主体的社会价值、“以人为本”的公共价值,是政府价值理念的有效转变。[13]47-48侯恩宾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分析了其内涵,认为以公共利益作为治理目标,强调社会个体的主体性价值,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进而以公共重塑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机制,形成善治。[14]这些解释基本厘清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在政治层面、价值层面和治理层面的内涵,对于正确理解新的治理格局有重要帮助。
其次,对于如何实施“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学界做了重点讨论。黎昕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七项原则和八个重点环节,从大视角分析了实施基本策略。[15]颜克高、任彬彬等探讨了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路径,即满足群众更高层次需求,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构建法治治理思维,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培养专业化人才队伍,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发挥互联网技术性治理优势,实现智能化治理。[13]50-52周进萍认为该行动体系的实施应包括共同体发现、共同体参与、共同体合作、共同体创新到共同体共享五个步骤。[11]91-94张国磊、张新文认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局要实现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由单中心的一元权威管制向多中心的多元合作共治转变、从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转变,提出了让社会自治来约束政府权力的理念。[16]张欢、王晔安、耿欣等分析了“共建共治共享”在社区治理中的运行机制,认为共享的内在基础是单位与社区间的广泛联系,共享的动机主要来自社会和政治动机两方面,而非经济动机,社会动机更具根本性,揭示了社会参与的重要性。[17]
最后,还有学者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着力点、重点进行了研究。薛瑞汉认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应把握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及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六个着力点,对于如何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认为重点在于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18]程萍认为,新治理格局建设重点在基层,动力来自于社区认同。[19]
以上研究揭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中国特色现代化政治文明的一部分,蕴含着深刻的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和公共价值,最终取向于社会善治。“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从多个方面共同建设。但社会自治、社会参与、治理中心向基层下移、社区认同等是其灵魂和核心理念。尤其在当前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一元权威向多元共治、“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坚守这一理念。
三、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基本模式演变
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是一个地区社会治理力量聚合的方式,即采用何种作用力将具有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以及不同行为结构的人群内聚为一体化的行动体系的作用方式。我国少数民族数量繁多,宗教信仰、价值体系、文化模式各不相同,历时来看,在民族地区发展出共同的作用中心、解决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过程中,形成了几种普遍有效的治理模式。
(一)乡规民约模式
乡规民约是指在某一特定的生活共同体中,特别是在乡村居民社区中,人们基于共同心理意识、共同文化信仰、共同行为规范在自然演化基础上逐渐俗成或由共同体成员特别约定而成的,具有较强内在约束力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们是由乡民共同制定的社会规范,内容产生于农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反映了乡民的意愿,在所在的乡村对于其参与者具有约束的作用。”[20]35一般存在两种基本形式:其一是“乡规”,如北宋吕大钧《吕氏乡约》中有“凡有婚姻丧葬祭祀之礼,《礼经》具载,亦当讲求。如未能遽行,且从家传旧仪。甚不经者,当渐去之”的说法,此段文字解释了民间婚丧嫁娶礼仪被《礼经》所记载,在后世不断修正下演变为“乡规”;其二是“民约”,如明代章潢《乡约总叙》中就有“又依朱子增损蓝田吕氏乡约四条: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记载,是乡民之间为达到共同目标而进行的约定。相对来说,民约的使用范围较小,外部扩散能力较弱。但民約注重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情况,因此在共同体内部的适用性反而表现得更强烈。本质上来说,乡规民约治理主要体现为“礼治”。
作为传统社会治理的普遍方式之一,乡规民约在以小农为主的农业社会中广泛存在。由于法治的缺失,乡规民约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民间公器的角色,为人们提供日常行为的规范体系。这是乡规民约出现的体制性条件。传统社会以农业生产为主业的乡民,农业生产行为的狭隘性限制了乡民之间的交往,逐渐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圈,表现为“内向型”民族。[21]乡民社会的交往方式则给予了乡规民约治理模式生发运作的社会性条件。乡规民约是乡民共同体所拥有的治理模式,乡间村落内生的“本质意志”[22]118,缔造了共同体产生的精神支柱。乡间村落的存在提供了乡规民约产生的自然性条件。
乡规民约长期扮演着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模式。民族地区较多地满足了乡规民约赖以作用的各种条件。就目前来看,乡规民约在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还有着较强的作用力。民族地区文化差异性较大,价值碰撞根深蒂固,法律的强制性并不能从根本上祛除因信仰不同而形成的价值冲突。乡规民约是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中形成的价值共识,遂成为处理民族内部、民族之间行为差异的理想工具。例如,1986年6月,宁夏西吉县沙沟伊斯兰教哲赫林耶教派内部300余人发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事件导致2人死亡、1人重伤、3人轻伤的严重后果。但当地人民法院在处理此案时,并没有按杀人罪论处,而是充分尊重了伊斯兰教信仰者以对宗教牺牲为荣的普遍共识,从轻处理了此案,这起事件的解决,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另如国家在贵州、云南等地的生态治理过程中,依照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充分尊重当地的乡规民约,制定适合于本地区生态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获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民族地区居民从业方式也发生着较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原有的乡规民约社会治理模式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逐渐发生了改变,这客观上需要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积极转型。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民族地区城市化水平进展较快,截至2016年年末,城镇化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过去五年中,全国城市化率增长了4.78%,其中五个省级民族自治区中,西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增速则远远超过了这一平均值,分别为6.81%、5.62%。在少数民族分布较多的贵州省和云南省,其城镇化的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7.74%和5.72%。西藏自治区虽然城镇化率不高,但增速在所有自治区中最快。由此可见,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较快,社会急速变迁。在此背景下,乡规民约治理模式因其治理基础的改变而较难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亟需创新。
(二)政、教、礼、法互嵌模式
在漫长的社会治理进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基于不同的区域文化价值体系背景,催生出不同的治理模式。其中政教合一模式、礼教合一模式、礼法合一模式均是在不同政治统治的文化背景下,为谋求良好的统治秩序、用以调和不同政治与社会力量之间矛盾出现的可能模式。不同的治理模式力图在政治统治、宗教统治、习俗统治和法律统治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由此形成了相互结合而又各有侧重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
政教合一治理模式在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统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当今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中,仍然延续着这一治理传统。“政教合一治理模式有其存在的基础,是世俗政权与宗教影响力无法一家独大所作出的最佳选择。”[23]政教合一表明了在政治和国家力量增长过程中,人类从蒙昧时代以来所依赖的宗教统治方式与文明时代以来的政治统治方式之间的博弈关系。在当代社会中,一般在欠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社会中,人们往往把宗教信仰作为个人行为和社会行动的评判准则,甚至利用宗教的法则来衡量整个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可见,现代国家与社会治理中,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强势地位仍然是政治统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但在政教合一的治理形式上与传统社会中又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宗教接受国家的政治领导和政治方针,国家承认宗教。国家行政部门管理宗教组织,宗教不介入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的“国家指导宗教”形式是现代国家中使用最多的一种形式。[24]从政教合一走向政教分立,最终实现政教分离,是政与教之间力量博弈的普遍结果。
礼教合一模式溯源于社会习俗治理,当社会习俗被赋予一种神秘意义之后,宗教即由此产生。宗教起源的社会事实学派认为,宗教生活的出现必须以人们的集体行为作为基础,[25]宗教活动赖以生发的群体生活建构,必然要依赖于社会习俗所固有的凝聚力。社会事实学派同时还认为,宗教的神圣意义只有在宗教达到相对进步的状态时才有可能被提出,亦即将群体生活赋予一种神圣意义的过程。[26]110如人类早期出现的拜物教就是将自然力量神圣化的结果。尽管礼俗治理先于宗教统治,但礼俗与宗教之间的内在关联十分紧密。礼俗的神圣化和神秘化即为宗教,这为礼教合一治理模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但在众多宗教统治的形式中,尽管排除了政治和法治的力量,却始终要借助于礼俗才能完成宗教由少数人信仰约束力转变为全体成员行为约束力的过程。礼教合一常常表现为宗教统治,但从治理机理上来分析,其中礼俗的力量十分重要,主要在民族建立与形成的早期作为一种普遍的治理方式,其传统性十分浓厚,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中则逐渐退出了社会治理的舞台。
礼法合一的模式是当代政党政治国家中普遍采用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本质上,礼法合一表明了在法治国家中对民众自主性给予了较大的活动空间,是社会治理民主化、公开化的表现。但从较多现实治理方式来看,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并不是法治主动纳入礼俗,而是法治被动嵌入礼俗道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相关研究表明,由于深受宗教传统的影响,当地群众的公民意识较为淡薄,有近半数的村民首先认为自己是上帝或神的子民,其次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27]可以认为,礼法合一模式是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由依靠民族地区民俗、宗教、信仰,甚至民族禁忌治理向依法治理转变中的一种中间过渡模式。礼法合一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存在两种基本状态:一是礼治框架下的法治,二是法治框架下的礼治。从礼法合一的终极价值追求來看,法治框架下融入礼俗宗教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普遍理想模式。
(三)行政治理模式
行政治理是国家政治权力介入社会治理的一般模式,集中体现了国家对内职能和政治民主化的目的取向。行政治理依靠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力,通过有效联结社会中各种分散力量,在可能的形式与途径下形成社会发展的合力,以积极地促进社会建设。行政治理的前提是国家威权和政治权力,但是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历史来看,行政治理是在国家产生之后逐渐融入民族地区宗教管理、传统习俗治理行列中的。对于一个有着极强传承性价值评判和群体行动体系的民族来说,行政治理是作为一种外在力量的嵌入过程而出现的。因此,行政治理必须在充分肯定民族地区原有治理体系与模式的前提下,秉承维护和建设的姿态,合理把握政治和国家强权的施行尺度,在有限的范围内释放行政治理力量,实现民族地区的善治目标。从我国民族地区行政治理发展的历程来看,存在传统行政治理与现代行政治理的模式、手段、效果等方面的区分。
传统行政治理则出现在产业基础脆弱、生产能力不足的农业社会。“以政府为中心、以行政权力为本位,行政主体主要运用强制手段对社会事务进行全方位的管制,它以单方性、命令性、强制性和封闭性为基本特征。”[28]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社会,生产领域内的封闭性限制了社会领域内社会交往的范围,整个社会处于相对隔离与分离的状态,政治治理必须依靠强权推动才能实现其治理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行政治理的模式和方式。传统社会崇尚皇权至上,以人而治的特色十分突出,演化出僵化落后、不鹜变革的政治统治,其开放程度、文明程度均远远不足。传统行政治理以服从和顺应为目的,压制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本质上是与社会治理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合作行政、柔和行政与开放行政等是现代行政治理模式的发展诉求。[29]现代社会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多种多样,产业形式不一而足。农业产业较好地克服了弱质性,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提升了产业对抗自然环境风险的能力,成为社会化生产序列中的重要环节。在农业之外的产业领域中,其社会化生产程度更高。工业领域的技术增长,为社会各个主体之间互融铺设了实体路径,交通、通讯、网络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地区之间隔阂与分离,逐渐形成一个共融共存的大社会。民族地区受现代社会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自然地域的区隔与限制,一个密切交往、互融共通的崭新的民族社会正在形成。表2中显示了第3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五个民族自治区网络普及率在全国31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中的排名。
从表中可以看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排名第10,互联网普及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民族自治地区普及率基本接近全国平均值,比安徽、河南等中部地区的普及率都要高。这说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正在朝着开放、共融的态势发展。这种社会发展现状,必然促使民族地区的行政治理方式进一步变革,强权命令式行政治理已不能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开放的、合作的、柔性的行政治理是其必然选择。
四、从“柔治”到“共治”:民族地区多主体行政治理的跨越式转变
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演变过程基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遵循了一般社会治理的演变路径,从习俗治理开始,经历了政教合一、礼教合一、礼法合一模式,最终选择行政治理模式,既是社会治理基础不断变迁的结果,也是行政治理模式持续完善的结果;其二,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又与一般社会治理有着明显的不同,政、教、礼、法的力量存在一定的博弈,即使在当前政、法力量居于中心地位的现代社会,礼、教的影响仍然十分突出,这使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必然以“柔治”为基本方略,在行政与法律的框架下融合习俗与宗教力量,谋取全面性社会和谐稳定。
柔性治理缘起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政府失灵所导致的治理危机中,在弥补政府管理危机、财政危机、信任危机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以及治理与善治思想,在对传统科层制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治理理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逐渐形成柔性治理理论。[30]柔性治理以善治为目标,采取非强制性的方式获取治理伙伴及治理对象的配合或参与,达到和谐治理的目的。柔性治理的出现与该阶段西方盛行的协合民主思想所倡导的权力分享主张[31]不谋而合,本质上是行政治理权力的分解。在民族地区治理中,柔性治理有特别的适用性。王丽华以沧源佤族传统政治体系转型为例,实证分析了柔性治理在传统政治体系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转型中的作用。[32]106-109曹召胜根据武陵民族地区Y村治理实践的考察指出,“柔性治理”能够改变中国乡村社会普遍“以力治理”的图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更能提升乡村治理绩效。[33]
从治理主体角度分析,柔性治理尽管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倡导行政权力分享,但治理主体仍然呈现明显的单主体倾向。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权力中心,采取各种“怀柔”的策略和方法,施于治理对象以一定的权力,或者采取平民化的施政方式,以获得治理对象在某一事件上的支持或短期的配合与参与,表面上实现了善治的目的,但根本上并未改变主体与对象的本质关系。毋庸讳言,柔性治理在改造传统“以力治理”“强力治理”的落后治理方式中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并未动摇单中心治理的格局。
2004年6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指示,开启了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之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了“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创新思路。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决定,至此完成了我国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也预示着社会治理从单主体向多主体的转变。十九大报告中倡导“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治”作为突破性的治理创新,表明了新的社会治理时代的来临。
从“柔治”到“共治”是治理模式的根本转变。“共治”理论是中国特色治理理论创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治”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和谐善治,建立“强国家、强社会”的理想格局。但对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来说,“共治”意味着政、教、礼、法秩序的再次调整。新格局下如何获得各种力量的多赢,是决定民族地区“共治”目标实现的重要变量。
五、从“共治”到“善治”:民族地区有效治理的进路
“共治”秉持治理视角,是主体多元、方式多样、秩序取向的混合型整合,其目标在于实现有效治理。[34]“共治”体系下民族地区社会有效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如张伟认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法律制度过宽泛、社会组织参与有限以及基层党委作用难以发挥等问题是影响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主要因素。[35]吴超详细分析了西藏地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存在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社会冲突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制度供给相对不足;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保护与利用宗教分裂祖国图谋并存;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引起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冲突以及维持礼法秩序的困难;人民对社会治理标准和新治理格局的期望日益提高。[36]这些分析提出了“共治”体系下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和政、教、礼、法之间的新问题。“共治”体系下应当具体分析这些问题,采取有效策略实现“善治”的目标。
“共治”体系同时提供了民族地区有效治理的机遇。一是治理理念发生根本转变,“力治”“强治”思维已不复存在,“共治”“善治”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根本指针。二是治理路径完全明确,党委领导、多主体参与、治理重心下移是解决现存问题、达到“共治”“善治”的根本策略。三是治理格局基本形成,表现为以党委领导居于顶层总体把控和设计、多主体参与位于中间层实施治理、法治保障处于底层进行兜底的三级稳固治理格局。另外,民族地区的宗教信条包含引导信众遵纪守法和自律的内容,民族地区的一些特殊性也蕴含着潜在价值和优势,[37]都是构成民族地区“共治”“善治”的有利条件。
“共治”体系下民族地区实现有效治理的根本是“善治”。“善治”是“共治”的目标取向,也是社会治理的最终价值追求,是秩序取向的保障。“善治”必须坚持人民本位,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立场出发搭建治理体系。“善治”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从人对美好生活需求的角度上出发设置治理措施。“善治”就是在充分保障民族地區各主体与力量之间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利益共享与治理和谐,营造以人的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为衡量指标的符合人的本性需求的治理局面。“善治”是“共治”的目标追求,也是“共治”建设内容。“共治”是“善治”的基础和保障,也是“善治”的根本途径。“共治”与“善治”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在“善治”的目标框架下,能较好地统一民族地区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为“共治”打开通途。
据此,谋求“共治”体系下的“善治”,必须重视以下策略:一是实化“共治”中的“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制度之一,实践表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民族地区善治做出了巨大贡献。[38]新的治理格局下,进一步实化“自治”,能够充分调动政、教、礼、法各方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治理主体的身份重新登入行政治理的舞台,引导各方力量的正向发挥。二是强化“一核多元”原则。“一核”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历史演变来看,民族地区治理一直具有“多中心性”[39],政、教、礼、法的力量相互融合渗透,治理中心更迭交替。“共治”体系下这些力量均以主体的身份共同参与治理,必须在“党委领导”这一新治理格局顶层设计与把控下,发挥各自的治理优势。三是治理重心必须向基层下移。从“善治”的根本出发点上来看,坚持人民的利益和以人为本的美好生活需求是善治根本,而基层与人民及其需求最为接近,治理重心下移是“善治”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本质要求。四是细化地方性法规。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特殊性,其中“乡规民约”与社会主文化有较多价值冲突,情理法之间次序难以协调。坚持“共治”中的“自治”,谋求“善治”中的人民利益和以人为本,就必须在充分尊重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细化法律法规,建立明确的、可行的行为标准,真正实现以法治兜底的保障功能。
六、结论与启示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本文立足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历史模式,探讨了新治理格局下民族地区“共治”的进路。主要结论为:
一,“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是构建新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核心思想,最终取向于社会善治。
二,民族地区历经“乡规民约治理模式”“政、教、礼、法互嵌模式”“行政治理模式”等历史治理模式,是打造新治理格局重要的历史遗产,也是谋求“共治”的重要基础。
三,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行政治理阶段经历了从“力治”到“柔治”再到“共治”的演变,只有“共治”实现了从单主体向多主体的跨越式转变。
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特殊性,“共治”体系下必须辩证地进行认识,坚持人民本位,坚持以人为本,合理搭建治理体系,有效设置治理措施,实现有效治理。
五,有效治理的根本是“善治”。“善治”既是“共治”的目标取向,也是“共治”的建设内容。“共治”是“善治”的基础和保障,也是“善治”的根本途径。两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
六,谋求“共治”体系下的“善治”,实化“共治”中的“自治”、强化“一核多元”原则、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细化地方性法规是其必然进路。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之间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为社会治理带来一定难度。“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提供新的社会治理思维,为实现民族地区长期稳定的“共治”和以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提升为旨归的“善治”带来清晰指向。“共治”体系下谋求“善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当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为此,应把握以下方向:
首先,“共治”体系构建不是断裂式变迁。民族地区社会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宗教多样,各种治理模式更迭交替,具有丰厚的社会治理累积。“共治”体系的建构应当在充分尊重历史环境的前提下柔性化谋求变迁。
其次,“共治”体系构建不是去中心化。民族地区存在政、教、礼、法多种力量,在“共治”体系下均以治理主体的身份出现,各种力量之间必然产生新的秩序和关系,但并不是返祖式博弈,而是在党委领导下的关系重建。
最后,“共治”体系下的“善治”不是无底线治理。“共治”的目标是“善治”,“善治”是人民本位和以人为本的治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终极价值取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治理没有底线,完善自治性地方法律法规是“善治”的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1] 刘建军.联动式治理:社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中国模式[N].北京日报,2018-10-15.
[2] 江国华,刘文君.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的理论释读[J].求索,2018(1).
[3] 杨军.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冲突与调适[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4] 青觉,闫力.共建共治共享: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的新模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视角[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3).
[5] D.Curry.Network Approaches to Multi-Level Governance:Structures, Relations and Understanding Power between Levels[M]. 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2015.
[6]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7] J.N.Rosenau,E.O.Czenpeil.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8] 王浦劬.國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3).
[9] 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1).
[10] 胡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而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OL].(2012-11-09)[2018-11-21].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09/c1001-19529890.html.
[11] 周进萍.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中国话语与行动体系[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7).
[12] 马海韵.“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视角[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13] 颜克高,任彬彬.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价值、结构与推进路径[J].湖北社会科学,2018(5).
[14] 侯恩宾.从社会管理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内涵、逻辑及其方式的转换[J].理论导刊,2018(7).
[15] 黎昕.关于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若干思考[J].东南学术,2018(5).
[16] 张国磊,张新文.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社互动取向:共建、共治与共享[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3).
[17] 张欢,王晔安,耿欣.共享的动机和机制:单位向社区居民共享服务资源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18] 薛瑞汉.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J].中州学刊,2018(7).
[19] 程萍.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J].人民论坛,2017(32).
[20] 刘笃才,祖伟.民间规约与中国古代法律秩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1] 马戎,潘乃谷.居住形式、社会交往与蒙乞又民族关系——从赤峰调查看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J].中国社会科学,1989(3).
[22]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3] 樊秋丽.政教合一制度过程论——词义新辨及其产生过程[J].世界宗教研究,2011(3).
[24] 韩星.儒家中国道、教、政视野下的政教关系问题[J].学术界,2014(6).
[25] 李存生.简述关于宗教起源的几种理论——以古典进化论学派及法国社会学派为例[J].思想战线,2013(S1).
[26] 史仲文,胡晓林.中华文化制度辞典:文化制度[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
[27] 马克林.宗教文化与法治秩序——兼论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中的宗教因素[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28] 石佑启.论法治视野下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J].广东社会科学,2009(6).
[29] 蔡武进.行政治理视野下的行政协商[J].北方法学,2014(3).
[30] 谭英俊.柔性治理:21世纪政府治道变革的逻辑选择与发展趋向[J].理论探讨,2014(3).
[31] 周岑银.论利普哈特协合民主对多数民主的超越——基于政治决策的视角[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4(2).
[32] 王丽华.民族乡村传统政治体系的现代转型[G]//刘光顺,王红武.中国族际政治和谐治理实证分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
[33] 曹召胜.从“力治”到“柔治”——基于武陵民族地区Y村治理实践的考察[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34] 慕良泽.村民自治研究40年:理论视角与发展趋向[J].中国农村观察,2018(6).
[35] 张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路径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8(4).
[36] 吴超.西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经验和路径[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37] 方静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综述[J].民族论坛,2017(4).
[38] 黄骏.理性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J].理论导刊,2017(6).
[39] 高永久,郝龙.民族问题的现代治理:概念与特征[J].思想战线,2017(5).
CHANGES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ETHNIC AREAS
——From "Rule By Rite" To "Good Governance"
Qi Yanzhong
Abstract: The social governance in ethnic areas is unique. For a long time, there are some historical governance models, such as "the rules of township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the model of political, religious, ritual and legal inter-integration",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model", and so on. The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of "co-construction, co-management and shared governance pattern" provides new thinking for the social governance of ethnic areas in the new era, and realizes the leap-forward transformation of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in ethnic areas from "hard governance" and "gentle governance" to "co-governance" which is multi-subject governance. The core idea of "co-governance" system is people-oriented governance,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to meet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to enhance the people's sense of acquisition,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It is the inevitable ways to seek effective governance under the "co-governance" system, realizing the "autonomy" in "co-governance", strengthen the principle of "one core and multiple components", shifting the focus of governance to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refining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Keywords: ethnic areas; eocial governance; "co-construction ,co-management and shared governance pattern"; effective governance; "good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