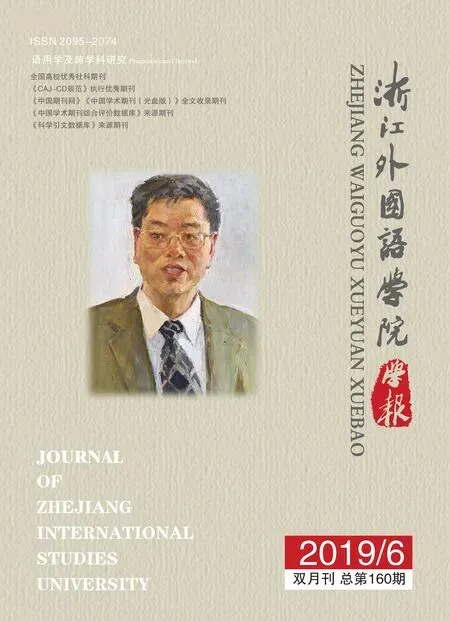《易经》意-象结构与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
单 谊,赵增韬
(浙江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23)
一、引言
中国传统译论的民族文化渊源是先秦诸子的话语乃至更古的《易经》等典籍。张佩瑶(2010)在编著《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一书时采用了不同于前人编著翻译论集时的一贯做法,不是直接进入佛典序言,而是以最早期典籍中涉及语言问题的话语开篇,包括《周易》中的两段文字,这体现了一种独到的文化洞见能力。两段文字见诸《易传·系辞》和《乾卦九三·文言》。《周易》的古经部分即《易经》问世于西周初,比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易传》早六七百年,为中国古代儒释道所共重。《易经》是中国哲学、史学的源头,“是中国文学传统最早也是最深的源泉之一”(李伟荣 2016)。《周易·系辞》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朱熹 1992: 14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论《易经》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回到中国文化的源头,从《易经》中生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乃至独具特色的翻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新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史来看,《周易》的影响深而远。其中,《易经》非文字符号系统所体现的表现思维对于中国译论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原发性影响。王宏印在2003 年版《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一书中继承中国传统译论的人文精神,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这个理论概念和方法范畴,后来又在该书2017 年版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述。作为理论概念,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并不属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那么,它的文化渊源是什么?它有何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学术贡献?它的提出思路对中国新译学建设有何启示意义?为回答上述问题,笔者首先回到《易经》,追溯其意-象结构和所体现的思维方式,然后论述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的概念和文化渊源,最后揭示这一概念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及其对中国新译学建设的启示。
二、《易经》的意-象结构
《易经》文本由六十四卦构成,含象和辞两类符号。关于“书、言、意、象”,《周易·系辞》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朱熹 1992: 149)孔子的自问自答论述了四者的关系。根据现代符号学,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赵毅衡 2011: 1),书、言和象都属于携带意义的感知,三者都是能指符号,而意则是其所指。书和言属于广义的象的范畴。因此,四者的关系可简化为象和意的关系,亦即卦爻象符号系统与意的关系。《易经》的意-象结构关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原发性典型思维方式,下文将主要对其展开论述。
(一)《易经》意-象内在流转结构
关于象,《周易·系辞》中有许多论述。例如,“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朱熹 1992: 143),说明象是古代圣人“见天下之赜”的工具,其功能是“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朱熹 1992: 153),说明观象是圣人作八卦的途径之一, 作八卦最初的目的是供 “观” 以明吉凶;“八卦成列, 象在其中矣”(朱熹 1992: 152),说明在古人看来,《周易》八卦符号系统就是象(卦象、爻象)。象是中国古人思维方式的一个基本范畴。作为符号系统,《周易》的象携带意义。其原始意义在于,古人通过观象来察觉显示人之吉凶命运的蛛丝马迹。关于《周易》象的内在结构,王振复(1991: 172)曾论述了客观物象及观之而生的心灵虚象、卦爻象及观之而生的心灵虚象这四个层次,并给出了《易经》意-象结构流转图。笔者将该图稍作修改,如图1 所示:

图1 《易经》意-象结构流转图
客观物象指自在的自然世界通过人的感知而构建的认知世界,虽称为客观物象,但它并不是纯客观的存在,特别是那些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如《周易·大过》所述“枯杨生稊”(朱熹 1992: 40)。在古人看来,它可能是前兆性物象。心灵虚象1 是古人观察到的物象在心灵中投射而成的心象,这意味着那些物象已经进入了某些特定的因果关系,即某种物象是某种事物的前兆或结果。当然,就古人而言,这些关系主要是由迷信观念所主导的。心灵虚象和卦爻象之间包含两个层次的关系:一是从心灵虚象1到卦爻象,即在卦爻象出现前,古人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占卜,在前兆迷信意绪的支配下,发明了卦爻象符号。这种象是客观物象借由心灵虚象1 这一中介而得到的文化符号。这一符号系统一旦建立,就使占卜超出了原始直观的观念水平,反过去又成为占卜自觉运演的依据(成中英 2006: 218)。二是从卦爻象到心灵虚象2,即后人利用先人发明的卦爻象进行占筮,通过筮法得到卦爻象及其变爻、变卦,再通过观象预卜人之命运吉凶休咎(王振复 1991: 171)。这种象是心灵通过物质媒介(卦爻象线条)而生成的。心灵虚象2 可以通过人的吉凶占断进而影响客观物象并最终导致客观世界的变化。对古人而言,心灵虚象2 是信从占筮的结果,进一步复制与重构了对占筮的迷信。
由上可知,《周易》占筮过程是象在实和虚之间的流转,四个阶段和层次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在象背后的则是始终伴随它的意。这个意即信从占筮的古人对象的神秘感觉、领悟和判断。象在各个流转阶段与意都是互动关系。自在的世界本没有意可言,但它一旦成为人的认知对象并进入占筮过程,则意味着有意灌注其中。从客观物象到心灵虚象1 是通过占筮之意促成的,是一种心理投射的结果。意不可能是纯粹抽象的、不涉象的。从心灵虚象1 到卦爻象的实象,是一种抽象的、蕴含一定占筮意义的符号表现,不是物象的客观模拟。从观卦爻象再到生成心灵虚象2 同样蕴含占筮意义,是卦爻象符号与意的统一。最后从信从占筮结果的心灵虚象2 再到客观物象也是一个意与象的互动过程,同时又具有生成性,因为这种互动最终带来客观世界的变化。象离不开其背后的意,意是象流转的中介。本文将《周易》卦爻象符号系统所体现的这种意-象内在流转结构简称为意-象结构。
(二)《易经》意-象结构体现的思维方式
《易经》意-象结构体现了中国古人独特的思维方式。首先以外物为出发点,观物取象,以观为构建方式,以范畴化、概念化和符号化为运行机制,以意为内在驱动力,形成了卦爻象符号系统(王晓农 2016: 4)。该符号系统实际上是古人提出的一种宇宙秩序和世界模式。这一取象过程主要是整体观取,而非像西人那样对所观对象的条分缕析。古人立象的原意是为了观象以明吉凶。客观物象心灵化后所生成的心灵虚象是一个骚动不安的心理因素,由于主体原在生命力的冲动,人的本质力量总是期待着全面实现和自我肯定(王振复 1991: 177),因此,立象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观物主体的外在表达,从而为求见意而立象。卦爻象是一种线条符号,可见而为实象,但不同于客观物象之实象,亦非模拟物象而成,是意与象在更高程度上的结合。《周易·系辞》云,“立象以尽意”(朱熹 1992: 149),但因为象是意的表现而非再现,立象实不能尽意。《周易》“弥纶天地之道”(朱熹 1992: 140),将纷繁复杂的宇宙天地万事万物仅仅概括为两个阴阳爻符号及其各种组合,作为千变万化的易理的表现。这里所谓的表现当然不是西方艺术领域的表现主义之表现的概念。仅用两个符号的能指就把一切符号的所指涵盖了,这不是文字符号可以做到的(王晓农 2017: 50)。钱锺书(1979: 39)说: “象虽一著,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象具有整体性、形象性、多义性,可以表现无限深远幽隐而丰富复杂的意念(陈东成 2014: 25)。《易经》的思维方式就体现为这种御极繁为至简的表现方式,实是一种重直觉感悟、整体性、生成性的中国式艺术表现原始思维(于涤非等 2019: 46-47)。
三、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的概念与文化渊源
《易经》意-象结构的表现思维对于后来中国文艺理论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有着重要影响。在卦爻辞尚未系于卦爻象之前,卦爻象是一种非文字符号的表现型文体。在王宏印(2017: 314)看来,翻译所涉及的文体可大致分为再现类和表现类。所谓再现类文体是指以写实和直接交际为主的文体,在创作上是实际的、实用的,在翻译上也是科学的、再现原作风貌的,例如应用文体、科学文体、论述文体以及新闻文体,这类文体要求更多的科学思维。表现类文体则要求更多的艺术思维、主观想象和艺术处理,除了指文学作品,例如散文、小说、戏剧和诗歌等,还包括某些专业评论和研究等一般不称为文学作品但充满艺术性言语的形式,如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如此方构成较完整的表现类文体范畴。
(一)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的概念
与文学创作主要反映现实世界不同,翻译的对象总是文体的世界。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作为理论概念主要是针对表现类文体的翻译而提出的(再现类文体在翻译方法上自然以再现手法为主)。王宏印(2017: 314-315)指出,文学艺术翻译中的表现手法类似于绘画中的写意画法和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手法,它在总体上模仿创作手法而不是求得字面形式的对应,但也不排除有意味的形式的模仿,是在模仿中进行创造性翻译,即承认和允许翻译的“创造性悖谬”①来自西方译论的“creative treason”一语,多译为“创造性背叛”。王宏印(2010: 98)认为,该译语有负面色彩,建议译为“创造性悖谬”,指译作和原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又保留着某种相似性,从而使读者产生一种“不似之而似似之”的审美体验。。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在方法论系统中处于翻译策略和翻译技法之间的中间层次, 它的应用基础延伸至包括若干基本的翻译技法在内的应用领域,而它本身的应用则受到具体的翻译策略的制约。王宏印还总结了文学艺术翻译实践中运用的十种表现手法,即“立名:同声相求”“走笔:运思取势”“简洁:如沙淘金”“规整:变化统一”“意韵:丘壑濡染”“形象:万象更新”“节奏:生命律动”“连贯:文气浩然”“谋篇:胸有成竹”和“标题:领袖风采”。显然,这些翻译表现手法的命名多取材于中国传统文论和画论,由此也可见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与中国传统译论及文艺理论在话语上的联系,但前者具有明确的概念界定和方法的系统性,因此属于中国现代译论(于涤非等 2019: 47)。
(二)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的文化渊源
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的直接渊源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而其原发性影响则在《易经》意-象结构所体现的重直觉感悟、整体观照的原始表现思维。由于译论之于文论、翻译之于创作的置后律,《易经》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译论的影响以间接影响为主,但其文化基因和原型仍在于作为《周易》卦爻象符号系统构建基础的艺术表现思维和审美取向上。
从心理学角度看,远古的原始经验、原始幻象已经悄然沉积在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形成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深刻地影响着人的文化和行为方式(宋伟 2011)。中国文学艺术创作过程的一个主要文化原型是图1 中以意为中介由客观物象到心灵虚象1 再到卦爻象的创造过程, 其思维方式主要是表现思维。以文学创作理论话语言之,图1 中的客观物象、心灵虚象1、心灵虚象2 和卦爻象分别变为客观世界、心灵世界1、心灵世界2 和文本世界;意则由信从占筮的古人对象的神秘感觉、领悟和判断,变为作家对以上几个世界的感觉、领悟和判断,原来的那种神秘性可能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而从卦爻象到心灵虚象2 再到客观物象的过程则是文学作品读者的阅读和接受过程,即从文本世界到心灵世界2 再到客观世界,最终互动性地影响和改变客观世界的过程。
在传统文艺创作中,表现手法不追求与对象的客观相似(当然,再现也不是机械地复制对象),而追求通过运用美学修辞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神韵,多依赖于作家、艺术家对对象的审美和情感体验。就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创作而言,不同文类应用的主导表现手法不尽相同,例如诗词的比兴、意象叠加、渲染、托物言志、卒章显志、欲扬先抑等,而散文则有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抑扬结合、比喻象征等。实际上,许多文学表现手法都可以在《易经》卦爻辞中找到用例。例如,据洪迪(2014: 147-152)研究,卦爻辞中运用的主要艺术手法有十二种,即省略与跳跃、原始蒙太奇、瞬时艺术、意识流、意象象征、映射振荡、暗示、意象叠加、总体象征、反讽与矛盾语法、意象描摹与抽象叙述相融合、言之有物有理。这些手法以表现手法为主。
中国古代文学具有不重物象之再现、崇尚情感之宣泄的强抒情特征。中国古代戏曲注重对人物和场景的抽象表现。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则重神似写意而非形似再现,强调“不似之似似之”(石涛语),因深受《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写实的路没有得到好好的发展”(徐复观 2011: 3)。即使是书法,也往往表现出对写意的追求,尤其是草书。中国古代文论如《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等受《易经》思维方式影响很大,其所标榜的“意象”“意境”都根源于《易经》意-象结构的内在思维方式。总体上,中国文学艺术具有抒情特色、重视艺术表现(王宏印 2009: 2)。整个中华文艺史所偏重的是表现而非再现的审美追求,其要点在于在理论上重对客观世界的神似而非形似,在实践上重表现而非再现,这意味着相当程度的创造性。
从原发性文化渊源上说,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源于《易经》意-象结构内在的艺术表现思维,扎根于极为深厚的文化沃土之中。在一定意义上,《易经》也可谓中国译论的源头。就文学艺术翻译的文化原型而言,同样可以认为是图1 中以意为中介由客观物象到心灵虚象1 再到卦爻象的创造过程。以文学艺术翻译话语言之(参见图2),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客观世界变为原语文本世界,文本世界变为译语文本世界;创造则变为用另一种语言文字的再创造;意则是译者对原语文本世界、译语文本世界、心灵世界1、心灵世界2 的感觉、领悟和判断,原来的那种神秘性同样可能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这里的再创造受主要源于原语文本世界的意的制约,因此不可能创而无度。而从卦爻象到心灵虚象2 再到客观物象的过程则变为文学译作读者的阅读和接受过程, 即从译语文本世界到心灵世界2 再到原语文本世界,最终互动性地影响和改变原语文本世界的过程。

图2 文学艺术翻译文化原型
四、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概念的提出受到中国文化源头之一的《易经》意-象结构表现思维的原发性影响,借鉴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特别是画论和文论。兹从以下三方面对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进行论述。
(一)继承中国译论构建传统并借鉴西方译论
关于中国传统译论的文化渊源,学界已经有了定论。罗新璋(1984: 18)指出,中国传统译论的渊源在于中国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王宏印(2017: 260)认为,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乃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从原发意义上讲,这些学科的根基皆可追溯至《易经》。实际上,中国传统译论不断地通过返璞归真来获得前进的动力,古代的道安,近代的严复,现代的傅雷、钱锺书等皆从古代文化资源中寻求新的资源。王宏印(2017: 264-265)历来倡导首先返璞归真,回到学问的根源处去寻找本质之所在,然后从根源处再返回当前,作有深度而超越现实表面浮躁之论。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继承了中国译论的构建传统,但其追求要高于传统译论所谓的忠实通顺之一般要求。另外,它借鉴了西方译论,包括诸如译文读者对译文以及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对等接受效果理论、翻译的“创造性悖谬”等,但与许多西方译论的核心概念又有所不同,如奈达的“语义优先”和“功能对等”、纽马克的“交际性翻译”等,且与今天的“归化”“异化”翻译策略也没有必然的联系(王宏印 2017: 330)。因此,作为理论范畴,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并不属于中国传统译论,而是新译学探索的成果、中国现代译论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一成果不仅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中国新译学的构建也具有积极的方法论意义。
(二)加深了对文学艺术翻译本质的认识
中国翻译史主要涉及的翻译类型是文学艺术翻译,“无论佛经是不是文学,而把佛经翻译称为‘佛经文学翻译’几乎已是定论”(王宏印 2017: 270)。在佛经翻译理论史上,西晋道安首次提出“五失本,三不易”,分别从客体角度和主体性差异角度论述了翻译本体论;唐代玄奘提出“五不翻”理论意在解决前人未能正面解决的翻译概念问题;宋代赞宁以“易”释“译”,并通过“枳橘”的比喻重申和拓展了翻译的定义。近现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于翻译本质问题有了比较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例如,钱锺书关于翻译的异化本质的思考已经触及翻译的“创造性悖谬”问题。随着翻译学界对翻译主体性问题的关注和译介学的发展,翻译学研究者对翻译的创造性本质有了深入的讨论。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的理论概念则是从另一个视角即文学艺术的表现思维揭示了文学艺术翻译的创造性,但如前文所说,这个创造性是创而有度的,这个度就是贯穿于不同翻译环节的意。笔者对《易经》意-象结构的分析表明,表现即基于意的艺术性创造,文学的翻译实质是艺术的翻译,非艺术的翻译则谈不上文学的翻译。因此,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对于我们认识文学艺术翻译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突破了中国传统译论的方法论
总体而言,中国传统译论关注文学作品翻译中原文神韵、意境、风味等的传译,但在方法论上没有形成明确的手法系统。佛经译论的焦点是“文”与“质”两个概念,并曾发生过文、质两派的理论之争。佛经翻译初期,盛行“圣人之言不可违”之观念,佛经译者对翻译的认识肤浅,缺乏翻译经验(谢天振 2009: 9),质派在理论上占上风。然而,如任继愈指出,质派虽然在理论上获得胜利,但实际结果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转引自陈福康 2000: 8)。后来,两派实现了调和,以译文“文质彬彬”为善。如前文所述,西晋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唐代玄奘提出了“五不翻”,宋代赞宁提出了“六例”,然而就翻译方法论而言,佛经译论未能在理论上明确提出类似于表现手法的方法作为文、质翻译策略和微观翻译方法的中间层次。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论、金岳霖的“译味”和“译意”论、傅雷的翻译“神似”论、钱锺书的翻译“化境”论、许渊冲的翻译“美化之艺术”论、汪榕培的翻译“传神达意”论等也同样没有在翻译方法论上明确论述翻译手法的问题。 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的提出在中国传统译论方法论系统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两个层次之间增加了翻译手法层次。 它承认并强调两种语言之间的差距和两种文化之间的张力,并力求艺术地克服或利用这种差距和张力,形成译文本身的多样性和表现力(王宏印 2017: 330)。就中国译者从事的英汉语间的文学艺术翻译而言,它似乎更适合于汉译英,因为它要求英译文摆脱汉语原文语言束缚的力度更大些。在翻译实践中,表现手法的着眼点要高于翻译技巧,同时受具体文本的翻译策略制约。如同《易经》意-象结构的整体性思维一样,它的思维方式始终是整体性的,并具有理想化的追求趋势。表现手法打破了句本位的翻译模式,更加重视译文的谋篇问题,涉及词句篇从标题到收尾的各个层面,旨在提高译文的艺术感染力,因此能够较好地解决翻译理论长期以来未能很好解决的文学艺术翻译形象性问题,并有助于克服翻译中不能脱离字面的忠实和一味执着于传达原文文化因素的问题。因此,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五、结语
《易经》意-象结构的内在思维方式是表现思维,其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居于民族文化源头的原发和原始概念,对今天世界性、普遍性的科学概念的考察来说,仍然可以作为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参照,对于新译学的产生也具有理论思维的原型启发作用。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这一理论范畴的建立是国内学者沿着国学为主的路径建设中国新译学的成果。 它继承中国译论构建传统并借鉴西方译论,加深了我们对文学艺术翻译本质的认识,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方法论实现了一定的突破。 人类思维不仅具有发展性和新颖性的一面, 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原发性和继承性的一面。极而言之,重视民族思维特征的特殊性质,正是为了最终达到人类普遍思维的高峰(王宏印 2017:85)。这正是国内学者提出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这一理论概念和方法范畴的初衷。今天,我们对于传统的理论资源是否已经挖掘殆尽了呢?显然不是。面对一大堆习以为常的旧材料,如何获得新的感觉和新的论题是我们依然要着力思考的问题。一个基本的路径是继续返回中国文化的源头,进一步发掘原始概念,寻求新的理论资源和学术增长点。这也是文学艺术翻译表现手法的提出带给我们这些译论研究者的启示。
——黄忠廉教授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