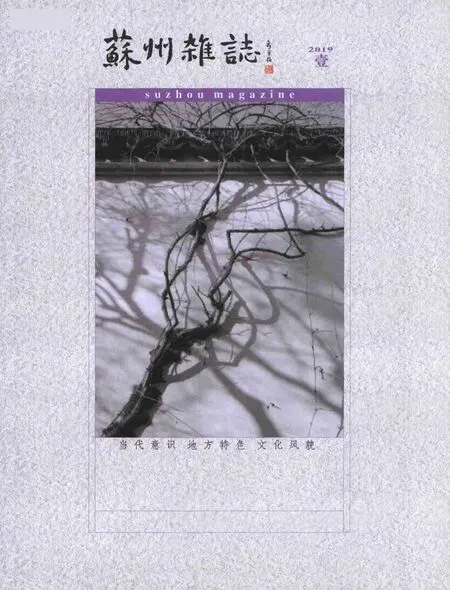医院里的陆文夫
黄恽

新版《美食家》书影
一晃,陆文夫去世已经十三年了,真是一晃,常见到这样的一晃,但人生又有多少个十三年这么一晃呢?2004年秋冬,在医院病房陪伴陆文夫的那些日子,傍晚来临,去关闭南边的钢窗,夕阳在山,返照着打开的窗户,转动的时候,玻璃上那夕阳余照便耀眼地一晃,大家沉默,心里在想又是一天了。
晚上,是治疗的间歇,晚饭后,陆文夫先生的精神开始好起来。探望的家属走后,病房复归静谧,谈话就开始了。我和他相差有四十年,说什么呢?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即使闲聊也不是好对手,我不善表达,在他面前更是如此。他是一座矿藏,我无力开采,也不知从何下手。我只读过他的几本小说集和散文集,写过一篇《探求者的命运》,除此以外,可以说对他一无所知。其时还是他苏州杂志社的下属,和别的同事一样,轮流在他病房里陪护一天。
如果说他能洞察一切,肯定是错的,但他的自信使他认定一切,形成自己对社会和个人的固定看法,不会轻易改变。这是真的。阅历丰富,经历坎坷的老人,他们都有一双X光一般透视的眼睛,或许他的诊断并不准确,但凭他的经验,他相信自己,甚至还用想象丰富自己的判断。他去世之后,上海《文汇报》用电话采访我,我心绪烦乱而伤心,没说几句话,结果刊出时变成了“和陆文夫谈话有如坐春风之感”,这离我的表达与真相都很远。说实话,我和他说话一直是战战兢兢的,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说话艺术是那么拙劣,而他的阅历和想象又是那么丰富,两人谈话难免不产生误会,且无法解释,因为越解释越糟。
有一天,说起几位老作家的事。陆文夫说,他是怕见“大人”的。到北京开会,除了在会场上遇见,他尽量不去拜访谁。在北京,名人伟人真是太多了,成堆成团,每个人都有不凡的身份,那么,你既然无法一一拜访所有的人,你拜访了其中一个,就会引起别人的猜忌:为什么拜访他而不是我?是不是对我有看法?还是觉得我地位不够,名位不彰?……为了避免这样的麻烦,他到北京从来就不去拜访别人。一次,大家把他拉上汽车,一起去看冰心。他说,一起去是推不掉,不过到了门口,他还是没有一起进去。找个借口,留在了车上。他的小心谨慎是坎坷的人生造就的,与其热就,不如冷离,保持一份距离感,也是对自身的保护。
这就是那个1956年和1957年初意气风发的陆文夫。1956年,冯亦代陪英国作家索默菲尔德来苏州游览时,年轻而俊朗的陆文夫就代表华东作协接待了他们,初出茅庐没有什么可怕的,前途还一片光明。只是不知道光明会那么短暂。
在文坛名人中,他只有和巴金走得近些。1957年6月,为了创办《探求者》,他(一说还有方之同行)从南京去了上海找巴金帮忙。陆文夫当时是华东作家协会的成员,找巴金是顺理成章的。到了上海,先碰到的是靳以,一谈,靳以很感兴趣,很支持,搞得而立之年的文坛新秀陆文夫更振奋了。然而随后被巴金泼了一瓢冷水。巴金不但不参加,而且坚决反对搞什么同人刊物:好好写文章吧,别搞这种小团体的东西。陆文夫有些懵,为什么?他不问,巴金也不说,就是劝他们别搞。
带着一肚子的疑惑,他踏上了返程的火车。路上细细琢磨,依然参不透巴金这个葫芦。决定先回苏州的家再说,回到家再想,还是想不明白,但有点栗栗不安,于是决定退出“探求者”,先写一封信到南京(有人写文章说是一封电报,据我听他说,是一封信,当时并没有什么危机感,一般只是写信,轻易不发电报的,电报贵而说不清楚)。他说:肯定巴金已经觉察出什么,又不能向我明说,只能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劝我别搞。也亏得这封信,他说,他最终没有被打成右派,逃过一劫。这件事,他给我讲过数次,印象深刻。
1962年,陆文夫重新在《雨花》露脸,他有思考和积累,所以每逢文艺界的政治紧张度放松,他即刻能拿出在那个时候最好的作品来。他从来不超越时代,但从来能走在时代前列一点,不多,就一点。那天夜里,我拿给他看我地摊上买到的1962年的《雨花》,上面有他的一篇报告文学《队长的经验》(第8期)。他看了一下,说这篇他已经没有了,复印一下留个底吧。我说好。
这样的报告文学,他说当时写了三篇,这是其中的第一篇。那年他复出了,叫他去几个地方采访,写报告文学,后来还写小说,但发得不多。但到1964年后,风声又紧,只能重新蛰伏。不过,于陆文夫先生,1964年有一件大事可记。
1964年,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且享有小说大家之名的茅盾撰文评论了陆文夫的小说,从此,“他力求不踩着人家的脚印走,也不踩自己的脚印走。”(茅盾语)成了陆文夫的标签。当时能得茅盾佳评的,全中国又有几人呢?陆文夫笔下的人物从不“高大全”,而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中间人物”。这个特点是他小说最具特征的标志。陆文夫是新中国小说的开拓者,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这需要多大的才华和勇气啊。茅盾的评论奠定了陆文夫在中国新时期文坛的地位,其作用不可轻估。虽然不久以后的“文革”,陆文夫重新历尽波荡与磨折,被批判与下放……茅盾的评价却不是任何人可以绕过的,即使他的评论能否总结陆文夫小说的全部特质,现在看来还有疑问,但我们也必须明白这个评论对陆文夫个人的意义。
看得出,茅盾对陆文夫有着知遇之恩,陆文夫会经常想起来,露出一点笑意,发出轻微的“呵呵”声。在苦难的日子里,这对于他来说,曾经是多么有力的一种支撑啊。
晚上十点钟,陆文夫吃夜点心了,通常是从医院周边面包店里买来的蛋糕或面包。谁陪护谁购买。吃点他们的应该。陆文夫对他的夫人管毓柔表示。是的,我们都是他从各处提拔起来进入苏州杂志社的,他有完全人事权。就如我来说,此前只是一个下岗工人,学历高中。
吃完点心后,我们再随意谈谈,而我,因为是整夜不睡的缘故,点心往往放在午夜以后再吃,那时,他已经睡着了。有一次,陆文夫很响亮地说起梦话来,我倒是吃了一惊,以为发生了什么,赶忙喊醒他,他怪我搅了他的好梦。我其实没听清他说了什么梦话,却打断了他的梦境,次日也没见他再次提及。
2005年之后,陆文夫的病看不到有好转的希望,换了一家医院,我们也不再连续陪伴,只是偶尔护工有事请假,我们才填补一下空缺,然而我们的担忧却与日增进了。隔三差五去看他一次,老人有很多故事,不想也无力再说了,整日沉默着,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的。
2005年5月2日,我又去陪护了一夜。这是我最后一次的陪护。早晨,我出去兜了一圈,在金狮桥畔吃了一点点心,回到病房。他对我说,他如今连电视也不想看了,报纸上新闻也不要知道了。我有点意外,他一向对时政或者说时代的召唤极具敏感和洞察力,妓女改造时他就写出《小巷深处》;改革开放的号角一响,他就创作出了《围墙》;房改成为热点,他的长篇小说《人之窝》也诞生了,这些都是他对时代脉搏的把握。2004年秋冬在四院(今市立医院东区)的时候,晚上,他总要问我有没有新闻?我略微讲几个,其实他都知道。然而,他这时却收回了敏锐的触角,对外界的喧嚣都不感兴趣了。我已有了不安的预感。
医院和医生换过后,治疗却终于束手,在每天用谎言来安慰老人的那些日子里,听着专家的分析,他笑了,但笑得很无奈无力。专家总许诺着:“不要紧,还有希望。”然而,希望却毫无起色地渺茫。他是否还想着茅盾巴金探求者……以及那许许多多的往事呢?没人可说,也不想再说了。
7月9日陆文夫先生去世,我并不感到突然,早有心理准备,因此也并不悲切,只是感觉心中有一个地方封住了,眼前有一个身影隐去了。人生如梦,他的梦醒了,我们还留在梦中,往事随风,吹过了十三年的岁月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