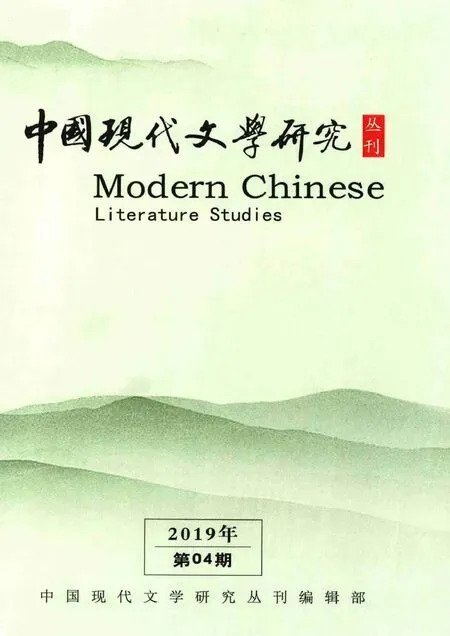发现商州:一个“地方社会空间”※
——重读贾平凹的一种方法
袁红涛
内容提要:评论者对贾平凹中篇小说《腊月·正月》主人公韩玄子这一人物形象的认识一直存在模糊之处,其实是缘于对其背后地方社会空间的漠视。在韩玄子近乎“乡绅”的社会角色背后,隐藏着这里的乡土社会空间虽经巨变依然绵延继而在新时期复苏的历史。作家所打开的新的文学世界,对于既有叙事模式的突破,在召唤批评者更新理念,亟须呼应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大潮,建立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从而超越传统与现代对立的先定框架。进而,只有以新的空间视野才可能贴近“商州系列作品”,感知贾平凹这一时期最深层的变化:作家在返乡之旅中发现了作为“地方社会空间”的商州,从而获得了创作飞跃的真正起点,建立起文学世界的时空坐标。推进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将更新并深化对当代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认识。
1982年,已初有文名的贾平凹面对批评之声,焦灼思考写作之路如何突破。他选择于次年早春回到故乡商州,“再去投胎!”“第一次进商州,对我震撼颇大,原来自以为熟悉的东西却那么不熟悉,自以为了解的东西却那么不了解。”①“震撼”之下、沉潜之后,遂有《商州初录》惊艳亮相,继之以“改革三部曲”誉满文坛,再以长篇小说《浮躁》集其成——这一组“商州系列作品”②,一举奠定了作家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直至今日的重要地位,“商州”也从此成为其贡献于世人的一方文学世界。多有批评家认为这一次返乡之旅,堪称是作家对于商州的重新发现。但是究竟发现者何?作家何以实现了这次创作生涯中的重要转折或者飞跃?或如近来有研究者追问:“商州何以成为贾平凹的起点?”③对此,迄今的研究囿于批评理念的局限,揭示得尚不充分,与作家的自我认知也有相当距离。或者说,作家的创作突破,挑战了既有批评观念,甚至于批评界迄今还没有做出足够有效的应对。
通览“商州系列作品”,笔者发现中篇小说《腊月·正月》在其中具有特别意义;通过重读《腊月·正月》,或可以对思考这一问题提供新的路径和视野。《腊月·正月》刊发于《十月》杂志1984年第4期,当年即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与作家稍早发表的《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被称为“改革三部曲”,一时好评如潮。如孙犁读过《腊月·正月》后赞赏有加:“贾平凹的这篇小说,……从现实生活取材,写的是家常事,平凡的农民。却也能引人入胜,趣味横生,发人深思,有时代和社会的深刻意义。”④不过,“平凡的农民”的“家常事”中何以蕴含“时代和社会的深刻意义”,迄今的解读并不充分。或者说,既有批评对于小说的“时代性”似乎阐释得相当充分,但其深刻的“社会”内涵仍有待细细品味。
小说虽落笔于一个小小村镇,然而开篇气势阔大。历史传说远溯秦代商山四皓,地理方位则涉及“长江”“黄河”“秦岭”,上下千年,纵横万里,最终才落脚于商字山下的这一隅土地,故事即氤氲在这一方灵山秀水之间。小说意蕴丰沛,若仅止于“改革题材文学”解读有些许买椟还珠之憾。若能开放批评观念,呼应当代社会科学“空间转向”大潮,从而超越传统与现代对立的先定框架,视野下沉、深入这个村镇内部,认识地方社会权威与秩序的变迁,方才能切实理解人物身份及其行动逻辑。由此在更准确、更全面发掘小说社会内涵基础上,对于“商州系列作品”内蕴的突破与创造也将有新的认识:那就是对于作为“地方社会空间”的商州的发现,乃是作家此行的最重要收获,并成为其此后创作的时空参照。
一 作为“乡绅”的“韩先生”
对于这篇小说的解读通常都围绕着韩玄子这个主人公展开。在小说发表当时的“改革文学”大潮中,韩玄子被定性为一个“保守派”,一个阻挠改革的反对派。关于其具体身份,蔡翔认为韩玄子是“旧式乡村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⑤。其后有研究者或将其定义为“农村贵族”⑥,或视其为一个狭隘的“庄园主”⑦。也有研究者认为“韩玄子对自己有一种类似于‘乡绅’的文化期许,肩负着秩序维持者的责任”⑧,不过点到即止,无意加以申述。
关于韩玄子身份的秘密,也是解读这部小说的钥匙,在第二段就已设下:
镇上的八景之一就是“冬晨雾盖镇”,所以一到冬天,起来早的人就特别多。但起来早的人大半是农民,农民起早为捡粪,雾对他们是妨碍;小半是干部,干部看了雾也就看了雾了,并不怎么知其趣;而能起早,又专为看雾,看了雾又能看出乐来的,何人也?只是他韩玄子!
这里既凸显出韩玄子的独特身份,也暗含了韩玄子何以保持独特地位的社会结构:他与“干部”和“农民”都不同,在镇街上拥有一个独属于他的社会地位。
作为小说的主人公,“韩玄子”系直接借用商州历史上唯一的举人的名字⑨,足证作者心目中这个人物形象的原型。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本,既是韩玄子不同于“农民”和“干部”的显著特征,也使其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村落领袖或地方精英。韩玄子出场,即表现出浓郁的“老文人”的气质。他习惯坐在花架下戴着老花镜怡然自得地吟读《商州方志》;满腹经纶,熟知历史掌故本地野史;在民国年代的县中受的教育,打下了良好的文墨基础,写得一手好铭旌,让韩玄子很是自信;在外教书三十四年,“桃李满天下”,学生中不乏领导干部,从而赢得四乡尊重。以其文化修养为基础,他有着显著的不同于农民和干部的情趣,成为其独特地位的标识。比如唯有他有欣赏“冬晨雾盖镇”这一自然景观的心境与品位。再如,“照壁前的一丛慈竹,却枝叶清楚,这是他亲手植的,在整个镇子上,唯有他这一片竹子”,因为“他老记得一副对联:生活顿顿宁无肉,居家时时必有竹”。另外,他还吸水烟,“吸这种烟在农村是极少的”,“这镇上当然只有他韩玄子才能如此享受”。这些都成为韩玄子独特地位的象征。“诸如兴趣、爱好、生活情趣等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村庄领袖区别于其他阶层的又一显著标志。”⑩
当然,韩玄子之所以成为“镇上的头面人物”,不仅因为他文化修养高,更因为他依恃文化资本广泛参与村、镇的各种事务。
首先,韩玄子负责组织镇上的文化生活。他从外地学校退休返乡以后,公社出面邀请他担任了镇上的文化站长。正如公社王书记所说,“农民富裕了,文化生活一定要赶上去”。于是一进入腊月,韩玄子就接受公社的委托,督促队长们收集经费、组织排练社火;到了正月,则督促社火队积极演出,参加全县社火比赛。请一位退休老师担任此职,可见这不是一个正式行政岗位;但是却显示了公社对其文化修养的尊重和社会地位的承认。
进而,韩玄子在镇街上承担着调解矛盾的职能,这既是其社会地位的体现,也是其个人威望的更重要来源。韩玄子面对家庭矛盾的时候感叹,“这镇子里多少家庭不和,都是我去调解的”。“调解”是乡土社会解决矛盾的首选方式,而调解人通常是民间社会内生的领袖。“乡间的调解,……更多的是看调解人的资历和威望。如果他具有足够的权威,那么双方都会给他‘面子’,从而平息纷争。”⑪调解纠纷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人生经验。韩玄子拥有文化上的优势,又是教师身份,所谓知书达理;年纪赋予了他经验和威望;而且作为“本地人”,“韩玄子对镇街上的二千三百口人家,了如指掌,谁家的狗咬人,谁家的狗见人不咬”。作为民间调解人,自身的威望与对本地人情世故的熟稔缺一不可。韩玄子以此调解纠纷,满足了村镇上居民的需要,从而也增加了自身的权威。因为“担当纷争的仲裁人是村庄领袖获得合法性权威的又一重要的象征性实践活动”⑫。
他的影响更广泛体现在镇街上的人,包括王才,要找政府办点事儿,都会来托付韩玄子办理。比如驼背巩德胜要办杂货店,“就来给韩玄子说好听的,央求能帮他办个营业执照”,“韩玄子去公社说了一回,从此驼背就成了店主”。正月里,王才一连三天来韩家,请求韩玄子帮他申请把加工厂需要的面粉、油、糖纳入国家粮站供应指标,“你在公社里人熟,给他们说说,盖个章,填个意见,呈报到县里去”。与其说这是通过韩玄子走后门,不如说是托他与正式权力机构打交道。韩玄子在这里承担的是沟通“干部”与“农民”之间联系的角色。这是韩玄子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从而也是其社会地位的支撑。也基于这种联系,韩玄子获得了某些特权。比如他就可以从公社拿到买化肥的指标。在自家田里撒化肥的时候,韩玄子心中充满了展示特权地位的快意。
最终,韩玄子对镇街社会具有全方位的影响。公社对于这位文化站长的借重,不仅仅是托付他筹办社火。前一年公社的社会综合治理工作,韩玄子就参与其中。该项工作受到县里表彰后,公社王书记特别恭维韩玄子:“你在这里威信高,比我倒强哩。”他已经介入了村镇权力的运作中。如狗剩等人在驼背巩德胜的杂货店酗酒闹事,巩德胜急忙找到韩玄子,由韩玄子给公社的张武干打招呼,张武干马上出面,狗剩等人很快就受到了惩罚,王才也因此受到打击。“韩玄子对这件事的处理,十分惬意。他虽然并未公开出面,却重重整治了秃子、狗剩这类人。”韩玄子确实可以影响村镇权力的使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生产队还是公社里这类事务,他都“并未公开出面”,而是隐于幕后。因为他明了自己的身份:当然不是普通“乡民”,可也毕竟不是“干部”。他确实很有影响,但这是非正式的权力,是一种社会影响力。
韩玄子在村镇上的地位从村民们对他的称呼中得到集中体现:“如今在村中,小一辈的还称他老师,老一代的仍叫他先生。”在镇街上碰面,村民们都喊他“韩先生”。这一称呼,无论是在这改革初兴的时代还是之前由革命话语主导的年代,都相当特别,而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兴起之前的乡土社会显示出隐而不绝的联系,接续起乡土中国的“乡绅”传统。确然,以文化资本为基础,退休“还乡”之后广泛参与镇街上的事务,沟通着农民与公社的联系,受到双方的尊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韩玄子的生活轨迹、社会角色与传统乡绅几乎是一致的。
二 在“韩先生”身后:“地方社会”的延续
是否可以根据社会史的概念,就此界定韩玄子的社会身份近乎传统“乡绅”,当然还可以讨论。不过,正如有评论者意识到的:“韩玄子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本身,还在于他所联结的根深蒂固、握有实权的社会权势。”⑬人物的社会角色并非由其自身设定,而是与其生存的社会空间联系在一起的。韩玄子的权威在地方社会中生成,并在地方社会中得以展示和体现。由韩玄子这一人物形象进而关注到他所置身的地方社会秩序,方能进一步体味小说丰富的社会内涵。
首先需要辨析的是,小说故事展开的是一个典型的以镇街为中心的“地方社会”场域,而不仅仅是村庄社会。主人公韩玄子生活在镇街上而不是村庄里。他确是东街的村民,但这里同时是公社所在地。与韩玄子打交道的不仅仅是村民,他还经常出入公社大院,与公社干部推杯换盏往来密切。“中国基层集镇作为地方性生活共同体的经济、行政和文化行政的空间区域”,这里是“国家与农民的地理中介亦即地方控制的核心”。⑭正因为生活在镇街上,是“地方社会”的中心,所以韩玄子具有遍及全镇的影响力,其权力空间与传统“乡绅”的身份更为相称。甚至小说中还透露,韩玄子这一地位还隐然有着家世传承的意味:韩家祖上经营着镇街上唯一的挂面坊;州河上“那个新堤,也是韩玄子的父亲经手,方圆十几个村的人联名修的” 。韩家世代生活在镇街上,韩玄子父亲组织乡邻修河堤的行为也体现出地方领导者的角色。其在地方社会的角色,似乎并未因1950—1970年代的基层社会剧变而改变。循此发现再来细读文本,一个乡土社会空间渐渐浮现出来,这乃是韩玄子现有地位的根本支撑。
其一,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民俗文化与活动是韩玄子权威地位的基础和体现,也是地方社会空间韧性延续的重要支撑。小说故事时间设置在“腊月”“正月”是颇富深意的,这是乡土社会一年中民俗活动最为集中的季节。全镇村民们在辞旧迎新之际办社火,拜大年,韩玄子为大女儿出嫁办“送路”宴席,成为小说情节主线。在这里,仿佛看不到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于乡村风俗与社会文化曾经带来的巨大冲击。因为民俗处于社会的底层,本身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民俗文化的绵延不绝,使得改革之初的基层乡村接续着乡土中国社会。在这篇小说中,办社火成为一条情节主线。韩玄子对此事可谓不遗余力。这是因为他的社会角色、他的威望与地方民间文化生活密不可分。诸如戏乐、庙会等乡村的各种民间性活动,需要村庄领袖来发起、管理和主持,而韩玄子通过对民俗活动的组织和引导也赢得了个人权威。
其二,家族观念和势力依然在这里延续。韩玄子为女儿出嫁办“送路”酒席,最开始的考虑是只请族人。后来请客范围不断扩大,方才遍及全村。这里也可见族人与村民的分野,家族观念依然在延续。家族对于韩玄子的意义在于,他不仅在家里保持着老家长的权威,而且借家族秩序掌握着生产队里的大小事务。生产队的仓房卖不卖,是否以抽签方式来确定买主,“侄儿队长”都要向韩玄子讨主意。而在传统的地方社会中,乡绅即与“家族”紧密结合,家族是乡绅权势的基本支撑,而乡绅的影响力会大大拓展、提升所属家族的地位。在四皓镇,韩玄子的影响力之一就在于他是家族的长老。王才想买仓房,径直来向韩玄子打探,因为他明白韩玄子不但是镇上的头面人物,“队长还是他侄儿”,要靠他拿主意。
其三,这里人们的社会分层观念、等级秩序也更接近于乡土社会,从而维护着韩玄子的地位。众所周知,以阶级身份为主的政治分层是1949年后划分社会等级的主要标准。然而,在小说中,在四皓镇上,却几乎看不到政治分层对人们观念的影响。韩玄子之所以瞧不上王才,对王才的崛起很是恼怒,是因为王才貌不出众,家境贫寒,本是“上不了台面的人”“就这么个不如人的人”。对此,王才本人也是承认的,这也成为他稍显自抑的个性的一个原因。不独如此,村民们也是奉行的这一标准。比如巩德胜讨好韩玄子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恭维他:
“你老哥英武一辈子,现在哪家有红白喜事,还不是请了你坐上席?正人毕竟是正人;什么社会,什么世道,是龙的还是在天上,是虫的还是在地上!”这话又投在了韩玄子的心上……
强调原有社会分层标准的延续性,让韩玄子大感宽慰。在这一以所谓“正人”为取向的等级秩序中,乡绅是居于中心地位的。
基于印象式阅读,评论者大都认定韩玄子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是一个逆时代潮流的旧人物。然而,韩玄子与改革新时代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因为,上述乡土社会形态不但悄然延续,而且在1980年代甚至还表现出了复苏乃至于复兴的迹象。作为这篇“改革小说”的时代背景,最重大的改革举措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现在,又是一个冬天,商字山未老,镇前河不涸,但社会发生了变迁,生产形式由集体化改为个体责任承包,他欢呼过这种改革,也为这种改革担忧过。”一方面,家庭重新明确地成为生活和生产单位,某种意义上小农经济形态的“恢复”,正是原有地方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是正式国家权力的收缩,小说对此也有表现,只是批评者多未曾留意而已。如韩玄子对巩德胜发牢骚时感叹:
现在你看看,谁能管了谁?老子管不了儿女,队长管不了社员,地一到户,经济独立,各自为政,公社那么大一个大院里,书记、干部六七人,也只是能抓个计划生育呀!
随着国家权力收缩,自近代以来由民族国家建设所推动的权力不断下沉、深入村庄社会的大势稍歇,更由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后建立起来直接对接农户的管理体制开始松动、后撤,重新释放出一定的社会空间,乡土社会的权威与秩序遂由隐而显,甚而“复苏”。这即是作为地方权威的韩玄子得以存在的现实原因。
在韩玄子的背后,隐藏着这里的地方社会空间虽经巨变、依旧绵延、终于复苏的历史。这一人物形象不是一个偶然的存在,也并非“封建时代”的孑遗,他的存在有着深广的历史与现实依据。并不能简单地说韩玄子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或者新时代的反对者。韩玄子不是前一个时期“大锅饭”政策的维护者,却是更为传统的、似乎已经瓦解的乡土社会秩序的体现者。贴近小说可见,新的改革时代对于韩玄子具有双重意义,他的欢呼是真诚的,他的忧虑也是真实的。由乡绅主导的地方社会“旧秩序”似乎迎来了复苏,同时却又在蜕变。这已经不仅仅是改革与保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葛,而只有置于“社会空间”视野才能充分揭示这一曲“改革颂歌”内部的冲突与张力。后文将就此进一步展开论述。
三 “面子”与“影响”:地方社会权威的竞争
如果说透过韩玄子的社会角色隐约可见其背后乡土社会空间的延续,那么他与王才的矛盾与竞争,则使得这一地方社会空间相当鲜活地呈现出来,且在改革年代表现出新的活力和生机。
正如有批评家所言,“这部作品使人不易理解、却又是最深刻的地方,正在于韩玄子与王才的冲突了”。⑮探究二人的冲突,是诸多批评家解读这部小说的兴趣所在。两人似乎没有直接利益冲突,他们的矛盾似乎没有缘由。而在认识了小说故事得以发生的地方社会空间之后,对于两人冲突的缘由与方式可以有更为准确、深入的认识。韩玄子居于“干部”与“农民”之间,实际具有了近乎乡绅的地位,履行着乡绅的职能,“这种绅士必然是要在本地保持社区的稳定,要尽量减少阶层的流动,要设法阻止和压抑任何绅士的代兴;对于整个局势也必然是要维护传统憎厌革新的”。⑯这正是韩玄子压制王才的根本原因,甚至于他本人对此都没有明确的意识,却近乎于本能地做出了反应。深入小说所展开的社会空间,在两人之间,不仅是宏大叙事的“改革”与“保守”路线之争;也不是含混笼统的所谓“封建”与“现代”行为、观念的冲突,而是具体地表现为关乎“面子”的一系列竞争,背后是对镇街社会“影响力”的争夺。
开始是在家庭争吵中老伴提及了王才,韩玄子动怒:“大大小小整天在家里提王才,和我赌气”,强调自己的心理优势,“他就是成了富家,地主,家有万贯,我眼里也看他不起哩!”他到镇街上,又处处感觉到王才的影响,更是恼火。“王才,那算是个什么角色呢?韩玄子一向是不把他放在眼里的。”王才曾经是他的学生,又瘦又小,家里很穷,本是个“不如人的人”。然而,“土地承包以后,居然爆发了!” 而且,“王才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成了这个镇上的头号新闻人物!人人都在提说他,又几乎时时在威胁着、抗争着他韩家的影响,他就心里愤愤不平”。王才财富的“爆发”带来了社会影响的扩大,“威胁着、抗争着他韩家的影响”,这是韩玄子愤愤不平的深层原因——他动摇了韩玄子现在拥有的社会地位,在这镇街上所据有的“绅权”。正如韩玄子在家庭会议上坦言的,他可以接受王才财富的增加,“他发了,那是他该发的”,“我也不是说他有钱咱眼红他”;矛盾在于“可没想到他一下子倒成了人物了!”王才可以有钱,但是不能成为“人物”,即社会地位和影响不能上升,否则就影响到了韩玄子的地位:“这些人成了气候,像咱这样的人家倒不如他了?!”研究者大都谈到,韩玄子和王才两人本来毫无利害,没有宿怨,但是德高望重的韩玄子,却总是处处把王才作为他的“重点打击对象”,这似乎是不可理喻的矛盾。只有在“社会空间”视野中才能发现,两人的矛盾来自镇街上权力空间的冲突。
王才虽然在韩玄子面前很是谦抑,但是他以个人财富为基础,已经于无形之中改变着镇街上的社会空间。他办的食品加工厂,吸收了几个村人入伙劳动,这几个人转向了王才。于是韩玄子借着他们在杂货店打架的事儿,由张武干出面处罚他们,打击了王才。听说王才出钱公映电影,韩玄子就指使巩德胜出面包了更有吸引力的新片《少林寺》,直接争夺人气。正月里则拦阻镇街上的狮子队去王才家喝彩,王才于是从远处请来了另一家狮子队,表演更加精彩。评论者常常以此批评韩玄子的狭隘固执,却不明就里。若能留意王才自愿赞助社火表演却被韩玄子拒绝这一情节,或更容易认识两人之间的关系。年后面临全县的社火比赛,四皓镇经费不足,王才愿意向公社捐出四十元。作为社火的组织者,韩玄子正为经费发愁,但还是不愿意直接接受王才的资助,而建议公社采取变通的办法:把一批废旧木料作价卖给王才。王书记不禁为之叫绝。这也确是小说高妙的一笔,写活了人物,也写出了地方社会的微妙与丰富。如前所述,诸如民俗等地方社会的公共活动,也是生成与展示地方权威的重要场域。韩玄子不愿意让王才成为赞助者,本意乃是拒绝王才进入镇街上的公共生活,进入唯有他可以主导的场域,一个由地方社会领袖所据有的空间。
两人竞争的最后一个回合是韩玄子为女儿出嫁“送路”置办的喜宴。本来喜宴准备规模不大,但是由于王才崛起的刺激,改变了韩玄子的计划:“他王才能发了家,咱韩家更要争气把家搞好!后天给叶子‘送路’,这也是耍人的机会,咱要鼓足劲儿,只能办好,不能办坏,要在外面把咱的脸面撑起来。”不料另一个因素最终打乱了韩玄子的苦心准备,县委的马书记正月十五这天去王才家拜年了。这让韩玄子难堪极了。马书记表达的是对王才这类个体户和专业户的支持,明确显示了政治方向的调整,从抓“路线”转而抓经济。这一姿态强有力地改变了这里的社会空间。狗剩立马在镇上张扬,马书记“来给王才拜年,就是代表党,代表社会主义来的!你算算,眼下这镇子上,最有钱的是谁?王才。最有势的是谁?还不是王才?!”马书记以更上一级政治权威的身份对于王才的支持,不但吸引出席韩家宴席的村民转而跑到王才家里,也让与韩玄子交好的公社干部颇为失落。马书记走后,公社的王书记和张武干赶到韩家,与韩玄子沉闷地喝着哑酒。
在改革文学大潮中,这被视为新旧交替过程中,“改革”战胜“保守”的一幕场景,得到批评家的欢呼。随着韩玄子的失意,他大约是这里的最后一个“乡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镇街上“绅权”形态的终结。其时的批评家从小说中看到的是改革派对保守派的大获全胜,然而进入地方社会的内部来看,韩玄子与王才二人的竞争结局,主要是新兴的经济能人对于传统文化精英的替代,这是乡村领导者阶层变迁过程中的重要调整。但是这里的社会结构与地方秩序并没有根本改变,比如村民们摇摆于韩玄子和王才之间,依然需要仰望或者依附于地方精英;公社干部和县委领导虽然支持对象不同,但都很重视与地方精英的沟通,或以此辅助地方治理,或以此传达政策导向。从另一方面讲,韩玄子与王才的冲突,以及干部与农民们围绕二人冲突的反应,使得这里的社会关系得以充分展现,可触可感,形象生动地显示了地方社会秩序的存在与新变。二人的竞争既是叙事推进的动力,也是社会空间活力的体现,精英的自然更替显示了这一空间的生机。相比就韩玄子与王才争斗故事的表面来证实改革步伐的不可阻挡,这才是改革年代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更为深层的体现。
四 “环境”之外是“社会”
总之,不独《腊月·正月》,新时期诸多文学作品如《古船》(张炜)、《二程故里》(阎连科)等都展现了在20世纪中叶空前规模的社会改造运动之后的乡村,其实依然有“乡绅”这一类传统阶层人物的影子。只是他们却成了熟悉的陌生人。评论者对于作品中此类人物形象的隔膜——宁可蹩脚地借用“农村贵族”等来指称韩玄子,却遗忘了并不遥远的“乡绅”阶层;既感受到此类人物形象的“真实”与丰富,却又否认其当代性——生动地显示了20世纪以革命为载体,现代性与现代国家携手对于乡土社会的强势进入与深刻改变。如果说当代文学世界中“乡绅”的消失,是以叙事建构的方式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改造乡土社会这一历史进程的配合;那么批评家对于散落在城乡社会角落里此类人物形象的陌生,则显示了现代性逻辑的强大力量,它不但主导历史叙述,更型塑着人们看取历史、解读文本的视野⑰。
作家已经打开了新的文学世界,召唤着批评家反思既有的认知思维。对韩玄子身份的模糊与隔膜,既与一些批评理念有关,更源于批评思维背后的现代性逻辑。细读文本,贴近作家的创作意图、辨析既有的批评理路,自觉的反思最终指向对当代社会科学“空间转向”大潮的呼应,即不但要更新批评理念、借鉴社会史的研究视野,更需要建立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促进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本文尝试将对既有批评理路的反思、对新的空间思维的认识析为“环境与社会”“国家与地方”“时间与空间”三个层面加以对比、申述。
对韩玄子身份认知的困难,首先囿于批评概念本身的束缚。
批评家大都赞许《腊月·正月》的清新文笔,肯定其展开了一组“风俗画卷”,呈现了商州的“地域文化”。然而,这些概括还停留在“环境描写”的意义上,对作家笔法的关注与赞赏常常只指向山川风物、民风民俗描写的生动细致,而忽视了在其中所渗透的浓郁的社会历史性,乃至“环境描写”所具有的社会本体论意义。事实上,作家本就不是在灵山秀水或者奇山异水的意义上呈现故乡,甚至也没有止步于塑造地域文化。贾平凹曾自述其创作“商州系列作品”的路径:“我想着眼于考察和研究这里的地理、风情、历史、习俗,从民族学和民俗学方面入手。”⑱具体而言,“我在商州每到一地,一是翻阅县志,二是观看戏曲演出,三是收集民间歌谣和传说故事,四是寻吃当地小吃,五是找机会参加一些红白喜事活动。这一切都渗透着当地的文化啊!”⑲就作家的关注和用心而言,已经超出了自然环境、历史地理乃至地域文化的范畴。通过本文对《腊月·正月》的重读,尤其是揭示韩玄子与四皓镇街“环境”的内在联系,作家的用心及其背后的深意豁然。在这方村镇,自然地理与社会历史、风俗民情、传统文化已经融为一体难分彼此,构成人物得以存在的“地方社会空间”。本文前述部分主要在社会史研究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下文将努力申述当代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理论热潮可以赋予这一概念的新的内涵。
就字面而言,“空间”概念包容更广,更具综合性和整体感,更贴近叙事文本的全息性特征。其实批评家对于《腊月·正月》整体上的“空间”效果早有体会。如有人赞赏:“作家对于四皓镇周围的山水风习的描绘点染,是那样的古朴,是那样的宁静,和外界又那样的隔离,这就造成一种浓郁的气氛,似乎在这种气氛中只有韩玄子才能生活得自由愉快、得心应手,他的威望也似乎是永恒的,而王才在这种气氛中则不宜兴盛起来。”⑳所谓“气氛”是批评家对于一种整体性空间的感觉,不仅仅包含着自然环境描写,也不仅仅是风俗画的描绘能够达到的,而是自然山水、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与现实的社会关系等融为一体的“空间”。
“空间”不仅仅包容更广、更为综合和立体;更重要的是,较之风俗画或地域文化等概念,当代空间理论所凸显的社会本体论意义。在传统地理学中,空间是先于甚至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客观自然,社会不过是给定的自然地理背景中的存在。而在当代空间理论看来,空间不是单纯的社会关系演变的舞台,反之它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又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㉑。列斐伏尔明确指出,“空间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㉒。“社会形成和创造了空间,但又受制于空间,空间反过来型塑着社会构型,人们之间的等级、政治、经济、种族、性别关系在空间中体现出来。”㉓由此回望《腊月·正月》中的“风俗画”,或有新的认识。时至岁末年初辞旧迎新之际,节日民俗格外集中,贯穿小说始终,诸如全镇办社火、拜大年、韩玄子家办送路酒宴,都不仅是一幅幅民俗场景,还构成了镇街上的社会场域。小镇上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就生成并体现在这些民俗活动中,而且随着节庆活动悄然变化、重组、更迭。韩玄子与王才两个人的矛盾、竞争体现于民俗活动,并在其中发展、加剧、转折;镇街上无人能够置身其外,围绕两人的矛盾村民们之间的关系也在分化组合。社火、拜年、送路酒不仅仅是相传已久的风俗或地域文化,而且是现实的社会场域,它们构成小说情节,聚集矛盾冲突,体现着社会变化,塑造着人物形象。各种社会关系铭刻在空间中,空间中也在生成新的社会关系。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空间理论建立在对传统的主客观二元对立论的超越之上,它凸显出存在的空间维度,揭示人与社会空间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而无论是风俗画,还是“地域文化”,都是基于环境与人物二分的理念,无论这种论述多么充分,人物不过是被放置在这个“外部环境”中,从而对于人物或者环境的分析都难以避免地相互割裂。由此,一方面无从深入揭示社会矛盾中人的因素,比如,关于韩玄子与王才的冲突,评论者常将其归因于韩玄子作为一个老年人的固执、保守性格,或者是他对于王才的“嫉妒”心理,并将嫉妒心理归纳为国民性缺陷来批判,以此来提升小说主题㉔。这其实是将人物心理表现本身归结为矛盾的原因和故事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不能充分揭示人物存在的社会性。既有批评对于韩玄子这一人物形象认知的模糊,原因就在于局限于这一人物本身,而没有充分认识他与“地方社会空间”之间互动生成关系,并在人物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阐释小说的情节进展与矛盾冲突。倘能打开空间视野,即可认识到,韩玄子的社会地位、身份和角色植根于这里的社会空间,其权威由社会空间中生成,其内心的波动、性格的变化也与社会空间的变化息息相关。反过来,韩玄子的存在也是这一地方社会秩序运转的重要因素,所以韩玄子的心底波澜才具有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这一人物形象之所以生动,不仅仅因为小说以出色文笔描绘了这里的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更在于将主人公与他所得以生存的社会空间整体性地呈现了出来。
五 国家之下有“地方”
《腊月·正月》对社会空间的展现,又是与商字山下这块具体的“地方”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因为叙事者立足于商字山下的这个镇街、立足于这一地方社会展开故事,才得以将环境描写推进到“社会空间”,在韩玄子这一人物形象的背后,展现了地方社会空间的延续。相对于观念史的研究结论而言,这一叙事其实隐含着对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改写。这无论对于贾平凹本人的创作道路还是对当代文学史而言,都具有尚未被揭示的重要意义。
文学史家注意到,“中国大陆当代,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小说,地域、风俗的特征趋于模糊、褪色”,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阶级观念和政治意识对文学观念的制约。㉕其实根源于现代国家主导的话语对于地方社会的覆盖与遮蔽。按照“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解释,自晚清以来,由于近代国家强化自身权力、向基层吸取资源,使基层秩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是乡绅阶层受到巨大冲击,这破坏了传统上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特别是在20世纪中叶,经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后, “消灭了社区领袖和民间精英层,把一切资源和权力集中于国家机器”㉖。这一过程不仅宣告了乡绅社会的覆灭,而且在话语层面确立了以国家为取向的单一视角,“基层社会是需要被改造的被动客体”,“基层社会秩序只是一个被改造、被控制的对象,从而失去了自己的主体”。㉗对于文学叙事而言,抽空了地方社会内涵的地域文化,只具有自然地理上的差异,这样的“地方”主要是作为国家行政区划下的不同地域而已,“地域、风俗的特征趋于模糊、褪色”实属自然。
因而,《腊月·正月》中所谓“风俗画”的重现,实为“地方社会空间”的延续,包含着在1983年后的几年间贾平凹重回商州之旅的重要发现。商州是作家的故乡,他对此不可谓不熟悉:“我早年学习文学创作,几乎就是记录我儿时的生活,所以我正经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就取名《山地笔记》。确切说,我一直在写我的商州。”㉘然而,1983年这次回乡之所以后来显现出重大意义,所谓从“无意识地写商州”到“有意识地写商州”㉙的转折,不仅仅是因为作家比原来更广泛地了解了商州七县百余个乡镇更多的情况,积累了更多的材料,关键在于作家的“意识”发生了变化,看待故乡的眼光和立场逐渐发生了变化,从而作家对商州乃至于对自己都有了新的认识。他一方面风餐露宿,具体地搜集和记录着这里社会空间的知识和信息;另一方面,也在时时思考着作为一个整体的“商州”是什么:
商州固然是贫困的,但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推移,它也和别的地方一样,进行着它的变革。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变革又不同于别的地方,而浓厚地带着它本身的特点和色彩。我便产生了这么一个妄想:以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而得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及这个大千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㉚
他一方面仍然在宏大的“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视野下看商州;另一方面,“以商州作为一个点”,也意味着将“商州”与“中国”、与“别的地方”做相对的区分,以其为考察的主体。从而既“考察它,研究它”,深入地、综合地研究这里的“地理、风情、历史、习俗”,由此发现了商州作为一个地方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它具有本身的特点和色彩”;同时,也开始立足于商州反观其他地方,并将其放回整个中国中来打量:“将这一切变化放入整个中国农村的大变化中加以比较、分析,深究出其独特处、微妙处,这就为我提供了写出《商州初录》之后的一系列中篇小说的创作素材。”㉛在这样的审视、考察、比较和分析中,作家悄然建立了“国家—商州(社会)”的双向视野——相对于现代国家,商州也确认着自己作为“地方”的主体性。“商州”由此不仅仅是作为作家创作的素材库与背景墙而存在,贾平凹不仅仅在这里寻找图解国家政策的材料,更逐渐意识到地方叙事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商州”不但是写作的对象,也成为写作的主体。
关于1983年这次返乡,多有批评家称之为“发现商州”,只是对于“发现”的内涵语焉不详;而作家则自述为是“寻找商州”㉜之旅。其实,作为自然地理的“商州”一直存在,作为行政区划的“商州”历史沿革清晰可追。所谓“发现”,所谓“寻找”,不仅仅是积累的现实素材量的增多,更因为作家内在世界发生的变化:作家的地方意识逐渐萌发,体认到地方社会的主体性,发现了一个作为地方社会的商州的存在,逐渐开始立足于“地方”的创作。
对于作家这一内在的变化,即由现代国家政治主导的宏大视野转而立足于地方社会内部,既有评论尚未充分认识。然而,对此作家本人其实深有感觉并且想尽力表达。对于《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这一组被批评家归结为“改革文学”的作品,贾平凹自陈:“这一组,我的目的并不在要解释农村经济改革是正确还是失败,政策是好是坏,艺术作品不是作为解释的,它是一种创造。所以,这一组小说的内容全不在具体生产上用力,尽在家庭,道德,观念上纠缠,以统一在三录(即“商州三录”)的竖的和横的体系里。”㉝然而,这一组小说仍然主要被纳入“改革文学”之列进行阐释,尽管也有研究者对小说的“改革”内涵提出质疑㉞。这是因为评论者对于作家着意强调的与“商州三录”“统一的体系”缺乏认识。这个统一的体系,也即商州系列作品内在的追求,其实指向对于一个作为地方社会的商州的发现与建构。随着《腊月·正月》进入商字山下这个镇街社会内部,可以发现小说讲述了一个在改革大潮下,地方社会权威发生更迭的故事。权威阶层的构成要素开始变化,新一代的经济能人替代了老一代的文化权威,成为地方社会新的焦点人物。在这一更迭过程中,可以感知地方社会秩序的韧性延续与复苏,无穷的变化和活力正在其中。相比简单地以韩玄子的失意、王才的崛起来证实当时改革大潮的浩然之势,拓展视野,证之以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地方社会”的复苏与活跃,无疑更接近这场历史巨变的核心,小说的现实主义力量由此更为强大而持久。相比局限于以其时政策为取向的阐释,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双向视野中对于小说的品读无疑更加丰富而悠远。
六 “时间”之外有“空间”
韩玄子这一“乡绅”人物形象不但与现代国家叙事冲突,还与现代性逻辑矛盾。现代性主要体现为线性进化的时间观念,批评家惯用的“传统—现代”这一框架即奠基于此。在社会进化的轴线上,乡绅阶层人物与其依存的乡土社会形态属于旧的、传统的、封建保守的社会阶段,必然也已经为现代社会进程所淘汰。因而,评论者一方面赞赏韩玄子这一人物形象富有魅力,另一方面却又对其社会身份很隔膜;一方面赞许他的真实、生动,另一方面却急忙定义其为一个落后的、过时的人物,只是封建社会一个残余而已。——这里隐含的一个问题是:韩玄子这样一个属于旧社会的旧人物何以跨越“现代”尤其是革命时期而存在,从而生活在1980年代新时期?
从小说中可见,民国时期韩玄子在县中学读书,打下了文墨功底。1950—1970年代在“外地”(县城)安稳地做着中学教师,直至退休返乡,现在成为镇街上的“头面人物”。他的历史似乎是清晰的,却隐含着一段空白:这个“封建遗老”式的旧人物似乎从未面对“现代”或者“革命”的冲击。这一空白并不仅仅是出于简洁叙事的追求,更隐含着小说时间设置的策略。小说在时间设置上隐藏着跳跃:“现代”尤其是革命时期在这里似乎是缺席的。与同时期几部工业题材“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品不同,这个山乡里的改革故事,不是针对改革之前由“左倾路线”主导的历史时期的拨乱反正,而是仿佛直接与更前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封建社会”联系在一起。由此,由1980年代改革大潮催生的个体户王才直接与“封建遗老”韩玄子碰撞了。而其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这里仿佛没有多少痕迹。然而读者似乎并没有觉察到历史阶段的跳跃。诚如有评论者的感受:“生活给韩玄子提供了这样一种现实的活动舞台,在商山脚下这个小小的自然村落中,弥漫着一种古老的情调……巧妙地暗示着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以至于我们留恋其中,常常忘记了沧桑演变。”㉟所谓“一种古老的情调”,主要来自对地方社会空间的呈现。如前所述,这里的村民生活节奏遵循民俗时间,家族力量依然存在,社会分层完全看不到阶级年代的影响,由此保持了以韩玄子为中心的地方社会秩序。主要由革命驱动的前一个时代在“社会空间”似乎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和遗产,除了已经被改革的“大锅饭”政策、依然叫“公社”的乡镇机构和被砸毁的四皓庙。“这闭塞的天地似乎是不变的,过去重大的政治斗争掀起的波澜也很快被传统的生活方式所平息”㊱,读者在其间不由得“常常忘记了沧桑演变”。小说以社会空间的延续掩盖了“现代”的缺席,或者说超越了现代性逻辑,从而回避了历史进化的意识形态,“旧人物”韩玄子的出场才给人以“自然”“真实”的感觉。
因而,对韩玄子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其置身的地方社会空间的呈现,其实隐含着对于现代国家与现代性逻辑的复杂态度。而现代国家与现代性逻辑紧密相连,正是评论者对于韩玄子身份认知模糊的深层原因。诚如有政治学者揭示,在中国乡土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国家、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是最重要的三种逻辑。相对于村庄社会,国家的进入与现代性的进入往往是一体的,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国家对于村庄的政治影响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权力进入与结构重塑,并且也不仅限于治理方式的变革,它同时还意味着作为文化意识形态权力的符号转换和现代性的进入。”㊲只是权力与话语的结合却遮蔽了地方社会的主体性与表达。然而,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尤其是田野调查发现,社会现代化的历程并非表现为国家权力与话语对地方性权威空间的单向进占,而是“表现为一种更为复杂的交切、互渗与博弈,以及由博弈所导致的新的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㊳。虽然“现代政治对地方社会的塑造从规模和力度上都是空前的”,看起来已无可争辩地取代了地方传统的位置,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上层政治”“依然与地方社会早已形成的传统行为逻辑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很难清晰地剥离开来”。㊴一旦立足于地方社会,打开地方社会空间的内部视野,就会发现由国家与现代性主导的叙事的另外一面,一个更丰富的世界。正是在这里,可以窥见《腊月·正月》乃至“商州系列作品”艺术上突破的内因。或者说1983年之后的几年间作家多次往返故乡,所谓“发现商州”,其要义究竟何在。作家重返故乡,立足于地方社会,获得了反观现代政治与现代性逻辑的场域,得以从两者携手建构的叙事模式中突围而出。随着地方意识的萌发、对于地方社会的更多发现并逐渐自觉立足于地方社会空间的写作,以及这种写作所得到的肯定,作家寻找、感知、确认着个人文学世界的时空维度:“商州”不再仅仅是国家版图下的一块行政区域,而是有着自己历史文化的地方社会;相比单一的政治,这里有包容更广的社会空间;相比现代性逻辑指示的直线向前的时间,这里时间形态更为多元,在大历史断裂的地方,作家发现了潜在的连续,在前进的意识形态下,作家发现了复苏与回归。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贾平凹发现了作为文学世界的商州,从而也发现了自己。因为商州也是作家的故乡,是作家成长的空间,在为商州定位的过程中,作家也逐渐确定了个人的时空位置。也只能在发现并建立文学世界的空间与时间坐标的意义上,作家当年就宣言,商州由此成为“参照”:“我这一辈子不可能目光老盯着商州,老写商州,但不论以后再转移到别的什么地方,转移到别的什么题材,商州永远是在我心中的,它成为审视别的地方、别的题材的参照。”㊵
七 结语:“发现商州”与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
作家的创作不是被动地等待着批评家的评判,真正的艺术突破常常带来对批评理念的挑战。评论家往往在发掘素材、深入现实的意义上评价贾平凹这次返乡,也因此主要把“商州”看作其题材库和创作基地,这与作家的“参照”说其实有相当大的距离。这是因为评论家没有深入挖掘作家本人时空间的感觉与变化。相对于作家的突破与超越,批评显示出滞后、脱节,日益暴露出评论者在认识论上的局限,那就是空间维度的缺失。虽然20世纪90年代已有敏锐者提出“时间神话的终结”㊶,但现有批评主要还是在现代性逻辑下展开,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即是最常见的框架。现代性的历史就是时间高扬、空间受到贬抑的历史;历史决定论则是现代性逻辑的集中体现,也正是“空间贬值的根源”㊷。然而,随着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理论大潮影响日盛,正在改变这一局面。它强调社会存在的空间性,不是对于“传统与现代”话语的简单反思,而是在时间维度之外,凸显存在的空间维度,以建立时间—空间—社会存在的三元本体论㊸。“空间转向”正在改变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的现状。
由《腊月·正月》打开的地方社会,重新进入“商州系列作品”可见,面对故乡商州,贾平凹虽然仍不乏基于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式的追问与思考,但空间意识已悄然萌发。二十多年后,作家如此总结自己“寻找商州”的最终所得:“随着商州系列作品产生了影响,我才一步步自觉起来,便长期坚守两块阵地,一是商州,一是西安,从西安的角度看商州,从商州的角度看西安,以这两个角度看中国,而一直写到了现在。”㊹“商州”“西安”“中国”,“空间”的差异与转换,才是激发作家至今笔耕不辍的不竭源泉。
只有建立“空间”意识才能把握作家的艺术追求。批评家常以《商州三录》为代表,对作家的“环境”描写赞不绝口,其中的深意或者达到的境界却不如作家自述心曲更为切近:“对于商州的山川地貌、地理风情我是比较注意的,它是构成我的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一部作品里,描绘这一切,并不是一种装饰,一种人为的附加,一种卖弄,它应是直接表现主题的,是渗透、流动于一切事件、一切人物之中的。”㊺在这一时期,贾平凹正逐渐突破“环境描写”的层次,在《商州初录》的高起点上,进而追求“渗透、流动于一切事件、一切人物之中”的空间呈现。这一空间渗透、流动于一切事件、一切人物之中,是自然地理与社会历史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社会与空间的统一,所以它才“不是一种装饰,一种人为的附加,一种卖弄”,而是直接表现主题的。反过来讲,“渗透在一切事件、一切人物之中”,“直接表现主题”的“山川地貌、地理风情”,就是“社会空间”。在作家寻求突破的这一过程中,《腊月·正月》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相比评论者单纯就韩玄子的人物形象大发议论,韩玄子与此地的“山川地貌、地理风情”的共生共存才更能体现小说的主题:商州在改革年代的变化。相比简单地以一个退休返乡的老教师的失意、一个个体户的兴起来诠释改革大潮的进展,在二者竞争故事的表面下,地方社会空间的绵延与复苏、变化与重组,无疑更接近这一仍在进行中的改革时代的核心,由此也可以阐释这篇小说能够跨越“改革文学”浪潮而具有更为持久的魅力之所在。
从社会空间的发现与建构的视角,才可以对作家的创作道路有更深层的理解。评论者一般认为贾平凹前期作品偏于主观抒情,时代性模糊,社会性不强,因此大都肯定作家此次深入商州以后加强了创作的现实性、社会性。事实上,这一变化具体就表现在从环境描写到社会空间的提升,从而呈现了社会存在的空间性与空间的社会性。所谓作家发现了社会,源于发现了相应的空间——作为地方社会的商州。始于《商州初录》,终于《浮躁》告一段落,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作品”文体各异、长短不一,连通起来可以具体看到对于作为地方社会空间的“商州”的不断发现与建构。而《腊月·正月》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如果说《商州初录》还给人“环境与人物相互剥离”“缺乏现实生活内容”㊻的感觉,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其价值还在于历史地理的踏勘㊼,那么到了《腊月·正月》这篇小说,不但如诸多评论者所言增强了现实性和时代感,更内在的突破在于,它立足于商字山下这片土地,发现了地方社会的绵延存在,从而直面现代政治和现代性逻辑,有突破、有回避、有调整,打通了自然与人事、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代,以相对圆融一体的艺术创造使得商州世界初显。其后,对于1950—1970年代的历史,贾平凹并没有一再回避,如《商州又录》即有意记录“文革”时期的各地轶事;《浮躁》进而直面这一历史时期创作出更为阔大雄浑的作品。比如它直接表现了1950—1970年代革命政治主导时期,家族观念和势力在地方社会的实际存在和影响。由此,在地方社会空间中,前现代、革命时代与改革时代缠绕、回旋,改变与冲突浓缩在这片土地上,所以才浮躁不已。自“商州三录”惊艳亮相,继之以《腊月·正月》所代表的“改革文学”,然后是“远山野情”系列一路走来,其间还有小长篇《商州》不甚成功的试验,至长篇《浮躁》,作家对于商州的表现终于骨肉丰满,时空贯通。作家至此宣言:“在这里所写到的商州,它已经不是地图上所标志的那一块行政区域划分的商州了,它是我虚构的商州,是我作为一个载体的商州,是我心中的商州。”㊽
对于这一时期在贾平凹整体创作道路上的意义,也只有加入空间维度才能有更内在的认识。比如,从这一时期的改革颂歌到二十年后故乡挽歌(《秦腔》)的变奏,只有立足于地方社会空间才能给予更合理的解释。“商州”不但作为作家创作基地,它还意味着作家由此建立了自己的时空坐标,因而才成为此后创作道路的“参照”。
“商州系列作品”也被视为新时期“寻根文学”的重要一支。洪子诚先生认为,当代文学尤其是“文革”时期作品“地域、风俗特征模糊、褪色”,因为这一时期“日常生活,体现‘历史连续性’的民族文化的、人性的因素,自然会被看做是对于阶级意识的削弱而受到排除”。而到了1980年代“寻根文学”大潮兴起,“不少作家认识到,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和人的日常生活,是艺术美感滋生的丰厚土壤,并有可能使对个体命运与对社会、对民族历史的深刻表现融为一体”。㊾“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和人的日常生活”何以能够解构主导前一时期文学的政治观念与阶级意识,成为体现“历史连续性”的因素?或许可以由本文对贾平凹商州写作内蕴的突破性的揭示得到新的认识。所谓“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和人的日常生活”的结合不妨理解为“地方社会空间”,对其的发掘与呈现,内含着对于由现代国家政治与现代性逻辑主导的叙事模式的突破,由此作家们可能自觉程度不一地获得了个人对时间与空间的感觉。这就是何以加强了解“某一地域的居所、器物、饮食、衣着、言语、交际方式、婚丧节庆礼仪、宗教信仰等”,可以成为作家“拓展创作视境的凭借”;这就是这一时期的批评家何以转而“重视特定时空的日常生活情景的创作,以之作为文学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条件”。㊿1980年代中期以后寻根文学大潮稍歇,家族叙事兴起,至今繁盛,包含“乡绅”“族长”等“传统”的社会阶层人物角色的小说独具引力51,乃至当下新农村建设中对“乡贤”的召唤,都可以由此视角重新认识或作参考。
推进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将更新并深化对当代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认识。
注释:
②既有评论者如此概括,作家本人也采用这一说法,可见贾平凹《寻找商州》,《收获》2008年第1期。
③程光炜:《商州何以成为贾平凹的起点?》,《文汇报》2016年6月2日。围绕这一问题,程光炜教授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贾平凹文学之路“源流考”,可参见《贾平凹序跋、文谈中的商州》(《文艺研究》2016年第10 期)等文。
④孙犁:《谈〈腊月·正月〉——致苏予同志》,收孙犁《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页。
⑥魏华莹:《时间在空间中流淌——读贾平凹小说〈腊月·正月〉》,《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⑧黄平:《贾平凹与80年代“改革文学”——重读贾平凹“改革三部曲”》,《渤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⑨参见贾平凹《商州初录》:“棣花之所以出名,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文人界的,都知道那里出过商州唯一的举人韩玄子。”《钟山》1983年第5期。
——商州实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