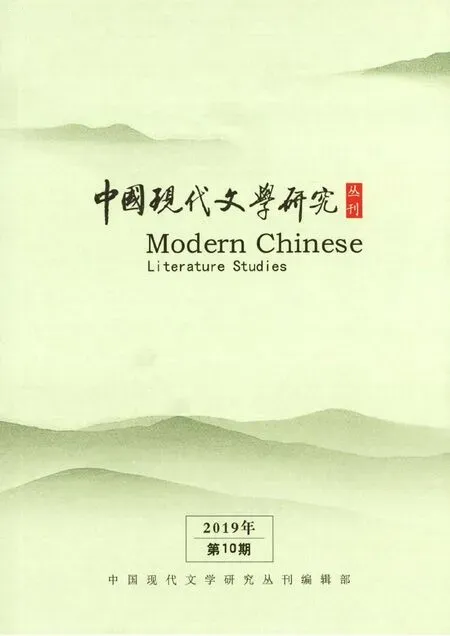《流求歌》的解读与晚清中日琉球争端※
孙洛丹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从知识考古的角度对黄遵宪《流求歌》等相关诗作进行解读,以诗中“舜天”身世为线索追踪隐匿在诗文创作及外交行为背后的认知逻辑,诗史互证,探讨与“终结两属”“吞并琉球”这一东亚地区近代之大变动相“配套”的知识生产和传播,而此种知识在跨文本写作中又被层层转写和重构,转换成为诗歌的语言和意象,并被“应用”在中日琉球争端的外交一线。而同时,诗人在诗歌中也有意识地进行抵抗的书写。
作为梁启超最为推崇的“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黄遵宪因其“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诗学价值引发很多关注和讨论,既往对黄诗的评价往往聚焦于其诗歌中引入“新事物”“新词语”的方面,批评也多集中于此,比如钱钟书认为,以“诗界维新”推崇黄公度,只是因为其诗“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①。在此论断之下,钱钟书举出《番客篇》和《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的例子,认为这不过是某些古诗的“翻版”。事实上,理解黄遵宪之于“诗界革命”的意义不能局限在中国诗歌传统之内,其展现出的“创造性”是对既有文学传统的突破。比如黄遵宪的若干咏史诗,所写的不仅仅是中国疆域内的历史,更涵盖外国/地域史、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其实也不光是黄遵宪,近代涌现出一批这样的诗人和诗作,比如康有为《地中海歌》、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等。其以诗写“史”不再是本国史,而其中的意象和语言也更具跨文化性和现实性,这些作品可以视作早期中国“全球史”视野中的写作。对于这类诗歌,仅仅从一般的诗歌技巧入手很难读懂,而囿于中国传统提供的资源和文化背景也经常会不着边际,因此我们需要探索新的解读方法。这些诗作与国际外交、政治有着密切的纠缠关系,诗中的意象和语词往往是历史/政治的折射,有鉴于此,对这一类诗歌的解读要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进行结构性的把握。
黄遵宪的《流求歌》就是这样一首以诗写史的七言歌行体,全诗一共76句,532字,叙述了从琉球建国到被日本吞并的历史过程。钱仲联对《流求歌》一诗做过非常详细的笺注,对诗歌中涉及的词、句、典故均做了细致的注释,但作为“笺注”只有“注”没有“疏”,并没有对诗歌进行整体的解读,这些词、句、典故与诗歌的结构的关系也没有展开。日本学者西里喜行根据钱仲联的笺注,对《流求歌》进行了逐句的日文翻译②,尽管是以翻译的形式进行的,但这是迄今唯一的对《流求歌》比较完整的疏解,也是对钱仲联相关工作的一个推进。在逐句翻译解释之后,西里喜行从《流求歌》中总结出了黄遵宪的若干琉球认识,他认为,黄遵宪对于琉球人因“废琉置县”而变成亡国之民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但同时黄遵宪又站在世界史的立场上,似乎将琉球的灭亡看成是某种历史的必然归结。②西里喜行此处所说的“世界史”的立场,指的是黄遵宪将日本吞并琉球视作明治维新一系列变革的一环,从而有了所谓的“历史必然性”④。
将《流求歌》放置在近代东亚国际政治冲突和地域秩序变迁的脉络中进行审视,西里喜行的解读完全是以内容为导向的“翻译”,忽略了诗歌的形式,而诗歌作为形式和内容紧密交织的文学文类,形式事实上是意义的生产者,而不只是意义的容器。因此,在对《流求歌》进行解读时,一方面要追踪隐匿在诗文背后的认知逻辑,诗史互证,探讨与“终结两属”“吞并琉球”这一东亚地区近代之大变动相配套的是怎样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另一方面要探讨此种知识又是如何经过转写和重构转变为诗歌的语言和意象,在诗歌的结构中形成意义。只有将诗歌形式和内容间内在的紧张关系挖掘出来,才能达成对诗歌以及诗人的理解。
一 《流求歌》与黄遵宪的驻日外交生涯
在黄遵宪作为驻日公使馆文化参赞出使期间,协助何如璋与日方交涉琉球争端⑤是其主要的外交工作之一。梁启超在《嘉应黄先生墓志铭》中曾简单描述道:“当为日本使馆参赞也,日本方县我琉球,且觑及朝鲜。先生告使者,乘彼谋未定,先发制之。具牍数千言,陈利害甚悉。”⑥此后许多相关的叙述和研究大多结合具体的史实和档案材料对黄遵宪参与琉球争端外交斡旋的经历进行细节化的论述,还原了一位在外交场域孜孜以求捍卫国家利益的使臣形象。
而这段出使经历也促发了他许多诗文的创作,正所谓“以诗写史”,著名的《日本杂事诗》以及《人境庐诗草》第三卷都是较为集中的体现。自然,琉球以及琉球争端也成为诗人关注的问题,在《人境庐诗草》中就收录了与之相关的诗作——长诗《流求歌》以及组诗《续怀人诗》中的两首。
组诗《续怀人诗》收录在《人境庐诗草》卷七中,这是黄遵宪多年后追忆自己初次外交官生涯的诗作,其中在“东方南海妃呼豨,身是流离手采薇。深夜骊龙都睡熟,记君痛哭赋无衣”一诗的注解中,黄遵宪详细记录了1877年11月从上海启程赴日本之际抵达神户时的特别经历:“初使日本,泊舟神户。夜四鼓,有斜簪颓髻衣裳褴褛者,径入舟,即伏地痛哭,知为琉球人。又操土音,不解其谓。时复摇手,虑有倭人闻之。既出一纸,则国王密敕,为言今日阻贡,行且废藩,终必亡国。令其求救于使臣者也”⑦。
给黄遵宪一行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位琉球人名叫马兼才,又名与那原良杰,生卒年不详,一说与黄遵宪同龄,一说比黄遵宪年长20岁左右,他是废琉置县前后活跃在琉球政治舞台的外交官。根据尚球《废藩当时的人物》的记载,马兼才“社交经验丰富、能够使用普通话”,是外交官的不二人选,“尽管他学问涵养不是那么深厚,但是为人温柔敦厚,左右逢源的性格非常适合外交工作,不与人为敌也不轻易交友,与此人接触有如坐春风之感”⑧。在日本强行吞并琉球前后,马兼才业已年迈,但仍背负使命奔波于琉球、东京之间。诗注中所描写的与何如璋、黄遵宪的见面,就是他事前得到情报清国的公使将在神户停泊,费尽千辛万苦逃脱日本人的监视从东京特意赶来的。
正是从马兼才的这次深夜拜访开始,何如璋和黄遵宪等人介入了横亘其整个任期的与日本关于琉球争端的交涉过程。不只是马兼才,黄遵宪在日本接触到的琉球人还有向德宏、毛凤来以及黄房等。无一例外,他们都试图以清国驻日公使馆为媒介就日本阻贡一事向清政府求助。自明治政府1872年借由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将琉球王国纳为帝国体系中的琉球藩,到此时已逾五年。其间1875年7月,更由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在首里城向尚泰宣布,琉球藩须断绝与清朝的封贡关系。马兼才等人的请愿活动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而对黄遵宪等公使馆成员而言,通过与这些琉球人的交往,深化了对琉球的历史以及中日间琉球争端的背景的认识,在此背景下,驻日公使馆与日本外务省展开了艰难曲折的交涉斡旋。
马兼才深夜求见的情形还被黄遵宪写在另外一首与琉球相关的长诗《流求歌》中——“白头老臣倚墙哭,颓髻斜簪衣惨绿,自嗟流荡作波臣,细诉兴亡溯天蹴”。比起前引《续怀人诗》的籍籍无名,《流求歌》的受关注度要高一些,经常被研究者用来引证黄遵宪对琉球争端的态度⑨。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该诗收录在《人境庐诗草》第三卷中,但实际上它并非作于事发当时。钱仲联在笺注《流求歌》时,注云:“《饮冰室诗话》题下注‘庚辰’二字。按:抄本无此诗,恐非庚辰年所作,而是后来所补。”⑩这里所说的“抄本”是黄遵宪在伦敦任外交官时编辑的《人境庐诗草》的初稿,大概成书于1891年前后。⑪而《流求歌》的最早“现身”在《饮冰室诗话》中是《新民丛报》1903年的刊载。有鉴于此,可以判断《流求歌》的创作是这期间的事情,彼时他已离开日本很久了。
尽管距离自己的初次外交官经历已逾十年,但马兼才的深夜拜访因其不同寻常的意义对黄遵宪影响很大,可以说,马兼才等琉球使者正是黄遵宪认识、了解琉球和琉球争端的窗口和途径,他们不仅身负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还带来了关于琉球的“身世”和故事。尽管这些不构成黄遵宪琉球认识的全部来源,但作为促发事件和知识背景介入了黄遵宪的诗歌创作和外交实践当中。马兼才正是结构长诗《流求歌》中的关键人物,全诗以他向清朝公使求救的方式展开:
流求歌
白头老臣倚墙哭,颓髻斜簪衣惨绿,自嗟流荡作波臣,细诉兴亡溯天蹴。
天孙传世到舜天,海上蜿蜒一脉延。弹丸虽号蕞尔国,问鼎犹传七百年。
大明天子云端里,自天草诏飞黄纸,印绶遥从赤土颁,衣冠幸不珠崖弃。
使星如月照九州,王号中山国小球,英簜双持龙虎节,绣衣直指凤麟洲。
从此苞茅勤入贡,艳说扶桑茧如瓮。酋豪入学还请经,天王赐袭仍归瑁。
尔时国势正称强,日本犹对异姓王,只戴上枝归一日,更无尺诏问东皇。
黑面小猴投袂起,谓是区区应余畀,数典横征贡百牢,兼弱忽然加一失。
鲸鲵横肆气吞舟,早见降幡出石头,大夫拔舍君含璧,昨日蛮王今楚囚。
畏首畏尾身有几,笼鸟惟求宽一死,但乞头颅万里归,妄将口血群臣誓。
归来割地献商於,索米仍输岁岁租,归化虽编归汉里,畏威终奉吓蛮书。
一国从兹臣二主,两姑未觉难为妇。称臣称侄日为兄,依汉依天使如父。
一旦维新时事异,二百余藩齐改制,覆巢岂有完卵心,顾器略存投鼠忌。
公堂才锡藩臣宴,锋车竟走降王传,刚闻守约比交邻,忽尔废藩夷九县。
吁嗟君长槛车去,举族北辕谁控诉?鬼届明知不若人,虎性而今化为鼠。
御沟一带水溶溶,流出花枝胡蝶红。尚有丹书珠殿挂,空将金印紫泥封。
迎恩亭下蕉荫覆,相逢野老吞声哭,旌麾莫睹汉官仪,簪缨未改秦衣服。
东川西川吊杜鹃,稠父宋父泣 鹆。兴灭曾无翼九宗,赐姓空存殷七族。
几人脱险作逋逃?几次流离呼伯叔?北辰太远天不闻,东海虽枯国难复。
毡裘大衣来调处,空言无施究何补?只有琉球恤难民,年年上疏劳疆臣。⑫.
《流求歌》借由马兼才之口叙述了自琉球建国到被日本吞并的历史过程,“白头老臣倚墙哭”不由得使人联想到春秋时代申包胥哭秦廷的典故,历史正在重演,琉球正如楚国,清朝能否如秦国?诗歌既由马兼才这位白头老臣歌哭而出,在韵律、节奏的掌握上别具用心,大凡涉及琉球本国内容的采用平声韵脚,大凡涉及中国、日本内容的则采用仄声韵脚,平仄韵脚的错综变化,显示出叙述者的情感张力,于本国是低沉悲哀的,于异国则激荡愤慨。马兼才从传说中琉球开国者天孙氏开始讲述,在其一脉相沿代代相传七百年后,琉球接受了来自明朝皇帝的诏敕,册封使的到来更意味着明朝皇帝对中山国及中山王的承认,由此琉球被纳入了以明朝为中心的册封朝贡体系之内。然而好景不长,随着“黑面小猴”丰臣秀吉的崛起,日本开始展现对琉球的征服野心。之后,萨摩藩岛津氏的舰队以鲸鲵吞舟之势武力入侵琉球,琉球王国无力抵抗,宣告投降,由此开始了一面臣服于明朝一面向萨摩藩进贡的“两属”状态。明治维新后,琉球的“两属”状态岌岌可危,在日本政府一系列政治操作下,最终被强行吞并成为“冲绳县”。不甘此命运的琉球人奔走呼号,幻想能够恢复琉球王国及其“两属”状态,但清朝天子远在北京无暇他顾,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停也毫无用处。与惨败的现实相对,诗歌最后描绘了在海上遇难漂泊到中国的琉球难民,只有他们还会被按照清朝的历代规定加以优待,这也是天朝上国最后的体面。
黄遵宪研究专家郑海麟对该诗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堪称“琉球国史诗”⑬。此言并不夸张,在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从朝贡明清到“两属”于中日、从琉球王国到琉球藩再到冲绳县,可以说琉球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该诗均有涉及,在此意义上称为“史诗”名副其实,然而,以诗写史不仅要关注这些重大转折点,还要有对历史的整体铺陈和叙述,那么《流求歌》向我们展现的是怎样的琉球历史图景?支撑起诗歌文本生成的是怎样的历史叙述?而此种历史叙述是如何被建构的?诗人所实际参与的外交经历与其诗作中的诗语、意象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结构性关联?这些在既往的研究中没有得到细致的描述和分析,都还有待深入地进行考察和讨论。
二 舜天“身世”之谜与日琉同祖论的建构
《流求歌》在讲述琉球王国最初的历史时,黄遵宪假托马兼才之口写道:“天孙传世到舜天,海上蜿蜒一脉延”,奠定了诗歌中琉球史叙述的起点。对于该诗句中的关键信息,钱仲联做了笺注:“《清朝文献通考》:‘琉球相传自天孙氏始建国,传二十五代,逆臣利勇弑而自立。浦添按司舜天者,日本人皇后裔,讨杀利勇,众推为王,遂代天孙氏。时宋淳熙十三年也’”⑭。按照钱仲联此处的笺注,琉球的历史始于传说中的天孙氏,后在宋淳熙十三年(1186)舜天讨杀利勇被推举为新的琉球王,由此“天孙传世到舜天”,可是传说中琉球本土的天孙氏如何与“见义勇为”的日本人后裔舜天形成“一脉相传”的历史渊源呢?在琉球的历史承继中缘何会出现一位有着日本血统的琉球王?“舜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笺注中这段简短的关于琉球历史的叙述来自何处,经历了怎样的流转和“旅行”?
钱仲联的笺注出自《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五“四裔三”。《清朝文献通考》作为所谓“清三通”之一,是官修政书,亦是研究清代中前期典章制度和经济生活的重要资料,被钱仲联用来参考并不奇怪,但这并不是清代最早关于“舜天,日本人皇后裔”的记载。最初记录该事的是康熙年间遣琉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徐葆光在琉球期间借阅了琉球国史《中山世鉴》,其中关于琉球建国的历史是这样叙述的:“大日本人王五十六代,清和天皇之孙、六孙王八世孙为朝公,为镇西将军之日,挂千钧强弩于扶桑,而其威武偃,塞垣草木。后逢保元之乱,而客于豆州有年。当斯时,舟随潮流,始至于此,因以更流虬曰流求也。国人从之,如草加风。于兹为朝公通一女,生一男子,名尊敦。尊敦戴一角于右鬓上,故为掩角居髻于右鬓上。其为人也,才德豪杰,超出众人,是以国人尊之浦添按司也。此时,天孙氏世衰政废,为逆臣所弑矣。尊敦起义兵讨逆臣,代之为中山王。国人效之结片发自此始。是为崇元庙主舜天王。”⑮《中山世鉴》中的这段叙述对后世影响很大,不仅被琉球另外两部国史《中山世谱》和《球阳》继承,清代遣琉史徐葆光、周煌等人在他们的琉球使录中,也皆如此转录。有清一代广为流传的《琉球说略》《琉球事略》以及黄景福《中山见闻辨异》、王士祯《记琉球入学始末》、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以及王韬的《琉球朝贡考》都提到了日本人后裔舜天成为琉球中山王的“历史”。
但是,这一被反复叙述和传播的琉球“历史”却是经不起推敲的。“舜天”日本人后裔的身份有赖其父源为朝,而“琉球王朝为朝始祖”的说法,却不过是在日本《保元物语》以及一些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作为一部描写保元时期战乱经过的军事题材故事,《保元物语》的具体作者不详,大约成书于镰仓时代,推定为1320年之后。根据《保元物语》的记载,1156年,猛将源为朝参与了“保元之乱”(发生在京都的一场皇室及摄政间的争斗),兵败后被逐放伊豆大岛(也称豆州)。嘉应二年(1170)遭遇追剿时,自杀身亡。⑯《保元物语》首次记载了源为朝被放逐伊豆的事情,为后世提供了可供生发的文本基础和脉络。而在文本层面,已发现的最早将放逐伊豆的源为朝“引入”琉球“建功立业”的是京都五山僧人月舟寿桂作于1530年前后的《鹤翁字铭并序》:
吾国有一小说,相传云,源义朝舍弟镇西八郎为朝,膂力绝人,挽弓则挽强,其箭长而大,森森如矛,见之勇气拂膺,怯夫亦立。尝与平清盛有隙,虽有保元功勋,一旦党信赖,其名入叛臣传,人皆惜焉。然而窜谪海外,走赴琉球,驱役鬼神,为创业主,厥孙世世出于源氏,为吾附庸也。与《一统志》所载不同,将信焉,将不信焉。⑰
文中月舟寿桂对源自日本小说的说法将信将疑,准备就此请教来自琉球的鹤翁智仙。此后,在琉球生活过三年的净土宗学僧袋中写于17世纪初期的《琉球神道记》也提到了源为朝渡琉之事。这两个例子都可以视作由《保元物语》引发的传说故事在琉球以及日本的流布和影响。而几乎与《琉球神道记》的出版同时,时任萨摩藩外交文书的南浦文之对“为朝渡琉”的大纲进行细节化的勾勒并将其用以政治动员,他在《讨琉球诗并序》中说道:
萨隅之南二百余里、有一岛名曰琉球,使小岛之在二四方者并吞为一,而为之酋长矣。予闻之黄耉曰,昔者日本人王五十六代清和天王之孙,其名曰六孙王本朝源家之曩祖也,八世孙义朝公、令弟为朝公为镇西将军之日,挂千钧强弩于扶桑,而其威武偃,塞垣草木,是故远航于海,征伐岛屿于斯時也。舟随潮流求一岛于海中,以故始名流求矣。为朝见巢居穴处于岛上者,颇虽似人儿戴一角于右发上,所谓鬼怪者乎。为朝征伐之后,有其孙子世为岛之主君,固筑石垒家于其上,因效鬼怪之容貌结发于右鬓上,至今风俗不异。中改流求二字,字从玉,而为琉球矣。盖黄耆之言未知是否。⑱
南浦文之的这段话是为了鼓舞行将南下征伐琉球的萨摩军人,但也随之进入《中山世鉴》作者向象贤的视野,几乎被后者原封不动地转写。作为琉球王国三大国史的第一部,《中山世鉴》成书于“日本庆安庚寅”(清顺治七年,1650年)。在该书正文之前有向象贤所作序言,主要说明此书为“琉球国中山王尚圆公七世嫡孙时王尚质公”“命摄政金武王子朝贞三法大里良安宜湾正成国头重仍会博古旧僚取其议论格言,以使臣象贤撰自古所无之世系图”⑲;此外序后正文前还有《琉球国中山王舜天以来世缵图》《先国王尚圆以来世袭图》和《琉球国中山王世继总论》三部分内容,记录了从琉球开辟神话天孙阿摩美久筑岛植山石草木次生人直至尚质公的谱系,是对正文五卷的内容简明扼要的概述。
如果说以上勾勒出“琉球王朝为朝始祖”的叙述如何进入琉球王国的正史,那么这还只是“故事”传播演绎的一个方面。1719年,新井白石用汉文写成上下两卷的《南岛志》,涵盖地理、世系、官职、宫室、冠服、礼刑、文艺、风俗、食货、物产等内容。在“世系”中,新井白石结合《保元纪事》《东鉴》《南浦文集》《琉球神道记》等书的记载,完整地讲述了源为朝在保元之乱后逃亡琉球与当地人结合的经过,强调源为朝之子即为琉球国第一代国王,明确指出琉球人与日本人的血缘关系。
除了从地缘与亲缘的角度论述日琉关系之外,在《南岛志》的其他部分,新井白石还从琉球的建筑风格、文艺曲调、饮食料理、语言文字等内容入手,分析其与日本的相似之处,由此推论日本与琉球在文化上的共通性。何慈毅在考察了江户以来日本的琉球叙述和对策后,指出德川幕府对琉球的认识,经过宝永年和正德年,逐步由江户初期的明朝中国的册封体系中孤悬海上的“小国”琉球,变为以日本为中心的“南倭”琉球,并由《南岛志》的奠基转向“南藩”琉球。⑳
在日本本土,“琉球王朝为朝始祖”的叙述达到高潮全赖江户时期著名的小说家曲亭马琴的《椿说弓张月》。小说《椿说弓张月》分为五篇二十九册,以《保元物语》中登场的源为朝为中心人物,描写了源为朝被流放琉球后励精图治东山再起的详细经过,其核心人物之一就是源为朝的长子舜天丸,即后来记载中的琉球开国国主舜天。如果说《南岛志》提供的是学理支持,那么《椿说弓张月》的流行则是做好了最充分的舆论动员。嘉永五年(1862)《大日本史》本纪和列传部分首次出版,“琉球”被纳入列传中的“诸藩”,成为日本“国史”的组成部分。
初源为朝配流于伊豆大岛也。侵略诸岛,到鬼岛,慑服岛人,掠一人而还,岁纳绢百匹。(保元物语)所谓鬼岛,亦琉球也。后为朝子逃岛中,代天孙氏为王云。(参取南浦文集、中山传信录。按,传信录云,舜天,日本人皇后裔,大里按司朝公男也。淳熙七年即位,年十五。续弘简录注亦引琉球人所著世续图云,舜天王为朝公之男子。而宋淳熙七年,则当治承四年。而其谓年十五者,适与保元物语为朝少子嘉应二年五岁之文合。则为朝子孙王琉球者,盖亦不诬也。附以备考。中山世谱云,舜天王,姓源,号尊敦。父镇西八郎为朝公。母大里按司妹。宋干道二年,西戍降诞。宋淳熙十四年丁未即位。宋嘉熙元年丁酉薨。在位五十一年,寿七十二。)㉑
一个附会于民间传说的“故事”最终写入了琉球和日本的史书,而在传播过程中,经过物语/神道记/地理专著/小说等不同文体的转写和演绎,成为一种“理所当然”“原本如此”的知识和言说。由此“舜天”进入黄遵宪的诗语就并不奇怪了,不管此种认知来自阅读还是来自与马兼才等人的交流,“舜天”作为意象被写入诗歌,就意味着在“舜天”话语背后所建构起的琉球和日本之间的亲缘连带关系得到了默认。
相比于琉球日后被明朝册封、受萨摩侵略、又两属于中日的命运,其独立于外部力量“一脉延”的历史是马兼才们请愿的重要立足点,也是黄遵宪笔下的琉球故事能够打动人心的情感逻辑所在—在孤悬海上的蕞尔小国与七百年的一脉相传所形成的对照中,弱小琉球的呼声穿透历史的层层书写显得格外凄厉。然而一脉相承的“历史”本身却是一段不断被再生产和建构的叙事,日琉同祖论借由舜天父子的传说有了可供瞻仰的肉身。诗歌中的“舜天”在承担意象功能的同时,又成为被重重前文本加持的符号。符号的意义也许是黄遵宪并没意识到的,但关于舜天身世的争论却在1879年前后聚焦于中日双方的外交一线。如果说作为意象的“舜天”是诗人黄遵宪离开日本若干年后的文学创作,那么作为问题的“舜天”却是外交官黄遵宪在当时必须面对的。
三 再现于外交文本的“舜天”叙述
在认真研究了马兼才等人的请愿书之后,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成员展开了与明治政府外务省之间艰难的交涉和斡旋。1878年9月3日,何如璋按照清政府“据理诘问”的指令,根据《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条——“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互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的原则,前往日本外务省,会见外务卿寺岛宗则,当面提出“近闻贵国使琉球内附禁止对我清国朝贡”,“其情甚乖,请率由旧章”的要求,而寺岛则称:“以往我国虽然漠视琉球之外交,但现在无独立之权者,有被他国吞并之忧,故而禁其私交”,并称琉球乃是日本属地㉒。9月27日,双方再次会晤,依然不得要领。于是10月7日(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何如璋向寺岛递交外交文书。
查琉球国为中国洋面一小岛,地势狭小,物产浇薄,贪之无可贪,并之无可并。孤悬海中,从古至今,自为一过。自明朝洪武五年,臣服中国,封王进贡,列为藩属。……又,琉球国于我咸丰年间,曾与合众国、法兰西国、荷兰国立约,约中皆用我年号、历朔、文字。……琉球虽小,其服事我朝之心,上下如一,亦断断难以屈从。方今宇内交通,礼为先务。无端而废弃条约,压制小邦,则揆之情事,稽之公法,恐万国闻之,亦不愿贵国有此举动。本大臣奉使贵邦,意在修好。前两次晤谈此事,谆谆相告,深虑言语不通,未达鄙怀,故持据实照会。务望贵国待琉球以礼,俾使琉球国体政体一切率循旧章,并不准阻我贡事,庶足以全友谊固邻交,不致贻笑于万国。贵大臣办理外务,才识周通,必能详察曲直利害之端,一以情理信义为准。为此照会贵大臣,希即据实照覆可也。㉓
此照会的内容可谓据理力争,其中所述的中琉关系,并无虚妄之辞,一来陈述琉球朝贡早已有之,二来强调其在对外交涉中均沿用中国年号、历朔和文字,可以看出,照会所突出的仍然是传统朝贡——册封体制内的中琉关系。此外,照会基于中日《修好条规》对日本进行谴责也非言过其实。然而,该照会却以“暴言”之由被日方拒绝,同年11月21日,寺道宗则对何如璋的上述照会作了如下答复:
前接贵历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来函,所述琉球岛之事,皆已知悉。查该岛之事,有如本大臣前与贵大臣两次会晤,谆谆相告,固系数百年来为我国所属邦土,现为我内务省管辖。不料,今忽接贵简,其文中有一节云,方今我国禁止琉球国进贡贵国,贵国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或云欺凌琉球,擅改旧章,又言废弃条约,压制小邦等语……贵国政府尚[且]未悉我政府有何理由发此禁令,而徒向我政府致有声称此等假想之暴言,是岂重邻交修友谊之道乎?若果由贵国政府饬令阁下,发出此等言语,则知贵国政府似有以后不欲保存两国和好之意也。即烦贵大臣将此情由转达贵国政府可也,为此复照。㉔
日方的答复并没有直面何如璋对琉球所属的疑问,相反避重就轻,一味纠结所谓“暴言”,回避本国政府的强行措施,要求何如璋道歉,如不撤前言,即不再商谈,于是由中国驻日公使馆主导的外交谈判刚刚开始就陷入僵局,在之后十个月内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与外交谈判的停滞不前相比,日方针对琉球的“处置”可谓势如破竹。1879年3月27日,松田道之在首里城宣布“废琉置县”,并强制琉球政府交出所有的文书、账簿。清政府在得悉日本废琉消息后,于同年5月10日向日本新任驻清国大使宍户玑递交照会,希望日方将“废琉为县一事速行停止”。5月20日,何如璋也向寺岛宗则表示了“适值琉球案件交涉之中,难以承认日本政府废藩置县”的立场。然而,寺岛在得悉中国政府的上述照会后,于5月27日,依然言称日本处理琉球,“乃是基于我国内政”,并对何如璋表示:关于光绪四年十二月九日书简中的不当言辞,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显然,寺岛仍是有意刁难,同时也是为了借故拖延对总署照会的答复。此后又有几次交涉,日方也都以类似的理由拒绝答复。
直到十个月后的1879年8月2日(光绪五年六月十五日),日本驻京公使宍户玑将寺岛7月16日发出的《说略》,转交清政府,以作为日本政府对总署前述照会的答复。《说略》内容中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为日本废琉置县寻找理论依据,其中就包括源为朝和舜天身世:
盖琉球为我南岛久矣,其土则弹丸黑子,足当萨摩州一郡覆,地脉绵亘在我股掌之间。(周煌《琉球国志略》所谓东与日本萨摩州隣,一苇之航,而去闽万里,中道无止宿之地者,正符其实也。)其文字(字母用我四十八字即源为朝所授也,文书杂用汉字仮字,皆与我同体)、言语(言语亦与我同种,自称其国为冲绳,冲绳土音屋其惹,始祖为天孙氏,天孙土音阿摩美久即其证也)、神教(岛祠祀我伊势大神、八幡天满熊野神等)、风俗(燕飨用我小笠原流礼,其他中国使臣所记席地而坐、设具别食等皆与我同俗)一莫非我国之物也。……保元中(当宋绍兴时),源为朝居伊豆大岛,浮海略诸岛,至琉球,娶岛酋大里按司女弟,生男尊敦。为朝还大岛,尊敦立为琉球王,是为舜天王(徐葆光中山传信录所谓舜天日本人皇后裔,大里按司朝公男是也。舜天之后,三世丧国。后二百余年尚圆复位,尚圆即舜天之后也云)。㉕
在中日关于琉球归属的外交交涉中,这是第一次将舜天的身世引入谈判的文本。除了加以人种的确认,还分别列举地理、文字、言语、神教、风俗的相同或相似以示“一统”,这里可以看到新井白石《南岛志》在近代外交文本中的回声。另外,《说略》还多次援引清人著述,如周煌《琉球国志略》和徐葆光《中山传信录》,颇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意。《中山传信录》中确实有“舜天,日本人皇后裔”的说法,但《说略》中紧随其后的“后二百余年尚圆复位,尚圆即舜天之后也”却与《中山传信录》完全无关。徐葆光在书中是这样记载尚圆的——“明成化六年(庚寅)、尚圆即位。《中山世鉴》云:尚圆,北夷伊平人——即叶壁山也。永乐十三年(乙未)生,字思德金。其先不可知;或曰义本让位,隐北山,疑即其后也。一云叶壁有古岳,名天孙岳;尚圆即天孙氏之裔也。父尚稷,为里主”㉖。这里实际上是日方在文本修辞上的小把戏,尚圆“舜天之后”的身份是其有意添加的,以注解形式置于《中山传信录》对“舜天”的记录后,并采用“……也云”的暧昧叙述方式,其背后用意可见一斑。
对此,清政府有足够的敏感,1879年8月22日清廷向宍户玑递交照会,内称:“本王大臣接阅来文所叙琉球各节,在贵国以琉球为贵国所属,固自谓信而有征矣。本王大臣查琉球自其国王舜天至尚泰,凡三十八代,中易五六姓。即谓舜天系国人源为朝所出,而舜天之统,三代已绝。尚泰之祖尚圆,仍是天孙氏之裔。……即就其地势、文字、神教、风俗而论,虽有近于贵国者,亦何尝不近于中国。至其言语,间有与贵国通商贸易者,能通贵国语言,余则仍操土音。是谓之两属之国则可不得谓之贵国专属也”㉗。清廷的照会捕捉到日方对尚圆身份的伪造,坚决予以反驳,也分别就地势、文字、神教、风俗和言语针锋相对做了说明,有理有据。但从中可以看出,清廷的用意仍在维持“两属”,希望日本同样以华夷秩序中的藩属关系去对待琉球,这与明治政府基于近代民族国家领土观念的版图欲望显然背道而驰。
琉球人向德宏在得知《说略》后,更是义愤填膺,奋笔疾书,分列十条意见进行反驳,尤其是关于《说略》极力渲染的日琉亲缘关系,向德宏反问道:
天孙氏传二十五世,为权臣利勇所弑。浦添按司名尊敦者,起兵诛利勇,诸按司推荐尊敦为君,即舜天王。舜天王父源为朝,乃日本人,遭日本保元之乱,窜伊豆大岛。嗣复浮海至琉球,娶大理按司之妹,生尊敦,即舜天王也。自舜天王至尚泰王,凡三十八代。中间或让位于人,或为所夺,如此者几易五六姓,舜天王之统三世已绝矣。察度王洪武年间,赐琉球名巴志王,永乐年间赐姓尚,至尚泰王,或虽有嗣承,同系天朝赐国号受姓之人。尚泰王之祖尚圆王,伊平屋岛之人,乃天孙氏之裔也。日本何得认为日本之后耶?总归时异世迁,断不能妄援荒远无稽之论,为此神人共愤之事。如按此论,则美国百年前之君为英吉利人,刻下英吉利能强要此美国之地乎?地球内如美国者极多,纷纷翻案,何有穷乎?㉘.
不论是对源为朝血统三代已绝的说明,还是援引美英的例子,向德宏都在试图反驳日琉同祖说,斥之为“荒远无稽之论”,但对于舜天的日本出身,他也是承认的。此外,向德宏还针对《说略》中列举的地势、文字、神教、风俗和言语的问题,一一驳斥。
上述寺岛宗则的《说略》、清廷的备文复照以及琉球人向德宏对《说略》的条陈,集中反映了当年围绕琉球归属问题所产生的分歧与矛盾。借由舜天身世所建构的琉球与日本的亲缘关系是《说略》叙述的重点,亦为论述地势、文字、神教、风俗、言语一致性提供了“史实”的支撑,而其叙述结构与前述《南岛志》却是惊人的一致。
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看到黄遵宪诗中并不起眼的“舜天”身后隐匿着复杂的身世传说,其偶然的出现却牵动起前后500年东亚世界历史/文学写作的脉动——一面是《保元物语》《椿说弓张月》《中山世鉴》为代表的日文/琉球文书写,一面是《中山世谱》《南岛志》《大日本史》《中山传信录》为代表的跨越国境的汉文书写。在彼此反复、胶着的征引、转写和叙述中,文本的真实已赫然凌驾历史的真实。而近代之后,再现于政治外交文本中并引发轩然大波的“舜天”则见证了东亚社会由传统的册封—朝贡体系向以万国公法为基础的条约体制转变过程中愈发膨胀的领土欲望和扩张的野心。对于明治政府而言,怎样讲述帝国日本与琉球的亲缘故事成为对清外交实践的重头戏,在浓墨重彩的演绎下,“舜天”是当仁不让的最佳男主角。在基于近代国家关系的外交谈判中,由前近代文本建构的“历史”叙述为论争提供了背景和焦点,亦成为验证现代国家关系的对象物。
四 “琉球”还是“流求”?
如前所述,使日期间亲历琉球争端的外交交涉、对琉球历史有相当了解的黄遵宪在离开日本若干年后有感于琉球兴亡命运,特赋长诗,取名“流求歌”。诗题中的“流求”是中国史料中最早出现的对琉球群岛的命名㉙,出自唐贞观十年完成的《隋书》。在《隋书》卷八十一列传四十六《东夷》中,“流求国”在高丽、百济、新罗、靺鞨之后登场——“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㉚虽然这里的“流求”最早出现,但并没有固定下来——《隋书》以降,陆续有“留仇”“留求”“流梂”“幽求”“流虬”“琉求”等不同的名称指代㉛,直至1350年《岛夷志略》中“琉球”的出现,特别是《大明实录》的“太祖实录”中对洪武五年明太祖派杨载作为册封使出使琉球国的记录,才使得“琉球”的名称开始逐渐固定下来。尽管此后关于琉球群岛的叫法也没有完全统一,在中文文献中也偶尔出现了“瑠球”“琉求”“流球”等不同的表述,但大体上,还是以“琉球”为主的㉜。到了清朝,更是如此。可以佐证的是,《通典》在唐和北宋的版本中皆写为“流求”,而清版则写作“琉球”;《文献通考》初版本中的“流求”在清代版本中也改了“琉球”。也就是说,在黄遵宪的时代,“琉球”是通行的对琉球群岛的称呼,黄遵宪也习惯于此,这一点从他与相关人士的笔谈、信函、照会中也能看出㉝。那么他在诗歌标题中为什么会使用“流求”呢?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就在同一首诗的结尾,诗人感叹“只有琉球恤难民,年年上疏劳疆臣”时使用的就不再是“流求”。㉞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钱仲联先生在该诗笺注中做了简略的解释——“宋元以前所云流求,指今之台湾,而公度此诗,乃借流求以指琉球群岛之琉球国”㉟。这个简短的解释释放出更多的疑问,缘何宋元以前的“流求”后用来指称台湾呢?这与琉球群岛又是怎样的关系?这和黄遵宪的诗作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隋书》中关于“流求”的记载被后世史书继承,如《北史》《通典》《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新唐书》《通志》《诸蕃志》《文献通考》《宋史》等。而从明代起,随着“琉球”成为相对固定和通行的说法,“流求”日渐被淡忘。不过,当时间到了19世纪末,情况有了改变。1874年,法国汉学家德里文(Hervey de Saint-Denys)在翻译马端临《文献通考》部分文本的过程中,对“琉球国,居海岛,在泉州之东,有岛曰澎湖,烟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产生怀疑,遂进行研究,发表论文《关于台湾与华人所称琉球诸岛》,提出“隋代流求是泛称今日台湾与琉球群岛,但隋人所到达的流求实际上是台湾”的观点㊱。1895年,荷兰汉学家希勒格(Gustav Schlegel)对圣第尼的观点加以演绎,杂取17世纪荷兰人在台湾南部的所见所闻与中国史书中的相关描述进行比证,提出“吾人敢与艾耳维氏共断定曰:古中国地理家之琉球,即今之台湾。至今之琉球,自1382年始,始有此名,即《明史》所谓中山山南山北之琉球也。此琉球吾人将来再研究之,兹仅考证古之琉球”㊲,他指出隋朝的“流求”、元朝的“瑠求”指的都是台湾,而从明朝开始称冲绳列岛为“琉球”。1897年,任教于东京大学的德国学者李斯(Ludwig Riess)出版《台湾岛史》,在书中他修订了圣第尼和希勒格的部分看法,但还是坚定地认为,隋人所谓水行五日所到“流求”只能是台湾,而中国人习惯将琉球群岛以及台湾都称为琉球。相比于圣第尼和希勒格,李斯的这一论点在日本影响更为广泛,据梁嘉彬的考察,《台湾岛史》问世后的一段时间内,除了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把《隋书》中的“流求”视作琉球群岛外,其他台湾相关研究几乎都遵从李斯的观点。㊳不仅如此,这些学说还被不同程度地译介到中国,冯承钧翻译希勒格就是一例,此外亦有研究者指出《新元史》作者柯劭忞对希勒格学说的接受进而影响到国内学界的观点㊴。由此来看,钱仲联的笺注内容有极大的可能是受到这一脉络的影响。
黄遵宪创作《流求歌》大约是在1891—1903年,尽管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在他创作之际是否了解上述关于“流求”“琉球”具体所指的争论㊵,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诗歌题目的处理上,他采用了差异化的写作,即选择了不同于当时的通行写法和个人书写习惯的“流求”。尽管《流求歌》是一首内容丰富的长诗,但是在诗中出现同一个词在标题与内文上写法的差异也是罕见的。这是否可视作诗人的一种抵抗呢?以中国史料中对琉球群岛最早的命名来对抗琉球被日本侵吞的命运。外交斡旋的失利、面对琉球使臣的无力、维持/恢复两属希望的破裂……在中日琉球争端中黄遵宪经历的种种挫败都只能通过当下已不常用的“流求”得以纾解。尽管诗中对中琉关系的追溯始于明朝,但由《隋书》的记载所唤起的“最早的”连带感却无时无刻不作为精神和书写资源温情脉脉地存在着。那么这里的“流求”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所指,而转变为一个诗歌意象。可以佐证的是,在黄遵宪另外一首慨叹中法战争的《越南篇》中写道:“流求忽改县,句骊不成国”㊶,这是黄遵宪诗文中“唯二”的第二个“流求”。用“流求”代称被强制“冲绳县”了的“琉球王国/琉球藩”、以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骊”指代朝鲜,这样的修辞选择凸显的是语词背后的典故、文献、文化和历史脉络,这不再是一个个具体的地理坐标,而是富含了隐喻色彩的诗歌意象。而诗人在《流求歌》的篇末感叹的“只有琉球恤难民,年年上疏劳疆臣”针对的则是“现实琉球”,是经过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即诗中“毡裘大衣”)外交调停无果、已然被纳入日本帝国版图的“冲绳县”。
西里喜行在对《流求歌》的翻译和解读中曾指出,黄遵宪在诗歌中只是对琉球表示同情,而从未积极地表示过有必要救助琉球㊷,并推测由于黄遵宪本人认同明治维新,因而“废琉置县”作为明治维新延长线上的一个环节而具有了某种“历史必然”。西里喜行此番论述的问题,首先在于他忽略了《流求歌》的创作时间,以这一创作于琉球争端十几年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作品去印证黄遵宪当时的态度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其次,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对诗歌的解读不能仅仅局限于表面的词句,诗歌的结构、意象的隐喻以及意象与意象之间相互作用的“网络”都应该成为解读的对象。甲午战争之后,对明治日本的侵略扩张有了切肤之痛的黄遵宪如何在诗歌中讲述琉球的故事,对诗人来说,这已经不光是一个诗技上的考量。在现实琉球和意象琉球的往复之间,诗人回望的目光是否也同时掠过被割让的台湾?
马普龙的脖子较短,但是相当结实。马普龙的前肢不长,每只手爪上长有三个有着锋利指甲的指头,可以用来固定猎物。与前肢相比,马普龙的后肢长而粗壮,正是靠着两条有力的后肢,马普龙才能够站立和奔跑。身后长长的大尾巴,则可以使它们在直立行走时保持身体平衡。
五 结 论
《中山世鉴》在我国第一次公开出版可见《国家图书馆馆藏琉球资料汇编》,根据序言部分的介绍,这里收录的《中山世鉴》是根据一个钞本影印而来的。该版本《中山世鉴》正文前三页文字说明了底版钞本的来历。第一页是明治12年(1879)3月6日日本外务省书记官致内五大书记(大丞)松田道之的照会,说明外务省需用《中山世鉴》,请即将第三次出使琉球的松田道之设法借回或买回日本,誊抄后可还给内务省。第二页是松田内务大书记官于同日致外务书记官之照会,说明内务省亦无此书,且此书为非卖品,自己到琉球后一定借到,抄写后交外务省用。第三页为同年7月9日松田致外务书记官照会,称其已于琉球借到《中山世鉴》,抄写完毕现送外务省存用。这就表明这一抄本为日本政府于1879年派内务大丞松田道之代表政府实施吞并琉球之际,设法“借原书”,“誊写完毕”,送存外务省的。㊸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间非常特殊,正是1878年10月何如璋照会被日方指为“暴言”、中日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之时,而此僵局直至翌年8月才被打破,宍户玑将寺岛宗则所拟《说略》转交清政府。如前所述,这是中日双方在外交场域第一次谈及“舜天”的问题。而这一切,从时间上推测,是在外务省看到《中山世鉴》之后。那么是否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在此之前,尽管从《保元物语》到《椿说弓张月》,“源为朝渡琉”以及“舜天是源为朝之子”的传说故事在日本已经相当普及,但这种日本国内单方面的文学叙事还不足以支撑起要在外交场域大展拳脚的所谓“日琉同祖”论,日方还须从琉球国史中找到更为“可靠”的史实根据,应对与清廷的外交交涉。基于此种需求,《中山世鉴》显然提供了最佳的“证明”。
与这样的一种“有意为之”相比,黄遵宪等清朝外交官对由《中山世鉴》等文本书写“史实”化了的舜天日本身世缺少敏感和质疑,未能识别借由舜天建构起的“日琉同祖”叙述的关节点。在这里可以看出,相对于领土扩张和政治建构,文学和历史书写中的帝国主义“叙事”更为隐蔽而不易被察觉。但与此同时,仍然是这位外交官诗人自觉地在传统历史/文本资源中找到了用以对抗明治日本吞并琉球这一政治行为的书写符号和诗歌意象为我所用。“流求/琉球”首先是作为地域概念存在的,但随着明治日本在武力强制下的一系列政治操作“琉球王国—琉球藩—冲绳县”的施行,“琉球”称谓的合法性被强行剥夺而岌岌可危,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叙述出曾经的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历史共享和文化连带成了困扰诗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由此,《隋书》中的“流求”、同时也是在19世纪晚期被热议的“流求”因其超出字面意义的隐喻色彩被诗人应用在诗歌当中,以陌生化/差异化的修辞效果寄寓诗人的抗争。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帝国主义的领土欲望叙事、现实世界的外交博弈,以及诗人的书写抵抗都共同交会在了黄遵宪的这首《流求歌》当中。
注释:
①钱钟书:《王静安诗》,见《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3页。
②③④㊷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関係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術出版社、2005年、541~564、565、565、565頁。
⑥⑦⑩⑫⑭㉟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2、587、323~324、322~331、323~324、323页。
⑧尚球『廃藩当時の人物』、那霸市役所絡務部市史編集室編:『那覇市史·資料篇』(第2巻中の4)、那霸:那霸市役所、1971年、634頁。
⑨如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日文版见第541页及564~567页;对应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见第498页及第516~519页)。需要指出的是,中文版《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中将黄遵宪长诗《流求歌》写作“琉求歌”,这一点非常奇怪。而西里喜行原文以及《人境庐诗草》的通行的版本均为“流求歌”。
⑪抄本中共有诗247首,大致相当于排印本的一至六卷,两相比照,抄本中有24题全删,共60首诗;题目存留而删去其中几首诗者有16项;另外有三首诗删改律诗为绝句。而具体到《人境庐诗草》第三卷,增删情况如下:抄本有而排印本无者5题21首,抄本无而排印本有者9题35首诗,两者皆收者有10题13首。《流求歌》并不在抄本收录当中。
⑬郑海麟:《黄遵宪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页。
⑮向象贤:《琉球国中山世鉴》,见殷梦霞等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841~843页。
⑯这部分内容可见《保元物语》上卷中「後白河院御即位の事」、「新院為義を召さるる事 付けたり鵜丸の事」、「新院御所各門々固めの事付けたり軍評定の事」的部分和下卷「為朝生捕り遠流に処せらるる事」部分。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的“古活字本”《保元物语》见『保元物語 平治物語』(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1)、永積安明 島田勇雄校注、東京:岩波書店1978年版、344~399頁。
⑰塙保己一編、太田藤四郎補『続群書類従』(第13輯上)、東京:続群書類従完成会、1959年、355頁。
⑱『古事類苑』(地部第2卷)、1373~1374頁(日本国文学研究資料館古事類苑データベースhttp:∥shinku.nichibun.ac.jp/kojiruien/html/chib_2/chib_2_1373.html)。
⑲㊸殷梦霞等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第825,825、827、829页。
⑳何慈毅:《明清时期日本琉球关系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㉑源光圀修『大日本史』(卷241)、東京:徳川総子1907年版。
㉒转引自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㉓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11巻、271頁(日本外務省外交文書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http:∥www.mofa.go.jp/mofaj/annai/honsho/shiryo/archives/mokuji.html)。
㉔日文原文参见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11巻、272頁;中文翻译采用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第182~183页。
㉕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12巻、182~183頁。
㉖徐葆光:《中山传信录》,见于《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九辑),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121页。
㉗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12巻、186~187頁。
㉘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天津大公报社1932年版,第156页。
㉙袁家冬、刘邵峰:《琉球群岛的地缘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页。
㉚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23页。
㉛㉜小玉正任『琉球と沖縄の名称の変遷』、那霸:琉球新報社2007年版,10、165~187頁。
㉝笔谈:1878年11月21日、大河内辉生、黄遵宪、何如璋、石川鸿斋笔谈中均写作“琉球”;1879年3月2日、宫岛诚一郎、黄遵宪、沈文荧笔谈中写作“琉球”。书信:1880年4月23日《致王韬函》写作“琉球”。查《日本国志》两个代表性版本浙江书局重刊版(版本、内容、形式同初刻本)和羊城富文斋改刻本其中涉及琉球的内容均写作“琉球”。
㉞《流求歌》第一次公开发表在《新民丛报》1903年第42—43期合本时该诗句写作“只有流球恤难民,年年上疏劳疆臣”(黄遵宪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诗歌作品是梁启超从不同渠道获得的,比如通过在日本从事商务和外交活动的梅州人,或是通过南洋的报纸,或是黄遵宪本人在通信中抄录给他的,具体的路径已不可考);而《人境庐诗草》最早的定稿本(即1911年横滨排印本)写作“只有琉球恤难民,年年上疏劳疆臣”,后来的版本均以定稿本为准。
㊱Marie-Jean-Leon Hervey de S aint-Denys, ‘Sur Formose et les Iles appelees en chinois Liou-Kieou’(1874), Patrick Beillevaire, Ryūkyū Studies Since 1854:Western Encounter Part II(Volume II), Curzon Press and Edition Synapse, 2002, pp.103-121。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晚期,法国汉学家突然对台湾等东亚岛屿的历史地理产生兴趣是否与法国自1850年代开始的对越南的殖民存在某种关联?笔者希望能够就此问题请教方家。
㊲希勒格1895年在《通报》(T’oung Pao)第六号发表《琉球之所在》(Le Pays de Liuoukieou)一文,1928年被翻译收入冯承钧《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今参考版本为冯承钧《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117页。
㊳梁嘉彬:《琉球及东南诸海岛与中国》,台中:东海大学1965年版,第231页。
㊴亓玉花:《历史地理文献中琉球名称之考述——以〈隋书·流求国〉地理考证为中心》,中国海洋大学2010届硕士学位论文,第8页。
㊵鉴于《日本国志》曾多次引用《隋书》,故推测黄遵宪对《隋书》中的“流求”有一定的了解。
㊶《越南篇》最初发表在1903年第42—43号《新民丛报》中,后陆续被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入《人境庐集外诗辑》(中华书局,1960年)、陈铮编入《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收录,相关诗句均写作“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