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身外的青春”
郜元宝
一
从清末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这二三十年,“少年”无疑是文化新潮中最重要的一个话题。梁启超《少年中国说》(1900)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直到今天,在各种媒体上还经常可以听到“少年强,则国强”的口号。青少年教育和成长,始终牵动着亿万中国家庭的心。
五四前后,《狂人日记》“救救孩子—”的呐喊振聋发聩,加上进化论思想的巨大影响,所谓“青年必胜于老年”,老年人要为青年人让路作牺牲,这种“幼者本位”的观念被鲁迅、周作人引进中国,也迅速流行开来。
当时的“少年”“幼者”,其主体相当于今天的“青年”,也包括今天所谓少年,因为少年转眼就成了青年。当时没有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说法,在青年和少年中间也没有划出清楚的界线。
青年(或青少年)的地位被抬得如此之高,在中国可谓亘古未有。这当然不可能是传统读书人的想法。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是《新青年》杂志,汇聚于此的是一帮自称“少年”的新派知识分子。《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一九一五年创刊时,主编陈独秀三十六岁,鲁迅三十四岁,周作人三十岁,钱玄同二十八岁,李大钊二十六岁,胡适、刘半农同龄,才二十四岁。一年后《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再过一年“文学革命”正式发动,上述几位也不过添了一两岁,今天说起来都还是青年。这些人发起“新文化运动”,当然要以“少年”为主体,老年人根本没地位。

《新青年》前身《青年杂志》,1915 年创刊号

《老实说了吧》刘半农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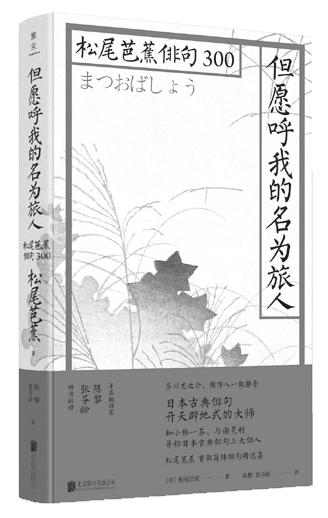
《但愿呼我的名为旅人:松尾芭蕉俳句300》[ 日] 松尾芭蕉著陈 黎 张芬龄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年版
二
然而当时社会上传统的“尊老”思想还很流行,这就势必要和“少年中国”“幼者本位”的观念发生激烈碰撞。但是随着新文化运动节节胜利,白话文很快战胜文言文,创作白话新文学的绝大多数是青年,所以不管“尊老”的思想如何顽固,如何强大,至少在新文化运动内部,活跃分子是清一色的青年,是非对错由他们说了算。
当然有例外。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五十一岁,梁启超四十六岁,当时都是老年了,但他们主动放弃老人和长者的姿态,甘心乐意跟在“一帮少年”屁股后面跑,被后者欣然接纳,引为同道,多少也能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
但与时俱进的老年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都被推到青年人的对立面,因此“父与子的冲突”非常普遍。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新文化运动主角们写到父辈或祖父辈,几乎千篇一律要加以丑化和漫画化,比如鲁迅《祝福》中的四叔,巴金《家》中的高老太爷及其不成器的儿子们,稍后还有茅盾《子夜》中的吴老太爷,钱锺书《围城》中的方遯翁。老年人几乎代表了糊涂、落后和闭塞,反动、腐朽而垂死,可笑而又可憎。对老年人的这种文化定位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创作。老年人的地位一落千丈。钱玄同甚至主张,人过四十,就该自杀。
这当然太偏激,也太簡单,必然激起反抗。但文坛、学界和舆论媒体既然被青年人和拥护青年的个别中老年权威所掌控,老年人的声音就很难发出来。我们现在看严复等人的通信,多少还能感受到那些迅速被推到历史舞台边缘的老人们的悲哀与无奈。
三
有趣的是“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终于有人以老年人的身份站出来为老人说话了,但并非章太炎、严复、林纾等曾经呼风唤雨后来被边缘化了的老人,而是新文化阵营内部的领袖人物。他们刚刚还以“少年”自居,一转眼发现自己也老了,就凭借自己所拥有的话语权,开始为老人说话。
五四以后,刘半农有句名言,说转眼之间,他们这些五四人物就被推到“三代以上”,不仅成了老人,还简直成了“古人”!刘半农是感叹时代发展太快,“后生可畏”,但他对后起之秀也很不满,禁不住要以老年人的口吻进行攻击。刘半农的杂文《老实说了吧》,就是说“我们”这班如夏商周“三代以上”的老人固然没啥了不起,但“你们”年轻人也不怎么样!刘半农说出这番话,爽快是爽快,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在文坛新秀们看来,尽管刘半农从法国辛辛苦苦挣回来货真价实的博士学位,学到许多新的治学方法,但他本质上已经站到青年的对立面,变成满身晦气的过时的老人了。

《老老恒言》〔清〕曹庭栋撰中华书局2011 年版
这一点,刘半农很有代表性。五四以后,所谓“京派文人”往往就属于这个类型,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形象通常都是些暮气沉沉的老人。并非他们真的老了,而是他们的思想起了变化,选择了和“少年时代”不尽相同的新的文化立场。
四
周作人五四时期写过一篇纲领性文章叫《人的文学》,但他所谓的“人”,只是抽象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并不包括老人。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开始大谈老年问题,一九三五年还专门写了篇杂文叫《老年》,对日本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兼好法师和德川幕府时代的诗人芭蕉赞不绝口,因为他们都有关于老人的通达言论。钱玄同说人过四十就该自杀,很可能就是受了周作人所介绍的芭蕉的影响。
回顾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周作人觉得大概《颜氏家训》有一点关于老人的通达意见,但他没有找出来。他所知道的只有陶渊明某些诗句,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的一篇《杂记》,和乾隆年间一个叫曹庭栋的人所著的《老老恒言》。
周作人特别欣赏《老老恒言》,说它“不愧为一奇书,凡不讳言人有生老病死苦者不妨去一翻阅,即作闲书看看亦可也”。周作人对这部“闲书”念念不忘,三年后又写了一篇书评,题目就叫《老老恒言》,反复说这是“一部很好的老年的书”,“通达人情物理,能增益智慧,涵养性情”,其中关于“养老”的论述,“足为儒门事亲之一助”,就是有助于推广《论语》《孟子》《礼记》中那些尊老养老的“孝道”。
周作人对某些同龄人为老不尊、整天跟在年轻人屁股后面跑,深表不屑。有人说这是在讽刺吃过青年的亏却仍然不肯放弃青年的鲁迅,但也令我们想起蔡元培和梁启超。
周作人主要反思,五四以后,为何会出现盲目抬高青年而一味打压老年的偏激思想?他发现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作家、思想家、言论家们很少想到人是会老的这一事实,因此为老年人着想、为老年人写作、适合老年人看的书寥若晨星。好像老年人就不是人似的。这就逼迫那些不甘落伍的老人只好假装忘记“老丑”,混在年轻人的队伍里胡闹。

鲁迅《颓败线的顫动》收入《野草》北新书局1927 年初版本
所以周作人呼吁要把老年人也算在“人”的概念里,给老年人适当的空间,至少要有一些让老年人说话、适合老年人阅读、可以听到老年人心声的书籍。
五
一般以为,直到一九二七年“广州事变”之后,因为看到青年的种种不良乃至罪恶的表现,鲁迅才声称他的“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论被“轰毁”了。
其实鲁迅早就怀疑“老人/青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一九二五年所作散文诗《希望》就说:“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是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所谓“身外的青春”,就是他所深爱的“青年人”。但《希望》接着又说:“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都衰老了么?”这就是鲁迅对于青年的怀疑和责备了,难道你们也都老了吗?他的结论是,“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就是说,即使没有青年同志,他这个老人也不怕独自去战斗。
如果说《希望》显示了鲁迅对青年的怀疑和不信任,那么另一篇《颓败线的颤动》就是写青年对老人恩将仇报,老人对青年爱恨交加。
《颓败线的颤动》讲一个女人,年轻时为了养活女儿,不得不去做妓女。但女儿长大之后,竟然跟女婿一起还拉着他们的孩子,声讨母亲年轻时的屈辱经历。他们说“我们没有脸见人,就只因为你!”“使我委屈一世的就是你!”“你还以为养大了她,其实正是害了她,倒不如小时候饿死的好!”面对这种指责,垂老的妇人无言以答,心中翻江倒海,激荡着“眷恋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种种矛盾的感情。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简直要“出离愤怒了”。
鲁迅始终对青年寄予厚望,他深知中国的希望只能在青年。但在与青年交往合作的过程中,他往往又忍不住失望乃至愤怒。他临终之前不久发表的对左翼青年的公开信,就毫不客气地说,在号称进步的左翼文学界有不少“‘恶劣的青年”。鲁迅杂文所攻击的对象,往往就是那些活跃于文坛的青年。
鲁迅对青年的怀疑、失望和责难,早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次笔战中就火力全开了。对自己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魏建功,鲁迅曾经这样大发雷霆:“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回想当初“救救孩子”的呐喊,岂可同日而语?
总之步入中老年之后,第一代五四人变得更稳健,更深刻了。他们提出“老年”问题,并非否定英姿勃发的青年生力军,更不是要回到以老年为本位的旧传统,而是强调,一个社会既要有青年的声音,也要有老人的声音。如果不把老人当人,老人的想法无论对错都无人倾听,这个社会就不够健全。
五四一代讨论老年问题,当然远没有他们当初呼喊少年时那么响亮。今天中国早已是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生态心态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此时此刻,回顾五四一代对青年和老年的论述,就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