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的现代转向
陈建华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个里程碑著作,今人谈词学很难绕过这道坎。最为脍炙人口的是他的三种“境界”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人间词话》 王国维著《蕙风词话》 况周颐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
今天我们常把这段表述抽离出来,看作伟大人物的理想追求与完美人格的寓言,而分别从晏殊、柳永和辛弃疾的词作中摘句来形容三种“境界”,极富象征演绎性。王国维把“大词人”与“大事业、大学问者”比肩,具备横空八极、坚忍不拔、睿智洞见的品格。的确,他在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哲学基础上构筑了一套足以回应现代性召唤的诠释架构,并声称“遽以此意解释诸词”,要对历代词作作出评价,而在如此高调的“境界”面前,整个词史经受考验,晏殊、欧阳修等“诸公”要自叹弗如,恐怕连“不许”也谈不上。
《人间词话》开卷便揭橥:“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人间词话》第1则,下文仅标数字)所谓“晏、欧诸公所不许”的“解释”,事实上是对词史的一次现代性价值重估,他独尊“五代、北宋”的词作,对南宋以来词的发展与成就几乎一笔抹杀,其气魄令人震撼。王国维站在现代的门槛上,与世界文学风云际会,在他看来南宋以来词学发展走错路头,斤斤于形式的雕虫小技,已成为一种区域性艺术体验,因此不再以传统词学的“音律”“雅正”等作为其出发点,将其“境界”这一核心概念建立在“主观”与“客观”、“物”与“我”的二元论支柱之上,基本上接受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哲学认识论的成果,标志着一次哲学与文学观念的中土移植。
什么是“境界”?首先“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6)。“境界”是人心与景物遭遇之际所引起的情绪体验,而文学描写即是对投射于我们心体的景物映像的语言行为。这种理论无甚新奇,但什么是“真景物、真感情”则取决于“自然”这一“境界”说的关键概念。他指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2)无论“写境”还是“造境”必须“合乎自然”,这个“自然”指主观感受的外部世界,“写实”即对世界实像的再现,不过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这世界必须是真实可见的,而“理想”指超乎“写实”的想象与反思功能,也不能脱离可见的“自然”,否则就不成其为“境界”。他又进一步说:“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理想家亦写实家也。”(5)

《哲学和自然之镜》[ 美] 理查德·罗蒂著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
对于“自然”的外在世界及其投影于我们人脑的认知,这一哲学认识论并非中国本土所有。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哲学和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一书中指出,如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格言,确立了人相对于外在世界的主体存在,通过感觉与思辨达到对世界真实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知识体系,而这些首先通过视觉机能,镜像般映现于人脑的外物也即被认作“再现”(representational)的自然。罗蒂认为西方的哲学认识论实质上是一种语言建构,这种对真实世界的认知与诠释,给人们的多元选择带来局限。且不论罗蒂的挑战性反思,事实上从文艺复兴以来通过康德等人反复讨论与阐述而建构的人与世界的二元体系,今天几乎成为我们的常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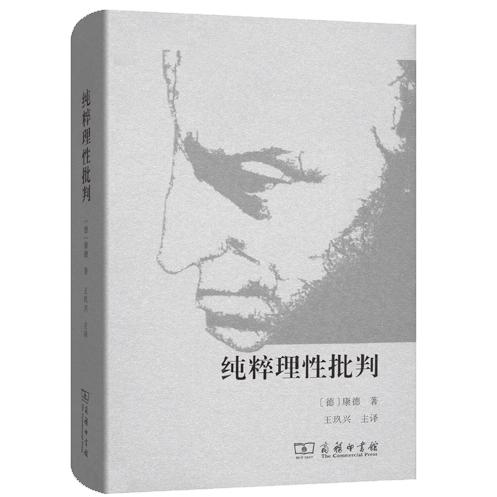
《纯粹理性批判》[ 德] 康德著 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18 年版
王國维在一九○四年发表《红楼梦评论》,深受叔本华悲剧观的影响。《人间词话》发表于一九○八年,其中的认识论则渊源于康德。早年王国维研究西方哲学,遍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叔本华、尼采、洛克、休谟、霍布斯等人,而最为他倾心且反复深究的是康德。一九○三年他在《汗德像赞》中颂扬康德“万岁千秋,公名不朽”,可见格外推重,而“人之最灵,厥维天官;外以接物,内用反观。……观外于空,观内于时;诸果粲然,厥因之随”等语则涉及康德的认识论。所谓“观外于空,观内于时”,即他在一九○四年的《汗德之知识论》中所说:“汗德既以知觉之对象之空间及时间的关系,全为心之形式”,“盖自彼观之,感官之性质,乃我心之观物时一偏及偶然之状态,而空间及时间之形式,乃吾心之普遍及必然之状态,而万物皆于此中显出者也”。在《人间词话》中关于人心内外观照的表述,如:“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60)不同的是“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属于生命体验,而“出乎其外”则具反观性质,能超越感性表象而达到“高致”的境地。心之内外观照也含有“写实”与“理想”的关系:“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草共忧乐。”(61)因此再现自然须情景交融,此为“写实”的真谛;另一方面如果赋予情感表现以“理想”,具有“言外之意”,更有所寄托,这就不仅关乎想象,也有赖“大事业、大学问家”的知性与伦理判断。
这些跟“境界”的“真景物”有关,那么何谓“真感情”?王国维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18)李后主的《虞美人》:“春花秋叶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或如《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暖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确,这两首词真实表达了一位亡国之君的悔痛,引起读者的深刻同情,可谓千古绝唱。王国维要求诗人表达生命意义的深切感受,像这样“以血书者”当然是“真感情”的樣板。他又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18)这里不无过度诠释之嫌,似不止含有他曾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的叔本华式的悲剧情怀,而更具慈悲众生的超越性,体现了王国维的末世悲怀,其中含有“大事业、大学问家”的理想投影。
李后主的作品之所以感人,不仅在于内容,还在于其对于“自然”的内在与外在体现,这就牵涉“隔”与“不隔”这一有关“境界”的重要论述。这固然是后主的“赤子之心”的自然流露,但从语言角度看,他把自己的处境与景物表达得如此真切,让人直接进入他的感情世界,与之交流互动,字字与“血书”密吻无间,所谓“得鱼忘筌”,语言失去了它的物质性,因此“不隔”。
王国维主张“不隔”,反对“隔”。大多数词作离不开因景抒情,他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41)这些例子确实精彩,但有的地方颇费斟酌,比方欧阳修《少年游》上半阕:“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这两句倒置),行色苦愁人。”王国维认为景色得到真切再现,“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对于下半阕“谢家池上,江淹浦畔”这两句,他说:“则隔矣。”(40)因为用了谢灵运和江淹的典故,似给“池上”和“浦畔”加了附加物,阻碍了景物本来面目的直接呈现,便产生了“隔”的效果。其实欧阳修的原句是:“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全宋词》,中华书局1980年)作者在抒发“行色苦愁人”的感情时,联想到谢灵运的《登池上楼》和江淹的《别赋》,于是将文学名篇嵌入自己的文本,与前人的“吟魄与离魂”相重叠,产生不同时空的情感交流,这不仅使感情表现复杂化,也增强了“行色苦愁人”的主题。就“文学性”来说这样的修辞手段是值得称道的,但王国维提倡对景物的“自然”再现,遂把这种修辞看作一种多余的形式而加以否定。
的确,过于讲究修辞形式会产生流弊。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把“代词”作为一种重要修辞手段,如“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35)。王国维对此十分反感:“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34)滥用“代词”的套路有碍创意,并不可取。但王国维以“隔”与“不隔”划线,所谓:“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39)尤其对于南宋以下几乎一刀切,以“隔雾看花”来形容姜夔、周邦彦、吴文英等人的作品,显示他反对“形式主义”的态度。

《全宋词》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80 年版
对姜夔的批评尤为严厉,最典型为这一段:“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39)所引之句分别出自《扬州慢》《点绛唇》和《惜红衣》三首,皆意象生动,情景交融,写得美。但为何王国维指责它们“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呢?这跟他深受康德认识论的影响有关。凡写实或虚构都必须遵从“自然之法则”。那些“不隔”的范例,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等,景物之间的因果链乃是“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的体现。而从“冷月无声”“商略黄昏雨”与“说西风消息”的例句看,由于作者的主观移入,景物变成含情的主体,这在王国维看来含有斧凿的痕迹,使景物的本真形态遭到扭曲,不属“合乎自然”的“真景物”。景物仿佛被人为涂上一层主观色彩,做不到“语语如在目前”,犹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了。
姜夔的《暗香》《疏影》一向被视为其代表作,词中借咏梅怀旧思人,记忆中意象影绰纷呈,融合梅花的文史典故,气氛清丽朦胧的气氛,意涵含蓄以致难以确解,而在造语、音韵与结构方面刻意精致。张炎在《词源》中标举姜夔的“清空”风格冠绝一时,更赞赏这两首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这遭到王国维当头棒喝:“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38)他不否认“清空”高“格调”,但以为过于讲究形式,套路太深,与“自然”毫不搭边。《人间词话》毕竟以“大事业、大学问家”的人格“气象”为标格,无怪乎一再拿苏轼、辛弃疾作比较:“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45)又说:“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46)与苏、辛相比,姜夔显得器局狭窄,钻牛角尖,但还称得上“狷”,仍有几分可取,至于张炎、吴文英等后来追步者则如“乡愿”,更没出息了。
今日所见《人间词话》共一百四十二则,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年《国粹学报》上的六十四则是王国维自己的节选本,已和盘托出“境界”宗旨,通过西方哲学认识论引进一种新的世界观,给中国词学传统带来现代性转折,也是沿着清代常州词派重视内容的路向,摒弃“形式主义”,既与世界文学接轨,也应顺了新媒体时代大众的文学美育的趋势。一方面是以“新名词”为核心的科学、理性的二元论,另一方面运用诗词文本与象征、隐喻的手段将“诗无达诂”的诠释方式发挥到极致。“境界”本身既是概念,又是意象,辅之以同类的“气象”概念,而“境界”说的三段语式与大量简捷而睿智的二段论语式,如“理想”与“写实”、“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隔”与“不隔”等,与“境界”说等形成对应、复调与参差的互文论证关系。这一“境界”论的语言建构方式极其奇特而复杂,却造成一种毫无违和感的中西兼容的批评范式,犹如七宝楼台储藏着无数密码,至今激发我们的诠释热情,也可见在二十世纪初知识结构与学术话语转型中王国维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价值选择与重构,这在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人间词话》主张词人的生命体验与人格修养、自然之情的真切抒发、对外界的深刻观察与反对矫揉造作等,形塑了中國人的现代文学观念,至今仍受其惠赐。确实,在理解与接受西方人文思想方面,王国维或许比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更为客观与深入。“境界”说以康德的哲学认识论为内核,尽管被包裹在大量中国传统批评语汇与诠释方法之中,实即一种西体中用的新范式。而对词学传统的激进反转,尤其是对讲究形式方面的扬弃,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一种简约化动作,与列文森把中国山水画的笔墨意趣看作文人自娱自乐的繁琐美学而缺乏现代价值一样,意在剔除“区域性”经验而融汇于“普世性”的世界潮流中,这一点在今日全球多元文化的境遇中是值得反思的。
如何看待词学发展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倾向?怎样看待“区域”与“普世”的关系?自后现代“语言转向”以来,我们对于诗歌语言及其“文学性”的认识变得更为复杂,在对马拉美、里尔克等“纯诗”形式的探究中新的文学理论也层出不穷。中国词人对完美形式的自觉追求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是抒情传统的奇葩异果,也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在区域与普世之间并无鸿沟,这是需要我们加强研究的。就王国维的“隔”与“不隔”之论而言,在主张对真实世界客观再现时,忽视了再现世界本身是语言建构的事实,而在要求“写实”的语言透明性方面,含有某种功利因素,却预示了后来新文学运动的语言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