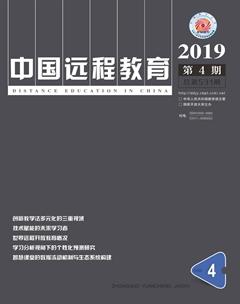MOOC平台的著作权风险及对策
何隽 乔林 林思彤
【关键词】 MOOC;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慕课;著作权;著作权归属;合理使用;风险;对策
【中图分类号】 G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9)4-0060-07
一、引言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也被称为慕课,是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支撑,向公众主要提供免费在线课程的新型教育模式。从2012年发展至今,我国MOOC数量已居世界第一位,460余所高校建设的3,200余门MOOC上线至课程平台,5,500万人次高校学生和社会学习者选学课程(李澈, 等, 2018)。
当前国内针对MOOC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主要从高等教育发展层面,研究MOOC的基本特征、发展趋势及其影响。相关研究指出,与传统课程相比,MOOC具有规模化、开放性、网络化和创新性这四方面特点(陈肖庚, 等, 2013),MOOC的快速发展对高等教育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王文礼, 2013)。第二类主要从课程组织层面,研究MOOC课程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具体措施。相关研究着重分析MOOC课程对现有教学模式的冲击(乔林, 等, 2016),指出高自主性和高退出率在MOOC中并存(高地, 2014),为推进MOOC发展,需要创新MOOC课程教学设计,加强学习支持服务以及建立平台标准(冀付军, 等, 2014)。第三类主要从平台运营层面,研究MOOC平台提供商和产业链模型。相关研究指出,MOOC平台的有效运营是保障MOOC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董晓霞, 等, 2014),其创新的运营模式集中体现在风险投资、协同創新、发展战略及免费分享与增值服务四个方面(陈文竹, 等, 2015)。
值得注意的是,MOOC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模式不仅对传统的课堂教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同时随着平台上线课程的增加,MOOC平台运营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这其中尤为关键的就是如何解决著作权风险,然而目前国内现有的研究中仍然缺乏这方面的系统分析。国外的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著作权对MOOC发展的重要性。美国学者研究指出,MOOC课程平台的运营需要完善的内容控制、平台控制和认证控制(McClure, 2016),其中内容控制的关键就是著作权问题。澳大利亚学者认为,著作权问题已成为教育机构参与MOOC的一大挑战,大学需要聘请专业人士处理MOOC涉及的著作权安排,以确保大学、教员、开发团队、平台提供商及合同第三方在处理著作权事宜时获得明确的指导(Fox, 2016, pp. 159-172)。
目前,MOOC进入快速发展期,更多社会资源加入MOOC平台建设,为确保MOOC平台的健康发展,需要未雨绸缪,对著作权风险做出应对准备。为了解MOOC平台的实际运行情况,本文对相关群体开展了问卷调查,调查问卷采用网上问卷形式,利用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内容包括两个部分:MOOC的著作权归属与MOOC的作品性质。调查对象包括清华大学参与“学堂在线”MOOC建设的授课教师、正在参加MOOC学习的在校学生和职业发展初期的人士。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73份。为验证调查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进行测量信度与效度分析。经计算,克朗巴赫α系数为0.9095,说明问卷整体信度良好。内容效度方面,调查问卷的内容设计与研究主题吻合,获得了相关咨询专家的认可,内容效度比CVR值为0.7143。问卷调查结果显示,MOOC平台与授课教师之间通常没有对著作权归属进行约定,而大部分教师也不认为MOOC制作属于其本职工作,详细数据将在下文分析时具体展开讨论。
基于MOOC平台的运行实践,本文以法理分析为基础并结合相关案例展开分析,从MOOC的作品性质、权利归属以及MOOC对他人作品的合理使用三个角度入手,就MOOC平台可能面临的著作权归属和著作权侵权纠纷的风险展开分析并提出应对建议。
二、MOOC的作品性质
与传统的个人授课行为不同,大多数情况下MOOC课程制作不是教师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除教师外还有摄像团队、平台维护团队和其他辅助工作人员的参与。另外,MOOC的课程制作经费通常由校方支付或由平台提供支持。因此,首先需要讨论MOOC是否属于职务作品或委托作品,作品性质的差别将直接导致著作权归属的不同。
(一)MOOC是否为职务作品?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因此,职务作品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作品是以作者履行职务为基础所进行的创作,即作者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存在一定的雇佣关系。第二,作者创作该作品的目的是完成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交付的工作任务。这里的工作任务,是公民在该法人或者组织中应当履行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工作任务,上级部门或领导根据职能分工以专门文件、领导批示、口头指示等形式下达的工作任务也包含在内(费安玲, 2003)。
因此,分析MOOC是否属于职务作品,首先,要考察授课教师与校方或MOOC平台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其次,要考察MOOC的录制、线上辅导及教案准备等是否属于授课教师的工作任务,如果同时满足上述两项,则属于职务作品。
授课教师与校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是毫无疑问的,但是MOOC制作和上线是否属于工作任务则存在疑问。通常来说,教师的授课工作只包括课堂面授部分,MOOC制作需要准备专门的教案、编写拍摄脚本、完成课程拍摄、进行后期制作和开展线上辅导,这些额外的工作显然并不能包含在教师原有的工作任务之内。对相关教师的问卷调研也显示,71%的教师并不认为录制MOOC课程属于完成教学任务的一部分。在MOOC课程建设中,目前一些高校采用给予教师工作量认定的激励形式,如清华大学在MOOC首次上线开课时,按照课程的三倍课时认定工作量。考虑到工作量的认定,可以认为MOOC课程建设是单位交付的其他工作任务,因此,可以认为MOOC属于职务作品。
(二)MOOC是否为委托作品?
委托作品是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要求所创作出的作品。委托作品具有如下特征:首先,作者对作品的创作是基于委托人的委托,而非作者主动地、自发地进行创作。其次,委托作品主要体现委托人的意志,即无论作者采用何种创作手法和方式完成作品,都不能脱离委托人的要求,必须在满足委托人要求的基础上完成委托作品的创作。此外,委托作品一般来说是有偿的,委托人与受托人通常会订立合同,对作品的要求、交付与报酬等事项进行明确的约定。受托人按照要求完成作品创作之后,委托人会支付一定的报酬给受托人。(李明德, 等, 2003)
因此,分析MOOC是否属于委托作品,重点要考察MOOC的制作是否基于平台的委托,主要体现平台的意志,同时委托方就此支付给授课教师相应的报酬。就委托作品创作达成合意并签署委托合同,是认定委托作品的重要依据。现有的收费在线教育平台,如“新东方在线”平台发布的课程,新东方迅程公司通过与授课教师签订委托合同的方式,约定完成后的教学视频和讲义的著作权归属于新东方迅程公司,授课教师仅享有署名权。对于MOOC而言,基于委托合同对著作权归属进行约定的方式同样适用。
但是,实践中MOOC平台和教师之间针对课程建设几乎都未签署委托协议,也并未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关系。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MOOC的课程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教师基于个人的知识储备和教学经验而完成的,通常并不是根据平台的意志来组织课程内容和选择教学方法,并不体现MOOC平台意志。对相关教师的问卷调查也同样表明,57%的教师在与MOOC平台合作时,仅确定了课程名称,未约定课程具体内容,由教师自行设计课程内容;28%的教师与平台合作时,对课程提纲进行了商定。同时,针对MOOC制作,平台方通常只提供课程拍摄等制作费用方面的支持,并不会直接给予教师报酬。由此也反映出MOOC平台与教师之间并未形成委托关系,MOOC通常也不反映平台的意志,因此,通常情況下MOOC并不属于委托作品。
三、MOOC的著作权归属
当前,MOOC平台的发展有政策支持和高校依托,著作权归属问题通常并未成为优先解决事项,也尚未出现争议。但是,从长远看,著作权归属是MOOC平台必须解决的问题,权利归属决定了收益分配,也决定了平台能否可持续发展。
针对如何解决MOOC的著作权归属问题,国外也尚无定论,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大学应该与教员充分协商后决定。比如,英国学者在对81所英国大学的在线教育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大约有76%的英国大学在其著作权政策中声称大学拥有在线课程资料的著作权,但是由于牵涉诸多方面的利益,权利归属依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该研究建议大学与教员之间应该就著作权归属问题进行协商合作,以平衡双方权利的方式解决著作权问题(Gadd & Weedon, 2017)。又如,美国学者指出,在传统的面授教育中,校方认为学术和教学自由是保证教学质量的最佳途径,教师通常拥有教学资料的著作权。但是,随着在线教育的出现,校方通过合同约定和著作权政策的方式拥有著作权的情况开始增加,而高等教育职业机构支持教师争取其著作权。该研究认为,知识产权分配问题反映了在教学模式转换期对高等教育中教学任务和机构目标的重新界定,相关问题需要充分讨论,而不能任由机构消解教师的知识产权(Aaron1 & Roche, 2015)。另一种意见则认为,MOOC应该遵循开放性原则。比如,南非学者指出,对于教育者而言,他们并不希望占有思想,而是希望传播思想,可以通过知识共享许可(CC许可)合法分享学习资源(Czerniewicz, Deacon, Glover & Walji, 2017, pp. 135-147)。又如,美国学者认为,基于MOOC开放性的特点,MOOC中的学习资源应该可以根据开放许可协议获取,或者干脆不受著作权保护(Spector, 2017)。德国学者指出,在以德国、奥地利、瑞士为代表的中欧德语区国家,实行严格的版权保护,且高等教育通常是免费提供或收费非常低,因此MOOC只有采用开放教育资源模式,才可能良性发展(Ebner, Lorenz, Lackner, Kopp, Kumar, Sch?n, et al., 2017, pp. 205-220)。
(一)MOOC作为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相同的使用方式使用该作品;经单位同意,作者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相同的使用方式使用作品所获得的报酬,由作者与单位按约定的比例分配。
就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著作权法》还规定了两类特殊情况:第一类,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第二类,直接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对于MOOC而言,如果MOOC制作被认为是教师的工作任务,则属于职务作品,但是并不属于《著作权法》所规定的特殊情况。作为一般职务作品,MOOC的著作权由具体授课教师享有,但校方有权优先使用,包括在MOOC平台上线。在MOOC完成两年内,未经校方同意,授课教师不得许可给第三方以相同的方式使用;经校方同意的使用,所获报酬需要在教师和校方之间分配。当然,校方可以通过合同与教师就著作权归属进行约定,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著作权仍然属于教师所有。
根据对相关教师的问卷调查了解到,绝大部分MOOC视频文件制作是由专业摄制团队完成的,且制作费用主要由校方或平台提供。另外,校方或平台所提供的费用主要用于MOOC视频文件的录制和制作,并不包括授课教师的报酬。也就是说,MOOC视频文件的制作主要是利用了校方或平台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这也为校方和平台就著作权归属与授课教师进行协商提供了条件。至于MOOC讲义,主要由授课教师独立完成,其著作权在没有转让的情况下均属于教师所有。
尽管目前教师、校方和平台对于MOOC的著作权归属通常采取回避态度,模糊处理,但是,就著作权归属的意愿进行调查,43%的受访教师认为MOOC(包括课程视频、音频和讲义)的著作权应归属于教师,28%的受访教师认为MOOC的著作权应该由教师、校方和平台共同所有。
(二)在线教育平台课程的著作权权属认定
MOOC自2012年进入国内,目前尚未出现直接针对MOOC的著作权权属争议。但是,先期发展的付费在线教育平台已经遭遇了多起著作权权属纠纷和著作权侵权纠纷,即使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首先也必须确定著作权权属关系。以下用“新东方在线”的两个案例来分析法院对在线教育平台课程著作权权属进行认定时遵循的原则,相关原则对于MOOC平台同样适用。
案例一为2015年新东方迅程公司(下称“新东方”)诉上海媒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媒沃公司”)侵犯其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案。新东方诉称,媒沃公司在天猫网开设的网店,未经允许销售新东方享有著作权的多个在线课程教学视频。庭审中,新东方提交的DVD课件视频均标明了授课教师;所提交的《作品登记证书》显示著作权人为新东方。同时,新东方提交了其与授课教师签订的《课程录制合同》和《课程直播+录播合同》,合同约定新东方采取直播课堂形式直播和录播该教师作为讲授人的课程,形式为视频,新东方对直播内容和录音录像制品享有所有权、著作权和其他相关权利,授课教师对直播内容享有署名权。对于新东方主张涉案5段视频的著作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新东方未能证明其所主张的涉案5段视频包含在《作品登记证书》所载明的作品中,从授课人与其签订的合同内容也无法看出涉案5段视频包含在合同所授权的教学视频中,因此,法院没有支持新东方是视频课程的著作权人的主张。对于新东方主张其享有涉案5段视频的录制者权,法院认为,涉案5段视频均显示了“新东方在线”及其网址标识,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涉案5段视频为新东方录制。即法院认可了新东方作为录像制作者的身份,但没有确认著作权人的身份。该案最终认定被告媒沃公司侵犯了新东方作为录像制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案例二为2016年新东方迅程公司(下称“新东方”)诉北京皖枫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下称“皖枫林公司”)和天猫公司侵害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案。新东方诉称,皖枫林公司在天猫网开设的网店,在销售考研英语复习资料等书籍时,未经其许可,将其享有著作权的新东方英语、数学及政治辅导教学视频、音频、电子文书等资料赠送给买家,给其造成巨大的损失。案件审理中,新东方提供的涉案视频文件上均带有新东方的标识;提供的涉案教学讲义文件上有主讲人的署名。涉案教学视频和讲义的授课教师均发表声明,称该案中本人所享有的著作权已转让给新东方,相应著作权由新东方享有。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因此认定:对新东方能够提供正版文件的教学视频,推定新东方为著作权人;对新东方能够提供正版文件的涉案讲义,推定署名主讲人为著作权人,现署名主讲人声明将著作权转让给新东方,故新东方享有涉案讲义的著作权。该案最终认定被告皖枫林公司侵犯了新东方对涉案录像制品和文字作品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天猫公司已履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不存在明知或应知的过错,无须承担侵权责任。
以上两个案件均涉及在线教育平台课程的著作权归属。在认定著作权归属时,法院遵循以下三条原则:第一,将在线教育课程区分为教学视频和讲义两类,教学视频属于录像制品,讲义属于文字作品。第二,在认定著作权归属时,根据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因此,在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况下,视频文件和讲义上署名人即视为著作权人或邻接权人。第三,讲义的署名人和教学视频的授课人可以通过授权合同等方式将著作权转让给在线教育平台。上述原则在MOOC平台面临著作权权属争议时同样适用。
四、MOOC对他人作品的合理使用
教育的本质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因此,教学过程中就必然会使用到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著作权法为此专门规定了合理使用制度,以确保为教学需要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作品,也无须支付报酬,以此达成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与公众受教育权之间的平衡。
(一)为教学需要的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制度作为著作权法的一项基本制度,指無须经得著作权人同意,也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著作权人作品的情形。可以说,合理使用制度是著作权人向作品使用者让渡部分财产性权利,以此协调著作权人、作品使用者和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试图在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同时不得出版发行。《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也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通过信息网络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少量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根据上述规定,“学校课堂教学”属于合理使用范围,但是使用的方式和范围有一定的限制,包括:不得出版发行,以及仅可向少数教学人员提供少量已经发表的作品。
2014年,浙江省东台市唐洋中学(以下简称“唐洋中学”)因为在学校网站上提供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中文在线”)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雾雨电》被控侵权。唐洋中学认为,其在网站上提供涉案作品供用户阅读、下载,是为了促进教育与教学,属于合理使用,故不应被认定为侵权。一审法院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唐洋中学在其网站上提供涉案作品供公众阅读、下载的行为,不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情形,即便是为了实现教育现代化,唐洋中学也应当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相关作品的使用权,故其抗辩理由并不成立,唐洋中学的行为构成了对中文在线关于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唐洋中学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为学校教学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使用对象仅限于教学人员,并非社会公众,且应将作品使用于教学活动之中。本案中,唐洋中学网站已从“内网”扩展到向社会公开的“外网”,涉案作品已处于为不特定的人能够通过正常途径接触并可以知悉的状态,故唐洋中学的行为不属于为教学需要而合理使用作品的情形。对于唐洋中学上诉中所称,学校网站的访问量一直很低,不存在侵权行为,二审法院认为,网站的访问量低与是否构成侵权无直接关系,仅影响到侵权赔偿责任的确定,故唐洋中学侵权成立。
在中文在线公司诉唐洋中学著作权侵权案中,二审江苏省高院的判决说明,为学校教学需要的合理使用的使用对象需要限定于特定的教学人员,使用范围应当限定于教学活动之中。如果社会不特定人群可以通过正常途径接触到相关作品,则不属于为教学需要的合理使用范畴。
(二)MOOC如何适用合理使用制度
MOOC的诞生为公众提供了更加方便、自由的学习平台和在线资源,随之而来,也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在线学习群体。如果MOOC不能适用合理使用制度,就会面临巨大的著作权侵权风险。因此,MOOC对他人作品的使用能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合理使用制度就变得非常重要。
我国《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所规定的合理使用制度均使用“学校课堂教学”作为教学需要的设定,这一规定是基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模式下,教师与学生进行面对面授课,授课群体有限,因此作品的使用群体人数有限。在线教育模式下,“学校课堂教学”不应继续作为适用合理使用的限定条件,而应该拓展到在线教育中。同时,MOOC授课人数大幅度增加,作品使用者范围也随之扩大,因此,在具体判断是否可以适用合理使用制度时,其标准也需要与MOOC的特点相适应。
首先,需要重视使用作品的量,特别强调所使用部分占整个作品的比例是少量。对于作品量的限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少量”的含义:第一,同整个作品相比,被使用的部分仅仅是该作品的小部分;第二,使用作品的数量较小,作品复制的数量与教学人员的数量相匹配,而且这种使用本质上对作品的潜在销售市场和价值影响不大(陈洁, 2005)。由于MOOC平台的开放性,课程选修人数超过千人很常见,一些热门课程的学习人数甚至达到几十万,针对这种情况就不能简单限定作品的使用人数,而是需要特别强调所使用部分占整个作品的比例。也就是说,关注的重点应当是,所使用的部分不能替代整个作品,不会影响整个作品实现其市场价值。
其次,需要重视使用作品的目的,强调是为了教学需要。第一,强调所使用的作品与课程内容和教学目标的关联性,排除任意扩大作品使用范围;第二,强调作品的使用群体是课程的学员,排除非特定人群接触作品。至于合理使用是否必须要求是非营利性的,由于立法中并没有规定,因此对于在线教育也不应做出非营利性的限制。也就是说,无论MOOC平台还是付费在线教育平台,只要符合规定,均可以适用合理使用制度。
五、应对MOOC平台著作权风险的对策建议
基于所调查的MOOC平台的运行实践,以及对现有收费在线教育平台著作权纠纷的阐释,结合上文对MOOC平台所面临著作权归属和侵权风险的法理分析,对MOOC平台应对著作权风险提出两条建议:
第一,MOOC平台、校方和教师三方需提前对MOOC课程的著作权归属及相关权益分配签署合同做出约定。
尽管目前尚未出现直接涉及MOOC平台的著作权纠纷,但现有在线教育平台在发展中面临的各类著作权纠纷对于解决MOOC作品著作权问题提供了一定思路。结合相关案例可以发现,目前法院对于在线教育课程著作权侵权纠纷的审理,首先是确定作品的权利归属,其中主要考察在线教育平台与授课教师之间是否就涉案作品签署了著作权授权或转让合同,以及合同是如何进行约定的。通过合同中的具体约定,可以确定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进而判断涉案主体是否构成侵权。
目前对于MOOC著作权归属问题采取模糊化处理,实质上不利于MOOC的课程建设,也会给MOOC平台的后续发展带来不确定因素。从避免纠纷的角度考虑,建议MOOC平台、校方和教师三者之间事先就MOOC课程的著作权归属、相关视频文件和教学课件的财产性利益进行约定。在明晰MOOC著作权的基础上,才能明晰MOOC课程生成性资源和衍生作品的权益归属。这通常涉及复杂的著作权安排。那些拥有一定声望和实力的高校,在MOOC课程开发过程中往往具有人力和资源优势,通常可以掌控谈判的进展(Fox, 2016),在著作权安排上处于有利的地位。
第二,MOOC課程和MOOC平台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时需要遵守少量和相关性原则,同时注意履行署名和提示义务,避免滥用合理使用制度。
合理使用制度的主旨是实现著作权保护与因教学需要使用作品之间的平衡。我国《著作权法》以“学校课堂教学”作为适用合理使用制度的限制性条件,MOOC作为一种在线教育形式,扩大了“课堂”的范围。但是,MOOC所蕴含的教育本质却并未发生变化。因此,MOOC应当涵盖在合理使用制度之中。
此外,考虑到网络传播的范围和速度要远远超出传统课堂,合理使用制度中关于“少量”使用的限制应当强调MOOC对原作品潜在市场的影响;强调MOOC所使用的量与原作品整体相比,应该是原作品的小部分,而对于参与教学的人员数量则不应过分强调。同时,需要特别强调所使用作品与课程的关联性,只有与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密切联系的作品才可以使用,以免滥用合理使用制度,对原作品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侵害。另外,作为合理使用制度的受益者,MOOC平台应当承担相应的署名和提示义务,MOOC中若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在课程内容中注明原作品的相关信息,并提示参加课程学习的学员禁止将相关作品使用于与教学无关的事项。
[参考文献]
陈洁. 2005. ETS诉“新东方”侵权案评析[J]. 人民司法(5):95-99.
陈文竹,王婷,郑旭东. 2015. MOOC运营模式创新成功之道:以Coursera为例[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135(3):65-71.
陈肖庚,王顶明. 2013. MOOC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特征分析[J]. 现代教育技术,23(11):5-10.
董晓霞,李建伟. 2014. MOOC的运营模式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330(7):34-39.
费安玲. 2003. 著作权法教程[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高地. 2014. MOOC热的冷思考——国际上对MOOCs课程教学六大问题的审思[J]. 远程教育雜志(2):39-47.
冀付军,李利聪. 2014. 我国发展MOOC的推进策略研究[J]. 中国远程教育(11):27-32.
李澈,龙超凡. 2018. 慕课如何“打开”教学新方式[N]. 中国教育报, 01-17(3).
李明德,许超. 2003. 著作权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
乔林,何隽. 2016.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实践与现存问题[J]. 教育研究前沿,6(4):138-144.
王文礼. 2013. MOOC的发展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J]. 江苏高教(2):53-57.
McClure, M. W. (2016). Investing in MOOCs: “Frenemy” risk and information quality. In J. Zajda, & V. Rust (Eds.), Globalis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reforms, globalis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policy research (pp. 77-94). Switzerland: Springer.
Fox, R. (2016). MOOC impact beyond innovation. In C. C. Ng, R. Fox, & M. Nakano (Eds.), Reform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Asia-Pacific universities. Singapore: Springer.
Gadd, E., & Weedon, R. (2017) Copyright ownership of E-lear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Policy approaches taken by UK universities.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2(6): 3231-3250.
Aaron, L. S., & Roche, C. M. (2015)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faculty in the digital age: Evolution or dissolution in 21st century academia?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3(3):320–341.
Czerniewicz, L., Deacon, A., Glover, M., & Walji, S. (2017) MOOC—Making and open educational practices. Journal of Computing in Higher Education, 29(1): 81-97.
Spector, J. M. (2017). A critical look at MOOCs. In: M. Jemni, K. Mohamed, & K. Khribi (Eds.) Open education: From OERs to MOOCs.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Ebner, M., Lorenz, A., Lackner, E., Kopp, M., Kumar, S., Sch?n, S., et al. (2017) How OER enhances MOOCs: A perspective from German-speaking Europe. In: M. Jemni, Kinshuk, & M. K. Khribi (Eds.) Open education: From OERs to MOOCs.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