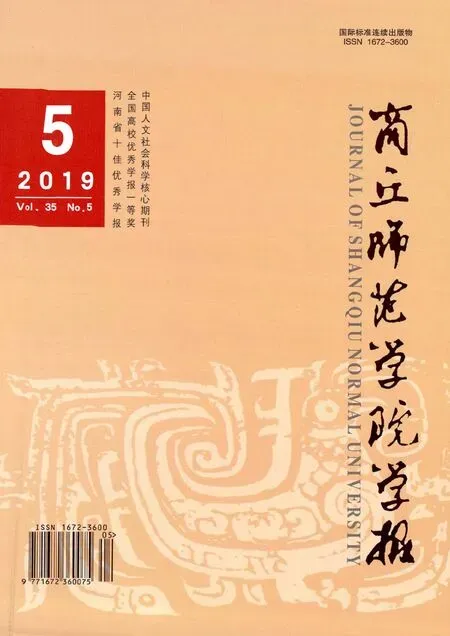《老子》“同”的思想研究
刘 海 成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从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到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和同之辨,从后期墨家到名家的同异之辩,从老子的“玄同”论到庄子的“齐物论”,似乎都昭示着“同”的思想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曾引起过广泛、热烈的讨论。那么,老子对“同”有过怎样的论述呢?对同异之辩、和同之辨又有过怎样的回应或影响呢?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一、玄同论
关于“玄同”的论述集中在《老子》第56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1](下文如无特别说明,《老子》引文皆为王弼本)

因此,“玄同”从字面上理解是浑沦不可分的混沌状态,具体地讲是由于深远不可及、幽明对转、有无相生所带来的浑沦不分、混同一切的状态。当然这不是简单的抹杀个性、不辨是非的混同一切。为更深层次理解“玄同”必须回到《老子》原文中寻找线索。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竹简本《老子》作“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②本文所引竹简本、帛书本《老子》均引自《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上卷,刘笑敢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弗”和“不”用法略有区别,“不知”“不言”都是泛指,“弗知”“弗言”则是实指的“不知之”“不言之”[4]546。这里“之”所代指的是道,道由于自身的特殊性而不可被言知。详味“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实则老子此处区分了两种“知”:一种是可以用日常语言所表达的名相之知,如“言者不知”,“博者不知”(第81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第2章)。语言是有限的,美恶、善不善是有对,皆不能代表无限、无对的道。拥有这类“知”不仅会造成人类知识的混乱,甚至会造成统治的混乱,因而需要经过否定和扬弃:“常使民无知无欲。”(第3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第19章)“爱民治国,能无知乎?”(第10章)另一类是通过扬弃语言表达的名相、相对之知后获得对道的体认之知,亦即是“知之者弗言”之知。体道之知在《老子》中还见于:“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第14章);“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第47章);“知常曰明”(第16章);“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第65章)。如何通过扬弃名相之知而获得体道之知,是《老子》此章讨论的中心问题。因此,“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作为开章第一句话似乎暗示给我们的是,“玄同”应首先作为认识论问题来理解,而非本体论。
下文“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论述经由排除名相、言语之知上升到体道之知的具体进阶理路。今本“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四句句序与竹简本、帛书本不同,竹简本作“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帛书本作“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而解其纷”。刘笑敢认为,简、帛本实有两个意群:“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是就个人感官来说的;“挫其锐而解其纷,是谓玄同”是主体对外界纷扰的主动平息。他言:“这两个意群意思连贯,而各有侧重。似乎没有不当。”[4]546丁四新原认同今本句序,认为“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都是否定句式,而“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都是要争取和保持正面的状态[5]121。但在其后著作中,他推翻了原来的看法而认同了刘笑敢的划分[6]149。笔者不能认同刘笑敢先生把“和其光,同其尘”仅认为是就个人感官而言,也不认同把“挫锐解纷”理解成对外界纷扰的主动出击,这显然是违背老子“贵柔守雌”的思想主张。虽然有竹简本与帛书本的地下材料证据,但并不能因此贬低今本的理论价值意义和正确性。在内在理路上,笔者更倾向于今本的句序,认为“塞兑闭门”、“挫锐解纷”、“和光同尘”分别对应的是对感情判断、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否定和排除[注]此一思想受启发于日本学者池田知久的《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著作,其在本书第五章《“万物齐同”的哲学》中把庄子学派的万物齐同思想划分为三个阶段的知识性否定,即对感情判断、价值判断、事实判断的否定与排除。详见池田知久著、王启发译:《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上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178页。,且分别与后文(“不可得而亲”以下)构成一个前后对应、紧紧相扣的整体。
“塞其兑,闭其门”喻指的是,闭塞人由以产生情感欲望的感官,排除喜、怒、哀、恶、欲等情感对认识事物的影响,从而达到无论“亲疏远近”,一视同仁的境界。“兑”与穴同义[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老子》‘塞其兑,闭其门’,兑借为阅字,阅同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05页)。王弼注云:“兑,事欲之所由生;门,事欲之所由从也。”[1]143兑和门喻指的是,人的情感、欲望由以产出和发泄的感官或官能。人常常因为个人感情、私欲的影响而产生亲、疏、远、近的偏见,不能做到一视同仁。老子主张“塞其兑,闭其门”,就是要否定和排除私人情欲对事物认识的影响,对事物的亲、疏、远、近关系等而视之,从而做到“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之境界。
“挫其锐,解其纷”是紧接着“塞兑闭门”来讲,喻指的是对造成人类各种知识、学说相互攻讦,纷争不休的价值判断的否定和排除。“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第2章)老子认为,人类的一切价值判断都是相对的,人性中所坚持的美好德性也是从它们的对立面产生的:“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18章)因而在这些相对的价值判断上建立起的知识、学说,就会产生出与之相对的各种知识、学说,造成不必要的纷争和混乱。因此要消解这些纷争,只有排除和否定“各以为利,互以为害”的价值偏见,从超越相对价值的“道”出发,齐同人我的利害关系,从而做到“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之境界。
“和其光,同其尘”喻指的是,在“塞兑闭门”、“挫锐解纷”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外界事物的五光十色、晦暗不明现象的否定和排除。光者,明也;尘者,暗也。光和尘、明和暗,喻指的是对外界事物现象的事实判断。因为道是“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第14章)的,所以光和尘、明和暗在道的眼光看来是无别的,故而是可以和同的。和同光、尘,喻指的是对事实判断的否定和排除。“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2章),老子主张世人所认为事物的“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的事实判断都是相依互转的,为达到对“独立不改”的道的认识都是应当否定和扬弃的。光尘无别,物无贵贱,达到的是“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之境界。
“故为天下贵”是对经过三个阶段的否定和扬弃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玄同论的肯定。
综上所述,“玄同”作为老子认识论系统的制高点,至少包含三层意涵:第一,通过否定感情判断而达到和同物我亲、疏、远、近之情之境界;第二,通过否定价值判断而达到和同人我利害之别之境界;第三,通过否定事实判断而达到和同物我贵贱之境界。如果说否定感性情感判断达到的是“忘我”之境界,那么在“忘我”基础上进一步对构成人知识、学说的价值判断的否定所达到的就是“无我”的境界。徐复观曾说过:“一般人之所谓‘我’,所谓‘己’,实指欲望与知识的集积。”[7]77徐先生此处的“知识”,实则是指普通所谓的名相之知。对感情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否定和扬弃就是要对这个“我”“己”的否定和扬弃,达到“无我”之境界。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否定事实判断达到“无物”之境界,从而最终达到物我无别,玄同一体的境界。这也便是道的境界,本体的境界,从而实现由认识论过渡到本体论。因此,我们说玄同论首先是个认识论问题,然后才是个本体论问题。由认识论角度名为“玄同”,由本体论角度名为“道”,二者异名而同实。
二、同与异
同与异是先秦名家论辩的重要议题,公孙龙讲“离坚白”,惠施讲“合同异”。在《老子》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老子对于“同”和“异”的深刻的辩证认识。
“同与异”在《老子》第1章便有讨论: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其中“无名天地之始”句,帛书本作“无名万物之始也”。王弼本虽作“无名天地之始”,但弼注却作“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为其母也”[1]2。由此看来,弼本也原作“无名万物之始”,同帛书本。因此,本章不是从“天地”到“万物”,从“无(名)”到“有(名)”的宇宙生成论论述,而是讲“无(名)”和“有(名)”共同作为万物之本根、原始。竹简本《老子》第40章:“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亡(无)。”也证明了此推论。因此可以说,有与无同出于道,都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根,有与无是道的一体两面。“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帛书本作“两者同出,异名同谓”。“两者”显然是指上文所讨论的有与无而言,“两者同出”是指有与无共同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根,同出于道,是道的一体两面。“名”是指名词概念,“谓”是“指称,所指”的意思。“异名同谓”是说,有和无虽是性质相反的名词概念,但在所指的实质上是一样的,即都是道生养万物的总根源。“欲言无耶,而物由以成。欲言有耶,而不见其形”[1]35,道既有又无,既“异名”又“同谓”,故而曰“玄之又玄”。
由上可知,有与无的“异”只是一种在名词概念上,或表相上的差异,从万物总根源的道的层面看有与无却又是“同”,有与无是道的一体两面而同为万物的总根源。其实在老子看来,现象界的一切差异、对立都是相待而生的,从道的角度看都是可以齐同的: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2章)
美丑、善恶属于价值判断,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皆属于事实判断,从超越无对的道看来都是可以齐同的,故而曰“玄同”。这在前文已有论断,此不赘述。
但老子哲学并不是要盲目的混同一切,无视差异,是非不分,而是要我们认识到语言、知识的局限性,从而以更加开放、“自然无为”的心态面对人世间的一切是非差别:
希言自然。……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第23章)
“希言”(少说话)、“自然”(自然而然)一直是老子强调的道的两大原则。对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历来学者多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思想相附会,如此理解或许不错,但容易忽略掉老子哲学自然无为的特质。据帛书本,后三句应作“同于得者,道亦得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刘笑敢在比对五种《老子》版本后提出,弼本“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是“道者同于道”的衍文,以与“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相匹配。“得”字,帛书本原作“德”,根据上下文义,此“德”与“失”相对,显然应该读作“得”,“全段皆讨论得失问题,与道德之德无关”[4]271。从帛书本我们可以看出,就像道兼有有和无,有、无是道的一体两面,道也兼有得和失。道不只是像通常理解那样的“独立不改”,超绝无对,而是也有得有失,有有有无的,只是道将这一切对立面都包容了,都“玄同”了。故而道可以顺应事物的发展,“同于得者,道亦得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两个“亦”字表明道不是强制事物与之同得失,而是道顺应事物的得失而同有得失。如此理解,更符合老子道“万物作而弗始”(帛书本第2章)的自然无为本性,因而是更符合老子哲学的解释。王弼在此句下注云:“言随其所行,故同而应之。”[注]原文作“言随行其所”,据楼宇烈校改。见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2页。,楼宇烈校释曰:“意为道随物所行而应之”,与帛书本义正同。
因此,老子的“同”一方面是指在形而上的超越层面,有无、得失等差异、对立“玄同”于道,是道的一体两面;另一方面是指在形而下的现象世界,道又是顺应事物的差异性,与事物同其得失,体现了大道自然无为的特性。
三、同与和
讨论《老子》中同与和的关系问题,不得不先提到一段文本: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第55章)
我们先了解《老子》文本中“和”字的意义。“和”字在《老子》文本中出现有7处,其中有1处可作“应和”理解(第2章:“音声相和”),其余6处大致可作“调和,柔和,和谐”理解。具体来讲,“六亲不和,有孝慈”(第18章)、“和大怨,必有余怨”(第79章)是指人际关系矛盾、冲突的协调与调和;“冲气以为和”(第42章)是指阴阳二气的相摩相荡而成均调和谐的状态[9]236-237;“和其光,同其尘”(第4章、第56章)中“和”,也可作“均和、柔和”理解。因此,“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应当是指初生婴儿阴阳二气协调均适,因而能终日号啕而不至喉咙沙哑。因此,“和曰同”中的“和”应指阴阳二气调和均适的状态。“曰”在此处有三种可能意思:1.作为动词,犹谓,译作“叫作”。2.作为语中助词,无义。联系上下文,显然不是,故排除。3.作为副词、连词,犹乃,译作“于是,才”。《诗经·棉》:“曰止曰时”,犹言“爰居爰处”,“爰”同“乃”[10]1045。再考查“同”。同,经过上文的讨论指的是物我不分、浑沦一体的最高境界,可以代指“道”。再根据“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42章),道在宇宙演化图示中显然高于和,和是由道生出的阴阳二气的调和状态产生的。因此,在老子哲学中同的观念高于和。因此,“曰”在此处应训为转折、递进关系的“乃”,而不当训为平行关系的“谓”。“和曰同”即是“和乃同”,意思是说达到和的状态才能进而达到同的境界。
有趣的是,在帛书本《老子》卷后佚书《五行》中出现了“和则同”的表达。对比儒道的“和则同”与“和曰同”思想,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儒道二家在先秦时期共享着相同的学术资源,并不如后世所理解的那样截然相对。
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同”常作为“和”对立面出现而遭到贬低和排斥,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但在孔子身后的思孟学派《五行》著作中,我们却发现了这样的论述:
四行之所和,言和仁义也。和则同,和者,有犹五声之和也。同者,□约也,与心若一也。言舍夫四也,而四者同于善心也。同,善之至也,同则善矣。(《五行》第19章)[注]本书所引《五行》原文与分章,请参见池田知久著、王启发译:《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线装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前一段引文是说,“四行”(仁、义、礼、知)的调和、统一(“和”),就像五声(宮、商、角、徵、羽)的谐调、统一一样;而“同”就是谐调、统一的“四行”与善心成为一体;这样“四行”与善心成为一体的“同”,就是善的极致,所谓“同则善”也。后一段引文是说,“和”就是小体(耳目鼻口手足)与心结合在一起而不违背,“同”就是谐调了的心和小体与更大的仁义心成为一体,这就是善的完成。无论是前一段的“和”了的“四行”与善心成为一体,还是后一段的“和”了的小体、心与仁义心成为一体,“同”似乎都是“和”的更高一级状态,代表着善的完成[11]353-363。
比较竹简本《老子》“和曰同”与《五行》“和则同”,在表达形式以及理论层次上,二者均认为“同”应高于“和”,但在实质内容上二者有本质区别:“和曰同”是通过阴阳二气调和进而可能达到的不分物我、玄同一体的“道”的境界;“和则同”则是通过“四行”与善心一体化,小体、心与仁义心一体化所达到的道德的“善”的境界。这些显示出儒道两家在共同思想资源开发上的差异。但无论怎么说,《五行》篇的“和则同”恰可以作为竹简本《老子》的“和曰同”的一个文本外证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