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爸爸再也不认得我是谁
□于 是

关于父亲的第二次走失,子清有过太多猜想,但最喜欢本命年生日的夜里梦到的这种可能——他,这个老人,佝偻着背,一个劲儿地往桥上的机动车道上骑,自行车的脚蹬被踩得咯噔咯噔响,这个老人身手矫健,如果不把衣兜里的身份证拿出来,没人相信他已经七十三岁了。这让他在车上信心满满,从不迟疑。
他欣欣然地看着一辆辆车从身边驶过,有的车猛按喇叭,有的车却放慢了速度。
在老人眼里,看到的只是些疯马的影子。跑疯的马是多么可怕,三哥没来得及上车,五弟被颠了下去,只有自己在疯马带领的路上。四岁的沉默男孩紧紧攥着马车的靠栏,闭着眼睛,不想被迎面抽来的树枝打中。他想起爹,爹一定会责骂兄弟三个赶坏了马车,他可心疼这匹马了。他闭着眼睛幻想爹暴怒的脸,等到的却是死于肺结核的蜡黄苍白瘦如刀削的一张脸。爹去世时是多少岁来着?四十?四十二?
爹早死了。疯马还在跑,跑到红灯前还在跑。老人不觉得自己犯了错,绿灯还是红灯,看起来差不多。但渐渐地真累了。等到自行车的链子掉下来,他从车座上趔趄着撑下脚尖,恍然间意识到自己迷路了。所以,这个老人孤独地站起来,忘了自行车,忘了塞在车篮里的外套,以及外套里的钱包、钥匙和证件。
梦到这里就醒了。她在深夜醒来,心也跳得像疯马在跑。她相信这是父亲的生灵在给自己托梦,向她解释那两天里发生的事。那是父亲一生中最神秘的两天空白,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走的哪条路。当她接到警察的电话飞奔到三十公里之外的派出所时,父亲只是说自己爬了一座山。一连好几天夜里,她都希望这些梦能像连续剧一样播映,仿佛这就能弥补父亲的失忆。
梦做得太逼真,醒来很累,但她还是决定去遥远的城郊看父亲。每周总有那么一两天心神不宁,她分不清多少是因为担忧,多少是因为愧疚。
父亲的病,扩大了她的版图。十号线转乘三号线到终点站,最快也要一个半小时。走出地铁站的时候,她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钟,刚好三点,距离福利院的晚餐时间还有一小时,她决定步行二十分钟,刚好过去陪父亲吃饭。
父亲住进这家福利院,是几个月前的事情,父亲和她都有些不适应。他也许有极其短暂的清醒时刻,也许会抓紧时间咒骂没良心的女儿和后妻,也许会很害怕地看到自己被一群陌生的老头围绕,每一个都不像是正常人,而等短暂的清醒过去,他又和他们浑然一体。而对子清来说,唯一不适应的就是负罪感,即便斜跨整个城市去看望父亲,实际上不过是消耗体能和时间,换来一点点心安理得的错觉,却根本无法改变她对病情无可奈何的事实:她把他交出去了,再也没有反抗,全然地向病症妥协了。
走进福利院,在门口签了出入证,走过两栋老人公寓,再走到小径的尽头,便是父亲所在的那栋楼,电子门锁意味着里面住着丧失自理能力的失智患者,他们不可以随意外出。二楼三楼住着老太们,四楼住着老头们。电梯和居住区之间也隔着玻璃门,从内部出来时需要门卡,通向楼梯的门也无法从外部打开。这些封闭策略都是针对失智者的,让他们几无可能独自走出去,从而杜绝走失和迷路的机会。
今天,一出电梯,她就觉得四楼的气氛有点怪异。大厅里的人影寥寥无几,摆在电视机墙对面的蓝色沙发上竟然没有一个人。
但她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他。她看到,父亲双手抱着一台微波炉,绕着长方形的大桌走成背影,插头线在桌脚绊了一下,又被拖着走,不情不愿地跟在一双白生生的赤脚后头,随着蹒跚的脚步一顿一顿。肩胛骨仿佛要刺穿汗衫耸出来,和怀里沉重的分量艰难对峙着。她不知道他这样捧着一台微波炉绕着桌子走了多少圈。她想象不出一个耄耋老人有多大的气力能完成一件荒唐透顶的事。
“我们不敢去碰他。他刚刚踢走了小黄,还差点用微波炉来砸我。”穿着靛蓝色护工服的胖阿姨走到她身边,却没有压低嗓门。她认得她,那是负责给老人清洗身体的女工,几乎每天给她父亲擦身时都会被父亲扬手掴掌,甚至握紧拳头砸向她。
“他走累了应该就会自己停下来的。”胖阿姨的语气显示她并没有太大把握,“怕就怕微波炉掉下来砸到他自己。”
这是她第一次在福利院里看到父亲衣冠不整,虽然听说过几次——他总是拒绝穿衣,或是拒绝脱衣——但从此往后,这样的场景只怕是越来越多。在第一个月里,护工给她打过电话,“你爸爸是不是以前常常打人?他把好几个护工都打了,因为护工要帮他穿衣或是洗澡……他拳头好重呀!”
子清紧握手机回答:“他以前从不打人的!肯定是因为他不习惯吧……他大概还有意识,觉得脱衣服是自己的事。以前,我不会硬脱他的衣服,我会哄他自己脱自己穿。”
“我们每个护工都要照顾七八个病人,没有时间哄的……”
子清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很担心父亲会被最后一家可以收容他的机构拒绝。就在这个短暂的三分钟里,她第一次意识到,如果父亲无处可去,只能回家照料,她一定会害怕的。
老男人拖沓的步伐近乎匀速,像是在催眠。她鼓起勇气,向前走了两步,但还没等她张口,胖阿姨就扯开嗓门叫起来,“老王!你看看谁来了!老王!老王!”
每一次,她都恨透了护工们的大嗓门、反复地问:“她是谁?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恨那种低级的测试。如果病人能说出家里有几口人,微波炉该放在哪里,十八减八等于几,那又何苦来这里?她也恨那种大嗓门,刻意地,对着理论上应该耳背、应已退智的老人们。她总觉得,既然言语已对这些人无用,那就该换成轻柔的语调、轻柔的抚触。但没有人赞同她,他们说,你必须大声点,引起他们的注意。
父亲不理睬任何人。微波炉仿佛就该是他的一部分,当他又一次在桌角拐弯,迎面向她走来时,她突然惊出一身冷汗,仿佛看到一个机器人捧着自己的遗像向自己走来。
于是,她也慢慢迎上前去,距离拉近,脸孔被推出镜面,很快变成胸腹、腿脚,在她伸手抱住微波炉的时候,清晰地意识到,她用肚子挡住了画面。她让自己倒着走,好像隔着金属箱子成为父亲的镜像,她希望不要吓到、打断他。她轻轻地说:“爸爸,我来了,爸爸。”就这样,她轻轻唤着,倒退着走完了半圈,父亲终于抬了抬眼帘。之前,他一直沉沉地低头看着地面。
微波炉那么沉。她感到父亲慢慢地把手里的力量转移给她,而那简直是她捧不动的沉重。
(移风
摘自《文苑·感悟》图/李倩莹)
诗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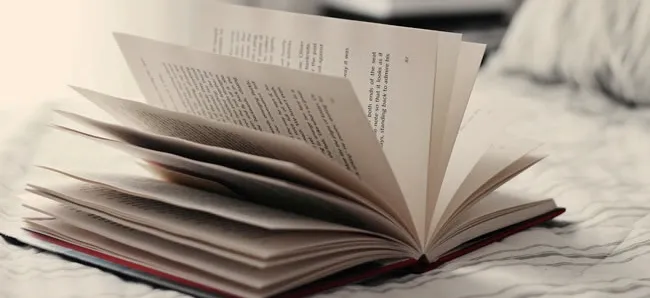
你是我们如今想起来仍感痛苦的
西西里岛上线条清晰的凹槽。
你是冰冷的狂想的
悲伤的音符——
只是几个人才觉得美的音符。
——理查德·阿尔丁顿《一个姑娘》
开心校园
目的
人的染色体有23对。有一天上课,教生物的老头慢悠悠地问:“染色体多少对啊,同学们?”
角落里某二货大声答道:“64对啊!”
老头淡定而严肃地点点头:“嗯,你告诉我,你来地球的目的是什么?”
翻译
期中考试老师出了一道翻译题: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老师改完考卷,很严肃地对全班同学说:“我们班有个人写:死去的那个人好像是我。”
喊口号
体育课上,老师教我们做健身操,带着同学们喊口号:“我真的很棒,我真的很棒……”
同学们都认真地学着,只有最后一排的小胖哭丧着脸,一边做一边喊:“我真的很胖,我真的很胖……”
不靠谱的孩子
班上有个同学,从小就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新曲子他听一遍就能记住,凭着记忆不看曲谱就能弹琴演奏。老师们都称赞他:“真是个不靠谱的孩子!”
口吃
口吃的监考老师发现一学生在作弊,便气急败坏地指着那学生吼道:“你……你……你……你……你竟敢作弊,站起来!”语毕,有五名学生站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