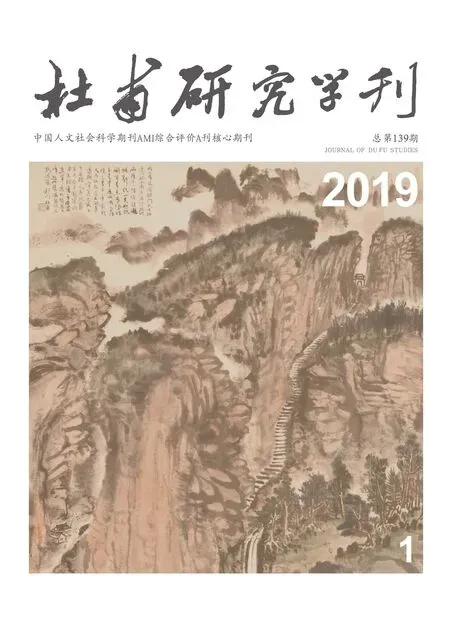清代顺康两朝杜集笺注的“江南现象”
罗时进
作者:罗时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5123。
钱谦益曾言“古今之诗总萃于唐而畅遂于宋”,这是一个对中国古代诗史的大判断;而将诗人置于诗史中时,钱氏则云“自唐以来,诗家之途辙总萃于杜氏”,这个论断与朱舜水“(杜诗)至今脍炙人口,独居诗坛之上,千年以来未能与之争鼓者”的看法相合,颇为清代以来学者认同,也能够从长期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得到证明。从历代诗歌文本的笺注情况来看,不仅宋代以“千家注杜”为盛,元明清三代的杜诗注解亦远超其他各家,这是文人崇杜的突出表征,也构成了杜诗形成广泛影响的推动力。这种“突出表征”和“推动力”的产生既有文学内部的原因,也有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深刻背景。清代顺康两朝江南地区出现了“诸家注杜”的现象,正需要从各不同角度加以探讨。
一、清前期江南诗界大量笺注杜集现象
学者们在研究清代杜诗学时,对清前期出现的大量杜诗注本做过统计,据之可以看出,清前期江南除产生了钱谦益《钱注杜诗》与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这类有重要诗学价值且成为学术公案的注杜著作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诗家进行了注杜的工作,形成了一种风尚,也表明学杜高潮的到来。管棆《说安堂集序》云:“古今来称诗者必曰少陵。诗之有少陵,犹文之有班、马也。於戏!宗少陵者,可谓至矣。当世注杜者不止数百家,评杜者亦不止数百家,灾及梨枣,卷比牛腰。”管棆是康熙时代常州人,其称当世“注杜者不止数百家,评杜者亦不止数百家”,应是就清初而言,而在海内“总体”之中,“江南”“局部”所占比例相当大。以下是一个粗略的统计:
杜律注本有:顾宸(无锡人,1607—1674)的《辟疆园杜诗注解》;俞玚(吴江人,1644—1694)的《乐句》;朱瀚(嘉定人,顺康间生存)的《杜诗解义七言律》;陈之壎(海宁人,顺康间生存)的《杜工部七言律诗注》;顾施祯(吴江人,康熙前期生存)的《杜工部诗疏解》;汪文柏(占籍桐乡,顺康间生存)的《杜韩诗句集韵》;毛张健(太仓人,康熙贡生)的《杜诗谱释》;李文炜(慈溪人,1653?—1725后)的《杜律通解》;范廷谋(鄞县人,1659—1728)的《杜诗直解》。
杜诗全集校注本有:钱谦益(常熟人,1582—1664)的《钱注杜诗》;徐树丕(1596—1683)的《杜诗执鞭录》;朱鹤龄((1601-1683)的《辑注杜工部集》;卢元昌(华亭人,1616—1693后)的《杜诗阐》;吴见思(武进人,1622?—1685)的《杜诗论文》;张远(萧山人,康熙间贡生)的《杜诗会粹》;朱彝尊(秀水人,1629—1709)的《朱竹诧先生杜诗评本》;周篆(青浦人,1642—1706)的《杜工部诗集集解》;仇兆鳌(鄞县人,1683—1717)的《杜诗详注》;浦起龙(无锡人,1679—1761)的《读杜心解》。
杜诗选注本有:金圣叹(吴县人,1608—1661)的《杜诗解》;吴兴祚(山阴人,1631—1697)的《杜少陵诗选》;吴冯栻(晋陵人,康熙间举人)的《青城说诗》;陈吁(海宁人,1649—1732后)的《读杜随笔》;何焯(长洲人,1661—1702)的《义门读书记·杜工部集》;王澍(金坛人,1668—1743)的《杜诗五古选录》;张雝敬(秀水人,顺康间生存)的《杜诗评点》。


二、社会历史背景下文人群体的选择
文学思潮、诗学风尚的出现,往往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如果说文学艺术作品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是受外部世界影响下的情感性创造,那么选择一定的文学路径,采用某种诗学方法,不仅是一种审美性取向,也是时代背景影响与压力下的社会性选择。
甲申之变,带来的是一场风轮火劫、神州陆沉的灾难。与某一朝代内部动乱不同的是,这是一次异族征服汉族的改朝换代,所引起的士心、民心的激荡与痛苦对明清之际人来说是空前的。而扬州、嘉定惨遭屠城,各地义师被残酷镇压,南京、苏州、杭州被马蹄踏平后,繁华胜迹顿成荒凉,“子女衣帛”遭受掳掠,凡此都在士人心中打上了国破家亡的羞恨戳记。随后,为彻底征服江南这片华夏士族聚集、文化高度发达之地,清廷以“三大案”连续进行残酷的打击,所涉遍及士林各个阶层。与此并行的招抚作为笼络士心的手段未必无效,但长期形成的“江南士气”是很难消弭的,不少被招抚者陷入矛盾与屈辱中,而更多的气节昂昂者在沿江、沿海进行着武装抗清。可以说,直至“三藩之乱”最终平定,江南都笼罩在一种特定的民族情绪之中。


然而江南地区受到的战争屠戮与政治高压更甚,文人的民族情绪借助知识化程度较高、擅长评点论次、好以实学究诘,且家族传续力强大、民间藏书丰富、刊印条件便利等多种人文因素,在杜集上更能实现广泛的情感投射和精神寄托,“诸家注杜”自能成为清初一个壮观的诗学景象了。这是江南特定人文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与社会变迁中的选择。
三、江南士人“定义杜诗”的努力
杜甫诗是中国古代诗歌高度发展的标志,而它又定格了那个高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它定义了中国古代诗歌。成为“高度标志”自然源于杜甫之伟大、杜诗之卓杰,然而“定格高度”则意味着诗歌创作发展中一种限度的存在,这是考察古代诗歌史理当回应的问题。
晚明上元人俞彦对此已有所注意,称其为“厄”。他在《范异羽先生集序》中说:

“诗厄人”一语实际上指出了千余年“作者林立”,“而好语亦几说尽”对后来者诗歌创造力的限制,而杜甫之“万卷”更使后来者高山仰止,望而却步。
在俞彦之前,围绕着杜诗“顶峰性评价”——“诗史”说已展开了讨论,杨慎即提出质疑:


其时江南士人为“定义杜诗”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在明清易代之变发生后,如何最能表现出深刻的民族情绪和忠君意识?回归杜甫的“诗史”性创作几乎成为共同的甚至唯一的选择,因此重新认识“诗史”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清初诗坛祭酒、文化大纛,吴中钱谦益与浙东黄宗羲对“诗史”的论述最具影响。钱谦益的论述极为辩证,一方面他肯定“史与诗同源”而“史亡诗作”:


黄宗羲的诗史观概见于人们已经相当熟悉的《万履安先生诗序》:

钱、黄之论的共同特点是呼唤“真诗史”,其中贯穿着他们对杜诗的理解,而这种理解不仅是对“诗史”观,同时也是对“杜诗”的一次权威性定义。



客观来看,在杜诗学史上清初顺康两朝江南士人的贡献巨大,不仅足以媲美宋人,且有积薪而上之成就。但笺注中一味考索,过度究根,造成对杜诗理解的碎片化乃至新的歧误解读的现象也随之产生。慈溪郑梁《观杜注有作》批评道:
陈言务去昌黎难,他人我先士衡怵。字字来历赏少陵,不满明者之一咥。奈何随声附和徒,无端笺注离其质。诬良为盗暴吏心,物物指为赃始毕。遂使千古诗中圣,仅同老蠹生简帙。目无所见耳无闻,一语不能如喑疾。假无古人生其前,世无工部集也必。岂知万卷读能破,然后有神出其笔。杜老自注已分明,世俗两眼徒如漆。五音之和律吕无,五味之调酸咸失。犹将梅盐金石求,千百中安能得一。呜呼!风雅之一途,非有性情人不悉。不图少达而多穷,既死犹遭人斧钻。(其一)

郑梁一生几乎完整地经历了顺康两朝,其《观杜注有作》的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在江南地区,其他各地学者、诗家都不断出现的杜诗笺注得失的评议。而正是这种持续的对既有(过去和当下)杜诗整理、研究的批评,形成了杜诗学发展的动力,也使得杜诗长期处在诗学视野的中心。从辩证的角度看,“争议”与“批评”,恰恰激活了“定义杜诗”的过程,丰富了“定义杜诗”的实践。
注释
:①钱谦益:《牧斋外集》卷二十五《雪堂选集题辞》。
②钱谦益:《初学集》卷三十二《曾房仲诗序》。
③朱舜水:《朱舜水集》卷十九《杜子美像赞》。
④按:本文江南指苏(含太仓)、松、常、镇四府与两浙地区,未包含江宁府和皖南地区。
⑤卢震:《说安堂集》,《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辑,第27册,第684页。
⑥以上据孙微《清代杜诗学》统计,在杜律注本凡15种中,江南人的著作占9种。
⑦以上据孙微《清代杜诗学》统计,在杜诗全集校注本凡14种中,江南人的著作占9种。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为康熙六十年夏撰写,雍正二年完成,主要是利用前十多年的读杜、研杜积累,故亦纳入。
⑧吴氏家族后移籍辽东清河,入汉军正红旗。
⑨以上据孙微《清代杜诗学》统计,在杜诗选注本凡13种中,江南人的著作占7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