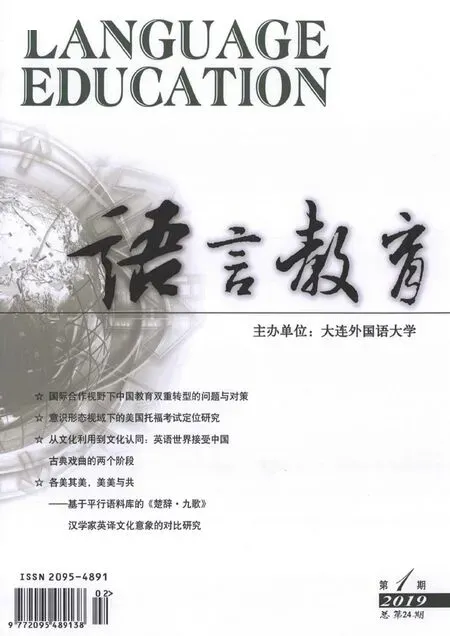论话语标记生成机制的研究
王银霞
(浙江大学,浙江杭州)
1. 引言
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或DMs)是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焦点。近年来,学者们分别从历时、共时和跨语言等角度对其进行了诸多描述、分析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任何一篇概述性文章或章节中,对“话语标记是什么”这一问题都难以达成一致的观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术语使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DMs具有多功能的语言形式却并不构成一个词类(如Fraser,1999, Fischer, 2006等)。Lewis(2011: 419-420)曾指出了几个颇受争议的问题,如“DMs到底属于句法范畴还是语用范畴,DMs包含哪些类型,DMs和连词、叹词、情态词、句子状语是什么关系,DMs与话语连接词、语用标记、语用表达式、语用助词等近义术语①如何区别和使用”等。这些争议反映了研究者对术语的选择、标识、功能和作用层面的观点大不相同,也展现了DMs的多功能性和本质描述上的复杂性。
目前,学界对DMs的生成机制争论不一。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理论和分析路径进行梳理。本文试图通过回顾和反思关于DMs演变的语法化、语用化、征派等理论的阐释力,以期更加深入了解DMs的生成、研究路径和方法,引起国内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和关注。
2. 话语标记的生成——语法化vs.语用化
2.1 话语标记的演变特征和语法化
一些语法化研究者认为,DMs 属于语法化现象。例如,Traugott(1995)指出,英语的indeed、in fact、besides发展成话语语首标记,展现了早期语法化的一些特征,如非范畴化、语音缩减、语义泛化等。尽管演变的结果是句法自由度的增强和句法范围的扩大,但语法化特征是显著的。Onodera(1995)讨论了日语中demo、dakedo获
得新的句法地位和语用功能而发展成DMs的过程。她认为尽管其中伴随着语用增强和主观化,但根据传统语法化的定义,此演变仍属于语法化的案例。同样,Brinton(2001)考察了看类结构(now) look (here)、lookyou、lookee、look it等的形成,认为它们展示了语法化的大部分特征,但她亦指出,看类结构的演变不同于一般的语法化,而是具有三种非典型特征,即:(i) DMs在获得语用和语篇表达功能的同时,其使用范围是扩大而非缩减的,这违反了句法压缩原则;(ii)DMs具有可选性,违反了句法上的固定原则;(iii) DMs是作为一个语段或一个完整构式而非单独的词汇开始演变,有悖于传统的语法化定义。
依照Lehmann的语法化参数模型(见表1),语法化是一个语言符号逐渐失去自主性的过程,其自主性程度由语言单位在聚合和组合层面的“权重、粘聚、变异性”决定。相应地,语法化程度可用音义完整性、结构辖域、聚合性、粘着性、聚合变异性和组合变异性这六个参数进行判断。词汇项或构式向语法项或弱语法项向强语法项的演化中往往伴随着语义、句法和语音方面的变化。但在DMs或具有话语结构功能成分的演变中,鲜有形式缩减、结构粘合和聚合层面的变化特征。跨语言的研究表明,传统的、狭义的语法化发生语音融蚀、语义虚化的现象是普遍的,而“那些具有分裂句法和韵律模式的语言如英语、日语和法语和其他语言中,语言演变的实例并不符合狭义语法化中各成分依附程度增强的模式”(Traugott, 2012: 228)。

表1 语法化参数(Lehmann, 1982/1995:110)
基于此,研究者提出,语法化不是结构缩减的过程,而是扩展的过程。扩展通常表现为四种类型——同构项类型扩展、句法环境扩展、语义-语用环境扩展(Himmelmann, 2004)和辖域扩展(Tabor & Traugott,1998)。扩展导致语言功能变化,词汇项常常变得更加抽象,构词能力更强,经历从概念义到程序义、从指称义到关系义的变化。扩展观同时主张,扩展而来的成分与语法化理论结合需要一个更为宽泛的语法概念。如果要把DMs看作语法化的结果,需要重新审视语法化在形态句法上的判断准则和语法本质(Traugott,1995: 5);在宽泛的语法概念里,语法不仅仅包括音系、形态、句法、语义的内容,还包括言语交际中对语言结构关系的编码、话语、语用和认知的成分(Andersen,2001:34)。语法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句法范围的缩小,而是一个词汇项在高度受限的语用和形态句法语境中获得某种语法功能,或者从一个语法形式获得更多语法功能的过程(Traugott,1995: 15)。基于此,扩展的、广义的语法化涵盖了DMs的演变。
2.2 话语标记是语用化现象
一些学者认为,尽管DMs的演变与语法化有相似之处,但其有悖于语法化的典型特征,用语法化解释其生成存在一些问题,他们由此提出了语用化路径,用以解释DMs和语气词的产生,试图将DMs之演变同典型的语法化路径区别开来,强调二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过程(Erman &Kotsinas, 1993; Aijmer, 1997; Gnthner & Mutz,2004; Frank-Job, 2006)。语法化导致语法标记的产生,其功能主要作用于句子内部;语用化导致DMs的出现,在话语层面起结构组织的作用。目前学界对语用化较为公认的定义是:
语用化,即一个词汇-语法序列或词汇形式在特定的语境中,丧失其命题意义而具有本质上的元交际话语互动意义的过程,语用化的形式或已有的语用成分进而可以发展出新的语用功能或语用形式(Claridge和Arnovick,2010: 187)。
研究者认为,当一个词汇项或构式向DM演变中,若无语法化这个中间阶段,其演变就属于语用化(Erman和Kotsinas,1993: 79)。譬如,英语的you know、I think、德语的obwohl(although)、西班牙语的bien(well)从完全的语法功能发展出话语功能,但没有形式、句法结构方面的变化和语音缩减,因而被判定为语用化的例子。
Degand和Evers-Vermeul(2015: 67)认为,把语用化、语法化区分开来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能够清楚划分语法和语用的界限,但这并非易事。 因为语法和语用并不像人们所认定的那样泾渭分明,Givn曾提出,语法本身就可以看作是凝固的语用锚(pragmatic anchoring)(转引自Diewald,2011:461)。尽管如此,语用化学者还是作出了不懈努力,尝试提出区分语法和语用的判断标准。Aijmer(1997: 2)提出了非真值条件标准,认为那些不能用真值判断的成分就是语用或语用化的成分,DMs之所以是语用化的成分,因为它涉及说话人对受话人的态度而非真值。Frank-job(2006)则归纳了语用化的5种形式特征——使用频率、语音缩减、句法隔离、邻近成分的意义共现、删除检验。她认为,语用化成分并没有为言语互动提供更多的命题内容,受程式化和功能明晰化的影响,标记语只是起了话语结构组织的作用。此外,Claridge(2013)讨论了goodbye、bless you、as it were等案例的演变,发现其语义上表现为虚化、滞留、(交互)主观化和语义分化,句法上表现出辖域扩展、形态缩减和句法可选性,并伴随着部分词汇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所讨论的案例中,虽然也有语法化的部分特征,但研究者声称,这些演化更适合用语用化而非语法化来解释。
语用化的提出提醒我们要关注某些语言现象的出现,如DMs如何具备了语用功能,同时也可以回避DMs是否为语法单位的问题。在特定语言实例中,当主观化和语法化的边界不能完全确定、所讨论的研究对象及其演变终点不能归于传统语法范畴时,语用化的解释就显得非常必要。
尽管如此,DMs的产生能否被看作一个独立的语用化过程仍备受争议。Beijering(2015)讨论了语用化、语法化和词汇化接口。他认为,DMs的演变可能具有语法化、词汇化和语用化的一种或几种特征,因此语言学家不愿为DMs赋予一个特定的语法地位。同时,已有的判断标准不能严格区分语用化和其他演变过程。例如,Aijmer的非真值条件标准并不具有绝对可选性,就主动结构和被动结构而言,它们显然既具有非真值条件的功能又是语法成分(Diewald,2011: 455)。根据Bazzanella(2006: 454)的观点,“DMs不直接影响话语真值,而是通过其语用意义影响话语真值的复杂性”。同时,DMs的一些特征如语义虚化、非词汇化、主观化和辖域扩展等也难以完全将语用化和语法化区分开来。
2.3 语法化、语用化之关系
语法化、语用化究竟是两个不同的过程还是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诸家观点迥异。参照前人的研究(Degand和Evers-vermeul, 2015: 62; Ocampo,2006; Heine, 2013),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1)语用化与语法化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应该对两种现象进行正确的描述。
2)语用化是语法化的次类。
3)根本不存在语用化,所谓的语用化只是语用功能的语法化。
持第一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DMs与语法成分不同,它们没有发展成强制性的语法成分,无固定的句法辖域限制,使用频率相对较低,且其新生的(交互)主观义尚未完全取代其命题义,因而可以把语用化看作语法化的初始阶段(Hansen,1998: 238)。然而,语用化过程一旦开始,其意义变化和语言演变随之发生。进一步的语用化可能导致DMs最终完全语法化,成为一个粘着语素或附着成分(Erman, 2001: 1357)。尽管语用化与语法化具有相似的特征(尤其在演化的最初阶段),但仍有必要区分这两种过程,因为并非所有语用化都导致语法化成分的产生。
第二种观点的研究者则坚持,语用化是语法化的自然发展,是语法化的一个子类。Wischer(2000: 359)指出,语用化是语篇或话语层面的语法化,而传统语法化属于命题层面的语法化,其相似之处是语言单位从一个较为开放的系统到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变化中都经历了非范畴化过程;语法化为连接两个相对独立的语言分支——语法和语用——提供了可行的分析工具。Wichmann(2011: 340)则提出,如果从韵律角度看,在未受到特别强调的情况下,典型的DMs是一个语调群的调首部分或核尾成分,如果用韵律结构变化而非句法结构变化来解释,DMs在演变中的韵律融合是增强的,这恰恰说明了它是语法化而不是与之相反。
第三种观点的学者声称,DMs是语法的一部分,无需把语用化看作一个单独的语言现象。Traugott(1995: 5)指出,在许多语言中,已经语法化的成分如时、体和语气词都具有一定的语用功能和非真值意义。Brinton和Traugott(2005: 136-140)认为,扩展的语法化能充分解释语用化术语下各种短语类和非短语类DMs的生成。Diewald(2011: 458)则表示,语法根植于语用,语法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语言项功能上锚固的过程,因而语用化可以看做是语法化的一个子类。
由以上讨论可见,语法化和语用化之争实际上涉及语法和语用关系之争。语用化和语法化在演化过程中互补分布,交互存在,有区别也有联系,但如何准确划分各自的作用域尚需深入探究(向明友等,2016: 168)。
3. 话语标记——边界vs.接口
尽管语用化、语法化都为DMs演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但也有研究者提出,二者都不足以解释DMs的本质,DMs的产生有可能是其他过程。其中两个最新、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为:(一)DMs是征派过程,属于边界现象;(二)DMs是常规化过程,属于接口现象。
3.1 话语标记是征派过程
3.1.1话语标记作为接入语
话语语法(Discourse Grammar或DG)的倡导者(Heine, 2013; Kaltenbck等,2011;Heine等, 2012)提出,语法是包含所有口语、书面语和手语的语言材料,可以划分为以动词及其论元结构为核心、通过命题概念和小句组织语篇的句子语法(Sentence Grammar或SG)和基于话语情境的接入语语法(Thetical Grammar或TG),SG、TG都有其内在的结构,在句法、韵律和语义上彼此不同。接入语是包括概念接入语、社交语、称呼语、祈使语、感叹语等不构成任何句法成分、具有人际语篇功能的话语信息单位,在特征上具有原型性。话语信息单位越多地呈现出如(1)的特征,就越有可能成为一个接入语。一般说来,若一个单位成分的出现不受句法制约,可以通过语调、停顿或标点符号与其主句分离,在话语中位置灵活且可以省略,那么该单位成分即可判定为接入语。DMs作为概念接入语的一种类型,具有(1a)-(1e)的所有特征。
a. 句法上独立;
b. 韵律上与话语语篇的其他成分相分离;
c. 意义上具有“ 非限制性”;
d. 语篇中位置通常自由;
e. 内在结构基于句子语法,但可以省略。
根据DG的观点,接入语的产生不应解释为语法化过程,而应解释为征派过程(cooptation)。征派就是诸如小句、短语、词汇等句子语法语块,为了话语组织的目的被征用为一个接入语成分,信息单位因此从句子语法层面转移到话语结构层面。以(2)为例:
(2)a. Bob is really a poet.
b. Bob is a poet, really!c. Really, Bob is a poet!
(2a)中的really作为副词使用,是SG成分。(2b)中的really不再是SG成分和句法、韵律的组成部分,其意义不再受SG规则的制约而是由话语情景决定,与语篇组织、言者态度、言者-听者互动、话语场景等话语成分相关,因此是被征用的、话语层面的接入语。
3.1.2 征派的特点、解释力及相关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者利用TG和征派理论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研究。在国外,Furk(2014)讨论了征派的阐释力,认为DMs作为一种语言范畴常常引起理论上的争论归因于其来源的多样性和判断标准的异质性。假设不同个体的DMs处于征派的不同阶段,它们就有可能并不同时共享该类型的全部原型特征。Davidse等(2015)借助TG及话语研究方法,重构了(there/it is/I have) (no) doubt从中世纪英语到近代英语向情态标记、DMs的演变,对比了它们同 (no) question 构式的演变差异。他们认为,与there be (no) question先词汇化后语法化的路径不同,there be no doubt的产生或多或少与瞬时语法情态义相关,而当时的存现结构促进了该构式向外置结构和插入语的征派,并发生进一步的词汇化。have/make doubt和have/make question演变过程相似,二者在否定语境中逐渐语法化,但I have/make no doubt逐渐具有了DMs的用法,而I have/make no question并未发展出此用法。现代英语中,只有there is no doubt保留了DMs的用法,这归因于语言使用的经济性原则以及由经济性和信息浓缩决定的语法完整性和明确性,也证明了征派的瞬时性和接入语在使用中的继续演化。在国内,龙海平和王耿(2014)利用征派理论,考察了“X是的”在近代汉语的演化。他们提出,现代汉语表肯定判断应答和疑问应答的“是的”均源自元明时期具有确认事件义的“是的”判断句,其形成和用法是一个未经任何中间阶段的瞬时征派过程而非语用化过程。杨望龙(2015)讨论了“你说、完了、别说、就是、然后”在不同时期作为SG和TG成分的用法,阐明了征派①杨望龙将cooptation译为“提取”。本文沿用了龙海平、王耿的翻译,一是便于术语统一,二是该译名更好反映了接入语的功能演变。的非渐变性、高频重复性和普遍性,认为征派本质上是一种认知交际策略。从以上研究案例来看,学人们十分强调征派的瞬时性、自发性及征派对DMs语法地位的解释力,但对具体案例的研究结论和观点又不尽相同。
概括时贤的观点,用征派解释DMs的生成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接入语本身为句法结构之外的成分,因此能阐明DMs为什么具有句法上的可选性而不影响命题的真值。第二,征派为DMs演变提供一种直观的、经验性的合理解释,有助于勾勒出它们演变的不同阶段。SG的接入语,被征派为一个TG成分后,与原句法环境的联系逐渐松散,最终被重新分析为一个句法上独立的成分。这种在句法上独立、在韵律上同源话语分离、在语义-语用范围扩大的事实不是语法化而是征派和接入语构成能够预测到的结果。第三,征派意味着特定DMs与其句法环境的联系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同DMs在组合层面上具有程度性,因此能更好解释DMs的异质性、为什么某些DMs具有接入语的典型特征而非全部特征。
然而,征派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DMs的生成,但它与语法化、语用化的界限并不泾渭分明。首先,从一些例子(如indeed, in fact, besides等)的演化来看,SG成分可能确实在征派之前就已语法化或词汇化。但如果DMs由瞬时接入语而来,语法化也可能发生在征派之后。一旦被征派,接入语就会经历语法化的过程,语法化程度越高,就越多地失去原有的词汇义。其次,征派也可能是语用化的一种形式。而且,由于征派具有瞬时性和自发性,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对特定语法表达而言,其首次发生征派的时间、在历史演变中被征派的次数就难以确定(Heine, 2013:1238-1240)。如果存在一个所谓的征派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有没有可能中断?征派同语用化、语法化、词汇化之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同时,征派的提出是建立在对语法二元划分的基础上,即存在着高于句子的DG,包括TG和SG。Heine等人(2014)曾利用神经语言学和失语症患者的证据论证了SG、TG的处理分别与左、右半脑活动紧密相联、新言语单位通常出现在SG层面而程式语大多出现在TG层面。但Kaltenbck和Heine(2014)指出,TG的瞬时接入语具有SG新言语单位的特征,而TG的程式语可看作句子成分历时演变的结果。从该角度讲,TG、SG并无严格的分界线,二者之间存在着竞争。由于人脑和语言的关系尚处于探索阶段,SG、TG和左右半脑的二元对应理论尚待证伪。相应地,征派有多大的实践价值和解释力还需要语言演变事实的进一步检验。
3.2 话语标记是常规化的结果
Detges和Waltereit(2016: 637-640)认为,如果从语用化、语法化的本质来看,语言标记的产生实际上都是常规化(routinization)的结果。常规化使特定语言符号使用更为频繁,逐步排除其他替代形式和可选项,进而限定了该符号的聚合变异度和组合变异度,同时淡化了其语音和语义。语言符号不同的常规化路径分别导致了核心语法项、语气词和DMs的产生。由于这些路径具有原型性而非范畴性,因此允许中间例子的存在。
从常规化视角来看,狭义的核心语法是言语说话人对(部分)命题相关性进行推理的无意识结果。推理的常规语具有交互主观性,是有效建构周期性情景的普遍模式,往往具有文化的、跨文化的乃至普遍的属性。一旦特定语言的说话人通过高频使用专门的语言形式表达之,常规语便获得了相应的语言地位(Hopper, 1998)。例如,时标记并非指时间本身,而是验证言语当时非现在事件状态所使用策略的副产品。语气词则显示了说话人对言语行为适宜性进行推理的特征。常规化使语气词不与任何单个词语或成分融合,从而与核心语法成分分离,在狭义范围内与句子结构融合,从而形成结构紧凑的范式。DMs有别于语气词,但同核心语法一样是在跨语言中得以证实的现象。
Detges和Waltereit(2016: 655)还提出,DMs在话语交流的语步中产生,在每次语步之后,说话人都要重新决定下一语步的内容,DMs就是协调话语语步常规化的产物。如look在Looka here,folkses, Jim Presley exclaimed.中为祈使语,提醒听者察觉语言内部或外部的刺激,而在Look, we don’t have to sit here. We could go down to the beach.中为DM,提醒听者注意话语的扩展,该用法的发展是祈使语协调言语活动中意义常规化和明晰化的结果。由于DMs辖域在话语层面,因此通常与句法结构松散结合在一起,出现在句子的左边缘或右边缘。可以说,DMs同核心语法、语气词一样,都是推理语步常规化过程的副产品,旨在解决不同交际问题,其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受语言使用的驱动。
按照Detges和Waltereit(2016)的观点,一方面,常规化是语言使用的本质特性;另一方面,常规化属于接口现象,它影响着语法模块的配置。在语义-话语接口,包含在每一语步中的原有推断都转变成语言项新的程序义。在句法-话语接口,语言项经过重新分析,失去原有的句法组合性。在话语-韵律(语音)接口,由于DMs并非关注焦点,往往直接导致其重音的丢失或语音实体随之消逝。当然,这些共同的变化也会受信息相关性、言语行为适宜性和话语连贯等语法本身之外因素的影响。简言之,常规化关注语言使用、聚焦于演变过程而非结果,因此可以解释DMs所具有的狭义语法化的部分特征,同时也能避免把DMs归属于语法化或语用化所引起的争议。
4. 结语
本文对DMs生成机制的几种理论①实际上, DMs生成机制不止文中所列,如词汇化也是常提及的一种(如Schiffrin,1987:319;董秀芳,2007)。但由于词汇化的结果往往是一个词汇项,故本文未将之单列。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阐述。从而得出,用以解释DMs生成的理论各有其有优点和不足:传统语法化与DMs演变具有相似之处,但不足以揭示DMs的独有特征;语用化能解释DMs如何具有了语用功能,但其判断标准并不能严格区分语用化和其他演变过程;征派能解释DMs的句法可选性、异质性,却难以确定那些在历史文献中难以考证的DMs发生征派的具体时间、次数,因此不易重构其演变过程;常规化揭示了语言使用影响着语法模块的配置和语法标记的接口问题,却不易解释DMs的异质性。
通过对不同理论的讨论,我们发现,DMs演变到底是语法化、语用化、征派还是其他,其本质上是否为语法成分往往取决于研究者如何定义、描写语法的概念和如何对语言演变的(子)过程(尤其是语法化)进行参数设置。如果研究者专注于单个DM的历时演变,语法概念就显得尤为相关,如果研究者聚焦于DMs的演变机制,就有必要考虑设置特定的参数模型。值得注意的是,Norde和Beijering(2014)提出了聚类分析方法,倡导从机制、基本变化和附带现象三方面对语言演变进行剖释,进而判辩某种(些)特定演变的典型案例和边缘案例,从而论证词汇化、语法化和语用化的梯度,获取边界案例和接口区域。这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分析路径。目前,相关的研究模式和理论亟待进一步深入,大样本的同种语言和跨语言类型学的实证数据显得相当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