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标志物对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预测的研究进展
郝 娟,陈嘉屿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消化内科,兰州 730000)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是胰酶(胰蛋白酶原为主)异常激活引起的胰腺急性炎症。AP具有起病急、进展快、并发症多、病死率高等特点[1]。炎性介质的过度释放和贯穿疾病全程的全身炎症反应是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乃至死亡的根本原因,早期识别炎症反应对疾病严重程度进行评估是减少并发症发生和改善预后的关键。目前,评估AP严重程度的评分系统或指标主要有临床指标[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APACHEⅡ)、Ranson评分、Glasgow评分(Imrie标准)、AP严重程度床旁指数、日本AP严重程度评分等]、生化指标[如血清淀粉酶、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降钙素原和脂肪酶等]以及胰腺形态学评估的CT严重程度指数评分等,在临床研究中以上评分系统或指标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已部分证实,但大多实施较复杂,甚至并不适用于AP早期评估。可见,寻找新的有价值的生物学标志物对尽早评估AP的严重程度有重要意义。现对预测AP严重程度的生物学标志物的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1 红细胞分布宽度
红细胞分布宽度(re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RDW)可反映红细胞体积异质性,其计算方法是将红细胞体积的标准差除以平均红细胞体积,结果用百分数表示。有研究表明,RDW与炎性标志物显著相关,如CRP、白细胞介素6和纤维蛋白原等[2]。Yan等[3]发现,RDW既能有效地区分急性间质性水肿性胰腺炎与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根据修订后亚特兰大分类),又能评估AP的预后,且简单、价廉、可重复[4]。有研究证实,RDW与AP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5-6]。Zhang等[5]对617例AP患者的研究发现,确定AP患者应在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治疗的RDW最佳临界值为13.55%,灵敏度为54.5%,特异度为73.6%。Gravito-Soares等[7]对312例AP患者进行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发现,RDW0h(即0 h的RDW值)和RDW0h-血清总钙比是AP的主要预测因子,RDW0h>13.0%和RDW0h-血清总钙比>1.4可较好地预测AP的严重性,RDW0h>14.0%和RDW0h-血清总钙比>1.7可较好地预测AP患者的病死率,且优于常规预后评分系统。一项横断面研究发现[8],RDW预测AP患者病死率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5.0%和89.8%,其与病死率的显著相关性不仅与贫血有关,还可能与炎症有关。炎症可以促进红细胞死亡或抑制红细胞成熟,也可改变细胞膜结构,导致红细胞形态学的变化,同时还会增加氧化应激,使红细胞增多,导致大量的不成熟红细胞释放到血液循环[9]。因此,RDW有望成为有价值的预测AP严重性的标志物。
2 钙调磷酸酶调节因子1
钙调磷酸酶是一种丝氨酸-苏氨酸磷酸酶,依赖Ca2+和钙调蛋白而参与细胞凋亡和神经死亡等生理病理过程。钙调磷酸酶调节因子1(regulator of calcineurin 1,RCAN1)最早是由Fuentes等[10]在21号染色体21q22.1~21q22.2区域发现的一种调节基因。RCAN1通过与钙调磷酸酶亚基A的直接结合,抑制钙调磷酸酶的活性,减弱下游底物活化T细胞核因子的去磷酸化作用,抑制活化T细胞核因子的核转移,从而减少细胞因子的释放。目前,关于RCAN1作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癌症、心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唐氏综合征等疾病,而RCAN1与AP关系的研究报道较罕见[11-14]。Wu和Song[15]研究发现,氧化应激导致细胞凋亡时释放大量ATP,而ATP是Nod样受体蛋白3炎症小体的经典激动剂,最终活化的Nod样受体蛋白3炎症小体会导致白细胞介素1β等促炎因子的产生,引起胰腺和胰周组织的损伤[16]。雷倩倩等[17]通过分离培养野生型小鼠和RCAN1基因缺失小鼠的腹腔巨噬细胞,对RCAN1调控Nod样受体蛋白3炎症小体的研究证实,RCAN1能够负向调控Nod样受体蛋白3炎症小体活化信号,参与调节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AP的炎症反应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氧化应激调节,而氧化应激也可以对RCAN1进行调节[18]。Norberg等[19]通过雨蛙素诱导C57BL/6J小鼠胰腺炎的研究发现,RCAN1由作为小鼠胰腺腺泡原代细胞替代物的AR42J细胞氧化应激引起,可检测到血浆中RCAN1蛋白显著上调,并可结合其他标志物用于AP的诊断;同时还发现氧化应激是炎症的共同特征,故认为RCAN1可能只是缺乏特异性的一般急性炎症标志物。综上所述,RCAN1仍具有作为AP诊断标记以及预测疾病严重程度的潜力。
3 穿透素3
穿透素3是穿透素家族成员之一,属多亚基糖蛋白,最早在内皮细胞及成纤维细胞中发现[20]。穿透素家族是一种参与机体免疫应答反应并介导炎症急性期的模式识别受体蛋白,根据一级结构亚单位的不同可分为短链穿透素(CRP和血浆淀粉样蛋白A)和长链穿透素(穿透素3)。穿透素3在先天性免疫反应中发挥很大作用,早期参与宿主抗感染免疫并清除异物,正常血浆穿透素3<2 ng/mL,但炎症时急剧增加,常被用于炎症进程的检测[21]。Bastrup-Birk等[22]对261例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ICU患者的研究发现,血清穿透素3水平与脓毒症发展有关,高穿透素3患者90 d病死率较低穿透素3患者高25%,可见,穿透素3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和病死率有关。Simsek等[23]的研究表明,AP患者的CRP、穿透素3和过氧化物酶水平均有所升高,并在治疗后显著降低。有研究证实,AP早期穿透素3水平的变化模式与白细胞介素6相似,穿透素3早于CRP或血浆淀粉样蛋白A达到最高浓度,第1天就能区分AP的轻度和中度或重度,24 h内血浆淀粉样蛋白A获得最佳预后价值,而48 h后CRP的预后效用才增加[24-25]。因此,穿透素3可能对早期评估和预测AP的严重性有帮助,但是其如何帮助监测AP的炎症程度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阐释。
4 亲环素A
亲环素A是亲环素家族中进化高度保守的细胞内蛋白,在体内广泛分布,被认为是免疫抑制药物环孢素的高亲和力受体。亲环素A具有肽脯氨酰顺反异构酶活性,使亲环素A具有分子伴侣、蛋白折叠、蛋白转运等多种生物功能。在炎症或氧化应激相关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溃疡性结肠炎和冠状动脉疾病等)中,周围血液亲环素A水平明显增强[26-28]。Yu等[29]研究发现,在牛磺胆酸钠诱导的AP中,亲环素A既能通过激活核因子κB通路促进胰腺损伤的表达,又能作为细胞因子直接触发炎症反应;在缩胆囊素诱导的胰腺炎腺泡细胞中,细胞释放亲环素A蛋白质并存在于培养基中,证明亲环素A的释放可能被用作坏死性生物标志。但有研究发现,亲环素A蛋白的表达在6 h达到最高,而与腺泡细胞死亡的严重程度没有直接关系,故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实[30]。Lu等[31]对4年内纳入的210例AP患者进行了一项前瞻性观察研究发现,血清亲环素A水平与AP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且对轻型AP及重症AP(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有明显的鉴别能力,其预测能力几乎与降钙素原水平相似,且明显超过了红细胞沉降率、白细胞计数和CRP等传统预测指标,说明亲环素A可能具有反映AP炎症和严重程度的潜力。
5 miR-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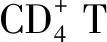
6 可溶性CD73
可溶性CD73即胞外-5′-核苷酸酶是一种产生腺苷的酶,具有核苷酸酶的活性和信号转导功能,在血液中以可溶形式循环,通过抑制白细胞渗出、免疫激活、血管渗漏、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功能、内皮细胞激活、细胞因子的释放和黏附因子的表达来抑制炎症,改善血管功能[36]。可溶性CD73与多种炎性疾病有关(如败血症、风湿性关节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动脉粥样硬化和癌症等),还可作为鉴定间充质干细胞的重要表面标志[37-39]。Maksimow等[40]对可溶性CD73预测AP严重程度的价值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可溶性CD73活性与AP患者的严重程度成反比;与CRP和肌酐相比,可溶性CD73可作为SAP的独立预测因子,且对重症AP的预测价值更高,因此,根据入院时可溶性CD73的活性就可预测还未显示任何明显器官衰竭迹象患者向SAP发展的可能。Jiang等[41]认为Maksimow等[40]的研究为AP严重程度的早期预测研究提供了新方向,也将促进对可溶性CD73和AP关系的进一步研究,但该研究样本量较小,且未与可溶性CD73以及其他成熟的预后模型进行比较,故目前可溶性CD73的预后表现仍不能确定。
7 载脂蛋白B与A-I比率
载脂蛋白(apolipoprotein,apo)是血浆脂蛋白中重要的结构和功能蛋白,已在心血管疾病和代谢综合征中广泛研究[42-47]。apoA-I是主要的高密度脂蛋白,它是一种抗动脉硬化脂蛋白,可作为结构蛋白调节胆固醇的反向转移,激活胆固醇酯化酶,并作为肝脏受体的配体,apoB是主要的低密度和极低密度脂蛋白,在动脉粥样硬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apoB/apoA-I比率可以预测动脉粥样硬化脂蛋白和抗动脉粥样硬化脂蛋白之间的平衡关系[48-49]。但是,很少有关于apoB/apoA-I比率与AP严重程度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实验表明,急性炎症性疾病和慢性炎症性疾病都会诱发对apo的翻译后修饰,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ICU患者apoA-I水平下降;相反,在炎症条件下,apoB的水平会升高[50-52]。因此,Huh等[53]推测apoB/apoA-I比率可能与AP及其严重程度有关,并通过一项191例的前瞻性研究证实,与其他脂质参数相比,apoB/apoA-I比率与AP的严重程度显著相关,这可能与动脉粥样硬化性血脂异常增强炎症级联反应并诱发胰腺氧化应激有关[54]。apoB/apoA-I比率随时可测量(不需禁食),可能是临床实践中预测AP及其严重程度的新的简单易行的生物学标志物。目前,apoB/apoA-I比率可预测AP严重程度,为评估AP严重程度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有关研究均为横断面设计,且未与其他生物学标志物进行比较,所以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证实其特异性、准确性和实用性。
8 油酸氯醇
油酸氯醇可能是通过过氧化物酶的催化反应参与AP的进展过程,活化的多形核中性粒细胞在胰腺和脂肪组织周围浸润,导致次氯酸产生[55]。随着AP的发展(尤其是炎症反应的增强),大量过氧化物酶与胰脂肪酶结合,导致脂肪酸氯醇的产生和释放,以油酸氯醇最多。油酸氯醇是由过氧化物酶和脂肪酶两种酶系统联合作用产生的,在SAP中尤为活跃。Franco-Pons等[56]在AP动物模型中证实了脂肪酸氯醇对腹腔巨噬细胞活化和全身炎症反应的影响,同时研究脂肪酸氯醇在脂肪组织、腹水、血浆中的含量发现,只能在AP患者血浆中检测到油酸氯醇。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队列研究发现,AP患者入院24 h内油酸氯醇含量显著升高,以7.49 nmol为界,油酸氯醇区分中度和重度胰腺炎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6.6%和90.0%,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0.3%和96.4%。而以32.4 nmol为界,油酸氯醇对SAP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以及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均为100%;同时还发现油酸氯醇较AP严重程度床旁指数、48 h血细胞比容、CRP等评估手段更有优势,可以作为预测AP严重程度的早期和准确的生物学标志物[57]。目前,油酸氯醇作为预测AP严重程度标志物的报道较罕见,只有两家医院59例患者(其中SAP患者仅13例)参与,限于油酸氯醇两种异构体参与机制不同以及样本量过小等,需要更多的大样本队列研究进一步证实。
9 小 结
AP的预防重于治疗,其病情发展迅速且变化多端,故早期动态评估和预测成为其治疗的关键。生物学标志物具有快速、简单、可重复检测、敏感性好等优势,对AP严重程度评估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目前,对于生物学标志物的研究很多,但多处于早期研究阶段,且部分研究样本量较小,还需更多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的证实。同时,继续寻找更有价值的新靶点,将为AP早期诊治带来新的希望和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