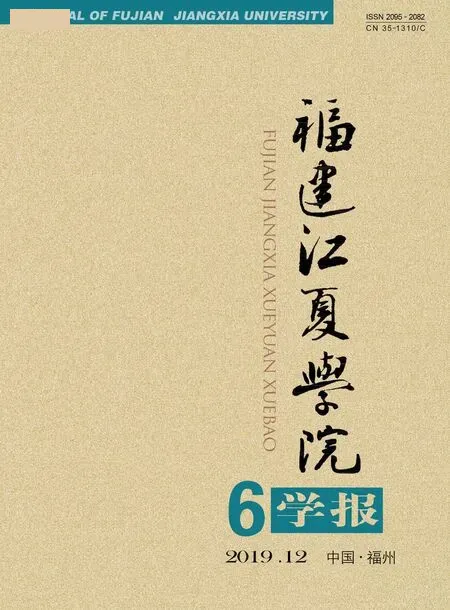冯梦龙“三言”:虚实空间的构建与转换
程慧琴,潘旭君
(1.2.福建江夏学院设计与创意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时间和空间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维度,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相对于时间来说,空间包罗万象,具有多变性、复杂性等特点。20世纪末,我国学者亦将文学研究视角投向空间问题,并在古代诗词、散文、戏曲等方面取得若干成就。它们或是以研究者对现实生活空间的观察与认知为基础,探讨空间创设与作品意境、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关系;或是从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地域范围等方面探索作品的时空演变;或是以文学创作中的意象为中心,凸显叙事过程情感空间伸缩转换及其所运用的艺术技巧,等等。这些文学形式的艺术空间一般是单向、简略的,小说空间则不然。小说空间往往是多向、复杂的,是情节发展所需的时虚时实、变幻多样的多维空间,它与人物心理空间、想象空间等紧密相连、互为衬托,从而形成立体式的“整体空间结构”。
文学作品或多或少都留存着时代的印迹。如果要突破时代的限制和固有的模式,作家往往会另辟蹊径、别出机杼,而构建独具吸引力的灵异虚拟空间便成了他们创新的一个重要选择。在古代神灵文化的影响下,为了表达丰富的心理感受,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惩恶扬善的期盼及高尚人格的推崇等,中国古代小说不但构建了人物活动丰富多彩的现实空间,展现鲜活的社会生活,而且还将现实生活中的众多无奈、愿景巧妙地移植到一个个奇幻的想象世界之中,从而创造出诸多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灵异虚拟空间,使得小说内涵更加丰富,人物形象更加饱满,艺术表达更具感染力。但要让读者能够轻松地接受从现实空间到虚构空间的转换,且陶醉其中,这对作家的生活观察能力和艺术创造力是个考验,明代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无疑就是成功的典范。他的杰出代表作品“三言”创设了大量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小说空间,而且在空间的构建与转换上独具特色,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呈现一个又一个形式与内容交相辉映的艺术世界。
一、虚实空间转换方式的合理性与多元化
小说中的“虚实空间”包括现实空间和虚幻空间。虚实空间转换首先应当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和阅读习惯,这样才有可能产生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艺术效果。“三言”中出现虚幻空间(或称神怪异域空间)的作品约占总数1/5,而由现实空间进入虚幻空间,作品主要是根据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采用多样、独特的插入方式,比如选择和运用梦境、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和睹物思情等一些日常生活情景来作为虚实空间转换的媒介,小说情节由此得以自然扩展和延续,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一)梦境——现实生活的折射与反映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是人人都有的生活体验。梦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与现实生活若即若离、似影随形的现象,常常使人惊叹不已;由此而演化出来的梦文化也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言”中的不少篇章便是巧妙地运用梦文化所具备的广泛接受性这一特点,通过主人公做梦的形式,灵活地构建众多生动形象的梦境空间,即构建现实客观基础之上的虚幻空间,而且虚实空间之间的转换又雁过无痕、合乎情理,正所谓“虚亦实时实亦虚”。例如《醒世恒言》卷25《独孤生归途闹梦》入话故事中的夫妇,新婚“刚刚三日,其夫被官府唤去。原来为急解军粮事,文书上佥了他名姓,要他赴军前交纳。如违限时刻,军法从事。”连个告别都来不及,便立刻起身。那丈夫“一路趱行,心心念念想着浑家”,“行了一日,想到有万遍。是夜宿于旅店,梦见与浑家相聚如常”。“自此无夜不梦。到一月之后,梦见浑家怀孕在身,醒来付之一笑。”不料,三个月之后,丈夫回到家中,“其妻叙及别后相思,因说每夜梦中如此如此。所言光景,与丈夫一般无二,果然有了三个月身孕。”[1]494夫妻因思念深切而“梦魂相遇,交感成胎”,这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故事,但因为它具备了情感的真实性和真善美,并借助梦文化的影响力实现虚实空间的自然转换与流动,由此成为了中华梦文化系统中顺理成章的一个经典符号。正如冯梦龙在作品中所写的那样,“大凡梦想者,因也;有因便有想,有想便有梦。那白氏行思坐想,一心记挂着丈夫,所以梦中真灵飞越,有形有像,俱为实境。”[1]514于是,当作品主人公独孤遐叔科考落第,一去三年,思念妻子之际,恰好路过巫山,便向巫山神女祈祷,帮自己托梦妻子,向家中妻子报平安,并“许他赋诗为谢”[1]498。无独有偶,遐叔之妻白氏亦因思念丈夫,在梦中来到巫山女神庙里,祈梦女神。于是相互思念的夫妻俩果真在梦中相见,独孤遐叔也果真如诺赋诗一首。这种借助梦镜,将现实空间和虚幻空间交融起来,不但没有阻断故事发展的进程,反而更加吸引读者,使读者产生一种与作者直接对话的感觉,从而获得了梦境现实化的艺术效果。
更为离奇的是《喻世明言》卷16《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中的范巨卿为了践约,“自刎而死,魂驾阴风”[2]238,飞速前往好友所在地,与好友在现实中如期相会;《醒世恒言》卷26《薛录事鱼服证仙》通过薛录事幻化为鱼,旁观同僚经历的现实,鲜活地展示了一个虚实互渗的梦境;《警世通言》卷30《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的吴清在病中梦见爱爱前来相见告别,并赠玉雪丹两粒,“将一粒纳于小员外袖内,一粒纳于口中”;回到现实后,发现“口中觉有异香”,且“一粒金丹尚在,宛如梦中所见”,[3]448等等。梦境源于现实,现实又回应梦境。这些以梦境为媒介,顺利完成现实空间虚幻化或虚幻空间现实化的独特艺术手法的交替运用,轻松地化解了因时空等条件限制而难以实现的人生愿望的障碍,弥补了人生未尽的种种缺憾,极大地满足了读者心理和精神上的美好需求;同时,在梦境与现实的互动激荡中,形成了令人遐思的多维空间结构,故事情节随之跌宕起伏,人物性格更加鲜活饱满。梦境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它对小说虚实空间的构建和转换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突发的自然力量——现实生活的自然延伸
以突发的、强大的自然力量为虚实空间转换的媒介,是“三言”独特的艺术手法。在大自然巨大的突发力量面前,如狂风、雷电、地震等,人们可能因惊吓过度或恐惧而产生独特的幻觉或幻象,这是一种已被科学研究与实验所证实的心理过度反应现象。“三言”作品中有些人物正是面对大自然威力之时,由现实空间进入虚幻空间,开启了他们奇异梦幻的历程。这样的空间切换表面上具有超现实的属性,实际上还是现实生活的一种自然延伸。《喻世明言》卷20《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陈从善携妻子张如春一同赴任,到梅岭下客栈投宿时,遇上了一阵狂风,这风“吹折地狱门前树,刮起酆都顶上尘。”“陈巡检大惊,急穿衣起来看时,就房中不见了孺人。”陈从善和王吉“主仆二人急叫店主人时,叫不应了。仔细看时,和店房都不见了”。“看时,二人立在荒郊野地上,止有书箱行李并马在面前,并无灯火,客店、店主人皆无踪迹。只因此夜,直教陈巡检三年不见孺人之面。”[2]285-286“一阵狂风”让张如春至此进入了申阳公所创设的梦幻空间中。《醒世恒言》卷5《大树坡义虎送亲》中的勤自励曾无意中救过一只大虎,投军十年后回家,获悉媳妇被逼嫁人,勤自励仗剑前往岳家质问,走到大树坡时,忽地刮起一阵大风,“舒着头往外张望,见两盏红灯,若隐若现,忽地刮喇的一声响亮,如天崩地裂,一件东西向前而坠。惊得勤自励倒身入内”[1]101。那坠物竟然是他未过门的媳妇,“从来只道虎伤人,今日方知虎报恩”[1]102,看又是“一阵大风”送来了勤自励的媳妇。这种借助大自然的某些力量来实现“时间、力量和空间”的契合,不但可以增加故事的曲折性和神秘性,而且为故事情节的进一步拓展提供更为宽阔的空间。
(三) “物”——嫁接现实空间与虚幻空间的媒介
睹“物”生情也是中国传统小说常用的空间转换方式之一。一方手帕、一块玉佩,一把头簪、一个箱子、一封信件或一张纸,甚至一只鞋子等,都可以成为各在一方、相互思念的情人或朋友之间的慰藉。“三言”常常就是借用这种转换手法来帮助主人公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故事人物也因此更加鲜活生动。《醒世恒言》卷32《黄秀才徼灵玉马坠》中的“玉马坠”不但是小说空间转换的重要媒介,而且直接影响了主人公的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展开。主人公黄损无意中将祖传之物“玉马坠”赠一投缘老者,因此成就了一段好姻缘。在意中人韩玉娥即将遭奸臣吕用之侮辱之际,“玉马坠”瞬间幻化为丈余长的白马从床头奔出,欲啮吕贼,吕贼惊慌逃去。“玉马坠”成了故事空间构建与转换的重要轴心。
而为众人所熟悉的《警世通言》卷32《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百宝箱”则无疑将是“物”的作用推向极致。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并投江自尽后,“百宝箱”竟然被监生柳遇春捞起。是夜,杜十娘入梦来,诉以李郎之薄幸,并奉匣以谢柳君曾经的慷慨相助。此“小匣儿”成了杜十娘报恩之信物。这种以情驭物,以物显情,“物”“情”之间完美融合与统一的境界,成了小说合理嫁接现实空间与虚幻空间的理想桥梁之一。
二、虚实空间场景切换的独特性与艺术性
用电影镜头语言来处理空间的转换与流动,是“三言”的又一艺术特色。现实空间与虚幻空间的切换,讲究的是自然流畅,如果切换过程缺乏舒缓适顺,留给观众将可能是生硬晦涩造作的不适感。为此,电影导演或摄影师在处理画面时,总是遵循由实渐淡、由淡入虚的原则,这与现实中人们观察事物的规律相契合,从而使电影作品达到流畅逼真的艺术效果。电影如此,小说也不例外。小说常常也运用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来构建空间的巨大差异。“三言”就是巧妙地运用了现代电影镜头语言艺术来实现空间的转换,从而获得流畅逼真的艺术效果。
(一)空间转换地点选择的独特性
“三言”中许多涉及情节与空间转换的地点精巧且韵味深长,不是人烟稀少、偏僻的荒郊野外,就是边缘地带的残垣断壁、枯井草屋、废园庙宇、厕所、洞穴等,如《警世通言》卷19《崔衙内白鹞招妖》中的定山草屋、卷27《假神仙大闹华光庙》中的华光庙、卷36《皂角林大王假形》中的皂角林大王庙、《醒世恒言》卷4《灌园叟晚逢仙女》中的花园、卷6《小水湾天狐诒书》中的茂林、卷37《杜子春三入长安》的波斯馆、《喻世明言》卷20《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的梅岭申阳洞,等等;这些特殊的边缘空间本身就具备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的特点,为神灵鬼怪特殊技能的施展提供便利的空间,亦为淡进淡出的空间转换预设了特殊的通道。《醒世恒言》卷31《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中的“古井”,处于城外边远的“路旁”,是个历年积尘、无人问津的枯井,一日突现“黑气冲天”的奇异现象。为了一探究竟,开封府大尹“即具奏朝廷,便指挥狱中,拣选当死罪人下井,要看仔细。”虽然,“一个下去一个死,二人下去一双亡。”[1]651-652连续数十人死亡,仍继续实行,于是便有了郑信下井,以及下井后的系列奇遇,巧妙自然地实现了枯井外的现实空间到枯井内虚幻空间的明暗转换。
(二)空间转换地点的现实性
作品空间转换的地点虽然偏僻异常、荒芜破败,与繁华热闹的市井空间有一定的差别,却仍是现实空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不过不是人们日常所关注的中心而已。仔细观察作品所涉及的空间内容,不难发现,妖怪神仙居住、所在的空间,无论是荒芜废址、深山峡谷,还是庭院花园、残垣断壁,都有现实空间的影子,与人间生活空间紧密相关,反映了各个阶层各个侧面的现实生活面貌,只是由于作者的有意渲染,才逐渐“变异”而成。故事的空间结构往往是以实际空间的“真实空间性”为外在基础,以虚幻空间的“非常空间性”为内在环境结合而成的,呈现虚实交错、由实而虚、虚中有实等特点,从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容易吸引读者。
(三)热闹到静寂、从静寂至虚空的渐进性
如果喧哗的市井给人一种强烈的真实存在感,上述这些虚静阴冷的场景则无疑透露即将出离现实的迹象,成了虚实空间转换的中间地带。如《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中的“古井”便是郑信进入仙境的重要转换点。如前所述,“古井”是现实空间中常见的场景,但是置放于人迹罕见的城外“路旁”,就明显不同于繁杂的市井生活空间,具有神秘怪异、变幻莫测的特征。进入这种特定的转换地带,读者便会油然而生一种即将追随作品主人公探奇历险之预感。郑信并非一进“古井”就立刻发现神仙洞府,而是经历“登危历险,寻径而往”的渐进过程,才进入“日霞之殿”和“月华之殿”。这种由热闹市井到静寂废墟,再由静寂废墟到虚空仙境的渐进空间转换过程,不仅可以产生水到渠成、行云流水的艺术效果,而且契合了读者的阅读心理和生活体悟。这与电影画面由实渐淡、从淡入虚的特点何其相似。
梦幻但不突兀,超越却有迹可循。优秀的空间构建和转换方式具有锦上添花的魔力,它能营造出特有的神奇氛围和动感世界,拓展出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而丰富作品的艺术内容,提升作品的可读性。
三、虚实空间意识变化的主动性与被动性
小说虚实空间的建构是以人的意识形态为内在基础,以人的主动行为、自由意志、存在意识等为基本要素而形成的,充满着人的自我回归精神和理念。如果现实空间受外力威胁或外界因素的干扰,人的自我意识和观念便会减弱,甚至失去自由意识与自我存在意识,从而被迫进入虚幻空间。“三言”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作品就是通过主人公的主动或被动进入虚幻空间的方式,来实现虚实空间的场景交替与转换。如果作品的主人公是主动进入虚幻空间,其空间构成往往为“自我存在”的“自愿空间”,并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空间意识,预示着他(她)可能即将进入快乐幸福的“天堂”;如果是被动进入,其空间结构则为“自我失去”的“拘束空间”,主人公容易失去自我存在的意识,等待他们的可能是地狱般的痛苦与磨难。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作品所蕴含的意义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即对光明、幸福的向往与追求,对黑暗、痛苦的憎恶与批判。
《李道人独步云门》中的李青在他七十大寿的这一天,主动要求自己的子孙将他放入云门山上的大穴洞中,从而进入了他梦想已久的仙境,历经种种磨难后,最终如愿化仙;《喻世明言》卷13《张道陵七试赵升》中的赵升,为投入张道陵门下,也是主动进入传说中神秘的龙虎山,经受了幻境中的辱骂、美色、黄金、虎暴、被诬、乞丐臭秽等种种考验,乃至舍命从师,最终亦成就了他的成仙梦想。而主人公如果是被迫进入“虚幻空间”,则将可能失去自我主宰的空间意识,产生丧失感和陌生感,甚至失去自我判断和思考能力。如《警世通言》卷19《崔衙内白鹞招妖》中的崔衙内在“红兔儿”的诱惑下,完全相信自己与上界神仙“红兔儿”有“五百年姻缘”,其心理上已经不存在自我意志的空间意识,被动进入虚幻空间,险些儿丧了性命。《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的陈如春被摄到申阳洞三年,完全失去了自我存在意识,只能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挑水灌花之活,等等。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皆因种种缘故而被迫进入虚幻空间,他们在心理和行动上都已失去自我主宰的空间意识,直至经历了自我空间与拘束空间的不断冲突和摩擦后,才回归本源,重新构建自我空间。
“三言”中也有“主动”与“被动”并行出现的现象,但无论“主动”和“被动”的顺序如何变化,都是为合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而服务。如《醒世恒言》卷6《小水湾天狐诒书》中的野狐为了夺回“天书”,便借用主人公王臣的身份自由穿梭于现实空间与虚幻空间之中;而王臣因一时好奇,夺走了野狐的“天书”,便多次自愿或被动进入野狐所营造的虚幻空间,形成了虚幻空间与现实空间互为交织的奇异世界。第一次在人烟稀少的茂林里,王臣用弹弓打中野狐,拾得“天书”,主动进入了虚幻空间;之后,固执的王臣拒不返还“天书”,野狐便不断缠绕,王臣多次被动进入虚幻空间;而当野狐从王臣手中骗回“天书”后,虚幻空间便戛然而止,王臣被野狐搅乱的现实生活轨迹至此回归正常。这个“主动进入”“被动进入”“被动逃出”的复杂时空场的流动过程,将现实空间与虚幻空间紧密连接起来,并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从而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醒世恒言》卷4《灌园叟晚逢仙女》中的秋先因受恶霸张委的欺占诬陷,多次或被动或主动进入虚幻空间,最后在花仙的帮助下,不但战胜恶势力,严惩了恶霸,而且还因“日饵百花”,广做善事,而“功行圆满,成为护花使者,专管人间百花”[1]90。同样,《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中的郑信起先是被逼下井(被动),但进入“日霞殿”之后,主动进入空间的成份就相当明显,不但流连仙境三年,还与日霞仙子生下一男一女;后因自己的功名前程未就,才主动要求出宫,投军卫国,累立战功,官至两川节度使,等等。
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在顺应自然与合乎人性等方面进行不懈努力。现实生活中,主动往往意味着阳光和快乐;被动则可能与黑暗和痛苦相关。天上人间皆出一理。“三言”在空间的转换上,巧妙地赋予“主动”和“被动”形式以 “快乐”和“痛苦”的意义,可谓情理相依、言意共生,形式和内容相得益彰。
四、虚实空间人神幻化的同构性与象征性
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中的虚幻空间常常闪动着鬼怪神灵的魅影,但写鬼怪神灵归根结底只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手段,写人才是真正的目的。在“三言”有关空间转换的作品中,无论神灵鬼怪多么神通广大,但是它们一旦进入人间,就只能入乡随俗、幻化为人,其外形、言辞和行为方式等皆与常人一样,也都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如《小水湾天狐诒书》中的野狐在现实空间里的形象与常人一般无二,变幻成客人、王福、王臣等,与原型分毫无差,就连原型的母亲、妻子、朋友都无法识破,直到从王臣手中骗还天书,才现出野狐的本相,跑得杳无踪影。《皂角林大王假形》中的皂角林大王变换成赵再理,其行为动作、语言、形象等跟真赵再理一模一样,真假难辨。假赵再理甚至还花重金贿赂官府,把个真赵再理发配到边缘地方,买通公差意图途中打死真赵再理,假赵再理冷静、残酷且思维缜密,比真赵再理还像赵再理。而且有些作品人物的原型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是现实人物的虚化,如《醒世恒言》卷37《杜子春三入长安》中的神仙太上老君,“童颜鹤发,碧眼庞眉。声似铜钟,须如银线。戴一顶青绢唐巾,被一领茶褐道袍,腰系丝绦,脚穿麻履”[1]766,俨然就是生活中常见的老者形象,等等。可见文学作品中神灵鬼怪形象无论如何离奇神秘,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生活的浓缩与提炼,亦是鲜活人性的影射和揭示。
到哪座山唱哪支山歌。生活空间的转移,意味着生活环境、文化习俗、文化氛围等也随之发生变化。即便是神通广大、呼风唤雨的神灵鬼怪到了人间也要调整心态,尽快去适应和认同人间的文化和习俗,这样才能与人类共生共存。“三言”中的神灵鬼怪时常穿梭于现实空间和虚幻空间之间,变幻莫测,无所不能,但不管作家用什么独特的技巧和手法,塑造什么样的特色形象,都离不开作家的思想追求和作品主题的一致性,即无论是真善美,还是假丑恶,这些神灵鬼怪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是人间生活的真实写照。神灵鬼怪世界只是人间生活的投影,离开了人,所谓的神灵鬼怪便不存在。可见,作品中虽然有虚实空间之别,但其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无不镌刻着人间的印记,无论何时何地,作者所要表达和推崇的应该都是扬善惩恶的思想和珍惜人间生活的希望。
小说空间是人物活动必不可少的场景或背景,它与人物形象的塑造紧密相关。比如一位主人公房间里的物件摆设、装饰风格或书房大小,都会透露出他的兴趣爱好、审美品味、价值取向等。所以,小说空间构建的能力往往会直接关系或影响到人们对作者艺术创造力的评价。如果说小说空间的构建与转换是小说情节发展的推进器,一旦这个推进器操控得当又能量充足,它就会产生“使故事发展跌宕起伏”和“让读者的感受舒缓和谐”的双重功效,而这无疑是对作者艺术创造力的最大肯定。“三言”中的许多作品在空间的构建和转换上,行云流水,游刃有余,尤其是空间转换的艺术手法的精妙老道,值得关注和探究。将“三言”放在更加广阔的知识背景和框架上进行研究,不仅能为深入解读“三言”提供更加多样的路径和方法,而且对小说的创作也能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