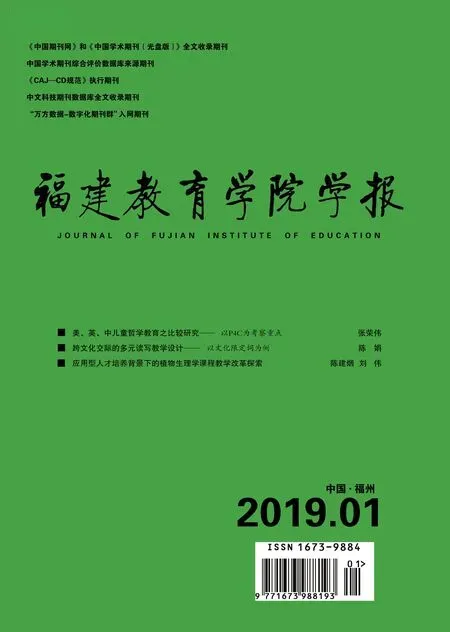身似异乡客 心是故乡魂
——赛珍珠与莫言对中国乡土的差异书写
杨华娟
(福建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25)
中国是世界农业最重要的发源地, 土地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繁衍万物、孕育生命的主要载体,土地皈依与地母崇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蕴与中国文学的审美定势。对于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则深深地镌刻着他们的行为活动和精神气质。享誉全球的美国作家赛珍珠是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自幼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称江苏“镇江”为“中国故乡”,并以书写中国乡土为己任,代表作《大地》可谓诺贝尔文学奖的首次“中国叙事”。《大地》塑造了王龙、阿兰等中国人形象,纠正了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对中国人的丑化与扭曲,第一次在西方读者特别是美国读者面前展示“有血有肉”中国人的正面形象,尤其是小说主人公阿龙对土地的依恋与热爱,与当时美国的重农主义思潮契合,引起了西方读者普遍的思想共鸣。当年的诺贝尔晚宴主持人对其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你赋予了我们西方人某种中国精神,使我们认识和感受到那些弥足珍贵的思想和情感……才把我们大家作为人类在这地球上连接在一起。”[1]74年后, 中国作家莫言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与前辈赛珍珠迥然不同的文化流向。他在思想和艺术上深受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和意识流作家福克纳的影响,并由于福克纳笔下“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发,开始描绘故乡“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版图,其作品“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运用魔幻主义文学形式开展了对中国乡土的独一无二的新叙事,以荒诞夸张的笔触迸射出中国文化的原始生命力。同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赛珍珠与莫言的创作都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并进一步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有趣的是,美国人赛珍珠的创作以东方的写实手法而闻名,又始终坚持西方价值观;中国人莫言以西方的魔幻主义色彩而著称,但始终固守着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 可以说赛珍珠是“以中为表, 以西为里”,莫言则是“以西为表,以中为里”,但又殊途同归,以各自的方式促进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两位诺奖获得者相隔半个多世纪,以中国的乡土与农民为书写对象,以东西方文化精髓为价值核心开展文学对话,谱写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独特篇章。
一、对中国社会的理性观察与深情浸入
赛珍珠与莫言的小说创作都以深厚的感情为基础,在浓墨重彩的描写中体现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顽强等宝贵品质, 塑造了丰满的中国农民形象,但二者的观察视角与切入深度存在巨大的差异。赛珍珠长期生活于中国,对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无论主观与客观,她都是“中国人民的友人”。然而,由于身份和生活的隔阂,对于与中国“土地”更为接近的现实图景、底层生活、原质人生来说, 赛珍珠始终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对中国社会只是一位旁观者,她对中国人特别是底层人民的苦难并没有切肤之痛,而是以欣赏的角度在中国传统文明的历史积淀中探寻“人类共有的思想感情”。王龙等人物对土地的眷恋超越了地域与时代, 《大地》三部曲的恋土之情源自王龙的父亲,归结于王龙的孙子,人对土地的依赖,似乎与具体的民族、地域无关,也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跌宕起伏的社会现实以及大多数国人的悲剧性命运缺乏相照应的紧密联系, 而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历史的诗意。如鲁迅所评:“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注:即赛珍珠)……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3]。正是由于这种差异,尽管赛珍珠对中国充满善意并在文学上取得了较高成就,却并未得到中国作家们的普遍认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面临危急存亡的生死关头,文学为政治服务已经成为“最强音”,描写共有的人性便显得“不那么正确”。不过,她的作品以“土地”为纽带搭建起了中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引起了西方读者的强烈共鸣,使他们对遥远陌生的东方国度与中国人民有了更加准确立体的理解和认同。
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莫言亲身体验过中国大地的政治运动和饥饿灾荒,目睹极端生活处境下人性的种种残酷行为。他秉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精神传统,其文学作品注重挖掘导致人物苦难命运背后的根源,展现社会矛盾和制度的弊端, 自觉寻找民族救赎之路——为“种的退化”寻找疗救良方,既非冷静旁观,也非理性审度,他把生命的激情与光辉投射给“我爷爷”“我奶奶”那一群人。这种在当时颇为新颖的叙事手法并非仅如作者所述的那样为了“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而是为了更为主动和真切的叙事,让读者对小说的故事发展与人物的苦难感同身受,并对复仇有着痛快淋漓的代入感。《丰乳肥臀》中上官家的女儿们无论是爱还是恨、生还是死, 都刻骨铭心、轰轰烈烈, 都体现出浓烈的感情色彩。作家放弃了以往农村题材小说拔高美化“农民英雄”的做法,写出他们“美丽与丑陋”“超脱与世人”“圣洁与龌龊”的复杂本质和本真状态。高密东北乡饱含着作家对土地的依恋,“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3]在作家笔下,《透明的红萝卜》土地长出的红萝卜成为某种神圣的象征;《丰乳肥臀》中土地被称为“血地”,婴儿降生于尘土中,脐血流在大街上;《红高粱家庭》青春迸发于高粱地中,流淌的鲜血归集于土地中。作家在崇敬、赞美前辈生命之力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后代种族退化的深深忧虑,那棵长在“在百马山之阳,黑水河之阴”的“纯种高粱”正是疗救的良方,他希望能够重构一个强健的、进取的、表现着生命活力的民族精神,使贫弱的民族走向世界之林。
二、对美与丑的辩证显现
赛珍珠与莫言的土地小说在情感抒发方式上都有浓郁的特性,但由于立场的差异,观察角度的不同,两位作家的作品呈现了审美与审丑的不同表象。
从赛珍珠的作品来看, 尽管她所经历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非常时期,但作为一位保持一定距离的旁观者, “距离产生美”,《大地》并未关注社会纷乱、人民苦难的现实,而是以“土地”这一世界普遍认同的文化符号为着力点,充满诗意地在永恒的时光中发掘人性之美。《大地》的开篇场景便是“朦胧的、天色微红的黎明,风吹动着窗户上一格撕破的窗纸”“一阵柔和的微风从东方徐徐吹来,透着湿意”。小说中的王龙是“土地”的化身,热爱土地,敬仰土地,土地不仅是其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其精神力量之源,他声称“我的地永远不卖……宁愿死在这块地上”,他的生命与土地早已无法分开。王龙简单而清晰的生命历程呈现出一种原始之美,浓缩着中华民族五千年农耕文化的生存智慧。阿兰则是“奉献”的化身,这位女仆出身的母亲任劳任怨,几十年如一日为家庭无私奉献,从不愿给家人添一点麻烦,怀孕了仍在土地上劳作,分娩时都不愿麻烦别人,甚至“忍着没发出叫声”,事后自己将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她从不要求什么,仅有的两粒小珍珠被丈夫送给妓女也不敢反抗,临死前都不愿花钱治病,“我的命不值得那么多钱,那能买好大一块地啊”。《大地三部曲》中没有真正的“恶人”,王虎是一位“非典型”军阀,不贪财、不好色,没有阴险、狡猾、残酷等“军阀本色”,凭着一腔热血,敢闯敢拼,打出一片天地,每日粗茶淡饭,痛恨部下的劫掠并亲自处决因抢戒指砍掉妇人手指的残暴士兵,他对儿子充满爱意,将其作为接班人倾注全部心血精心培养。丑陋的“豁嘴”是一位忠仆,几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辅佐王虎。王源身为军阀的儿子,却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留恋老屋、喜欢种田,在美国留学时自律自省,时时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崇尚简单自然的生活。《东风·西风》中的桂兰外表端庄秀丽,言谈文雅含蓄,体现了中国妇女的传统之美。赛珍珠笔下的这些人物也许缺乏深刻的人性刻画,缺乏广泛的社会意义,但却展示了人类情感中最为单纯且美丽的一面。
莫言的小说则如手术刀般剥开现实的表层,着力展现了层层压迫下农民的苦难,战乱、疾病、歧视和压迫充斥其中。他以冷静甚至残酷的笔触描写生之艰辛、人之丑陋,其中的人物又由于对命运的抗争焕发一种生命的力量、一种野性之美,正如巨石压迫下顽强冒头的小草,《红高粱》中写道“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4]这片土地的丑与美已融为一体,不可分离。《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出身贫寒,16岁杀人,四处流浪,如野草般疯长,在弱肉强食的残酷角逐中胜出,成长为土匪与抗日英雄的双料货。九儿美丽活泼,先是被父亲贪图“大黑骡子”许配给麻风病人,后受到土匪、日本人的多重欺压,可谓命运多舛,然而九儿从不屈服,与轿夫余占鳌相恋相依,与土匪、日本人周旋、抗争,野性十足,精明能干。她死前的那段意识流动酣畅淋漓, 简直就是反抗封建束缚的中国式的人权宣言。《欢乐》开篇便是“苍老疲惫的家门”“散发着腐败气味的隔年柴草垛”“女人有一嘴比猪屎还要黑的牙齿,稀疏的头发溜光溜光, 像狗舔过一样”;《酒国》中文质彬彬的金刚钻却是“吃人野兽”;《透明的红萝卜》黑孩儿“裤头染着一块块污渍”;《食草家庭》中手脚上粘连着蹼膜的孩子和漫山遍野的红蝗虫;莫言的小说中缺少优美的语言、精致的场景、和睦的家庭,却随处可见粗俗的咒骂、流血的痔疮、人性的扭曲,这种以丑衬美、以丑为美的创作手法无疑对读者的神经是一次挑战,却也更加接近于社会现实。美与丑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两位一体,莫言生于贫苦之家,成长于疯狂时代,对世界的荒诞与异化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作为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直视现实中的荒诞与丑陋, 并以艺术的手法呈现给读者, 正是其使命所在, 其中隐含的是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呼吁人们去颠覆和解构“丑” 的伦理价值和社会秩序,重建新的伦理价值和社会秩序。[5]
三、对外族文学形式的借鉴与对本族文化核心的固守
身为美国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儿时生活在中国,父亲对中国文化的肯定与认同对她产生了重要影响,她从小就学习中国文学,师从一位孔姓秀才学习中国文学经典、孔孟之道,正如其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说:“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在,都是在中国学到的。”她用中国传统的写实手法,在刻画富有民族特性的社会生活与习俗的同时,出色地描绘了全世界共同感兴趣的主题。《东风·西风》采用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叙事,以白描手法刻画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塑造人物。《大地三部曲》中采用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结构,众多人物的故事同时推进,形成互相影响、同步推进的网状的结构,王龙、阿兰等人物塑造也受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多采取写实的白描手法,即使有心理描写也多以第三者角度讲述,人物爱憎分明、目标明确,没有激烈的心理冲突,更没有当时西方已流行的意识流式的内心独白,这种创作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物刻画的深度。王龙、王虎等人物情感色彩浓郁、个性鲜明,但存在扁平化倾向,小说中只有情节的推进,没有人物性格相应的线型变化。同时,创作手法的中国化并不影响赛珍珠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与尊崇,她的价值观、爱情观、婚姻观终究属于西方,《东风·西风》中桂兰对丈夫的怀疑到理解到信任,表达了对西方文化的肯定与称颂,《大地三部曲》中王源终究要赴西方学习,寻找民族的出路,并选择了具有现代西方女性特征的梅琳作为伴侣。
莫言则成长于特殊的历史时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思想的禁锢和摧残之后,挣脱束缚的中国作家迎来了一次革命式的文学创作飞跃,众多外国文学作品流入中国,长期压抑的青年们如饥似渴地疯狂汲取营养,勇敢地尝试各种创作手法,而西方文学经过二战后的飞速发展表现手法日益丰富,寻根文学、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风靡一时,从莫言的作品可明显看出这种“海纳百川”的风格,既有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特征,又带有魔幻现实主义成分, 他深受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作家影响, “用虚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实融为一体”[5],并在30年的创作中一以贯之地保持魔幻风格。《透明的红萝卜》中“红萝卜晶莹透明, 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食草家族》中手肢生蹼的祖先、疯疯癫癫的族人,锔锅匠可以“伸掌打落一颗漂游的子弹头”;《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死时鲜血散发着浓郁的高粱酒香;《酒国》中骑着小黑驴、一身鱼鳞皮的小男孩;《丰乳肥臀》中患恋乳症的上官金童;《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历经六世轮回,转生为带有先天性不可治疾病的大头婴儿。可以说,莫言的小说充满了荒诞离奇、似魔似幻的情节, 令人震撼与痴迷,为高密东北乡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透过夸张扭曲的表象以及人物的迷惘与孤独,莫言的小说表现出了“精神失根的孤独”[6]等精神危机, 折射出作家对生命价值、文化关怀等严肃主题的思考。同时,莫言的魔幻小说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鬼仙文化、祖先崇拜等传统文化,“莫言作品中的思想是归于习见一类的,是来自熟人的乡土社会中朴素的认识论,是一种直觉式的、带有判断性的知识,它包含有天命观、泛神论、因果报应论,它相信历史运行的重复和生命的轮回,崇拜力和自然。”[7]他深受《聊斋志异》等传统文本及民间戏曲、乡间故事的影响,其艺术技巧、审美对象、审美思维方式来自于农村生活、农村体验, 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式的。
跨越时代与国度,赛珍珠与莫言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某种交流与对话,一方面, 人类对土地的眷恋、对爱的追求等共性使两位分属于东西方的文学大师有着相同的思想根基,另一方面,个性、文化、时代的相异与错位又使两位作家各自奉献出独具特色的作品,交相辉映,共同为世界文学长卷添上绚丽的色彩,这种交流与对话对于促进世界各国各民族相互间的沟通与理解,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赛珍珠的作品在西方广为流传,在中国却没有得到普遍认同;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在国内也曾广受质疑。两位作家对中国乡土的书写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获得了至高的荣誉,但在寻找中西方文化的最佳融合点方面仍存在某种缺憾,有待后来者进一步突破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