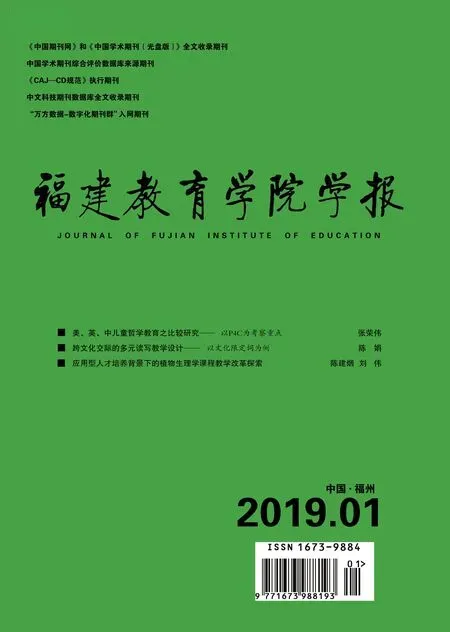儿童哲学内涵和儿童哲学教育目标与特征探析
徐容容
(福建教育科学研究所,福建 福州 350003)
儿童哲学教育较强的学科渗透性,探究共同体教学模式以及培养儿童学会思考的目标取向,在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方面表现出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儿童哲学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迫切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儿童哲学教育内涵,梳理儿童哲学与儿童哲学教育的内在联系与区别。基于此,笔者认为儿童哲学理应有两层意义指向:其一是属于儿童的哲学(philosophy by children),其二是关于儿童的哲学(philosophy of children)。儿童哲学教育意义指向是为了儿童的哲学(philosophy for children)。儿童哲学是成人对童真、童趣、童心的再次修行,让人们意识到保护儿童好学、好思、好问品质的重要性,教会人们重新审视儿童的世界。儿童哲学教育则是对理念认同的基础上践行理念,其首要意义是给予我们正确方法指导,使我们懂得运用特定的教材,明确主题,教儿童学会思考。儿童哲学与儿童哲学教育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一、哲学本义
哲学来源于英文“philosophy”,其含义就是“爱智慧”,泛指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如果人们对“哲学”只是这样宽泛的理解,很容易误以为“哲学”就是“智慧”,就是一种抽象的名词性概念,这便脱离了哲学本质。哲学是对智慧追求的动态过程,智慧则只是哲学追求的一种结果。以往学者从“philosophy”的源起大量论述过哲学本质。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关子伊先生运用语源学方法,以文字学研究为中心,别开生面地介绍了“哲”字源起,论述哲学本身。他在著作《语默无常——寻找定向中的哲学反思》中首篇《从“大克鼎”和“史墙盘”中的“哲”字看哲学》就开门见山地讨论起“哲”古文多种写法,古文“哲”动词性格等问题。
首先,“哲”在《说文》中解释为知也。从口折声。悊,哲或从心。嚞,古文哲从三吉。伊先生也发现“哲”在古代有多种异体字而吉祥的“吉”和折服的“折”就这些异体字中共同元素。其奥妙之处在于“吉”,从士口,居质切,《说文》中解释为善也;在于“折”引申出“断疑”“明辨”等抽象的概念[1]先生以此种语源学方法,推导出“哲”的本义就是追求真理,探索善,就是明辨之,慎思之,求善之。其次,哲学的“哲”应该是动词性格。如“克哲厥德” 意思是“能在各种环境中借着断疑和选择来实践德行”。[1]《说文》曰“哲,知也”, 《尔雅》亦作曰:“哲,智也”。可见哲学并不局限于由概念、范畴构成的逻辑体系,更是一个动态过程。人们用思维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本义的哲学。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哲学的本质不是掌握真理,而是探究真理。这样看来,哲学并不是满腹经纶者的专属,不是辨析概念的游戏,而是积极探索生命中的困惑,认真思考、批判和抉择的全过程。
不管“philosophy” 源起何处,或是古文“哲”的动词属性及多种异体字,都得出“哲学就是爱智慧”的结论,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哲学,这包括儿童。李普曼认为儿童哲学教育就是培养儿童批判性思维,马修斯则认为哲学本就在儿童世界,儿童有自己的哲学,应该与他们对话来“做”哲学。[2]国内学者刘晓东指明,儿童哲学应有三层内涵:一是作为思维训练的哲学启蒙;二是作为智慧探求的哲学启蒙;三是作为文化陶冶的哲学启蒙[3]张荣伟教授也曾指出,儿童哲学内涵应该有两层意义指向,即属于儿童的哲学(philosophy by children)、关于儿童的哲学(philosophy of children),儿童哲学教育就是为了儿童的哲学(philosophy for children)。[4]笔者十分认同张教授的观点认为儿童哲学有两层意义指向。儿童哲学教育即P4C,是在尊重儿童世界和科学儿童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运用适宜的教材内容,采用群体探究方法,教儿童学会思考。
二、儿童哲学的内涵
儿童哲学本质是对儿童世界、儿童观的探析。在儿童世界里,儿童的幻想、追问、探索、思考的过程,就属于儿童的哲学。成人尊重儿童,保护儿童质疑、批判和追问的哲学品质就是关于儿童的哲学。
(一)属于儿童的哲学
儿童哲学第一层意义指向是属于儿童的哲学,即philosophy by children,指儿童所特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对儿童世界的总体认识。其核心问题是儿童“怎么看待世界”“怎样和世界打交道”。
1.儿童如何看世界
儿童初临人世,周围的一切都充满神秘色彩,他们带着疑惑的眼光、惊奇的心理打量着五彩缤纷的世界。与成人复杂、老练地看待世界、思考问题相比,儿童则显得如此的单纯、稚嫩。但正是因为儿童对周围一切事物满怀好奇和新鲜感,使得其能看到被成人忽略的世界。如,牛顿坐在树下单纯的思考苹果为什么不是向天上飞的问题,《皇帝新装》里的儿童勇敢地说出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事实,伊恩直率地提出三人自私为什么比一个人自私好的问题……无论是记录在册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儿童言论,人们都不难发现儿童单纯的看待世界,勇敢地直面问题,坦诚直率的与周围事物相处,极像浩然正气的文人墨客。
此外他们还热爱想象、梦幻,经常在游戏里结合现实世界来创造幻想形象。冯契在《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书中提到创造幻想形象是思想幼芽迅速发育的最好土壤。儿童的想象、幻想是儿童思考世界的另一种表征形式。在幻想的世界里儿童可以是诗人,是艺术家,一切生物都可以人格化,具有灵性。在儿童眼里,每天都是新奇的,大到浩瀚的星空、广袤的土地、无边无际的汪洋,小至一颗流星、一只蚂蚁、一滴雨,一次又一次触动儿童的感知和想象。
2.儿童怎样与世界打交道
依据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儿童与世界打交道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即从感知觉到动作、语言;从依赖具体的、可感知的事物到独立的逻辑推理。在整个动态变化过程中,有一条主线贯穿之中——追问。刚会说话的儿童会指物问名。如果经常接触儿童,就会很容易发现,商场里的小朋友指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不停地问“妈妈妈妈,这是什么?那又是什么?”直到告知答案之后才会有片刻的沉默和满足。4岁之后,儿童开始接二连三地追问,并且不再满足于成人给出的回答,每次成人给出的答案又成为儿童新问题的开始,永远不会完结。
案例一:伊恩之问[5]
客人的三个孩子将电视节目转换到他们想看的频道。伊恩没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节目而难过。妈妈安慰说:“三个人快乐比一个人快乐好。”伊恩疑惑地问:“为什么三个人的自私比一个人的自私好呢?”
伊恩之问看似简单,实则是直率地表达出儿童心中疑问,可以从中发现三个关于哲学范畴的主题讨论。
主题一:谁的快乐更有价值
三个人的快乐真的大于一个人的快乐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该由谁来判断?判断快乐的价值标准又是什么呢?
《理想国》第九章中苏格拉底与格劳孔探讨哲学家以永远献身真理的研究为乐,爱胜者以受到敬意为乐,爱利者以获得利益为乐,三种人的不同快乐,究竟哪一种才是最快乐的呢?从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中可以厘清如下思路:对事情的判断需要用经验、知识和推理,哲学家比其他两种人拥有更多的经验、知识和推断能力,故而应该由哲学家来判断出灵魂中用以学习的部分的快乐是最真实的快乐,也是最快乐的生活。
当儿童被告知“三个人快乐比一个快乐要好”时,他们会继续追问“为什么三个人快乐比一个快乐要好?”儿童的追问,其实是希望有人能告诉他们结论产生的过程,即判断标准和判断者是谁的问题。此类哲学思维虽然还尚未被儿童发觉,但已经出现在他们的脑海里。
主题二:民主
妈妈的观点实际是对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社会契约的默认,是民主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伊恩的反问传递出他对现实真理的质疑。在儿童的小脑袋里已经开始思考着什么是民主这一亘古命题。从一般层面来说,民主保证了大多数人的权利。但现实生活中,真理不一定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三个人的快乐”瞬间也会转化为“三个人的自私”。
主题三:伦理道德行为
在《哲学与幼童》书中,马修斯依据《伊恩之问》引导儿童对道德行为进行讨论。客人来家做客一般以客人为主, 尽量满足客人的需求。在讨论中,这群孩子们试图维护公平, 引入了做事的黄金原则。但是公平是相对的,没有绝对公平,最后孩子们理解了只有每个人都遵守黄金原则,才能达到相对公平状态。通过讨论, 儿童体会到生活中的伦理道德,也逐渐帮助儿童养成正确的价值观。
儿童有自己的哲学,儿童看世界单纯、率真、“想入非非”——梦幻、遐想、想象而不拘泥。儿童用追问的方式搭建了通往世界的桥梁。儿童的追问、感悟、积极探索以及思考的过程就是儿童的哲学,就是philosophy by children。马修斯的儿童哲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属于儿童的哲学。他在《哲学与幼童》《与儿童的对话》收录了大量富有哲学韵味的儿童言论,而且还对言论中蕴含的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为儿童哲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
有学者说,儿童看世界的角度,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与伟大的哲学家惊人的相似。其实不然,philosophy by children 告诉世人:伟大哲学家们看世界的角度,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与儿童惊人的相似。儿童是成人之父,儿童哲学是成人哲学的理想型。philosophy by children 意在研究儿童的世界,发现并保护儿童的哲学天性, 使其在脱离童年时代之后,仍旧永葆儿童时期的好学、好问、好思,不论处境如何都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像儿童一样栖息在诗意的土壤里,过“想入非非”的生活。
(二)关于儿童的哲学
儿童哲学第二层意义指向是关于儿童的哲学,即philosophy of children,指成人对儿童的总体认识,也就是教育理论中的儿童观核心问题是成人“怎么看待儿童”“怎样和儿童打交道”。
1.成人怎么看待儿童
告子论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卢梭论出自造物者之手的东西, 都是好的;洛克论儿童心灵像一张白纸;蒙台梭利论儿童是成人之父;苏霍姆林斯基论每个孩子都是一个世界——完全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世界……这是哲学家、教育家笔下的儿童。在一般人眼中, 儿童是不成熟,依附性极强的个体存在。当下流行语“熊孩子”或许可以包罗成人对儿童又爱又“恨”的千万种看法。
成人看待儿童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其一,儿童是一个独立的、具有能动性个体,他们天性善良、正直;其二,儿童是“乳臭未干”的个体,他们天性恶,需要接受严格地训练。人们看待儿童的不同态度也曾引发学术界“儿童能否学哲学”“儿童是否有哲学”等问题争辩。一些人认为儿童太小,认知水平有限,没有能力进行哲学思辨;哲学就应该是成人的专利,儿童不应该学哲学。另一些学者则著书立说反对上述观点。马修斯在《幼童与哲学》文中明确指出,儿童具有好学、好问、好思的特性,他们天生就是哲学家。费鲁琦也在《孩子是个哲学家》文章中论述道:孩子的思考方式与我们不大相同,它们的想法和举动都是突发奇想和无法预测的,随兴所至,走到哪儿算哪儿。[6]因此,philosophy of children 就是要成人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儿童,相信儿童天性善良, 他们敏锐、好奇、好问, 天生就是哲学家。
2.成人怎样与儿童打交道
苏格拉底产婆术, 孔子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夸美纽斯直观教学法都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成人与儿童交往的方式。从儿童哲学层面来说,成人与儿童打交道前提是相信儿童天性善良,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 因此,成人与儿童打交道方式可以多样化,但必须以善待“熊孩子”和善待儿童之问为基本条件。
(1)善待“熊孩子”
“熊孩子”是中性词,指儿童做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说了不可思议的话,使得成人无法招架。该词即展现出孩子们的可爱、机智的一面也表达出成人对调皮捣蛋的孩子们的无可奈何。
案例二:帮妈妈洗手机
一日,琳冉(4 岁)捡起掉在地上的吃苹果就往嘴巴里送,妈妈拿走苹果跟琳冉说:“苹果掉地上脏了,需要用水冲洗干净才能吃。”
又过几日,琳冉发现妈妈手机掉地上,她赶忙将手机捡起来说:“妈妈,你的手机脏了,我帮你洗干净。”话还未说完,就听见手机撞击盆底的咚咚声。
在日常生活中,苹果脏了,用水洗;手帕脏了用水洗。因而琳冉看到手机脏了,不假思索地认为需要用水清洗。由此看来,琳冉小脑袋里可能已经形成由“个别”推论“个别”的简单的推理方法。假设当时母亲能静心去思考“琳冉为什么会水来清洗手机”这一问题,或许除了训斥之外,还会发生一段精彩的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对话。
“熊孩子”的行为是儿童的天性使然,需要成人在尊重儿童的基础上循循善诱。如果成人对“熊孩子”继续保持沉默,或是秉承老古话“一天不打,上房揭瓦”地粗暴打骂责备,那么也许有一天,机智、无拘无束的“熊孩子”突然变为“坏孩子”。这是矮化儿童哲学的悲哀。
(2)善待儿童之问
儿童的哲学天性应该得到成人的保护。善待儿童之问就是要保护儿童早期对富有哲学意问题的好奇心和探究冲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儿童的哲学天性常常受到成人的阻碍。成人要么依仗权威,自以为是,不屑与儿童对话;要么成人本身对哲学问题不感兴趣,对儿童追问置之不理;要么成人苦于能力有限难以回答儿童的提问。不管成人出于何种原因都将导致儿童哲学天性的压制。
成人要想做到善待儿童的哲学天性,可以遵从以下两点:一是面对儿童的提问能回答时,成人要有耐心,试图了解儿童的困惑,用儿童的语言进行解释。就像哲学鸟飞罗,用解释加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自己探索。同时成人在引导过程中防止儿童“好问”的头脑转向功利化,继而埋下精致利己主义者的胚芽。二是面对儿童的提问似懂非懂时,成人可以与儿童一起搜集材料,共同探讨。或是向玻普尔的父亲学习,为儿童寻找一位善于解决儿童问题的智者,给出一个有助益的答案。
philosophy of children 意指成人理应承认儿童能学哲学,儿童天生就是哲学家;应该善待“熊孩子”,善待儿童的提问。成人从儿童主体性出发,尊重儿童,相信儿童,与儿童对话,保护儿童的哲学天性, 保护儿童质疑、批判和追问的哲学品质, 使其在步入成人之后能更高层次再现儿童的天真 ,保留儿童的敏锐而又超于儿童的幼稚,[7]就是关于儿童的哲学,就是philosophy of children。
三、儿童哲学教育目标与特征
儿童哲学教育就是为了儿童的哲学,即philosophy for children(P4C),是指对儿童进行哲学教育的理论、内容和方法。其核心问题是怎样教会儿童思考。
(一)儿童哲学教育三种目标取向
儿童哲学教育研究历史可追溯到美国学者李普曼创办的philosophy for children (p4c), 旨在训练儿童批判性思维。学术界关于“怎样教会儿童思考”核心问题的探讨,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目标取向:思维训练取向、智慧探求取向、文化熏陶取向。思维训练取向是以李普曼儿童哲学教育思想为依据,以思维素质训练为着眼点来构建儿童哲学课。因此,儿童哲学教育不是讲授简单的哲学理论,而是在探究情境中,儿童自由对话、讨论,从而掌握哲学的思考方式。智慧探求取向关注儿童精神世界,儿童自己寻找生活意义。因而,儿童哲学教育并不是要求儿童掌握思维技能,而是帮助儿童学会反省自己及身处的世界。文化熏陶取向是儿童哲学教育本土化过程中必然的结果。一方面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源头,能够与儿童哲学教育有机结合,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丰富的道德思想,且一些道德思想内涵发生变化,而道德思想内涵的变化发展本身就是最佳的哲学探究主题。因而,从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中挖掘素材,推进本土化研究进程是当前国内儿童哲学教育发展的趋势。
三种目标取向既是儿童哲学教育发展的时间轨道,又是儿童哲学教育内涵的变化发展史。从李普曼创设p4c至今,其内涵演变成“为了儿童的哲学”(P4C),具有较强的容纳性和丰富性。与李普曼创办p4c不同,P4C不再单纯强调儿童思想过程的形式推理,开始关注儿童思维过程中实质内容[8]。因此,P4C不再是单一的目标取向,而是多维目标取向,是在融合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注重儿童批判性思维训练的同时关心儿童精神世界的发展。从P4C内涵看,儿童哲学教育包括儿童世界、儿童观、儿童哲学教材、哲学探究方法。
(二)儿童哲学教育特征
儿童哲学教育是在尊重儿童世界和科学儿童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运用适宜的教材内容,采用群体探究方法,教儿童学会思考,因此儿童哲学教育具备四个特征。其一,目标明确。儿童哲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儿童哲学思维能力和发展儿童精神世界,不是学习哲学知识和简单的思维方法训练。其二, 教材丰富。儿童哲学教育教材有儿童哲学绘本、校本儿童哲学教材以及儿童哲学IAPC经典教材。IAPC经典教材就是李普曼和儿童哲学促进会同事共同编撰了一套从幼儿园至高中阶段的系列儿童哲学教材,IAPC教材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哲学理念,分为儿童用书和教师用书。其三,主题鲜明。儿童哲学课程的对话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儿童通过阅读哲学小说提出问题,大家从所提问题中选择几个最感兴趣的作为主题。其四,参与讨论。探究共同体讨论是儿童哲学课的核心。整个讨论过程中,师生双方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在教师帮助下,儿童通过“就事论事”的讨论和对话学会哲学式思维方式。
儿童哲学不等于儿童哲学教育,儿童哲学教育不仅仅是儿童哲学。儿童哲学是成人对童真、童趣、童心的再次修行。儿童哲学教育首要意义是给予我们正确方法指导,使我们懂得运用特定的教材,明确主题,教儿童学会思考。儿童哲学是儿童哲学教育的理论基础,儿童哲学教育是对“儿童世界”“儿童观”认同的基础上对儿童哲学理念的践行,是集理论、内容、方法为一体的广义概念。儿童哲学与儿童哲学教育是理念与实践的统一。相信厘清儿童哲学与儿童哲学教育关系,把准二者内涵后,我国儿童哲学教育将会迎来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