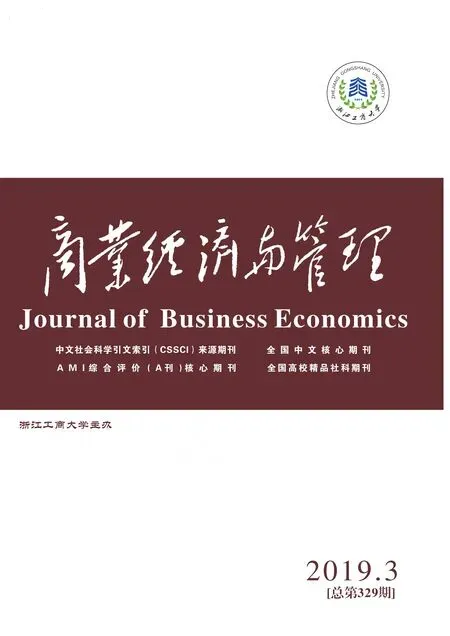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许永斌,鲍树琛
(浙江工商大学 财务与会计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 引 言
企业风险承担是企业投融资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反映了企业实现更高盈利过程中愿意付出成本的倾向(Lumpkin和Dess,1996)[1]。虽然承担过高的风险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糟糕的财务决策,但是没有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就没有回报(Stulz和Rene,2015)[2],因此风险承担是企业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不少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阶段已经或正在遇到风险承担方面的难题,海翔药业少东家四年败掉四十年家业的故事对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最大的震撼莫过于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抉择产生影响,进而引发人们对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阶段如何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思考。
Segal等(2015)将不确定性分为好的不确定性与坏的不确定性,好的不确定性能给企业带来发展机遇,坏的不确定性会给企业带来严重的损失[3]。现有的研究表明,当经济不确定性提高时,企业的投资水平以及银行借款水平都会显著下降(饶品贵等,2017;蒋腾等,2018)[4-5]。同时也有文献基于风险追求效应角度指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显著提升非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刘志远等,2017)[6]。但是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产生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决策的文献仍然十分匮乏。
从深层机理角度上分析,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不确定性的产生是由于老一辈即将退出组织,企业家能力、声誉、权威和关系等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特殊资产难以转移到继任者身上;而继任者欠缺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同时面临家族内部控制权争夺、继任者与高层员工之间的冲突以及重构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等传承时期特有的困境。代际传承中的不确定性会影响继任者的风险偏好,而继任者对风险的态度会决定其在企业风险承担方面的决策。那么家族企业在进入代际传承时期时,继任者如何选择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一代家族成员或职业经理人将企业治理层或管理层职位移交给家族子辈继任者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何差异?企业创始人参与程度大小又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目前鲜有文献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探讨,这也为本文留下了研究空间。本文选取2004年至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讨论分析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
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为代际传承时期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是一项能够影响中国民营经济基业长青且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研究话题,由于样本观测值偏少的限制,多数学者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而较少通过经验研究方法提供证据。本文运用手工搜集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数据,首次探讨了代际传承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是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文献的有益补充。第二,现有关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企业财务行为影响的文献尚未对离任者与继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创始人的参与程度进行细致探讨。实质上,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高低受到更为微观层面上的幕后人关系的影响,故不同的接班方式可能会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通过手工搜集高管关系背景数据,对此类文献进行拓展和补充。第三,本文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视角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主题的文献。已有的文献多从宏观环境、公司特征以及管理者个体特征等方面考察对企业风险承担和财务行为的影响。本文借助代际传承这一角度分析在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实施期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化,为研究企业风险承担话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中国人行为最核心的概念是“家”。汉语中提到家的概念,无外乎包含人和财产两层意义。类似地,在谈到代际传承的含义时,自然就浮现两种关系:其一,传承人与继承人的关系;其二,继承财产关系。换言之,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实施期的终点为控制权(财产)完全移交给家族二代继任者,但始点按继任者来源的不同可分为两类,即将经营权移交给职业经理人或家族二代。与发达国家家族企业倾向于选择职业经理人的传承方式不同,我国家族企业普遍从家族后代中选择继任者,存在“代际锁定”现象(胡旭阳和吴一平,2017)[7]。此外,在本文筛选的家族企业样本中,作者未发现老一辈企业主将控制权完全移交给家族二代继任者的同时,将经营权移交给职业经理人的接班案例,这亦验证了前述观点,因此本文将家族二代继任者接手企业关键领导岗位视为企业开始进入代际传承实施期最为关键的事件。基于我国的制度情境,造成这种代际锁定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从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看,由亲缘关系产生的信任和忠诚度降低了企业代理成本,家族荣辱感更会使得家族成员表现出“利他主义”行为——以家族整体利益为核心而适时舍弃个人私利;从正式制度层面上看,我国私有产权并不能得到法律制度的充分保护,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早期在兰州黄河、国美电器等企业中发生的经理人败德行为使得众多家族企业创始人不敢安心放权给外人(王明琳等,2014;李新春,2003)[8-9]。
家族企业进入代际传承实施期可能受到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创始人的能力、声誉、权威以及其他特殊资产难以转让给下一代,具有某种黏性特征。黏性来源于复杂的过程而招致的额外成本,这一过程包含特殊资产的自觉重建、传播与整合以及在企业形成新的惯例。因此这种黏性使得这类特殊资产处于惰性状态——一旦获得,就难以被其他人触及或修正,并且在转移过程中就容易出现使用价值的损耗(Agarwal等,2002)[10]。第二,代际传承实施期存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由于代际传承通常需要集体行动,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增进自己的利益会寻找最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故而集体行为会产生搭便车、败德危险等问题。家族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经营权与控制权的争夺,使得家族成员忙于企业内部政治运动,降低了经营资源配置活动的效率。继任者掌握经营权后,也可能遭到企业高管利益集团的制衡,出现组织功能性紊乱(贺小刚等,2011)[11]。第三,继任者需要重构与供应商、销售商、银行、政府等外部相关者的关系网络。在弱法律制度的市场中,保持距离型的“规则”并没有得到发展,而是在家族、社会或政治制裁的强制下,选择关系型的“惯例”主导市场交易作为替代性安排(Fan等,2012)[12]。继任者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努力与资源重新赢得外部相关者的信任,甚至采取有损商业道德的寻租方式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并获取资源。第四,继任者欠缺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家族后代作为继任者,即使家族候选人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成为公司领导者。当创始人选择一个能力不足的家族继任者来管理公司时,可能会损害公司声誉与价值,于是出现所谓的逆向选择问题(Burkart等,2010)[13]。
由于代际传承时期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继任者如何选择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根据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家族企业主要的关注点是他们的社会情感财富的损失。家族对于企业具有特定的社会情感禀赋。社会情感财富对家族的价值是内在的,而且家族在心理层面上对企业具有认同感与归属感。家族的命运通常与家族企业绑定在一起,若代际传承失败,则可能导致家族与企业灾难性的社会情感损失与财务损失。传承中的不确定性会影响继任者对风险偏好的态度,而继任者对风险偏好的态度会决定其在企业风险承担方面的决策。为了避免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流失,继任者可能会提高损失预期,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厌恶性,进而使得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低于最优状态,即“风险厌恶效应”。
从风险厌恶效应的角度上看,在代际传承实施期,家族企业可能倾向于减少长期融资和长期投资,进而抑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首先,代际传承的不确定性可能提高了企业长期融资的成本。我国家族企业进入代际传承实施期后,普遍出现业绩下滑的现象(Bennedsen等,2015)[14]。在这种情境下,签订长期债务契约相当于将额外的风险负担转移给债权人,债权人就会倾向于预期不看好企业未来业绩,从而要求提高长期债务资本成本以确保资金安全。此外,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中,由于缺乏发达的第三方实施机制,民营企业融资风险都很大,商业判断经常需要利用一些不易标准化和量化的信息,因此融资契约的签订与执行不得不利用个人声誉效应、政商关系等长期信任关系(青木昌彦,2011)[15]。代际传承使得老一辈高管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起来的联系逐渐被打破,债权人不能迅速掌握继任者个人才能和素质的意会知识,便会使用严格的审查程序对企业执行信贷评估,从而加大了长期负债融资的难度。其次,代际传承的不确定性可能减少了企业长期投资行为。风险厌恶的家族继任者可能会主动规避代际传承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在制定战略决策时变得更为保守,因为他们可能更关心保留社会情感财富而不是企业目标。自古以来,中国人非常重视家族成就,视家族之成功为个人之荣耀,彰显“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的家道维系主义。若企业经营失败,则家族继任者可能会背负“败家子”的恶名。同时,家族继任者可能是因“堑壕效应”和“裙带关系”而上位,他们的禀赋(包括职业声誉、工作经验、认知水平等)更低。由于长期投资项目回报不确定且需要较长的等待时间,他们不太可能进行长期投资,而更可能希望通过短期项目快速地证明能力,稳固职位,从而使得企业偏向更简单、更短视的投资。此外,当一个长期投资契约形成时,由于决策者的变更,新的缔约双方可能对彼此的可靠性缺乏充分的了解,任何一方的违约都可能付出高额的交易成本,所以损失厌恶型的家族继任者在进入代际传承实施期后降低长期投资,而可能选择可以减低执行契约条件成本的短期投资,这样更有利于契约再谈判时资源的再配置(Cheung,1969)[16]。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家族企业进入代际传承实施期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降低。
进一步地,本文探讨接班方式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对于接班方式本文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探讨:第一,家族二代继任者开始担任企业关键领导岗位时,必然会使得原先在位的高管调离,故本文从离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为家族成员角度将接班方式分为两个类别,即“家族—家族”类别(家族创始人传位于家族二代继任者),以及“职业—家族”类别(职业经理人归位于家族二代继任者)。此外,由于本文没有发现创始人将控制权完全移交给家族二代继任者,并且将经营权移交给职业经理人的接班案例,所以本文对这种接班情况不做分析。第二,本文又从创始人的参与程度角度将接班方式分为两个类别,即创始人强参与类别(创始人保留控制权,且与继任者共同经营)与创始人弱参与类别(创始人无经营权)。
首先,考察离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为家族成员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Macdonald和Koh(2003)的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的交易是由简单的利他主义所驱动的。家族成员之间财富和收入的转移并不平等[17]。父母根据子女的需要分配财富,而不是根据子女的能力[18]。这种利他主义理论可以应用于家族企业,在位家族成员可以为后辈继任者提供更多的利益,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并且他们之间利益目标是相一致的。尤其在代际传承实施期,老一辈家族成员更有动机帮助继任者识别并利用风险中蕴含的商业机遇,获取利润和创造价值,进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主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主难以对职业经理人实行彻底的监控,同时职业经理人由于业绩考核压力而容易出现追求现期收入、厌恶长期激励的短视观念。职业经理人作为圈外人可能无法认同家族企业精神资产,甚至可能会存在“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顾虑,并不会像家族企业创始人一样在离任时面临情感或经济上的负面压力。诚然,职业经理人将职位传给家族继任者时,可能出于情感依附而帮助继任者,但这种利他主义程度会小于家族内部传承。因此职业经理人在离任时可能没有太多的动机去帮助企业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与“家族—家族”类别的接班方式相比,在“职业—家族”类别的接班方式下,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负效应更显著。
其次,考察创始人的参与程度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企业是共同的中心缔约人签订的多边契约的集合,而家族企业中心缔约人身份被权威化和家族化,即企业主(Alchian和Demsetz,1972)[19]。家族企业是一种科层制组织,居于最高地位的企业主决定着一切行动,公司治理形式为权威治理。权威治理的供给曲线取决于企业主支付多大的成本来维持权威治理。权威治理对企业主的价值等于从权威治理的收入减去维持权威治理的成本。代际传承会极大地改变创始人维持权威治理的成本,那么权威治理的供给弹性就会降低,在家族企业中的具体表现为原先拥有绝对权威的企业主参与程度逐渐衰减,直至完全退出企业。而继任者在代际传承实施期,权威合法性尚未完全确立。他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努力以及资源来改变原先的惯例,同时新规则执行的基础非常薄弱,故权威治理的供给曲线仍然因成本过高而较弱,公司治理形式由权威治理弱化为规则治理。接班方式不同,其所遇到的交易成本也不同,不确定性也就不同。在创始人与继任者共同经营企业的接班方式下,公司治理形式仍然表现为权威治理。保留部分经营权的创始人作为职业导师仍可以发挥社会资本优势,为继任者平稳交接提供“职业庇护”(包括提供有利的曝光机会、承担挑战性工作以及提供工作建议等),这可以减弱代际传承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在创始人无经营权,甚至交出实际控制权的接班方式下,公司治理形式表现为规则治理。由于创始人的参与程度较弱,当继任者重新构建行为规范和意识形态时,新规则总会偏离“传统”,这往往会面临“少主难服众”的变革阻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可能相对较低。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创始人弱参与下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低于创始人强参与下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对于如何界定家族企业仍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他往往涉及经营权、所有权以及控制权三个维度。本文借鉴了黄俊和张天舒(2011)的研究[20],对家族企业的界定标准如下:首先,本文找出截至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家族的企业,且最终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不低于10%;其次,本文对公司历史进行追溯,剔除最终实际控制人因并购重组等外生因素发生变更的公司;最后,本文通过查询年报、招股说明书、董事会决议公告以及百度搜索引擎等方式确定董事长、总经理与企业创始人之间的关系。
本文选取2004-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之所以以2004年为研究样本的起点,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从2004年开始在年报中详细披露实际控制人信息。同时考虑本文是以每三年为一个观测期(t-1年至t+1年),采用滚动方式计算企业风险承担Risk,所以按此方法计算Risk时采用的样本期间为2003-2017年。在剔除ST公司、金融行业公司、变量数据缺失观测值、异常值后,最终得到65家进入代际传承期的家族企业,总共523个公司-年度观测值。其中,“家族-家族”类别的公司为47家,“职业-家族”类别的公司为18家。由于创始人参与企业经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不同年份的创始人参与程度可能会有所变化(即同一家公司可能在不同年份会先出现创始人强参与的情况,后出现创始人弱参与的情况),创始人强参与类别的公司为43家,创始人弱参与类别的公司为33家。为了消除离群值可能对结论带来的不利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缩尾处理(Winsorize)。
(二)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1,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1)。
Riski,t=β0+β1Succi,t+β2Sizei,t+β3Levi,t+β4Growthi,t+β5Firmagei,t+
β6Lossi,t+β7Topi,t+∑Year+∑Industry+εi,t
(1)
因变量Risk表示为企业风险承担。借鉴John等(2008)[21]以及Faccio等(2016)[22]的度量方法,本文采用盈余回报率波动性指标计算企业风险承担。盈余回报率波动性越大,表明企业从事高风险项目越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强。具体而言,本文采用两个指标度量Risk:(1)Risk1是以每三年作为一个观测期(t-1年至t+1年),[注]本文也采用另外一种观测期(t年至t+2年)计算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重新对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并没有改变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每个公司经调整后的ROA(息税前利润/期末总资产)的标准差,其中经调整后的ROA等于每家公司的ROA分行业分年度减去同行业同年度ROA均值进行调整;(2)Risk2是以每三年作为一个观测期(t-1年至t+1年),每个公司经调整后的ROA(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期末总资产)的标准差。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自变量Succ表示家族企业是否进入代际传承实施期,若观测值年度在代际传承始点后,则赋值为1,反之为0。家族继任者接手企业关键领导岗位是进入代际传承实施期最为关键的事件,换言之,本文将创始人的子辈(儿子、女儿和女婿)首次担任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视为代际传承的重要标志。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可能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其他因素。Size为公司规模,等于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ev为财务杠杆,等于公司年末总负债除以年末总资产。Growth为公司成长性,等于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率。Firmage为公司上市年限,等于观测年份减去公司上市年份加上1后取自然对数。Loss为本年度是否存在亏损,若本年度公司净利润小于0,则取1,反之为0。Top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为了检验假设2,本文将样本按离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为家族成员分为两组,分别代入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家族-家族”类别组表示离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家族成员,“职业-家族”类别组表示离任者为职业经理人。
为了检验假设3,本文将模型(1)中变量Succ细分为变量Power1和变量Power2。变量Power1表示创始人强参与类别,若创始人为实际控制人且担任董事长,与继任者共同经营,则Power1赋值为1,否则为0;变量Power2表示创始人弱参与类别,若创始人无经营权,不再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则Power2赋值为1,否则为0。其他控制变量不变,具体的回归模型(2)如下:
Riski,t=β0+β1Power1i,t+β2Power2i,t+β2Sizei,t+β3Levi,t+β4Growthi,t+β5Firmagei,t+
β6Lossi,t+β7Topi,t+∑Year+∑Industry+εi,t
(2)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1 描述性统计
(一)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1报告了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Risk1和Risk2的均值均大于中位数,呈右偏分布。Succ的均值为0.511,说明代际传承始点后的观测值占该样本总观测值的51.1%。表2列示了变量Risk的均值和中位数差异检验结果。本文比较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始点前后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均值和中位数,结果表明无论是考察均值还是中位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代际传承始点后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小于代际传承始点前。

表2 变量Risk的均值和中位数差异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以及10%水平显著。

表3 假设1检验结果
注:***、**、*分别代表在1%、5%以及10%水平显著。
(二) 假设1的实证检验
表3列示了假设1的实证检验结果。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的结果显示,各变量VIF值远小于10,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本文在表外进行了WHITE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0,拒接同方差的原假设,即存在异方差问题。为了降低异方差对回归系数的影响,本文在计算标准误时,采用稳健标准误的方法。回归结果显示,在第一栏中Succ的回归系数为-0.014,在10%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同样地,在第二栏中Succ的回归系数为-0.015,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从经济意义上分析,表3第一栏和第二栏的结果表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始点后比代际传承始点前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依次低0.014和0.015个单位,这大约为Risk1均值的17.72%(0.014/0.079),以及为Risk2均值的18.75%(0.015/0.080)。因此家族企业进入代际传承实施期后会使得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下降,这不仅在统计意义上显著,而且在经济意义上也非常显著,以上检验结果验证了假设1。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得假设1的检验结果更为可靠,本文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稳健性检验(附于篇幅,回归结果不再显示)。
首先,改变因变量Risk的度量。本文采用改变计算企业风险承担的窗口期,以每五年(t-2年至t+2年)作为一个观测期,重新计算两类Risk。检验结果仍然证实,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其次,本文所选择的样本仅检验代际传承家族企业在进入代际传承实施期前后的风险承担改变,并不能控制企业外部因素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由此本文采用DID-PSM方法解决研究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首先,根据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以Size、Lev、Year和Industry四个维度按一对一匹配方式找出配对的非代际传承家族企业样本。代际传承家族企业与非代际传承家族企业构成了研究的“实验组”与“参照组”,生成虚拟变量Post。Post=1表示代际传承家族企业;Post=0表示非代际传承家族企业。由于交互项Succ×Post和解释变量Succ的信息完全同质,在引入DID模型后被视为同一个变量,因此模型中不需要设置交互项Succ×Post,而仅需关注变量Succ的系数及显著性。结果显示,变量Succ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前述结论仍然成立。
最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时机选择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偏误,导致研究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两阶段处理效应模型对样本进行修正。在第一阶段,以Succ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工具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如创始人的年龄(Dirage)、创始人的教育程度(Diredu)、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比例(Ucsvr)、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比例(Ucscr)以及实际控制人是否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职务(Ucpd),构造Probit回归模型。第二阶段,构造自选择系数λ作为第二阶段回归的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自选择系数λ均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存在自选择问题,使用两阶段处理效应来控制偏误是必要的。在控制自选择问题后,Succ仍与Risk呈显著负相关,与前述回归结果一致,说明结果是稳健的。
(四) 假设2的实证检验

表4 假设2检验结果
注:***、**、*分别代表在1%、5%以及10%水平显著。
表4报告了在“家族-家族”和“职业-家族”两种不同接班方式下的检验结果。[注]本文也采用交互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并没有改变。回归结果显示,不管是用Risk1还是Risk2,“职业-家族”类别下的Succ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而“家族-家族”类别下的Succ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异于零。这说明与家族成员传位给家族成员的接班方式相比,在职业经理人归位于家族成员的接班方式下,代际传承可以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假设2得到了验证。
(五) 假设3的实证检验
表5列示了假设3的检验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在第一栏中,Power1的回归系数为-0.012,但未能显著异于零,而Power2的回归系数为-0.024,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在第二栏中,Power1的回归系数为-0.013,在10%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而Power2的回归系数为-0.024,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可见无论是用Risk1还是用Risk2,Power2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大小与显著性水平均大于Power1,那么相对于创始人强参与的接班方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创始人弱参与的接班方式下更低。该结果支持了假设3的预期。
五、 进一步研究

表5 假设3检验结果
注:***、**、*分别代表在1%、5%以及10%水平显著。
(一) 考虑继任者的背景特征对代际传承的调节作用
根据高阶理论,继任者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等背景特征差异反映了个体不同的认知模式,造成个体不同的风险偏好,而继任者的风险偏好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例如,继任者在接管企业时,年龄越大,在企业中的经营管理经验、社会资本等可能会越丰富,那么会更有自信地表现出风险追求态度,进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女性继任者相对男性更为保守,领导的企业可能表现出较低的风险承担水平(Faccio等,2016)[22]。继任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学习能力与认知能力越强,对抗不确定性环境的能力也会越强,这为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提供了个人能力方面的保障。
本文引入继任者年龄(Age)、性别(Female)和受教育程度(Edu)三种背景特征变量以及他们分别与变量Succ的交互项。Age表示继任者在接班当年,其年龄是否超越在本文样本中平均接班年龄34岁的公司样本。若继任者在大于等于34岁时,才开始担任公司董事长或者总经理,那么这类公司的变量Age赋值为1,否则为0。Female表示继任者是否为女性的公司样本。若继任者为女性,那么这类公司的变量Female赋值为1,否则为0。Edu表示继任者是否为高学历的公司样本。若继任者的学历为硕士及以上,那么这类公司的变量Edu赋值为1,否则为0。表6给出了继任者的背景特征对代际传承的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从表6中可以发现,交互项Succ×Age的系数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继任者在接班当年,其年龄越大,越能缓解代际传承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效应。交互项Succ×Female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女性继任者在代际传承时会表现出更低风险偏好,进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Succ×Edu的系数并未显著异于零,说明在本文的样本中,继任者尚未展现出受教育程度所带来的风险管控能力。

表6 继任者的背景特征对代际传承的调节作用
注:***、**、*分别代表在1%、5%以及10%水平显著。
(二) 代际传承与企业投融资行为

表7 代际传承与企业投融资行为的检验结果
注:***、**、*分别代表在1%、5%以及10%水平显著。
投资和融资风险是企业承担的较为常见的风险。家族企业步入代际传承实施期,企业承担投融资风险水平是否也随之下降?本文将企业的投融资情况按周期长短分别分为长期投资(Linv)与短期投资(Sinv),以及长期负债(Llev)与短期负债(Slev)。长期投资(Linv)等于(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期末总资产;短期投资(Sinv)等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总资产(2007年之前,使用短期投资/期末总资产)。长期负债(Llev)等于长期负债/期末总负债,短期负债(Slev)等于短期负债/期末总负债。从表7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Succ的回归系数依次为-0.008、-0.001、-0.013和0.025,显著性水平依次为10%、不显著、5%和10%。这表明家族企业在进入代际传承实施期后,倾向于降低长期投资与长期负债,增加短期负债,但对于短期投资并没有显著影响。换言之,代际传承使得企业承担长期投融资风险能力均有所下降。
(三) 代际传承、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会计绩效
前文研究表明,代际传承会引起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下降。那么代际传承是否会通过企业风险承担引起企业会计绩效变化?根据“高风险-高收益”的财务学原理,企业风险承担应与企业会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代际传承会增加经营不确定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下降会减少企业盈利机会,并最终给企业会计绩效带来负面影响。针对企业风险承担是否为代际传承影响企业会计绩效的一个中间路径这一问题,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三者关系进行检验。
表8报告了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变量Succ和Risk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第2列、第3列、第5列和第6列Sobel检验的Z统计值(表外)分别为-2.241、-2.271、-2.167和-2.182,均在5%水平显著,说明企业风险承担可能是代际传承影响企业会计绩效的部分中介变量。第1列和第4列中,变量Succ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代际传承引起了企业会计绩效下降。在引入企业风险承担这个变量后,变量Succ的系数仍然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代际传承通过企业风险承担这项路径引起了企业会计绩效下降。

表8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注:***、**、*分别代表在1%、5%以及10%水平显著。
六、 结论、启示与展望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风险承担问题是一个新的研究主题。本文尝试建立一个风险分析框架,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与利他主义理论,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如何随着代际传承阶段变化做出检验,从而更好地理解代际传承因素对我国家族企业风险承担决策的影响。以2004-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结果发现:家族企业进入代际传承实施期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降低,验证了风险厌恶效应。由于父辈向子女转移财富的行为带有利他主义精神,与“家族-家族”类别的接班方式相比,在“职业-家族”类别的接班方式下,代际传承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负效应更明显;创始人弱参与下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低于创始人强参与下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代际传承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还受到继任者年龄与性别特征的影响;代际传承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长期投资与长期负债降低;代际传承通过企业风险承担这项路径引起企业会计绩效下降。
每家企业都会经历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直到最后的衰败。我国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时期屡屡遭遇“交托之痛”。代际传承不应该成为家族企业陷入衰败的黑手,相反应该是成为延续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的推手。但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始点后,往往出现风险承担水平降低,在统计意义上暴露出企业传承败象的苗头,这也验证了《2016中国家族企业健康指数报告》指出的我国家族企业普遍缺乏有效的接班计划的现象[23]。由此本文得到以下三点启示:第一,代际传承是家族企业自我更新换代的必经之路,接班规划的制定有利于增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减少不利的动荡。当前我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代际传承,有计划地对传承时期的制度及财产分配进行合理的安排,这将有助于减少产权转移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并适当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推动家族企业高质量的发展。第二,由于家族企业在中国的合法性地位依然不稳定,在“严监管”“防风险”的政策高压期,企业财务政策应定位长期以适当增加风险承担水平。本文的结论进一步指出,代际传承时期,家族企业承担长期投融资风险水平均有所下降。因此企业应在传承各阶段对财务政策执行适当的调整,以应对外部大环境的变化。第三,风险承担是影响企业会计绩效的重要路径,企业主在代际传承过程中应深刻理解企业风险承担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培养继任者的企业家精神,调动其勇于承担风险的积极性,并且有效识别合理承担风险的投融资项目,最终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
最后,本文的未来研究展望有以下两点:本文只探讨了代际传承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并未考虑继任者社会资本以及企业战略转型规划的影响。一方面,随着继任者羽翼逐渐丰满,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也应逐渐提升。另一方面,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实施期的风险承担水平能够得到提升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应对不确定性环境时企业实施的战略转型规划能够持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