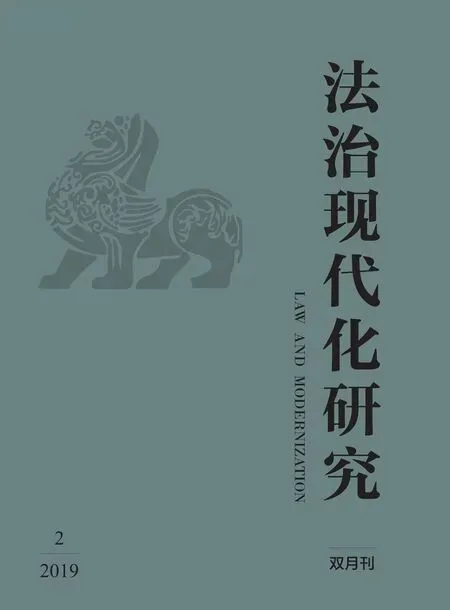论民法精神的行为性与生态性
王利民
民法精神是法治精神的具象形态,是制度化、行为化、秩序化和生态化的民本社会精神;民法精神是以民为本的精神,是民本社会的法治文化精神;以民为本的民法精神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在诉求与民本模式。
考察民法精神的本质,应以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发展需要为根据,从民法的规范属性和社会生态秩序的文化价值方面进行总体把握。民法精神是民法规范的以民为本的社会精神,反映市场经济与民本社会的基本秩序价值,是与社会主义宪法精神相统一的民法规范意识,是贯穿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民法思想原则。①民法是权利法,民法精神作为民法的精神,是一种权利精神。权利是以一定的社会规范形式赋予人们的为了实现一定的人身与财产利益目的而可为一定支配或者请求行为的行为自由。权利是人类文明社会所具有的一种实质性要素,它既是人的利益实现的条件,也是人的基本价值需求,并代表了人类一种基本的社会秩序体系,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不可少的秩序形态与行为动力。“在法律和法学文献中没有一个词比权利更加含糊不清。在最普通的意义上,它意指公民生活中的一种合理的预期。”它有五种含义:一是指利益;二是为了赋予利益以法律效力而要求另一人或者所有其他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一种被认可的主张;三是一种创设、剥夺或改变第三种意义上的权利的能力和因此而来的一种创设或改变义务的能力,即最为恰当的词是“权力”;四是指不受干涉的自然行为能力的某种一般的或者特别的条件,这种条件是法律不干涉的,即法律通过留给某人以其自然能力的自由行使来保护其利益的情况,它们最好被称为自由和特权;五是用来表示与正义相一致的事物,或者确认道德权利并使道德权利发生效力的事物的性质。参见[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4卷),王保民、王玉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4页。民法精神作为权利精神,也就是一种权利本位的精神。权利本位一方面是指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中,个人权利是根本与决定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是指在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中,权利是决定性的和起主导作用的一面。“权利本位”概括地表达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的实质条件与根本特征:(1)每个人都是权利主体,都具有平等的人格。没有人因为性别、种族、语言、宗教信仰等特殊情况而被剥夺权利主体的资格,或在基本权利的分配上受歧视;(2)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中,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的实现;权利是第一性的因素,义务是第二性的因素,权利是义务存在的依据和意义;(3)权利主体在行使权利时,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这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他人的权利给予应有的承认、尊重和保护;(4)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或强制的情况下,可以(应当)作出权利推定,即推定公民有权利去作为或不作为。民法精神作为以民为本和反映人的主体地位的行为与生态精神,是以市民社会为根据的基础法治精神。
一、民法精神的行为性
民法精神既是代表民法并由民法形式表现的制度精神,也是民法所调整的民事主体的行为精神。民法精神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条件的规范性与秩序性,根本在于它作为主体和实践的行为规范所具有和实在的行为秩序性。没有民法精神的行为性,也就没有民法精神的社会生态性,更没有民法精神作为民本模式的法治条件性。民法精神作为市民社会的生态秩序精神,被以市民社会的法律形式——民法所抽象概括和集中表现出来,并通过民法形式的实在规范及其具有的国家强制力进一步转化为市民社会的行为条件与秩序,即成为具有法治文化与文明价值的社会构造形态。
(一)民法精神的行为主体性
民法精神的行为性,首先是民法精神的行为主体性,即民法精神是一定行为主体的精神。民法精神的行为主体,也就是民事主体,即市民社会的主体,其根本上是自然人主体。②虽然民事主体在自然人之外还有所谓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但是,“法人是一种社会秩序的人格设计,是被确认为法律人格的一种社会秩序条件。这一社会秩序,包括一定的组织秩序、财产秩序和行为秩序等。当这些秩序符合一个人格化的特定目标时,这个秩序条件就被法律以一定人格的形式所承认,这个被法律所承认的人格秩序就是法人”;“法人作为一定社会秩序的人格化并作为权利主体存在,并不是在自然人之外真正存在一种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人,或者说并不是自然人彻底摆脱了责任的负担,它只不过是自然人权利义务的转化形式,是自然人间接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中介秩序”。参见王利民:《人的私法地位》,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6-67页。法人如此,非法人组织也是如此。民法精神既是自然人的内在本质与生态需求,也是自然人的规范条件与行为实践。民法精神的行为主体,作为市民社会的自然人主体,代表了民法精神主体的普遍性和根本性。民法精神的主体是普遍的民事主体,而普遍的民事主体所具有的民法精神,也就是普遍的社会精神,即对社会关系与秩序具有决定性的精神,也就必然成为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所不可缺少的普遍的和基础的社会精神。民法精神的主体作为自然人主体,不仅是普遍的主体,而且是根本的主体,是作为社会目的与价值的主体,一切社会构造都必然遵循和追求自然人的人性目的和价值,以自然人的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规定性为根据,形成公正合理的社会行为秩序。
可见,民法精神根本是人的社会行为精神,人即市民社会的主体,是民法精神的行为主体。人的民法精神的行为主体性,构成了人的基本社会人格属性。人是自然的产物,也具有社会的人格属性,人以社会的方式生活,构成社会的行为主体,遵守社会的行为秩序,需要社会的人格实现。③西方中世纪后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就是“突破了传统的神权统治,人的观念首先被发现,人文主义被社会普遍接受,人格尊严和自由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与人格、人格权的概念逐步形成”。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人以自己的生态方式自然地构成了社会,又以社会主体的地位与身份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化条件和要求,民法精神就是代表这一条件和要求的行为秩序。民法精神作为主体性的内在规范,不仅代表了主体的外在行为,而且代表了主体的目的与价值。④“一个合理的人可社会化为一个社团的规范和惯例,因而他的目的符合公共的价值观,而他对这些目的的追求符合集体的规范。”参见[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也就是说,人以民法精神的行为主体构成了普遍的社会行为秩序,从而不仅是法治和法治文化的主体,而且是法治和法治文化的根本缔造者。
民法精神的行为主体,也就是法律行为的主体,其行为性根本是个人所追求的一种社会利益性,即以民法所调整和保护的权利义务关系所表现的个人利益条件。⑤“人的保护,维护其个性及人格关系,为民法的首要任务。”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法律行为主体也就是权利义务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行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这不仅为法律行为的主体及其行为的性质进行了定位,而且也对法律行为的主体及其行为条件提出了要求。⑥自从《德国民法典》引入“法律行为”概念以来,虽然人们对这一制度设计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法律行为”的概念已经成为民法和民法思维所不可缺少的结构性支点,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每个人都通过法律行为的手段,来构成他同其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作为能够引起一定私法结果的主体行为,是主体有目的实施并能够达到主体目的的行为,其目的性结果的实现,一方面是因为法律承认这样的目的性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主体基于自己的目的追求这一结果的发生,而后者作为主体的精神和意志条件,对法律行为的发生及其引起的目的与秩序效果具有决定的意义。“法律行为之所以产生法律后果,不仅是因为法律制度为法律行为规定了这样的后果,首要的原因还在于从事法律行为的人正是想通过这种行为而引起这种法律后果。”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6页。这一条件和要求,就是民法精神的根本内涵,也就是民法精神的目的及其伦理问题。民法精神的行为主体,以具有民法精神和遵守民法精神的条件和要求为本质,在民法精神之外,既无民法精神的合理社会行为,也非民法精神的正当行为主体。因此,基于民法精神的市民社会主体的普遍性,人人都是民法精神的行为主体,人人都应当具有与法律行为要求相适应的民法精神,人人都应当以民法精神的行为秩序构造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民本模式的根基所在。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法治和法治文化只有生根于民法精神的行为主体,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和法治文化的生态秩序构造。
(二)民法精神的行为意志性
民法精神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与秩序精神,是一种社会行为意志,即民事主体实施一定法律行为的主观意志。⑦意志是指“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往往由语言和行为表现出来”。参见《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意志”词条,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618页。人作为主体不过是意志主体,而民法精神也不过是作为主体的意志形式而已。⑧“人的全部本质就是意志,人自己就只是这意志所显现的现象。”参见[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96页。民法精神只有在行为意志的普遍意义上,才构成社会行为规范与生态秩序。换言之,民法精神的行为意志,是一种规范意识,是一种社会秩序共识。它一方面是意志性的;另一方面是规范与秩序性的,并且是一种自然与必然趋同的社会行为体系。人类的行为及其规范与秩序无论反映和表现为何种形式,最终都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都是一种意志形态,人不仅决定自己意志的表现形式,而且决定自己意志形式的实行效果。因此,无论是意志还是表现意志的形式,本身都具有意志的属性并反映意志的本质。⑨人是有灵之物,行为和行为规范必然出于人的意志。“如果不谈谈所谓自由意志、人的责任、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讨论道德和法的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2-153页。“原来意志作为真正的自在之物,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独立的东西,所以在自我意识中必然也有一种原始性的,独断独行之感随伴着这里固已被决定的那些意志活动。”参见前引⑧,叔本华书,第398页。“人类行为由意志引起,但一个人的意志行为并不总是前后一贯的,不同的人意志倾向也各不相同。而人已获得秩序并体面行事,所以必然存在着意志可以遵守的规则。”⑩[德]塞缪尔·普芬道夫:《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鞠成伟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4页。只要是意志的东西,就必然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差别性,所以构成行为条件的意志是必须自主接受规范条件的,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规范,包括民法的或者法律的规范,与其说规范的对象是人的行为,不如说是人的意志,意志的规范性是根本的秩序形态。⑪“意志是给自身立法的,甚或它自身就是法则。”参见[美]亨利·E.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人们以自己的意志创造一种行为规范,并要求自己的意志接受这一行为规范的条件和要求,从而使这一规范成为自己的意志存在。因此,如果人们的行为意志接受一种普遍的行为条件即规范的要求,那么这种行为意志就构成一种规范与秩序的意志——民法精神就是这样的意志。民法精神不仅是意志的,而且是规范与秩序的,当民法精神构成人的行为意志,就不仅会产生代表这一意志的普遍的民法形式,而且必然形成普遍的民法行为秩序。所以,真正的法治和法治文化条件不是法律的规范条件,而是人们的行为意志条件,也就是人们的规范与秩序的思想与信仰条件。
因此,民法的规范构造,只是立法者的法律形式构造,只有民法精神的行为构造,才是现实的法治和法治文化构造。民法精神以其形式规范与行为意志的统一与结合,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和法治文化的生态体系。可见,民法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调整市民社会关系,而且在于承认和尊重市民社会主体的行为意志并使其意志人格化。“人的资格本质上是实践或形成自己的意志的资格,享有人的资格的标志是与同类享有实践或形成自己的意志的平等资料。”⑫李锡鹤:《民法哲学论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在市民或者私人社会关系中,每一个主体都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意志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利益目的,所以承认和尊重主体的行为意志,就是承认和尊重主体的利益目的与需求。通常情况下,主体的利益是通过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换来实现的,也就是表现为一定的交换关系,而这一交换关系是以意志的即意思表示的交换方式来完成的。“主体可在对象上实现自己的意志,故主体必须有意志。所谓主体支配客体,其实是主体的意志支配客体。意志是主体的核心和灵魂。主体是意志的存在形式,主体的根据就是意志。”⑬前引⑫,李锡鹤书,第32页。人之所以成为主体,就在于它的意志性。人在以意志条件构成主体的同时又以意志支配主体的行为,并实现主体的利益和维护主体自身的存在。
意志的主体意义与价值决定了意志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正当性才能够作为主体条件存在。换言之,意志是自由的,但是作为主体条件即构成民法精神的行为意志,则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社会的;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受到限制的,⑭自由的社会设计本身就是对自由条件的社会限定。“因此,任何时代的社会自由都以限制为基础。它是一种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有的自由,也是一种从那些不伤害他人的活动中进行选择的自由”;“全部社会自由都立足于限制”,“在一个方面对一个人施加限制是其他人在该方面获得自由的条件”;“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获得的自由不是好的自由,所有生活在一起的人都能享有的自由才是好的自由,这种自由取决于法律、习俗或他们的感情使他们防止互相伤害的圆满性,并用这种圆满性来衡量”。参见[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6-47页。应当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性的意志条件,只有这种意志才具有社会正当性。主体行为的正当性,是由主体意志的正当性决定的,根本是一种主体意志的正当性,没有正当的意志性,就不会有正当的行为性。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哲学观点认为,“文明社会的每一个人所作所为应该符合某种‘正当’的规则”,⑮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如果人们的行为不符合某种正当性规则或者失去了控制,那么什么危害自己、他人和社会的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因此人的行为必须接受一定的意志条件。近代自然法之父格劳秀斯将意志作为行为的核心要素而成为判断行为及法的正当性的主要标准,认为自然法是“正确理性的命令”,是“不可改变的”,即使“上帝也不能改变它”。⑯前引⑮,张乃根书,第91页。人的行为意志应当符合自然理性,具有道德的基础和根据,否则就走向了社会伦理即规范与秩序的反面。基于自然意志的要求,格劳秀斯将“对允诺的遵守确定为人的本质和品行,而具有这种本质和品行的人是依据自身理性行事的主体。人之所以是理性的,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意志,能够预知自己行为的后果并加以控制”。⑰窦海阳:《论法律行为的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意志既然作为主体条件被承认和尊重,那么人就应当信守自己的意志和基于自己意志的承诺,否则,意志就成了可以用来损害他人利益的主观恶意。显然,任何人都有形成和实践自己意志的权利,但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或者以自己的意志损害他人。这种意志的正当性决定了,一方面,人要对自己的意志负责,不能滥用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人接受某种统一的意志是必要的和有可能的,这就是作为民法精神的普遍行为意志。
(三)民法精神的行为自由性
民法精神的行为意志,虽然是一种规范与秩序的普遍意志,但是它在根本上是一种行为自由的意志。“一个人,当他在自己身上找到支配他去行动的动因,或是在从事于这些动因所支配他去做的事情上他的意志遇不到任何阻碍的时候,这个人就叫作自由的。”⑱[法]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下卷),管士滨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7页。霍布斯认为,自由与必然是相容的,“因为人出于意志的每一行为、欲望和意向都是始于某种原因的,而这种原因又始于因果链条中的另一原因,不断地追问下去,一定存在一个一切原因的原因的第一原因,所以这自由的行为也是具有必然性的行为”。⑲[英]霍布斯:《利维坦》,吴克峰译,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03页。康德认为,“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⑳[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3页。自由是人的生命的本质,必然构成人的社会条件和要求。没有自由,也就没有意志,意志只有体现为自由,才是意志和具有意志的本质。自由是主体根据自己的意志实现自身利益目的的可能性。意志和行为是构成和表现主体自由的两个核心要素。意志是决定自由的内在因素,行为是表现自由的外在条件。外在行为与内在意志的统一,就是行为自由。就自由的本质而言,内在意志是决定外在行为的根据,外在行为是表达内在意志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行为自由就是意志自由,而有意志不一定有自由,意志只有可以转化为行为并且可以作为自己的利益实现条件,才是真正的意志和意志自由。当然,如前所述,民法精神的行为自由作为一种社会自由本身就是自由的条件和限制,㉑“个人自由必须约制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但是如果他戒免了在涉及他人的事情上有碍于他人,而仅仅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上依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断而行动,那么,凡是足以说明意见应有自由的理由,也同样足以证明他应当得到允许在其自己牺牲之下将其意见付诸实践而不遭到妨害。”即民法精神的行为自由是一种自主构序的行为自由,是主体自由与秩序的内在协调与统一。
民法精神作为一种形式与行为统一的规范与秩序构造,在意志与自由统一的基础上构成了主体的人格条件。“正因为人格,人才从人的动物性当中脱离出来,凭借自由的意志而成为自身神圣的道德律主体。”㉒周清林:《从“Recht”转向“fäigkeit”:论作为民法基础的消极人格》,肖厚国主编:《民法哲学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正是基于意志自由,人不仅可以认知自己的利益需求,而且可以确定自己的利益条件,并且能够自由地实现自己的利益目的,从而人便在自己的意志中获得了自由,并在自由中构成了人格。“人依其本质属性,有能力在给定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自主地和负责地决定他的存在和关系,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㉓[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46页。民法精神作为一种行为自由的人格形态,既以人的意志为根据,又以人的自由为条件,在意志与自由中实现了人的自然伦理与社会伦理的本质统一。民法精神的行为自由,不仅承认和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和自由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同等地位,而且把行为自由作为人们实现利益的一般社会条件与手段。㉔“人类在他的童年时代生活得自由自在,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他的喜好满足他的欲望,按照他的心意发展;今天,如果你们要想使人类重新自由,就要给社会一种组织,这个组织便利一切人在同等的地位上满足他们的欲望,发展他们的能力。”参见[德]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孙则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69页。这样,整个社会既构成了一个行为自由的利益共同体,也构成了一个行为自由的社会秩序体系,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行为自由的主体,都接受行为自由的社会秩序,都可以根据普遍的自由规则而以行为自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并达到自己的利益目的。人在被承认和尊重自由和自由的利益条件的前提下,自然成为自由的人格主体。这种自由不仅是意志的,而且是规范和秩序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与生态文化和文明形态,从而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本质。
(四)民法精神的行为自治性
民法精神的行为自治性,是民法精神在意志性、自由性基础上的更高本质性。如果说意志是民法精神的主观性,自由是民法精神的意志性的社会形态,那么自治则是自由的实现条件与方式。自由的社会实现应当是自治,自治是自由与自由限制的结合与统一。自治一方面是行为自由,另一方面是行为自理,也就是说,自治既是主体的自我自由,又是主体的自我限制,不仅要求行为的自由性,而且要求自由的规范性与普遍性。作为民法精神的行为自治,是通过意思自治即私法自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即所谓意思自治或者私法自治,根本是民法精神的行为自治。㉕所谓私法自治,是以私法与公法的划分为前提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并不是单纯的法律技术创造,而是法律技术接受的现实社会关系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社会有私益与公益之分,而在此基础上必然产生两种社会及其不同的社会诉求,并产生不同的法律调整——公法是调整国家或者公共利益关系的法律;私法是调整私人利益关系的法律。在私法意义上认识的民法是一个更直接揭示民法本质的概念。不论是主体的人还是民法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与“私”的概念与含义联系在一起的私人和私人关系的范畴。私法自治是民法即私法的条件和要求,也必然构成民法即私法的价值与本质。“私法最重要的特点莫过于个人自治或其自我发展的权力。”㉖[德]罗伯特·霍恩:《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个人自治和自我发展的“权力”就是人在私法上的根本地位,是作为普遍的社会秩序条件存在的。私法自治是由私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关系的本质所决定的,市民社会关系即私人社会关系的本质就是自治。换言之,私法自治作为一项私法原则和条件,是市民社会关系的本质要求,代表个人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社会规定性。自治的问题,既是个人行为自由与自律的问题,也是民本模式的法治文化与法治生态的根本问题。㉗“‘私人自治的生活塑造’作为法权应当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与完整,而在这自由与完整之中,所有的成员相互承认彼此的自由和平等。”参见[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在自治的条件下,一个人作为私法主体,是自我行为的决定者,在对自我事务的决定中既享有私法承认的自由,又接受私法的自由限制,形成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个人行为体系。
民法精神的私法自治作为一种行为自治,是法律行为的自治。“私法自治的工具是法律行为。”㉘[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由于法律行为的个人利益性,私法自治构成了个人利益实现的社会秩序条件,是个人利益条件的自主性及其实现的行为自由性。“私法自治之意义,在于法律给个人提供一种法律上的权力手段,并以此实现个人的意思。这即是说,私法自治给个人提供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使个人获得自主决定(Selbstbesti mmung)的可能性。”㉙前引㉘,梅迪库斯书,第143页。基于自治的要求,一个人不能代替另一个人作出决定,国家或者社会也不能以一般意志的形式剥夺个人作出决定的主体地位;相反,个人为自己作出决定的主体地位必须得到承认和尊重。因此,一个人不能对另一个人的行为作出强迫,国家作为市民社会的代表也应当选择任意法的形式辅助当事人有效地构造市民社会的法律行为。
自治是私法相对于公法的一个规范特征,也是私权区别于公权的本质属性。㉚“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上,问题并不在于它们之间的相近性而在于它们之间的客观差别性,并且这种差别性是否构成它们之间划分的必要条件。公法与私法的二元论并不是否定它们之间的相近性,相反,二元结构的法律体系是以两者之间的相近性为条件的,正是这种相近性表明了它们之间的体系性联系,而差别性则体现出它们在体系内部的相对独立性,这也正是公法与私法划分的意义所在。”参见王利民:《民法的精神构造:民法哲学的思考》,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212页。“公法从根本上讲是强制性的,个人不能违反它的规定。而私法给个人意愿留出了较多的余地,它的规则往往是补充性的,只要在没有相反意愿的情况下便可以适用。”㉛[法]法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私法自治作为以私法形式承认的民事主体的行为自治,是基于意思表示而可以产生设权效果的自主行为条件,具有市民社会关系的必然规范属性,㉜意思自治一方面是根据行为自由原则制定的一个民法体系,另一方面是这一民法体系对行为人根据自己意志设定法律关系的一种承认。意思自治是民法本质的一个反映,它代表了一个法律体系,而基于这一法律体系的调整必然产生一种以意思自治为条件的法律关系秩序。是“各个主体根据他的意志自主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㉝前引㉘,梅迪库斯书,第142页。也就是说,私法自治是法律承认的行为人可以根据自主意思设立法律关系的一般制度规则。“法律制度赋予并且确保每个人都具有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法律行为特别是合同来调整相互之间关系的可能性。人们把这种可能性称作‘私法自治’。”㉞前引㉓,拉伦茨书,第54页。私法自治是民法本质的一个反映,它代表了以民法精神为基础的一个私法体系,而基于这一体系的调整则必然产生以个人行为自治为条件的法律关系体系。
自治不仅是市民社会关系的本质性,而且是市民社会关系的道德性。市民社会作为私人社会,“人总是生活在同他人的不断交往之中。每个人都需要私法自治制度,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自己的切身事务方面自由地作出决定,并以自己的责任处理这些事情。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他才能充分发展自己的人格,维护自己的尊严。因此,每一个成年公民都享有私法自治,这是私法的一项主要的原则和基本的原则”。㉟前引㉓,拉伦茨书,第54-55页。市民社会是个人利益关系的社会,为了个人利益目的存在,追求个人利益目的实现,除了个人利益,市民社会没有其他的根本性要求。人类是能动的社会主体,具有自然的、能动性和自治的本质性,自然要求和本能实践人格的自治地位。自治是人的本性,也是人作为主体的社会即市民社会关系的本质性。这种本质性超越人的意志与精神范畴,具有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类社会构造的自然形态,是社会生态秩序存在的基本形式。自治是一种人性条件的必然要求与结果,个人自治不仅是一种基本人性,而且也是人的自然权利,㊱根据自然法理论,私法人格就是作为自由的一种自然权利。“作家们一般称作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遵照自己所想象的方式使用自己的力量维持自己的本质属性——也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命——的自由。所以,这种自由就是用人本身的判断和理智以最恰当的手段做每一件事情的自由。”参见[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吴福刚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可见,自然权利与一般私法人格的本质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人的自然属性在社会条件下的要求与反映,体现人类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规定性,是上升为法律即作为人的社会属性的基本人性,这一人性的本质是自由。人基于自然本性,应当处于一种自治生态或者起码应当具有一定的自治条件以维持自己应然的生存状态。“存在着一种人性,并且这一人性对所有人来讲都是共同的,人天生就具有智力,具有智力的人在行为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也有能力决定自己追求的目的。”㊲前引⑩,马里旦书,第17页。由于人类的行为受制于统一的利益需求及其实现条件的规定性,所以,一个人既知道自己也知道别人的需求和目的,从而能够在自主与自治的前提下产生共同的行为意识并形成共同的行为条件。这样,人们能够通过个人的行为自治达到共同的利益目的,从而满足普遍的人格条件和要求。这一条件和要求,以人性为根据,既没有理由否认或者不予承认,也没有其他条件和要求可以替代,因此构成了市民社会关系的本质存在。
行为自治具有深厚的法治和法治文化的内涵。以民法精神为主旨的行为自治,是一种以民为本即民本模式的法治理念与法治文化形态。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代表和实现人民利益的社会行为文化,人民利益及其实现始终是这个文化的根本价值与目的。人民利益是每个人的个体利益的集中体现,而对于个人利益而言,选择什么利益,通过什么样方式实现个人利益,应当由人民主体自主决定或者应当允许个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通过行为自治的方式决定和实现。因此,以民法精神为条件的行为自治,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行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民本模式,应当根植于行为自治的社会基础之上。
(五)民法精神的行为秩序性
民法精神的行为自由与自治,是一种个人行为的秩序形态,不论是自由还是自治,只有构成社会秩序才具有民法精神价值。
1.民法精神的行为私序性
民法精神是一种私法行为精神,调整私人社会关系,规范私人社会行为,构造私人社会秩序,追求私人社会目的,具有行为的私序性本质。换言之,民法精神首先是一种私人社会的行为精神,是私人社会秩序的行为条件,其建构的行为秩序在根本上是私序而不是公序。私序也就是民法即
私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关系的秩序,私法秩序的构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主体与核心,是法治和法治文化的根本秩序。民法精神的行为秩序在私序的意义上,一方面,民法精神是一种私人利益秩序,以实现私人利益为目的,反映私人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规定性;另一方面,民法精神是一种私人行为秩序,是通过私人行为自主实现私人利益的社会秩序形式,应当遵守私人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规定性。因此,在行为私序的意义上,民法精神同样回归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民本性。
民法精神的行为私序性,要求民法精神和以民法精神为基础的法治文化,必须以私人利益为目的,尊重私人利益的社会行为条件,体现私人社会秩序的核心价值,反映私人社会关系的规律与规定性。可见,以民法精神的行为私序为基础的法治和法治文化,在根本上是私法之治和私法文化,其核心仍然是个人在社会秩序构造中的主体地位问题,而这一切又都建立在对人的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社会条件的承认与尊重上。必须承认个人利益是社会的根本利益,而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民法精神及其行为私序,则是法治社会与法治文化的根本精神与秩序,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和法治文化应当建立在民法精神的行为私序的坚实基础之上,㊳“利益,也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个人提出的请求、需求或需要——如果文明要得以维持和发展、社会要避免无序和解体,法律就要为利益提供支持。”参见[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3卷),廖德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民法精神及其行为私序,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只有合理的个人利益分配,才能够构建和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也才能够满足一个社会的法治和法治文化的实现条件。以民法精神的行为私序展示社会主义法治和法治文化的民本价值与秩序本质。因此,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和法治文化的行为私序观念,一方面,法治是个人行为之治,法治文化是个人行为文化;另一方面,法治和法治文化的民本模式是一种私法自治与私法文化,它以个人行为的私序构造为实现条件。这就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和法治文化,应当以个人利益的社会秩序条件为根据,充分认识民法精神的行为私序在法治和法治文化构造中的根本地位和作用,并建立以民法精神及其行为私序为条件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即一种社会治理的民本模式。
基于个人利益的根本地位性,对个人利益的承认和尊重,首先应当承认个人行为私序是个人利益实现的最好行为方式,即个人利益首先应当通过个人私序的形式实现,公序只能是个人私序自力不足的补充条件。㊴公序是通过公法或者公共治理的方式建立的社会公权秩序。社会及其管理者即国家或政治社会存在的根本目的和合理价值,就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有序满足私人利益的需要。因此,必然确认个人的社会主体地位,也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㊵《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的主体地位,根本是个人利益及其实现的自主地位,也就是个人行为秩序在个人利益实现中的地位。不承认这一地位,就是不承认人的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社会规定性。人的利益,是作为自然与必然需求的人身与财产利益,本身就是私人利益关系,只有通过私法或者个人的行为私序的方式调整与实现,才符合这一利益关系的本质,也才能够形成这一利益关系的合理秩序。
民法精神的行为私序,是以个人诚信为基础的行为秩序。这是由民法精神的市场经济条件决定的。诚信是人类社会古老而恒定的精神传统与道德要求,没有诚信就没有民法精神的行为实践及其行为秩序。㊶虽然在不同的民族与社会条件下人们有不同的诚信意识与行为要求,但是诚信本身则始终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与践行的精神原则和行为秩序。
诚信是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维系和促进社会整体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社会秩序条件,具有弥补法律和其他强制性规范之不足的地位与作用。因此,诚信被奉为民法的最高原则与“帝王条款”,而民法精神也必然以诚信作为个人行为秩序的本质条件与要求。诚信内含着人类社会理想秩序的自然生态精神,构成了个人意志及其行为秩序的一般原则。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直接形态就是个人行为秩序,个人行为秩序所应当具有的正当性、合理性则必然以诚信为条件。诚信是个人行为秩序的精神基石,是建设法治和法治文化民本模式的必然个人行为秩序要求。
2.民法精神的行为公序性
民法精神虽然具有行为私序的本质,但是它并不是单纯的私序性,而是在具有私序本质的同时构成一种社会公序。换言之,民法精神的个人秩序行为,不仅是一种私序行为,而且是一种公序行为,是私序与公序的结合与统一。也就是说,民法精神的私序性并不是一种狭隘的个人意识和非理性条件,它是一种个人或者私人秩序的公共性,其本身既不能远离社会道德,也不能脱离公共秩序,而是和社会公德与秩序要求相统一的个人品行条件。民法精神及其行为秩序,必须具有社会公德意识,理解私人利益关系的公共秩序条件和要求,能够把私人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公共秩序遵守,从而以自觉的个人行为秩序维护私人社会关系的公共秩序条件,从而以私人社会关系的公序良俗性构造社会生态的秩序文明。
一方面,民法精神是私人社会的公序性。民法精神的主体是个人,民法精神是个人精神,但是民法精神是公德而不是私德,民法精神的行为秩序是私人社会的公共秩序条件。虽然民法精神是市民社会关系
㊶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有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的箴言。罗马法认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为人诚实,不损害别人。”参见[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页。“罗马人承认‘诚信’是一种规范要素,‘诚信’创造出一系列罗马的规则,当然这些规则既适用于罗马人,也适用于异邦人。”参见[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237页。的条件,不能在个人利益目的之外而有民法精神,但是,民法精神的行为秩序,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秩序或者私序,而是个人的公共道德品质,反映的是个人在私人社会关系中的公序良俗条件,即社会公共秩序。所以,民法精神的行为秩序,不仅是个人利益的秩序,而且是个人利益的公共秩序,是个人利益的公共秩序形态。换言之,民法精神的行为条件,不仅是个人的行为条件,而且是个人的社会行为条件,即普遍的社会公共秩序条件。因此,私人社会关系的民法精神条件已经超越私人社会的范畴而成为一种公共秩序条件,在公共秩序条件之外不存在民法精神的行为秩序。所以,作为私人社会关系条件的民法精神,应当反映公共秩序条件并以公共秩序作为行为的目的和基础,从而为私人社会关系正确定位并确定其合理的行为标准,以符合社会公共秩序的条件维护和实现个人的利益目的与秩序,而不是简单地反映私人社会关系的条件或者简单地顺从私人社会利益的目的和要求。
另一方面,民法精神的私序不能脱离公序。民法精神及其社会规范与秩序的本质决定了个人行为私序与社会公共秩序的内在联系与统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秩序意志,但是个人的行为秩序只有与社会公共秩序相统一才具有民法精神的秩序意义,因为民法精神只有作为普遍的社会秩序才能够反映社会的秩序本质并成为社会的秩序条件和要求。然而,个人的行为秩序作为一种主观意志总是具有它的差别性和层次性,它在个人利益的支配下总是可能接近或者远离社会的一般公共秩序条件,而这样的个人行为秩序并非全部构成民法精神的行为条件。那些远离或者脱离一般社会秩序要求的个人私德观念,是一种自以为是的个人行为品质,是从个人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以公共秩序为条件并寻求相互关系的利益均衡的一种个体要求。这一要求作为一种个人利益目的和条件,是自闭的而不是开放的,是自利的而不是包容的,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直觉的而不是逻辑的,是失衡的而不是秩序的,因此,它不构成民法精神的个人行为及其秩序本质。
个人行为的公序性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基础的一种道德条件,商品交换关系不仅使民法精神的私人社会关系具有了明显和直接的公序性,而且能够产生与公序要求相适应的开放与包容的公共关系条件。公序作为民法精神的个人行为目的与要求,在根本上不是制度形式而是行为秩序,即人的社会精神文明与法治文化的秩序构造。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不断克服那些与现代社会公共秩序条件相矛盾甚至对立的各种非秩序性的传统社会私序现象,建立和形成与现代法治与法治文化相统一的私人社会的公共秩序形态。这在根本上就是民法精神的社会秩序构造。民法精神以私人社会的秩序构造,反映了私人社会及其秩序的公共本质。在民法精神的社会秩序构造及其实现中,私人社会离不开一定的公共秩序条件,这就是民法精神的行为公序性,只有将民法精神的行为秩序或者私序上升为公共秩序并以一定的公序形式和条件支配私人的行为秩序,才能够真正实现民法精神的社会秩序构造,即一种法治和法治文化的社会文明形态。
二、民法精神的生态性
民法精神是社会精神,但它作为人的精神,根本是人的生态精神。民法精神的生态性决定了民法精神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与秩序体系即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只有在生态的基础上,才能够把民法精神作为特定对象来把握其实质与本质,也才能够真正认识民法和民法精神。
(一)民法精神与人的生态性
民法精神作为人的精神,根本是人的生态精神,是由人的生态性决定的。没有人的生态性,就没有人和人的精神性。
1.民法精神与人
民法精神的生态性,根本是由民法精神的主体——人的自然生命性所决定的。民法精神是人的精神,人是自然生态的产物,遵循人的自然进化的规律,而作为人的自然生态与进化的产物,人的精神亦必然具有生态性的本质。所谓生态,一般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㊷“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意指家或我们的环境。后来通常指生物的生活状态,即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它们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人们也常用‘生态’来定义美好的事物,如健康的、美的、和谐的等事物均可以用‘生态’修饰。”参见方印:《论民法生态化的概念及基本特征》,载《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广义的‘生态’概念,意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各种关系的和谐,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等各种关系的和谐,也就是指与人类有关的各种关系的和谐”;“狭义的‘生态’概念,意指作为自然性的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即人类与自然环境的自然性和谐,也即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参见黄爱宝:《政府作为“理性生态人”:内涵、结构与功能分析》,载《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5期。人是生态系统中的活生物体,遵循着自然生命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因此,人的社会精神包括人的民法精神,必然具有和反映人的自然生态的本质。换言之,民法精神作为人的精神,也就是人的生态精神,具有人的生态性,它首先是人的生态选择并遵循人的生态规律,然后才是人的社会选择并构成人的社会性和形成人的社会规律。民法精神的社会性必然是人的生态性的要求和反映,具有人的生态规定性。
2.民法精神与生态
民法精神不仅是人的意志性,而且是人的生态性,是人的生态条件与存在。这是一个涉及民法和民法精神的本质的问题。民法和民法精神是基于人的生态需要而产生的社会现象,作为人的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条件,与人的生态性具有直接的联系。民法精神反映人的生态条件并构造人的生态秩序,是人的生态条件的社会规范化与秩序化。人的生态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反映人的生命利益及其实现条件的内在秩序需求。人的生态性主要是人的生物与生理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它是人的存在与发展的自然根据与基础。人的生态性既决定了人的生存目的,也决定了人的生存与发展条件,这个目的与条件在市民社会关系上主要就是通过民法精神的形式反映出来的人的主体性及其实现的规律性与规定性。人的生态性决定了人的精神性,而这个精神在人的生态性基础上构成每一个人的要求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是任何一个民族和社会都必然具有和需要的社会构造并具有人类永恒的价值属性。也就是说,人的生态性是民法精神的根据和来源,决定了民法精神及其制度原则与价值的一般性与普适性。民法精神作为人的生态性条件要求,是一种自然的社会规范精神,需要在人的自然与生态中发现它的真实与本质。民法精神虽然是人的社会意识形态,但是在根本上它是人的生态性要求,是以民法形式反映的人的生态条件及其精神本质,它通过民法规范与制度而具体化和形式化,并内化为人的行为意志与秩序。因此,人的生态性是民法精神的根本性,人的生态精神是民法精神的真实精神。
基于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以人的生态条件为根据和本源的民法精神,需要在人的生态性中去发现和寻找其本质并揭示其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而不能在单纯的人类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中去编制它的理想与蓝图。人是在自然生态的基础上发展和构造自身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的,人类的社会关系与秩序的产生和发展反映的不过是人的生态关系与秩序条件要求,虽然人类社会本身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它根本上是人的自然生态秩序的一部分,是由人的自然生态秩序所决定的,不能超越人的自然生态的规律与条件而有单纯的社会形态与文明。
(二)民法精神的自然生态性
民法精神作为生态现象,既是社会现象,也是自然现象,是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统一。㊸“自然现象是一种按不变的规律共存和相随的事物体系。”参见[英]伯里:《思想自由史》,周颖如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4页。当然,自然现象只具有相对的不变性,而不具有绝对的不变性,任何运动的事物都是变化的,但变化是遵循一定规律的。民法精神的生态性,根本是人的自然生态性。“人是自然的产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服从自然的法则,不能超越自然,就是在思想中也不能走出自然;人的精神想冲到有形的世界范围之前乃是徒然的空想,它是永远被迫要回到这个世界里来的。”㊹“由自然形成并且被自然限定的东西,一点也不生存于大的整体之前,它是这个大整体的一部分,并且受整体的影响;人们设想的那些超乎自然或与自然有别的东西,往往是些虚幻的事物,我们永远不可能对这些虚幻的事物形成真实观念,也不可能对它们占有的地方和它们的行动方式形成真实的观念。在包容一切的这个圈子之前,什么也不存在,什么也不能有。”[法]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管士滨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页。人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一切存在,根本是人的自然生态存在,必然反映人的自然生态本质,不能脱离人的自然生态的规律性与规定性。虽然民法精神是人的社会精神,具有人的主观意志性,是人类社会的规范与秩序条件,属于一定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范畴,但是民法精神作为人的意志,必然反映人的自然条件与生态需求,具有人的自然生态性,体现人的自然生态本质,遵循人的自然生态的规律性与规定性。
民法精神的自然生态性是民法精神的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根据。民法精神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与秩序精神,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能够形成共同的规范与秩序认知并能够内化为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与秩序条件,就在于民法精神所具有的自然生态属性。换言之,民法精神基于人的自然生态性,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因此,无论任何一个民族以及在任何一种社会条件下,都会存在共同的民法精神,不同的只是在这种共性条件基础上的表现差异而已。虽然不同的民族以及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条件下会存在不同的民法精神,或者民法精神在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往往表现出各种不同程度和水平的差异,但是在不同民族和社会的法律与法律文化中都能够找到民法精神的共同本质,这就是基于人的一般生存利益——客观利益需求所必然表现出来的自然生态的规范与秩序条件。这一共同的客观利益需求及其存在的社会基础,正是人类在全球化的普遍联系及其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民法和民法精神不断趋同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人类在全球化和普遍联系的社会条件下不仅具有了民法精神存在的共同基础,而且在这一基础上能够发现和认知民法精神的人类一般性即作为民法精神共同条件的自然生态本质——人的客观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规定性。
(三)民法精神的社会生态性
所谓民法精神的社会生态性,就是民法精神的自然生态性的社会性表现与实现,是这种基于自然生态的社会表现与实现所必然具有的生态本质。换言之,任何一种人的社会性都不可能超越人的自然性,而只能在人的自然性的规定性中表现人的自然并归于人的生态。也就是说,民法精神既是人的自然生态性,也是人的社会生态性,是通过社会生态表现的自然生态,是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统一形态。可见,民法精神的社会生态性,就是人的社会关系及其条件的生态性,即通过人的社会关系及其条件所表现的人的自然生态性,也就是表现人的社会关系的规范与秩序条件所具有和应当具有的自然生态性。民法精神的社会生态性,是由民法精神的自然生态性所决定的,根本是人的自然生态性,是人的自然生态性的社会表现形式。虽然民法精神在人类的文明体系中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人类的社会文明,但是人类的社会文明是人类自然生态存在与发展的结果,是人类自然生态的要求和存在条件,它反映和表现的不过是人类的自然生态罢了,否则我们就找不到包括民法精神在内的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进言之,生态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社会的,人类以其主体的自然生态性构造了以自身为主体的社会关系条件的生态性,社会不过是人类主体的一种生态性生存结构——人类自然生态在相互关系中的展现形式与结构性条件。因此,人类的社会形态,既不能超越人类的自然条件,也不能违背人类的自然条件,这就是一切人类社会现象的规律性与规定性。民法精神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现象,既不是在人类头脑中任意产生的,也不是随意可以改变的,它同样是人类自然条件的产物,与其说是社会形态的,不如说是人的生态构造的,是一种社会或者社会形式的人类生态现象。
当然,民法精神作为人类的社会生态性并不是人类直接的自然生态性,而是经由人类的意志表现出来的人类生态性,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被归入社会意识形态范畴而一般不作为人类的自然属性来认识。民法精神在意识形态上是人的主观意志条件,特别是民法的精神作为以民法形式规范和表现的精神,代表和体现一定的国家意志,具有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强制性。不过,民法精神的意志性,并不意味着民法精神的任意性,它仍然受人的自然生态条件的规定。因为人的意志是人的自然智慧的结果,是人的客观利益需求即自然生态需求的必然意志性条件与反映,因此,人的精神或者社会现象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自然生态性的条件需求,它不能脱离人类的生态本质。
同时,民法精神作为意识形态,既是人类自然生态的社会表现形式,也是超越人类自然生态的社会价值体系,其以人的自然生态条件为根据,反映人的自然生态本质,但是它在人的意志性中可能存在于人类的自然生态条件之外,即构成人的自然生态条件的异化形态,也就是人的本质的社会异化。这一方面表现了民法精神作为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反映了民法精神在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中的复杂性及其可能出现的与人的自然生态相背离的现象。因此,追寻和发现民法精神的生态本质就成为人类走向法治和法治文明的一个基本价值需求与目标。人类探索民法精神的道路和过程,虽然是艰辛和曲折的,但是人类又总是能够在民法精神的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般规定性与正义性中不断朝着实现民法精神的共同目标迈进。这就是民法精神研究与认知的科学目的与意义。
(四)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与秩序认知
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作为民法精神的规定性,决定了民法精神的一般社会秩序认知,即人的民法精神的秩序认知必然受制于民法精神的生态性条件,并需要在民法精神的生态性认知中表现民法精神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民法精神是人的社会精神,具有社会伦理性,不同民族和社会可能基于不同的民族条件与社会基础而产生不同的民法精神,不同的人或者集体也可能产生对民法精神的不同认识,从而表现出民法精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民法精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代表了不同民族和社会的民法精神的不同发展及其所具有的不同文化特征,也必然影响不同民族和社会的法治和法治文明的历史进程。然而,在民法精神的生态条件的规定性中,人类又总是能够在不同的民族与社会条件下发现民法精神的共同本质并实现关于民法精神的一般秩序认知。
民法精神的生态性是民法精神的社会秩序认知的根据。要发现民法精神的本质,实现关于民法精神的一般秩序认知,就必须承认和尊重民法精神的生态性,发现民法精神的生态性本质,即人类客观利益需求及其实现条件的生态规定性。人类不可能在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之外发现民法精神的一般性和实现对民法精神的共同秩序认知。民法精神的一般秩序认知即它的共性,也就是它的价值性与科学性,根源于民法精神的生态性,民法精神的生态性是民法精神的价值性与科学性的根据。由于民法精神的价值性与科学性代表了民法精神的正义性,所以民法精神的正义性在根本上来源于人类对自身所具有和应当具有的生态性及其一般秩序认知,没有民法精神的生态性及其一般秩序认知,也就不会有民法精神的正义理想,这不仅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民法精神认知的科学水平,而且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民法精神的正义价值。
总之,民法精神的规范性与秩序性根源于它作为社会认知的普遍性,而民法精神认知的普遍性即民法精神的一般条件性,是由民法精神的生态性决定的,生态性是人的社会存在所不可改变而必然遵从的自然属性,人类正是在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中找到了民法精神的普遍性,并把这一普遍性作为自身的一般价值性而成为人类共同的法治和法治文化的基础。没有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也就没有民法精神的普遍性,更不会形成关于民法精神的普遍性的认知,也就没有了作为人类法治和法治文化基础形态的民法精神。
(五)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与行为习惯
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作为一种自然形态,是以一定的行为习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换言之,行为习惯作为民法精神的自然表现形式,也就是被自然规定的社会生态条件。
1.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与行为习惯的统一性
民法精神的生态性所反映的人的自然规律性与规定性,决定了人为实现这一规律性与规定性所应当具有的社会条件要求和反映,也就决定了人的社会规范与秩序形态,而这一形态则必然被规定和表现为一定的社会行为习惯。民法精神作为社会规范与秩序形态的普遍性,正是由人的生态性所决定的社会习惯性结果,是由人的社会习惯性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趋同性。所谓“习惯成自然”,在社会规范与秩序的本质上是自然成习惯。
民法精神既内化为人的自主意志,又践行于人的行为习惯,是自主意志与行为习惯的整体与统一。㊺“人的社会生活,甚或社会动物的群体生活,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个体依照某些规则行事。随着智识的增长,这些规则从无意识的习惯(unconscious habits)渐渐发展成为清楚明确的陈述,同时又渐渐发展成更为抽象的且更具一般性的陈述。”参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4页。换言之,民法精神作为人的生态性是从自然的习惯条件发展成为社会规范与秩序条件的。习惯是一种自然生态的规则事实,是人的行为的自觉支配性,是人类在自然生态的支配下形成的循环往复和不易改变的行为方式。“少成若性,习贯之为常。”㊻《大戴礼记·保傅》。分析法学派创始人约翰·奥斯丁认为:“在立法机关或法官赋予某一习惯惯例以法律效力以前,它应被认为是一种实在的道德规则。”㊼[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不论人类的行为规则最初是怎样形成的,都在生态上表现为一定的社会习惯性。习惯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的社会调整方式与控制能力,也是人类自发自为的共同行为秩序。习惯是人类的自然生态法则,其本身具有道德的合理性,人类的社会秩序构造是自然建立在习惯方式的生态基础上的,人类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首先必须把共同的行为条件以习惯形式确定下来,而一定的生态习惯结构也必然构成人类最初的社会规范与秩序条件,任何社会的规范与秩序都必然从习惯起步并从习惯的生态条件中逐步发展起来。㊽习惯性不仅具有社会生态秩序的属性,而且直接构成法律条件并影响法律的形式和产生。历史法学派甚至认为“法律就是习惯性规范,后者在起源上完全独立于政治团体,在司法过程中获得承认并生效”。参见[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民法并不是直接的人的习惯但它必然表现并需要符合人的习惯,民法对人的习惯的符合与反映水平必然影响到它的实然效力。因此,习惯本身不仅具有社会行为体系与生态秩序的意义,而且具有法律价值。
显然,民法精神不仅是一个民法的制度构造,而且是一个现实的行为及其习惯的生态构造。人的行为习惯越是符合或者接近于人的生态规范与秩序,人的利益需求也就越是能够在其生态性的行为习惯中获得现实性。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仅要培养民法精神,而且要通过民法精神培养人们理性遵守社会规范的行为习惯,实现社会规范与习惯秩序的统一。
2.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与行为习惯的矛盾性
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人的实现活动怎样,他的品质也就怎样。所以,我们应当重视实现活动的性质,因为我们是怎样的就取决于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从小养成这样的习惯还是那样的习惯决不是小事。正相反,它非常重要,或宁可说,它最重要。”㊾[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7页。习惯的重要性在于它作为社会与民族的自然生态秩序性及其现实的行为条件性。“习惯规则依然绝对地有着现实的特征:至今仍然发生的、作为传统的东西,也应于将来发生,它要求凡是大家都做的,大家所需要的,你也应该去做;它崇尚习惯势力,平常之人就是它的理想之人,而且正常就是它的标准。”㊿[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民法精神是社会规范与秩序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而行为习惯是人的规范与秩序的现实性与特定性。两者之间既存在统一,也必然存在统一基础上的矛盾。民法精神要转化为普遍的社会秩序就必须有人的行为习惯与之相统一,即人们的行为习惯与民法精神的条件和要求的一致性或者趋同性,从而能够习惯性地服从民法精神条件而不与其相背或者不至于普遍地偏离或偏离得太远。换言之,人的行为习惯只有在公序良俗上保持与民法精神的统一,才构成与民法精神相统一并维护民法精神的社会行为秩序。[51]民法精神要成为普遍的行为秩序,需要人们养成与民法精神相统一的行为习惯。“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要存在的话,至少有某些人必须将有关行为看作该群体作为整体应遵循的一般标准。”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换言之,一方面,民法精神应当具有构成人们社会行为习惯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行为习惯也应当具有符合一般民法精神的应然性。“只有一个行为的执行被评价为积极的,它的缺失被评价为消极的,此时,那个行为才是应然的。”参见[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特别是对于法律移植的中国社会,虽然我们制定的民法及其体现的民法精神具有中国特色,但是现代民法和民法精神作为源于西方并以西方文化传统为主体的一个规范与价值体系,必然存在与中国传统的社会行为习惯及其秩序体系之间的矛盾。[52]这一矛盾和冲突的主要方面是人们的社会行为习惯。中国人的许多传统社会行为习惯是与民法精神或者法治条件相悖的,如随地吐痰、到处吸烟、大声喧哗、横穿马路、排队插楔、嫉贤妒能、损人利己等有损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习惯。这些与民法精神或者法治条件相悖的非文明行为习惯是现实和客观存在的,体现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中国社会法治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中国社会的民法精神和法治条件与传统习惯之间作为不同法律和法治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有关。特别是中国人传统思维模式的非理性与非秩序性习惯,是桎梏中国法治和法治文化发展的一个根本因素。这一矛盾的解决是一个中西方不同法律与法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律与法治文化和文明的形成过程。“本土法律文化和外来法律文化,作为对立体系的融合、吸收本来就是不容易的事件,更由于中国封建传统法律文化的强大和特有的历史原因,这一过程就显得更为复杂和缓慢。”[53]潘大松:《中国近代以来法律文化发展考察》,载《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2期;李楯主编:《法律社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如何把已经形成的法律体系及其所代表的民法精神转化为民族的行为习惯与秩序信仰并生根于民族的法律与法治文化,是“后法律体系时代”中国法治和法治文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并预示着推进民本模式的法治和法治文化建设之路的艰难过程。中国作为一个非传统的法治国家,人们缺乏作为法治意识的理性思维和自觉守法的行为习惯,人们的社会行为往往在法律体系及其精神条件之外表现为另样的社会秩序生态。如果说在法律体系建立和形成时期中国法治和法治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是现代法律体系的制度移植与形成,那么,“后法律体系时代”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法治文化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对人的法律行为的习惯矫正,在不断消除主体的法律行为习惯与民法精神之间矛盾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实现行为习惯体系与民法精神的价值体系相对统一的法治和法治文化的生态系统及其运行常态。
(六)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与社会秩序
对于具体的行为人来说,有什么样的民法精神,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行为和行为习惯,也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民法精神的生态性最终通过人的社会行为及其习惯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秩序,从而形成和构造一种公正与和谐的社会生态,这种社会秩序在民法精神的生态性的统一规定性中表现为一种连续、稳定和普遍的自主与自为的社会生态秩序。
民法精神的生态性是通过一定社会秩序表现并构成一定社会关系条件的。民法精神的生态性在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习惯的同时也决定了人的社会生态秩序。一个社会的秩序形态——主要是市民社会的人身与财产关系的秩序形态,根本是行为主体的自主与自律的民法精神的生态秩序,以行为主体的自主构序的民法精神为行为条件,而行为主体的自主构序既是一种生态的行为条件,也是一种生态的行为要求。换言之,没有自主构序的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也就不会形成普遍的社会生态秩序及其秩序的合理性与公正性。普遍的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秩序主要表现为个人自主构序的民法精神的生态秩序,而非法律强迫的行为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54][德]卡希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个人的行为意志决定了个人的社会行为秩序,个人的社会行为秩序不是个人的外在秩序,而是个人的内在秩序。“人为自律生物,严格而言意味着他本身就是自己行为的法则,他是自己的立法者。”[55][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法律实施的国家强制力只是法的终极意义或者是对法律责任的必要负担而言的,已经形成的法律体系只是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一种客观的行为标准,而不是已经内化为了人的内在行为秩序并能够直接外化为人的秩序行为。个人社会行为的守法性与秩序性,在根本上不是源于法律规范对个人行为的规范与要求,而是决定于行为主体的自主构序性的民法精神及其对法律条件本身的符合水平与程度。
显然,由个人行为条件构成的社会秩序并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现象,而是一定生态驱动的现实结果,这一生态驱动的现实目的与条件是人的自然与必然的客观利益需求。在利益目的与条件面前,个人的社会行为秩序及其稳定性和普遍性是相对的和有局限性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城邦建立的理由和意义指出:“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很多东西。”也就是说,建立城邦是为了以城邦的社会秩序条件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利益的需要。在亚当·斯密理想的社会体系中,“允许每个人在平等、自由和公平的条件下,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利益”。[56][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张晓林等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28页。休谟指出:“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利益所支配的,并且甚至当他们把关切扩展到自身以外时,也不会扩展得很远。”[57][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74页。人的社会行为及其秩序是人的生态利益的自主实现方式,而人的社会行为秩序并不是法律强制力的直接形态,而是人对利益选择的现实结果,决定于人们对利益选择的实际态度——一种行为精神的生态秩序条件。然而,在同样的利益面前,人们的态度选择并不完全一样,这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每个人所处的生存地位和实际的利益需求的不同;另一方面是每个人处理利益关系的理性水平与道德标准的差别。前者是物质与客观的规定性,后者是精神与主观的规定性,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这两个规定性而有单纯的利益态度和行为秩序选择。休谟又指出:“人类若非借着普遍而不变地遵守正义规则,便不能那样有效地达到这种利益,因为他们只有借这些规则才能保存社会,才能不至于堕入人们通常所谓的自然状态的那种可怜的野蛮状态中。”[58]前引[57],休谟书,第574页。然而,人们能否自觉服从作为正义规则的法律,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自觉服从法律,既不最终决定于法律所具有的国家强制力,也不根本决定于法律体系及其制度本身的完善程度,而是决定于人本身作为利益主体在利益取舍面前根据利益需求所作出的利益判断与选择,并由此决定的人的生态利益行为,这就是人的精神或者民法精神问题。
人的民法精神是一种生态精神,人的生态地位是一种利益地位,其实现离不开人的生态利益选择与利益行为,“因此在私法上要求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维护法律,在自己岗位上做法律的看守人和执行人”,[59][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实现个人的生态利益行为及其法律条件与民法精神的生态性要求的协调与统一,从而使个人的生态利益行为及其秩序构造符合民法精神的生态要求并构成社会秩序的普遍现实条件。
(七)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与法治文化
民法精神是市民社会的文化形态,是市民社会文化的法律和法治文化。民法精神的生态性同样决定了以民法精神为基础的法治文化的生态性。法治文化有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两种形态,民法精神的法治文化属于精神文化即法治精神文化的范畴。一方面,民法精神的生态性决定了法治文化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法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在反映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上具有一定条件和形式的局限性,这就是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与法治文化的传统性之间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虽然在通常情况下,有什么样的民法精神,就有什么样的以民法精神为基础的法治文化,但是法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传统,往往具有脱离民法精神的社会异化性并与民法精神的生态性相矛盾。换言之,一个社会的现实生态文化,并不一定是符合民法精神的一般生态性条件即人类客观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规定性的文化,一定的法律或者法治文化可能在自身的传统中表现出民法精神的生态性异化,这就是我们研究和强调民法精神的生态性即民法精神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的价值及其重要性。
1.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与传统法律文化
虽然民法精神具有生态性的本质并构成了法治文化的基础文化形态,但是人类初始和传统的法律文化由于在“蒙昧”条件下对人类自身的生态性认知的局限性,并不一定是以人的生态性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即民法精神为基础的法律或者法治文化,换言之,人类法律和法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认知和发现人的社会生态性及其规律性与规定性的过程,是逐步实现人类自身的法律和法治文化与民法精神的一般与普遍的社会生态性秩序条件相统一的过程。法律或者法治文化不仅具有民法精神的生态性,而且具有特定民族与社会的历史传统性,这一生态变异的传统性作为一种保守性和落后性必然在民法精神的生态性及其全球化和趋同化的一般社会发展中产生与民法精神的生态性所代表的人类客观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规定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在不同法律和法治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法律移植与文化变迁所实现的法律与法治文化的体制革新和生态转型来完成的。
然而,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可能在法律移植的制度革命中发生体系性的变革,但是这个社会传统的法律文化即生态变异的法律精神却仍然会在法律移植的制度变革中延续自身的历史发展,即不可能随着法律移植的过程而同时完成传统法律文化向以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秩序文化形态的变迁。这就是“近代变法”[60]近代变法即清末变法。清末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近代法律转型的重要标志,唤起了中国人法律意识的觉醒,从此中国法律摆脱了孤立的地位,开始与世界法律发展相对接,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中国社会从此不可逆转地接受了自罗马法以来的民法传统——西方法律文化,结束了中国古代传统法制模式的历史,标志着中国法制史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法律变革警示我们,欲使法之更新,必先使国人观念更新,这是在传统封建法律意识凝重的中国社会进行变法改革能否成功的先决条件。以来中国社会所产生和存在的自身文化传统与从西方移植的法律体系及其法律精神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实现文化变迁的漫长性和复杂性。“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是在一种封闭的历史环境中发展的,它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又陈陈相因,充满保守性和孤立性。作为古代法制的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的儒家法律思想,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稳定的体系。”[61]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页。中国社会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在自然经济和专制统治基础上形成的以身份等级为核心的伦理法律文化,这一传统法律文化与源自西方的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以相互关系的人格尊重与利益均衡的民法和民法精神为核心的法律文化,存在着价值体系上的先天性和生态性差别。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不仅没有以具体的制度形式确立以人格和人的生态性为基础的民法精神,而且社会的生态结构也远离民法精神的社会生态秩序,所以,建立在法律移植基础上的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与生态变异的中国社会本土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法律移植是中国社会通过现代法律体系构造走向法治和法治文化的必由之路,但是这必然是一个艰难的面对自身社会传统挑战的历史过程。[62]“中国民法正在走向现代化。在中国民法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主张改造和重塑传统,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传统和接受传统事实。因此,必须在对传统因素认识与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民法现代化的道路。”参见王利民、张国强:《中国民法现代化的传统性》,载《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5期。显然,法律移植的法律文化变迁是人类法律文明进步的需要与产物,但它的存在和发展并不能完全代表人类的法律文明与进步。人类法律文明的真正进步表现为反映人类客观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社会规定性的法治和法治文化的建设与形成,而这是以民法精神为基础的社会生态秩序的确立,其本质是追求本土传统法律文化在融入人类法律文明的一般发展中与以当代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为基础的法治和法治文化的统一,即实现在自身优秀传统基础上的法治和法治文化的现代化与生态化。
虽然人类具有共同的生态本质,但是这一共同的生态本质在自己的社会构造中会基于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产生和形成不同的社会生态模式,并具有一定的社会生态模式的变异性,即人的生态本质在自然封闭的特定环境与条件下的不同社会形态反映,从而形成以特定的社会构造与生态模式为特征的社会文化,表现出人类在共同的自然生态本质基础上的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与发展。换言之,虽然人类具有共同的自然生态本质,但是人类自然生态本质的社会实现会在不同民族与社会条件下产生不同的社会生态变异,即形成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包括不同的法律文化,即一种传统和多元的社会文化。
2.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与当代法治文化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类之间已经建立起普遍的交往与依存关系。“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0页。这是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突破民族与国家界域而发生的普遍联系,“即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核心,实现跨国家、跨民族、跨地域利益分配与信息、资源配置的一体化,交流规则和社会秩序的一体化,等等”。[64]吕世伦:《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不同民族和社会的传统法律文化虽然代表一种既定的或惯性秩序,但既非一成不变,也并非没有统一的规定性。“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形成一个社会的基本命题,并且形塑了支配社会秩序的原则,这些原则通常是毋庸置疑的前提。传统行为暗含着未来行为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却可因为社会的实际的或察觉到的需要而发生变化。”[65][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当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建立起人类社会的普遍联系,则必然在这一普遍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社会文化包括法律文化的趋同化或者统一化,即在打破多元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不同社会文化的融合,并在融合的基础上发现和认知共同的法律和法律文化的社会生态性本质,这就是以民法精神的规范与秩序条件为基础的现代法治和法治文化,也就是民法精神的法治生态文化。
人类对民法精神生态性的一般性与普遍性的认知与接受,代表了当代法律与法治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必然性与规律性。虽然人类民法精神的生态性在不同民族和社会中会产生和表现出不同或者生态变异的多元性法律与法治文化,但是人类又必然在自身的社会发展中不断认知和发现民法精神生态性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共同价值与原则的一元性法律与法治文化,从而改变传统的生态变异的社会与法律文化并实现其生态趋同与统一。显然,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并不是“只有一种永恒、不变并将对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有效的法律”,[66][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4页。“自有国家以来,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相融,形成的本国的法律文化都避免不了与其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法律移植发生关系。历史文化发展到今天,几乎没有不受他国影响或世界文化大潮影响的国家,所以说法律移植是国际文化交流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67]肖光辉:《法律移植及其本土化现象的关联考察——兼论我国法的本土化问题》,载何勤华主编:《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1页。虽然现代法律与法治文化在民法精神生态性的一般性与普遍性的认知与发现中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法律或者法治文化传统,而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法律和法治文化又必然保有其历史传统与社会特殊性,但是在民法精神的生态性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基础上的法律或者法治文化的全球化发展,则代表了当代法律和法治文化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在我国,“随着我国与世界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与西方市场经济上百年发展、完善的过程相比,我国的社会转型是‘压缩饼干’,以历史浓缩的形式,将社会转型中的各种问题呈现出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68]朱力:《变迁之痛——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我国的法律移植与变革及其实现的以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是法律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选择与结果,其必然突破我国社会传统的单一民族法律文化的历史界域,从而在法律文化趋同化的全球背景下实现自己的法律与法治文化的生态转型与超越发展。“然而,在当今中国,如何看待本国固有的法律传统却成为一个极其复杂和艰难的问题。我们首先会面对基本价值完全不同的判断。”[69]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8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法治文化的形成,是中国社会法律与法治文化的形成与再生过程,而这一切又都是建立在一个非传统法治国家的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基础需求之间的矛盾基础之上的,因此是一个历史的传统法律文化与移植的现代法律制度及其所代表的法治文化之间的矛盾过程。中国作为一个非传统法治国家并不具备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法律文化传统与制度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及其法律体系的形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作为现代法治基础的制度条件,但是这种在非法治传统社会所进行的“变法式”的制度移植与法律文化变革,并无法满足这一社会在实行法治过程中对内在法律和法治文化的生态需求。已经形成的法律体系及其所代表的法律制度作为在借鉴与吸收西方法律文化基础上的形式构造,在非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必然存在着与自身机体功能的兼容性矛盾与免疫性问题,从而需要一个不断消化、吸收和融合的过程。换言之,建设以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仅需要一个法律体系的形成,而且需要全新价值体系的法律与法治文化的内生与再造。
“后法律体系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与生态实现,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转型与再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当代民法精神的法律条件与生态秩序所代表的中国法治文化的内在精神与先进价值需求,直接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人文品格。这一品格绝非一个形式的法律体系所能代表,也不像一个制度的形成那么简单,更不是通过法律移植可以解决。毫无疑问,以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为基础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是对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与生态的变革运动,在终极的社会生态秩序的意义上是以民法精神为核心的私法文化的现代化。它既涉及对中国传统私法文化的合理扬弃,又涉及对西方私法文化传统的有益吸收。“这一理想式方案和梦想一经落入传统社会的现实之中,便会褪尽它在西方社会中的神圣色彩,而变成被传统社会文化所支配和制约的一张标签。”[70]前引[69],尹伊君书,第348页。显然,“非民法传统国家的民法移植与精神构造,不是一个形式上的制度变革与形成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内部结构的全面更新与发展,是一个改造社会的过程,是一个人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深刻的社会进步与超越的过程”。[71]前引㉚,王利民书,代序第3页。不同的文化与精神的碰撞,必然产生各种矛盾与冲突,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法律移植与制度构造而在短时期内完成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从“死法”到“活法”的内变与生成。[72]“所谓民法的活法化,指主要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法制度、民法原则、民法文化被国人普遍接受、认可和自觉地遵循。”参见罗晓静:《我国民法现代化前瞻》,载《中州学刊》2004年第4期。我们要把对法律体系—法治基础需求—法治生态秩序目标的追求和中国社会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与再生结合起来,使中国社会作为法治基础需求的法律体系的形成能够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生态构造的真实条件,从而建立以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民本模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