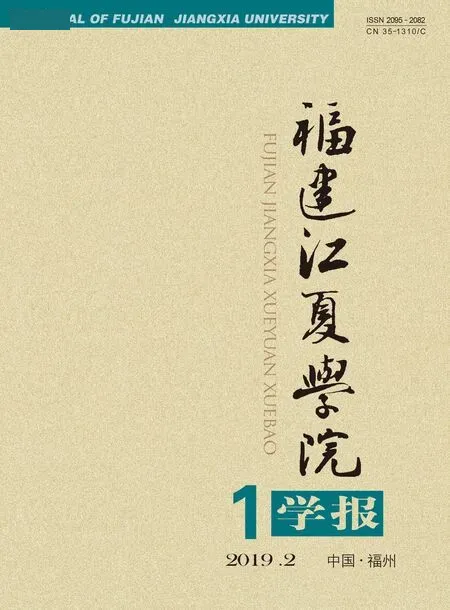冯梦龙对《太平广记》接受的文化诉求与文学意义
曾礼军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太平广记》是由宋太宗诏令李昉等儒臣编纂而成的类书体小说总集,古代文言小说由此而第一次得到了官方的重视和整理。《太平广记》的编纂成书对于后世的小说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浦江清说:“《太平广记》的结集,可以作为小说史上的分水岭。”[1]186所谓“分水岭”,一方面是指《太平广记》对宋前小说具有承上的总结作用,另一方面则是指《太平广记》对后世小说发展具有启下的创新作用。明代冯梦龙小说的编著即深受《太平广记》的影响,无论是《太平广记钞》,还是《情史》《智囊》《古今谭概》等文言小说辑纂,抑或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话本小说再创作,都有着《太平广记》的文学渊源和文化烙印。冯梦龙对《太平广记》的接受既有特定的历史机缘,又是出于作者强烈而明确的文化诉求。就前者而言,冯梦龙正处在《太平广记》开始广泛传播的时代。虽然《太平广记》早在宋初就已编纂成书,但“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收墨板藏太清楼”,直到明代后期才开始广泛刻印和传播。先是有嘉靖、隆庆年间谈恺刻本刊印,后又有隆庆、万历年间的活字本和明末许自昌刻本等版本刊印。就后者而言,冯梦龙接受《太平广记》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即借助《太平广记》旧文本接受来重构情本内涵、诠释经国理念和重估“三教”关系,以宣扬其身处庙堂之外而不能实现的经世理想。冯梦龙的《太平广记》接受虽然有突出的经世致用目的,但同时也推动了小说的文体独立和地位提升,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
一、接受形式:钞删、辑纂与再创作
冯梦龙对《太平广记》的接受主要是通过钞删、辑纂和再创作三种形式来进行的。钞删的接受形式主要体现在《太平广记钞》当中。冯梦龙非常喜欢《太平广记》,但“厌其芜秽”,于是以钞删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芟繁就简”的接受。《太平广记钞》“小引”曰:“予自少涉猎,辄喜其博奥,厌其芜秽,为之去同存异,芟繁就简,类可并者并之,事可合者合之,前后宜更置者更置之,大约削简什三,减句字复什二,所留才半,定为八十卷。”[2]1具体而言,钞删的接受形式表现在三方面:类目合拆调整、文本删减重组、文献校订考辨。
第一,类目合拆调整。《太平广记》原有类目92个,《太平广记钞》则通过合并、拆分和重拟等方式调整为131个。一是类目合并。如《太平广记钞》卷十“道术”眉评:“原本道术外,尚有方士,而事义多相类,故去方士部,并入道术。”卷十九“感应”眉评:“旧另有情感在妇人部,今并入。”卷二十二“名贤”注曰:“旧尚有儒行,今并入。”还有一些未注明者,如“虎”和“狐”两个类目合并为“野兽”。二是类目拆分。由于《太平广记》原有类目统绪的文本内容异常丰富,由此也造成类目与文本不能一一对应的矛盾,冯梦龙根据文本内容对原有类目进行了拆分。如《太平广记》原有“草木”类目被拆分为“木”“花”“果”“竹”“五谷”“蔬”“茶”“草”“苔”“藟蔓”“芝菌”和“香”等12个类目。原有“水族”类目则拆分为“鳞族”“介族”和“海杂产”等3个类目。三是类目重拟。如卷二十九“侠客”注曰:“旧名豪侠。”此外,冯梦龙对原有类目的顺序也有微调。如《太平广记》中“禽鸟”类目居于动物类目板块的末尾,《太平广记钞》则调整到前列。类目增多和调整,体现了接受者对于文本分类的思路更为清晰和明确,体现了知识分类的时代进步。
第二,文本删减重组。所谓“芟繁就简”,主要体现在文本删减上,由原来500卷变成后来的80卷。这种“芟繁就简”既包括文本篇目的删减,也包括文本文字的删减,以前者为主。一是文本篇目删减。《太平广记》原有篇目7100多篇,经冯梦龙删减后只剩下2500余篇,删去了约65%的篇目。如“仙”类目原辑有55卷257篇,删为7卷121篇;“鬼”类目原辑有40卷467篇,删为4卷112篇。二是文本文字删减。如卷一《老子》原有2100多字,删为500余字;卷三《阴长生》原有1000余字,删为170余字。三是文本顺序调整。如卷七《古元之》眉评:“此条元本载蛮夷中,今移入神仙。”卷十九《卖粉儿·崔护》原为两篇,合为一篇,总评曰:“二事恰好对股文字。”两者都是叙男女相爱,死而复生,前者为男死复生,后者为女死复生。文本删减重组主要体现了接受者对文本主题凸显的要求。如七卷“仙”类目分别有眉评曰:“杂载周秦及汉初仙迹”“杂载两汉仙迹”“杂载汉晋唐得道之士”“多载唐开元天宝中仙迹”“多载唐时天仙及仙官降世者”“多载信心之事”“多载仙境及杂事”。这既体现了文本内容的时间性,又突出了文本主题的集中性。
第三,文献校订考辨。由于明代刊刻的《太平广记》多有错讹,《太平广记钞》“小引”曰:“间有印本,好事者用闽中活板,以故掛漏差错,往往有之。万历间,茂苑许氏始营剞厥,然既不求善对校,复不集群书订考,因讹袭陋,率尔灾木,识者病焉。”[2]1因此,冯梦龙对文献进行了校订考辨。一是文献出处校订。如卷十五《孙敬德》注出《冥报录》,《太平广记》作《冥祥记》;卷十九《晋元帝》注出《洞庭记》,《太平广记》作《洞林记》;卷七十二《朱都事》注出《原化记》,《太平广记》作《广异记》。二是文字异同考辨。如卷二《东方朔》有“得声风木十枝”句,眉评曰:“《杂俎》作声木,亦作汗杖。里语生年未半杖不汗。”卷三《韩愈侄》眉评曰:“本传云韩愈外甥。今从《酉阳杂俎》改作侄。世传韩湘子,不知何据,然为侄无疑。”三是内容辨析补充。如卷七《僧契虚》:“故学仙者当先绝三尸。”眉评:“《太上三尸中经》云:上尸彭在人头,中尸彭质在人腹,下尸彭矫在人足,状如小儿,或似马,长二寸。在人身中,利人之死,乃出为鬼。”卷四《孙思邈》叙孙思邈与胡僧斗法胜利后,眉评曰:“或作叶法善事。龙为东海龙,僧为婆罗门。五月五日,秘丹符救之,海水复旧,龙为致泉,名天师渠。”①关于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删订情况,还可参阅傅承洲:《冯梦龙〈太平广记钞〉的删订与评点》,《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辑纂的接受形式主要体现在《情史》《智囊》和《古今谭概》等文言小说辑纂上。文言小说辑纂对《太平广记》接受主要表现在类目编排和文本辑录两个方面。
从类目编排来看,文言小说辑纂接受了《太平广记》以类相从的编排原则,同时把《太平广记》类目统绪文本具有专题性的特点充分放大,使全书的类目编排围绕一个专题来进行。《情史》分为情贞类、情缘类、情私类等24个类目,全书围绕“情教”专题来编排类目。其序曰:“是编分类著断,恢诡非常,虽事专男女,未尽雅驯,而曲终之奏,要归于正。善读者可以广情,不善读者亦不至于导欲。”[3]1《智囊》分为10个类目,上智部、明智部、察智部、胆智部、术智部、捷智部、语智部、兵智部、闺智部、杂智部,全书围绕“益智”专题来编排类目。《古今谭概》分为迂腐部、怪诞部、痴绝部等36个类目,全书围绕着“疗腐”专题来编排类目。《太平广记》有些类目在辑录文本时还往往以小字标示出二级分类,冯梦龙对此也有所接受。《情史》几乎每卷下面都有二级分类,如卷一情贞类下面分“夫妇节义”“贞妇”“贞妾”“贞妓”等。《智囊》则直接以二级类目来作为全书的标卷,如上智部有4个二级类目,分别是卷一见大、卷二远犹、卷三通简和卷四迎刃。
从文本辑录来看,文言小说辑纂大量辑录了《太平广记》的小说文本。其中,《情史》是突出代表。全书共有870篇作品,其中有211篇作品载于《太平广记》,约占《情史》四分之一的篇目数量,这211篇作品中又有130余篇作品载于《太平广记钞》。除了卷三情私类、卷七情痴类、卷十五情芽类、卷十七情秽类等四卷无《太平广记》载有的小说文本外,其他各卷都有。其分布如下:卷一有7篇,卷二有8篇,卷四有16篇,卷五有11篇,卷六有4篇,卷八有10篇,卷九有13篇,卷十有17篇,卷十一和卷十二各有6篇,卷十三有8篇,卷十四有5篇,卷十六和卷十八各有6篇,卷十九有31篇,卷二十有17篇,卷二十一有24篇,卷二十二有3篇,卷二十三有9篇,卷二十四有4篇。②具体篇目可参见曾礼军:《〈情史〉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金源熙:《〈情史〉故事源流考述》,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由此可见,《太平广记》对于《情史》文本辑纂的重要性。《情史》接受《太平广记》的小说文本多着眼于男女之情的文本。如卷四《红拂妓》,原是《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三《虬髯客》,辑纂者着眼于红拂妓与虬髯客李靖之间的两情关系,突出红拂的“情侠”情怀:“红拂一见,便识卫公(李靖),又算定越公(杨素)无能为,然后相从,是大有斟酌人。”[3]123由于选题的特殊性,《智囊》《古今谭概》两部小说集对《太平广记》的文本接受则要少许多。
再创作的接受形式主要体现在《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话本小说创作上。“三言”与《太平广记》有关联的作品,包括入话和正话,共有25篇作品,约占“三言”全部作品的21%。③统计资料源于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其中,《喻世明言》有11篇,《警世通言》有6篇,《醒世恒言》有8篇。“三言”对《太平广记》的接受是以再创作的形式进行,涉及到题材再创作、母题再创作、局部情节再创作和入话再创作。其一,题材再创作,即以原题材为基础的小说书写,两者故事内容基本相同。如《醒世恒言》卷三十七《杜子春三入长安》就是以《太平广记》卷十六《杜子春》为基础再创作而成的。此类作品还有《喻世明言》卷五《穷马周遭际卖䭔媪》、卷六《葛令公生遣弄珠儿》、卷八《吴保安弃家赎友》、卷十三《张道陵七试赵升》、卷二十《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卷三十三《张古老种瓜娶文女》,《醒世恒言》卷五《大树坡义虎送亲》、卷六《小水湾天狐贻书》、卷二十六《薛录事鱼服证仙》、卷三十八《李道人独步云门》等。其二,母题再创作,即以原题材的叙事范式为基础的小说书写,两者叙事情节基本相同。如《醒世恒言》卷三十《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与《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五《义侠》的叙事情节相同。两者都是叙甲官宦救出乙囚徒,乙得救后为官负义,派侠客刺杀甲,侠客得知真情后杀死乙向甲谢罪。此类作品还有《喻世明言》卷九《裴晋公义还原配》,《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卷二十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醒世恒言》卷三十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等。其三,局部情节再创作,即部分故事情节与《太平广记》的一些小说文本内容相同。如《警世通言》卷八《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叙述李白创作《清平调》三首词的情节即与《太平广记》卷二○四《李龟年》相同。此类作品还有《喻世明言》卷二十一《临安里钱婆留发迹》、卷三十七《梁武帝累修归极乐》,《警世通言》卷四十《旌阳宫铁树镇妖》等。其四,入话再创作,即话本小说的入话由《太平广记》的文本故事改编而成。如《警世通言》卷三十八《蒋淑真刎颈鸳鸯会》入话即是由《太平广记》卷四九一《非烟传》改编而成。此类作品还有《喻世明言》卷二十八《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入话、卷三十《明悟禅师赶五戒》入话,《警世通言》卷三十六《皂角林大王假形》入话、卷四十《旌阳宫铁树镇妖》入话等。由此可知,“三言”对《太平广记》的接受方式也是广泛而又多样。
二、接受诉求:经世理想的寄托与阐释
冯梦龙对《太平广记》接受不仅有着多样的接受形式,而且还往往自作评点,其评点条目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与多样的接受形式相得益彰,传达了冯梦龙接受《太平广记》的主观意图和文化诉求。这种文化诉求即是围绕其经世理想来重构情本内涵,诠释经国理念,重估“三教”关系。
第一,情本内涵的重构。晚明盛行王学左派哲学思潮,其中“情本”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李贽、徐渭、袁宏道、汤显祖、张琦等是情本思想的代表人物。冯梦龙与这些人物交往密切,受时代思潮影响,其哲学思想亦主情本。冯梦龙接受《太平广记》很重视情本思想的宣扬,《情史》辑纂即是典型。贯穿《情史》的核心观念是情本思想。《情史序》曰:“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情”是生命的根本和源泉,生命因情而存在,无情就无生命。因此,《情史》“择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各著小传,使人知情之可久”[3]1。由于情本思想的贯彻,《太平广记》的旧文本被赋予了新内涵。如卷十四《莺莺》原属《太平广记》卷四八八,为元稹《会真记》,叙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原文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持肯定态度,冯梦龙对此则作了批判。其尾评曰:“传云时人以张为善补过者,夫此何过也?而如此补乎?如是而为善补过,则天下负心薄幸,食言背盟之徒,皆可云善补过矣!女子钟情之深,无如崔者。”[3]484冯梦龙的其他作品对情本思想亦有贯彻。如《太平广记钞》卷一《秦役夫》叙仙人古丈夫对毛女说:“吾与子邂逅相遇,那无恋恋耶?”眉评曰:“邂逅犹恋恋,乃知仙家非真无情,特无尘世恶薄之情耳。”[2]10卷十三《支遁》眉评:“生死交情,孰谓佛子无情哉!”[2]247
虽然冯梦龙也大力倡导情本思想,但他又对情本内涵有所修正和重构。如汤显祖是情本思想的突出代表,他认为“情”与“理”具有水火不容的对立性。其《寄达观》曰:“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冯梦龙则重视调和“情”与“理”的矛盾,认为“理为情之范,情为理之维”,把忠孝节烈都纳入到“情”当中。其曰:“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熟知情为理之维乎。”[3]36冯梦龙的《太平广记》接受很重视贯彻“情”“理”调和的思想观念。如《情史》卷一《邺中妇人》,叙邺中妇人原为魏文帝宫人,为窦建德掘墓所得,并受到宠爱。唐太宗灭窦建德后欲纳邺中妇人,邺中妇人感于窦建德之情而饮恨自死。该文原属《太平广记》“再生”类目,作者辑入“情贞类”,评曰:“独其守窦公之节,硁硁不渝,是可录耳。”《太平广记》的旧文本接受过程中,冯梦龙既张扬了男女情爱观念,又倡导了传统的节烈思想。
冯梦龙调和“情”“理”矛盾,既不是为了否定尊情思潮,也不完全是对理学思想的肯定,而是为了重建和重构儒学话语系统,从而拯救世风、经国治世。这固然有其保守的地方,却为经世实践提供了可行的建设性话语系统。因为以李贽为代表的晚明尊情思潮,虽然有助于传统礼教压制下的生命个体获得解放,回归本真,求得真心,但往往重“破坏”轻“建设”,对原有儒家话语系统作了极大的破坏,却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设性话语系统;并且在“尊情”的名义下同样容易导致个体沦落和世风日下,缺乏有效的话语系统来制约。冯梦龙的《太平广记》接受对情本内涵进行重构,调和“情”“理”矛盾,正是出于经世实践的需要,其意义不言而喻。
第二,经国理念的诠释。冯梦龙出身于“理学名家”,自小习经治儒,虽几经科场沉浮,但晚年也担任过县令、训导、知县之类小官,经国治世一直是其理想追求。《中兴实录序》曰:“余草莽老臣,抚心世道非一日矣。”因此,冯梦龙的《太平广记》接受也贯彻着其经国理念。具体而言,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倡导仁政爱民,二是强调重视人才。
贯彻仁政爱民的文本接受如《太平广记钞》卷四《翟乾祐》,此篇属《太平广记》“神仙”类目,本是叙翟乾祐调集诸龙和神女铲平险滩以除商旅之劳的神仙故事,冯梦龙则在文末总评中结合现实事例,借题发挥,宣传为官者的牧民要诀。其评曰:“‘宁险滩波以赡佣负,毋利舟楫以安富商’此语直是牧民要诀。盖久习劳者不苦,骤废业者难堪。裒多益寡,自然之理也。犹记昔年吾吴一抚台,欲行维风之政,首革游船。于是富家儿争赁山寺园亭,挟妓宴乐如故。而舟人破业数百家,怨声腾路,未几复之,此足永鉴。”[2]66这种文本接受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冯梦龙认为,牧民之策应持宽恕之道。《太平广记钞》卷五十二《一字天王》眉评:“上帝设阎罗,犹尚恕而恶严,况阳间牧民者。”[2]1005因此,冯梦龙在文本接受中对于酷政暴政屡有批评。如《太平广记钞》卷十七《长孙无忌等》总评:“害人人害,总此杀机。杀机动时,此身之生机便已绝矣。商鞅殉车,周兴试瓮,仰天喷唾,还堕己身,刻薄者果何利哉?”[2]319并且告诫为官者需慎用权势。《情史》卷四《裴晋公》尾评:“以裴晋公之人品,而郡牧犹有强夺人妻以奉之者,况他人乎!一分权势,一分造孽,非必自造也,代之者众矣。当要路者,可不三思乎?”[3]136
冯梦龙还善于在旧文本接受中贯彻重视人才的思想观念。如《太平广记钞》卷五《李泌》眉评:“往时天子爱才如此,故天亦往往产奇才以应之。吁!今亡矣夫。”[2]93同书卷三十《李固言》眉评:“怜才至矣。若遇今人,方将借之以立名誉,肯置榜首乎?”[2]569卷二十五《李邕》眉评:“想见古时人情好才,若今日争认尊官高第耳。”[2]489《情史》卷四《于崸、韩滉》尾评曰:“于、韩两公,固一代豪俊,亦见唐时之重才矣。设当今世,虽日进万言,何益!”[3]139这些评点都是借助旧文本接受,通过古之惜才与今之弃才的对比来批判当下统治者不重视人才。
第三,“三教”关系的重估。在晚明的文化格局当中,儒释道三教早已形成了一主二从的“三教合一”形态,儒学占据着绝对中心的地位,而释道则自觉地依附于儒学,成为儒学的附庸和配角。虽然宋明理学的理论建构充分吸收了释道的文化精华,但程朱理学及其继承者往往批判甚至否定释道文化;阳明心学论者重视禅道文化,却过从甚密,乃至以狂禅自居。冯梦龙从经世致用出发,在《太平广记》旧文本接受过程中,对“三教”关系作了重估,以儒学为中心,既不简单地肯定释道,也不简单地否定释道。首先,冯梦龙认可“三教”并存的状态。《太平广记钞》卷五十七《王弼》眉评曰:“三教不妨并存,先辈何轻?”[2]1106其次,冯梦龙并不信教,尽管他在《情史序》中戏言死后“必当作佛度世”,但他在小说文本接受过程中对佛道信仰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如《太平广记钞》卷一《黄安、孟岐》叙孟岐“年可七百岁”“后不知所之”。评曰:“谁人对证,颇似少君大言,流为醒神说谎。”[2]7同书卷五十四《柳智感》眉评:“修福免祸,岂可不信,但必非僧道家斋醮可转耳。”[2]1042而对于儒教,冯梦龙非常尊崇,文本接受中贯彻了崇儒的思想。如《太平广记钞》卷八《织女婺女须女星》叙夫人(仙女之母)召孔子教三婿,“夫人临阶,宣父拜谒甚恭。”眉评曰:“胡说可笑。”又叙夫人“命周尚父示以玄女符玉璜秘诀”,眉评曰:“胡说!”[2]157《情史》卷十九《织女婺女须女星》亦评曰:“夫人是何名号,夫人之偶又是何人?能令宣尼、尚父伛偻奉命,真可怪也!”[3]662再次,冯梦龙主张三教并存,其目的在于“以二教为儒之辅”,充分发挥佛道服务于治世经国的文化功能。《三教偶拈序》曰:“是三教者,互相讥而莫能相废,吾谓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而袭其迹皆不免于误世”“余于三教概未有得,然终不敢有所去取。其间于释教,吾取其慈悲;于道教,吾取其清净;于儒教,吾取其平实。所谓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者,此也!”[4]1-2冯梦龙的《太平广记》接受贯彻了佛道服务于治世的文化观念。如《太平广记钞》卷一《老子》总评曰:“安息国者,喻身心休歇处。黄金还汝,欲以金丹度之,非顽金也。‘不能忍’三字,极中学道者之膏肓。所以不能忍者,由贪财好色故。阅《神仙传》等书,须知借文垂训,若认作实事,失之千里。”[2]2借神仙修炼来批评贪财好色的世俗丑态。
概而言之,冯梦龙的《太平广记》接受在于其经世理想的寄托和阐释,有着强烈的主体性、时代性和功利性,其接受行为既激活了旧文献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作用,又传达了接受者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三、接受意义:小说文体的确认与重释
冯梦龙接受《太平广记》固然是出于其强烈的主观诉求,但同时也推动了小说的文体独立和地位提升。这主要表现在冯梦龙对《太平广记》的接受确认了小说的文体特征,拓展了小说的文体内涵,宣扬了小说的社会教化作用。
《太平广记》的小说文体性质在宋代就已经得到认可。《杨文公谈苑》曰:“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即《太平御览》);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5]48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对此有同样的记载。《玉海》卷五四《景德册府元龟》引《册府元龟》御制序亦云:“编小说而成《广记》,纂百氏而著《御览》,集章句而制《文苑》,聚方书而撰《神医》,次复刊广疏于《九经》,校阙疑于《三史》,修古学于篆、籀,总妙言于释、老。”[6]1032因此,《太平广记》编纂凸显了宋人对小说文体观念的认识。此后,《宋史·艺文志》把《太平广记》编入子部“小说家”类当中,进一步确认了其“小说”的文体性质。冯梦龙对《太平广记》的接受正是基于其小说的文体性质,并对小说的文体特征作了评点和确认。《太平广记钞》中冯梦龙屡屡用“奇”字来评点其钞录的小说文本。如卷四《魏方进弟》眉评:“奇事!”卷七《李清》眉评:“奇志奇策,真奇人也。”卷八《白螺女子》眉评:“蜗斗何物,乃能除残,大奇!”卷四十三《黄彻》评:“奇谈。”卷六十《郑生》眉评:“魂嫁魂,更奇。”全书涉及“奇”字评点的条目多达45条。此外,还有7条“异”字评点。如卷二《凤纲》总评:“未闻采百花为丹者。吁!亦异矣。”卷六十二《崖山》眉评:“鬼神亦救护亲家,异哉!”有3条“怪”字评点。如卷四十二《刘录事》眉评:“事怪甚,得非鱼崇乎?”这些“奇”“怪”“异”等文字评点不仅揭示了《太平广记》的文体性质,还确认了小说的文体特征,因为志怪传奇小说的本质就在于“怪”和“奇”。有些评点则直接揭示了“作意好奇”的传奇文体特征。如《太平广记钞》卷五十八《薄太后庙》尾评:“相传《周秦行纪》乃崖州李相门客伪譔,欲以累奇章,想当然耳。”[2]1144同书卷八《织女婺女须女星》总评:“此皆小说家有托而云。”《情史》卷二十一《猿精》评:“纥子欧阳诵面似猴。长孙无忌嘲之曰:‘谁于麟阁上,画此一狝猴?’同时因戏作此传以实之。非实录也。”[3]824这些都表明冯梦龙对《太平广记》接受有着明确的小说文体观念导向。
冯梦龙的《太平广记》接受不仅巩固了小说固有的文体特征,而且还适时拓展了小说文体的新内涵。“三言”的话本小说创作虽不完全是接受《太平广记》固有题材的结果,但其序论基本上体现了冯梦龙对小说文体新旧观念的认识,是建立在《太平广记》接受为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冯梦龙认为,“小说”有“文人之笔”和“说书之流”的区分,前者是志怪传奇,盛行于开元以降,后者是通俗演义(包括说书话本),自宋代开始兴起。两者最大区别就是“文心”与“通俗”的差异:“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冯梦龙不仅动态地把握了小说文体的历史演变,而且以历史进化的眼光肯定和重视小说新文体,即通俗演义。其曰:“以唐说律宋,将有以汉说律唐,以春秋战国说律汉,不至于尽扫羲圣之一画不止,可若何?”“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这是时代的发展规律,应该“惟时所适”,而不应该食桃废杏。[7]2就小说内容而言,冯梦龙重视志怪传奇的“事奇”性,而强调通俗演义“事不必真赝”“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8]663这是对小说虚构理论的肯定和重视,体现了冯梦龙进步的小说文体观念。冯梦龙说“史统散而小说兴”,即指出了小说观念由“事真”到“事奇”再到“事赝”的历史演变过程。
冯梦龙的《太平广记》接受还宣扬和凸显了小说文体的社会教化功能。《太平广记钞·小引》曰:“宋人云:‘酒饭肠不用古今浇灌,则俗气熏蒸。’夫穷经致用,真儒无俗用;博学成名,才士无俗名。凡宇宙间龌龊不肖之事,皆一切俗肠所构也。故笔札自会计簿书外,虽稗官野史,莫非疗俗之圣药,《广记》独非药笼中一大剂哉!”冯梦龙认为,《太平广记》是一大剂“疗俗之圣药”,因此辑钞《太平广记钞》以充分发挥其社会教化作用。其友人李长庚也指出了冯梦龙辑钞《太平广记钞》的教化目的:“友人冯犹氏,近者留心性命之学,书有《谭余》,经有《指月》,功在学者不浅。兹又辑《太平广记钞》,盖是书闳肆幽怪,无所不载,犹龙氏掇其蒜酪脍炙处,尤易入人,正欲引学者先入广大法门,以穷其见闻,而后可与观《指月》、《谭余》诸书之旨也。”[9]2-3《情史》中冯梦龙更是提出“情教”说来凸显小说的教化作用。其曰:“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有《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非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亦因而导之,俾勿作于凉,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馀乎!”其辑选《太平广记》等小说文本,编纂《情史》就在于“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3]1-3“三言”等话本小说的再创作也有很强的社会教化意图。其曰:“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10]1具体而言,其义即是“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8]663。
冯梦龙之所以重视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是因为小说比经史更具“适俗”性,更能吸引广泛的读者群体,因而能更好地发挥社会教化作用。冯梦龙指出,“经书著其理,史传述其事,其揆一也”,皆“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但是“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8]663,且“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皆“不足以触耳而振恒心”。[10]1冯梦龙从与经史比较的角度来凸显小说的社会教化作用,这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对于“君子弗为”和“刍荛狂夫之议”[11]1745的传统小说观念进行了间接而有力的反拨和辨正。
当然,冯梦龙的小说教化观主观上是出于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因为冯梦龙有丰富的治经生涯,有根深蒂固的经国治世理想,他希望以小说教化来拯救晚明腐败政治和颓废世风,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小说的地位提升。因此,冯梦龙的《太平广记》接受对于小说的文体独立和地位提升都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