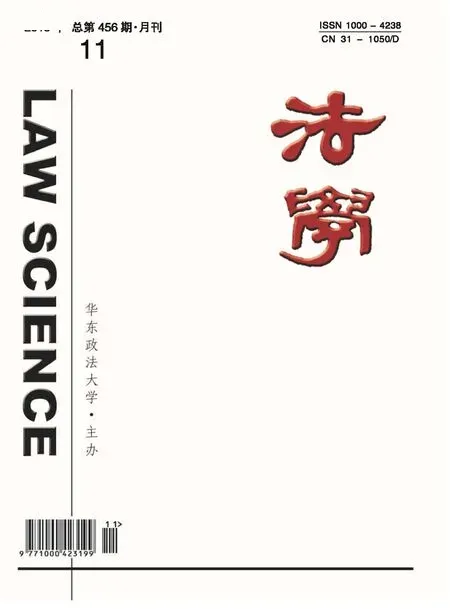著作权兜底条款的是非与选择
●刘银良
在著作权法下,作品类型和著作权是否需要“兜底”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一方面,作品是著作权(版权)客体,其范畴决定了著作权制度的“宽度”;另一方面,作者的著作权权项规定了作者可以控制其作品使用行为的范围,决定了著作权制度的“长度”。二者结合即可从权利客体和权利内容两个方面共同决定著作权制度的范畴。各国著作权法皆重视作品范畴和著作权内容界定,《伯尔尼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等国际著作权条约也是如此。自1990年立法伊始到其后两次修正,我国著作权法分别以“其他作品”和“其他权利”规定了开放式的作品类型和著作权,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作品类型与著作权“兜底条款”。〔1〕参见我国《著作权法》(1990年、2001年修正、2010年修正)第3条第9项(规定“其他作品”);《著作权法》(1990年)第10条第5项(规定其他权利);《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2010年修正)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其他权利”)。从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看,虽然措辞有所调整,但关于作品类型与著作权的兜底式立法模式似乎仍将持续。〔2〕参见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2014年)第5条第2款第16项、第13条第3款第10项。著作权法释义者和研究者亦对这一独具特色的立法模式表示支持或赞赏。释义者将著作权“兜底”解释为选择性兜底,认为它既可涵盖著作权法没有为作者明确列举的部分权利,也可拒绝“在一切情况下都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3〕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1~67页。有研究者认为著作权下的“弹性条款”是必要的,有助于解决立法预见性不足的问题。〔4〕参见李琛:《论我国著作权立法的新思路》,《中国版权》2011年第5期。也有研究者认为著作权兜底条款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5〕熊琦:《著作权法定与自由的悖论调和》,《政法论坛》2017年第3期。恰逢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之际,兜底的作品类型与著作权这一特色立法路径是否必要与合理值得探究。为重塑我国著作权制度,或需突破思维定式,检讨一些已被我国著作权法接纳但未必有充分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规定。本文认为,著作权兜底条款就是此类需要反思的规定,它或可成为改进我国著作权制度的支点。
一、作品类型“兜底”辨析
作品是著作权客体,对作品进行类型化规定也基本是各国著作权法的通行做法,但规定作品类型兜底条款却是我国著作权法的特色。该特色条款始终存在于我国著作权法文本。《著作权法》(1990年)第3条首先列举了文学、艺术、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类型,然后兜底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6〕我国《著作权法》(1990年)第3条第9项。著作权法释义者在解释为何规定该作品类型兜底条款时说明了两点理由:其一,伴随文化和科技发展可能出现的新的思想表达方式需要列入著作权客体给予保护,如计算机软件;其二,有可能“将现在尚未作为著作权客体的列入著作权客体”,如录音制品。释义者指出能否作为其他作品“必须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能由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以保证法制的统一”。〔7〕胡康生主编:《著作权法释义》,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著作权法》第一次修正案(2001年)和第二次修正案(2010年)对作品类型兜底条款未作任何修改。〔8〕参见我国《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2010年修正)第3条第9项。释义者的解释也完全相同。〔9〕同前注〔3〕,胡康生主编书,第21页。《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2014年)亦延续该作品类型兜底传统,只是将其修改为“其他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似乎不再强调须为法律或行政法规所规定的要件,从而可能为司法判定新作品类型预留一定的空间。〔10〕参见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2014年)第5条第2款第16项。
就作品类型兜底条款设置而言,它需满足必要性、可行性与合理性的论证,其中必要性与可行性又是合理性的前提和基础,合理性的判断亦需涵盖必要性与可行性,因为一项制度若无必要性或可行性,其合理性将难以得到支撑。著作权法释义者给出的上述两条理由看似仅涉及必要性,实则亦关涉可行性与合理性。然而本文认为,就我国著作权法下的作品类型兜底条款而言,其必要性、可行性与合理性皆难以成立。与释义者的解释不同,随着文化、科学和社会发展,无论是否需要将新的思想表达方式列入著作权客体给予保护,或者是否可能将现有的邻接权客体转为著作权客体,皆属著作权法修订所决定的事项,立法者将其纳入作品类型兜底条款,希望司法或行政机构藉由司法或行政程序予以决定,既无必要性,亦无可行性,合理性也难以保障。在释义者列举的两类著作权客体中,计算机软件由《著作权法》第一次修正案纳入著作权客体范畴,而录音制品至今仍属邻接权客体,这说明著作权法是否接纳新作品类型基本是由法律修订所决定,而非依赖作品类型兜底条款的适用。这意味着著作权客体范畴并非司法机构在案件审判中可决定的事项,尤其是在著作权法明确规定录音制品属邻接权客体的情形下,并无法院藉由司法程序认定其为著作权客体的可能性。而且现行规定亦排除了司法介入的可能性。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著作权法的作品类型兜底条款明确了必须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前提,并且释义者排除了法官的“扩张解释”,因此该条款的司法适用“存在障碍”。〔11〕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知民终第1404号民事判决书。
根据释义者的解释,著作权法的最初立法意图是将设置“其他作品”的权力保留在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制定机构即国家立法机关或国务院。然而,依据立法法的逻辑以及部门法的分工,除著作权法外,针对属于著作权法基础内容的作品类型或范畴,其他法律并无介入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合理性。在排除了其他法律介入的可能性之后,则只有行政法规介入的可能。这或可意味着在立法者或释义者的视野下,与著作权法修订相比,由国务院颁布行政法规可能是更为可行的“其他作品”设置办法。但在我国著作权法体系下,仅有在特定历史时期由国务院发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国务院令第105号)涉及作品类型。该行政法规分别规定了对外国实用艺术作品、计算机程序、编辑作品(实质是汇编作品)、录像制品的保护,包括将外国计算机程序作为文学作品保护以及将构成电影作品的外国录像制品作为电影作品保护。〔12〕参见国务院1992年发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国务院令第105号)第6~9条。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行政法规对新作品类型作出规定。可以理解的是,该行政法规赋予外国著作权人超国民待遇基本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过渡性措施,其内容完全可以为其后的著作权法修正案所吸纳。〔13〕参见管育鹰:《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其他法律或行政法规并未增设作品类型或将本来属邻接权的客体改变为著作权客体,也基本没有此种可能性。在著作权法并非长期不修订的情形下,将增设作品类型的权力保留给其他法律或行政法规并无切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其合理性亦难以得到论证。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拟删除“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定条件,从而将增设作品类型的权力交由法院,依据司法解释或通过具体案件审判决定是否需要补充新作品类型。然而本文认为,该规定同样缺乏必要性、可行性与合理性。在现实中,研究者或法官多以著作权纠纷案可能涉及“新作品”为由论证作品类型兜底条款的必要性,但相关案件涉及的作品是否属新作品类型尚需斟酌。例如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先后审理的“音乐喷泉案”就涉及“音乐喷泉”是否构成新作品的问题。当事人、研究者或法官对该作品性质认识不一。当事人曾将其登记为“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的作品”,也分别有研究者认为它属“视听作品”或兜底的“其他作品”。〔14〕参见袁博:《从西湖音乐喷泉案看作品类型的界定》,《中国知识产权报》2017年7月7日第10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涉案“音乐喷泉”或“音乐喷泉编曲”虽非著作权法规定的类型化作品,但该作品本身确实具有独创性,应当受到著作权法保护。〔15〕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海民初第15322号民事判决书。这相当于实质利用了作品类型兜底条款。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涉案音乐喷泉喷射效果的呈现是借助声光电等科技因素精心设计所展现出的艺术美感表达,它虽然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典型作品类型,但又是艺术领域的智力成果,具有独创性和可复制性,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法院继而认为涉案作品是由灯光、色彩、音乐、水型等多种要素共同构成的动态立体造型表达,具有审美意义,符合美术作品的构成要件,属于美术作品范畴。〔16〕同前注〔11〕。可见,与一审法院相比,二审法院将涉案音乐喷泉明确界定为美术作品,而非笼统地认定为作品,这相当于回避了作品类型兜底条款的适用,更为符合著作权法立法者或释义者的本意。
本文认为,所谓“音乐喷泉”其实就是相关音乐作品的“表演”而已,只不过该表演通过音乐协同控制灯光及色彩变换和喷水过程完成,其本身未必构成作品,就如音乐作品或舞蹈作品的舞台表演并不构成新作品一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该音乐喷泉是“将所选定的特定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与项目的水秀表演装置,根据音乐的时间线进行量身定制设计,设计师根据乐曲的节奏、旋律、内涵、情感等要素,对音乐喷泉的各种类型的喷头、灯光等装置进行编排,实现设计师所构思的各种喷泉的动态造型、灯光颜色变化等效果,利用这些千姿百态喷泉的动态造型与音乐结合在一起进行艺术形象的塑造,用来表达音乐情感、实现喷射效果”。〔17〕同前注〔15〕。该音乐喷泉所要保护的对象是喷泉在特定音乐配合下形成的喷射表演效果、具有美感的独特视觉效果。〔18〕同上注。法院叙述的显然就是该音乐作品的表演效果。对此亦可从“表演”与“作品”的关系加以判断,即设想在该“音乐喷泉”的表演中去除“音乐”,则该“音乐喷泉”可能成为无情感亦无灵魂的灯光及水声的机械混合,“美感”亦难以寄托。因此该案完全可以通过保护相关音乐作品或其表演实现保护该音乐喷泉之目的。即使如二审法院或研究者一样将该案所涉音乐喷泉认定为美术作品或视听作品,也都是在不适用“其他作品”条款的情形下就使纠纷得到解决。这有助于说明作品类型兜底条款的设置缺乏必要性。
亦可从比较法视角分析该问题。国际公约和多国著作权法一般在概括性的作品概念后列举确定的作品种类。如《伯尔尼公约》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应当包括在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中的任何作品,无论其表达方式或形式为何。〔19〕See Berne Convention,Article 2(1).可见《伯尔尼公约》虽然是以列举形式规定作品种类,但仍强调作品应属“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这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作品类型界定。各国著作权法在作品概念和类型化规定方面各具特色。美国版权法规定版权保护及于固定在任何有形表达介质上的原创性作品,包括文字、音乐、戏剧、舞蹈、图形图画或雕塑、电影等视听作品、录音和建筑作品。德国著作权法列举了7类作品,包括语言类作品(如著作、讲演和计算机软件)、音乐作品、哑剧(如舞蹈作品)、美术作品(如建筑作品、实用艺术作品及其草图)、摄影作品、电影作品、科技领域的示意图(如绘图、规划图、地图、图表或三维模型)。日本著作权法规定了9类作品,包括文字作品(如小说、戏剧、文章、讲演或其他文字作品)、音乐作品、舞蹈作品、艺术作品(如绘画、版画、雕塑和其他艺术作品)、建筑作品、地图和图形作品及模型、电影作品、摄影作品、计算机程序作品。〔20〕See 17 USC 102(a); Germany Law on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Section 2(1); Japanese Copyright Act,Article 10(1).可见多国著作权法皆未兜底规定作品类型,而基本是在作品概念或作品类型概念方面保持开放性。
多国著作权法并未规定作品类型兜底条款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只要作品概念或类型化的作品概念具有开放性,就可涵盖文学、科学或艺术领域的作品,鼓励人们自由创作,如日本著作权法规定的文字作品或艺术作品皆属开放性概念。其二,考察人类的创作或表达,无非是藉由文字、声音、图形、图像、动作等可为人们所感知的符号要素,创作出文字、音乐、图形、图像或其组合如美术作品、摄影作品或视听作品等,从而满足人们的文化欣赏或知识学习等需求,否则就可能既不利于作品创作,亦不利于作品传播。就此而言,现有作品类型或足可涵盖人类的创作。至少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修法期间),并无其他新奇作品类型产生之可能。或言之,著作权法并非长期不修订,而在下次修订前的数年间,人类未必创作出全新的作品类型从而难以为既有作品类型所涵盖。当然如果将来确有新作品类型产生且需要著作权保护,亦可通过及时修法因应这一需求。其三,作品的意义在于能够为公众获得、阅读或欣赏,如果一类新奇的作品难以为公众所获得、欣赏或使用,其存在难有社会意义,赋予其著作权亦无必然的理由。其四,著作权法并不需要涵盖人类在文学、科学或艺术领域的任何智力创造,亦无需涵盖其他领域的人类创造或创作,因为毕竟还存在其他的激励措施或市场激励机制。
有研究者认为,开放的兜底条款可能导致案件判决向一般条款逃逸,因此著作权法应尽量避免兜底条款。如果不能避免,则需利用立法技术,如诉诸“半兜底条款”,从而既能为技术发展和法律的扩张性解释和适用保留空间,又能防止或避免过度自由裁量和司法的不确定性。研究者还提出对待新作品的两项司法原则,即首先坚持“作品法定”,对于未被著作权法明确列入的新作品类型不予保护;其次法官可以或应该尽可能地将涉案作品解释为现有作品类型,而著作权法列举的具体作品类型已可提供“足够的裁量空间”。〔21〕参见陈锦川:《法院可以创设新类型作品吗?》,《中国版权》2018年第3期。本文认为,诉诸“半兜底条款”其实是诉诸开放性概念的路径,并且如果可将涉案作品解释为既有作品类型或其表演,它就可能并不属于新作品类型,如前述音乐喷泉。这亦表明在作品概念和作品类型概念皆具开放性的前提下,著作权法未必需要再附设作品类型兜底条款。还有研究者认为,如果“某种新表达毫无争议地符合作品要件,立法也没有排除保护,仅仅因为无法在现行法中归类而拒绝予以著作权保护”,则违反了作品类型的例示性原则。〔22〕参见李琛:《论作品类型化的法律意义》,《知识产权》2018年第8期。如前所述,人们在文学、科学或艺术领域的创作,无非是利用文字、声音、图形、图像或动作等因素进行创作,研究者所设想的“毫无争议地符合作品要件”且难以归入既有作品类型的“新表达”未必存在。在立法或修法实践中,为便于法律的适用与解释,可通过扩展概念开放性的方法涵盖可能出现的新表达方式,如前述日本著作权法对艺术作品的界定。
概言之,在作品类型兜底条款没有法律适用意义的前提下,将其长期规定于著作权法中,既会造成著作权法文本的繁琐与累赘,亦可能危及法律解释的逻辑,进而影响著作权法尤其是作品类型条款的司法适用,损及著作权法的确定性。作品类型兜底条款的合理性因而难以得到论证,著作权法无需为未知的作品类型预留空间。这意味着为弥补立法预见性不足的理由不能成立,著作权法下的作品类型并不需要“其他作品”加以兜底。至此可知,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类型兜底条款的设置并无必要性、可行性与合理性。
二、著作权“兜底”辨析
我国著作权法自立法伊始就为作者规定了开放的著作权,并在第一次修正案中正式设置著作权兜底条款。《著作权法》(1990年)将作者享有的作品使用权规定为以复制、表演、发行、改编“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23〕参见我国《著作权法》(1990年)第10条第5项。《著作权法》第一次修正案为作者规定了系统的经济权利(财产权),其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了“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24〕参见我国《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第10条第1款第17项。根据著作权法其他条款对该项权利的规定,可知该兜底条款规定的权利仅指作者享有的经济权利,不涉及其精神权利(人身权)。〔25〕参见我国《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第10条第2款与第3款、第19条、第25条第1款。《著作权法》第二次修正案对该内容未作修改。《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亦延续该开放式赋权传统,保留了著作权兜底条款。〔26〕参见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2014年)第13条第3款第10项。
针对《著作权法》第一次修正案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的“其他权利”,释义者表明它应该包括注释权、整理权、有线传播权、制作录音制品权、按照设计图建造建筑物等权利,但又申明它不能当然包括其他未明确列举的权利如追续权。〔27〕同前注〔3〕,胡康生主编书,第61~67页。关于设置该兜底条款的必要性及理论基础,释义者指出这是由于“作品的新使用方式层出不穷,无论如何都是列举不全的”。“理论上讲,作品有多少种使用方式,作者就有多少种权利。著作权立法有一个一般原则,凡是没有进行明文限制,其权利归作者。”“各国著作权法对作者权利的规定都是开放式的,不限于明文列举的项目。采用列举式,是为了更加明确作者权利,便于适用法律,未列举的并不表明作者没有这些权利。”〔28〕同前注〔3〕,胡康生主编书,第61页、第66页。
本文认为可将释义者的前述观点归纳为两点。其一,作者的著作权可覆盖所有作品使用方式,既包括著作权法明确列举的作品使用方式,也包括法律未明确列举乃至尚未出现的作品使用方式,即只要著作权法没有予以明确限制,相应的权利就属于作者,这是著作权法的一般原则。其二,各国著作权法都为作者赋予了开放式的著作权。易言之,除非著作权法予以明确限制,所有与作品使用相关的权利皆属作者。释义者的该解释应该是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次修正案设置著作权兜底条款的理论基础或立法指导。而且在司法实践中,释义者对《著作权法》及其修正案的这一解释亦为法院所信赖和引用。〔29〕同前注〔11〕。然而本文认为,释义者的该解释不仅与著作权法基础理论相违背,也与多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严重不符,因为很少有国家通过著作权法规定开放式的著作权兜底条款。鉴于释义者的该认识对于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正案关于著作权兜底条款如何修改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值得全面辨析。下文将首先考察若干代表性国家的著作权法(版权法或知识产权法典)文本,澄清是否有其他国家的著作权法赋予作者开放式的著作权,继而讨论是否存在释义者所称著作权法的“一般规则”。
美国版权法针对所有类型的作品或特定类型的作品,明确赋予版权人复制权、演绎权、发行权、表演权、展示权,还针对录音规定了数字表演权。〔30〕See 17 USC 106.英国版权法为版权人规定了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表演权、向公众传播权、改编权。〔31〕See UK Copyright Act (2003),Articles 16-21.澳大利亚版权法赋予版权人复制权、出版权(包括复制和发行)、表演权、向公众传播权、改编权和出租权。〔32〕See Australian Copyright Act 1968 (updated 2005),Article 31.这些版权法体系下的法律文本规定的权利皆具逻辑清晰、体系完整的特点,并且皆无兜底权利条款设置。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为作者设置了复制权和表演权。“复制”包括通过任何方法固定作品,使其可通过非直接方式向公众传播的情形。“复制”还包括对作品的演绎,建筑作品的复制包括重复实施设计图或标准规划图。“表演”包括以任何方法向公众传播作品的情形,例如现场表演、机械表演、远程传播等。〔33〕See Fren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de,Articles L122-1,L122-2,L122-3,L122-4.可见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下的复制和表演涵义广泛,皆具开放性,目的是有助于法律适应不断发展的技术与社会,进而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但它并未为作者设置兜底的著作权。基本属作者权体系的日本著作权法为作者设置了复杂的财产权体系,包括复制权、表演权、上映权、公开传播权、朗诵权、展览权、发行权、出租权、翻译权、改编权等,甚至规定了一般性的作者权利,但也没有设置兜底的著作权条款。〔34〕See Japanese Copyright Act (2015),Articles 17,21-27.
同属作者权体系的德国著作权法可能是有特色的例外,它也可能是我国著作权法下著作权兜底条款所借鉴的主要立法例。德国著作权法采取一般利用权加法定利用权的综合立法模式。一般利用权条款规定:针对作品有形方式利用,作者享有专有权,尤其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和展览权;针对通过无形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作者享有专有权,尤其包括朗诵权、表演权、放映权、公共传播权、广播权、音像制品传播权、广播和公共传播再现权。〔35〕See Germany Law on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Article 15(1)(2).法定利用权条款则详细界定了各法定利用权的具体内容。〔36〕See Germany Law on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Articles 16-22.关于一般利用权和法定利用权的关系,雷炳德教授等在其新版《著作权法》(2018年版)中认为:“司法无权在某种程度上任意承认无名利用权(所谓‘无名情形’)。相反地,如同其他法律上的规则范例那样,(法院)应当首先审查是否有相关法定利用权。根据法律规定在著作权权能之外的利用类型,不能简单地基于一般利用权而保留给作者。相反地,(法院的)解释表明,相关(作品)使用应当有意识地保持开放。”〔37〕Vgl.Rehbinder/Peukert,Urheberrecht und verwandte Schutzrechte,18.Auflage,C.H.Beck 2018,S.118.此前版本的相关叙述,可参见[德]M•雷炳德:《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可见,德国著作权法的特点是既为作者赋予多项类型化的法定利用权,也为其设置概括性的一般利用权,意图涵盖随着技术发展不断增加的作品利用方式,有助于司法适用。但在其一般利用权条款下,作者并非能够控制作品利用的每种方式或每个环节。或言之,一般利用权条款虽然具有开放性涵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涵盖新的作品使用方式,但其适用前提却是该使用方式可被解释为著作权法明确规定的法定利用类型,否则法院就可能将有关使用方式排除在作者著作权控制之外。这与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与列举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具体条款之间的关系基本一致,法院在具体案件中采取的法律适用规则也基本一致,即法院应尽量适用该法列举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条款,对一般条款的适用仅属特别例外。〔38〕参见李明德:《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几点思考》,《知识产权》2015年第10期。法院对著作权法下一般利用权条款的适用应更为审慎与谦抑。由此可知,德国著作权法下的一般利用权条款与我国著作权法下的著作权兜底条款具有不同涵义。
在国际公约层次也未见开放性的著作权兜底条款。除精神权利外,《伯尔尼公约》分别为作者设置了翻译权、复制权、表演权、广播权、朗诵权、改编权、电影改编权和公映权以及追续权,但并未设置“兜底权利”。〔39〕See Berne Convention,Articles 8,9,11,11bis,11ter,12,14,14ter.在其基础上,WCT赋予作者发行权、出租权和向公众传播权,从而补充和扩展了数字环境下作者的著作权体系。〔40〕See WCT,Articles 6,7,8.WCT强调缔约方应根据其法律体系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本条约实施,应有法律实施程序保障有效制止侵权,其中包括便捷的救济措施以威慑侵权,但并未规定或要求缔约方的法律设置任何兜底权利条款。〔41〕See WCT,Article 14.此外,TRIPS协议为作者规定了出租权,但也未要求WTO成员对作者的著作权实施兜底保护。〔42〕See TRIPS,Articles 9.1,10,11.欧盟相关法律也未要求成员国为作者提供兜底著作权保护,如欧盟《信息社会版权指令》仅赋予作者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复制权、向公众传播权、向公众提供权以及发行权,但并未设置著作权兜底条款。〔43〕See European Directive on the Harmonis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01),Articles 2-4.
可见,在国际法或比较法视野下,似乎并无国际条约或一些国家的著作权法赋予作者开放式的兜底著作权。无论是隶属于版权体系的美国、英国或澳大利亚,还是隶属于作者权体系的法国、日本或德国,虽然其立法路径不同,著作权体系各有特色,但其赋予作者的著作权体系皆呈封闭式,基本为作者设置了控制作品复制、发行、表演、传播和演绎的权利,但没有为作者设置开放式的兜底著作权。我国著作权法释义者所称各国著作权法皆为作者规定了开放式的著作权并不正确。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兜底条款虽然在表面上看是意图保护作者的“其他权利”,使其可控制针对其作品的非类型化使用,但其实质立法目的却可能是意图保护我国加入的国际著作权条约所明确规定但我国著作权法尚未明确规定的类型化权利,如(初始)有线广播权等。也有研究者认为,著作权兜底条款的范围应解释为我国加入的国际著作权条约已经规定但我国著作权法尚未规定的权利范畴。〔44〕同前注〔5〕,熊琦文。然而立法者或研究者应该认识到该“其他权利”路径并非履行我国在国际著作权条约下的义务的充分或必要且合理的方式。因为就该兜底条款而言,它也只能间接地用于维护著作权人的相应权利,而且不能确保该权利得到始终一致的保护,著作权人针对该权利的自由许可实践亦会受到不利影响。也似乎没有其他国家通过该路径履行其在国际著作权条约下的义务。
为何国际著作权条约和多国著作权法皆选择保护作者类型化的著作权,主要包括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传播权和演绎权,而不选择赋予作者开放式的兜底著作权?这应有深层次的原因,而非立法技术高低所能简单解释。那么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何在就值得分析,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在著作权法下作者有无开放式的著作权需要“其他权利”条款予以兜底保护。与此相关,有无释义者所称作者有权控制所有作品使用行为的“一般原则”的问题涉及著作权的正当性与权利渊源,对其分析需回归至著作权法基础理论。
三、著作权的正当性与范畴
我国著作权法的基本目标是促进社会文化和科学发展,其实现需依赖作品的创作与传播。〔45〕参见我国《著作权法》(1990年、2001年修正、2010年修正)第1条。这与多国著作权法(版权法)的基本目标相一致。美国国会在伯尔尼公约实施法立法报告中重申,立法机构必须衡量保护作者版权时所产生的公共成本和收益,版权法的基本目标并非奖励作者,而是保障公众获得或使用版权作品的利益。〔46〕See Berne Convention Implementation Act of 1988,H.R.Rep.No.609,100th Cong.,2d Sess.23 (1988).该论述阐明美国版权法的立法宗旨是通过赋予作者版权促进学术或知识发展。以著作权法的基本目标为指引就可探析著作权的正当性及范畴。
(一)著作权法定原则
作者的著作权属自然权利还是法定权利是著作权制度的基础问题,涉及著作权法定原则的适用范畴,亦涉及著作权法的立法或修法策略。〔47〕See Carys J.Craig,Locke,Labour and Limiting the Author’s Right: A Warning Against a Lockean Approach to Copyright Law,28 Queen’s Law Journal 1,40-60 (2002).一方面,作者的著作权尤其是精神权利具有自然权利属性,在理论上可契合洛克的劳动学说或黑格尔的人格理论。〔48〕See Paul Goldstein & P.Bernt Hugenholtz,International Copyright: Principles,Law,and Practice,3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6-7; Justin Hughes,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77 Georgetown Law Journal 287,296-366 (1988).但另一方面,在著作权法体系下,赋予作者精神权利或经济权利的却只能是一国的著作权法或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本,不可能是自然权利理论或学说。有研究者认为,在美国版权法框架下,国会是法定权利主义者,联邦法院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是自然权利论者,相应地,联邦司法判例是自然权利论的主要渊源,联邦版权法则集中体现了版权法定理论。〔49〕See L.Ray Patterson and Stanley W.Lindberg,The Nature of Copyright: A Law of Users’ Right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Athens & London,1991,pp.11-13,109-122.该总结未必准确与全面,因为如下所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亦是坚定的版权法定主义者。
本文认为,法学界对于著作权理论基础之争或可说明自然权利论和法定权利论皆有其合理性,否则它们也不会伴随著作权制度持续存在。它们可分别用于解释作者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从而使著作权法的理论基础与制度设置相协调。作者的精神权利(尤其是署名权)具有自然权利属性,是作者不可分割的权利,它源自作者对作品的精神创作。作者的创作性劳动使作品从无到有,使之成为人类文化的事实性存在,既符合洛克的劳动学说,又符合黑格尔的人格理论,即作者因创作作品而与之产生人格上的联系。〔50〕同前注〔48〕,Paul Goldstein、P.Bernt Hugenholtz书,第6~7页;同前注〔48〕,Justin Hughes文,第296~366页。从自然权利角度可容易理解我国著作权法关于作者精神权利保护期不受限制的规定,亦可理解为何日本著作权法规定作者的精神权利(人格权)仅属其个人,不得剥夺或让与,且在其去世后仍需得到保护而不得侵害。〔51〕See Japanese Copyright Act (2015),Articles 59,60.
作者的经济权利则源自实在法规定,其权利种类、范畴和侵权界定标准等皆由著作权法明确规定,属规范性权利,即仅为规范某种行为而设置的权利。作品虽然是作者的精神创作,但作者要在市场上获得经济利益,需要将作品(以其载体、表演或传播等形式)作为商品投放市场,为保障作者获得经济利益,著作权法需赋予作者专有的经济权利,藉此维护作者等著作权人的经济收益,此为功利主义立法路径。〔52〕同前注〔49〕,L.Ray Patterson、Stanley W.Lindberg书,第192~193页。由此可见作者的经济权利需附加保护期等限制。〔53〕同前注〔48〕,Paul Goldstein、P.Bernt Hugenholtz书,第7~8页。从作者经济权利设置的目的与逻辑亦可知经济权利的有限性。作为法定的规范性权利,设置经济权利的目的仅在于帮助作者控制作品的传播性使用以获得经济利益,其根本目的仍在于促进著作权法基本目标的实现。
由上可知,赋予作者著作权(包括精神权利)虽然可能在理论上具有自然权利基础,但赋予其实在法效力的只能是法定权利。此即著作权法定原则的根本体现。反过来可说明关于著作权的自然权利学说和法定权利学说在理论层次上并不必然矛盾。但在法律实施层次,著作权肯定是法定的权利而非自然的权利,即无论作者的精神权利还是经济权利皆属法定权利,其法律渊源仅是著作权法或其他制定法(包括法律、行政法规等)以及相应的国际条约。换言之,作者的著作权属于法定权利,其权利范畴与救济方式皆需由著作权法明确规定,如果针对某种作品使用行为著作权法没有赋予作者专有权,则该作品使用行为就可能属于自由使用或合理使用的范畴。〔54〕参见崔国斌:《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
关于如何认定版权是自然权利还是法定权利,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曾在1909年版权法立法报告中强调,美国版权法的立法不是基于任何自然权利,而是通过授予作者在有限期间内的独占权实现促进公共福利和科学进步的基础目标。立法者需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即版权法如何激励作者创作并有益于公众,以及授予作者独占权将如何不利于公众。如果条件与保护期适当,授予作者独占权对公众的益处可能超过其短暂垄断的消极影响。〔55〕See H.R.Rep.No.2222,60th Cong.,2d Sess.7 (1909).可见美国立法者对于版权法所涉及的各方利益冲突有清晰的认识,并试图藉由合理的制度设置达到各方利益平衡。按照立法者的理解,如果制度设置合理则版权制度可能对公共利益有利,如果制度设置不合理则公共利益可能受到消极影响,最终也将不利于版权法基本目标的实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在“索尼案”中引用该论述,说明其赞同该立法哲学。〔56〕See Sony v.Universal City Studios,464 U.S.417,429 (1984).
在“Twentieth Century Music Corp.v.Aiken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版权所有人法定垄断的有限范畴,和宪法要求的有限版权保护期一样,反映了针对公共利益冲突诉求的平衡:创造性的作品将得到鼓励和奖赏,但对私人的激励最终一定要服务于促进文学、音乐和其他艺术的广泛公众可及性。版权法的直接效果是保障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得到合理回报,但其最终目标则是激励为公共利益目的进行艺术创作。”〔57〕See Twentieth Century Music Corp.v.Aiken,422 U.S.151,156 (1975).相应地,美国版权法的唯一利益或授予作者专有版权的首要目标就是促进公众在使用作者的作品中获益。〔58〕同上注。在“索尼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申明,国会立法授予作者的版权既不是不受限制,其初始目的也非提供特定私人利益,相反它却是达到公共目标的手段,因为它意图用特别奖励激励作者的创作活力,从而在其独占性版权到期后公众可以获得其作品。美国国会在制定版权法时需要在作者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维持平衡,而公共利益则包括社会公众在思想、信息与商业自由流动方面的利益。〔59〕同前注〔56〕。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强调,美国版权法从未赋予版权人完全控制所有可能的作品使用行为的权利,而仅赋予其控制5种作品使用行为的权利,即作品的复制、发行、表演、展示与演绎,而且并非所有的作品复制行为皆可受到作者版权约束,如一些复制行为可能属于公有领域,其中包括个人为合理使用目的复制某作品。〔60〕同上注,第432~433页。易言之,并非所有未经版权人许可的作品使用行为皆属侵权,而只有落入版权法规定的专有权范畴的行为才属侵权。〔61〕同前注〔57〕,第154~155页;同前注〔56〕,第447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申明,美国版权法列举了版权人享有的数种专有权利,“如果一个人未经版权人许可以归属于这些专有权范畴的方式使用了版权作品,其就侵犯了版权”,但如果行为人是以法律没有列举的方式使用作品就不构成侵权。〔62〕See Fortnightly v.United Artists,392 U.S.390,393-395 (1968).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美国版权法以及宪法“版权条款”的阐述既体现了版权法定主义原则,也体现了版权法赋予作者专有版权的工具性,还当然提示了作者版权的有限性。可以说在美国版权法框架下,依据联邦最高法院的阐述,作者版权的存在仅有激励作品创作与传播的工具性涵义,其范畴仅限于版权法所明确规定的权利,而非无限的自然权利。
著作权法定原则并非单独存在的原则,它其实源于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立与制衡。著作权制度是重要的无形财产权制度,承载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重任,它需要在赋予作者专有权和保护公共利益之间维持平衡,其中包括明确界定作者著作权的范畴。由立法机构所主持的立法或修法过程本身就是利益的表达与平衡过程,各利益主体可充分表达其利益关切,立法者则需充分听取并吸收各方主体的合理诉求,使之固定在法律文本中,藉由司法程序等加以保障,以期实现著作权法基本目标。而在具体案件审理中,法官仅需面对双方当事人并作出法律解释与适用,因此与立法或修法相比,司法更可能缺乏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在此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下,著作权法定原则才得以存在并反过来体现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立与制衡。
本文认为,著作权法定原则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指作者享有何种著作权需要由著作权法明确规定,包括权利的种类、范围以及侵权界定标准等,这些事项不得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由法官自由决定。这是研究者通常讨论的权利法定的涵义。第二层涵义是指著作权法不得随意改变作者的著作权范畴,包括不得随意扩展或限缩作者的著作权,否则著作权法下的权利或利益平衡就可能被打破,著作权制度的合理性亦可能被摧毁。例如在数字传播时代,立法者不可能实质性地忽略或删除作者在电子传播环境下的向公众传播权。又如在充分论证前,立法者亦不可随意将著作权客体的范畴延伸包括人工智能生成物。第三层涵义是指立法者不得随意将应该由立法机构决定的事项交由司法(或行政)机构决定,否则也可能打破立法与司法(或行政)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从而可能损及相应的权利或利益平衡。鉴于作品是著作权客体,直接影响著作权制度的范畴,它应属立法者在著作权法立法或修法过程中明确规定的事项,而不应由立法者以立法预见性不足等理由交由裁判者在具体纠纷案件中决定。
质言之,著作权法定原则的第一层涵义在于约束司法行为,防止其无端侵入立法的权力范畴,进而打破在立法或修法中可维持的利益平衡。第二层涵义是约束立法的积极行为,防止立法者突破著作权法基本原则制定不合理的规则,进而打破著作权制度应有的利益平衡。第三层涵义是约束立法的消极行为,防止立法者将本应由其权衡和决定的事项交由裁判者在司法过程中决定,从而防止立法者擅自放弃自身职责。因此著作权法定原则的第一层涵义是司法涵义,后两层涵义则属立法涵义。这三层涵义相结合才可能形成完整的著作权法定原则,维护正当的著作权制度构造和运行,实现著作权法基本目标。我国著作权法研究者多关注著作权法定原则的司法涵义,而未意识到其立法涵义,有只见司法未见立法之憾。司法层次的著作权法定原则主要关注严格适用著作权法文本,其标准相对明确。而立法层次的著作权法定原则既需遵循著作权法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实现著作权法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又需敦促立法者正当履行其立法职责,防止其由于自身立法能力不足而制定不合理的著作权法,或将部分立法权让渡给司法机构,其最终目的仍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实现著作权法基本目标。著作权法定原则的三层涵义也是著作权法立法或修法需遵循的基本原则。
从著作权法定原则出发,可知在著作权法框架下,作者能够享有的著作权皆需明确规定,著作权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利就可能不是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无可主张享有。而且,立法者既没有权力赋予作者无限的著作权,使其可以控制针对其作品的所有使用方式或行为,也没有权力将其职责让渡给司法机构,因为此种制度安排可能侵扰公共利益,有违著作权法的基本目标,从而缺乏著作权法理论基础。由此可知,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兜底条款的设置既无必要的立法权力基础,亦无必要的正当性。
(二)著作权的有限性
著作权法理论需论证著作权设置的必要性与范畴。著作权法的基本目标是促进社会文化发展,这是衡量著作权制度要素合理性的标准。相应地,赋予作者著作权仅是为激励作品创作与传播继而实现著作权法基本目标的制度工具。这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制度工具仅有有限的价值,它应仅以维护实现著作权法基本目标为限,否则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其二,制度工具的价值不能与著作权法基本目标相冲突,否则就会丧失合理性或正当性,从而归于无效。这意味着作者著作权的设置与保护不能与著作权法的基本目标相冲突,否则就可能使著作权制度丧失合理性。
或言之,作者的著作权仅是著作权法为实现其基本目标设置的激励措施或制度工具,它因而具有有限性,应该受到约束。从表面上看,赋予作者著作权是为了保证作者在著作权市场的垄断性,藉此保证其经济收益,但在实质意义上,赋予作者著作权的价值仅限于激励作者创作作品所需要的范畴或程度,否则就会既无必要性,亦无合理性。〔63〕同前注〔49〕,L.Ray Patterson、Stanley W.Lindberg书,第192~193页。这与著作权法定原则相一致。从积极的角度看,作者仅享有有限的著作权,其权利的种类与范畴等仅以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为准,针对著作权法没有规定的作品使用行为,作者未必享有专有的控制权。而从消极的角度看,作者并不享有无限的著作权,并非有新的作品使用方式就会自动产生新型著作权。研究者之所以认为著作权兜底条款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其中包括弥补类型化著作权范畴的不足,就可能在于将著作权拟制为物权,然后再借助物权的特征等反过来界定著作权的特征。〔64〕同前注〔5〕,熊琦文。如前所述,并无充分的著作权法理论支持作者对其作品使用的绝对占有或控制,因为作为一种制度工具的著作权具有有限性,且需满足著作权法定原则。
为实现其基本目标,著作权法需要在各主体之间维系必要且合理的权利或利益平衡。作者在创作作品后可依法享有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藉此维护其精神权益和经济利益,但其权利却需要受到公共利益或著作权法基本目标的约束。如前所述,立法者既不能赋予作者过多的著作权,司法裁判者亦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随意赋予作者额外的著作权,立法者亦不可将其立法权随意让渡给司法或行政机构,而约束著作权法立法者行使立法权力或让渡立法权力以及约束司法裁判者适用著作权法的标准就是考察著作权法的基本目标能否得到有效实现。概言之,在著作权法基本目标的指引下,赋予作者著作权并非目的,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仅以实现著作权法基本目标为限,其存在与范畴亦需以工具合理性加以约束,如果对作者著作权的设置与保护超越了著作权法的基本目标,就无合理性或正当性可言。
(三)著作权法的适应性与确定性
在著作权法中是否设置兜底的作品类型或著作权条款,其实质是将增设作品类型或权利的权力保留给立法机构还是交由司法机构的选择,因而该问题也涉及法律的确定性与适应性。本文认为,如果将其让渡给司法机构,从表面上看著作权法可能具有较高的适应性,但法律的一致性、稳定性及确定性可能受到影响。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将该权力保留在立法机构,则可维系著作权法的相对稳定性或确定性,并且其适应性却未必降低,因为著作权法可通过开放性的作品类型或权利概念增加其适应性。从该角度看,较高的法律适应性未必能够成为支持设置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的理由。
如前所述,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的设置涉及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立与制衡。基于现代社会治理规则,在立法或修法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关切可能得到相对充分的表达,而具体案件的司法审判因为仅涉及双方当事人而缺乏此机制。虽然在个别案件中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可能有助于解决纠纷,但由此将一种新型作品纳入著作权法范畴,或者赋予作者额外的著作权,则未必有充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前述“音乐喷泉案”中,二审法院无需将所涉作品认定为新作品类型就能解决纠纷,如一审法院那样将它认定为新作品类型反而不符合法律适用的逻辑,亦可能带来不确定的法律适用后果。
基于权力分立与制衡原理,立法者的立法权不能随意让渡,否则就可能导致不一致的法律标准,带来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著作权法下各主体的权利或利益平衡既是著作权法的基础,也是保障著作权制度良好运行的机制。该机制需要以法律的确定性作为保障,其中尤以立法层次的确定性为重。在此基础上,再有法律适用层次的相对确定性,包括法院判决的相对一致性。如果在立法层次关于作品类型或著作权的范畴不具确定性,司法的确定性将无可预期,法律的不确定性就是当然的后果。立法者在著作权法中设置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的立法模式,看似赋予法院根据技术或社会发展随时纳入新作品类型或新权利的自由裁量权,但实质却是将法律的不确定性由立法传递给司法,立法者在放弃立法权的同时也为法律适用混乱埋下伏笔,进而导致司法的不确定性。这正是当前我国著作权制度的症结,包括著作权法律纠纷频发以及裁判标准不一等,从而导致著作权制度的高成本。或言之,兜底的作品类型或著作权条款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使司法取代了立法,进而可能导致权利或利益失衡,带来著作权法的不确定性。虽然从表面上看立法者设置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是弥补立法预见性不足的事前补救措施,属负责任之举,但在本质上它却可能属于立法者放弃自身职责的做法。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立法者或研究者没有认识到此种开放式作品类型或著作权条款的本质及其可能导致的法律适用后果。
综上,基于著作权法基本目标以及著作权法定原则,针对其作品利用行为作者只有有限的著作权,释义者所称作者的著作权可覆盖所有作品使用方式的著作权法一般原则并不存在。〔65〕同前注〔3〕,胡康生主编书,第66页。相应地,著作权法需明确规定作者的著作权,而不能随意设置兜底条款以解决想象的立法预见性不足等问题。结合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和修法历史,可知至少从表面上看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是积极乃至激进的著作权制度,更倾向于保护著作权人,而防御同业竞争者和作为消费者的公众。此种缺乏权力制衡或利益平衡机制的“亲著作权”立法倾向与策略已经导致我国著作权制度偏离社会现实,引发较多的侵权纠纷,著作权制度本身亦难以得到有效构建和良好运行。
四、著作权“兜底”的弊端
从立法目标看,著作权法设置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的基本涵义在于根据技术或社会发展,由司法机构及时补充应当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新作品类型或著作权。但需要辨析此种立法期待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具有合理性基础。如前所述,将一种新型作品接纳为著作权客体,或者赋予作者控制新型作品利用行为的专有权,皆因涉及广泛的权利或利益平衡而需要由立法者予以全面权衡,仅关注双方当事人利益冲突的个案判决难以具有此种能力。甚至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也是如此,因为司法解释仅是关于著作权法的适用性解释,因而难以突破著作权法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6年)曾规定,“在网络环境下无法归于著作权法第三条列举的作品范围,但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其他智力创作成果,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6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 11号)第2条。该司法解释自2013年1月1日起被废止。在司法实践中曾有法院认定“网页作品”的做法。〔67〕参见孙海龙、姚建军:《具有独创性的网站网页属于作品》,《人民司法》2009年第10期。甚至有法院在该司法解释被废止后仍然利用它判决案件,并得到二审法院认可。〔68〕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5)沪知民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然而上述规定却未必有法律依据,因为如果某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的“智力创作成果”无法归于著作权法明确列举的作品范围,则意味着它不属于类型化作品,甚至也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此时如果它具有独创性且可被复制,法院就认定其属于著作权客体而予以保护,法院的权力源自何处?法院此时已经不是在解释法律。该司法解释后被2012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决定》废止,在后者中并无对应内容,或可反映该规定缺乏必要性、合理性或合法性。〔6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决定》(法释〔2012〕 20号)第16条第1款。如前所述,该问题涉及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立与制衡,基于其各自的权力与职责,立法机构不得随意让渡其立法权,司法者亦不能随意超越司法权进入立法者的权力与职责范畴。
事实上,如果网页设计具有独创性且满足其他可版权条件,法院可以将它认定为属于既有作品类型或其汇编作品。但是如果某“网页”的确难以落入任何作品种类,它就可能难以构成作品,从而难以归属为著作权客体,相应的网页使用行为(如模仿设计)亦可能不属于著作权法所规范的范畴:它可能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行为,也可能属于自由使用行为。和其他知识产权法一样,著作权法也不宜造成限制竞争的效果,否则就可能不利于市场正当竞争行为。研究者多主张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兜底条款不宜滥用。“试图将(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凌驾于法律规定的具体事例,或者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行为纳入违反诚实信用的范畴,是没有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的。”〔70〕同前注〔38〕,李明德文。与之相似,著作权法下关于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需谨慎论证。
在司法实践中,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可能导致法律适用或法律解释的多样性。案情相同或相似的案件在不同法院可能有不同乃至相反的判决,法律适用的混乱和不确定性由此可致。甚至针对同一种侵权行为应该适用何种权利条款予以规制,不同法院亦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判决,侵权判定标准杂乱无章,亦可能导致案件判决向一般条款逃逸,架空本来可以或应当适用的既有权利条款,使相关权利无名化。例如在“央视国际诉百度和搜狐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被告未经许可通过互联网实时转播了原告的“春晚”节目,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广播权。〔71〕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20573 号民事判决书。二审法院认为初始传播采用无线或有线方式将导致相关转播行为分别属于广播权或“其他权利”范畴,为弥补立法缺陷,遂决定利用“其他权利”规制被诉行为。〔72〕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终字第3142号民事判决书。一些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审理指南或指导意见甚至明确指引此类案件判决适用“其他权利”条款。〔73〕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试行)》(2010年)第10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2011年)第18条。此种诉诸兜底条款的法律适用可导致著作权法的不确定性,进而引发较多的著作权侵权纠纷。可以想象,如果法院试图将所有互联网转播行为都归入“其他权利”范畴,就可能让本属广播权范畴的行为失去其控制,从而不利于权利人对广播权的许可或转让,广播权法定许可制度亦可能受到干扰。从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工看,法院此时已经实质上超越其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权限,进入立法权的领地,将本属广播权范畴的行为纳入“其他权利”范畴。由于其他法院未必遵循“其他权利”路径规范此类行为,法院裁判标准的不一致性由此而生。当然法院亦有为难之处,因为如上所述,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理论指导的错误和法律文本的缺陷,其司法适用混乱乃在预料之中。
在“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诉重庆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出版针对其英语教科书的同步教辅书,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应被视为对原告教科书“在著作权意义上的使用”,且不属于合理使用。〔74〕参见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3)渝中知民初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法官认为,关于行为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出版其教科书的同步教辅书的行为性质及规制著作权法并无明确规定,但是《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了“弹性”的“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从而可以“将该条没有列举而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纳入其中”。“允许他人根据自己编著的教科书出版同步教辅是教科书著作权人的一种重要财产权”,属于“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被告因而构成侵权,应承担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75〕参见张焱、周振超(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未经许可依他人编著的教科书出版同步教辅书构成侵权》,《人民司法》2013年第18期。该案的判决理由极为典型,它可揭示著作权兜底条款的部分弊端。本文认为,法官的上述认定至少有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就该案所涉行为来说,法院基本可诉诸复制权或改编权对此类行为予以规制,因为被告的行为基本属于演绎原告作品的行为。出版业界代表也有相同或类似观点。〔76〕参见张晓霞(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权部):《如何看待教辅与教科书之间的著作权关系》,《中国图书商报》2011 年8 月19日第S02版。其二,如果不将该行为视为受复制权或改编权控制,那么法官将许可他人针对其教科书编写同步教辅书视为著作权人的“一种重要财产权”并将其归入兜底的“其他权利”予以规范,是否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法官是否有权力通过简单论证就可判决控制一种作品使用行为的权利属于著作权人的“重要财产权”?答案均是否定的。
人们或有疑惑,在现实的著作权纠纷案中,对于一些诉诸既有作品类型或著作权权项本来容易得到解决的问题,为何当事人、法官或研究者总希望归因于“其他作品”或“其他权利”予以解决?这或许是“向一般条款逃逸”现象的体现,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受兜底条款的引导或诱导。可以设想在可实质援引既有作品类型或著作权权项处理相关纠纷案件的情形下,如果没有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法官是否可能更好地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从而实质性地降低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现实的法律实施情形或许与立法者、释义者或研究者的期望相反,即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不仅可能无益于著作权法适用,反倒可能引起法律适用的混乱,带来立法者预期不到的法律适用后果。
本文认为,著作权法立法者或释义者可能无意将著作权法规定的“其他权利”视为一种关于作者著作权的弹性规定,从而鼓励法官在案件判决中随意添加任何其认为合理的权利。然而在现实的案件判决中,确有法官将“其他权利”条款理解为弹性条款,进而将其作为赋予当事人其他“著作权”或“财产权”的法律依据之做法。从前述审理法官的分析来看,在审理中当遇到可能引起争议的边缘性行为时,法官可能倾向于适用“其他权利”条款,从而便于其在简单论证后就将可能受其他类型化著作权(如复制权、传播权或演绎权等)规制的行为乃至未必可能构成侵权的行为纳入“其他权利”条款规制的范围。这意味着在存有兜底条款的情形下,因为有节约论证、模糊论证或“正当化”论证其判决结论的实际效果,法院的判决可能呈现向一般条款逃逸的倾向,使之成为法律适用“洼地”。这属不当立法误导司法的例证。
在著作权法适用层面法官回避适用既有权利条款而诉诸兜底的“其他权利”条款的做法可能导致多方面的消极后果,其中包括导致法律适用标准的不统一以及法律的不确定性,因为不同的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对相关行为的性质可能有不同理解,其是否决定适用著作权兜底条款也因而具有不确定性。更有甚者,将本来不属于作者著作权控制的自由使用行为纳入“其他权利”的范畴更可能损及正当的市场竞争行为和公共利益。司法标准的不一致和法律适用的混乱可能打破立法过程中达成的权利或利益平衡,最终导致著作权法适用标准不确定、不统一等混乱情形,并引致著作权法律纠纷频发,进而损及著作权制度的合理性。这意味着设置有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的著作权法可能有较大的法律不确定性,而没有兜底条款的著作权法却可避免这些缺陷,并且在合理的立法技术支持下它也可拥有较高的适应性。
曾有研究者批评知识产权法领域的“法官造法活动”,认为它可能对知识产权制度造成危害,包括可能否定立法政策、打破利益平衡、威胁公共领域的行动自由以及法律统一性等,并认为要避免法官造法活动泛滥,需要采取的根本措施是“清除司法活动中的自然权学说的不良影响”,“强调知识产权法的独占适用”。〔77〕同前注〔54〕,崔国斌文。而且法院应正确认识和处理自己作为司法机构的角色与功能,不能擅自否定立法确定的基本原则,随意扩展知识产权法的客体范围。〔78〕同上注。然而本文认为,就著作权法下的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而言,却是立法者引导或迫使司法机构“造法”,相应的消极影响也由此而生,如打破了可能存在的利益平衡、损及公共利益和法律的确定性等。研究者还认为,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者也像美国立法者那样选择了功利主义的立法思想,我国著作权法是在“知识共享和自由竞争的主流原则”之外为著作权人提供有限的权利保护。然而研究者却仅引用了美国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论述。〔79〕同上注。这些论述并不能证明我国著作权法具有该特点。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至少从表面看,我国著作权法立法采取的是“亲著作权”的策略或路径,否则立法者就应该不会在著作权范畴方面设置兜底的“其他权利”条款供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选择适用。
结合我国著作权法的司法实践可知设置开放式的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并无充分的理由,甚至也没有必要的理由,相反该路径却有极为广泛的弊端,可谓有多害而无一利。难以想象此种兜底条款当初为何能够为立法者和研究者广为接受。想当然的或者具有良好愿望的立法不仅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反倒可能事与愿违,损及著作权制度的合理性。善良愿望并非都能得到良好结果,这在著作权法立法或修法中亦得到充分体现,立法者或修法者对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所可能带来的法律缺陷不得不察。
不同法律中不同性质法律规范的兜底条款可能具有不同逻辑。禁止性法律规范兜底条款的一般涵义在于预防对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的消极影响。例如刑法兜底条款的基本功能在于弥补刑法漏洞,预防和惩治新型犯罪,目标是维护公共秩序等社会利益,因而有“维护公共秩序”之底可兜。〔80〕参见王安异:《对刑法兜底条款的解释》,《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5期。再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兜底条款的涵义在于预防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而维护正当竞争秩序。〔81〕同前注〔38〕,李明德文。然而规定专有财产权的法律规范在赋权的同时,亦设定他人乃至公众的义务,因此需严格坚持权利法定原则,以免损及公共利益,如我国物权法就严格坚持物权法定原则,并无物权兜底条款存在。〔82〕参见《物权法》第5条、第7条、第8条。也可参见前注〔5〕,熊琦文。在著作权法中,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的本质是赋予作者著作权,从而可能损及公众的创作自由或获得信息的自由等。根据前述著作权法定原则,在著作权法下并无著作权需要开放式条款兜底。作者的著作权本来就应该为著作权法所明确规定,藉此为公共利益保留必要的空间,著作权法不能藉由兜底的权利侵扰公共利益的空间,进而损及著作权制度的合理性。
立法者或研究者可能认为,没有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著作权法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技术时代。但该主张并无必然的逻辑。第一,结合著作权法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人类对于作品的创作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似乎难有其他表现类型,即使有亦可通过开放性的作品概念或作品类型概念加以涵盖,或藉由及时的修法加以吸纳。第二,在相对概括和具有开放性的著作权概念下,除作品的复制、发行、表演、传播和演绎行为外,亦难有其他作品使用方式,因而无需赋予作者控制其作品使用的“其他权利”,即使将来有某种新型作品使用方式需要予以著作权保护且难以涵括在既有著作权范畴中,亦可通过修法及时吸纳。第三,无论国际公约,还是一些代表性国家的著作权法,均基本赋予作者特定的著作权,而未设置兜底的著作权条款。即使规定了一般利用权的德国著作权法,在其适用过程中,法院亦尽量将相关作品使用行为归属于受法定利用权所规范的使用类型中,而对于未被法定利用权涵盖的“无名利用”形式法院基本倾向于将其保留于公有领域供公众自由使用,而不是简单地赋予作者“无名利用权”。〔83〕同前注〔37〕,Rehbinder、Peukert书,第118页。这与我国著作权法下著作权兜底条款的开放性适用形成对照。概言之,基于开放性概念和合理的著作权法修法周期等因素支持,没有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并不必然导致著作权法适用僵化,也不会当然削弱著作权法在互联网技术时代的适应性。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著作权法对邻接权的设置并未采纳兜底形式,虽然作品的传播同样会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然而在著作权法的适用中封闭式的邻接权设置似乎并未产生不能适应技术与社会发展的现象。在同属知识产权部门法的我国专利法中亦无关于可专利主题或专利权的兜底条款,其法律适用未出现因立法预见性不足而导致无法可依的情形,也未出现各法院关于某种行为侵犯何种专利权的广泛争议。这与规定了著作权兜底条款的著作权法实施乱象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一种无形财产权制度能否充分激励作者或传播者创作或传播作品,或者激励发明人从事创造,与该制度是否提供兜底保护并无必然联系。对创作者、传播者或发明人的激励均应仅以促进其制度目标有效实现为基本判断标准。
针对我国著作权法下的著作权兜底条款,国内研究者多有支持乃至赞赏。甚至倡导知识产权法定的研究者也认可该兜底条款,认为它属于立法者通过法律授予行政或司法机构活动空间的情形,由此可化解知识产权法定主义所导致的制度僵化。〔84〕参见郑胜利:《论知识产权法定主义》,《中国发展》2006年第3期。有研究者认为,它契合了美国法或德国法扩张保护著作权的传统或历史趋势。〔85〕同前注〔5〕,熊琦文。也有研究者认为它是著作权法对本土司法实务经验的吸纳,如果“采用完全封闭式列举的方式规定著作财产权”则“显然忽视了司法实务累积的经验”。〔86〕同前注〔4〕,李琛文。本文认为,这些论证未必正确与合理,并且著作权法修法也不宜将因立法缺陷而导致的司法探索作为本土经验再加以吸收,否则可能带来更多的司法歧义。
综上,我国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的设置弊端众多。在立法方面,它既是立法惰性和立法技术阙如的体现,也忽视了著作权法基本原则,从而可能危及既有的类型化权利,使特定权利无名化继而不利于其许可或转让。在司法方面,兜底条款可能导致司法惰性,进而导致法律的适用标准不一致乃至相互冲突,从而造成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法律的不确定性亦可进一步破坏著作权法下的信赖利益,损及版权产业的可预期性。作者的著作权需要在著作权法中得到明确规定,无边界的著作权的信赖利益无从产生,也无从保护,从而既不利于作者等著作权人,也不利于同业竞争者和公众,因为公众自由使用作品的空间可能被挤压,公共利益可能受到侵害。立法惰性导致司法惰性,两者的叠加即可损及著作权制度的合理性,使之运行呈现较高成本,却没有必要收益。设置兜底条款还有违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立与制衡原则,并可能由此打破相应的权利或利益平衡。由于违背了著作权法基础理论且有违著作权法的基本目标,著作权兜底条款弊端重重。这可从根本上否定在我国著作权法下设置著作权兜底条款的正当性。概言之,著作权兜底条款的设置既无著作权法理论上的合理性,也无现实的必要性,还缺乏相应的权力制衡机制约束,并且我国著作权法司法适用该兜底条款的消极经验亦可构成不容忽视的否定性理由。
五、结论
被视为我国著作权法“特色”的作品类型与著作权兜底保护路径并无必要的著作权法理论基础,它已导致我国著作权制度的严重缺陷。根据著作权法定原则,立法者既没有权力赋予作者无限的著作权,使其可以控制针对其作品的所有使用方式,也没有权力将其职责让渡给司法机构,因此著作权法对著作权兜底条款的设置并无正当性。作者享有的著作权皆需明确规定,著作权法没有规定的权利就不属于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无可主张享有。此类著作权兜底条款有多害而无一利,其设置并无必要,是缺乏著作权法理论基础的错误立法选择。我国著作权法立法者或研究者之所以没有认识到开放式著作权规定的谬误,反倒认为其是合理乃至明智的立法选择,可能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不当的乃至错误的著作权法理论指导,如释义者所称作品有多少种使用方式作者就有多少种著作权是著作权法的一般原则。其二,对外国立法例粗浅乃至错误的认识,如释义者所称各国著作权法对作者著作权的规定都是开放式的。其三,立法者对其立法研究水平或立法技术没有信心,为防止立法预见性不足从而设置开放式的兜底条款以期填补可能的立法漏洞。其四,没有认识到在著作权法中设置著作权兜底条款与在其他法律中设置兜底条款可能具有不同逻辑。其五,没有认识到著作权兜底条款可能引起著作权法的适用混乱并带来较大的法律不确定性。
概言之,我国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类型或著作权的兜底条款似乎是针对臆想的问题提供的未必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解决方案。令人遗憾的是,该多余且无益的作品类型或著作权兜底条款却在我国著作权法下长期存在,其消极涵义不容忽视。著作权法基础理论或著作权法定原则并不支持兜底的著作权保护,赋予作者有限的著作权仅是著作权法为实现其基本目标而设置的制度工具,作者的著作权无需兜底保护。我国著作权法采取的“亲著作权”立法策略既违背了立法与司法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也不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充分的合理性,且已带来我国著作权法司法标准的冲突与混乱。此等教训务必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中予以吸取,藉此回归著作权法定原则,遵从立法与司法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维护著作权法适用的一致性和确定性。本文建议删除此类兜底条款,并以开放性的概念作为相应的修订措施。作品类型与著作权设置直接涉及著作权法的权利哲学,也与著作权法的立法目标及制度设置休戚相关,务必审慎对待。想当然的立法措施需要摈除,从而有利于构建更为合理的著作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