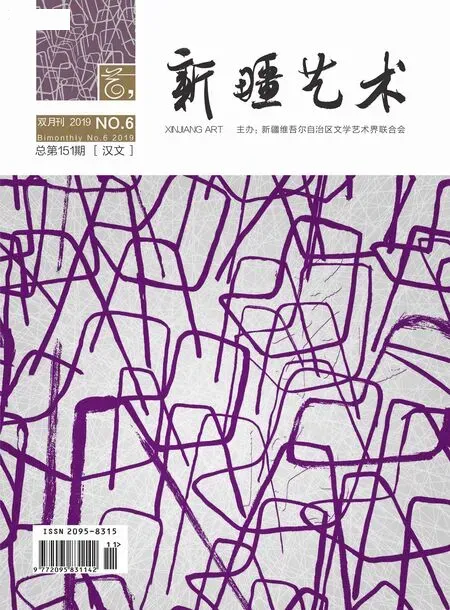辨析唐诗中西域歌舞的古今嬗变
□
唐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之一,唐诗是中国人精神基因的千古传奇,唐诗更是泱泱大气的盛唐气象。而唐诗中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让我们的心境一下子拉到了西域的辽远、粗犷、超拔、雄浑、大气之中,当然在唐诗中我们可以更多地找寻到西域歌舞的雪泥鸿爪、异域风情和人文情怀,也可以循着唐诗的印记贯通新疆歌舞的前世今生。
唐诗中的西域歌舞不仅仅是文化现象,更是当时海纳百川、融汇万千的盛唐气象的直观体现。“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更是我国文化最隆盛辉煌的时期,也是音乐舞蹈艺术高度繁荣发展的时期。唐初,西域商人和艺人大量涌入长安,西域文化习俗随之传入,以西域乐舞为先导的西域艺术,以其浓厚的异域情调,新颖独特的风貌,进入中原汉文化领域,冲击和影响着中原朝野固有的文化观念和精神生活。如果说黄钟大吕是唐朝的高雅文化,那么西域歌舞可谓是唐朝的流行文化。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旧唐书·礼乐志》“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新唐书·西域传》载:龟兹“俗善歌乐”,于阗“人善歌舞”;康国“好歌舞于道……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泼为乐”。嘎斯……戏有弄驼、狮子、马技、绳技,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说“屈支(龟兹的另译)……管弦伎乐,特善诸国。”《酉阳杂俎》前集卷四载“龟兹国,元旦斗牛马驼,为戏七日……婆罗遮,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为戏。”唐代对乐舞的重视程度达到极致,朝廷设置专门的乐舞机构教坊,初唐乐部编制基本上沿用隋制,隋宫廷乐部定为九部乐,即:《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至唐代高宗时,在隋九部乐基础上加上《高昌乐》,组成十部乐,这十部乐中有七部与西域有涉:龟兹、疏勒、高昌、安国、康国五部源于西域,西凉乃变龟兹之声而为之,天竺经由西域东来。

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胡旋舞摹本
这些记载西域歌舞的历史文献在唐诗中都有形象生动的体现。唐诗与西域歌舞在历史的时空中风云际会、交相辉映、水乳交融迸发出跨越千载的神韵和风采,一个热情奔放、一个摇首撼目,一个恣意汪洋、一个轻拢慢捻,一个雄浑大气、一个风情万种。唐诗自有气韵生动的一番意境,不但韵律美,而且还可以直观地勾勒出一番生动活泼的景象,让人读之仿佛置身于其情其景,流连忘返。诗画同源。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唐诗虽不能如舞谱那样记录舞蹈,却可以形象生动地描述舞蹈动作,还原它的舞蹈律动,描绘它的形态、风韵。无论是面部表情、举手投足、节奏急缓、艺术结构等等。具有高度艺术表现力的唐诗,描绘唐代西域舞蹈律动,不仅接近实际情况,而且传达出当时的风范、韵味、情调和现场产生的艺术感染力,当我们追摹唐代西域歌舞律动的艺术魅力时,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唐诗提供的线索和情景,比照龟兹壁画、敦煌飞天壁画的千古风韵,描述更具有真实性、可视性和恢复西域舞蹈原貌的可行性。尤其在描写西域乐舞典型的苏幕遮、狮子舞、胡腾舞、胡旋舞、拓枝舞时,令人如见其形、如闻其音、如述其情。体现了古代西域歌舞高超的技艺和水平,与泱泱唐诗一起光耀华夏千载。在此通过一些唐代诗人的诗章中的西域歌舞从形、音、情的动态描述可以更好地辨析出古代西域歌舞同现代新疆歌舞的历史渊源,探究他们之间的根脉相承的关联,更是解码新疆歌舞传承的一把密钥。

现代维吾尔族顶碗舞
如今流行在内地的泼水节、狮子舞是从新疆古代龟兹(现库车)一带传过去的,唐段安节的《乐舞杂录》将其列入龟兹部,称其乐舞“戏有五方狮子,高丈余,各衣五色,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这在唐诗中有着详尽的描写和体现,例如唐代诗人张说《苏幕遮》写下了《亿岁乐》歌词四首:“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眼紫髯须。闻道皇恩遍宇内,来将歌舞助欢娱。绣装帕额宝花冠,夷歌妓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阴气,不虑今年寒不寒。腊月凝阴积帝台,豪歌急鼓送寒来。油囊取得天河水,将添上寿万年杯。寒气宜人最可怜,故将寒水散庭前,惟愿圣君无限寿,长取新年绩旧年。”该诗体现了苏幕遮这一流行于古代西域乞寒戏传入长安后,让这个原先祈求丰沛的天山雪水灌溉农田,来年丰收的仪式,演变演绎成称颂皇恩浩荡的庆典仪式。其中“琉璃宝眼紫髯须,绣装帕额宝花冠”的诗句形象地把狮子舞的造型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跟我们如今的狮子舞如出一辙,“豪歌急鼓送寒来”,让人仿佛看到激越的鼓声中,狮子腾挪起跃的姿态,“油囊取得天河水”,“故将寒水散庭前”描述了乞寒戏中用油囊盛水相互交泼的情景,活脱脱地把一个祥瑞活泼的狮子展现在世人面前,古代龟兹狮子舞喜庆、欢快、吉祥的表演风格在当时可谓是风靡大漠塞外和中原大地,唐朝时常派遣龟兹乐队到四邻各国、各民族地区去巡回表演,并在外交礼仪活动中将《龟兹乐》做为厚礼相送馈赠。唐中宗景龙三年时,吐蕃使纳贡并请婚联姻,唐朝金城公主前赴和亲,随嫁的就有一部《龟兹乐》。如今云南的泼水节即是源于苏幕遮。新疆谓之“乞寒泼胡”,云南叫泼水节(“爽琅目”),据《新唐书·南蛮列传》载,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南诏(今云南)王皮逻阁遣子凤伽异赴长安,返回时唐玄宗赐给“胡部、龟兹音声二列”,龟兹乐队和乐舞由此直接而完整地传到云南。傣族“以清明节前数日泼水,男女以竹筒汲水,互相泼洒为乐”,“互相泼洒,以湿衣为乐”。傣族泼水节跳孔雀、啄木鸟、马鹿、大鹏、猴等舞蹈时,间以“戛批鲁批派”(魔鬼之舞)。这些情形同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1903年带走库车出土的一个木制面具和一个绘有《苏幕遮》乐舞图的舍利盒十分相似,据考证正是玄奘到库车之前(大约六至七世纪)的遗物,这件艺术品成为《苏幕遮》歌舞戏的形象物证和最好脚注,画卷沿圆形舍利盒展开,由一女一男两个手持舞旌者为先导,三女三男六个手牵手的舞蹈者和两个持棍独舞者,均带各式假面具,他们依次作披方巾的武士,身着甲胄的将军,戴竖耳勾鼻的鹰头、浑脱尖帽的人面以及猴面长尾的假面动物等。这些习俗虽经千年,却在不同的地域空间被兼容并蓄、发扬光大,成为中华不同地域民族文化融合的千古典范。

新疆罗布人狮子舞表演
之前前秦大将吕光把龟兹乐舞从龟兹带到凉州,融汇了中原音乐及其他少数民族音乐,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颖别致,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音乐新品种——《西凉乐》,《隋书·音乐志》曰:“此声所兴,盖符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有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也,”由此苏幕遮及《狮子舞》而成为《西凉乐》的组成部分,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新乐府·西凉伎》写到狮子舞的情形则有一种戏剧表演的意味。“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讯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双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词。道士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须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绝归不得。泣向狮子涕双垂,凉州陷没知不知?狮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贞元边将爱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娱宾犒士宴监军,狮子胡儿长在目。”诗歌中“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讯毛衣摆双耳”详细描述了西凉伎扮演狮子舞的外貌特征,仿佛千年的狮子舞栩栩如生地跃然眼前,于当今毫无任何差异。在这里狮子舞更有歌舞戏的特征,我们仿佛在诗中看到这只狮子更像是一个思乡的游子,当跳狮子舞的胡儿听说回安西老家的路被隔断时,表演的狮子向着西边看去,长长地哀嚎一声饱含着对故乡的无限思念,让观看的人悲从心来。以至于“贞元边将爱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
唐诗中狮子舞的情、形的描述在新疆的历史文物上也有所体现,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36号墓的出土文物中,有一组乐舞百戏的彩色泥俑,其中就有一彩色狮子舞俑:高12厘米,长10厘米,狮子头部与身躯为一整体空壳,壳底边厚约五毫米,用掺有毛绒的细泥塑成。躯体下露出四肢,明显为两装扮人的足形。泥俑造型优美,栩栩如生。(《中国舞蹈卷·新疆卷》p82页至83页)
后随着伊斯兰教进入西域,因在佛经中经常用狮子比如佛、佛法。在佛教艺术中,狮子既为万兽之王,具有辟邪护法之作用,狮子神格化后,以神兽、灵兽、仁兽色彩在佛教造像中出现,也做为佛的化身被崇拜信奉,狮子在佛教艺术造像中成为首先推崇者,在西域普遍盛行的狮崇拜为西域伊斯兰教政权所不容,盛行西域千年的狮子舞被取缔禁止,而在西域偏远人迹罕见的伊斯兰势力影响式微的地方得以保存下来。现在在新疆和田、于田等边缘地区尚有此舞的遗存,维吾尔人民称这种舞蹈为“西尔舞”,舞者为两个男子,头戴特制的狮头,翻穿染制的彩色皮袄、裤,装扮成狮子的形象,合着鼓点做一些表现狮子的神态和习性的基本动作,如“搔痒”、“舔毛”、“抖毛”或“蹦跳”等,音乐采用当地维吾尔族民间乐曲(《中国舞蹈卷·新疆卷》p 83页)。狮子舞“还流布于尉犁县尉犁镇、墩阔坦乡和喀尔曲尕乡等地的维吾尔族聚居区,在若羌也有流布,……通常在聚会、娱乐、游戏时为助兴而表演。狮子舞有专门制作的道具,由一人披挂髯须和铜铃作为装饰,随着苏乃依奏出的旋律,踏着鼓点,模仿狮子的行走、嬉戏、打斗、欢腾等基本动作,无固定的模式,由表演者即兴发挥,动作巧妙幽默,观者兴趣盎然。”(《中国新疆民间文化遗产大观》p85页)如今狮子舞遍及全国各地,南北都有,甚至远至西藏,已成为中华民族避邪免灾、吉祥纳福不可或缺的的形式,形成了北、南两方风格迥异的两种“狮舞”形式,形态可掬、温文尔雅,以表演戏球,踩踏板与人亲昵似猫的“文狮”和矫健迅猛、虎视眈眈、以高难度杂技性表演为主的“武狮”。

维吾尔族民间舞《纳孜库姆》
唐朝著名健舞《胡腾舞》,从西域石国(唐属安西都护府管辖,故址在今中亚塔什干一带)传入中原,其舞蹈风格以迅疾敏捷,腾踏跳跃的步伐,举止轻飚、惊人目眩的舞蹈技巧,撼头弄目、情不自己的浓烈情感,体现了古代西域舞蹈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唐代诗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毛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葡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跳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瞠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诗中指出了胡腾舞的出处石国,诗歌中的“蹲舞尊前急如鸟”,用飞鸟的形象来比拟屈膝下蹲,步伐急速变换的舞蹈动作,至今,新疆塔塔尔民间舞蹈,维吾尔族民间舞《纳孜库姆》还保留着类似的动作,还有高难度的腾空技巧,诗句“跳身跳毂宝带鸣”,舞者纵身腾跃,出现如车毂旋转似的动态,鼓是车轮中心的圆木,腾空完成类似毂的旋转的舞蹈动作,和维吾尔民间麦西来甫中使用的旋子带空转的技巧如出一辙,这种舞蹈在现代维吾尔创作舞蹈中多有体现,“弄脚缤纷锦靴软”,体现了胡腾舞高超的脚步技巧,脚步动作快捷,脚步的着力点轻巧灵活,好像柔软的锦靴支撑着舞者旋转跳跃。“横笛琵琶遍头促”形象地描述了横笛和琵琶从头到尾激越的演奏风格,“酒阑舞罢丝管绝”,形容了当舞蹈停止的时候,乐器的声音也戛然而止,这都和现今的维吾尔乐舞的特点十分吻合。
李端《胡腾儿》:“胡腾儿时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诗歌中“帐前跪作本音语”这种舞蹈前的仪式在今天新疆维吾尔族很多民间舞蹈中,还可以寻到它的踪迹。一些传统的维吾尔族男子和女子独舞表演,依然保留着以致礼为先导的特定方式,显然它们之间存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忽而前俯,忽而后仰的“醉却东倾复右倒,双靴柔弱满灯前”欢喜若狂的表演神态,跟刀郎麦西来甫的“且克特曼”部分很相似,首先男女舞者起舞,先面对面向右走斜线,做“两步一跺”的动作,互换位置,再向左走斜线回原位,“两步一跺”即每拍向前一步,第三拍吸腿跺步。这一部分音乐节奏沉稳古朴,舞蹈动作刚健有力,上身稍带晃悠。而“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跟刀郎麦西来甫中的“赛勒凯”部分,“色利尔玛”部分一样,都是音乐节奏欢快跳跃,舞者队形变成一个环形的大圆圈边舞边疾走如飞,而现在维吾尔族的《萨玛瓦尔舞》《击石舞》《盘子舞》。哈萨克《卡拉角勒哈》,蒙古族《萨吾尔登》也都有类似的舞蹈动作和环状队形。
新疆克孜尔千佛洞69窟的一副伎乐图就很有代表性,舞蹈姿态自然弯曲的形体线条,明显透露出直而硬的两臂曲线,体现着一种遒劲古拙的气势,特别是躯干部的扭曲,胯部的耸出,富有节奏感的跃动的舞步,显现出西域舞蹈所具有的三道弯式的典型姿态,揭示出整个肢体律动深含着生命的意蕴,倾吐着不可抑制的激昂情怀。不难看出,或踊、或跃的肢体动态,跃动不已的节奏韵律,是早期龟兹舞蹈和西域舞蹈肢体律动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豪放的西域人“情发于中,不能自止”的民族情感的外化。河南安阳县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瓷扁壶上,有一副反映胡腾舞的舞蹈图象,黄釉瓷扁壶上的舞乐图完全是龟兹乐舞的历史再现,图中的男性表演者,鼻高目深,具有西域人的外貌特征。一人奏琵琶,一人吹横笛,一人击铜钹,一个双手欲拍掌。舞蹈表演着立于四人中间,正挥动两臂踏步而舞。不但舞蹈动作是龟兹舞蹈的典型风姿,服饰装扮也完全是龟兹式样,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个双手拍掌的人物造型,拍掌是龟兹舞蹈的固有形式,即所谓“抃,击其节也,情发于中,手抃足舞,抃者因其声以节舞”(《通典》卷一百四十二)这个双手拍掌的人,并非只限于拍掌击节的职能,他分明是一个为胡腾舞伴唱的歌者。歌与舞的结合是古代西域舞蹈的一个突出美学特征,这一美学特征同样体现在胡腾舞的表演形式中。胡腾舞表现出龟兹舞蹈的典型特征,这雄辩地证明了胡腾舞是古代西域各地普遍流行的舞蹈类型,它是古代西域各民族的共同创造。
大数据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实现应用信息的快速转发与海量汇总,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传输大量信息。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各种应用消息也得到了很细致的分类与汇总,使人们得到的各种信息更加详细、准确,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大数据中心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将把智慧城市建设带入“共享时代”,实现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卫生设施建设的城市共享。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下建设新型民主保障基础设施,实现多个渠道的资源共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建设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能源的多级利用[2]。

哈萨克族舞蹈《卡拉角勒哈》
唐朝著名健舞《胡璇舞》,发源于康国、史国、米国(均在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一带,《新唐书·西域传》记述了这几个城郭邦国曾向唐廷献送胡璇女之事,隋、唐《九部乐》《十部乐》也均有《康国乐》“急转如风,俗谓之胡璇”的记载,可见这种舞蹈的动作特点以急速连续旋转为主,节奏鲜明,轻快敏捷。
白居易《胡璇女》:胡璇女,胡璇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赚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己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这在新疆各民族舞蹈中都有体现。从《赛乃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维吾尔人每当打起手鼓,会随着手鼓的节奏翩翩起舞。胡旋舞,左旋右旋,和如今的维吾尔舞蹈特点很相似,“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己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在《刀郎麦西来甫》最后一组动作《色利而玛》部分,舞者保持大圈队形,一手握拳高举过头,小膊稍弯,各自不停地踏步旋转。凡亲自置身于刀郎舞蹈海洋中的亲临其境者,都会体会到对于《色利尔玛》这部分舞蹈来说,“左旋右旋不知疲”是多么生动的写照。塔吉克《鹰舞》,随着鹰笛的节奏,两人徐展双臂,如双鹰盘旋翱翔,随后节奏转快,两人互相追逐嬉戏,忽而肩背近贴侧目相视,快步行走,又蓦地分开跃起,如鹰起隼落,由低向高拧身旋转,扶摇直上。在旋转或是在前进时,舞者随着曲调的节奏不停地一上一下抖动,隐约可见古代西域的“胡旋舞”技艺的遗姿。

哈密《赛乃姆》表演

塔吉克鹰舞
岑参《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旋歌》: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毛毛,试舞一曲天下无。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且叹。慢脸娇娥纤复秾,轻罗金缕花葱笼。回裾转袖若飞雪,左旋右旋生旋风。琵琶横笛和未匝,花门山头黄云合。忽作出塞入塞声,白草胡沙寒风风。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见后见回回新,始制诸曲不可比,“采莲”,“落梅”徒聒耳。世人学舞只是舞,姿态岂能得如此。
诗歌中“此曲胡人传入汉”交代了胡璇舞由胡人传入到中原地区的背景,而“回裾转袖若飞雪,左旋右旋生旋风。琵琶横笛和未匝。”中的“回”、“转”、“旋”突出胡璇舞的特点,回环转动裙子,挥舞起袖子,仿佛满眼都是雪花在飞舞,左右旋转的身形好似一股转动的旋风。琵琶和横笛的乐音伴奏还未过一遍,花门山顶的黄云因之已合拢到了一块,音乐中忽然奏出《出塞》《入塞》两曲,顿时身边好像响起了吹折白草、卷起胡沙冷飕飕的风声,就算是《采莲》《落梅》也不过是烦扰耳朵的噪音。其形、音、情令人目不暇接、身临其境、叹为观止。如今在新疆的《鼓舞》、吐鲁番《火舞》中这种疾步旋转的动作仍然可以让人窥见唐诗中的如此景象。
元稹《胡璇女》: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璇,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胡璇之义世莫知,胡璇之容我能传。蓬断霜根羊角疾,竿载朱盘火轮炫。骊珠迸弥逐飞星,红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嗡旦海波,回风乱舞当空散。万过其谁辩始终,四座安能分背面。才人观者相为言,承奉君恩在圆变。诗人元稹更是把胡璇舞描述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用“火轮”、“飞星”、“流电”这类形容词把胡璇的艺术魅力和舞蹈特色表现得形神兼备,这在当下新疆创作舞蹈《带羽毛的姑娘》《顶碗舞》中也都活灵活现的体现。
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中也保存了一些发带飞扬,衣裙飘起、正在旋转起舞的人物形象,可被视作《胡旋舞》在佛教壁画中的反映。现在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的民间舞蹈中,都仍然保留着急速旋转的特点,伴奏也以鼓(如手鼓、纳格拉、冬巴鼓等)为主,舞者动作急转起伏,欢快热烈,从音乐舞蹈诸方面看,可以推想唐代自由、奔放、洒脱胡璇舞的风貌。

吐鲁番火舞
唐代著名“健舞”《拓枝舞》。公元五六世纪传入中原,原为女子独舞。传入中原后,深受各阶层欢迎,宫廷教坊舞伎、营伎、家伎等竞相学习,后还出现了名曰“拓枝伎”的专门艺人。白居易《拓枝伎》“平铺一合锦筳开,连击三声画鼓催……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拓枝来,带垂细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维吾尔族民间舞蹈《花腰带》有应鼓起舞的习俗,随着手鼓鼓点的击打,女子随着鼓点有节奏的翩翩起舞。“带垂细胯花腰重”,把西域女子的柔美的姿态展现出来,新疆舞蹈《铃铛舞》有很多拓枝舞的身形。章孝标《拓枝》:拓枝初出鼓声招,花铀罗衫耸细腰,移步锦靴空绰约,迎风绣帽动飘飘,亚身踏节鸾形转,背面羞人凤影娇,只恐相公看未足,便随风雨上青霄。新疆舞蹈《朱拉》把诗句“花铀罗衫耸细腰,移步锦靴空绰约,迎风绣帽动飘飘,亚身踏节鸾形转,背面羞人凤影娇,”体现得惟妙惟肖。
我们在研究唐诗中西域歌舞嬗变中有一个贯穿千年的历史现象对这一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斯兰教传入西域的结果是使西域各民族开始了伊斯兰化进程,同时也促进了西域伊斯兰教地区各民族的突厥化或回鹘化过程。正是在一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回鹘不断融合其他民族成员,发展壮大,最终形成近代的维吾尔族。11世纪以后的喀什噶尔、于阗、库车等地,15世纪以后的焉耆、吐鲁番、哈密等地居民大都改信伊斯兰教。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中有关伊斯兰教的词汇进入维吾尔语中”(《新疆史鉴》马大正著,P341页)。
古代西域伊斯兰政权对西域的文字吐火罗语、佉卢文、粟特文、汉文、佛寺、建筑、佛像、壁画、佛教文献书籍资料、乐器、音乐舞蹈等,进行了彻底破坏和改造,造成西域文化艺术断层和变异,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新疆。
譬如汉唐时期龟兹音乐的乐器相当丰富,它把各方面的优秀乐器汇集在自己的乐队中,龟兹音乐使用的乐器有竖箜篌、凤首箜篌(或称弓形箜篌)、曲颈琵琶、五弦琵琶、阮咸等弹奏乐器;横笛、筚篥、萧(包括排箫和洞萧)、笙、贝、铜角等吹奏乐器;羯鼓、答腊鼓、毛员鼓、鸡娄鼓、腰鼓、手鼓、大鼓、铜钹、碰铃等打击乐器。上述乐器的来源是多方面的,阮咸、排箫、笙是中原传来的,竖箜篌、曲颈琵琶、凤首箜篌及一些鼓类是从西亚和印度方面传来的。龟兹自身还创造了一些乐器如筚篥等。而自从伊斯兰教进入西域以后这些乐器大部分都被废弃,如今也只能在库车地区残存的壁画和苏巴什古寺出土龟兹舍利盒中为我们提供上述乐器的形制、演奏姿态甚至技法的图象。
当时阿拉伯受伊斯兰教影响,还处在“断饮酒,禁音乐”的时期,阿拉伯人直到公元十世纪才出现重视器乐曲,显然是受到西域音乐的影响,据埃及艾哈迈德舍菲克、艾卜奥先在他的《阿拉伯音乐简史》中说:“阿拉伯音乐中的记谱法在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才开始”。而西域早在北周龟兹音乐家苏祗婆就已经提出了完备的“五旦七声”的音乐理论。从西域伊斯兰宗教政权对这些乐器的摧毁和改造中,我们可以推断,作为世代流传下来的西域歌舞,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繁衍,必然要接受这些来自阿拉伯的乐器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但是由于古代西域和阿拉伯文化形态上的巨大差异,阿拉伯乐器根本无法展现出西域这些庞大的乐舞形态和内容,于是必然迫使维吾尔族会对这些乐器进行改造,对流传千年的隋唐时期西域歌舞进行伊斯兰化改造,这种改造必然是一个长期、复杂而又漫长的历史进程。对于现在新疆目前使用的乐器而言,我们知道“人的音乐行为不但表现为有意识的活动,也可以表现为潜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活动,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有许多东西已是人们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作为一种行为的模式,在某些活动中参与者并不真正懂得(意识到)他们行为的动机、目的和意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再不能直接追溯的最初的动因,这样我们就不得不从现有的音乐事实中去探寻他所据有的人的内涵”(《民族音乐学概论》p59页)。
于是西域乐器的大变革到了“公元十五世纪后,波斯、阿拉伯的乐器大量传入天山南北,有“弹拨尔”、“沙塔尔”、“纳格拉”、“达甫”、“桑图尔”、“卡龙”、以及“卡曼恰”,印度人的“沙塔尔”、“尾那”、“沙软吉”等乐器也出现在南疆。虽然这些乐器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而取代了原来西域使用的乐器,而在天山南北,维吾尔族并没有全盘吸收,更没有照搬使用。维吾尔族尽管在伊斯兰文化的强制下放弃了原来使用的乐器,然而他们却在外来乐器的使用中,重新发明了新的乐器,而渐渐取代外来的乐器。首先表现在“沙塔尔”上,古代西域人参照波斯人的“沙塔尔”以及印度的“沙塔尔”,并吸收“沙软吉”的弓弦特征,而创造了“沙塔尔”这一弓弦乐器,并由沙塔尔来主奏木卡姆,而不使用其它外来乐器。这不仅说明沿承西域歌舞的维吾尔人民的音乐天才和创造能力,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其地域文化感情的坚韧性。
维吾尔族在龟兹乐的“五弦”基础上参照印度的“尾那”又创造了新的五弦乐器“热瓦甫”,这一乐器,无论是波斯、阿拉伯,还是印度都没有,维吾尔人大胆地开始使用。波斯人的“弹拨尔”,原来只有二弦和三弦,维吾尔人民将它改制成五弦,显然是一种继承传统而不甘受外来艺术支配的表现。来自波斯的“卡曼恰”,原来是胡桃形的,只有两根弦,后来被维吾尔人渐渐地改制成四根弦,形成今日的“艾捷克”。龟兹乐中的音乐结构为十二木卡姆所继承,龟兹乐中的“五弦”为维吾尔音乐中的“热瓦甫”提供了历史渊源。龟兹乐使用的“笛”现在仍在使用,龟兹壁画中的“手鼓”与今世的“达卜”如出一辙,龟兹乐中的“筚篥”就是现今维吾尔乐器“巴拉曼”。
而在歌舞方面,隋唐时期西域成熟乐舞形制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革,可以说龟兹乐舞达到古代音乐高度发展水平的标志,是乐曲分类和结构形式的出现和规范化。《隋书音乐志》记载:“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盐,意为曲子)这就说明,龟兹乐舞已经很成熟了,除了歌曲、解曲(器乐曲),还有专门的舞蹈伴奏曲。“歌曲、“解曲”、“舞曲”又可组成套曲(也称大曲),进行大型综合表演。与龟兹同为丝路北道重镇的疏勒,其乐舞也很发达,据《隋书音乐志》记载,《疏勒乐》的代表性“歌曲有《亢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疏勒乐舞也有了“歌曲,解曲、舞曲”的分类和歌、乐、舞组成“大曲”的结构形式,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所以,《疏勒乐》和《龟兹乐》一起,被列入隋、唐九部乐和十部乐中。这些历时千年形制成熟的西域歌舞在伊斯兰教政权进入后,必然要求在演唱演奏这些歌舞中剔除原来的所有佛教元素加入跟伊斯兰教有关的词汇和内容,剔除原先的古代西域当地歌舞的词汇而改用阿拉伯语的乐舞词汇。
这一点上在伊斯兰教进入西域后的当地萨玛舞、夏迪亚那和刀郎麦西来甫演变中都得到了深刻的体现等。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宗教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就于人们受社会盲目的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无法摆脱,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在于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精神手段。尤其在喀喇汗由佛教转入伊斯兰教时期,西域这些歌舞艺术被统治者大力改造,为伊斯兰宗教政权利用和服务,成为麻痹、控制和奴役百姓的精神工具,《中华舞蹈志·新疆卷》中详细地阐述《萨玛舞》和《夏地亚那》在西域伊斯兰政权时期这些舞蹈的伊斯兰宗教特性,成为为极力宣扬古代西域伊斯兰宗教政权和宗教战争服务的政治工具。但就其历史根源和歌舞特征而言它们根本不是属于起源于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舞蹈。从长诗《真理的入门》中的记载“学者丢弃了善功,隐士丢弃了虔诚,哲人竟跳起欢快的萨玛,手舞足蹈,禁止异教的人已无影无踪,异端邪说却猖獗风行”,(转引自《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231页)可以看出古代西域伊斯兰政权即便千方百计对百姓禁锢,也无法约束老百姓对西域歌舞根深蒂固的历史情感和自由向往,所谓的异教和异端邪说都是对隋唐西域歌舞的历史污蔑和践踏。历史雄辩地证明这些舞蹈都是赓续隋唐乐舞《龟兹乐》、《疏勒乐》以及早期西域原始舞蹈的特点,其中《萨玛舞》的特点与唐代玄宗龟兹乐立部伎有共通之处。擂大鼓“杂有龟兹之乐”的就有五部,“洪钟骇耳,声震百里”。而在唐朝军乐舞《秦王破阵乐》为宣扬唐太宗“以武功定天下”而作,又名“七德舞,”其“舞蹈充满战斗气息,舞姿豪迈,伴奏用大鼓,乐声气势雄浑,声韵慷慨、声震百里,动荡山谷,使观者凛然震,惊心动魄,初演完毕,十几个少数民族首领当即要求同舞,获太宗批准”。此后一直作为宫廷保留节目在各种场合以不同形式演出,《乐府杂录》将《破阵乐》列入《龟兹部》,可见为此舞伴奏的乐器具有龟兹的风格,并载晚唐藩镇冬春犒军舞《破阵乐》情事,此舞从初唐到晚唐流传近三百年。而《夏地亚那》的舞蹈语汇以跳跃的舞步为核心,并且始终贯穿于整个舞蹈的始终,各种小跳步变化多端,复杂多样,如单腿跳步,双腿跳交替跳跃步,跑跳步等可以说舞蹈动作不仅有腾还有踏,用或踊或跃来表述它的动态特征,才是确切而形象的,这充分表明夏地亚那保留着某些胡腾舞的遗风,或者说存留古代西域舞蹈腾踏跳跃的典型特征。夏地亚那民间舞蹈与古代西域的胡腾舞,当存在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例如塔塔尔族的男子舞蹈,也以下肢的跳跃为其特点,舞蹈热烈奔放,舞步迅急,弹跳轻巧,各种跳跃步伐的技巧性比较高,有很多胡腾舞的遗风。唐朝的著名软舞《春莺啭》《屈拓枝》《霓裳羽衣舞》等都是中原和西域歌舞融合的典范。
从今天新疆各民族的民间舞蹈和新疆各文艺院团新创作的民族民间舞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隋唐时期的胡腾舞、胡璇舞,拓枝舞之间相互融合和发展的景象。同时以史为鉴,结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新疆歌舞历史文化慎思明辨、剔除糟粕、取其精华、去伪存真、除恶扬善。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把与宗教有关的词汇和内容清除干净,尤其要把那种体现宗教政权、宗教狂热和宗教迷信的音乐、歌曲、舞蹈部分清除干净,不断地剔除掉狭隘民族主义、宗教极端思想、暴力恐怖思想、双泛思想等各种历史垃圾的渗透和侵害。隋唐西域歌舞的历史牢牢佐证了自古以来就深深扎根在西域的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文化认同意识,对于新时代的新疆歌舞就是要把壁画和唐诗中描述的苏幕遮、狮子舞、胡腾舞、胡旋舞、拓枝舞等西域歌舞的精华充分地展现出来,同时对流传至今的新疆各民族民间舞蹈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辩证地撷取历史上曾对人类文明、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贡献的丰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