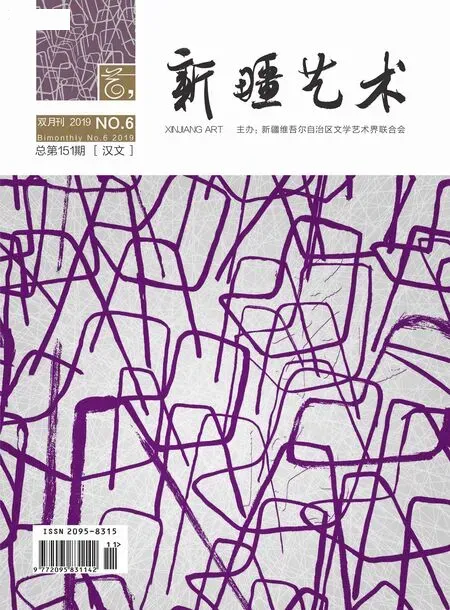新疆民间刺绣产品的叙事分析
——以新疆大学非遗刺绣传承人群培训成果为例
□
新疆民间刺绣产品具有鲜明的艺术与文化特色,在进入消费市场时,如何将这些特色转化为优势成为了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本文试通过叙事学视角分析新疆大学非遗刺绣传承人群培训成果“花之毡·民族刺绣”刺绣品牌与“疆绣小妞”、“西域美人”文创品牌在产品开发中所运用的商品叙事策略。
自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实施以来,相关研究成果叠出不穷,部分研究者反思了非遗研培计划的实践,讨论了课程设置与培训模式问题,认为培训的基础与关键在于确保非遗项目的核心技艺及价值,尊重非遗项目自身的传承和发展规律;[1]另有研究者从知识产权保护研究的角度出发,对传统手工艺及其相关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此外,更多的聚焦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现状与产业化研究,总体而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开展至今,对于培训作品与成果的研究尚且较为少见。
在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发展的过程中,“叙事”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产生了变化。研究者对叙事的定义不再局限于讲述和文本,而是扩展到了阐释模式和认知方式层面。申丹提出,叙事学研究的对象从作品本身转向了读者的阐释过程,从文学叙事转向文学之外的叙事,同时,研究者也更加关注社会历史语境如何影响或导致叙事结构的发展。[2]在这种转变之下,在现代消费社会中从叙事学角度研究商品成为可能,也是笔者将叙事学视角作为本文切入点的理论依据。

新疆大学刺绣培训项目手绣新疆动物普氏野马
在商品叙事这一领域之中,本文的研究方向与黄柏青的文章较为贴近,其在《消费社会语境中设计美学的商品叙事》一文中从设计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消费社会之中商品设计对于商品形象建立的重要性,并指出,设计美学表达着一种商品化叙事与消费价值观,“其商品化特征表现了以象征性的形象符号再现商品内在结构的内涵特征,直接以形象话语的方式演绎着后现代社会的消费寓言与商品逻辑,实现了商品生产与形象表征的完美结合”。研究者认为,现代消费社会带来的是一种普遍商品化同时日益美学化的语境,对于其中的事物而言,图像性与商品化的存在成为了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融合日益加深,而迎合这种语境,通过有意识地精心设计中介进入生产、流通领域的商品,便成为了“景象的商品”,遵循着“资本统帅一切的逻辑”,并演绎了一出“景象与商品密谋同构的寓言神话”。[3]此外,齐蔚霞的博士论文《广告叙事研究》也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思路,文中研究者通过叙事学视角感知和阐释广告文本,并运用经典叙事学深入到广告文本的叙事形态和结构之中,通过原型叙事分析得出广告叙事的9种基本结构模式。研究者指出,广告叙事主体在叙事情境的人为构建、广告的修辞、广告传播的媒介以及叙事中的原型在广告叙事的产生、传递、接受之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4]
目前,国内通过叙事学视角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多集中在影视图像文本之中,对近年来几部优秀的手艺人电视纪录片的分析成果较多,但从商品叙事的角度分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培训成果以及新疆刺绣手工艺的研究尚少。本文在继承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叙事学视角分析新疆大学非遗刺绣传承人群培训成果“花之毡·民族刺绣”刺绣品牌与“疆绣小妞”、“西域美人”文创品牌所运用的商品叙事策略,试总结商品开发之中的经验,为该领域工作的推进提供一份可供借鉴的思路。
一、前消费社会语境下的新疆民间刺绣
刺绣技艺产生于本地民俗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符合其生活需要和情感需求,新疆各民族刺绣技艺由各族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自发创造并代代完善,作为民俗事项之一,具有民俗的历史性、自发性、地域性、传承性和变迁性特点,并在色彩、图案、质料、技艺方面拥有独具特色的惯制。其中,地域性的差异源于各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也是最重要的将各民族刺绣进行区分的特点。周莹指出,“自然界的外在环境为少数民族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前提,人们本能地同自然有种亲近感与和谐的一致性。在各少数民族群众自然情感表达中,将既然形态的原型转化为一种新的形式、新的符号,浓缩出该地域或民族人们精神意识和生活状态,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共同性”。刺绣的原料“因地制宜,取之自然”,[5]带有地方特色。而刺绣的纹样、加工方式也都与当地的生产与生活息息相关。
从传统民间刺绣的图案来说,花卉纹饰是最早出现的图案之一。早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绣品中就能辨认出专门的茱萸绣。新疆民丰县出土的东汉刺绣中,有用各色丝线绣成的卷草、成丛的金钟花、菱形的回旋纹、豆荚形的对叶等图案。早期的刺绣花卉多为简单重复的缠枝纹样,而唐代开始,随着绘画艺术的发展,出现了形象写实、造型丰满、色彩富丽的以花卉为主的花鸟纹图案。[6]在今天,与画面愈发精致、写实的苏绣、湘绣不同,疆绣的花卉纹饰依然偏向于缠枝纹样,更多是由抽象化的植物、动物纹样组合形成,而重复出现、首尾相连的钩针绣图案也成为了人们对新疆传统民间刺绣的重要印象之一。
传统的民间刺绣同时承载着浓厚的情感,经过一代代的发展,劳动人民将“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偏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社会观念”都沉淀其中,构筑成了文化与技艺的精神内涵。而民俗事象的抽象化功能所具有的整合特性,则为其传承提供了条件。民间刺绣中的每一个图案都默默传递着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寄托着人们浓厚的情感,正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茱萸绣寄托着古人辟除恶气,求取吉祥的愿望,人们也将石榴花绣在裙摆上祝愿多子多福,将马纹绣在腰带上祈求身强体魄,并无法不将这些图案与其蕴含的祝愿与新疆的石榴园、游牧民族联系起来。
二、培训作品对新疆刺绣的重述
依托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培计划新疆大学刺绣培训项目,项目组研发团队尝试开发了“花之毡·民族刺绣”刺绣品牌与“疆绣小妞”、“西域美人”文创品牌。继承项目“强基础、增学养、拓眼界”的指导思想、脱贫攻坚的重要任务与针对新疆民间刺绣技艺的生产性保护的目标,品牌商品开发的主要目的在于结合新疆民间刺绣的特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意开发,为新疆刺绣产品增添文化内涵与旅游纪念价值。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疆各民族刺绣具有其原本的惯制与意义,但在运用这种技艺加工需要进入消费市场的商品时,其本意也必将面临重述。

新疆大学刺绣培训项目雪莲花刺绣屏风
社会的历史、文化由其市场之中的商品最直观的反应出来,消费者、尤其是异地的消费者,对于本地的认识和第一印象即由市场之中的商品所提供。市场之中的商品、纪念品作为消费者、旅游者对本地首次接触的媒介,与作为民俗事项的刺绣一样,是传递本地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内涵的载体。但这种传递是显性的,并非悄无声息地融入本地人的生产与生活之中,而是通过异化突出自身,吸引注意力,帮助消费者基于对该商品的认识形成对于商品产出地、制作者的第一印象。周宪认为,这种消费社会之中“物”对人形成包围的现象可以直接体现为“形象对人的包围”,消费社会就是一个景象社会,而商品即景象。[7]黄柏青指出,呈现为“景象”的“商品”是经由有意识地精心设计后加以生产、流通的。商品的“形象”需要经由有意识地精心设计,才可能进入到生产环节、流通领域之中。“商品不但成为功能性消费的对象,而且成为视觉性审美的对象。”[3]
商品的种类日益丰富,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转型,“功能性”不再是第一选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也产生了依靠消费取向来表达自我的诉求,转向“功能性”与“审美性”的同时满足。黄柏青将这种趋势称为从“合算”向“合意”的转变。传统的新疆民间刺绣产品在进入现代消费市场时,面临的不仅是产业化,还需要依靠设计来突出自身的独特性,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样的服务与更加优质的审美体验,在同类型商品中提高竞争力,因此,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对民间刺绣进行由外而内的重述是必要的。
自然、历史、人文资源均可作为被消费的对象与刺绣品结合,但“要成为消费品,物品必须变成符号。即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外在于这种与生活的联系,以便它仅仅用于指意:一种强制性的指意和与具体生活联系的断裂;它的连续性和意义反而要从与所有其他物类符号的抽象而系统的联系中来取得。正是以这种方式,它变成了‘个性化的’,并进入了一个系列等等:它被消费,但不是消费它的物质性,而是它的差异性。”[8]新疆大学非遗研培项目组研发团队将提取元素并转变为一种可供消费的符号的方式作为刺绣品开发的主要路径,从两个角度切入,对新疆民间刺绣进行了个性化的重述与再设计的尝试。两个角度分别为对新疆自然风光与动植物资源的重述以及对新疆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的重述。
首先是对新疆自然风光与动植物资源的重述,该类作品集中体现在“花之毡·民族刺绣”刺绣品牌之中。项目组研发团队取国家级传承人绣国家级景区、国家级传承人绣国家级保护动物的思路,进行了新疆刺绣与新疆自然资源的结合尝试。截止2019年6月,新疆共有12家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这是文化旅游产品的主要消费地点,其自然风光作为一种可被叙述的对象进入刺绣之中是顺理成章的。但正如前文所述,新疆民间刺绣的针法较为粗犷,图案高度抽象化,不善于风景刺绣,因此,项目组研发团队大胆将新疆刺绣传承人群、新疆风景与苏绣之中的乱针锈结合。同样,新疆因为地形地貌丰富,是许多野生保护动物的乐园,在将这些动物作为元素添加到刺绣品之中时,新疆民间刺绣针法遇到了能够发挥长处的领域,掇针绣与平针绣交织,在布面上完美展现出普氏野马、北山羊、跳鼠等小动物毛茸茸、活灵活现的模样。通过这种途径,项目组研发团队对当下新疆文化旅游商品做了新的解读,刺绣品背后的文化附加值可以来自图案本身,也可以来自手艺人、刺绣传承人与其背后的故事。显性与隐性的叙事共同构建了刺绣品作为商品为消费者所呈现的“景象”。
其次,是对新疆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的重述,该类作品于“花之毡·民族刺绣”刺绣品牌与“疆绣小妞”、“西域美人”文创品牌中均有体现。以“西域美人”文创品牌为例,商品研发之初,项目组研发团队首先从新疆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之中提取出七个著名的女性形象作为叙事原型,包括西王母、传丝公主、胡姬、楼兰美女、细君公主等,根据从文献之中提取出来的气质特征,将其进行形象重绘,并根据故事情境、传说背景分别搭配一种新疆植物,设计成为“西王母与雪莲花”、“胡姬与石榴花”、“传丝公主与棉花”、“楼兰美女与红柳”、“细君公主与薰衣草”的形象。依托这一套形象,项目组研发团队制作了书签、笔记本等文化创意产品,并将其与刺绣结合,采取大面积图案印制+细节手工刺绣的方式,制作了局部刺绣的帆布包、团扇等手工刺绣产品。在商品设计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文化旅游市场、开发文化创意产品的需求,也是对当今主流消费观念之中拟古慕贤价值取向的迎合。在加工过程中,传说与故事往往会经历选择、过滤和改造的过程,甚至被无视以及重新书写,在这里,项目组研发团队采用了解构—重建—融合的叙事策略,将神话传说中的女性形象、新疆植物与手工刺绣结合起来,为消费者、尤其文创产品所针对的年轻一代构建出了一个新的可供观赏的新疆刺绣“景象”。
三、传统技艺进入消费社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如今,在自然与文化资源进行的重述与创意转化之中,已经可以见到一些成果,但行业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诸如盲目开发与结合、符号指涉不明、纹样混乱、误读与乱用等。对此,黄柏青指出,当商品成为景象时,首先,人们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被消费者对商品单纯的占有取代;其次,“占有”转向“炫示”,实在的物及其内涵被经由开发者提炼的符号表征所掩盖,而人的主动创造让位于被动接受,单纯的视觉审美“压倒了其他观感”;第三,作为景象的商品缺失互动性,脱离了人的活动,成为了单纯的观赏对象;最后,这种商品将会不断地自我复制。总的来说,商品化将其所提取成为符号元素的文化高度平面化后,将会使得这种文化丧失其原本的多义性与不同的解读可能,而流于该商品的表象。[3]如居伊·德波所说,“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中,生活本身展示为许多景象的高度聚积。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9]
在现代市场经济与消费社会的语境下,传统的文化与手工技艺需要通过转型来重新获取生命力。无法良好适应所处时代的文化与技艺将会逐渐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与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为其寻找一条可以长久生存的道路是十分必要的。所幸在新时代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我们对传统技艺与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有了更多的可操作性。在将传统技艺引入现代消费市场的过程中,新疆大学非遗研培项目组研发团队坚持用字引领的原则,秉持“创意源—创意作品—创意产品—创意商品”的转化链,在传统与现代、实用与时尚的交融之中,尝试将各民族传统技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旅游市场、文化创意产品联系起来,虽然过程中必定会面临许多难题,但仍将不懈尝试从利用与保护之间寻找出一条有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