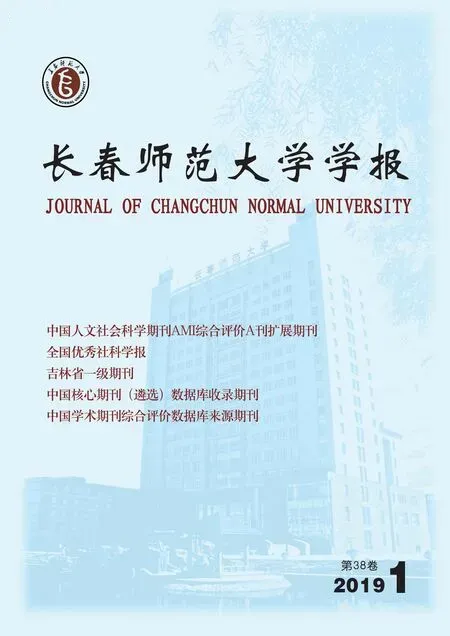基于精神分析学的《痴人之爱》解读
王秀霞
(阜阳师范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唯美派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在其长达五十五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形成了“恶魔主义”与“古典回归”的创作风格。谷崎文学以丰富的内容、流畅的叙述、熟练的表达技巧以及对官能美和日本古典美的思考和描写,获得了“大谷崎”“谷崎朝时代”等盛赞。他于1937年被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于1949年以作品《细雪》获得朝日文化奖,于1960年和川端康成一起获得了日本最初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63年,晚期作品《疯癫老人日记》荣获每日艺术大奖。1964年,谷崎润一郎成为全美艺术院·美国文学艺术研究会会员。《痴人之爱》是谷崎润一郎早期的文学作品,除了延用了其女性崇拜的创作主题及“恶魔主义”的创作风格外,还讽刺了大正时期日本人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故事主要讲述了就职于东京的电力工程师河合让治想将15岁的少女娜奥密培养成自己理想中的女性,却最终被长大后的少女所控制的故事。
在西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弗洛伊德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提出了关于潜意识、泛性论、人格结构、本能说以及论梦等一系列理论,指出人的精神是由本我(无意识的先天的本能、基本欲望)、自我(有意识的根据外部世界的需要来活动)和超我(道德化了的自我)组成的。弗洛伊德学说影响到现代西方人文科学、语言文学、宗教、艺术、哲学、伦理学等,并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精神分析法在文学上的引入使文学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角度更加新奇,使文学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富。本文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出发,重点分析《痴人之爱》的男女主人公——河合让治以及娜奥密人格发展的过程。
一、本我的奴隶
本我是最原始的、潜意识的、非理性的心理结构,充满着本能和欲望的强烈冲动,受着快乐原则的支配,一味追求满足。[1]142女主公娜奥密出身卑贱,原本是在东京一家咖啡店打工的女服务员,在那里认识了经常来店里的顾客河合让治。娜奥密西式的名字和洋气的长相吸引了河合让治。当时的娜奥密忧郁含愁、沉默寡言,经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默不作声地拼命干活。河合决定将娜奥密留在身边,照料她的生活,并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努力将其培养成自己理想中的女性。经过与其本人和家人的协商沟通,娜奥密辞去了咖啡店的工作,搬去了河合的家中。娜奥密本来是个能够自食其力的人,但最终丧失了自我,渐渐沦为任人摆布的玩偶。比如河合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培养她,经常让她穿上各种西式服装、摆各种西方明星的姿势来满足自己崇拜西方的心理,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出“娜奥密既是妻子,也是世间罕见的偶人”[2]112。在河合的培养下,长大后的娜奥密外表变得更加性感和魅力。但是,她在内在修养方面却有所不足,满口谎言、贪慕虚荣,为了满足自己的本能和欲望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不仅如此,她还变得更加骄纵和放荡,在河合、滨田、熊野等几个男人之间周旋,贪图物质和肉体上的愉悦,成为本我的奴隶。
在二人关系中,河合让治本来扮演着调教者和施惠者的角色,却最终拜倒在了娜奥密脚下。从二人的几次发生矛盾中可以看出这种主导关系的转变。当娜奥密没有好好学英语而发生冲突时,河合说要送她回家,娜奥密立马就软了下来,因为她还需要依靠河合,只有河合才能满足她当时的物质生活。当发现娜奥密私生活混乱的丑事后,河合再次驱逐她时,娜奥密却马上收拾好行李离开了。因为她知道利用自己肉体的魅力,即便没有河合,也会有别的男人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后来,河合忍不住思念去追寻娜奥密时,发现她依靠着别的男人依然过得光鲜亮丽。娜奥密心中知道河合已经离不开自己,为了有更稳定的物质来源,她便总以收拾东西为借口不断回到两人位于大森的家中来引诱河合。最终,娜奥密通过自己肉体的魅力征服了河合,使其心甘情愿地听命于自己。小说中,娜奥密骑在河合背上:“以后什么都听我的?”“嗯,听。”“我要多少钱就给我多少钱吗?”“给。”“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许干涉,行吗?”“行。”[2]277由此可看出,河合最终也沦为了本我的奴隶。
二、自我的挣扎
自我是受知觉系统影响,经过修改的来自本我的一部分。它代表理智和常识,按照现实原则来行事。它既以大部分的精力来控制和压抑发自本我的非理性的冲动,又迂回地给予本我以适当的满足。[1]142在学习知识方面,娜奥密刚开始知道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于是非常用功,并明确表示一定要成为让治理想中的优秀女性。但是,她后来却开始慢慢懈怠和堕落,最终什么都没能学好,成为庸俗不堪的女人。其实在堕落的过程中,娜奥密也是有过痛苦和挣扎的。她知道河合让治有恩于自己,不应该辜负河合的期望。所以,刚开始在一起时,她会给河合做饭,会照顾花坛里的花,还会自己动手缝制窗帘。但是,随着河合对她一味地包容和妥协,再加上追求享乐的诱惑,她的自我开始动摇,情感的天平慢慢倾向了本我。在河合从同事那里听到关于娜奥密不好的流言后,娜奥密开始发生改变,“虽然照样去跳舞,但不像以前那么频繁,跳的时间也不算长,适可而止,时间差不多就回来。那些客人也不来找她玩。我从公司回来,总是看见她一个人规规矩矩地呆在家里,不是看书,就是织毛线,或者宁静地听留声机,或者在花坛里种花……”[2]186然而,她这种按照理智和常识生活的自我很快又被本我打败了。为了能够继续享乐的生活,她和熊野、滨田设计好了骗局,将河合骗到了镰仓。她在白天河合上班时出去和其他男人一起鬼混,晚上河合下班后又在家装出一副贤妻的模样。当骗局败露后,与河合分手了的她彻底堕入了享乐的深渊。由此可看出,娜奥密徘徊在自我和本我之间,最终还是成为了本我的俘虏。
河合让治在受制于娜奥密之前,亦在自我和本我之间苦苦挣扎,主要表现在学习和生活方面的各种冲突上。在娜奥密学习英语时,河合对她的不努力十分生气,这却引起了娜奥密的逆反心理,两人的屡次对抗中妥协的总是河合。河合对娜奥密的娇惯使得娜奥密越来越傲慢不逊、恣意任性,不再听命于河合。“以前不论怎么撒娇耍赖,只要我正色说几句,她还听得进去。可最近只要稍不顺心,立刻板着面孔,噘起嘴唇。”“有时不论我怎么声色俱厉地苛责,她竟然不落一滴眼泪,装聋作哑,实在令人可恨。”[2]119河合心里明白,期待娜奥密有朝一日成为优秀女性的愿望已成泡影。他一方面对娜奥密灰心绝望,另一方面却越来越沉迷在她的肉体里。“我越想她是一个‘愚蠢的女人’‘无可救药的家伙’,越是居心不良地接受她的美色的诱惑”,“我本来想把娜奥密培养成身心两方面都很美丽的人。虽然精神方面失败了,但毕竟在肉体方面获得了圆满的成功。”[2]120从这时起,河合开始放弃了自我的追求,而沉醉于本我所产生的快乐,甚至想如果娜奥密真是狐狸精,那也心甘情愿地被迷惑。此时,河合的月收入已经不能满足只注重享乐的娜奥密。她从不做家务,每月的外卖账单、洗衣费是一大笔支出,还要经常购置新衣新鞋。尽管生活已捉襟见肘,河合对娜奥密的挥霍还是一味的纵容。在二人拿着河合母亲寄来的钱去跳舞时,河合感到了娜奥密的虚荣和庸俗粗鄙。但是,只要回到两人位于大森的家里,她对河合又充满了诱人的迷惑力。“我对她爱憎的情绪就像猫的眼睛那样一个晚上能变化好几次”[2]167。这种爱憎的变化充分体现了河合自我与本我的冲突。在两人因“镰仓事件”分手后,理智告诉河合娜奥密做出了不可饶恕之事,不能再和她继续纠缠下去。但是,他却依然无法忍受对娜奥密的思念之苦,到处寻找她的下落,并最终拜倒在她的脚下。“我的兽性迫使我盲目地向她屈服,终于抛弃一切条件和她妥协”。由此可见,经过一番自我挣扎后,河合还是堕入了本我的深渊。
三、超我的幻灭
超我是人格中高级的、道德的、超自我的心理结构。它以良心、自我理想等至善原则来规范自我。[1]142娜奥密本来也是一个天真烂漫、淳朴善良、懂得知恩图报的小姑娘。在两人还没住到一起时,娜奥密喜爱辽阔的田园,怜惜美丽的鲜花,拥有孩童般的天真。刚住到一起时,和河合一起想尽办法来装饰新家,并会好好地料理家务、照顾花坛里的花,富有生活情趣。当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学习的机会时,也是非常努力。她会眼含泪水地对河合说,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女性,不会忘记他的恩德。然而,随着河合的骄惯以及自身的堕落,她最终沦为了男人的玩偶、享乐的奴隶。在沦落之初,她还会想方设法地瞒过河合,因为她的内心终究还是对河合有所愧疚。当河合发现她的丑事并将其逐出家门后,她便索性彻底沦落,超我的意识也就此幻灭。
河合本来是一个勤勤恳恳、认真诚实的公司职员,在公司口碑也一直不错。但是,这样一个“正人君子”却被娜奥密拖入了享乐的地狱。在为公司同事送行的宴会上,公司同事S、K、H的话都说明大家已经知晓了其荒诞颓废的生活。后来当发现娜奥密一直在欺骗自己之时,河合则更是经常请假去跟踪娜奥密。工作的懈怠以及私生活的丑闻导致河合在公司的人缘大不如前,失去了上司、同事的信任,勤奋努力、品行端正的“正人君子”形象彻底坍塌。以至于当母亲去世请假时,他被同事嘲讽又是借口休假。最终,河合辞去了电力工程师的工作,变成了一个懒散之人。此外,从其在与母亲的关系中亦能看出其人格发展的变化。河合自幼丧父,由他的母亲一手抚养成人。母亲从来没有打骂过他,对他充满慈爱、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河合去东京之后,依然相信他、理解他、为他着想。河合本来是一个孝敬父母、勤奋努力的好儿子,但为满足娜奥密的虚荣和奢侈,却开始骗取母亲的钱财。当母亲去世后,河合自觉有愧于母亲,悔恨交加,把母亲的死看成对自己的规诫和垂训。“这个巨大的悲痛使我得到净化,变得晶莹剔透,把淤积在我身心里的龌龊肮脏洗涤干净。如果没有这悲痛,也许我至今不能忘记那卑鄙猥亵的淫妇,还在继续遭受失恋的痛苦的折磨。”[2]253由此可以看出,此时河合的超我已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当娜奥密以拿东西为借口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位于大森的家中来诱惑自己之时,河合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本我,终拜倒在娜奥密的脚下。尽管后来的娜奥密同时和多个男性交往,河合却表现得温顺服帖。“她的水性杨花和任性恣意我早已清楚,如果没有这个缺点,也就失去了她的价值。我越想她是一个淫荡的家伙、一个任性的家伙,越觉得她可爱,从而陷入她的圈套。”[2]258至此,河合的超我意识彻底幻灭。
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释放压抑在无意识深处的力必多欲望通常至少有三条途径:一是经由自身心理结构内部的调整,如自我和超我对伊底(本我)的制约作用,逐步在力必多释放之前就克服之。二是将投射目标移向他方,例如艺术家的宣泄方式往往是将其“升华”为艺术形象。三就是将压抑的欲望直接投射到异性对象上去,以实现欲望的满足。[3]《痴人之爱》的两位主人公——娜奥密和河合让治都选择了第三种,将自己的欲望投射到异性对象上来释放压抑在深处的力必多①。他们的人格发展过程都经历了超我的幻灭—自我的挣扎—最终沦为本我的奴隶这三个过程。通过对两位主人公人格发展过程的分析,可以加深人们对谷崎润一郎这位集“恶魔主义”和古典情趣于一身的作家的了解,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解读谷崎文学“恶魔主义”的创作风格。
[注释]
①精神分析学认为,力比多是一种本能,是一种力量,是人的心理现象发生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