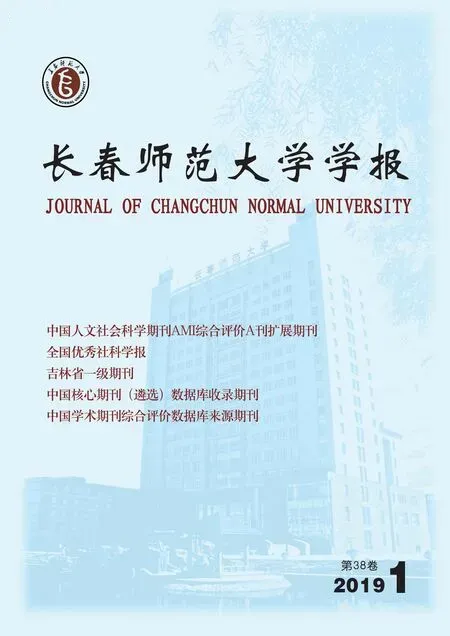诗人的激情与理性
——谈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诗歌创作
张晓雯
(南京中医药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 1914—1998)生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有西班牙和印第安人的血统。土著传统和殖民印记、欧美思潮和东方艺术都是帕斯诗歌创作的不竭之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坚韧的文学信仰让他的诗歌具有多声部的表达特性。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帕斯参加了那里的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结识了智利诗人聂鲁达和秘鲁诗人巴列霍。其中,聂鲁达对年轻的帕斯有知遇之恩,并深刻地影响了他早期的诗歌创作。1946年,帕斯担任外交官职,出使美国、法国和印度。外交官生涯让他与欧美文学思潮和东方文化艺术有所接触。帕斯一生著述颇丰,从处女作《狂野的月亮》(1933)到结集《回归》(1976),诗集达数十本,长诗《太阳石》尤为出色。1990年,他因其“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渗透着感悟的智慧并体现了完美的人道主义”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一、灵魂的歌者
西班牙黄金世纪诗人贡戈拉曾说:“用笔如用情”。诗歌创作是情感的宣泄与表达,与创作时内部的生命体验和外部的社会情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在诗歌创作动机和创作语言上情感这一非理性因素承载了重要角色,思索则在诗歌书写和诗歌诉求上发挥着功用,二者各具其能、并行不悖。帕斯曾在《批评的激情》中这样评述自己的创作生涯:“这是各种具有双重性工作中的一种:既是一种活计又是一种神秘,既是一种消遣又是一种圣举,既是一种职业又是一种激情。”[1]3帕斯的诗作中感性因素与理性态度二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平衡关系,激情与哲思是其诗歌表达中的重要一笔,形成了他独有的诗歌风格。
灵感在诗歌创作之初尤为重要,因为它凝结了诗歌创作所必须的一切非理性因素。关于灵感,帕斯这样认为:“一般来说,我对将要写的东西没有一个明确的构思。很多时候我觉得脑子一片空白,没有一点主意,然后突然出现了第一句。”[1]164对大多数诗人或作家而言,创作灵感有时会毫无征兆地突然闪现,有时则源于各种不现实或荒诞的经验。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的短篇故事《被侵占的住宅》就复制于其清晨的一个噩梦。关于灵感,帕斯曾在《诗》中这样写道:
你来了,悄悄地,秘密地,
将激情和快感激起,
还有一丝忧虑,
点燃碰到的东西……[2]164
有时,灵感甚至可以完全控制诗人的思想,诗人也会在创作中对自我有所怀疑。在《写作》中,帕斯说:
有人在我身体里,
移动我的手,写诗,
他挑了一个词,犹豫……[3]133
灵感拥有神秘而强大的力量,让诗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以及灵感的本质:
他是判官,也是囚徒
审判我时,也审判自己:
他不写给谁,亦不呼唤谁,
他写给自己,却忘了自己,
他赎回自己,重新成为我自己。[3]133
帕斯的诗歌,不管是诗句的尺度或节奏,还是诗歌的语词和意象,具有一种“争论的,战斗的,激情和爱欲的”鲜明个性。[4]22这些强烈的情感使他的作品明媚生动,各类大胆的、充满隐喻、顿悟、先验的瞬间以及感官至上的自然之声十分常见。如《语言》中所写:
用脚踩它们,放荡的公鸡,
扭下它们的脖子,厨师,
拔掉它们的羽毛,
割开它们的肚皮,公牛,
母牛,把它们拖出去,
处置它们吧,诗人,
让它们吞下它们的全部语言。[5]22
在选择语词并在组合它们时,帕斯十分注意对应词的使用,如:“脚踩”“扭下”“拔掉”“割开”“脖子”“羽毛”“肚皮”“公鸡”“厨师”“母牛”“诗人”。将这些在语音、语义和韵律上对应的词串联起来,使诗的意义更加变幻不定、摇曳生姿。换句话说,诗歌中的语言并非简单的语言,或者说不再是一堆可以移动的、有含义的符号,诗歌超越了语言自身所赋予的既定的意义。
在帕斯的诗作中,我们能够读出诗歌的大胆。他无所顾忌地表达出了人的激情、人的欲望和梦想,对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而言,这类非理性的人类情感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但从人的角度来看,诗人的确还原并塑造出了大体真实的人物和意象,这也是诗人作为灵魂的歌者的真实发声。
二、哲思的行者
诗歌从何而来?人类为什么要创作诗歌?帕斯认为人类的第一行诗是灵感碰撞下的产物。所以,灵感对诗人来说是十分可贵的。但诗歌却不能沦为灵感的工具,需要有另一个理智的声音存在,将灵感引入“一种向往,一种前进的运动中去,让诗人走向自身,获得新的自我”。[3]16如果说灵感在第一行诗句涌出的关头闪现,并奠定整首诗作的内涵和基调,那么“另一个写诗的生灵”即为后续的思维运行,偶然巧合与精密谋算的合力成就了诗歌的整个书写过程。
帕斯是哲思的践行者。在他的诗作中,不乏对印第安传统、印度禅宗、日本俳句和道家文化进行过独到的阐释与表达。他尤其崇尚中国的道家思想,认为人在道德言行上的心性觉悟和明心见性是拯救自己、解放自己、升华自己、解脱自己的根本途径,并最终达到“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内在和谐与统一。在古老东方文明的浸染和洗礼下,帕斯对大地与生命、创造与消亡、迷途与救赎、诗歌与哲思的辩证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解决哪里是诗人的理想天地、何处是诗歌的乌托邦的问题上,帕斯的“在途”论认为,只有不懈前行和不停反思,方能无限接近彼岸的这片净土。比如,在《世界》一诗所写:
在海洋的黑夜里,
只有鱼儿或闪电。
在树林的黑夜里,
只有鸟儿或闪电。
在躯体的黑夜里,
骨骼是闪电。
世界啊,一切都是黑夜,
而只有生命是闪电。[6]27
庄子的《齐物论》认为:“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在对“道”的认识中,帕斯体悟到了物化的内涵,即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移,其形态绝不固定,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和谐并存,所谓“万物一齐”。因而,有了这样的诗句:
所有的名字不过是一个名字,
所有的脸庞不过是一张脸庞,
所有的世纪不过是一个瞬间。[6]28
世间万物更迭交替,点亮这片混沌与黑暗的是生命,但生命转瞬即逝、归于泥土,唯有诗歌见证我们与万物的同在。在诗歌面前,诗人自己无足轻重,他的生命终将消失在字里行间,化作虚无。
语言?是的。属于空气,
并在空气中消失。
让我消失在语言中吧,
让我变成口唇中的空气,
一股飘荡、无形、
被空气冲散的气流。
光线也在自身中消失。[2]18
东方体验与泛神论让帕斯超越了世俗,突破东西方文化思想的界限,刷新了诗人的人生观和文学观。东方是帕斯诗歌创作的另一个起点,融汇了他的历史与未来、孤独与普世、诗歌与哲思。
三、艰难的博弈
和同时代其他伟大的诗人相比,帕斯首先是位诗人,再而是文人,最后是哲人。诗人的第一身份决定了情感在他诗歌创作中的不可替代性。在文人和哲人、激情与理性之间,帕斯历经艰难的抉择与取舍,这仍旧源于诗人的多重身份属性。诗人帕斯是一回事,哲人帕斯是另一回事。但是,帕斯始终以平和心态接受大众的审视。聂鲁达是帕斯诗歌生涯的引领人,也是他诗歌创作早期少有的赞扬者。思想上,帕斯坚定地追随过这位精神领袖。但在创作方向上,聂鲁达对帕斯的干预使其与曾经的精神导师渐行渐远。正如苏格拉底的死彻底改变了柏拉图对诗歌的看法一样,托洛茨基的死让帕斯对早年的革命理想和人生追求恍然大悟。
1957年,帕斯的诗集《太阳石》横空出世,作品世界性的眼光和高度超越了时代的思想局限。随后,帕斯将顿悟后的笃定深入地更为彻底,那涵盖一切的理念在彼时已幻化成充满“灵感”与“神圣瞬间”的生命感悟,对诗歌无上的礼赞与景仰。如:
生命是他物,
永远在更远的地方,
在你我之外,
永远在地平线上。[7]28
诗歌和旋律一样,能控制人的潜意识,即我们所说的本能。当然,很多文艺形式都拥有这种“控制”的特质,比如小说、绘画、电影都会让人产生代入感,但诗歌对人的控制和渲染最为明显。柏拉图在《诗人的罪状》中认为:“诗歌是危险的,它体现了人的非理性部分,人的激情、人的欲望、人的梦想”。所以他主张“将诗人们逐出共和国”。希腊人认为诗人是神话的作者,但柏拉图反对神话,更反对诗歌,他对诗歌的敌意有其道德归因,之所以驱逐诗人,是因为诗歌中出现的那些非理性的行径,尤其是诗歌中的情欲让人软弱无能、内心阴暗、人性扭曲、灵魂腐朽。诗歌的随意性、情感的发散性和挥霍本质破坏了人完整的人格发展。
帕斯充分肯定柏拉图观点的前半部分,但反对他从哲学的立场看诗歌本质,即诗歌容易激发人性中的非理性成分,使人们挣脱理性对人的控制。在《火焰,说话》一诗中,帕斯这样反驳:
我看过一首诗说:
“讲话是神做的事”。
可是神祗都不开口,
只在创造又毁掉一个个世界,
而人却在说话。[6]26
帕斯认为,神并不具备“讲话”的能力,真正讲话的是诗人。原因有二:首先,任何一首伟大的诗作都比枯燥的词条释义更加有血有肉、煽动人心、撞击心灵。他颂扬以梦想、欲望和激情创作诗歌的诗人,对以“真、善、美”为追求的诗歌创作褒以肯定,对实用主义、现实主义下的宣传诗嗤之以鼻。第二,帕斯不是二元论者,认为人由肉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诗歌创作亦是肉体和灵魂交织碰撞迸发出的产物。如果说激情和欲望是诗歌创作的外在驱动,那么理性和思考则是诗歌的灵魂和精神内核。帕斯深谙灵感和激情是优秀诗歌产生的条件,而这些恰恰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它始终伴随着一种非理性的痴狂状态。这种非理性的情感纽结、回忆或先验是诗人与诗歌、与他人以及与自己进行对话的媒介。帕斯将“非理性”体现在词藻的选择和意向的运用上,将情感与思想在诗歌中融为一体,以此区别于理性的柏拉图们。
在现代社会中,诗歌具备一种破坏与叛逆的作用,这种作用是现代思想所缺少的伟大因素,它重新点燃了人的激情、感情、梦想、欲望,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人类是具有自觉或不自觉的冲动的生灵。忘记这一点,会导致人的非人性化。矛盾的是,强化这一点,却会使诗人在捍卫这一相对真理时成为艰难的人而遭到许多人的诅咒。柏拉图为了“理式”这一最高标准和理想,义无反顾地推开了他自幼景仰的诗人荷马,坚决地将诗人逐出了理想国;帕斯却正因抛弃了“理式”而与聂鲁达决裂三十载,饱受时代和中心人物的诟病。因此,诗人的态度很艰难。
四、化解与融合
古老的印第安文明在帕斯的血液中流淌,是他诗歌创作的根基与源泉。正如他自己所说:“哥伦布以前的墨西哥,连同它的庙宇和诸神,已是一堆废墟,然而赋予那个世界以生命的精神并没有死。它在用神话、传说、共同生活的方式、民间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密码语言同我们说话”[1]4。在长诗《太阳石》中,帕斯这样歌颂本国的文化精髓:
玉石上火的字迹,
岩石的裂缝,蛇的女王,
蒸气的立柱,巨石的源泉,
月亮的竞技场,苍鹰的山岗,
茴香的种子,细小的针芒……
生命的葡萄,伤口上的盐……
八月的雪,断头台的月亮,
麦穗、石榴、太阳的遗嘱,
写在火山岩上的海的字迹,
写在沙漠上的风的篇章。[7]22
也许正是由于印欧混血家族的特殊起点,奠定了帕斯一方面积极吸纳西方现代文明,一方面不断汲取东方传统思想的文学信仰。他对印度佛教、中国的老庄和周易有其独到的见解和阐释。此外,他还译过李白、王维、苏轼和李清照的诗作及小传。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博大精深的学识是帕斯能够将诗作提升到人类视野的广度和高度的重要原因。柏拉图以理性驱逐诗歌,帕斯又用非理性将其召唤;聂鲁达向革命文化抒发赞美,帕斯却亲近传统一古一今的不同抉择引人思索。
诗学与哲学的官司由来已久,诗人与哲人的争论是自古希腊起就有的古老议题,争论延续至今未有定论,只有态度。帕斯秉持古老的诗歌传统,同时追求用理性主义哲学指导下的文学艺术来审视世界和人类的一切活动,他将诗歌的内容定位为理性的,形式为非理性的;目的为理性的,而过程为非理性的,从而来追求文艺的“真、善、美”。所以,作为诗人的帕斯有别于哲学家和作家,因为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被大众接受和喜爱,而诗人却敢冒失去支持的风险,不愿将诗歌创作当成是一种取悦大众的手段,更愿忠于自己的选择,正是这种坚持让帕斯择高处立而向宽处行,就像他的诗中所写:“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前进、后退、迂回,总能到达要去的地方”[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