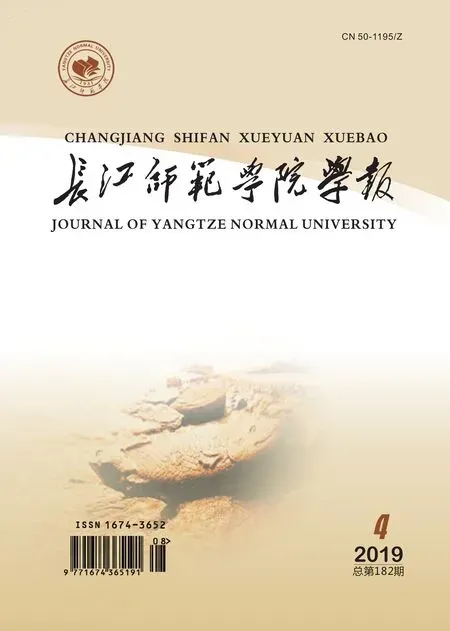哈尼族婚姻关系维系方式变迁
——以子雄下寨为例
张 宇,黄建生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昆明 650504)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绿春县是哈尼族人口聚居大县,截至2017年底,常住人口达23.46万人,其中哈尼族人口21.48万,占总人口的87.6%[1]。当地哈尼族有哈尼、哈欧、白宏、腊咪、期第、白那等多种自称,其中以哈尼自称的人数最多,子雄哈尼族属于腊咪支系。哈尼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臧缅语族彝语支,分为哈雅、碧卡、豪白三个方言。哈雅方言中又有哈尼次方言和雅尼次方言,戈奎乡子雄下寨流行哈雅方言中的哈尼次方言[2]。下寨距离子雄村委会7公里,辖区国土面积4.15平方公里,海拔1 100米,有耕地464.4亩,共有农户114户559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当地哈尼族在不同时期分别用婚姻成本、空间限制和婚姻模拟等方式来维持婚姻的稳定性。
一、当地哈尼族的婚姻特点
子雄下寨哈尼族婚配以一夫一妻的氏族外婚为主,近亲之间极少结婚,目前村内仅有一户人家是近亲结婚。同姓内婚配至少须隔四代以上,同时严格遵守“血不倒流”的姑舅表优先婚。正如村民李某某(男,45岁)所言:“如果你是我的姐姐,那么我的儿子、女儿就不能和你的孩子在一起①在当地方言中,“在一起”的意思是“结婚”或者“婚配”。。”子雄下寨哈尼族中,离婚现象较少。据初步统计,目前村里共有114户,离婚的只有5对夫妇,离婚率为4%。
在结婚仪式方面,当地哈尼族缔结婚姻关系需举行两个仪式,即简单仪式与复杂仪式[3]。所谓简单仪式,指男方将女方领进家门时举行的仪式,即女方开始在男方家长期居住时举行的仪式,从内容和形式上类似于汉族的“定亲”;复杂仪式是指男女在生育孩子之后举行的正式婚礼仪式,等同于汉族的结婚仪式。不管婚配几次,当地哈尼族男女终其一生只能举行一次复杂仪式。
从仪式内容上看,简单仪式主要是行磕头礼,当地人称为“wu du tong”。男方家先请莫批①“莫批”是哈尼族仪式专家,在仪式中用哈尼语所说的大意是:“两人从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女方不能再任意回娘家,男方家要让女方吃饱,男女双方以后要相亲相爱,同心同德,不能有异心。”选定一个良辰吉日,再邀请女方来到男方家中。当天男方家会宰杀一公一母两只鸡,待鸡煮熟后便开始献饭,由男方家母亲端着竹篾桌,桌上放着盐、花椒、酒、米饭、鸡肉,面向家中墙上不同地方的两个祖先祭台②两个祭台分别是男方男主人与女主人各自的祖先祭台。,男方和女方分别下跪磕头两次。磕头后,家中最长者先吃竹篾上的米饭与鸡肉,然后男方爸妈吃,最后再端到桌上大家一起吃。所谓复杂仪式,当地人称为“lao bei ba de”,即“摆酒席”的意思,摆酒席是复杂仪式的核心内容。男女双方分别在同一天宴请本族亲人和本村村民,上午先在新娘家摆酒席,一对新人给在座的亲朋好友磕头行礼,男方将彩礼钱全数交给女方父亲,意思是将女方“买”走,这时女方家长辈便开始哭泣,意思是自己养大的女儿从今往后再也不是自家的了;下午在男方家摆酒席,男女双方从女方家去男方家的途中以及跨进男方家门时都要由莫批举行一系列的仪式。在办酒席期间,男女双方的亲朋好友不能互串,即男方亲友不能去女方家做客,女方亲友也不能去男方家做客。此外在摆酒席当天新人的子女是不能参加婚礼的,须被送至亲友家照顾,并且不能吃酒席上的任何食物③哈尼族最初是不允许未婚先孕的,而现在的先育后婚是与最初传统相悖的,所以为了尽大可能地还原未婚先孕的传统,故而在新人结婚当天是不允许其子女出现的。。
从表征意义上来看,简单仪式实际上是向家庭(包括已经离世的祖先)公布男女双方确定恋爱关系的一个程序。通过仪式中的献饭祭祖活动,告知祖先及家人男方已经将女方领进家门,女方今后可能成为这个家庭的媳妇。一方面,主人想借此祈祷祖先保佑两人之间的关系稳定,希望他们能够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另一方面,祈求祖先保佑整个家庭安康。复杂仪式主要是向社会(即整个村子甚至周围村子的人)公开夫妻关系,同时将女人的魂引进家门,使女性的整体身心都正式归属夫家,自此以后女性必须自觉接受夫家的约束,两人成为当地社会认可的正式夫妻。简单仪式后两人间的男女朋友(或恋爱)关系获得了祖灵、家人、亲朋好友和邻里的认可,双方父母将不再干预双方的关系和行为。从此,女子开始公开居住在男友家,同男友家人共同生活。虽然简单仪式后双方开始同居,但在当地人的观念中,这一阶段仍属于恋爱阶段,两人间的关系仍然充满可变性,需靠双方自觉维护。
在当地哈尼族的婚姻生活中,离婚的程序比结婚简单得多。如果离婚由男方提出,则女方不用退还彩礼钱;如果离婚由女方提出,则女方需要退还双倍彩礼钱。现代社会还存在财产分割问题。如果分家了,无论哪方提出离婚,男方家产均要被平分。此外,双方都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日子进行“su la gu”(叫魂),离婚后女方的魂不能留在男方家,需要被叫回娘家;男方的魂也不能留在女方的身上,否则男方将会生病。在从简单仪式到复杂仪式的期间,如女方未怀孕,男女双方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分开或继续在一起生活;如果女方已经怀孕,但不超过3个月,女方可以选择堕胎,男方一般不会干预;如果女方怀孕超过3个月,男方家一般会要求女方将孩子生下来,当然,如果女方执意不肯,男方亦不会过分强求。假如在从简单仪式到复杂仪式的期间两个年轻人生了不止一个孩子,那么女方选择离开的时候可带走其中一个孩子,其余归男方家。
二、从“婚姻成本”到“空间限制”[4]
大致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分界线,子雄下寨哈尼族的婚姻维系方式经历了从“婚姻成本”向“空间限制”的转变,这一转变背后体现的是现代化进程影响之下当地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下文将以这两个时期为例分别予以说明。
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缔结的婚姻多为父母包办,即由父母给孩子安排婚事,并不考虑孩子自身的意愿。有意思的是,这种包办婚姻并没有导致较高的离婚率。据当地老人说,在那个年代,村内离婚的只有3对夫妇,现在那些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那时,当男孩差不多十五六岁的时候父母便开始为他们操办婚事。男方父母会提前找人打听哪家有合适的姑娘,对象多半是本寨或周边寨子的。接着便请姑娘那边的熟人上门说媒,该过程通常要进行3~4次,姑娘家才会答应。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一是对男方家庭进行一定的了解;二是将所有上门提亲的人进行对比,选出最合女方父母心意的。然后双方定亲,由媒人出面商量结婚日期,男方要交付部分的彩礼钱。彩礼钱包括两部分:一是用于将婚事定下来的礼钱;二是作为姑娘置办嫁妆的部分钱财。到了婚礼前一天,新郎在“巴里”(舅舅)及媒人的陪同下来到新娘家,将剩余的彩礼钱交付完,这时女方家中的长辈便会“哭嫁”。第二天女方家杀猪摆酒席,饭后,媒人带走一条猪腿,新娘在许多未婚姑娘的陪同下前往男方家。次日早晨,男方家摆酒席。酒席办完后,新娘立刻就要回门。回门的时候,新娘只带糯米粑粑回去,分发给跟她同姓的人。
老一辈离婚率很低,主要和家庭经济有关。如今已70岁的张某说,他15岁左右就在家长的包办下结了婚。女方家离他家大约七八里路,婚前双方都没见过面。村子里有不成文的规定,一旦建立婚姻关系,如果男人先提出离婚,那么女方家就不退还男方家送给的彩礼;如果女方先提出离婚,那么必须翻倍退还当初男方家送给的彩礼。由于他家的经济状况比较好,而他妻子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即便他殴打妻子,妻子也从不提出离婚。值得注意的是,老一辈人重男轻女观念较为严重,他们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父母不会再管她们婚后的生活。在当时并不宽松的物质条件下,女方家愿意退还彩礼的并不多,甚至有些人家是将彩礼钱作为今后儿子娶媳妇用的。因此女方提出离婚的少之又少。虽然那时的婚姻都是包办婚姻,但即便对女方不满意,男方也很少提出离婚,原因是担心损失彩礼。
当地通婚圈较小也是离婚率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笔者调查的3对夫妻中,相互间最远也只隔步行大半天的距离,其中有一对是本村的,有两对是邻村的。大家都沾亲带故,或者是朋友的子女,或者是远房亲戚的子女,再或者是托亲戚朋友提亲的。如果结合的新人闹离婚,亲友关系不免会受到影响。比如,李某(女,80岁)说,她很小的时候父母便给她包办了婚姻,两家算是有点亲戚关系,婚后她与婆婆的关系不好,丈夫和她的脾气也都很暴躁,经常吵架。当时双方家庭条件一般,周围又都是亲戚朋友,离了婚双方家人面子上都挂不住,后来家庭条件好了,儿子长大了,分了家,她就直接搬过去和二儿子住了。有时候,婚姻关系的维系也有出于对劳动力需求的考虑。1950年实行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土司制度,按家庭人口划分土地。正如李某(男,41岁)所说,媳妇进了门就算自家人了,也会分到一份耕地。1958年后实行并社,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按工分分粮食,媳妇就成为家里挣工分的重要劳动力。
“广义上的婚姻成本是指完成婚姻形式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时间、情感、金钱、机会等一系列物质与精神的总和。通常所说的婚姻成本是指狭义的婚姻成本,指完成婚姻形式过程中所付出的经济成本总和。”[5]从中可以看出,子雄下寨哈尼族这一时期的婚姻维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狭义的婚姻成本相吻合。子雄下寨哈尼族建寨至今有近200年的历史,地处山区,交通封闭,人员流动性小,农耕是唯一的生计方式。1958—1979年,在子雄下寨人们的生活特别困难,张某(男,55岁)回忆说:“那时候娶得晚的到处都是,家里没钱啊,有的人40多岁才结婚。”由于婚姻关系是在父母包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婚姻关系的维系不仅是个人的事,还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婚姻是礼品交换最基本的一种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以女人为礼品的结果远比其他礼品交换意味深长,因为这样建立起来的不仅仅是互惠关系,还有亲属关系。”[6]因此,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姻亲关系能够使大家互帮互助,共同渡过难关。而离婚会造成双方(特别是女方)经济上的损失,女方往往因为考虑要双倍返还彩礼而不得不在婚姻关系中采取隐忍的态度,即便受到丈夫的虐待,也尽量不先提出离婚。而对于多数男方家庭而言,他们亦无力支付第二次娶妻的钱财,所以即便不喜欢女方,也会尽可能地将就着过一辈子。
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教育、医疗、交通等各方面开始得到较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渐出现好转,经济因素在婚姻选择中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村内开始出现自由恋爱现象,村民李某(男,45岁)说道:“那时候我们谈恋爱都是在树林子里。”在这一阶段中,出现两次仪式①这里的两次仪式与1990年后的两次仪式不同,主要原因是因为男方无力支付全额彩礼,或双方或某一方无法直接凑齐婚宴所需的钱财,需要一段缓冲期,一旦钱的问题得到解决,第二次仪式便会提上日程。1990年后的两次仪式主要是给予先婚后孕一定的“合法性”,两次仪式的间隔在3~5年。现象,与此同时婚姻形式也由单一的包办婚姻转变为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共存。在当地部分家庭,男孩不读书后父母便会张罗给他们包办第一次婚姻。村民张某(男,41岁)说道:“我的第一个媳妇是我爸介绍的,才半年就离婚了,已经办过酒席了。后面娶的是自愿的,自己认识的。”如果老人主导的婚姻失败了,那么他们将不再干涉孩子的第二段婚姻,让他们自由恋爱。在这一辈中,离婚率也仅有4%。
这辈人离婚率低主要是因为文化教育水平低,人们的社会资本不足。对于女性而言,由于缺乏教育,她们的婚恋观常常是在老一辈的教导下形成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思想便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故而在婚后多数女性存在认命的想法,即便老公出轨、家暴,两人感情不和,只要没到不能忍受的地步,她们往往会选择隐忍。就如村民张某(女,40岁)说道:“我老公在外面找了个女人,不过他不敢带回家,村里人会说,嫁都嫁了,唉,就这样过一天算一天吧。”由于文化水平低,她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退而求其次,守住现有的生活方式。郭某(女,45岁)说道:“我最远也只到过绿春县城。”村子里像郭某这样的妇女占据了绝大部分。较低的文化教育水平让她们没有外出谋生的技能,没有外出交谈的语言能力,无法跨出这狭小的地域限制,只能以家庭为主,依靠家中的“一亩三分地”过活,从而家庭成为了她们的全部,故而她们不会轻易提出离婚。对于男性而言,由于高昂的生活成本和较低的职业技能,他们在外地只能从事最底层的抑或最基础的活计,所赚取的钱远远不足以负担其远在外地的生活所需,例如买不起房、娶不起妻子、养不活孩子等。如张某(男,20岁),曾经有过一个妻子,妻子生孩子后就与他分手了。外出打工的时候他遇到过一个心动的女人,听说女人是河南的,他直接就放弃了。他苦笑道:“他们那里彩礼钱要10万元左右,我哪里拿得出来?”因而即便是成家也只会选择在家乡或家乡周边。费孝通曾说,有限的地理空间令人们处在熟人社会中,社会舆论对他们的影响特别大。在当地,婚姻是一件很神圣的事,一生只能缔结一次,所以如果男女双方离婚,就会受到当地人们的指指点点,也会对自己的下一段婚姻产生影响。李某(女,20岁)说,她前男友是结过婚的,由于他凡事都听父母的,没有主见,而父母又与儿媳关系不好,所以两人离婚了。她不清楚情况才与他在一起,时间久了了解他的具体情况后,她也选择了离开。不久该男子又找了一个附近村子的女人,结果对方父母一听说男人的情况,当即不允许两人交往。因此,男性选择离婚的也很少。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的不足导致了社会空间的局限,间接促进了婚姻关系的稳定。福柯认为,空间不仅“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也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7],他通过对权力关系的分析为空间生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在当地,社会空间上的局限导致男性和女性的权利无法实现,这一“枷锁”有效地维系了当地哈尼族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
三、从“空间限制”到“婚姻模拟”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基本上都是先生育后结婚。在当地,虽然人们比较看重男孩,但并没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在他们的观念中男孩可以传宗接代,但姑娘更孝顺。正如村民李某某(男,45岁)所说:“没有儿子后面就没有传承了,家里有多少钱都没人继承,就成了别人的了。姑娘全部嫁出去了,自己的家都管不了,爸爸妈妈这边更顾不上了,人老了,就没有人能照顾我们了。平时姑娘对父母亲要好一些,现在我的姑娘嫁出去了,每隔一两个月她都会问我是否有酒钱。”因此,当地人在生了儿子之后,必须再生一个姑娘,认为这样才叫做好事成双,家里才会多禄多福,人生才圆满。等到儿女双全时,男女双方才会举行复杂仪式,正式缔结夫妻关系。由于教育的普及,原先因资源不足导致的婚姻维系方式已然失效。农业的现代化减少了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因而有更多的人口开始流向城市。在笔者调查的子雄下寨,当地16~25岁适婚年龄的男性女性均在外务工。随着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许多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她们越来越多地选择外出务工,这样的行为既增长了她们的见识,也扩宽了她们的接触面;更多的女性开始选择嫁到外地。根据择偶梯度理论,女性择偶是偏向比自己家庭条件优越的,而男性则相反,这样就出现了“男高女低”的婚恋模式[8]。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乡下女性嫁到城市,却极少见乡下男性娶城市中的女性。因此,农村女性开始大量外流,从而导致村子里适婚男性的人口数量多于适婚女性的现象。在男多女少的情况下,为了找到婚恋对象,男性青年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态势。女性不愁没人嫁,男性却愁没人可娶。虽然1990年之后,年轻一代的婚姻跨越了地理上的界限,婚姻关系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辈,但离婚率却非常低。截至2018年8月底,笔者并没有听到有离婚的夫妻。根据访谈的20名适婚年龄的村民口述,笔者将离婚率低的原因归纳如下:
首先,从包办婚姻向自由恋爱的转变。2013年,当地二级公路修通,这彻底改变了村里与外界隔绝的局面。村里大部分男女最多读到初中毕业便选择外出务工,多数前往广州或深圳的电子厂,在那里男女相互认识,然后谈朋友,如果合适便将对方带回家中,如果不合适便与对方分手。在自由恋爱的婚恋模式下,子雄下寨男女的结婚年龄普遍比老一辈大,思想心智更加成熟,更加有责任意识,这为他们日后的婚姻生活提供了一份保障。村内有一名21岁的男青年,他是在绿春县城和女朋友认识的,相处了两三个月后,他便随女方去了广州打工,可最终因为性格原因还是选择了分手。对于另一个20岁的李姓小伙而言,虽然家里一直催婚,可他觉得自己年龄尚小,连立业都难,所以尚无成家打算。他说:“做事情要考虑方方面面,更何况这是婚姻大事。结婚后要有能力让女方生活好,不然娶她干什么?”
其次,从先婚后孕到先生育后结婚的转变。最初,在当地未婚先孕是极为丢脸的事,一旦发生,就要请莫批洗寨子。当天男女双方牵着猪、狗绕寨子转,未婚先孕的女性被村里的老人像敲狗一样地打,经过这样的事情后女性的声誉严重受损,嫁人就必须选择远离村子的地方。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实际上,任何人类社会里,凡未经相宜的社会认可而要度过结婚生活的男女都要多多少少地受到苛罚。”[9]而如今未婚先孕却成为了一种常态,如果女方被领进家门时已经怀孕则不用进行简单仪式,如果没有怀孕则要举行简单仪式。从简单仪式到复杂仪式期间约有3~5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两人会生活在一起,性关系也得到固定,直到生育两个或多个孩子后才将复杂仪式提上日程。只有通过复杂仪式,男女双方才算是真正的夫妻。被调查人白某(女,22岁)坦言道:“在我们这里如果没有摆酒席,就算不得是夫妻,最多是我男朋友。”两个仪式中间的时间段则是给男女相处磨合的时间。通过磨合能够有效地降低婚后离婚的风险。李某(男,45岁)说:“村里的年轻人都是自己选择婚姻,生了小娃娃以后才办婚事,生了娃娃后的几年里看看她的性格,这个家族能不能稳得住。如果早早地办了喜事他们却合不成,离婚就不好看了。有了儿子姑娘就很少会离婚了,那个时候才能稳定。没生娃娃之前我们都不叫儿媳,而是把她当成朋友。”
最后是女性地位的提升。杜杉杉曾以“筷子成双”理论来阐述拉祜族的性别平等模式,通过两性合一来展现拉祜族社会中的男女平等。杜杉杉认为:“在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中,其主导意识形态、核心社会制度,以及主流生活实践对两性作出的价值评判是同等的,而且与性别角色无关。”[10]在笔者调查的子雄下寨,起初男女平等现象并不明显,而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男性竞争压力的加剧,村内男女的相处模式也开始改变。他们开始给予女性更多的自主权,开始考虑女性的想法,开始为女性分担劳务。村民白某(男,21岁)说道:“现在媳妇之所以难找了,是因为男女平等了,男人会做的事女人也会做,女人会做的事情男人也会做。”村子里打女人的现象基本没有了。村民李某(男,21岁)说道:“我爸以前经常打我妈,我从来没有打过我女朋友,打女人的男人不是男人。”张某(女,19岁)说,她爸爸以前也打女人,打跑了几个,后来娶到她妈之后就没再打过,并且早上最早起来喂猪、做饭,等东西都弄好了,她妈妈才起床。男女之间相处模式越发趋于平等。李某某(男,47岁)说,以前他只需要在山上犁田耙田,其余的事都归他媳妇管。现在,他媳妇割谷子,他打谷子,最后两人一起把谷子背回家;栽秧的时候,他搬秧苗,他媳妇插秧。而他的儿媳妇除了做家务基本不用干其他任何活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子女辈之所以婚姻关系稳定,最主要是与自由恋爱背景下的先生育后结婚习俗有关,与包办婚姻相比,自由恋爱中的男女有更深的感情基础。模拟是一种仿照的行为,由模拟的主体与客体构成。在子雄下寨,真正的婚姻是客体,先育后婚及简单仪式是主体。在主体模拟客体的过程中,客体的文化内在与形式并不完全同质地再现,而是介于似与不似之间。先育后婚的习俗实则是在模拟婚姻生活,简单仪式则是模拟婚姻中的结婚仪式,增强男女双方生活的仪式感。正如霍米·巴巴所指出的,“殖民主义规划了为自己的利益而必然实行模拟的策略;这个策略有自己的矛盾之处——它企图让被殖民者与殖民者又相同又不完全相同”[11]。在这里可以进行一定类比,复杂仪式处于强势和具有约束性的地位,而简单仪式则处于弱势和协商性的地位,它模拟了婚姻仪式,与真正的婚姻具有相似性,让男女双方能提前经历真正的婚后生活。在这种模拟的婚姻生活中他们“结婚”、生子,过着夫妻的生活,但又不具备婚后生活所有的因素。这种弱势对强势的模拟又是符合当下一代人的心理诉求的,即他们并不想过早地结婚,只是想提前感受一下婚姻生活,以便进一步了解双方是否适合。其次,先生育后结婚的模式通过模拟婚姻建立了稳定的“家庭三角”。费孝通指出,丈夫、妻子、孩子,分别为三角的三个顶点,三者之间的关系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结构,而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建立这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夫妇关系以亲子关系为前提[12]。村民杨某某(男,41岁)坦言道:“一般生了孩子之后家庭就相对稳定了,我们吵架了,一想到孩子就不想离婚了。”最后,先育后婚的婚姻模拟也是规避无后的重要手段,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观念影响下,男性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而先生育后结婚便是在该观念驱动下的产物。两人磕头行礼后只是确定了稳定的性关系,并不代表建立了稳定的婚姻关系。而在男多女少、竞争压力大的年代,男性很有可能在分手后出现长时间找不到女人的现象。因此,先生孩子,即便今后两人分开了,至少为传宗接代提供了保障。当然,为了确保香火由男人传下去,子雄下寨存在入赘的现象,如果家中只有姑娘没有儿子,那么有一个姑娘便不会出嫁,而是将男性招上门。作为回报,老人过世之后,家中的财产便归属两人所生的孩子,也就是说从孩子生下来后,男人才能被记入家谱。
四、结语
变迁是文化发展的永恒主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哈尼族社会生计方式的改变、教育水平的提升、国家政策的引导等各种因素,令当地婚姻关系的稳定性不断遭受冲击,而每一次的婚姻关系维系方式的变迁都对由冲击而带来的风险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
婚姻成本高是第一阶段哈尼族人离婚率低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高昂的婚姻成本约束了人们的行为自主性,从而降低了婚后离婚率,间接使婚姻关系维持稳定;另一方面,高昂的婚姻成本限制了人们对自由恋爱的追求,违背了人的本性和意愿,为今后婚姻关系维系方式的变迁埋下了伏笔。社会空间的限制在某一段时期内的确对婚姻关系的维系起到了积极作用,将人们限制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从而间接降低了离婚率;但从另一方面而言,与“婚姻成本”一样,它们都是一种外在性的约束,一旦社会环境改变,该方法就会自然而然地失去效力。先生育后结婚的婚姻模拟,给予了男女双方一定的选择缓冲期,降低了离婚的风险。婚前落夫家有助于女方提前了解男方家庭,减少了在结婚之后所带来的婚姻成本。相较于包办婚姻,自由恋爱的男女双方都比较注重自己的意愿,通过自由恋爱能够增进男女双方对彼此的了解,有利于结成性情相合、志趣相投的夫妻。然而,当地目前稳定婚姻关系的手段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生育孩子后,如果孩子父母最后并未结婚,那么孩子将会在儿童时期缺失母亲的照顾。众所周知,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共同陪伴。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其心理极有可能受到创伤,严重者离婚甚至会影响孩子今后的生活。离婚也会给男女双方带来一定的创伤,这些创伤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的。当地哈尼族为适应当下的婚姻形势而选择的婚姻关系维系方式有其自身的优点,也存在着隐患,在将来的发展中必将经受时间的考验,但可以预见的是,当地哈尼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生活智慧应当足够让他们面对未来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