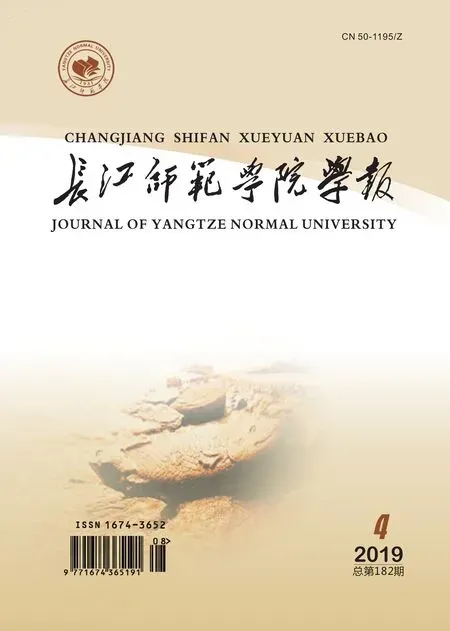论20世纪80年代乡村叙事中“进城”话语的生产
贾鲁华,尤丽洵
(黑河学院 人文传媒学院,黑龙江黑河 164300)
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一个生活拮据、愚昧的前现代乡村空间和一个物质充裕、文明的现代城市空间被捆绑在一起生产出来。如何安置农民、特别是乡村青年的问题,成为了突出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实,在柳青20世纪50年代的《创业史》中,就出现了改霞进城的难题,改霞和作品中诸多人物反复、细致的辩驳之后,最终还是进了城,其中蕴含的是特定时期如何处理乡村知识青年与农村建设关系的“难题”。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中,乡村知识青年与农村建设的关系“难题”又重新回到文学叙事当中,然而,经历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及改革开放的浸润,这一“难题”的现实指向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柳青在《创业史》中虽然力图构建农业集体化生产的话语空间,但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新中国成立后优先发展工业的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的话语空间中,一个与现代化城市相“对立”的落后乡村被生产了出来,从而使得当时的乡村青年对城市生活产生了美好的想象,并尝试通过“走进”城市寻求异于乡村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说,乡村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进城”意识已然成为20世纪80年代话语空间中的显明性元素。
一、“进城”意识的生产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多个乡村叙事文本中,皆出现了苦难乡村映照下的一种美好城市想象。在贾平凹的《小月前本》中,经常外出做生意、见过世面的门门向小月讲述了城市男女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去动物园接吻的事情,小月就开始认为自己什么也没见过,从而羡慕起城市人的“好”来。其实,农村改革时的小月已经与喜爱土地的父亲产生了生活与生产选择的分歧,小月在选择撑船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不愿在土地上“煎熬”的想法。当经常往返于城乡的门门向小月讲述了一个物质丰裕、文明的城市时,那个纯净、自然的河流已经无法承载小月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当小月的父辈承载着千百年来农民的生活习惯安然于农业生产时,小月这样的乡村青年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了相对多样化的选择。人们可以如才才般承继农民的衣钵在土地上负重前行,也可如小月般在乡村空间中做副业生产,更时兴的做法是如门门那样穿梭于城乡之间做生意,当然也可以在国家已然开放的情势下进城……
1982年,谌容发表的小说《弯弯的月亮》更清晰地讲述了乡村如何安置青年生活想象的故事。小说中一对小恋人在麦收后去县城看电影,但在二人去看电影的路上,展示了小莲子向往城市的意识。小伙子金泉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去过镇里、县里,还去过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在金泉向小莲子喋喋不休地讲着北京的故宫、北海、博物馆等,小莲子产生了进城当工人的想法,这种想法直接来源于对北京的想象与乡村劳作生活的对比,结果是一个美好的城市空间和一个辛苦劳作却贫穷的农村空间被捆绑式地生产了出来。见过世面的金泉对未来的想象中畅想着“消灭城乡差距”与农村的美好明天,然而,在公社何主任把金泉们的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时的埋怨看作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表现时,人们仿佛已经看到了乡村美好生活构建的难题。金泉与小莲子冒险去县城看电影的举动,或可被看作乡村青年进城的预演。
郑义的《老井》展现了一个封闭山区缺水的苦难生活状态,以及外来文化介入其中时人们的思想变迁与挣扎。为群众找水的旺泉作为传统文化的承继者留在了乡村,而去过北京、觉得在太行山生活憋屈的赵巧英在故事的结尾还是离开了乡村要出去干一番事业。
显然,小月和小莲子对城市的美好想象已然被生产出来,甚至在《老井》中,郑义让赵巧英走出了乡村,但是乡村(知识)青年进入城市后的生活状态在叙事中是空缺的。然而,当乡村生活无法满足乡村青年美好生活的想象,对城市的向往必然会促使他们进城。
二、乡村(知识)“青年”的进城书写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初期)进城的农民不得不面临着“过渡期”的世界性难题,恰如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其名著《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所言:“大多数农业劳动者意识到了传统世界的崩溃,但还不善于在现代世界中从事活动,他们的生活跨越两个世界,一方面被禁锢在旧的结构里,另一方面不断地受到‘现代人’进步和城市的吸引。”[1]142显然,孟德拉斯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转型期农民面临的生活选择与意识生产的讨论。具体而言,这种旧的结构首先表现为“户籍制度”对农民人身与思想的束缚,但“现代”的吸引又让具有一定知识与能力的乡村青年率先开始了对这一难题的冲击。当然这一过程容含了人生困境的挣扎,同时是一个深刻的文化构建,以及一个痛苦的实践过程。
最先在文学中触碰“户籍”问题的是作家路遥。1980年2月22日,路遥给谷溪的信中说:“国家现在对农民的政策具有严重的两重性,在经济上辅助,在文化上抑制(广义的文化——即精神文明)。最起码可以说顾不得关切农村户口对于目前更高精神文明的追求……大量有文化的人将限制在土地上,这是不平衡中的最大不平衡。如果说调整经济的目的不是最后达到逐渐消除这种不平衡,情况将会无比严重,这个情况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示出。”[2]显然,路遥的思考是现实的。路遥已然表达出“有文化的人”在土地之上还有着“更高精神文明的追求”的想法,这当然是典型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但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户籍制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着20世纪80年代农民的生活诉求,而破除户籍制度也确是现代化话语的应有之意。然而,这却是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话语结构之中的显明性难题、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现实性难题,路遥的思考放置在《人生》与《平凡的世界》的叙事中,高加林与孙少平这两个乡村知识青年就背负着这一难题,走进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追求的实践路径之中。
在路遥的两部小说中,都有着显明的城乡生活的比较,直接指向的是贫困乡村和丰裕城市的话语生产结构,特别是《人生》直接面向户籍制度中的城乡分立,及对农村青年的限制。或可直接说,路遥已经超越了表面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思考,进入到人的生存价值层面的讨论:这不仅事关进城的现实性需求,还关联到了进城的价值构建。
在路遥的叙事中,通过城乡二元体制中日常生活的比较,一个底层的乡村被凸显出来,而有现代知识的乡村青年高加林和孙少平也就顺势而出,成为了冲击城乡二元结构的先锋。人们永远不能忘记孙少平在雨雪交加的寒冷中“偷偷”去取“黑面馍”时让人们热泪盈眶的情景;也不会忘记高加林去城里掏粪时遭到克南妈妈羞辱的悲愤……
董丽敏在讨论《人生》时,认为这些“危机”通过一系列理论话语呈现了出来:“农村基层社会的权力变异,利益重组所带来的内部分化,劳动意识形态的崩溃,私领域的个人诉求强行楔入公领域……”[3]并进而认为,高加林的所作所为只能放置进这一系列危机语境中,“才能被精准地定位与讨论”[3]。即是说,从“共和国前三十年”到20世纪80年代,乡村的结构性变迁已然使得整个社会结构中出现/生产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从而致使乡村(知识)青年找不到集体化生产时期由“劳动意识形态”构筑的主体意识,从而走向城市并不仅仅意味着富足生活的构建及其现代化的美好指向,更关涉到乡村(知识)青年如何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语境中寻找主体意识,以及参与到乡村建设与宏观社会的构筑之中。
路遥让高加林和孙少平读书,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牛虻》、读《红与黑》,读各种报纸……这是截然不同于农民身份的一种日常生活元素,或者说,路遥不断地生产着他们不同于农民的身份意识,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现代化生活想象。两个高中生拼命读书的背后有着一种与农民日常生活状态不同的生活诉求,就如路遥赋予高加林读书的意义:“不必隐瞒,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4]5我们不得不说,路遥的这种身份认同取向当然是有问题的,且不说曾经作为革命主体的农民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只说农业生产在人类生存条件中所居的地位,也不可能让大批乡村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但是对路遥的思想取向又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恰如董丽敏所言:“从身体到精神,高加林近乎本能地排斥自己的“农民”符号,这显然可以看作是历史转折期劳动乌托邦崩溃传递到农村知识青年身上一种结果,这种排斥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却不能仅仅依据这种排斥就简单地对高加林进行批判和否定……更多可以理解为高加林不屈服于历史与现实所给予农民之子只能当农民的固定人生道路的反抗……当农民永远沦落在社会底层任人鱼肉的时候,当青年一代的农民只能简单复制父辈们的宿命的时候,无论如何,对此的逃离甚至反抗,都是天然具有一种正当性的。”[3]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不仅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而且是现代化知识替代劳动意识形态转换的必然结果。
显然,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知识成为乡村青年逃离乡村的一种资源。于是,路遥让高加林和孙少平都成为农村少见的高中生,其中寄寓的思想指向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当他们高中毕业时,大学不在高中招生的政策以及“从哪来到哪去”的就业原则,使得他们不得不再次回到农村。虽然二人都有着短期民办教师的经历,但是由于乡村权力体系的影响或者乡村小学被取消等原因,他们终归又成为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此时,通过读书而建构起来的“生活在别处”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读书而产生的走出乡村的理想与贫困的现实处境的鲜明反差,依然是高加林们进城的原初动力。
此时,我们不得不看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虽然孙少平与高加林的离开乡村、走进城市的生活想象和原初动力是相似的,但是就进城的价值取向来说,路遥对孙少平的塑造要比高加林丰富得多。高加林在县城读高中时勤于读书、眼界开阔,高干子弟黄亚萍便与高加林有了朋友般的交往。如果说,读书打破了城乡子弟的界限,但是高中毕业之后的现实遭遇使得问题凸显出来。高中毕业之后,依据回户籍所在地的原则,城市里的学生留在城市找工作,农村户籍的学生必须回到农村,如城市的黄亚萍做了播音员,克南也在县副食品商店找到了做保管的工作,但高加林只能回农村。虽然高加林初回农村时做了民办教师,但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着,而且是两个不同生存空间的隔离与不同身份的巨大差异。本来对高加林有好感的黄亚萍很快与克南确定了恋爱关系,并非她不再喜欢高加林,而是她不可能嫁给农民,她受不得农民的苦!城乡分割成的两个世界在文化和经济层面都凸显出它们不可逾越的鸿沟。
高加林回乡后虽然做了一段时间民办教师,但是很快就被大队书记的儿子顶替了职位,他只得重新回到土地上劳作。此时,路遥准备了充分的理由让高加林构筑与众不同的日常生活。首先,作者让高加林有着完全不同于农民的外在形象,一副经过规范体育锻炼造就的身材,并没有在土地劳动过的痕迹。其次,路遥让高加林时刻具有充分的远离农村的意识,就算回乡落魄时有一位姑娘主动奉献自己的爱意,高加林却会提醒自己,与没文化的巧珍处对象就是堕落、消沉的表现,并进而认为这是甘心当农民的心理在作祟。最重要的是,路遥不断地为高加林制造读书的机会和场所,让其具有不同于农民生活的精神性元素。
这样的一种人物形塑足以显示出路遥是如何痛感于农村与城乡二元结构,如何想让高加林走出贫困落后的高家庄。但是,在户籍制度仍然在起着作用的年代里,高加林即使有才干,要想实现进城的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路遥设置了一个在部队的叔叔转到地区做了劳动局长的情节,这一概率极小的设置是情节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同大队书记儿子顶替他的教师职位一样,权力成为比知识更有威力的元素,使得高加林成为县委通讯组的干事。而高加林的知识素养与能力又使得他在县城里迅速成为一个“人物”,并且重新赢得高干子弟黄亚萍的青睐。此时,知识与权力显然成为高加林进入城市生活的主要推动力,其中透露出显然已经与以前劳动意识形态力量迥然不同的情景,因而使得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变迁的“秘密”得到浓缩性的呈现。
高加林进入城市后,小城的现代青年黄亚萍用现代化的“物”包装着高加林,从而使得他内有现代化知识、外有现代化“物”的装饰。这一“屌丝逆袭”的叙事方式使得高加林激烈的心理冲突呈现得较为简单,虽然他对自己抛弃的农村姑娘巧珍心存愧疚,但是自己走出农村、进入城市/现代化的渴求压倒了他的愧疚。高加林进入城市的主要目的是:一是摆脱农村的贫困,二是走进现代化装饰的梦想。显然,在高加林身上,路遥作了不同于“共和国前三十年”的价值构建。恰如董丽敏所言:“从民办教师到通讯干事,高加林这一个案正好暗示了农村知识青年人生道路选择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一个巨大变化——不只是彰显了职业知识生产者的魅惑,使得从体制外走到体制内,成为了农村知识分子毋庸置疑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充分展现了城市的吸纳力,使得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了农村知识青年显示自身成功的唯一砝码。在这一转变中,不仅农村知识青年的自我价值认定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且其在社会与历史中承担的使命也随之蜕变;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的知识在特定的时空中发挥作用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3]
但是,好景不长,高加林的命运发生了一个反转,权力将高加林带出了农村,之后却又戏剧般地把他抛回到土地上。当高加林趴在土地上痛哭时,人们只是看到了路遥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空间中的无目的徘徊,甚或只是一种人生状态的无奈。显然,路遥是对乡村知识青年与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乃至于城市空间的现实审视,但张高领认为:“无论路遥是否自觉,高加林并未克服柳青在改霞身上所遭遇的难题,城乡差别这一结构性不平等变为个人的不平等,而个人主义式的想象性解决不但无法提供回应上述难题的有效方案,反而遮蔽了这一难题的复杂历史内涵和现实困境。”[5]20世纪80年代,以西方现代化为主要路径的话语构建中,个体性被迅速生产出来,从而使得城乡的差距呈现出的“不平等”“理所当然”地移植到了个人身上。
问题在于,即使人们论证了高加林进城的合理性甚或可行性,即使人们冲破了“户籍制度”,那么,城乡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如何安置乡村知识青年?如何塑造时代“新人”?城乡问题若不仅仅是“户籍制度”造成,那么如何追寻其根源并解决这一难题?董丽敏的判断无疑是深刻的:“如何在历史的同情的立场之外,为高加林们探寻可能的出路,是否像高加林这样因果报应式地回归农村就足以赎罪,像刘巧珍这样悲天悯人地宽恕一切就可以超脱世俗生活的伤害,抑或像黄亚萍这样得放手时且放手才能获得解脱……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提供了对现实的思考,却没有能力想象并探索通往未来的可能性,因而,它显然是未完成的,只能被看作是一种有限度的现实主义。”[3]显然,如若在此思维路径中讨论高加林的现实性境遇,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路遥很难给出一个答案。
相比而言,路遥塑造的孙少平形象却要复杂得多。孙少平虽然也在竭尽全力走出苦难的家庭和贫穷的双水村,但似乎超越了城乡对立、超越了对现代化之“物”的非理性追求。孙少平同高加林出走的动力类似,读书而得的现代化意识与贫困乡村的生活状态的鲜明对比,确实是孙少平出走的最初动力。但是我们不得不重新还原的一个事实是,田晓霞在孙少平的生命中所起的“导师”般的作用,这当然指的并非仅仅是田晓霞从家里拿书、拿报纸让孙少平读,而是一种与爱情有关的人生路径的引导,其中最典型地体现在田晓霞对孙少平高中毕业时的嘱托,也有对他毕业之后农民生活道路的判断:“不管怎样,千万不能放弃读书!我生怕我过几年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满嘴说的都是吃;肩上搭着个褡裢,在石圪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为几抱柴禾或者一颗鸡蛋,和邻居打的头破血流。牙也不刷书都扯着糊了粮食囤……”[6]313其实,田晓霞描述的是一个“典型”农民的日常生活状态。当然,不能忽视田晓霞的嘱托在孙少平心中留下的印迹及其产生的动力,但孙少平其时并未把进城当作必然的出路,而是要去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希望自己扛着很重的东西”。这样一种生活选择明显比高加林的理想要复杂得多。
在孙少平后来的生活中,读书确实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双水村的土地上劳作时、在黄原城做小工时、在暗无天日的煤窑里,孙少平一直在读书,他没有像田晓霞说的那样成为一个典型的农民。在路遥的描述中,孙少平并不鄙薄乡村与农民,他坦然接受并赞誉着农民的世界;但同时又想象一个农村之外的世界,他不愿受到农民“狭隘性”的局限,从而成为一个有着“混合型精神气质”[6]319的人。这样的想象使得他不甘心在农村生活,并幻想着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去闯荡一番。他并不惧怕劳苦,但是害怕农村的辛苦劳作会使自己失去自我的精神世界。于是,孙少平走出了双水村,去黄原城的桥头做了揽工小子,承受着比农村更重的劳苦。事实上,路遥让孙少平离开乡村成为一种仪式。
此时,路遥的叙事已经不同于创作《人生》时那般简单了,高加林进城是现实的选择,他回到土地时又有些不知所措。路遥赋予孙少平一种精神性的取向,通过苦难的承受去探索生命超越现实的可能,所以他走出了双水村,但又拒绝了城市。在孙少平给妹妹的信中谈到了他对苦难的认识,这也表明了他对生命的认识:“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7]326这是一种仪式性的命运探索。虽然,人们很难从孙少平的遭遇中去解读城乡二元结构,但是路遥赋予孙少平的精神气质却多少有了一些稍显另类的启蒙性质,当人们走向一个能够忍受苦难的深层次生命体验,并且能够彰显其所产生的力量时,权力、城市等对农民就会失去压迫性。
当然,此处对路遥小说的解读是在摒弃/忽略了小说中非常丰富的内容基点上,仅仅通过高加林和孙少平两个人物形象阐释了一些有关城乡的问题,它们当然容含了有关集体化与家庭联产责任制、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性变迁等诸多内容。即使这样,人们也会看到,路遥对城乡二元结构更多付诸于精神性的超越,这当然与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语境与路遥的现代化想象相关。
三、“农民工”进城的初步想象
事实上,在对20世纪80年代社会结构的讨论中,很难冲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定;在文学叙事中,很少有对非乡村知识青年进城谋求生路的描述。这大概是由于当时的特殊语境决定的,一方面是户籍制度并没有放开对流动人口的限制;另一方面即使有所松动,农民千百年的负重前行并未让其有改变生活的充分准备。当然,最主要的一点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农民解决了“吃”的需求,暂时还没有产生别的生活的需要。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改革转向城市,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效益的逐步释放,农民的“好日子”出现了某些不理想的状况,如田中禾的《五月》描述了卖粮难的问题,郑万隆的《古道》则揭示了卖棉难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民开始进城寻求经济来源的多元化。应该注意的是,此处讨论的农民进城显然不同于前述诸如赵巧英等人的想象,更不同于高加林在现代化召唤下的进城实践,他们进城是由于生活的困窘,而农村已然不能满足农民的切实需要。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叙事中,但农民工形象仍然很少,直陈农民工问题的小说也还不多。
在1988年阎连科发表的小说《两程故里》中出现了对农民进城打工生涯的简单描写。小说主要描述的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基层政权与宗法制在乡村的结构性变迁,变迁的动力是外出打工赚钱。小说围绕着程氏家族的同辈兄弟程天民和程天青二人争夺村长职位的矛盾展开。程天民虽然是公社秘书,但在“共和国几十年”的岁月中,他在两程故里的权力结构中,比书记、村长的权力都要大;而程天青是地主出身,在“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地位可想而知,对他最大的压制性力量就是程天民。程天青被迫去县城寻求生计,慢慢成为了村里的富裕人家,并且逐渐带动村里的不少人外出闯荡。正是程天青在城里做生意赚取了钱财,使得他有力量重新改变两程故里的权力与宗法关系,并挑战着传统与现实的政治权力的权威。程天青依据手中的钱财,广播善缘,帮助穷苦人家渡过难关、招揽村里喜忧诸事,逐渐取得了村民的好感。特别是被县里评为致富能手后,又买了汽车做运输生意,逐渐有压倒程天民的地位之势。二人的矛盾爆发于修缮祖庙之时,程天民设计使程天青的财产损失殆尽。小说结尾并没有揭示村长的最终人选,但是在整个叙事中,分明可以看到钱财正在改写着乡村的权力结构和宗法结构,而钱财的来源却非来自于土地,也不是来自于乡镇企业/副业,而是来自于城市。如若暂时忽略20世纪80年代之后乡村的现实情况,阎连科的叙事无意中表现出满足农民致富欲望的另一种路径:进城打工。
事实上,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匹配的改革是逐步放开农村劳动力以使其自由流动,特别是1984年开始的城市改革,使得农民开始尝试性地走进城市。从《小月前本》萌发的向外意识,到《人生》中高加林“走出-回归”的悲情展示,再到孙少平执着于外面世界的想象与实践,都展示了农民走向城市的人生姿态以及饱含的对城市的美好想象,这当然是作家们对中国社会改革与现代化取向的乐观想象,如论者所言:“现代性作为一种关乎物质形态、秩序准则、伦理道德、思想意识等发展与变迁的时代特征,俨然成为当代作家统摄文学创作话语的重要标杆”,然而,“现代性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促进人类社会迈向文明的征程中,也必然对长期栖居在相对静态的地方的人们产生很大影响。”[8]94即是说,走向城市的意识与现代化想象的背后,掩盖了农民面对这一变化所产生的惶惑、恐慌心理,以及社会变迁中的复杂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