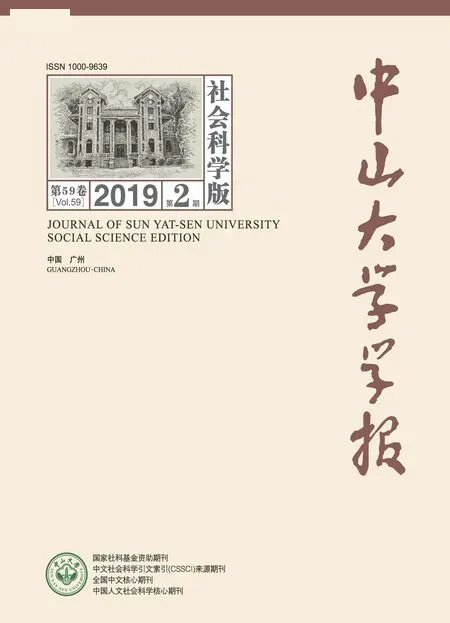晋唐时期的山水认知与地学山水记的文体流变*
李 翠 叶
山水记是中国古代散文重要的文体类型。关于地学山水记,学界关注较少,一般将其作为文学性山水游记产生的源头进行简单介绍。这两者在文体特征、文体流变、表达技巧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单篇的山水记文献最早出现于魏晋时期。至唐代,山水散文创作一直存在文学性与地学性两种倾向。《全唐文》中现存地学山水记文献共有16 篇,但一直未得到关注与重视。我们需要对地学山水记的来源、性质、文体变革的历史语境和文体流变作更深入的梳理。地学山水记,它的产生背景是魏晋地学知识革新下所创造的截然不同的“山水认知”体系。在文体流变上则经过了从记述形态向记体文的转变。
一、魏晋州郡地记中的山水认知与记述形态
文学性山水游记,主要以“山水描述”这一要素为判断标准,因此这一文体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禹贡》《山海经》《封禅仪记》《登大雷岸与妹书》等一切有山水描写的段落。“就体例来说,山水记有序记体、书信体、日记体、记叙体和速写体等多种形式。”*罗宗阳:《漫话古代山水记》,《九江师专学报》1989年2、3期合刊,第109页。但是,地学山水记,它的产生背景是魏晋地学知识革新下所创造出的截然不同的“山水认知”体系。认知和审美的区别在于,认知是基于对事物整体知识要素和认知架构的记录,而审美是对事物某一项知识要素的详细刻画。审美背后是文学技能的展现,目的在于情感的抒发交流。认知背后是知识体系的发展,其目的在于有补于公共认知。
魏晋州郡地记中的山水,确切地说是山川、河流。山水记文体的生成,在知识的储备上,首先取决于对山、水认知体系的成熟与完善。魏晋州郡地记中的山水认知,主要是通过“见闻认知”和“汇集认知”这两种方法来把握。其中,“见闻认知”通过对山水物象的命名、分类、特征描述、空间区分等方式,以一种理性架构描述经验中的存在,体现记录背后的理性控制,从而建立地学的认知架构。“汇集认知”,是指汇录关于一地的各种自然知识和历史人文知识,将见闻认知、官方文献、口传文献汇集,围绕一种知识进行理性有序的整理,从而使以前散见的知识得到系统的、理性的保存。这就形成了以山水为经,融合人文历史与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于一体的文体特色。刘知几《史通》曾讥评此类州郡地记内容过于丛杂[注]刘知几,浦起龙通释:《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8页。。而从认知角度讲,这正是地学认知的一种重要途径。
人类有了认知能力后,记述成为重要的语言表达方式。查看明清及当代关于记体的研究,有进行文体区分的,如“朱石君言古文有十弊……‘记、序不知体裁’”[注]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434,1254,1241,1294页。;有提到源流的,如“记,记其事理,必具始末。其原为事记、物记、杂记,其流为柳宗元”*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434,1254,1241,1294页。; 提到文体特征的,如陈绎曾言“叙事,依事直陈为叙,叙贵条直平易。记事,区分类聚为记,记贵方正洁净”*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434,1254,1241,1294页。;“记,以记事,贵方整。纪,以纪事,贵切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434,1254,1241,1294页。。陈平原认为:“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杂记的得名却是晚近的事。明人吴讷、徐师曾仍只讲‘纪事之文’的‘记’,以夹杂议论者为变体;姚鼐为‘杂记’正名,可也未曾仔细分疏。直到林纾,方才明确提出‘综名为记,而体例实非一’。”[注]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2页。山水记即属于杂记。杂记中的认知性记述,本是对于各种知识的一种存在性记录和描述。它的复杂性在于行文本身就是认知架构和知识要素的形成与使用。它是一种智力训练和语言表述习惯的逐步形成。客观知识在一定的语言体式下取得一种清晰性和审美性。这种“简洁生动,不事雕琢”,我们称其为“记述形态”。魏晋时期州郡地记的山水记述,完全按照山川水脉本身的自然属性进行描写。它的文体价值在于形成了山水专题的记述典范,确立了山水认知的思维方式和知识架构,是知识细化的一个表现。“文体其实就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文体发展与人类思维能力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有关系。”[注]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而这些正反映在它的书写形态、记述方法、记述架构与记述对象上。
在书写形态上,州郡地记中的山水认知采用的不是篇章形式,而是一条一条的记述,以单行散句行文,随物曲折,务在传达地理之实。它反映的是人类在感性认知下的一种经验积累。在记述方法上,主要有记录、描述、考证三种。所谓记录,其本质是对感官所能接触到的天地万象的分类、存录,即“区分类聚”。这种区分定名即是撰文的第一步。而描述,则是对山水物象因分类而凸显的各种特性和知识架构的掌握。考证,主要是辅助于记录与描述,始终以山水自然形态为经,重视对山、水、地名、古迹及有关历史人物、事件的确凿记录和考订。
在记录层面,首先要定名,记述对象由此产生。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辨区域、征因革。如蜀国谯周的《三巴记》:“初平六年,荆州帐下司马赵韪建议分巴郡诸县,汉安以下为永宁郡。”[注]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8,178页。它的记述方法在于写其分合隶属。二是在区域范围内存录一地之地理物象。在记述方法上,则以郡县为中心,按照方位里数引出地理物象,并对地理物象进行史地文的综合记述,并辅以考索、实证,如山谦之《丹阳记》:“江宁县南四十里慈母山,积石临江,生箫管竹。王褒《洞箫赋》所称即此也。”*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8,178页。这种语言架构是地记非常鲜明的表达方法。三是对于各种地理形貌进行区分类聚。如山,有“岗、岩、陵、洞、穴”;水,有“湖、泽、陂、塘、池、潭、峡”等等。这些分类成了后来唐朝类书“地”部的二级分类。葛兆光认为:“七世纪的人们……他们试图把所有的知识这些分类,清理成一个结构性的体系,以便自己能对这些知识提纲挈领。”[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15页。记述的目的在于对地理物象进行分类以尽格物之用。
魏晋州郡地记的描述并不指向审美,而是指向认知。关于地理物象的形貌特征,通过上下南北、间隔广修及数量词来表达。这种记述方法,其本质在于传达物象在空间中的位置与延伸。如盛弘之《荆州记》:“始安有甘岩,岩林峻茂。下有穴,达南北。其间可二百许步,口高二丈五尺,广十九尺。其西北有三溪,殊源别涧,合注其下。”[注]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216,189,182,106、73,247,252,239,192页。在记述山上物产时,魏晋州郡地记多以“出”“有”字结撰。如山谦之《吴兴记》:“於潜县西六十里有晚山,悉是松木真墨所出也。”*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216,189,182,106、73,247,252,239,192页。吴穆之《义兴记》:“阳羡县塘西潜壤中有黄土,色如精金。”*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216,189,182,106、73,247,252,239,192页。其记述方法在于描绘物产之形状、颜色、功用。关于各种水貌特征,先须认知河、泉、堰、溪、池、涧、温泉等不同体貌,然后才能有不同的记述内容和方法。如泉水,则关心其水质之清浊、甘美,而堰、池、塘为人工所造,故多记何人修筑和修葺之事及其功用。如《吴兴山墟名》:“蠡塘,昔越相范蠡所筑。”《洛阳记》:“河东盐池长七十里,广七里。水气紫色,有别御盐。”*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216,189,182,106、73,247,252,239,192页。作为“知识性著述”,州郡地记中对山水认知所产生的记述对象与记述方法成为后来单篇地学山水记的基本语言表达体式。
州郡地记在存录和描述地理物象之外,已经有山水“风景”。这种“风景”内涵的构成,目的不在于传达美感和情趣,但确是后来文学性山水描述的取资之处。小川环树认为:六朝时期“风景”一词的意涵,着重在空气、光影与氛围的变化,并非如中唐以后的“风景”已作为观览物的全称[注][日]小川环树:《论中国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首先,这种“风景”是对山水、云雾、风雨、光照关系的描述。即最初在地记中描写山,只写山与云、风、雨、日的关系。这是最高理念的,也是最直接的经验之象。周易以“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注][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说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96页。为最初的自然现象,这是山水记述形态产生背后的认知架构。如雷次宗《豫章记》:“(风雨山)在南昌,山高水湍,激着树木。因霏散远洒如风雨。”*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216,189,182,106、73,247,252,239,192页。荀伯子《临川记》:“(灵谷山)悬岩半岫,有瀑飞流,分于木末,映日望之如掣练。”*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216,189,182,106、73,247,252,239,192页。地记的这些描写奠定了最初“风景”的内容。地记对山水特性的把握,是后世山水散文创作的源头。其次,写山势与水流的结合,常从山的实际形势,造成的水流样貌来写。作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不同区域的山水关系的认知和保存。如《南康记》的雩都峡,因“高岭稠叠,连岩石峙。其水常自激涌,奔转如轮,春夏洪潦,经过阻绝”*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216,189,182,106、73,247,252,239,192页。。记述水源流向和山脉的关系,是地学认知的又一关键要素。这些描写并不在于创造一种烟雨氤氲的审美意境,而是客观的描写。而越是客观,其中内蕴越丰富,可以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最原始的、最丰厚的创作素材。再次,写山水光色的明暗及山水相映之势,尤其是光的参与,是山水记中比较明显的特色。宋郑辑之《永嘉记》:“大溪南岸有西山,名为城门。壁立,水流从门中出,高百余丈,西流瀑布,日映风动,则洒散生云虹,水激铿响,清泠若丝竹。”*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216,189,182,106、73,247,252,239,192页。它形成了后来山水记作品中常见的一种记述内容。另外,有关声音描写的,有岩间泉声、树间风声、林间猿声等。光照、声音以及山水之间多样的关系,本为事物本身之特征,地记通过这种记述方式扩大了时人的认知能力。后来晋朝山水诗、山水赋在内涵上的进一步提升都得益于此。地记对各地山水的真实描述对于魏晋文人的地学认知和语言表述都是一个极大的拓展。
魏晋州郡地记的山水记述展示了时人对山水认知的成熟。由认知型记述所确立的记述对象,形成了基本的地学知识要素,而采用的记述方法和角度,形成了基本的地学认知架构和稳定的文体特征。这些典型的句式和认知要素,在同时期的各类州郡地记以及后来的单篇地学山水记、山水游记的流变中一直保持不变,有非常鲜明的文体区别意识。到了宋代地理学再次兴盛后,伴随各种认知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一些新的角度。
魏晋州郡地记的记述功能在于存录“物之本末”。州郡地记作为一种载录知识的文体,并没有叙述者的主观色彩和对事物局部特征的文学渲染。在这类作品中,作者并不是要展现自我独特的生命体验,而是对客观知识及共有文化进行描述。可以说,地记是时人知识传承体系中的一种文体形态。《广雅·释诂》:“记,识也。”[注][清]钱大昭撰,黄建中、李发舜点校:《广雅疏义·释诂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88页。识,志也。记最初的含义,在记载之外,有备而不忘的意思。用简单的线条作一个记号,是符号体系内的记,用语言文字保存一类知识或事件以备忘,是文献体系内的记。在后来的文体流变中,如山水记、山水游记文类的结尾还保留着“……记之”这样的语言痕迹。
二、独立的山川记到单篇山水记文类的生成与流变
魏晋时期,伴随由北而南的政治大迁移,中国的文化中心转移到了荆扬以南。全新的地域空间,独特的地形地貌,唤醒了文人的地理感知能力。在地记写作中,山水内容从州郡地记中脱离开来,形成了专题的山水记,主要有:张野、周景式、王彪之、惠远《庐山记》,袁宏《罗浮山记》,徐灵期《南岳记》,葛洪《幕阜山记》,王恂《虎丘记》,卢元期《嵩山记》,宗测《衡山记》,贺循《石箕山记》,卢元明《嵩高山记》,周景式《羊头山记》,殷武《名山记》,袁山松《宜都山川记》等等。我们将这些文献称为“记体”,在于它的功能主要是保存传承一山之知识总体,是舆地意义上的“山川记”。在文体特征上,此类山川记以条目为书写形式,并且都结集为著作。
与州郡地记中的“山水记述形态”相比,“山川记”主要有三个变革:第一,出现了主观的审美动机。同一山川,不同学者鉴赏眼光不同,其笔下山川描述各异,记开始具备主观性质;第二,在认知一山物象上,开始涉及峭岩、孤松等,更为具体细致;第三,最重要的也是学界长期忽略的一点,即“游观”视角的建立。这种游观的视角与由此而衍生的记述结构发展成为后来单篇地学山水记的文体特征。
“游观”是指“游目骋观”,而非“游踪”。“游观”是将全部景物融会胸中,然后分类写出。“观”这种行为在独立的山川记中已经成熟。如《宜都山川记》:“对西陵南岸有山,其峰孤秀。人自山南上至顶,俯临大江如萦带。视舟船如凫雁。”[注]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119页。《勾将山记》:“登勾将山,南望见宜都江陵,近在目前。沮潭沔汉诸山,嵎嵎时见。远眺云梦之泽,晶然与天际。四顾总视众山数千仞者,森然罗列于足下。千仞以还者,崔巍如丘浪势焉。今在上洛县西北。”[注][宋]李昉:《太平御览》卷49,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游观,是空间认知的一种方式和结果,“不是抬头望见一眼那种看,而是看得高、看得远、看得广的那种看。所以《释名》云:观,观也,于上观望也……《说文》说:台、观,四方而高者也……辄称高楼为观,正因为它便于远眺广览,所以才称之为观”[注]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4页。。观,首先就是要看一个大的空间,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注][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58页。。仰视俯察,合而为之便形成一个“游目骋观”的行动。地学山水记中这种“观”望视角的根本在于对地理空间分布的把握。它是一种全知视角,赋予空间一种审美意识与文化意识。
目前所见最早继承这种“游观”来记述山水的单篇记文是慧远的《庐山略记》。它的观照角度、记述方法一同于州郡地记与山水记体中的描述,是将六朝认知山川的诸多知识要素融为一体,从条录走向篇章,展示了时人对山川在认知话语上的文学实践。
《庐山略记》文本共四段。在《四库全书》中,文本保留最全[注]李勤合、滑红彬:《〈四库全书〉残本〈庐山记〉的文献价值》,《图书馆杂志》2014年第3期,第109页。下引《庐山略记》均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5册,不再出注。。第一段写山的地理位置、山之得名:“山在江州寻阳南,南滨宫亭,北对九江之南,江为小江,山去小山三十余里,左挟彭泽,右傍通川,引三江之流,西据其会。”这是认知一山的基本要素。之后,引《山海经》考证庐江,又引匡续 “神仙之庐”的故事,考证地名。此一段如单独成文,则无异于州郡地记与山川记体中的话语表达。第二段则在“游观”的视野下,写其山形、山势,其次言风、气、云、雨、声,在于自然之本身。它的观照角度亦同于地记的认知架构。“其山大岭,凡有七重,圆基周回,垂五百里,风云之所摅,江湖之所带,高崖仄宇峭壁万寻,幽岫穷岩,人兽两绝,天将雨则有白气先抟,而璎珞于山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大风振崖,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奇声骇人,此其变化不可测者矣。”第三段则讲述了庐山其地的历史和人文遗迹,采用的是汇集型认知记述。第四段虽讲述山中的佛教之事和佛教物象,却并不以佛意观山川,而是根据地记的自然物象,写一地之事、一地之物。如“上有奇木,独绝于岭表数十丈,其下似一层佛,浮图白鹤之所翔,玄云之所入也”。《庐山略记》综合之前的地学认识,以篇章的形式,对庐山进行客观描写,其文体功能在于存录物之本末。
除《庐山略记》外,《四库全书》还存录了《游庐山记并诗》,虽俱为慧远所作,文体区别意识已经比较明显。《游庐山记》文体价值在于,以游踪步数的变化来存录物象,不再只是骋目游观。出现了“践、登涉、出、过、力进”等词,这样,由全知视角存录物象,转变为个人行踪所能见闻到的物象记述。因此,它不同于州郡地记中以条目的形式保留一山的地学知识,而是主体意识下的山水游记。《游庐山记》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地学山水游记。唐时,柳宗元的《游黄溪记》就是这一文体的延续。另外,还有李逊的《游妙喜寺记》、达奚珣的《游济渎记》、窦群的《重游惠山寺记》等,均以游踪带起地学描述。
因为忽略了六朝山水记的存在,学界在“记”这一文体源流的追溯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如:“作记之法,《禹贡》是祖。而下《汉官仪》载马弟伯《封禅记仪》为第一,其体势雄浑庄雅,碎语如画,不可及也。其次柳子厚山水记,法度似出于《封禅仪》中,虽能曲折回旋作碎语,然文字止于清峻峭刻,其体便觉卑弱。”[注]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116、3665页。这一观点,视《禹贡》为祖,主要是追法它的“记述形态”,或者追《山海经》为祖,继承了早期对山水描述的认知架构。而马弟伯的《封禅仪记》曰:“仰视岩石松树,郁郁苍苍,若在云中。俛视溪谷,碌碌不可见丈尺。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窔辽如从穴中视天。直上七里,赖其羊肠逶迤,名曰环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挟,前人相牵。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重累人矣,所谓磨胸石,扪天之难也。”[注]孙星衍辑:《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76—177页。这段文字常被称赞刻画逼肖,而其中描写风景处,正是运用“游观”的视角。前人多重视这三种文献,却忽略了在魏晋六朝的山水记中已经成熟起来的认知架构、游观视角与记述形态。魏晋时期“记”作为知识保存的文体功能和形式,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六朝山水记的内容和文体表达皆源于山水认知体系的成熟。为山水作记,目的不在于游赏,而是广其阅历,对新世界进行探索,又借此博古、证闻。它并非考验作者的感受力,而是展现了作者的认知力。
综合考察魏晋时期已经成形的山水记文献,它的文体功能在于存录“物之本末”。这一功能先后经历了“记述形态”向记体、记文的转变。它的本质是山水认知在知识性著述中得以形成和确立之后,革新了当时文人的地学修养,形成了新的文体形态,以单篇记文的方式向文学领域发展。
三、唐代山水记文类的确立与文体特征
在唐代,除柳宗元的山水游记颇负盛名外,还存在大量其他文人创作的地学类山水记,如颜真卿、达奚珣、苏师道、元结、独孤及、窦公衡、于劭、陆羽、李勉、梁肃、李逊、柳宗元、欧阳詹、窦群、李季贞、陆庶、韦宗卿、李渤、吴武陵、元晦、穆员、孙樵、杜光庭、贾耽、康仲熊、张西岳、李讷、藏诸、王化清等,都撰有以“某山记”为题的山水记。可见,地理观察开始成为唐代文人的一种自觉行为。只有综合分析各家所创作山水记的整体状况,才能对记文类的特征有更明晰的认识。

表1 《全唐文》所载山水记
唐朝的山水记,大率作于地方官员之手。如李季贞:“余因守此藩,行县至……”[注][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241,3424,3768,7134,7387,3950页。而后有作《石门山记》。又如颜真卿于大历三年,作抚州刺史,“大历三年,真卿刺抚州,按《图经》,南城县有麻姑山”*[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241,3424,3768,7134,7387,3950页。,故刻碑《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谢灵运曾以条录方式作《游名山志》记浙江诸山,而唐元晦作《叠彩山记》《四望山记》,两山相连,也以游踪为转换。柳宗元先到石渠而后至石涧,作《石渠记》《石涧记》。由六朝山川记到唐代山水记文类的发展,“记”依然是身为地方官员的士人对所辖地区进行地理认知的一种文体。
依据《全唐文》中所存留的山水记作品,除青城山为道教名胜外,其他所记山川在唐前不曾有所描述。有些未曾载于图经、地志,有些虽有记载而语焉不详。有些实为偏僻之地,因文人撰写文章后,遂能以“记文”传之天下。苏师道《司空山记》称“湖南攸邑,为地最僻”,遂为之作记曰:“有司空山,去县四十五里。”*[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241,3424,3768,7134,7387,3950页。韦宗卿《隐山六峒记》:“石不能言,人未称焉……且谥为隐,若夫地因人传,山自人显。”*[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241,3424,3768,7134,7387,3950页。还有吴武陵《新开隐山记》:“夫兹山之始,与天地并,而无能知者”遂“伐棘导泉,目山曰‘隐山’,泉曰‘蒙泉’,溪曰‘蒙溪’,潭曰‘金龟’,洞曰‘北牖’、曰‘朝阳’……嘉莲生曰嘉莲,白雀来曰‘白雀’,石渠寒深,若蟠蛟蜃,特曰‘蛟渠’。或取其方,或因其端,几焯乎一图牒也。”*[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241,3424,3768,7134,7387,3950页。图经、图记之文体功能在于存一地之物象,而作者能为无名山之洞、泉、溪、潭命名而记之,此山之所有,则因记文而得以彰显。描写山洞、石室者,如李渤《南溪白龙洞》、韦宗卿《隐山六洞记》;描写新开石室者,如郑叔齐《独秀山新开石室记》、莫休符《栖霞洞》;描写石渠、石涧者,如柳宗元《石渠记》《石涧记》;描写仙坛者,如颜真卿《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描写山谷者,如穆员《新安谷记》等等。唐代山水记的创作,形成了对于一地之山水零星而广泛的认知。
在文人山水记文类繁盛的同时,国家层面记载山川内容的图经、方志亦存,但是对于一地之山川物象多仅存物名,记载过于简单,士人则常参看图、志而有进一步的记录。独孤及《慧山寺新泉记》:“山下灵池异花,载在方志。山上有真僧隐客遗事故迹,而披胜录异者,贱近不书。”*[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241,3424,3768,7134,7387,3950页。唐元晦《叠彩山记》:“按图经,山以石文横布,彩翠相间,若叠彩然,故以为名。东至二里许,枕压桂水……”[注][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第7423,3877,11227,3950,3950,6242,4182,6241,8329、8330,3876,5274,8431页。文人依志按图所创作的记,更在于山川之形态。这些记文虽以篇章形式存在,但记录简短,行文宗旨在于存录物象,很少蒙上作者的主观情感。
同时,唐代文人也图画山脉,为山川作图记。如元结《九疑山图记》:“图画九峰,略载山谷。传于好事,以旌异之。如山中之往迹,峰洞之名称,为人所传说者,并随方题记,庶几观者易知。”*[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第7423,3877,11227,3950,3950,6242,4182,6241,8329、8330,3876,5274,8431页。戴科《玲珑岩记》:“始兴令谢君成贤来款曲,居数日,遍搜岩之奇,复按邑志证之,盖有志,所未及载者,谢君属为记。”按照县志对验其地之景,大多都有记载,没有记载的,谢君嘱咐记下来。又言自己为此岩作记的原因:“科不敏,窃以张曲江公产此地,凿山通道,古今人颂之,而于此岩未尝为之表。”[注]屈毓秀等编:《中国游记散文大系》(广东卷,海南卷),山西:书海出版社,2002年,第203页。唐代士人在创作记体时,有非常清晰的补志之意。
唐人山水记一方面继承了六朝山川记中“某县有某山”的文体形式;另一方面以自我游览的方式,扩大地学知识见闻,发展地学游记这一文体。唐代王化清《游石室新记》:“高要郡北十五里,有石室。诡怪万状,崆峒其中。发挥灵踪,盘薄厚地。皆神仙之窟宅,为区奥之胜概……的皪琼脂,色如截肪矣,旁引危窍……西通于上武林,东抵于零羊峡。”最后交代此次之游,为“博陵崔公,领僚属及将吏,游于兹室,探讨奇迹……化清时官守司马,得倍盛游,辄叙鄙词,纪于前事”*[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第7423,3877,11227,3950,3950,6242,4182,6241,8329、8330,3876,5274,8431页。。虽有游,然并未有“游兴”和“情意”,而主要是对石室山做更为细致的描述。
唐人的山水记,虽为私人所作,其目的依然在于能补公共认知,遂将记文随物刻于碑石之上,或题诸岩侧,以使后之登览者,了解该山之状貌。如窦公衡令僮仆亲量瀑布之准度,作《石门山瀑布记》:“命僮携絙准度:自上潭直泻至天壁三百五十尺,自天壁飞洒至下潭四百五十尺,凡八百尺。庶登览者不昧于高深,迟想者每凭于文字,题诸岩侧,永寤区中云。”*[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第7423,3877,11227,3950,3950,6242,4182,6241,8329、8330,3876,5274,8431页。独孤及为慧山作志,谓“乃稽厥创始之所以而志之,谈者然后知此山之方广,胜掩他境”*[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第7423,3877,11227,3950,3950,6242,4182,6241,8329、8330,3876,5274,8431页。。李季贞《石门山记》:“聊勒石纪事,以贻诸来者。”*[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第7423,3877,11227,3950,3950,6242,4182,6241,8329、8330,3876,5274,8431页。在于借石以传文,保存关于该山之地学信息。
山水记在语言上多以骈文为主,骈散相间。如《石门山瀑布记》:“观其惊喷垂逶,淋漓,明灭芬敷,空濛霭昧。”*[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第7423,3877,11227,3950,3950,6242,4182,6241,8329、8330,3876,5274,8431页。《石门山记》:“观乎杰出氛霭,势凌霄汉,峭断穹壁,呀开石门……瀑布千尺,奔厓照日,望为晴虹。触石乘风,散为绝境……层峦蓄翠,风木含韵。”*[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第7423,3877,11227,3950,3950,6242,4182,6241,8329、8330,3876,5274,8431页。《龙多山记》:“因山带川,青萦碧联,莽苍际云,杳杳不分。月上于天,日薄于泉,魄朗轮昏……千状万态,倏然收霁。”*[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第7423,3877,11227,3950,3950,6242,4182,6241,8329、8330,3876,5274,8431页。其行文架构,仍是“山经地志”式描述山川所在、物产所有的知识体系的延展。在这些山水记文类中,于山水描写,刻肖其物,亦不减于柳氏。明清文论家常以柳宗元的游记为最高代表,并将记文的这种写实倾向推溯到早期经典文献如《禹贡》《考工记》中,而这种专题性摹物写实的描述,在当时的山水记体文中已是常见的笔法。当然也有些作品,在山水记载中,因其意、其形、其名而有情感的描写,除柳氏“永州八记”外,又如元结《右溪记》,在描写形胜中不乏情感抒发,但依然“刻铭石上,彰示来者”*[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第7423,3877,11227,3950,3950,6242,4182,6241,8329、8330,3876,5274,8431页。。
关于人工水利工程,唐人为记,往往征其始末以记之,文风简约,并多刻石依存于工程,如唐梁肃的《通爱敬陂水门记》,记载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杜公下令新建水西门,以沟通水渠:“岁在戊辰,扬州牧杜公命新作西门。所以通水庸,致人利也。冬十有二月,土木之工告毕。从事征其始,请刻石以为记云。”行文非为游赏,而在于彰显工程的千秋之利。“水门之作,将以重成功,示长利,非登临游宴之为。”*[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第7423,3877,11227,3950,3950,6242,4182,6241,8329、8330,3876,5274,8431页。《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不独贾客巨艘,居民业舟,往复无阻。自春徂秋,亦足以劝六乡之人业于茗者,专勤是谋,衣食之源,不虑不忧。”*[清]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第7423,3877,11227,3950,3950,6242,4182,6241,8329、8330,3876,5274,8431页。这样的作品,还有穆员《新修漕河石斗门记》、乔潭《中渭桥记》、陈鸿《华清汤池记》等。这类文章体现了记体文存录“事之始终”这一文体特征。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山水记文体变革的历史语境,可以对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记,在于存录“物之本末,事之始终”,有格物之美,对事物本身的秩序进行描述。在语言表达上,以记述为主,考证、辨析为辅。其文体功能在于保存、备忘,这决定了记体具有历经时间沧桑、超越个人的公共认知品格。如果有实体的物质存在,往往是铭刻在物上。后来的单篇记文,不一定刻成碑文,但每作记,而后常言“既归为记,以启后之好游者”等语。早期山水记体文均以条目的形式组合,可长可短,实际上是人类的感性认知积累的记录,在文献形式上表现为以著作形式呈现的州郡地记。唐代以降的山水记是士人地学知识修养提升后的一种文体进步,在文献形式上表现为单篇的地学山水记、地学山水游记和文学性山水游记。这是从地学到文学的演变过程。
唐代古文运动中记体的兴盛,实质即文以载道的实践。后人作记常宗法韩、柳,不知韩文多有经术,而柳之记体更得山水物理之实。记体的创作,不仅要以文章为法式,还要尊道为本原。唐前记体,实际上更多是以知识形态存在,即“物理之实”。山水记体文献从记录而至于撰文的演变,是地学知识普及的过程。这类文献最核心的要素,就是对于事物的认知,它体现着以记为名这一类文体的共通性。长期以来,我们过多重视柳氏“永州八记”的纯文学之美,而对柳宗元《游黄溪记》和八记之外的地学山水诸记关注太少。韩柳古文运动的实质,所提倡之道者,即为物理、事理。所谓物理、事理,即知识架构。在文体表征上,即为“笔”的复兴。清恽敬《与王广信书》言:“子厚八记,正而之变矣。其发也以兴,其行也以致,杂词赋家言,故其体卑。其余唐、宋、元、明诸名家,作记如作序,如作论,而开其始者,亦退之,《新修滕王阁记》是也。”[注][清]恽敬著,万陆、谢珊珊、林振岳标校,林振岳集评:《恽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60页。评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其体卑”,失之偏颇,但称为“正体之变”,是符合事实的。柳宗元的八篇山水游记文正是“认知性”记体文向“文学性”记体文的跃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