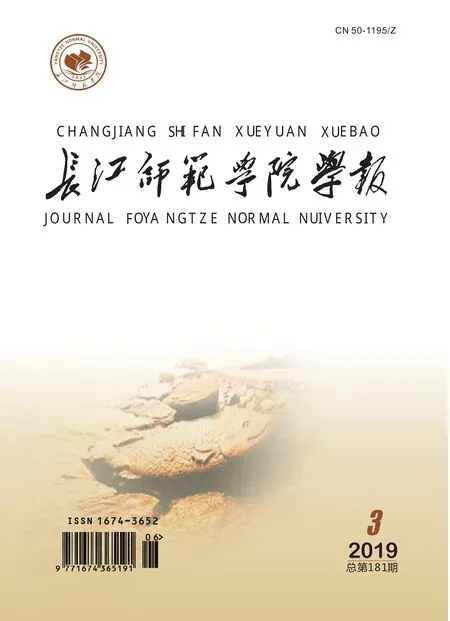试论刘永济词学观念的儒学印痕
——以刘永济与常州词派的渊源关系为重点
冯春祥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礼乐教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儒学观念,兼具道德指向和文学指向:既体现于道德修养层面,也在儒家的文学主张中占据关键一席。《礼记·经解》篇曾记录孔子之语:“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1]800就是说,经过涵泳《诗经》诸篇章,一个人可以得到教育,成为温文敦厚的谦谦君子。儒家这一著名的诗教原则,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清代中后期,张惠言等常州派词人为推尊词体,也将词同诗相比附,大谈词之意义与价值,极大地推动了此后文人填词与论词的大繁荣。刘永济是朋友口中耿介宽厚、性情诚厚的湖南才子,也是深受常州派词学观念影响的“清末四大家”中朱祖谋、况周颐的学生,其为人、填词、论词都呈现出礼乐教化的儒学印痕。
一、其人其词,君子敦厚
刘永济,字弘度,别号诵帚,湖南新宁人。他的祖父曾任清朝直隶、云贵总督,他的父亲先是在广东、云南等省做过几任知县,后弃官归隐,其家庭一直保持着读书人的家风。刘永济自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读书,接受儒学教育,并最终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儒雅君子。作为刘永济的“声应气求之友”,缪钺曾在《刘永济〈云巢诗存〉序》中评价他“为人耿介宽厚”[2];而吴芳吉《与吴雨僧》称许他“性情诚厚”,非“世上俗人”[3];程千帆《刘永济传略》也说他“非常谦虚谨慎而且平易近人”[4]。他的学生金绍先也曾在文章里回忆说,刘先生“态度始终亲切和蔼”,而且学生们都知道他“只对年轻人、学生、小人物客气,对大官、大人物就不客气”[5]。邓国栋在谈及其师刘永济《满江红·憔悴尘埃》一词时,也评论道:“先生则始终庄重儒雅。文如其人,词格即人格,即如此词,无轻薄之情,无绮媚之态,亲切、和雅、典重。”[6]
刘永济是现代词学研究的大家,有《词论》《宋词声律探源大纲》《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与《微睇室说词》等著作传世。即以《词论》而言,巩本栋评论说:“从总体上看,它实已建构起一个相当完整的词学理论体系。”[7]此外,刘永济论词又极具特色,由于他自己也从事词的创作,并卓然成家,所以他便格外关注词的创作与鉴赏。对于《词论》这一部“通论词学的著作”,程千帆曾回忆说:“先生曾经对我说:‘这事实上是一部词话选,前人的精论要语,都在其中。’”[4]巩本栋也认为,像《词论》这样的理论著作,其撰写的初衷,“主要是教人学词”,并评价道:“刘先生词学研究的特色,是以作品为中心,即通过创作、阅读、鉴赏、考证和批评等一系列方法来对作品进行探索的。他在词的创作上的造诣,使他对作品的阅读和鉴赏,往往能作出十分恰当的选择和深具会心的剖析。”[7]
刘永济出自书香门第,热爱读书,所以其填词、论词之时,都透出一种儒家气度。他曾在词集自序中谈到,词人贵在“其情果真且深,其词果出肺腑之奥,又果具有民胞物与之怀”[8]3,强调作品应写出真情,而且为人要有心系苍生之襟怀。我们可以从他的朋友和学生记录的几件事情,对他的君子品格有更为真切的体认。作为世交,程千帆对亦师亦友的刘永济非常熟悉和敬重,他曾撰文谈及刘永济在湖南中学任教时候的一件事:
一九一七年,先生应老师长沙明德中学校长胡元琰之约,回湘任教。次年,军阀张敬尧因胡校长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密谋逮捕,胡校长仓皇离开,学校濒于解散。先生就将多年积蓄起来预备出国留学的三千银元,全数取出,作为学校开支,而自己也仍然留在校中教授语文,和全体教职员一样,每月拿八元的生活费。后来,因为学校经费困难,胡校长始终没有将那三千元还给先生,先生也从未索取。[4]
金绍先则讲到其师《惜秋华·倦羽惊风》这一首词作的由来。刘永济早先在东北大学任教,后因东北沦陷,于是南迁并被聘为武汉大学教授。然而,他当时满怀对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哀痛之感,并未因个人的生活安定而有“任何欣慰之情”。在这首词里,刘永济从梦境写起,“倦羽惊风,渺天涯寄泊,沉哀何地?残夜梦回,还疑醉歌燕市。冰霜暗忆胡沙,怅一霎,红心都死”,深情倾述了对东北沧陷、心灵漂泊无依的哀叹之情,而下阕所写“须知玉树声妍,浑不解人间愁味”又以“玉树后庭花”之典,抒发他对当时执政当局无力救国安民的悲愤之情,令人读之动容[5]。
其实,刘永济此类忧国伤时的词作很多,东北沦陷前后,刘永济痛心国难,接连填下《满江红·禹域尧封》《满江红·憔悴尘埃》《水调歌头·银液泻溟澥》《解语花·烘莲旧节》等词,述说“金瓯破缺”“天柱倒,坤维折”之痛与“赁庑愁坐”“客枕无寐,竟夕忧危”之愁,而在忧闷之外,刘永济也在词中标举“敌忾之气”“沉雄之气”,抒发“填海志,终难灭”“把乾坤大事共担承”的救国壮志[8]2-4。“七七”事变以后,刘永济更是时时忧心家国百姓,1938年51岁时,他在居无定所的客行途中写下《庆春宫·寒野烟垂》,痛感“东南犹自鏖兵”,而不禁“骚兰新恨,歌黍前悲,无限牵萦”[8]10-11。1940年53岁时,他眼见国土狼烟四起,而“极目心伤”写下《水龙吟·客怀如梦如烟》。在词中,他痛心战事之惨烈,“汉上旌旗,湘中鼓角,岭南烽火。正忠肝义胆,争城陷垒,能余几,清平土”[8]17,为将士之英勇无畏而深情讴歌,为民族命运之多舛而忧心如焚。
事实上,刘永济现存词作,有一半以上都填于1937至1945年,其《惊燕集》120余首词作,屡屡倾述“野哭千家肠已断”[8]26(《临江仙·闻道锦江成渭水》)、“榆边旧恨换新悲”[8]26(《鹧鸪天·岁月匆匆去似飞》)、“残劫关河赚泪多”[8]54(《鹧鸪天·残劫关河赚泪多》)、“苌弘怨血晕秋花”[8]64(《浪淘沙·风雪卧天涯》)之痛;也每每为国民政府之无能而愤懑不已,“前事渚宫漫数,尽沉酣、琼筵歌舞”[8]17(《水龙吟·客怀如梦如烟》),“玉树歌中应有泪”[8]60(《浣溪沙·一自华胥好梦惊》),因而拒绝加入国民党,“眉样画难工,何关心不同”[8]56(《菩萨蛮·花边谁唤娉婷出》)。然而,痛心之外,他又全力投身于教育事业,不计辛劳,先后在浙江大学、湖南大学讲学,《点绛唇·惊燕天涯》《南柯子·晓驿收烟净》等即言其事;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以后,他又赶赴此地任教,《鹧鸪天·岁序潜移悄自惊》即彼时所作,后来又力劝陈寅恪“来乐山讲学”[8]51(《喜迁莺·鲛尘掀户》),以助力民族教育。
儒家鼓励人们“学为圣人”,而“学为圣人”的前提便是要有一颗温热的“圣人之心”,即仁心[9]。缪钺曾回忆说,好友刘永济在蜀地时,“外患日亟,中原沦陷,每相与论及国事,慷慨激昂,弘度谓吾中华民族有数千年刚健特立之操,终将有以自振”[2]。程千帆《刘永济传略》也写道:“他早年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尤其注重民族气节。”[4]苏轼曾评论其弟苏辙“其文如其为人”[10],刘永济也是如此,不仅其为人,即其填词、论词,都体现出典型的儒家君子品格。
二、儒家诗教:刘永济对张惠言、周济词学观之沿袭
相比前代,清代学术愈加重视考据之学,文人们探讨文学之时,很自然地将经史观念融入其中;特别是到了乾嘉时期,“文学与学术的合流”,已成为一种风潮[11]。作为常州词派的开山宗师,也是经学名家的张惠言,从诗歌借概念而嫁接入词,其词学理论颇有儒家诗教的意味。这可以由他的《词选序》中清晰感知:
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畅,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12]
而在《〈七十家赋钞目录〉序》中,张惠言也说:
赋乌乎统?曰:统乎志。志乌乎归?曰:归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概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有动于中,久而不去,然后形而为言。于是错综其词,回牾其理,铿锵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经则为《诗》。[13]
陈水云认为,张惠言所倡导的比兴寄托美学思想,源于“执着于言象”的汉代经学,因而在文学批评之时,会“与人事活动(主要指作者的美刺意图)联系起来”[14]。在另一篇文章里,陈水云也指出,在张惠言所处的年代,“词已完全成为一种‘句读不葺之诗’”,并分析说,张惠言“把作为经的《诗》之义引入词”,“要求人们将词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之,将向来被视为小道末技的‘词’,提升到与诗、赋平起平坐的地位,从而也让词肩负起厚人伦、美教化的社会责任”[15]。
张惠言之后,常州词派的另一位大家周济提出“词史”之说,进一步加深了词与儒家理念的密切联系。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周济提出:
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16]
对此,谢桃坊《中国词学史》指出,周济“要求词体把握现实历史内容,表现时代精神”[17]311,而这“与其经世致用观点是有联系的”[17]310。陈水云也认为:“周济不满于写作行为个人化的创作倾向,反对把词作为抒写个人‘离别怀思’或‘感士不遇’的手段,而主张作者‘感慨所寄’应该和时代盛衰相联系,把张惠言词学中‘志’的内涵由贤人君子的幽约怨悱提升到关系时代盛衰的高度。”[18]可知,周济的“词史”说,是紧承张惠言比兴寄托的词学观念而来,并对词的内容作了更细致的规定。
而考之刘永济的词学研究理路,实与张惠言、周济的词学观有着很深的承袭关系。在《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一书,陈水云剖析了刘永济与常州词派的密切学缘关系:常州词派“从毗陵二张开派,到周济、董士锡、宋翔凤弘扬其宗旨,而后从之者渐众,其影响亦从常州一隅走向全国。……在京师,有端木埰、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等人,结词社,校词籍,薇省唱和,影响至大”[19]273。而“刘永济曾师从朱祖谋、况周颐学词,……朱祖谋、况周颐都是在王鹏运提携下步入词坛的,词学观念亦深受王鹏运的影响,他们在体制上都主张严守词律,在词旨上则推崇常州派的‘比兴寄托’说。刘永济的师承关系决定着他不可避免地要受常州派词学的影响,对常州派开派领袖张惠言的‘意内言外’说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还沿着周济‘词史’说的思路,指出词和诗一样可以‘为后人论世之资’”[19]325。
正如陈水云所言,刘永济确实屡屡称引常州派词学观念。以《词论》一书为例,该书上卷《名谊第一》即引张惠言《词选序》与况周颐《蕙风词话》以证其“词者音内而言外”[20]5之观点;下卷《总术第一》也多次引用周济、况周颐等人词论,并高度评价张惠言之词学贡献:“自毗陵张皋文氏以意内言外释词,选词二卷,以指发古人言外之幽旨,学者宗之,知词亦与古诗同义,其功甚伟。”[20]60此外,刘永济也接受周济“词史”之说,他在《词论》下卷《赋情第三》即明言:“文艺与时会相关至切也。”[20]74同样,在《唐五代两宋词简析·总论》一篇,他也以史家视野细致分析了词在唐、五代以至北宋、南宋时期的发展变化,分析之时,很注重对时代盛衰与社会风气等因素的考量[21]。
当然,对词学观念的一些具体理解上,刘永济也并非对前辈亦步亦趋。即以“寄托”说而言,从张惠言到刘永济,对“寄托”的解释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刘永济曾在《词论》下卷《总术第一》指出,张惠言对于“寄托”的理解不见得很高明,因其“但知词以有所寄托为高,而未及无所寄托而自抒性灵者亦高”;尽管如此,刘永济却绝非否定词之“寄托”,他只是在内部作一纠偏,主张“无寄托而有寄托”,因而从根本上,他还是认可张惠言提出的“寄托”一说[20]60。曾大兴《20世纪词学名家研究》也认为,张惠言只是“在鉴赏实践上出了问题”,即过于重视阐发词的微言大义,而不免造成解词的牵强附会、胶柱鼓瑟,而在此之外,张惠言从儒家诗学的角度讲求词之“寄托”,其实“在理论上是有贡献的,在创作实践上也有可取之处”[22]331-334。可知,虽然刘永济可能在一些具体看法上与张惠言等人有所差异,然而他们本质上又是一致的,都服膺儒家思想。
三、温柔敦厚:刘永济与谭献、陈廷焯词学观之一致
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一脉,谭献、陈廷焯等人也对该派的词学发展有颇多贡献。常州词学能在浙西枝繁叶茂,当首推庄棫、谭献的引导与努力,陈水云认为:“常州词学扎根浙西是以谭献的出现为标志的”;此后,冯煦、陈廷焯、徐珂、陈栩等人又接连编撰词选、词话,“对常州词学均有推衍之功”[23]。此处分别以谭献、陈廷焯的词学理论为例,揭示出刘永济与他们词学观念的一致之处。
在词学方面,谭献提出“比兴柔厚”“折中柔厚”之说,其《箧中词》在评庄棫(字中白)《高阳台·飘拂微风》一词时,曾指出:“予录《箧中词》,终以中白,非徒齐名之标榜,同声之喁于,亦以比兴柔厚之旨,相赠处者二十年。”[24]在评周济《词辨》时,他也写道:“予固心知周氏之意,而持论小异。大抵周氏所谓变,亦予所谓正也,而折中柔厚则同。”[25]对此,在《中国词学批评史》一书,方智范高度肯定了谭献所主张的“比兴柔厚”“折中柔厚”审美原则,并分析说,“谭献认为词体最宜用比兴寄托,以达‘柔厚’之旨”,“‘折中柔厚’所体现的要求在总方向上与周济的‘寄托出入’一致。”[26]345-348
可知,谭献所提倡的“比兴柔厚”“折中柔厚”,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密切相关。方智范也认为,谭献深受儒学影响,其文学观可用“于忧生念乱之时,寓温厚和平之教”[27]一语概括之;又分析说,“‘温厚和平之教’,就是儒家的诗教。谭献推崇诗教大义,首先着眼于文学与政教相通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指出,“‘折中柔厚’,是谭献‘寓温厚和平之教’的文学观在词学批评方面的具体化。它既包涵着儒家诗教的第一义——确立了与政治教化相关的道德伦理规范;又蕴含着儒家诗教的派生意义,即揭橥了中国古代传统悠远的审美原则”[26]343-346。
谭献之后,陈廷焯再次强调词的温柔敦厚之旨。在《白雨斋词话·自序》,陈廷焯一开始便感叹真正能符合儒家诗教旨趣的词作太过稀少:“倚声之学,千有余年,作者代出。顾能上溯《风》《骚》,与为表里,自唐迄今,合者无几。……《大雅》日非,繁声竞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极。”接着,他分析说:“夫人心不能无感,有感不能无所寄。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郁,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在陈廷焯看来,那些能“为言也哀以思,感人也深以婉”的好词,比如温庭筠、韦庄、周邦彦、姜夔等人的词,“皆发源于《风》《雅》,推本于《骚》《辩》”。由此,他主张“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28]3-4。
除了自序,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正文屡屡言及温柔敦厚之于词的重要意义。以卷一为例:词话第五条即认为,“十三国变风、二十五篇《楚词》,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词之源也”;接着,又评冯延巳词“缠绵忠厚,与温、韦相伯仲也”;也评论秦观之词“最深厚,最沉著”;还称赞周邦彦之词“既有姿态,又极深厚,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28]6-7,16-18。不一而足。对陈廷焯而言,“温厚”是词之“体”,温厚与否直接关系到词品之高下。方智范也认为,陈廷焯所理解的《风》《骚》之性情,就是温厚和平,并分析说:“‘温厚和平’,是儒家诗教标榜的一种理想人格精神,也就是性情之正。词应以温厚和平为本,从词体的情感性特征来看,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词的情感内容及其品格的问题。”[26]358至于陈廷焯“温厚”之说的内涵,方智范认为,应是指“词应该表现具有深刻社会性的情感内容,而不应以啸傲风月、歌咏江山、规模物类为能事,或仅仅沉溺于身边琐事、个人哀怨之中。关心社会人生,将个人命运融入时代的洪流之中,这是儒家人格精神的重要特征”[26]358。
而考之刘永济的词作与学术论著,可知,其词学观实与谭献“比兴柔厚”之说、陈廷焯“温厚以为体”之说一脉相承。刘永济为人温柔敦厚,其词常具忧国伤时之情,前已有详论。此外,在学术论著中,他也明确强调过这一点。早年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时,刘永济曾作《文学论》一书,贯通中西,要言不烦。在这部著作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温柔敦厚风格的推崇:在该书第一章《何为文学》,刘永济指出:“文学以能了悟一切人情物态,而复具判断之力者,为最完满也;以能增高情感,纳于温柔敦厚之中者,为最优美也”;接着,他又写道,“文学家具敏锐之耳目,虚灵之心思,敦厚之性情,自能深入以得其精神,而熟悉其内容。……性情敦厚者,哀乐俱真。故凡可歌可泣可喜可愕之事,一入文学家之手,皆情景毕露。而人之读其文者,亦歌泣喜愕不能自已”;关于温柔敦厚之于文学乃至世道人心的重要意义,刘永济反复申辩:“文学家自身即性情敦厚者常以他人之喜怒哀乐为喜怒哀乐,见人之困苦如己之困苦。……如此,则人道纯粹无污,而世风可至醇厚。孔子删诗多取寓美刺、道疾苦之作,即此意也。”[29]这里虽是统论文学,其实也涵盖了他对词学的看法。就这一点来看,刘永济与谭献、陈廷焯在文学观念上是相当一致的,都体现了对儒家温柔敦厚诗教观念的由衷信服。
四、尊师重道:刘永济对况周颐词学观之推重
席鲁思曾为好友刘永济的词集作序,称其“少时受词法于朱、况两先生,由是以名其家,而涉词以教于上庠者垂三十年。论词则一主况先生”[8]1。席鲁思认为,经过“清末四大家”之中朱祖谋、况周颐两位先生的点拨,刘永济最终成为一代词人、词论家;而在词学研究方面,况周颐对其影响特别大。对这一说法,曾大兴一方面有不同意见,认为席鲁思所言刘永济“论词则一主况先生”,不免“有些简单化”[22]330,强调刘永济对前辈词学秉持兼收并蓄的理性态度,但也承认“他的词学主张,主要渊源于况周颐的《蕙风词话》”[22]328。刘永济对老师况周颐词学观的推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刘永济遵奉老师的词学观绝非门户之见,而是受儒家尊师重道观念影响的自然结果。《礼记·学记》有言:“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1]577《后汉书·孔僖传》也说:“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30]在《词论》这一“通论词学的著作”[4]中,刘永济屡屡称引常州一派词人观点,而尤多引用其师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其实,他的老师早已在这方面作了表率。在《蕙风词话》导读中,孙克强即指出,况周颐“常常引用王鹏运之语,可以说,王鹏运的词学思想已经融入了况氏的《蕙风词话》之中了”[31]8。而况周颐对其亦师亦友的王鹏运的推重,也许在无形中影响到了他的学生。
当然,作为词人兼词论家,刘永济确实如曾大兴所言,论词之时是持着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程千帆回忆说,刘永济告诉他,《词论》这部论著“事实上是一部词话选,前人的精论要语,都在其中”[4]。而刘永济之所以特别推重他老师的词学观,既是因为《蕙风词话》对前人词学理论的总结,也对前人的舛误观点作了纠偏,如同赵尊岳《〈蕙风词话〉跋》所言,书中实有着颇多的“至精之言、不刊之论”[32]937。朱祖谋亦曾对《蕙风词话》称誉有加,据唐圭璋、龙榆生记载,朱祖谋曾评价这部书是“八百年来无此作”[33],“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34]。在《清季四大词人》一文,龙榆生也赞叹道:“周颐实为近代词学一大批评家,发微阐幽,宣诸奥蕴。”[35]而这些评价,足以说明刘永济对《蕙风词话》的遵奉,绝非狭隘的门户之见。
有关况周颐《蕙风词话》的词学理论,学界已有详论。赵尊岳《〈蕙风词话〉跋》曾概括其有词格、词心、词径、词笔、词境五个方面的内容[32]936,近时学者也主要从这几个角度展开研究,而特别关注况周颐的“重拙大”理论、“寄托”说、“词心”说、“词境”说、“词外求词”说等。“重拙大”理论即赵尊岳所说的“词格”。况周颐承袭端木埰、王鹏运之说,其所著《蕙风词话》最早对“重拙大”之旨进行阐释:该书卷一即明言,“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接着,又解释为:“重者,沉著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填词先求凝重。凝重中有神韵,去成就不远矣”,“情真理足,笔力能包举之。纯任自然,不假锤炼,则‘沉著’二字之诠释也。”[31]3-8对此,曾大兴分析说,况周颐所说的“重”,就是“沉著”“凝重”之意,强调“词的感情的深沉与厚重”[22]209,而陈水云也将“重”的内涵概括为“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所体现出来的‘气格’”[19]290。相比对“重”的明确诠释,《蕙风词话》对“拙”与“大”的解释要模糊得多,或者直接援引王鹏运的说法,或者在评词之时略略点出[17]391-393。不过,况周颐在《词学讲义》里面倒是有过一些说明,他认为:“其大要,曰雅,曰厚,曰重、拙、大。厚与雅,相因而成者也,薄则俗矣。轻者重之反,巧者拙之反,纤者大之反,当知所戒矣。”[36]对此,陈水云分析说,况周颐之所以倡言“重拙大”,“意在戒轻、巧、纤之失”;并指出,“拙”包括内在之意与外在之笔两个方面,“讲的是词意的朴质与笔法的真率”,而况周颐所说的“大”也具有寄意和气概两层含义,“它们都一致地指向作者感情的真挚自然”;此外,陈水云也认可夏敬观之“(重拙大)实则一贯之道也”的说法,认为从整体的角度去把握“重拙大”的含义,是有可取之处的[19]290-293。
总体来看,况周颐所言“重拙大”,特别注重抒发情感的真挚、厚重与自然,也即他所说的“真字是词骨”,“填词先求凝重”,“填词之难,造句要自然”[31]6-8。对此,刘永济极为赞成,他在个人词集自序中即写道:“词人抒情,其为术至广,技亦至巧。……然而,苟其情果真且深,其词果出肺腑之奥,又果具有民胞物与之怀,而又若万不得已必吐而后快之势,则虽一己通塞之言,游目骋怀之作,未尝不可以窥见其世之隆污,是在读者之善逆其志而已。”[8]3可知,刘永济认为写作技巧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具有“果真且深”之情,以及“民胞物与之怀”,如此其情感才称得上真挚、厚重;而且还要“出肺腑之奥”,“若万不得已必吐而后快之势”,如此才称得上自然。
对于况周颐的“寄托”说,刘永济也深表认同。常州派谈词之“寄托”,始于张惠言,后来周济、谭献等人都有补充、修正,而况周颐也结合词之创作实际,进行了一番新颖的诠释。《蕙风词话》卷五写道:“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横亘一寄托于搦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则是门面语耳,略无变化之陈言耳。于无变化中求变化,而其所谓寄托,乃益非真。”[31]151在《词论》下卷《总术第一》,刘永济评论道,“介存所谓‘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况君所谓‘即性灵,即寄托’,语异旨同。填词必如此而后灵妙,是又无寄托而有寄托也”;接着,又解释说:“作者当性灵流露之时,初亦未暇措意其词果将寄托何事,特其身世之感,深入性灵,虽自写性灵,无所寄托,而平日身世之感即存于性灵之中,同时流露于不自觉,故曰‘即性灵,即寄托’也。……此所寄托,即其言外之幽旨也,特非发于有意耳。”[20]60
当然,对于其师的“寄托”说,刘永济传承之时,也有所发展。在《词论》下卷《总术第一》,他写道:“盖研诵文艺,其道有三:一曰,通其感情;二曰,会其理趣;三曰,证其本事。”并指出,要理解词的情感与理趣,较易,“可由其词会通”;而要“证其本事”,则既要努力“察其所处何世、所友何人、所读何书,所为何事”,又须“涵泳其言”,如此方能得其“言外之旨”[20]60。此论确是深得文学鉴赏之三昧。曾大兴即指出,对况周颐而言,“寄托”理论所指向的,仍“只是一个创作理论方面的问题”,而没有照顾到读者的鉴赏需求,而刘永济的贡献便是,他把“寄托”理论“由写作的层面引入鉴赏的层面,丰富了‘寄托’这一理论的内涵,并使之具备了实践的品格”[22]337。
其实,刘永济对其师之推重,不仅表现于某些具体的词学观点方面,还反映在一些更隐微也更深刻的层面。在《词论》卷下开篇,刘永济接连引用刘勰、黄庭坚以及其师况周颐之语,以作为填词之法门。他所引况周颐之语来自《蕙风词话》卷一:“词中求词,不如词外求词。词外求词之道,一曰多读书,二曰谨避俗。”[31]4刘永济将之视为填词必由之路径而终身遵奉,这已经不只是彼此词学观念相同这么简单了。
可知,刘永济是服膺儒学的,不仅其为人严守儒家规范,不愧为一个坦荡君子,即其填词、论词,也都可以看出他的儒者情怀。因师承关系,其词论观点与常州派有着深厚渊源,特别受到其师况周颐的影响。然而,不能因此断言他存有什么门户之见。刘永济之所以遵奉常州词派,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这一派的词学理论较之前人以及同时代人,更为系统、合理而深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