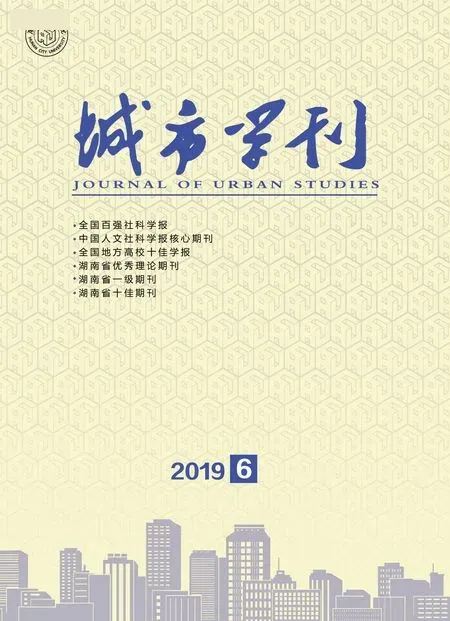周立波诗歌的家国情怀书写及其当代启示
王 泉,罗孝廉,孙 霞
(1.湖南城市学院 人文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2.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周立波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存在,在一生中创作和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撰写了不少文艺评论。迄今为止,学界较多关注其小说和报告文学,而对其诗歌的研究很少。其实,周立波的诗歌作品虽然不多,但立足于现实生活的沃土,记录了他的生活感受与真实情感,表现了社会进步的诉求,流露出浓郁的家国情怀,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
一、故乡:周立波创作的源泉
家国情怀是文学常写常新的话题,包含了作家对于故乡的记忆、现实生活与理想世界的审美把握与精神超越。周立波1908年出生于湖南益阳清溪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小领略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养成了朴实、坚强与乐观向上的品性,为他今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
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离不开大自然的滋润。作家与大自然共舞,在对大自然的感恩中产生了对于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之沉思。作家感受、表现自然的过程也是其心态释放的过程,他们的创作往往着眼于自然,指向的却是现实的生活与未来。因此,与大自然共舞往往成为作家的审美之维与自我人格的彰显方式。作家周立波自幼热爱自然,向往自由。周立波的童年是在清溪村度过的,他对自然的认识也从故乡开始,故乡的一草一木都化作了他以后创作的动力。
故乡既是人类童年的生活场所,又是其精神原乡。原乡包含了移居异乡的人记忆中的族群生活图景和精神世界,通过作家的想象,构建的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情感坐标。胡光凡认为:“周立波少年和学生时代对各种文化知识的渴求,不但使他从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吸取了充分的养料,而且培育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情愫。”[1]青年时期的周立波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并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到延安之后,他自觉地践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精神,通过大量的文学创作及对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翻译,成为一名真正的为工农兵及劳苦大众服务的文艺战士。可见,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与生活阅历的丰富,周立波以他对故乡的爱为起点,扩展到对于劳苦大众的关注和国家命运的关切,形成了他的家国情怀,为其创作打开了局面。
在周立波的眼中,对故乡的痴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深。1955年,他返回益阳,担任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为创作《山乡巨变》等积累了深厚的基础。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写他熟悉的故乡的风物与习俗,《山那面人家》《盖满爹》《伏生与谷生》《“割麦插禾”》等短篇小说也是如此。因此,从故乡出发,周立波深入到中国底层群众之中,深刻地反映了不同时期人民的精神风貌,实现了与时代的对接。由此周立波的家国情怀与其作品中的人民性紧密相关,成为中国红色文学中的亮丽风景,成为当今红色文化传承的经典。
二、独特的诗歌意象
诗人的情感经由想象凝聚而成意象,意象是诗歌的核心,是意境构成的重要元素。周立波在诗歌中喜欢描写家乡常见的山茶花,维系着他心系故土的情愫。山茶花是南方常见的一种花,因其叶子四季常青、花香清淡而备受文人的喜爱。陆游的《山茶》、范成大的《十一月十日海云赏山茶》及沈周的《白山茶》,都是歌咏山茶花的名诗,表明了诗人们对于山茶花的偏爱。周立波写山茶花,没有停留在山茶花的形态美上,而是把它同时代的氛围联系起来,把它同自我的感受紧密结合在一起,并由此及彼,引发出其他意象,形成了诗的境界。
周立波的《可是我们的中华》写在国统区经历的生活,表现了诗人的恐惧、希望与梦想。面对荒草遍野的大地,诗人似乎感到了绝望,但想到国家的命运与未来,他很快被激发出了旷世的热情。尤其是山茶花和故乡人民的深情引发了诗人的遐思:
我想起了
山茶花下的金色的年头,
那时候,人还在。
春花未尽。
秋叶走了。
那山茶花下的笑和情意呀,
于今是,梦一样的迢遥,可是我的中华,
我的慈爱的母亲大地,
你,还是一样,
不断地用春风,秋雨,
抚慰着你的儿子。[2]231-232
追忆往事,不免有些许的惆怅,但独处异乡的诗人从山茶花的勃勃生机和父老乡亲的笑容中获得了生活下去的勇气。诗人留恋这样的大地,感叹青春的易逝。东北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更令他牵肠挂肚,无法入眠。
我没有做声,
也从此想忘记个人幸福的梦和追忆,
我知道,
这是我还报母亲大地的爱的时候。
向苍天,
我默默地发誓了:
献给她,去医治她的伤体,
去消灭她的仇敌![2]234
沉默,不是懦弱的表现,而是情感的火山喷发前的力量蓄积。残酷的现实打破了诗人的幻梦,让他幡然醒悟,产生了报效祖国的强烈诉求。个人的幸福存在于国家的安稳,在祖国母亲遭受涂炭的危机时刻,有良知的中国诗人更应责无旁贷,把诗作为战斗的武器。田间的《给战者》和艾青的《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是这方面的佳作。同样,周立波没有陶醉在温柔多情的南方,也没有在怀旧中自我怜惜,而是借洁白的山茶花象征家园的美丽,道出了捍卫家园的急迫心情与神圣使命。
诗歌书写历史与记忆,不同于小说,它不靠故事的新奇取胜,而是取一点因由而言及其他,于细微处发现历史与记忆对于现实的启迪。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思古中抒发的是自己的远大抱负,余光中的《乡愁》则把离乡背井的个体命运与群体漂泊的感受融为一体,突出了家国情怀。据林蓝回忆,周立波在1935年至1937年间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翻译了大量外国进步作家的作品,并开始了诗歌创作。他的《牵引你的》写到山茶花,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表达了对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历史的追寻,呼唤新的征程。诗人以“十月的山茶花”“古史的神奇”“星的神秘”和“大海的滔滔”烘托出大革命振聋发聩式的呐喊,动静相宜,激活了历史。《“饮马长城窟”》从唐代王建的诗《饮马长城窟》中汲取灵感,借题发挥,反观爱国学生的义举,表达了收复河山的心声,从而推陈出新,演绎出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赋予古诗新的活力。这两首诗或追思历史,或以古韵反思现实,字里行间流露出周立波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切。
诗人对意象的选择离不开自然的景物,当自然的景物投射于诗人的心灵时,与之共振,便诞生了诗的想象世界。“诗的意境都是以时空的形式存在,而诗中的时空,又未必是自然客观的,甚至也非纯然心理的,而是现实时空、心理时空以意象化的方式绾合在一起的审美时空。”[3]周立波的《南方与北方》借时空的变幻表现心情的变化,显得自然而贴切。诗人先通过南北方不同的景色描绘出中华大地之美,梨花、山茶花、峨眉山之秀丽、三峡之神奇与洞庭湖之波涛交织成一幅壮丽的河山图。突然笔锋一转,写到了衰败的长城和荒废的秦淮河,巨大的反差让人不得不感叹岁月的沧桑巨变。而南北方春、秋季的变幻象征时局的变化与社会的动荡不安,更令人彷徨。诗人在跨越时空的意象中抒发着爱与乡愁,呼唤中华青春活力的复苏,表现出强烈的家园意识。与艾青的《北方》相比,这首诗没有直接描写生活的苦难及人民的顽强,而是借景抒情,借季节的转换隐喻了时代的症候,由个人的忧思引发出民族的忧患。这样的诗情景交融,以小见大,显得自然而委婉。
不难看出,周立波的这几首诗以“山茶花”为核心意象,表现了浓郁的故土情结。或追忆往事,或反思历史,或表现现实,将个人的忧郁与民族的苦难结合起来,呈现出忧郁之美。这样的忧郁一方面是由当时严酷的社会环境导致的,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统治造成了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局面;另一方面远离故乡的漂泊感加深了周立波的忧郁。同时,受到肖洛霍夫的影响,当他书写普通人的痛苦时,其忧郁色彩就显得格外突出。这使得周立波这一时期的诗歌祛除了许多左翼诗歌流于革命浪漫主义形式的弊端,显露出更多的生活底色。诗人内心的苦闷、民族的苦难与革命的激情交织在一起,还原了20世纪二三年代中国社会的镜像。
20世纪40年代,周立波由国统区来到延安,结束了以前游击式的生活状态。受到边区人民积极向上精神的感染,他不再一味地忧郁,而是把苦难转化为自我鞭策的话语,写下了《我们有一切》《我凝望着人生》《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等诗歌,张扬了不屈服于命运摆布的乐观主义精神。在《我们有一切》这首诗中,面对人生遭遇的种种不幸:忧愁、褴褛、饥饿和鞭子,诗人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试图去玩味这一切。苦中求乐,苦也是乐,这是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周立波敏感于边区人民的生活,从中汲取积极向上的力量,写下了《因为困难》一诗。
因为困难,我更要歌唱,
因为狭窄,我更爱广阔。
杜鹃不怕春夜的饥寒,
飞鹰最爱苍茫的天地。
高举呵长歌,
为了世间的更多的梦幻,更大的强壮,
更深的思想,更好的反叛。[2]247
杜鹃啼血,只为春光的明媚;鹰击长空,只因他喜欢独享自由。诗人借这两种鸟来象征自己对于光明和自由的渴望,准备迎接全新的生活。
人是情感的动物,也是理性的动物,从人之初的感性体验到后来的理性自觉,生命在演变中变得日益完美。作为一名追求进步与人性解放的知识分子,周立波对自己走过的道路有着清醒的认识。《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发表于1941年的《解放日报》,这时的周立波已经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一名教师,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该诗直接取材于边区人民的新生活,格调比较明快。诗的开头勾勒出延安的自然与人文风情:酸枣、青色的麦野、清亮的延河、矮小的泥屋,而领袖和人民的真诚则让诗人感激。他由陕北的风沙天想起了故乡的景物:樟树、竹鸡、春笋、阳雀子、独尾巴草,这些南方丘陵、山区常有的风物让他记忆犹新,而生病的母亲对儿子的思念更是铭刻在心里。但诗人没有沉溺其中,而是为被压榨、被欺侮的人们歌唱,并为自己拟好了墓志铭,自称是洞庭湖边的“乡野的居民”,“和人打过架”,喜欢歌唱“强悍和反抗”,[2]254凸显自我解剖的勇气和献身革命事业的气魄。同样,《我凝望着人生》也充满了自我解剖的色彩。诗人把自己比作“一只森林里的野兽”,[2]248书写了自我从无知、好奇到勇于探索的蜕变,凸显了人性的转变。从幻梦到现实的踏实生活,周立波渐渐悟到了人生的哲理。可见,这样的书写正是诗人坦然面对生活挑战的真实写照,表现了诗人内心激烈的冲突。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周立波在延安时期的诗歌格调要比他以前的作品显得更为明朗,视野也更为开阔。一方面,南北方气候的差异影响到诗人的心理,使他在慢慢的适应中寻找新的创作灵感;另一方面,延安的政治环境对诗人的成长有利,当他积极拥抱新生活时,喜悦之情不禁溢于言表。
解放后,周立波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的诗歌格调更为明朗,风格清新自然。《赠步涵》是他写给林蓝的诗,诗中借延安夏季如春的景象抒发了俩人深厚的革命友谊。这显然有别于一些爱情诗,没有粉饰的情感,只有朴实的回忆与真切的期盼。《清溪村》是他描写故乡变化的作品,写出了村里村外的不同景象。全诗只有四句,前三句勾勒村里荒草萋萋的面貌,最后一句“村外机车逐鸟鸣”,[2]255画龙点睛地道出了村外正在发生的变化,也隐喻了诗人迎接新生活的喜悦。
“一个艺术家反映时代,是一件曲折而且复杂的事情。他要躺在时代的胸怀,真实地、亲切地感着了它的脉搏,写出自己所感受的东西,就写出了他的时代。”[4]周立波作为一名左翼作家,深深领悟到时代对于作家创作的重要性,并自觉地融入时代,寻找灵感,表现了时代进程中个体的焦虑与抗争,并从中升华出民族的希望与生机。他的诗歌主要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也有少量的乡土诗,这些诗歌都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同时,以情见长,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想象,渗透了家国情怀。在他的眼里,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成为创作的灵感,化作情感的寄托。其诗歌中的“山茶花”是被高度理想化的意象,是明快与喜悦之象,是自由之花、生命之花和爱之花,这与艾青诗歌中的“土地”意象有异曲同工之妙。艾青诗歌中的“土地”意象是沉郁之象,连接的是劳苦大众的苦难,寄寓了诗人的悲悯情怀,周立波诗歌中的“山茶花”连接的是故土的温馨,二者都没有局限在故乡的风物和民俗上,而是放眼世界,表现了对于中华大地的深深依恋,突出了民族性的诉求。漂泊异地的不适与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没有让诗人放弃诗歌的创作,反而转化为诗人的审美冲动。回忆往事,抑或回到生活的现场,诗人都能自觉地将自我的情感体验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形成了诗的张力。因此,可以这样讲,故乡完成了周立波童年时期的最初启蒙,深沉的母爱与故土之恋赋予他想象的翅膀,他青年时期的革命活动则丰富了其诗的内涵,加深了其思想的改造,使他成为红色文学的代表作家。在远离故乡后,尤其是在延安时期,在研究鲁迅的小说《阿Q 正传》时,周立波受到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启发,自觉地解剖自我,思考“家”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心系国家的安危与前途,表现出一名先进知识分子勇于探索真理的可贵品质。后来,又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明确了自己的创作方向,成长为延安文学的新生力量。因此,周立波诗歌的家国情怀书写契合了家国同构的中华文化传统,直抵读者的心灵需求。
三、启示
真正优秀的诗歌不是诗人个人情感的简单宣泄,而是诗人对他所属的群体及其社会发出的宣言。周立波的诗歌呈现了特殊历史时期的个人情感与民族郁结的结合,实现了个人话语与民族话语的统一,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不无启迪。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要重拾中国诗歌的传统。诗是诗人情感的抒发,更是现实生活的呈现与表现。刘勰所谓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5]强调的正是诗人对于客观对象的情感投入的重要性。《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和《离骚》开创的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在中国具有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一代又一代诗人的创作。周立波认为:“在退步的浪漫主义中,幻想对于现实常常有一种‘病态的逃避’作用,它总是麻痹和腐败生活里的有毒的东西,但在进步的浪漫主义乃至现实主义当中,幻想始终保持着现实的基调,不但发挥着照耀现实、充实现实的作用,而且提供着灿烂的实践地理想。”[6]在他看来,进步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都离不开现实,现实为幻想之源,也是推动理想实现的根基。他将自己的这种主张付诸创作的实践,获得了成功。他的诗歌受到《诗经》和《离骚》的影响,继承了以屈原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一方面,直面当时的生活,再现了民间的疾苦,记录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创伤与个人的情感,凸显生活之真与艺术之真的统一;另一方面,他以发自内心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表现了自己的理想与人生追求,使得个人的心史与民族历史的风云相交融,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
中国传统诗歌强调意境之美,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7]表明了诗对于现实环境的超越之重要性。“诗情、诗意、诗境的美自然源于现实生活,却又异于现实生活,它是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创造性再现或重构,其中融入了诗人对美的独特理解和把握,也融入了诗人对现实生活美的独特感受。这样才能言人所未言之情境,而使读者感到新奇振奋的愉悦,并使读者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8]在中国文学迈入21世纪之时,在大众传媒的推动下,一些新生代作家的快餐式写作几乎引领了文学的风潮。例如,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杂志在青少年群体中拥有广泛的读者。新诗的创作也呈现多姿多彩的态势,一些民间诗刊在开放的环境中得以壮大。然而,在越来越多的作品中,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把握显得力不从心,少有沉稳的大气之作。而各种不痛不痒的作品研讨会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界的浮躁之气,文学生态亟需调整,以恢复到原本平静而深沉的状态。周立波诗歌立足生活,把生活本身当作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审美情感的升华,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轨迹之象征。其诗歌中的“山茶花”意象,既是诗人故乡的象征,又是诗人理想的乐土,表现了一种朴实而持久的情感——对于故乡和劳苦大众的爱,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可见,现实与理性的糅合构成了“山茶花”意象的独特性。现实的生活具有多面性,诗人的审美态度决定了其诗歌的品质,周立波的忧郁气质加深了他对于生活的理解,也提升了其诗歌的境界。
中国传统诗歌强调“言志”,关键是言说什么样的“志”。诗歌需要进入读者的视野,实现与读者的“对话”,激活作品的意义,这是诗歌经典化的路径。如果创作的诗歌仅仅是个人渺小愿望的载体,也许也能打动部分读者,却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获得大家的认同。但如果表现的是人民之“志”、人类之“志”,则能引起广泛的共鸣,跨越国界,成为世界的经典。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几个高峰,已经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成为海外汉学必研的内容。中国现当代诗人艾青、北岛、舒婷和海子的诗歌也走向了世界,说明了中国诗歌“言志”传统的魅力。周立波的诗歌所言之志,既是个人之志,又反映了时代进步的需求,凸显了感召力,成为中国现当代诗歌中不可或缺的风景。
其次,弘扬红色文化精神,离不开红色经典文学。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是民族性、人民性和时代性的结合。红色经典文学通过塑造崇高的精神世界表现民族的性格,注重以美的形象感染读者,是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周立波文学创作的动力来自于他对故乡的深情,来源于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其诗歌中的家国情怀构成了红色文化的本色。
家国情怀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是文学常写常新的母题。从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到闻一多、艾青、李瑛,中国诗人的家国情怀可谓源远流长,成为贯穿中国文学的一根红线。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倾斜,自私自利的行为严重阻扰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也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导致了一些作品格调的低下,给大众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些作品的文风浮躁,缺少对于现实问题的关切,缺少对于国人精神流变的深入把握。有的作家甚至陶醉在个人化的叙事中,显示出对于国家、民族历史的遮蔽态度。
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文学界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乱象,网络的恶搞,消解了文学经典的崇高与神圣,背离了创新的本质,甚至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因此,文学需要正本清源,把握好发展方向,以便在书写中国故事中有所作为。周立波的诗歌没有陶醉在个人情感的迷宫里,而是把自我的命运融入到革命的熔炉中进行煅造,获得了新生。其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渐渐觉悟的革命者形象,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成长的缩影。
中国当代诗歌经过70年的发展,经过几代诗人的共同努力,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的发展一方面使诗歌的创作与传播变得快捷、多样化,互联网的普及,加速了读图时代的到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呈现勃发之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大众的欣赏习惯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在碎片化的阅读中忘记了必要的思考,使得他们对于传统的诗歌作品的理解肤浅化,不尽如人意。诗歌是抒情的艺术,读者的内心情感只有与诗歌作品的审美风格相契合,才能真正读懂,诗歌的意境之美才能呈现出来。微信等新媒体传播文学的过程是文学被消费的过程,作品自身的审美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重温红色经典,弘扬家国情怀,需要在传统的阅读中感悟与体验,需要在沉潜的姿态中保持对于经典的敬畏之情。
“民族文化是长期以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是一个民族的根脉。由于人口、种族、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等存在差异,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风俗习惯,造就了多元文化,而且每一种文化都有无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9]实践证明,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可能主宰其他民族的文化,我们只有坚守中华文化的民族性,才能在多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的灵魂,也是得以存在于世的根基。无论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如何,无论世界文学的格局如何变化,民族性都始终是文学书写的核心。诗歌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诗人对于民族情感的审美把握与表现上,语言的运用、意象的选择、意境的建构等方面,都要体现民族的风格与欣赏习惯,以利于塑造民族形象。这就要求诗人处理好小我与大我的关系,让个性风格在时代的浪潮中得到充分体现。经过茅盾、丁玲、周立波、艾青、贺敬之、王树增、石钟山、徐贵祥、柳建伟等几代作家的创作,中国的红色文学已经蔚成风气,滋养了广大读者的心灵。
语言是诗歌的外衣,情感和思想是诗歌的内核。周立波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凸显了情感的真实与思想的火花,其自我解剖精神将个体的焦虑转化为心系民族解放的忧患意识,突出了人生的真谛。在21世纪的今天,重读周立波的诗歌,发掘其艺术个性与思想资源,重温其家国情怀,一定会收获更多的良知,对于重整诗歌精神,促进诗歌的经典化,都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