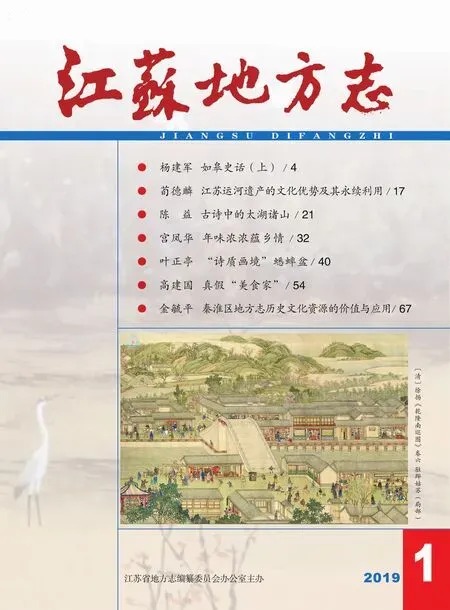年味浓浓蕴乡情
◎ 宫凤华
柴火旺旺熬年糖
“年,像淡烟,又像远山的晴岚,我们握不着,也看不到,但它走来的时候,只在我们的心头轻轻地一拂,我们就知道,年来了。”读到季羡林先生这句雅致的句子,扑面而来的浓浓年味如缕缕春风轻轻地温暖我的心田。
汪曾祺在《炒米和焦屑》一文中写道:“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这是很便宜的食品。孩子买了,咯咯地嚼着。”多暖心的文字。
小时候,到了腊月,母亲就会把碾米筛下的碎米攒起来,装进罐子里,用来兑糖丝。冬阳惨淡,我们背着米袋子,跑几里路,到镇上粮管所兑糖丝。一路上总是累得人仰马翻。但一想起喷香的炒米糖,脚下不知哪儿又冒出劲儿。
清寒薄暮,乡下炸炒米的老汉忙活开来。常见他们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风箱炉灶,另一头是黑黢黢的炒米机和长袋子,晃悠悠地来到村子的空场上。“炸炒米喽——炸炒米喽——”搁下担子,支好炭炉,便亮开大嗓门来回叫喊。
炸炒米的老汉多为六十开外的老人,满脸的沧桑。他面前摆着一个黝黑的煤炉,炉上有一个头小肚大、尾巴上还有个气压表的葫芦状铁罐子——炸炒米的高压铁锅。地上有一条很长的口袋。炉火熊熊,映着老人皱纹纵横的脸庞。他神情专注,盯着铁炉把手处的气压计。他很少说话,别人在一旁说笑,他也不答腔,一脸的严肃。几个顽皮的孩子,有时趁老人起身给炉子添煤时,冷不丁地猛拉几下他的风箱,炉子里的火便一下子蹿了起来,他不愠不恼,只用眼睛斜睨一下他们,以示训斥。
他左手不断地按顺时针方向摇动炒米机,右手有节奏地拉着风箱,动作配合十分协调。随着风箱吧嗒吧嗒地响,炉火也闪烁跳跃。不大会儿,看一看表,立起,将葫芦状的炒米锅扳起来,把顶端套进一圆锥形的网袋中。然后左脚踩到上面,左手拿着扳手套到容器的“耳朵”上,右手抓住摇柄,高喝一声“响呶——”,左手用力一扳,“嘭——”一声巨响,容器盖便被冲开了,一股浓烟腾空而起,瞬间把我们淹没。
我们松开紧捂耳朵的小手,蹦跳着,一头扎进白雾里,拼命地吸着热乎乎、香喷喷的炒米香,一种说不出的舒坦和惬意流遍全身。空气中的香甜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呼声,捧把炒米塞进嘴里,那满嘴的香、甜、酥、脆,总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在心底荡漾。
寻常日子,泡一碗炒米可代早晚茶,待客可作点心,正如郑板桥所说“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比下一碗面条简单。汪曾祺念念不忘的一种吃法是“用猪油煎两个嫩荷包蛋——我们那里叫做‘蛋瘪子’,抓一把炒米和在一起吃。这种食品只有‘惯宝宝’才能吃得到的”。而我们在腊月里常常吃到母亲下的粉丝炒米蛋茶,谁说我们不是“惯宝宝”呢?
熬糖多在清寒冬夜,小院里月光清如溪水,静似画布,草屋和枯树闲适安逸地嵌在画布上。青霜平添一份柔和,显得寂寥而悱恻。院角苦楝似宋词中的女子,清瘦婉约带有几许凄凉。黑黝黝的土灶上置一口大铁锅,倒些冷水,再倒进糖丝,搅匀。旺火烧煮,棉花秆燃烧时哔哔剥剥作响,屋里弥漫着甜味和烟味。祖父用铜铲子不断地在锅里搅拌,里面掺些姜末、橘子皮、红枣,适时添进半铲猪油。最后把炒米倒入锅内搅匀,此时,炒米显得格外晶莹剔透,闪烁着珠玉的莹润光彩。
桑木桌上放一块案板,抹上菜油,四周用木框固定好,盛入滚热的炒米糖,用木板使劲来回滚平。磨得锋利的菜刀也抹上菜油,等到糖半冷不热的时候,祖父拿出模子,用刀切成小块的长方形或正方形,手起刀落,动作迅疾。
熬切好的炒米糖,吃起来,脆香爽口,咬得“咯嘣咯嘣”的。花生裹上糖浆,切成小片,就是花生糖,入口脆甜。黑色的芝麻浇上糖浆,切成小片,就是芝麻糖,咬一口,香甜酥脆,像一场舒缓的芭蕾,在味蕾间跳跃旋转,荡出鲜艳的滋味。
熬糖时,铁铲在锅里“呼啦呼啦”翻动着,“咔嚓咔嚓”的刀切声,风箱的“吧嗒吧嗒”声,柴火的“哔哔剥剥”声,我们的笑语声,组成了一首暖心的交响曲。熬糖是一个恬静、幸福的细节,里面蕴藏着温暖的亲情,是舌尖上梦魂牵绕的故乡。
那样的夜晚,我们不停地吸溜着鼻子,饱吸着那浓郁的甜香,烦恼和贫困都在温暖的润泽中变成天边的一片云。冬日的寒冷化作灶膛里旺旺的火苗,化作祖父面颊上忙碌滚动的汗水,化作我们嚼糖时脸上绽放的朵朵红晕。清夜无尘,月色无垠,星光迷离,天空邈远而空阔。坐在院里木桩上,我们柔软得像一根青藤。
那种阳光般简单明快的幸福感和快乐感,日渐湮灭于浮躁而喧嚣的尘世。陪朋友逛超市,漫步于琳琅满目的商品间,偶有包装精美的炒米糖赫然入目,心中便涌起感念的潮水,一股柔软的乡愁倏忽从心底传遍全身。
有时徜徉在城市清冷的街头。天色向晚,偶尔瞥见街巷一隅,一位头发苍白、沧桑满面的老人在吆喝着卖爆米花。老人生意惨淡,神情淡定,如一幅古画。一缕残阳披在他单薄的身上,我不禁心生戚戚,一种苍凉袭遍全身,一缕乡愁溢满心胸。
正如汪曾祺感叹:“炒炒米都是把一年所需一次炒齐,没有零零碎碎炒的。过了这个季节,再找炒炒米的也找不着。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
梁实秋说,味至浓时即家乡。品尝着喷香的炒米糖,我一下子回到纯净古意的乡村月夜,想起亲人们熬糖时那种忙碌而欢快的场景。那浓郁的熬糖香芬芳着陈年的梦,成了一种留在心底最温馨的回忆。
热气腾腾蒸年包
江南农村,每进腊月门,家家都忙着蒸萝卜包子、咸菜包子,一直吃到过大年。
萝卜水灵瓷实,吸足了秋天的衰脆和萧寒,莹润光洁如同贵妃出浴。咬一口,嘎嘣脆,声响犹如春冰开裂、积雪断竹,正如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冬月吃萝卜的感受:“琼瑶一片,嚼如冰雪,齿鸣未已,众热俱平,当此时何异醍醐灌顶?”
萝卜熟吃,花样繁多,诸如萝卜烧五花肉、萝卜丝包子、萝卜丝拌海蜇、萝卜丝饼、素炒萝卜丝、酸辣萝卜丁、萝卜鲫鱼汤、羊肉炖萝卜等。萝卜不偏不倚的中庸之性,配什么都可以。无论怎样烧、炖、炝、拌,味道温和醇厚又不张扬,仁厚平易,颇有君子之风。
萝卜烧豆腐是地道的家常菜,是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执拗,是安贫乐道、宁静致远的境界。蓝花汤碗盛出来,撒一把翠绿的蒜花,色彩明丽。吃在嘴里,萝卜鲜甜,豆腐糯软,清新爽口。
萝卜切丝,浇上生抽陈醋,淋点麻油凉拌吃,简单方便。难怪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生萝卜切丝做小菜,伴以醋及他物,用之下粥最宜。”糖醋炝萝卜味道不凡。把萝卜切块拍碎,放到大瓷碗里,盐渍糖腌,掺入陈醋,淋上麻油,佐粥下酒,脆生生、麻辣辣、酸溜溜,清凉润肺,是家常菜肴中的佳品。
萝卜丝饼也叫油端子,极其爽口。把红萝卜去皮刨成丝,撒进葱花、细盐,拌匀,面粉加清水调成糊状。平底锅放油烧热,模具“鏊”放入,兜一勺面糊倒入模具中,用勺子摊匀,在面糊上放萝卜丝葱花馅,再兜一勺面糊浇在馅上。等萝卜丝饼底部凝固后,抽出鏊,翻面煎至两面金黄即可。经过了热油高温煎烤,萝卜的清香渗入面皮,吹一吹,外脆里糯,咬一口,萝卜丝的清香蔓延开来,直透肺腑。
萝卜羊肉汤是年关岁末的一道美味。萝卜汤有补胃益气、散寒壮阳的功效。萝卜羊肉用文火煮烂后,加陈皮、生姜、胡椒、葱花,温火炖熟。冬天里,一家人围桌舀喝鲜美爽口的羊肉汤,顿觉一股热气周身窜腾,是一屋子的亲情和温暖。羊肉肥润,萝卜绵甜,汤汁浓稠,寻常幸福,就在这氤氲炊香里深藏不露。
萝卜炖排骨味道鲜美。梁实秋曾啧啧称赏:“揭开瓦钵盖,每人舀了一小碗。喔!真好吃。排骨酥烂而未成渣,萝卜煮透而未成泥,汤呢,热、浓、香、稠,大家都吃得直吧嗒嘴。”大师们在饕餮中自塑一份风雅。冬天蔬菜稀缺,从地窖里扒几个萝卜,煨蹄髈,炖排骨,香气四溢。客人来了,披一身雪花进屋,先盛一碗汤喝入,暖身又暖心。
过年前几天,蒸萝卜包子和水咸菜包子可是母亲的拿手好戏哩。母亲将猪肉斩碎煸熟,倒入剁碎的萝卜或咸菜和切成末儿的香干,上下翻炒。再加入姜末、蒜叶、米虾、蛋皮炒熟。馅儿做好了,就包馒头了。最后还要用蒸笼蒸。火要烧得旺。厨房里热气弥漫、香气缭绕、笑语盈盈。
清寒冬夜里,逼仄的土灶间洋溢着浓浓的亲情。大火旺烧片刻,萝卜包子就会出锅了,掀开锅盖的瞬间,氤氲的热气漾着萝卜的香味,立时将我们淹没。刚出笼的包子腆着雪白的大肚子,惬意地躺在蒸笼当中,十来只环绕排开,隔开朦胧的热气,能看到包子顶部褶子组成的花蕾中一星点泄露出来的红萝卜丝,像熟透了的石榴咧开嘴在开怀大笑。
母亲蒸的萝卜包子咸香入口、经久耐贮,来串门的亲戚,吃了母亲包的萝卜包子,都赞不绝口。
萝卜又名莱菔、萝菔,像从《诗经》或《汉乐府》里走出来的,让人想到心思纯净、秀美轻灵的美女罗敷。萝卜缨的嫩苗,或凉拌或腌制成炒食,虽不如范仲淹所说的“腌成碧、绿、青、黄,嚼出宫、商、角、徵”,但在尽享荤腥之余,偶尔夹青嫩着眼、清口辛香的萝卜缨小菜,倒也胃口大开。
每到小寒时节,巧妇们总要腌萝卜干。将红萝卜或白萝卜削去头尾,洗净略晒,在长桶里滚刀切块,拌上细盐铺入缸中。当缸中渗出卤汁时,把萝卜捞出放到阳光下晾晒数日,把盐卤煮沸,萝卜入热卤中烫一下。用棉线把萝卜干串起来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晾晒,或平摊在匾子里和席子上,待萝卜干晒成表面干燥略带湿润后,就可以入缸了。装缸时还要把萝卜分层压实,最后将口密封。
萝卜干是家乡最平民化的咸小菜。大家粥碗一捧,咯吱咯吱地咬嚼着爽脆的萝卜干,咕噜吐噜地喝着滚烫的粳米粥,生活的恬淡和温馨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清雅萝卜深受文人雅士的青睐。宋人陈著诗曰:“晓对山翁坐破窗,地炉拨火两相忘。茅柴酒与人情好,萝卜羹和野味长。”柴扉破窗,地炉粗酒,啜吮萝卜羹,洋溢着一种襟怀旷达的山野情趣。“东坡羹”其实就是将萝卜、蔓菁等茎块捣碎,加上研碎的白米,烹煮而成。台湾女作家到汪曾祺家做客,汪老特地做了“杨花萝卜炖干贝”飨客,浓香扑鼻,女作家赞不绝口,回到台湾后,大肆吹捧,弄得汪老一不小心就扬名港台文坛。
萝卜以鲜艳的色泽、温润细密的质感,为人们的餐桌提供了一份红偎翠倚的色彩言说,张扬出活泼的生气,演绎浪漫的小资情调。萝卜,从农耕时代走来,有着诗经的古雅,渗透着乡村的精神,在我们的心中氤氲出一片温润的绿意。让我们深情地凝望萝卜,静静地缅怀那些远去的恬淡岁月和田园诗情。
苏轼有词:“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在苏轼眼里,雪沫乳花,蓼茸蒿笋,都是清欢,一如萝卜清汤,一如萝卜包子。冷凝冬日,年味袅袅,浮世纷扰,一碗滚烫的萝卜汤、一只喷香的萝卜包子,足以祛除沁骨的寒冷。一家人在热气氤氲中举杯畅饮,亲情弥漫,这何尝不是寻常生活中的“小确幸”呢?
腊味飘飘唱年戏
一进腊月门,苏中乡村便有一种“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的氛围。青霜覆瓦,冬阳惨淡,家庭主妇们清脆的吆喝声,催醒了慵懒的小村。她们忙着腌腊网、腌腊肠、腌猪头、腌咸鱼。屋檐下、南墙头、房梁上都挂着腊肉。一股浓浓的腊香在小村的深巷里飘荡。
伴随着浓郁的腊香,故乡的年戏便粉墨登场了。故乡的年戏如同栀子花、老水车、古窑洞、小木桥一样,装点着乡村清贫恬淡的日子,弥漫着幽幽的香气,醉了四处散落的小村子,醉了四邻八舍的乡亲们。
约戏班子、筹戏款子,是村中唱年戏的前奏。一般是村中能说会道的德胜嫂呀、张大伯呀,他们平时热衷于看戏,又有闲空儿,这些事自然便落到他们身上了。
一大清早,北风呼呼的,白霜浓浓的,他们就挨门逐户地敲门,说又来烦了,不好意思啊,又要唱戏了,热热闹闹哟,想问你家筹点钱,你看行不?话说到这个份上,哪有不捐上一点的呢?谁不怕人家嚼啐舌头、指戳后背呢?
小村唱年戏,搭戏台子不算讲究,一般选在学校的操场上,或者村南头玻璃厂的空场上。场子上砌了一座大方台子。有的戏班子自备木板、铁管,几个壮汉两三个钟头就可搭成;有的戏班子叫村民搬桌子平放着铺成戏台,再扯上篷布便成。戏班人手紧,但生旦净丑、唱做念打倒也有板有眼、颇具韵味。
唱年戏前几天,人们竞相传告,家家邀亲约客,人人笑语盈盈。孩子们个个喜笑颜开,浑身有使不完的兴奋劲儿。小村里,亲朋欢聚,杀鸡宰鹅,其乐融融。
唱年戏前最热闹最隆重的仪式是杀年猪。那火爆的情形令人想起作家阿城《会餐》小说中杀猪场景的描写:“杀猪师傅用膝骨压在猪身上,猪就乱蹬,用一辈子的力气叫着。师傅上火了,左手一拧猪耳朵,猪叫就又高上一个八度,右手执刀从项下往胸腔斜里一攮,伤口抖着,血连着沫出来,并不接,只让它流在地上……杀猪师傅就在猪脚处割开口,用铁条通上去,再吹进气,用线缚了,使棒把气周身打匀,鼓鼓的在热水里刮毛,又把肉卸开,肠头,肚头弄干净,分盆装了。肉拿进灶间,放在西灶上煮。”猪肉拿回家,便开始腌制,挂在南墙头,渲染着一种喜庆、吉祥的氛围。
开戏当日,夕阳西沉,缕缕炊烟水袖般款款飘过清清爽爽的天空,飘过寂寂静静的原野。而戏场上早已摆满了小杌子、柳条板凳。早有村民在观望、唠嗑,所谈论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家常事。
孩子们则台上台下猴子一样又蹿又跳,不住地扮着鬼脸。大姑娘小媳妇细心梳洗打扮,刘海儿有的自然飘逸,有的用剪刀瞄过一刀,头发上搽了梳头油,滑滴滴的,亮灼灼的。发髻形状又圆又扁,有的罩上黑线网子,穿一根银簪子,有的插一根发夹,戴一支绒花儿。穿了平时舍不得穿的花衣裳,拿了自己一年来积攒的零花钱,结了伴儿、拣了近路往戏场赶。
暮霭沉沉,戏场上响起密切的锣鼓声,把人们的心撩拨得急慌慌的,年味儿也更浓了。锣鼓咚咚锵锵过后,大家开始放鞭炮、点斗香,祁祷吉祥平安。放鞭炮时,个个群情激奋。先是“破台”,扮演赐福的天官,上蹿下跳,随手抖下“恭喜发财”“财源茂盛”的条幅。走在最前面的花旦双眸含情,轻抖水袖,樱桃小嘴一张,那清脆的嗓音立即招来人们的阵阵喝彩。领班的郑重说明本场的包主是村中鱼老板,下一场是跑运输的王大和王二。戏场上人头攒动、烟气缭绕。卖糖球的、炕山芋的、炸肉串的、蒸鲜藕的,生意一片红火。大人们很慷慨,将吃的玩的塞满了我们的口袋。
婆婆媳妇们看到动情处潸然泪下,抽噎声此起彼伏;汉子们站在后面,有时也跟着喝彩几声;年轻男女则在外围相互调情逗笑,借以散释青春时代过剩的精力和激情!
戏班大戏照唱,什么《玉堂春》《赵五娘》《秦香莲》《莲花庵》《刘贵成私访》《钦差行》《碧玉簪》《打碗记》《哑女告状》《白虎堂》《十把穿金扇》《秦雪梅吊孝》等,十来天唱下来绝不重复。街头巷尾,田塍陌头,大家聚在一起就谈戏。村民们喜听淮剧,也许是淮调的苍凉悲切正契合他们充满沧桑和苦难的内心吧!
正月里,北边桑湾村有时能请到泰州陈德林的淮剧班子。那可就调足了村民们的胃口了。你瞧,花旦在戏台上轻歌曼舞,兰花指纤细修长,嫩嗓子如燕啄泥。小生圆润的唱腔流入每个人的心扉,引来小媳妇的温情脉脉。戏台上的人演到悲情处,台下的人也看得动情,台上台下一起悲欢。那委婉细腻的唱腔和轻翘起的兰花指让村民们的心变得丝绸一般柔软。
大家听戏的次数多了,也能随口说出安寿宝、蔡伯喈、小方卿、赵五娘、陈世美等戏曲中的人物。秀英嫂有时还翘起兰花指、甩起袖子,咿咿呀呀地哼一段,大家笑得前俯后仰,随即口中也咚咚锵锵地擂鼓助威,一地的欢乐在流淌。
看年戏的日子可是乡亲们最快乐的时光。可现在有些乡村再也不唱年戏了,有些年轻人对一些传统的曲目和流派都很陌生。电脑、电视、手机占据了他们所有的闲暇时光,他们失却了亲近自然、享受传统艺术的机会。
年戏是古老农耕生活中一面精神旗帜,凝聚着村民的悲喜忧伤,抚慰着村民们沧桑粗糙的心灵。人们从戏曲中学到了传统的生死道义、处世哲学,满足了崇拜英雄、释放痛苦的愉悦。
在清寒和腊味包裹的纯净时光里,故乡的年戏给我们物质匮乏的生活带来的幸福和快乐是那样的真切,那样的刻骨铭心,让我们避开现代生活的浮躁和喧嚣,撷拾遗落在岁月深处的纯真和质朴、诗性和唯美、柔软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