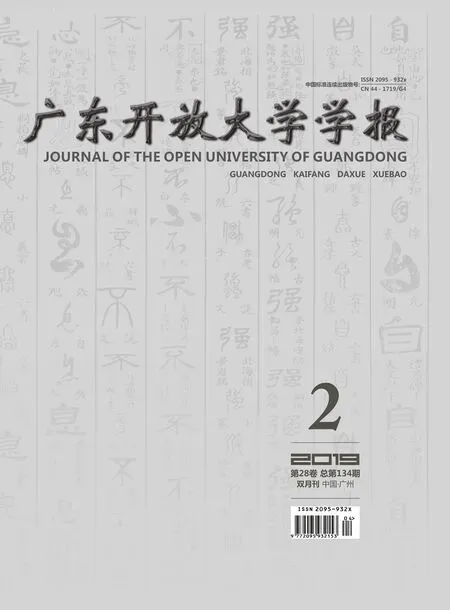《上海孤儿》主人公班克斯的身份困境
王飞
(长沙学院,湖南长沙,410003)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是身份书写大师。他对文化遭遇背景下身份的焦虑和认同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迄今出版的所有作品当中。在他独特的身份书写中,石黑一雄透过移民主角的个体视角,思考全球化时代移民族群的心理症状和身份问题,对文化交流中的跨文化冲突和融合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但他并未直接描写自己或者父辈的移民生活,而是通过刻画与自己差别极大的人物来思考身份问题。《上海孤儿》虽然以石黑一雄祖父的经历为蓝本,但读者也可以在主人公班克斯身上发现石黑一雄自己的影子。石黑一雄5岁时从日本移民英国,日本和英国既是他的两个家园,也是他的两个异乡。同石黑一雄一样,《上海孤儿》中的班克斯也是典型的移民,甚至可以说是“双重移民”。他是从小生活在上海租界的英国人,但父母失踪后又被送回英国。在英、中两个家园之间的徘徊让他的身份产生了分裂。正是这种特殊情况使得他拥有比石黑一雄其他小说中的主人公更为严重的身份困境。在上海追求“英国化”、重返伦敦却又成为“移民”,对两个家园的异化与追求,使得班克斯一直徘徊在两种文化和两个认同倾向之间。
一、双重家园与身份分裂
正如巴里·刘易斯(Barry Lewis)所论,包括《浮世画家》中的小野和《长日留痕》中的史蒂文斯在内,石黑一雄小说主人公内心深处都有着“无家可归(homeless)与‘在家’(being at home)[两种感觉]①[]号内文字为笔者增加的说明,下同。的激烈竞争”[1]3,形成所谓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班克斯可能幼时随父母一同从英国迁至中国,也可能就像山下哲那样,本身就出生在上海租界。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像他这样的移民主体必然同时拥有了两个家乡。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在另一方面却又让移民主体产生无家可归的身份焦虑,因为当他们身处一个家乡时,就必然会去怀念另一个家乡。这在为他们的流散身份建构提供更为丰富的认同资源的同时,也构成他们产生身份焦虑的根源所在。
对于“移民主体而言,思乡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活动之一”[2]88。作为石黑一雄小说的基本基调,思乡或者怀旧(nostalgia)同样也是《上海孤儿》传递给读者的一种情绪。从词源上来讲,nostalgia一词源自希腊词根nostos和algos,分别意指“回家”和“痛苦”[3]16,其发端于病理学的词源语义正好指向移民主体体验到的身份焦虑。茨威格曼(Charles Zwingmann)结合病理学基础和现代社会背景对“怀旧”进行研究,认为怀旧来自于“生活的不连续性”,“即人类必须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某种突然中断、剧烈分裂或显著变动的生活经验,才有可能产生怀旧的情绪”[4]78。“双重移民”给班克斯带来双重的“不连续性”,对“两个家园”的怀念让他产生双倍的身份焦虑。
在小说中,班克斯多年后重返上海,在战场上偶遇儿时伙伴山下哲时,他对山下哲所说的“家乡”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他(哲)点点头。“我在这里打了好几星期的仗,对这里熟悉得就像”——他突然咧嘴一笑——“就像是自己的家乡”。
我也笑起来,但有些不解他说的话。“哪个家乡?”我问。
“家乡,我出生的地方。”
“你是指租界?”
哲沉默了一会儿,说:“对,就是它,租界。外国租界。我的家乡。”
“是啊,”我说,“我想它也是我的家乡。”[5]233
加快向发达国家开放,对接欧美日韩等先进经济体国际旅游体系。推进中美、中欧等国际旅游战略合作项目落地。整合旅游资源,互推旅游精品线路,互送客源,开拓新兴旅游市场。极力争取入境免签政策,吸引更多境外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扩大国际市场。不断开拓国际航空圈,推动试行第五航权开放政策,加快提升国际通达性和航空保障能力。
正因为他们都拥有两个家乡,班克斯才会问山下哲到底指的是哪个家乡。关于上海租界,班克斯向山下哲袒露了隐藏心中许久的秘密:“我在英国住了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真正觉得它是我的家。只有外国租界,它才是我永远的家”,“可正如你刚才说的,它是我们的家乡。唯一的家乡”[5]233。班克斯向山下哲所做的这段坦白,表面上似乎说明他的认同对象是上海租界,但其实不然,因为这只是凸显了他多年生活在英国所体验到的身份焦虑而已。其实,早在上海租界的童年时期,班克斯就已体验过类似的身份焦虑。随着父母失踪、离开上海,这种身份焦虑又伴随他回到了故国英国。
在回英国的船上,就像多年后在上海战场上那样,班克斯平生第一次对“家乡”进行了深入思考。带班克斯回英国的张伯伦上校曾这么规劝班克斯:“我敢保证一旦你在英国安顿下来,就会很快忘了这里的一切。上海不是个坏地方,可八年时间够我受了。希望你也这么认为。再呆下去,你就要成为中国人了”。张伯伦上校所谓“就要成为中国人了”本身就意指一种国族身份认同。他规劝班克斯要“高兴起来”,因为“你现在是去英国。回自己的家乡”[5]26-27。正是他关于家乡的说法引出了班克斯对“家乡”意义的思考:“前面等待我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国度,那里我谁都不认识,而此刻在我眼前逐渐消失的城市,却一草一木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毕竟那里还有我的父母……。我抹去眼里的眼泪,把目光最后投向岸边,企盼着此刻能看到母亲的身影——甚至父亲的身影——冲下码头,向我招手并呼唤我回头”[5]27。这正好印证了上文的论点,即拥有两个家乡的班克斯却又焦虑重重,因为身在上海时,他会怀念英国,然而当他回到英国,却又开始怀念上海。在传统意义上来讲,“家”是一种“地点的话语,在这个地方有着扎根的感觉”,它意味着“家人、亲戚、朋友、同事以及其他各种‘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所组成的网络”,意味着“通过社区和家乡体验到的社会及心理地理”[6]4。但对于班克斯这样的移民主体,“家”“同时具有流动与扎根的含义”。也正是“家”的这种矛盾含义产生了班克斯的身份困境。
事实上,班克斯的身份困境贯穿于他的整个人生。按照小说故事的时间顺序进行考察,不难发现,班克斯在不同人生阶段都经历了身份困境。班克斯的人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上海租界的童年,在英国的青少年,以及长大成人后的中年(中年的前段,生活在英国;后段,则重返上海)。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在每个人生阶段,石黑一雄都为班克斯设置了一个“影子人物”,分别是儿时伙伴山下哲、英国寄宿学校校友安东尼·摩根以及养女詹妮弗。在这些“影子人物”身上,也能够从侧面窥到班克斯自身的身份困境。
二、“英国化”与身份焦虑
正是在班克斯与其童年“影子人物”山下哲的一次“不同寻常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班克斯自己童年时期感受到的身份焦虑。当问及爸妈之间为何偶尔不说话时,山下哲告诉班克斯:“因为你不够英国化”,接着说自己爸妈之间不说话,是“因为我不够日本化”[5]67-68。山下哲与班克斯的情况相似,都随同自己的父母一起待在上海租界,只不过山下哲是日本人,而班克斯是英国人罢了。山下哲借用一名日本高僧的话告诉班克斯:“我们当孩子的,就像[百叶窗上]把那些板条连接在一起的麻绳。虽然常常不尽如人意,却不仅能够连接整个家庭,而且还能连接整个世界。假如我们不尽自己的力量,那些板条就会掉下来,散落在地上”[5]69。由于这一意象贯穿整部小说,不妨认为,既“连接整个家庭”又“连接整个世界”的“麻绳”便是国族身份认同;而总是对“板条……会掉下来,散落在地上”的担心便是一种身份焦虑,因为山下哲借用日本高僧的引言目的是在证明他所谓的“英国化”和“日本化”,或者说他们不够“民族化”的身份焦虑。
“英国化”也正是幼年班克斯努力想要达成的目的。其中一个事例便是将到自己家中的“暂住客人”当做“极力效仿的对象”,因为他们“往往会带来我从《柳林风声》中读到的英国乡间小路和草地的气息,要么就是让我感受到柯南·道尔推理侦探小说中描写的大雾蒙蒙的街道。这些急于在我们家人中间留下好印象的年轻的英国人,对我冗长甚至有时不可理喻的问题是有问必答”[5]50。在上海租界的班克斯却对自己的另一个家乡——英国充满了好奇。而菲利普就是这么一位“暂住客人”,一个班克斯“极力效仿”、选择认同的对象。这也解释了为何父亲失踪后,班克斯并未感到那么担心,而生发了他自己后来认为“荒谬得出奇”的想法:“多年来他一直是我崇拜的对象,以至于爸爸刚失踪时,我曾经想过自己无须为此太过担心,反正菲利普叔叔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替代父亲的位置”[5]107。但是这些“父亲人物”只是真正父亲的替代品,从另一侧面体现出班克斯的身份焦虑,书绪芳岳(Fumio Yoshioka)就指出,小说中“真正的父亲很少看到,或者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父亲人物或者继父所替代。这构成“小说人物”悲剧情境的重要一维”[7]25。
单伟爵(Wai-chew Sim)发现,小说中的山下哲是作为班克斯的“影子人物”存在的[8]338,而山下哲的焦虑正是班克斯自己焦虑的一种映射。所以有必要细察一下班克斯童年“影子人物”山下哲返回日本一段时间所体验到的身份焦虑。与其说是幼年班克斯通过山下哲提前体验身份焦虑,还不如说是成年班克斯回顾往事,将自己当年回英国后的焦虑与“影子人物”山下哲交相比照。据班克斯猜想,“从他回日本的第一天起,哲的日子就苦不堪言……但据我推测,由于他身上的‘异国成分’ ……使他被众人无情地排斥在外。不仅同学取笑他,就连老师,甚至包括让他寄住的亲戚——这一点他暗示过不止一次——也都嘲笑他。后来他实在痛苦不堪,父母只好不等放假就将他带回上海”[5]83。有趣的是,这段对山下哲的描述大多出自班克斯自己的“推测”,只是“猜到了他在日本过得并不开心”[5]82。通过小说接下来的叙述,当然可知,班克斯的“推测”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他的“推测”到底是出自儿时呢,还是出自现在?或换句话说,到底是基于对山下哲焦虑经验的想象,还是基于返回英国后的自身遭遇呢?因为我们知道,小说叙述者是成年后的班克斯。他对一段往事的回忆必然带有双重记忆的滤镜。所以,本文认为,这段对自己“影子人物”山下哲的描述其实是班克斯的“自我描述”,间接地反映了班克斯自身的身份焦虑,反映了他从上海回到英国后的那段“文化冲击”的经历。在回应山下哲“我永远不想回日本”时,班克斯说“我也永远不想回英国”[5]91。但最终,想要永远在上海生活的班克斯却由于父母双双失踪而成了一个孤儿,不得不被送回了英国。“孤儿”状态产生的原因便是时空变迁导致的“激烈变化”[8]74,本身就是一个身份缺失的象征,而班克斯对父母的追寻正反映出他对自身身份的焦虑与追寻[9]202。
三、“移民”体验与身份游离
事实上,回到英国后的班克斯同样也感受到严重的身份困境。上文提到的山下哲回日本的遭遇已经为班克斯回英国的经历打了伏笔,因为那也正是班克斯回到英国后的“移民”体验。小说伊始,班克斯便说:“从中学到大学,经过多年与众多学友同窗朝夕相处的校园生活,独处的日子令我倍感快乐”[5]3。说独处的日子快乐,从反面理解便是说与学友同窗共处的日子没那么快乐。这一点在小说稍后便可得到印证,班克斯昔日同窗奥斯本称学生时代的班克斯为“大怪人”。虽然班克斯自己反驳说“那天上午奥斯本居然会这么说令我很是迷惑不解,因为我记得自己可是完全融入了英国的校园生活”[5]6-7,但他接下来举的例子却与返回日本时的山下哲遥相呼应,从反面刻画了他作为一个“异国成分”十足的局外人的形象:“记得到校第一天,我就注意到许多男生站着说话时喜欢摆一种姿势……我清楚记得我就把这套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同学中谁也没有觉察出什么奇怪之处或拿我取笑”。班克斯不无自豪、略带夸张地继续说,“我以同样大胆无畏的精神,很快精通了同伙中时兴的其他种种手势、措辞和惊叹语,同时还对新环境中流行的、藏而不露的习俗规范与社交礼仪了如指掌”[5]7。叙述者班克斯“所讲的故事正好出卖了他自己”,也就是说,从他的话语中“接收到[的是]相反的信息”,“明显看出他是一个不能融入环境的男孩”[10]。班克斯的叙述对他自己的身份焦虑欲盖弥彰。透过班克斯肯定、自信而又略带自我嘲讽的语言,我们看到了一个可爱、可怜甚至有些可笑的、与环境格格不入的局外人。
这一点,从班克斯重返上海租界时遇到的另一个昔日校友、“影子人物”安东尼·摩根的口中得到了证实。摩根对班克斯说:“我想我们早应该携起手来。两个可怜的孤独孩子。应该这么做才对。你和我,我们早该联合起来。真不懂当初为什么没这么做。假如我们联合起来,就不会感觉受人冷落了”。同班克斯一样,摩根也是一个“可怜的孤独孩子”,但班克斯对自己的这种形象却矢口否认,认为安东尼·摩根的这种说法“令我大吃一惊。过后我才意识到这不过是摩根自欺欺人的念头罢了——完全可能是他多年以前臆想出来的,为的是让那段缺少欢乐的日子回忆起来有趣一些”[5]166-67。让班克斯“大吃一惊”的,其实是他从上海回到英国后生活的真相。他的矢口否认,一方面体现了他的身份焦虑,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一直在努力为自己建构某种身份认同。这也正是他为何多年来一直在追寻父母,甚至到了一种偏执狂的地步。同时,父母的缺失也从更为基本的层面促成了班克斯的身份困境。这一点又从小说中另外一个孤儿、作为班克斯“影子人物”的养女詹妮弗身上反映出来。
小詹妮弗是班克斯收养的孤女,与班克斯自己有极为相似的遭遇。她在十岁时失去了父母(班克斯自己也正是在十岁时父母双双失踪),不得已被送到身在加拿大的祖母那里(班克斯则是被从上海送到英国的姑妈家里)。不仅这些外在的情形是类似的,据班克斯自己说,父女俩同时也能“相互理解,对各自的想法有一种本能上的心灵相通”[5]283。显而易见,詹妮弗是作者为班克斯设置的另一个“影子人物”。与班克斯一样,作为“孤儿[的小詹妮弗]是一个失去个人和文化认同的他者”[11]84。小詹妮弗实际上侧面反映了班克斯自己的身份困境。
小说对詹妮弗的叙述不多,除了小说中间部分插入的关于她的收养过程以外,就是多年后的1958年詹妮弗随同班克斯一起去香港看望他母亲那段。这时的詹妮弗已人到中年。班克斯最终决定带詹妮弗一起去香港,是因为“她确实希望离开一阵子——她也有自己的烦恼,出去走走可能对她有好处”[5]274。那么詹妮弗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烦恼呢?下面是小说结尾处父女之间的一次对话:
哎呀,你别为我操太多心。
可我就是放心不下。我怎么可能放心?
“一切都过去了”,她说,“去年发生的一切。我不会再做同样的傻事。这我已经向你保证过。不过是一段心情特别糟糕的日子罢了,仅此而已。我并非真心那么做。当时我特意让窗子敞开着的。”
但你还年轻,詹尼弗,前面还有大好年华。一想到你竟有那种念头,我就感到伤心。[5]280
根据詹妮弗所说的“特意让窗子敞开着”,可以推测她去年所做的“傻事”应该是想要通过煤气自杀。自杀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婚姻的不幸,但正如班克斯所说的,其根本原因却是班克斯在詹妮弗的成长阶段,没有花时间陪她、帮助她,没有尽到养父的职责,让詹妮弗成了又一个无父无母的班克斯。而这一切的原因又在于班克斯自己也一直深陷身份焦虑,同时又努力追寻父母、建构身份,无暇照顾詹妮弗。如是,班克斯自己的身份焦虑不经意间“遗传”给了自己的养女。对于班克斯来说,与詹妮弗类似,失去父母就意味着身份焦虑。对于詹妮弗的身份焦虑和危机,班克斯说:“不可否认,它令我十分欣慰,现在完全可以相信她已经穿过生命中的一段黑暗隧道,顺利到达另一头。虽然那里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尚不可知,但依她的个性,决不会轻易接受失败”[5]283。事实上,班克斯在养女詹妮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表面上是在思考养女的人生,其实是在为自己能够勇敢面对身份困境而鼓气加油。
结语
作为移民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说更加关注小说人物产生身份困境的空间维度,即移民的空间位移与身份焦虑之间的关联。这些人物由于进入他国,进入另一种文化,要么对母国和移入国两种文化都不能取得认同,如《远山淡影》中日本母女悦子和景子的失根与困境,要么与母国和移入国的两种认同产生冲突,如《上海孤儿》中班克斯的内心分裂。
面对文化冲突,不同的小说人物选择的文化协商因人而异,也就造成了他们独特的身份认同。小说人物的身份困境是石黑一雄自身文化遭遇的反映,也是作为个体对时代课题的回应。石黑一雄基于自身移民经历思考身份问题,探究考察人物各不相同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协商模式,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交流、移民适应、文化交融,甚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