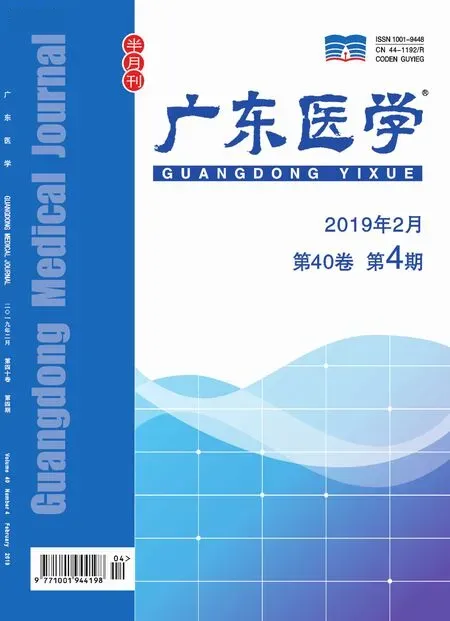非编码RNA与卒中研究进展*
马蓉, 徐弘扬, 杨锡彤, 王光明△
1大理大学临床医学院(云南大理 671000); 2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基因检测中心(云南大理 671000)
脑卒中是威胁生命的疾病,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导致残疾的主要原因,缺血性卒中由于脑血流量供应减少,造成脑组织氧和营养物质缺乏,最终导致神经元细胞死亡和脑梗死。根据脑卒中的高发病率、高病死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以及并发症多的特征。脑卒中与冠心病、癌症并列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2016年《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报道:我国现有脑卒中患者7 000万人,不同地区的卒中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为(260~719)/10万人,每年新发卒中200万人,而每年卒中致死人数高达165万人,占所有其他原因死亡人数的22.45%[1]。在中国,约75%急性脑卒中患者是缺血性卒中[2]。幸存的脑卒中患者往往会伴随着残疾和劳动能力的丧失,对社会经济造成负担[3]。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扩大,脑卒中对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造成的负担相应的增加。由于卒中涉及的病理生理级联反射复杂多样,导致目前卒中的临床治疗研究进展缓慢。为了进一步阐明脑卒中发病的分子机制,目前非编码RNA(noncoding RNAs,ncRNAs)在脑卒中中的作用得到了阐述。本文就ncRNAs在卒中患者中的作用及其相关机制进行综述。
1 ncRNAs概述
ncRNAs来源于非翻译或非转录区和内含子的不编码蛋白质的RNA[4]。一般来说,根据链的长短次序长度小于200 bp的RNA称为小ncRNAs,长度大于200 bp的RNA称为长ncRNAs[5]。目前,ncRNAs被认为是体内代谢、发育和分化等各种生理和生物学反应的重要介质,也与机体的某些病理状态有关[6]。在缺血性损伤后对神经元修复中各种ncRNAs有积极的作用,且与ncRNAs相关的治疗技术已经应用于心血管疾病,不同类型的ncRNAs对预防心肌细胞死亡及促进血管生成有积极的作用[7]。因此,用各种类型ncRNAs的组合对缺血性卒中的病理学进行标记或对卒中治疗进行探讨,本文将集中讨论3个家族的ncRNAs在卒中中的活动和已知的关联:微小RNA(microRNAs,miRNAs),它们控制转录后基因表达;长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s,lncRNAs),它们在基因组维持中起作用;环形RNAs(circular RNAs,circRNAs)在基因表达中起调控作用。
2 miRNAs与脑卒中
miRNAs是普遍存在的、内源性的非编码短单链RNA,其长度通常为19~25个核苷酸,其通过与3-非翻译区(3-UTR)结合以序列依赖的方式介导转录后基因沉默[8]。在大脑中,神经元网络的复杂性和可塑性以及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的功能特异性都依赖于高度组织化和协调化的基因表达。据估计,至少有30%的蛋白质编码基因受miRNAs调节[9]。有数据表明,miRNAs在脑内的表达受控于时间和空间,它在突触可塑性、神经元分化和发育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10]。目前,已建立了多种用于研究大脑和血液中的miRNAs的调控作用及神经保护作用的实验模型。在小鼠和人脑中发现存在特异性的miRNA-9、-124、-124a、-128、-135、-153、-185和-219,且指出脑缺血时miRNA-9、-124和-128下调,其余5种无明显变化[4]。此外,循环miRNAs在不同的卒中患者中的表达有所差异[11]。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miRNAs作为脑卒中生物标志物的作用以及作为调控卒中级联相关通路中大量基因的靶点等方面。因此,miRNAs作为卒中新型的生物标志物以及潜在的治疗靶点备受关注。
目前研究认为,miRNAs参与了人类约1/3基因的表达调控,其基因调节功能使它们成为疾病的潜在候选标志物。Mirzaei等[11]也阐述了基于miRNAs的脑卒中治疗的应用、治疗的潜在机制以及通过靶向特异性miRNAs预防卒中损伤的药物制剂等,有了以上理论基础,较少被研究的2个ncRNA组在卒中后脑血管病理生理学中的功能意义和机制也将得到更多的研究。在中脑动脉闭塞的大鼠模型中,使用miRNAs芯片技术鉴定了缺血性损伤的脑中miRNAs的变化情况,在缺血再灌注后3 h,miR-140、miR-145和miR-331逐渐增加,缺血再灌注后3 d内,miR-140、miR-145和miR-331逐渐增加,而miR-153、miR-29c、miR-98、miR-204等多个miRNA的表达逐渐降低[12]。脑缺血后miRNA的变化表明miRNAs可能在脑缺血早期应激反应中作为细胞存活的负或正调节因子在起作用。用神经元细胞培养实验证明多个miRNAs(miR-200b,miR-200c,miR-429)本身具有细胞保护作用,用中动脉闭塞(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MCAO)的小鼠模型发现,miR-181的区域表达变化与脑血流分布呈负相关,并且抗miR-181可以保护脑免受缺血损伤[13]。在大鼠中脑动脉闭塞的模型中显示miR-23a的表达水平有性别差异,部分解释了卒中发病机制的性别差异[14]。这些发现证明了miRNAs转录后调控的复杂性,其表达的改变对细胞生存或者死亡都有影响。因此,miRNAs作为新的生物标志物和作为卒中治疗干预的潜在靶点具有很好的前景。
miRNAs作为基因表达的关键调控因子,不仅为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还为缺血性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但miRNAs亲水性强不易跨越血脑屏障,此外,miRNAs稳定性不如DNA,因此,miRNAs治疗脑卒中的潜在用途受到了包括血脑屏障渗透和稳定性的若干因素的影响。通过化学修饰等技术可以改变miRNAs的稳定性和跨越血脑屏障的能力,从而为miRNAs在卒中方面的应用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作为预防或治疗卒中的生物分子,miRNA在人体内的量应该具有可操作性,其增加或减少大脑中miRNAs含量的技术方法处于实验室尝试阶段。鉴于缺血性卒中病理生理分子信号的复杂性,单一基因的靶向治疗干预在临床上失败也是常有的。具有调节大量进化保守编码基因的能力的靶向非编码基因如miRNAs,在未来基因治疗方面是极具代表性的。
3 lncRNAs与卒中
lncRNAs是一类较长的ncRNAs。它们种类繁多,数量众多,至今已鉴定出的人类的lncRNAs超过50 000个[15]。在多发性疾病方面,lncRNAs在包括表观遗传调控、转录调控和翻译后控制等的发生发展相关的蛋白质编码基因表达水平调控以及相关信号通路的调控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lncRNAs作为一种新型的具有生物学功能的临床生物标志物,具有广泛的临床应用前景。依据它们的结构特征,lncRNAs可以直接结合同源基因组DNA和RNA。lncRNAs也可以通过形成复杂的二级结构与许多蛋白质相互作用。近年来,lncRNAs在分子功能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包括RNA加工、转录以及基因表达和作为小RNAs前体的转录后调控,很明显,lncRNAs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生物学过程,如细胞存活、增殖、分化、染色质重塑和器官的形成[16]。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lncRNAs在缺血性卒中的发病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某些lncRNAs在缺血性卒中的体外和体内的差异随时间而改变,并可作为生物标志物广泛应用于临床。在啮齿动物卒中模型和中风患者[17]的血液样本中也发现了lncRNAs水平的改变,并且可以作为潜在的标志物。血液样品中lncRNAs水平变化,提示循环lncRNAs可能是反映脑的病理生理状态的一个有前景的标志物。最近的研究表明,lncRNAs下游转录因子c-fos(Fos downstream transcript,FosDT)通过与神经元限制性沉默因子(repressor element silencing transcription factor,REST)相关的染色质修饰蛋白相互作用来促进缺血性脑损伤[18],lncRNAs也可通过调节REST下游的基因来治疗卒中后偏瘫,提示lncRNAs可以作为治疗靶点,以减少卒中后的脑损伤。其他的lncRNAs如SNHG14、TUG1等也被报道能介导缺血诱导的神经元死亡、神经发生和神经恢复[19-20]。有研究[2]指出,H19基因的多态性增加了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缺血性卒中风险,提示lncRNAs H19可能是缺血性脑卒中的一个新的诊断或治疗靶点。但关于lncRNAs的探究仍然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就如lncRNAs功能上的复杂性就阻碍了对其分子机制的研究,而且许多lncRNAs只在灵长类中表达。即使我们已经证实了其部分的分子机制,但这在临床应用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circRNAs与卒中
circRNAs是近年发现的一种新型的内源性ncRNAs,是RNA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与链端有5′帽和3′尾的线性RNA不同,环形RNA形成共价的闭环结构,既不具有5′-3′极性,也不含有多聚腺苷酸尾[21]。circRNAs是在研究植物类病毒和酵母线粒体RNA中发现的一种独立类型的ncRNAs。当一个前体信使RNA分子的5′和3′端通过共价键连接在一起时,另一个亚组的ncRNAs就形成了环形结构,这样的结构被命名为环形RNAs。它没有明确意义上的5′帽端和3′多聚腺苷酸尾端,因此,环形RNA的性质不稳定,加之检测技术的局限性,circRNAs的研究报道较少。根据它们的序列和起源,circRNAs可以分为循环内含子、保留内含子和外显子3种类型[22]。circRNAs具有miRNAs结合元件与蛋白质结合位点。当circRNAs与靶蛋白结合时,蛋白质的功能将会受到抑制。被释放到细胞质中,甚至在细胞外释放的circRNAs具有作为生物标志物的潜力。然而,少部分留在细胞核中的更小的circRNAs可以与宿主基因启动子区的RNA聚合酶Ⅱ反应并调节转录[23]。
据报道,circRNAs在诸多病理生理过程中也有重要作用,包括热衰老、阿尔茨海默病、心肌肥厚和心力衰竭等[24]。然而,其在脑损伤和脑卒中修复中的作用报道很少。Bazan等[25]在临床研究中指出,急性颈动脉相关缺血性卒中的患者血清中某些circRNAs如circR-284与miR-221含量升高,提示circRNAs可能作为诊断颈动脉相关脑缺血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另外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卒中后一些circRNAs如circ-016423、circ-008018、circ-006696等会发生改变,含有大量miRNAs结合位点,此外,由这些circRNAs控制的主要生物学和分子功能包括代谢加工、细胞通讯、生物调节以及与蛋白质、离子和核酸的结合在短暂性脑缺血之后都被改变[26]。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表明,circRNAs在生物学发展和疾病的发生和演变过程中具有特殊的调节作用,有望成为新的临床诊断和预后标志物,并为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方向。
总之,circRNAs的功能与相关机制可能是多种多样的。circRNAs可能会影响病理生理过程,作为疾病的诊断或预测生物标志物,也可能提供新的潜在治疗靶点。然而,与miRNAs和lncRNAs相比,我们目前对circRNAs的了解较少。探究circRNAs的作用及功能,可能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有巨大的应用潜力。近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circRNAs的生物机制上,而在各种疾病的发展中,circRNAs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尚未完全了解。随着技术和研究的发展,将会发现其他的circRNAs序列。此外,进一步的研究将揭露出更多的circRNAs在疾病生理和病理过程中的作用。
5 挑战与展望
目前磁共振成像技术仍然是卒中诊断的主要方法,虽然卒中患者血清/血浆中几种蛋白标志物会变化,但卒中缺血损伤的特异性标志物尚未建立。且对ncRNAs作为缺血性脑卒中生物标志物的研究相对较少。其次,大多数miRNAs和lncRNAs被细胞内循环/内吞噬中丰富的核糖核酸酶迅速降解,因此作为脑卒中患者诊断或预后的生物标志物还有待研究。另一方面,与miRNAs和lncRNAs相比,circRNAs的半衰期相对较长,它更能成为脑卒中诊断和预后的的理想候选标志物。研究表明ncRNAs参与缺血性损伤,ncRNAs的调控作用可能是继tPA后对卒中治疗的有促进作用的方法,因此快速和可靠的ncRNAs检测可能对卒中的早期诊断以及患者的卒中预后的预测有用。对实验性卒中模型ncRNAs的调控机制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ncRNAs在卒中中的作用。总之,ncRNAs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可以确定的是ncRNAs对卒中的治疗是有促进作用,其在细胞存活和神经保护方面的治疗效用还需要做大量的探究。
尽管面临挑战,但以ncRNAs为基础的治疗卒中的策略是很有前景的。为了更好地了解ncRNAs是如何通过数百个靶点发挥作用,还需更多的研究开发新的方法来识别候选ncRNAs标志物,设计化学或修饰制剂以更好地递送ncRNAs,并不断优化减少不良反应。基于ncRNAs的临床试验和有效的药物研究肯定会促进卒中治疗领域的发展。随着生物学信息的进步,更多关于ncRNAs的研究得以开展,确定其潜在的机制也是迫切需要的。随着我们对卒中发病机制中ncRNAs表达和功能的认识,有希望能识别出新的卒中诊断生物标志物和有靶向治疗意义的ncRNAs,随着ncRNAs相关疗效和准确性的不断研究,卒中患者也可能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