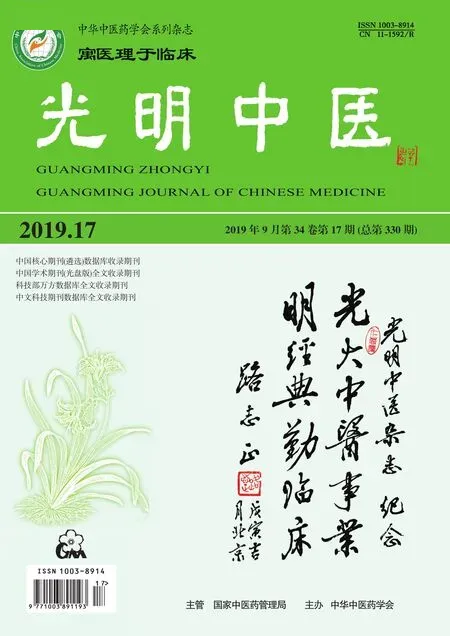也谈中药“毒性”(上)
张 良 尹亚东
中药的“毒性”问题,其实是个很大的话题。以我们的学识修养,其实很难说清楚、说透彻。但因为这些年国家对中医药的重视程度加强,尤其随着电视剧《老中医》的热播,出于种种原因,在有些别有用心者带动之下,社会上对中药“毒性”的议论又突然热络,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也谈一谈这方面的认识。毕竟,笔者中医药大学毕业历从事中医药行业已20多年,而且作者之一还是祖传7代[1]的中医药世家子弟。
1 中医学对中药毒性的传统认识
中、西医学因为理论体系不同、思维方法不同、研究方法不同[2,3]会导致对药物尤其中药的“毒性”认识大相径庭。
在中医的发展史上,甚至把一切药物都看为“毒药”,《周礼·天官冢宰》曰:“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素问·汤液醪醴》曰:“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素问·异法方宜论》曰:“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素问·胀气法时论》曰:“毒药攻毒”,以上论述都是这种认识。一直到明代,仍然有医学家谓“毒即药”,如张介宾在《类经》中就说:“毒药者,总括药饵而言,凡能除病者,皆可称之为毒药”。
简而论之,目前中医业界公认,中药的“毒性”认识可分广义、狭义2种。狭义之毒,指药物本身确有毒性,使用常用剂量或比较低的剂量,也可能对人体以及机能产生特定的损害作用,甚至中毒、死亡,如砒霜之类。广义之毒则是指中药的寒热温凉偏性、补泻清润作用。如黄连大寒、附子大热,这个大寒、大热就是药物的“毒性”。所以张介宾就说:“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是以气味之有偏也”。《神农本草经》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应该就是这种认识。我们常说的“是药三分毒”也基本上是从这个道理讲的。
客观上讲,历代药物经典对中药毒性的认识受制于历史条件,相对是比较粗糙的。传统对于中药毒性的认识和分级均来源于临床,基本上是以临床实践中观察到的服用药物后的身体反应来作为药物毒性的认识依据,除中药本身的毒性反应外,往往还包括了中药的偏性等。这种研究方法明显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缺乏准确的、量化的、统一的标准[4]。如《神农本草经》将中药分为有毒与无毒两类;《吴普本草》把药物二分为大毒、有毒,《本草经集注》(陶弘景著)把中药分为大毒、有毒、小毒三类,《本草拾遗》(陈藏器著)则把中药分为大毒、有毒、小毒和微毒四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5]和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中药学》[6]对中药毒性和分级标准也一致分为“大毒”“有毒”“小毒”三级标准。所以后世以及当代医家一般都认为:“大毒”中药,是使用剂量比较小即会引发中毒症状,中毒反应发生较快且比较严重,更容易造成死亡。“有毒”中药,则是使用大剂量或较大剂量才会出现中毒,中毒反应发生比较缓慢,但后果仍然可能非常严重,甚至会造成死亡。归类于“小毒”的中药,则是在标准剂量下不易或不会中毒,超大量使用才会发生中毒反应,而且症状比较轻微,不会造成死亡[7]。但是这种“小剂量”“较大剂量”和“超大剂量”并没有什么量化标准,从而缺乏实际上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
2 中药毒性的现代医药学认识
现代医药学对于中药“毒性”的研究路径和认识方法与中医药学几乎全部来源于临床实践不一样。西医毒性试验的一般方法,是先用一组动物,如小白鼠,给同样的药物和用量,使用相当一段时间后,观察某些理化指标或者解剖观察某些指标,来确定毒性的有无及大小,然后再运用于临床观察。应该说,这种方法是西医药规范化、标准化的特色体现之一,和工业化的要求一脉相承,也就是目前“科学”的研究方法[2,3]。
现代医药学和中医药学对药物“毒性”的认识有很大区别。认识方法、研究方法不同,结果、结论肯定不同。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未必就是绝对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可行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从中医思维看来,在追求标准化、规范化的同时,实质上会忽略用药的个体差异以及中医最注重的“辨证论治、对证下药”[2,3]。当然,西医的理论体系关注量化的理化指标,而中医从气血、阴阳、虚实、寒热出发,认识到的个体差异以及基于“辨证”得出的结论,因为无法规范所以西医基本是不认可的。
我们可以举个直观的例子。假如要研究白酒是否“有毒”,西医的研究方法可能是每人每天喝半斤,连续喝几个月,然后观察肝功能指标。而中医则会区别各人情况,酒量大者喝半斤,酒量小者可能喝一两,且喝一两的还有可能配合一些醒脾解酒的药物,如果有湿热表现者就直接排除不让喝酒,过一段时间后看各人舌脉神气、谈个人感受。这样不同的试验方法必然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结论。西医试验结束后可能是50%受试者出现了肝功能异常。中医试验结束,即便也使用肝功能指标来佐证,异常者恐怕也微乎其微。姑且不谈这样截然不同的试验方法孰优孰劣,仅就试验结论而言,西医恐怕会得出每日饮酒半斤有害健康的结论。事实上,这个结果对另外50%的人可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酒量的大小其实是因人而异而且差别很大。而在中医,因为这样喝酒其实并没有谁感觉不舒服,而且有些人还会感觉很舒服,所以结论就是酒不但无毒还能入药。所以就有了“藿香正气水”和各种治疗风湿的药酒。
客观上讲,中西医理论体系各有所长,也肯定各有所短。笔者不反对、不攻击西医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当然,中医药可以借鉴西医药的研究方法,但完全照搬移植西医药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药,恐怕是不合适的。这并不是门户之见、义气之争。主要是中西医学是不同的医学体系。认识方法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结果、结论自然会不同。如以下这些研究:长期大剂量服用细辛会导致血清TBIL水平明显升高,病理检查可见肝细胞明显损伤[8];中小剂量的大黄有泻下、利胆、退黄作用,但如果疗程过长、剂量使用过大会引起胆红素代谢异常[9]。细辛在《神农本草经》虽列为上品,但后世公认其“辛温有小毒”,并有“细辛不过钱”的说法,所以真正的中医医家临床上大概率不会长期频繁使用。而“大黄”药性峻猛,属于“中病即止”的用法和品种,疗程不大可能过大、用量也不大可能过长。所以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对于指导中医临床,没有太大的实际作用。就此而谈中药的毒性,意义也不是太大。而林小琪等[10]通过对144味“肝毒性中药”(未查到认定标准)分析研究,归类统计以后,认为肝毒性中药和普通中药在性味以及归经方面,没有明显的分布趋势差异,结论认为中药肝毒性与中药的药性理论无相关性。尚秋羽等[11]研究也认为肝毒性中药与一般中药在性味归经方面分布差异不明显,说明中药肝毒性与中药药性没有相关性。这些研究的临床意义不大,但至少也说明了完全西化的中药毒性研究方法,可能是值得商榷的。
3 “马兜铃酸事件”对中药“毒性”认识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看前些年国际上突然发难、国内公知精英推波助澜,热炒中药毒性的“马兜铃酸事件”。自此而后,中药的“毒性”问题,每隔一段时间,总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出来热炒。
“马兜铃”这味中药国人应该都不陌生,电视剧《西游记》里用马尿为朱紫国王治病,猪八戒失口说出一个“马”字,孙悟空赶紧以“马兜铃”打了圆场。马兜铃就含有马兜铃酸成分。另外,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还包括关木通、汉防己等数十个中药品种。
国内六十年代就报道过因大量使用关木通造成肾损害。但没有多少人关注,因为是“大剂量”。1990年至1992年,比利时有很多人服用减肥药“苗条丸”,服用时间均在1年以上,有的长达3年。其中150名女性服用者中70人被查出肾脏受到损害。一家比利时研究机构认为是“马兜铃酸”中毒所致,比利时及一些西方媒体便开始以“马兜铃酸肾病”为名进行报道。英国在1998年发现了2例“服用过”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治疗湿疹而“引起”的肾衰,随即便称其为“中草药肾病”,1999年7月29日英国政府宣布:全面禁止使用、销售所有含马兜铃属植物的全部药物以及补充剂。2000年初,美国媒体直接使用“中药肾病”字眼大肆炒作。2000年6月9日,美国药品与食品管理局(FDA)在“未收到类似不良事件报告”的前提下,命令全面停止含有或疑似含有马兜铃酸的药品和原材料的进口、制造和销售,70余种中药材被列入黑名单。搞笑的是,有些被禁中药品种仅仅因为英文翻译名称和“马兜铃”有关系就受到株连,而其实根本不含马兜铃酸成分。美国无端发难之后,西班牙、奥地利、埃及、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等国纷纷效仿跟进,最终酿成了世界范围的“马兜铃酸事件”。而国内的某些公知、精英也上蹿下跳、推波助澜,弄得中药都快和“毒药”画上等号了。
4 “马兜铃酸事件”完全归过于中医药是不公平的
首先看“苗条丸”的主要成分:芬氟拉明、安菲拉酮、波希鼠李皮、颠茄浸膏、乙酰唑胺、防已、厚朴等。首先这样的处方就很不严肃,纯粹是不中不西的怪胎!马兜铃酸可能真的有肾毒性(下文论及),但处方西药中就含有西医明确认定有肾毒性的药物。如芬氟拉明,在2009年1月已被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宣布停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且不论配方里中药饮片炮制以及制剂制备过程、中药品种配伍选择是不是合适,仅仅从组方上来说,中医就要从理、法、方、药理论出发,讲究君、臣、佐、使的配伍,治疗原则是“中病即止”。《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另外,处方还要灵活机变,“病万变药亦万变”。《吕氏春秋·察今》中“是故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为寿民,今为殇子矣”,说的就是“机变”这个方面。
再有,即便使用中药养生,需要久服长养的话,也必会选取平和中正的药品,绝不可能使用“汉防己”“关木通”之类不适合养生的药物而大量久服数年。以上对中药的“使用”方法显然全部都未遵循中医药指导原则。既然如此,即便是服用这些中药造成了伤害,究竟是中医药之过还是运用者无知,这一板子恐怕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结结实实直接打在中医药屁股上。
另外,因为马兜铃酸有问题,就要求禁用所有含马兜铃酸成分的中药,恐怕也是过度反应的双重标准。
从事临床专业的同仁可以想想,西药哪些品种没有毒副作用。20世纪90年代我们读大学时,西药第十三版《药物学》序言明确指出,收录的药物除了叶酸和葡萄糖没有毒副作用外,其他所有药物都有毒副作用。其实即如所谓无毒的葡萄糖,临床实践中某些胃病病人服用以后胃里也会不舒服。所以,有毒副作用也未必就要禁用。舞蹈“千手观音”美轮美奂的表演者们,以及她们之外很多人,失聪的明确原因就是因为使用了链霉素类药物,青霉素因为过敏反应也可能一针毙命,抗肿瘤类药物的肝肾毒性等造成全身的严重毒副反应,从其问世到现在几十年期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程度上,可能远超中医药几千年毒副作用的总和,但是这类西药也一直在临床上大量普遍应用,没有谁呼吁禁用、停用过。所以可见体系差别导致的认知差异有多大,足见双重标准的运用者有多无耻!足见西方体系对中国、对中医的文化傲慢、文化压榨有多厉害[12]!
5 渲染中药“毒性”有非专业因素
事实上,除了文化、体系的原因导致的认知差异,对于中医药的压榨攻击,恐怕还有深层次的世界医疗市场话语权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问题。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然需要文化软实力的输出以彰显民族个性,也必须取得世界级话语权、规则制定权以赢得自己应得的利益,中医药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加上中医药因为毒副作用微弱、疗效确切,这些年来在欧美得到了极其快速的发展,国外前些年都在谋划制定中医药法律法规。受到马兜铃事件的倒逼,最近这几年中国中央政府密集出台中医药发展新政,以避免中医药话语权旁落。中医药让欧美日制定标准才真的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笑柄!但话语权的争夺必然是激烈的。大家可能不太在意一个事情,西非“埃博拉病毒”肆虐的时候,中国在大量援非的同时,提出要捐赠中成药“片仔癀”用于试验治疗,但最终被以法国为首的欧美国家以“片仔癀”不良作用不确定而全力阻击,最终未能成功。屠呦呦教授研发的“青蒿素”获诺贝尔奖以后,中国的宣传口径与西方的巨大差异,其实都源于此。虽然笔者也并不赞同把青蒿素看作是单纯的中医药发展成果而最多只能算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结果[13,14]。“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那么中医药客观上不可避免要挡某些医药利益集团甚至是某些国家的财路,不被黑才怪!
——凹脉马兜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