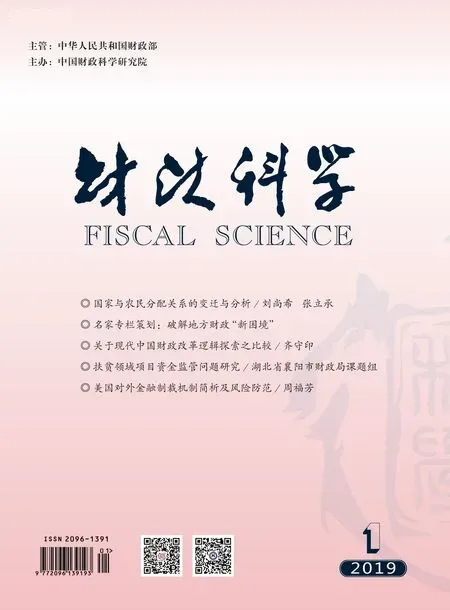基于社会共同需要的财政学如何可能?
——中国的逻辑
陈莹 唐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阐述中国逻辑和思维方式,进一步讨论了社会共同需要在历史变迁中的缘起和社会共同需要的现代诠释,通过古代和当代两个层面的说明,试图回答为什么基于社会共同需要的财政学是可能的。本文认为,中国的“团结主义”“家长制”观念和“士大夫”精神是理解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基本逻辑,同时是构建中国社会共同需要的重要因素,而财政的“国家治理论”则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现代诠释。
一、引 言
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我们不断学习并吸取西方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走出了一条全新的国家发展之路。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文化进步,也正是人类文明多样化的体现。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指出,中国具有“攫取型政治制度”和“包容型经济制度”两种特征,但是却依然囿于意识形态地强调中国没有“西方式民主”而未看到中国政府的“有为”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无论是西方学者将中国经验纳入自身逻辑范式的尝试还是中国学者使用西方理论思想来解释中国发展的努力都存在一定缺陷,这就为学科理论研究制造了一个难题:中国是否特殊到需要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既有向西方国家学习的部分,也有基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实践而不断完善的部分,且后者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而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是要求更为迫切的基础理论研究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游故宫的时候曾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走到今天,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我们会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在人类文明史上和西方世界是具有同等地位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和欧陆文化随着英法等国家的殖民扩张传播到其他大陆,而中华文化亦通过历朝历代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进入整个泛亚地区。照搬西方思维体系形成的理论基础已经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长期实践中对已有的西方理论进行改造,并主动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体系。
中国的财政学理论发展与实践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从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财政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又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从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诞生了“国家分配论”“社会共同需要论”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基础理论,通过借鉴西方财政思想和不断完善现代财政制度,部分学者也提出了“公共财政”的倡议。何振一(2012)认为,“社会共同需要论”研究的是财政一般,“公共财政论”研究的是市场经济财政个别,“国家分配论”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财政个别。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三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但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家分配论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解释力度不足,而公共财政论仍然未脱离“西方式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色彩,故而未能与中国国情与现实进行有机结合。社会共同需要论从历史的、唯物的角度阐释了财政起源与发展的基本问题,但是对于当代中国财政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指导仍缺乏有效的途径。理论化、抽象化的认识必须经过一定的转化、解读乃至“降维”,才能具体指导中国财政实践与理论研究,而这是社会共同需要论亟待进一步阐明的问题。
本文希望站在历史变迁的角度,基于国情背景和国际视野,从中国的逻辑与思维方式出发,讨论为什么中国财政符合社会共同需要论的理论范式,进一步阐释社会共同需要论在指导当代中国财政实践与理论研究中的启示,以为后续研究中国财政基础理论、讲好中国财政故事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建议。
二、中国的逻辑:作为文明国家
汪丁丁(2009)认为,财政学原理应当最终属于社会构成原理的研究范畴,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原理,有什么样的政府原理就有什么样的财政理论。中国社会是与西方社会有很大区别的①201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傅莹在朝核问题中对“中国是否已对前盟友朝鲜失去了控制?”回答,“这个用语非常西方(That sounds very western)”,体现了中国已经有意识地区别“西方式”的价值判断,而更为强调中国的逻辑。。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以“差序格局”来描述中国的社会结构,即通过血缘亲疏、情感关系来划定自身社会关系的圈层。和西方“如一棵棵干柴捆绑在一起”的群己关系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则更为具象化地验证了何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周王朝的宗法礼乐到汉王朝的独尊儒术,汉族人的集体认同一直延续了数千年,乃至不断同化、融合其他异族文化,从而构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中国”一词,也不仅仅是一个政权或是一个国家的称谓,而是一种基于文化与社会的称谓。马丁·雅克斯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指出,中国是一个与西方文明地位平等的文明国家,具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特质。而基于此,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有自身规范融洽的逻辑范式,并且在这样的逻辑范式下产生了社会共同需要。通过识别中国的逻辑特征,我们能够进一步研判社会共同需要的起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集体分成“真实的集体”和“虚幻的集体”,而区分标准则是看待个人在集体中自由与否,即个人是否“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刘荣荣,2008)。西方常以“集体主义”来暗指中国民众个体的“不自由”,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自由的联合体,是真实的集体状态,个人在集体中也是充分保证其自由的。在强调集体和国家利益的同时,中国人也需要个人个性的追求,李贽在《焚书》中曾言“士贵为己,务自适”①出自《焚书增补一·答周二鲁》。,故而仅仅用“集体主义”其实并不能准确说明中国的逻辑。中国的集体性往往是具有某种条件的,比如“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于“大事”与“小事”的判断其实就回答了中国什么时候遵循“集体主义”,什么时候尊重“个体主义”的问题。所以为了避免语义上的歧义,本文更愿意用“团结主义”来定义中国在群己关系上的价值判断。对于中国人而言,最广泛意义的、人数最多的“集体”当属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的概念下,我们维护汉族与少数民族团结、维护华侨华裔与中国民众的团结,亦维护大陆地区与港澳台地区的团结。在“团结主义”的指导下我们设立了少数民族自治区,其面积占据整个中国大陆的45.4%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而在处理港澳台问题上我们开创性地推动了“一国两制”的设计,这都是对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主义”的有力挑战。但是在汶川地震、北京奥运面前,我们又惊人地团结一致,让世界领略了何为“举国之力”。“团结主义”是社会共同需要的基础,也是社会公共需要的粘合剂。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中国“家长制”的政府观念也是中国文明的典型表征。长期以来一直令西方各界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眼里“专制”的中国在政治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拥护,同时又在经济上超越了“民主制度”下的印度,甚至正在赶超美国?中国的“家长制”观念完全无法被西方式的价值观念所理解,但却支撑一个又一个王朝维持他们的统治。虽然“家长制”政府观念有其固有的封建局限性,在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中我们亦强调公共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家长制”也已成为我们衡量当代政民关系的标杆,“有事找政府”已经成为中国民众的共识,而政府呵护民众的能力亦成为民众衡量政府优劣的标准。从“也门撤侨”“利比亚撤侨”到巴厘岛火山喷发紧急撤离中国游客,中国政府运用强大的政府能力帮助民众脱离险境,这深切地体现了“家长制”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政府”关系的基本意涵。政府并不是利益群体斗争的平台,而是引导社会进步、维护社会稳定的助推器和稳定器,并不能简单以“民主或者专制”来判断中国政治的存续状态。姚洋(2018)认为,正是因为有一个不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中性政府”,才能使得中国的经济政策具有高度包容性。由此想来,正是中国政府的“中性”,才能够产生并包容社会的共同需要,财政工具并不会因为利益集团发生“偏离”,而始终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进行决策。耐人寻味的是,世界银行、IMF等倡导的“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之所以在很多国家深入人心,不能说没有中国“社会共同需要”文化与理念的“浸润”③Anand,Rahul;et al.(May 2013)."Inclusive Growth:Measurement and Determinants"(PDF).IMF Working Paper.A-sia Pacific Department: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Retrieved 13 January 2015.Elena Ianchovichina and Susanna Lundstrom,"What is Inclusive Growth?",The World Bank,February 10,2009。,而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倒行逆施,从根本上其实也是对“社会共同需要”的背离。
除“家长制”和“团结主义”之外,“士大夫”精神也是理解中国逻辑的重要层面。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颇为不同的是,“士大夫”精神并非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施加的道德约束,而是对统治阶级本身给予的道德约束。“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国家观(诸葛忆兵,2001),“死节殉道”的生死观(黄苑峰,2003)共同建构了对于统治阶级行为的框架。“士大夫”精神虽然缘起于孔子“崇尚礼乐、效法尧舜”的理想,但是却逐渐成为了政府约束官员的基本纪律和最高守则。“士”作为政府官员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共同需要的直接接触者,也是社会共同需要的政策执行者,通过树立官员道德伦理的权威,官员的效用函数将社会地位、社会风评以及身后之名纳入进来,与西方国家通过法律来进行政府约束的情况有极大不同。因此,政府的财政支出也需要考虑到社会需要,逢遇灾年则救济灾民、对于老人实行徭役税负减免、乃至设立养老机构①公益时报网.古代如何介入养老[N].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yaowen/10594.html 2016-11。以及设置公墓从而让穷人得以安葬(张新宇,2008)。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使得社会共同需要得以顺利上升到国家决策当中,通过义理约束让政府行为符合社会共同需要,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政府财政支出框架的发展。
三、历史变迁的社会共同需要
在中华文明漫长的五千年历史中,困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最大问题一直是如何有效且统一的管理如此大的疆域。替代某个王朝的统治者往往坚持于两件事:第一是继承前王朝的所有土地,第二则是继续稳固并开拓前人的领土。在早期,中国与西方都通过土地分封来尽可能地扩大本国的统治范围。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诞生了儒家思想以调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基本矛盾,而转向了“国家有机化”,中国大陆上蔓延了几千年的战火,但是中国一直艰难地作为一个整体而存续。哈维·罗森在他的《财政学》导论部分中论及“国家机械论”和“国家有机论”两种观点,在“国家有机论”的说明中,他特意提到了杨昌济先生的思想“国家是一个有机整体,就像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一样,它并不能像机械一样随意拆分”(罗森,2015)。在中国古代,“国家有机化”的具体内容,就是“家长制”和“士大夫精神”,而同时对于财政的社会共同需要,亦起源于此。
从中国古代起,财政就是国家存续的关键因素之一。《左传》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②出自《左传·成公十三年》。就是强调国家财政的重要性。古代财政的主要目标可以简单分为两类,维护君王的统治和赢得战争的胜利。先秦时代的税收主要用于军事和王室支出,而在汉朝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仁义”作为指导王朝政策实践的思想开始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民众向帝王纳税不再是天然的、不受任何报偿的义务,帝王亦需要施行“仁政”来保持民众纳税代代不息,从而保障王朝的存续。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的农民起义只有在被政府的苛捐杂税压迫到了极致的时候才会出现,从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汉末的黄巾军起义到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当税收征纳使得农民出卖生产资料,甚至其收入无法满足基本需要时,才会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出现。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螺旋演进一个必不可少的注脚,在以血缘纽带为主观联系、以山河地理为客观约束、以安土重迁为生活重心的中国古代,农民的集体无意识使其对于政府税收力度大小有着极高的适应性。依“黄宗羲定律”所言,中国王朝的更替并没有根本性地消除税收对于社会生产的破坏性影响,虽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对于税收的承受度也越来越大,但是当税收力度越过了承受边界,则依然会导致王朝的崩坏。从另一个方面讲,古代社会对于“仁义”的推崇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民众-政府”关系。与西方作对比,西方对于政府行政的观念起源于繁荣的商业文明,从商业契约的诚信原则、权责对等原则等演化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而中国古代的政府观念则起源于农业文明的昌盛,当农业生产的规模扩大,对于天气、外族入侵等方面的风险规避则变得更为艰难,并且从某种方面来说,这并非个人主义能解决的问题,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民众往往寄希望政府力量的强大来应对这样的风险,这就导致了政府力量扩散到民众的方方面面,并在儒家思想的引导下,最终形成了民众“家长制”的政府观念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精神。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的脚步就从未停止,从保皇派到吸收日本经验的君主立宪派再到传承欧美经验的民主派,知识分子经过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洗礼,但西方式民主思想在广大的农民阶级和萌芽的工人阶级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唯一深入农工阶级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代朴素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士大夫精神是有所融合的,而从前苏联借鉴而来的政治经济体制又和民众朴素的“家长制”政府观相融合,故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传统观念的批判继承,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与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五千年来的历史惯性是十分巨大的,作为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轴的国家,我们在近代革命中证明西方式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这也说明西方世界的思想与中国的思维逻辑体系及历史现实并不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悖、相互借鉴的关系。武斌(2007)指出中国的儒家思想所代表的“伦理道德权威”在启蒙运动中成为西方思想家对抗神权开放理性的武器。虽然儒家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和阶级性,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批判改造之中儒家思想反而成为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典型特征而存在。
西方财政基础理论的发展是以社会契约和宪政民主为基础的。政府是民众缔结社会契约的产物,而宪政民主是民众用以约束政府的工具。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民众从王权和神权中逐渐解脱,强调个性解放,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而通过抗税运动对国家财政的进一步约束,民众得以普遍接受“有限政府”的观念。而从个人主义和“有限政府”出发的财政基础理论是否适用于从“家长制”和“士大夫精神”走出来的中国,是仍然存在疑问的。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中国的问题往往会引起意识形态的论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法治和民主层面。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财政实践充分表明,我们并不反对财政法制化,这和“有机国家”并不冲突。社会共同需要论也和公共财政不相矛盾,但是一味地以“西方式”的价值判断来衡量甚至否定中国财政发展与实践,则是形而上学的。
四、国家治理财政学:社会共同需要的现代诠释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以“强有力的政府”和“包容开放的经济”来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我们确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国家财政的作用却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定位。部分溯源西方理论的学者仍秉持“市场失灵”理论并认为国家财政仍未脱离“市场失灵的补充”这一定位。而李俊生(2014)已经对“市场失灵为财政的起点”这一观点作出了有力的反驳。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极大区别的,这两者并不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而是相互包含又相互独立的关系。故而将“市场经济”衍生而来的财政理论直接用以解释中国的财政现实是不妥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包含了社会主义的部分,也包含了市场经济的部分,故而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建筑是兼容国家性和公共性的。闫坤(2012)指出,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发展不仅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点上,更要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点上。财政职能的界定就必然是既有与西方市场经济财政相通的部分,即市场经济下财政职能的共性,又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职能特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从理论基础层面深刻阐述了国家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在财政国家性和财政公共性之外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维为(2016)认为,当今时代,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分类已经无法解释世界,而应当从“良政”和“劣政”的分类中出发,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可能出现“良政”和“劣政”。这就要求国家财政需要具有社会性,成为社会有机的一部分,从而为社会和谐发展提供经济基础,为政府施行良政、善政提供有力支撑。换言之,这进一步要求财政坚持来源于社会共同需要,发端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需求,从而真正发挥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国家财政的社会性正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有力论证。中国在“十五”计划中就已经推出了“村村通”工程,让所有乡镇村落通电通讯通网,支援贫困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充分体现了国家财政的社会属性。而与此同时,与中国人口和地理复杂度不相伯仲的印度直到2018年才实现全部村落通电①中华网.印度所有村庄通电 举国欢呼[N].https://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180501/32365278.html 2018-05。。而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事业一直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重点。联合国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的8.36亿,其中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②新华网.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中国奇迹”普惠世界[N].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0/16/c_128325 377.htm.2015-10。。在中国的扶贫事业当中国家财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国家财政支持扶贫也充分体现了国家财政的社会性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扶贫政策和西方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体系是有所区别的,中国更侧重于使贫困人口获得劳动能力或者生产资料,从而更好地加入社会生产,而“西方式”的福利国家削弱了民众的劳动意愿,本文认为是不符合“社会共同需要的本质来源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中国的国家治理并非出于选民投票的需要,也非政党政策的需要,而是真正出于社会共同需要,让改革开放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除此之外,这也要求财政不仅仅面向国内社会共同需要,也要面对国际社会的共同需要。随着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伊核协议”,国际社会期盼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与国际义务,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一直为环境保护、人权、核不扩散等相关议题而不断努力。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深化区域自由贸易区体系,在亚洲地区深化跨国财政经济合作,在欧洲、非洲和南美洲等地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这充分说明了我国日益加深与国际社会联系,要求新时代的财税改革思路要放眼全世界。要使财税改革为我国深化对外开放战略而服务,为“引进来和走出去”而服务,为我国承担国际责任、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服务,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服务。
叶子荣(2017)认为,财政的“国家治理论”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本质的科学诠释,财政“国家治理论”是对财政本质的深刻认识以及精准打造财政功能的理论准备。而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属性则脱胎于社会共同需要论的逻辑范式,财政的“国家治理论”也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现代诠释。
五、小结与启示
本文通过阐述中国逻辑和思维方式,进一步讨论了社会共同需要在历史变迁中的缘起和社会共同需要的现代诠释,通过古代和当代两个层面的说明,试图回答为什么基于社会共同需要的财政学是可能的。本文认为,中国的“团结主义”“家长制”观念和“士大夫”精神是理解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基本逻辑,同时是构建中国社会共同需要的重要因素,而财政的“国家治理论”则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现代诠释。本文得出的启示如下: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个人主义方法论无疑是极为重要的。通过个人主义建构集体行动再推导政府决策的数理模型能够很好地增强财政基础理论分析的逻辑关系,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无疑是行不通的。中国没有西方式选举制度的土壤,直接通过假象的选举个体和选举制度来讨论中国的财政问题是脱离现实的。无论是数理模型建构还是实证分析,都需要重视中国内在的“团结主义”,所谓“选民”并非是独立决策的个体,而是受到其他个体影响和集体无意识影响的、隶属于某个“集体”中的一份子。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重视工作职业的划分,而非地域选区式的划分,这一点使得中国的人民代表往往从职业倾向出发来关注社会问题。与公共选择理论假定“被选举人为了胜选而代表选民偏好”不同,中国的人民代表往往是某个群体中的“典型”,是群体偏好进行“最大公约”后的结果,所以照搬西方个人理论主义来分析财政政策决策过程是不妥当的。
财政的社会性是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的关键。近年来已经有如马珺(2012)、李俊生(2017)等学者注意到国家财政的社会属性,并通过大陆财政学派来进行规范性的理论解释。从各个国家的政府行政实践上看,政府是否施行“良政”才是民众是否支持政府的关键。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的基本矛盾已经转变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这需要财政更好发挥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同时也要求国家财政具备深刻的社会性,通过与市场的良好互动、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以及对改革红利的全体性分配,不断实现社会共同需要。
社会共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强有力的政府需要强有力的财政。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中提出,国家能力是解决贫困的关键,而国家能力的提高亦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而新时代面临的贫困等方面的挑战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更需要强有力的财政。作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美国在国际秩序中角色的模糊和欧洲角色的衰落,出于国际社会的共同需要,我们亦需要有力的财政政策与财政工具,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