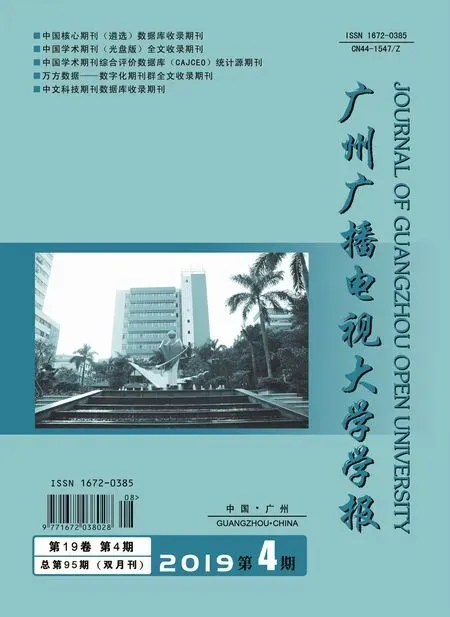通变与时中:《文心雕龙》“情采”篇的文质观*
王玉琢
(陕西理工大学,陕西 汉中 723000)
文质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与中国古代“内圣外王”“重本轻末”的思想密切相关。《文心雕龙》作者从文学本体论的高度建立了文质结合新范畴的核心理论体系。“情采”篇作为文学创作论“雕琢性情”之章,在论及文质观点的重要篇章部分,其独特的创作思想和写作理念,“为情而造文”“要约而写真”[1]的创作主张,突破了原有的“为文而造情”“情文不符”“淫丽而烦滥”的文风,指明了文学发展新的方向。
文质概念是一个有着民族特色的经典古代文论命题,追根溯源,最初只是一种从意识中升华出来的一对审美范畴,是指对于一切事物包括人所必具有的内容与形式最朴素,又是相当恰切的表述。春秋之前,关于文质也存在着“文益于质”的相关说法。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文质并未成为文学上的一组相对应的概念,只是获得了其美学意义,见端于《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质地胜过文采就显得鄙略、粗俗如野人,文采胜过质地则有如浮夸的史官。文采和质地配合适当,这才是个君子。这种观点最初指的是作为一个理想当中君子应该有的高尚的人格操守,具备杰出的道德标准。何晏《集解》也略有提及:“包咸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质少。彬彬,文质相半之貌。”
一
魏晋之前,文质作为一种审美观念,就已经出现在人们思想文化和社会教化诸多领域,成为其热议的问题之一。如《易经》当中的“贲”卦包含了文与质的关系,《诗经》中《国风·卫风·硕人》篇“巧言倩兮,美目盼兮”引发了一场关乎文质的思辨讨论。文质运用领域之广,涉及范围之大,使之不仅出现一定运用意义上的混乱,还表现人们对文质二者关系思论。如《论语·八佾》中子夏问诗于孔子,谈及到“会饰后素”,再如《论语·颜渊》中“文犹质也,质犹文也”的平等思想。此后儒家另一人物在《墨子》提及“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其大概意思是人生在世,衣食住行必须得到满足,一定程度上解决人的基本生理需求,才能涉及外在“美”“丽”“乐”等其它方面的需要,带有实用理性主义的价值观。谈及人们现实生活生存的客观需要,同其他观点“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一脉相承。强调人的合理欲求是其自然本性正常抒发,而这里的质与文更多指涉内外之意,即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从事其他活动,沿袭了儒家的文质理念。韩非子在这一观点上与儒家学派微显不同,在《韩非子·解老》中,他提到“文,为质饰者也”的观点,反对儒家重视的过分复杂的礼制观念,认为“夫物之待饰,其质不美也。”强调自然之文质远胜刻意的矫揉造作人为之物,并把文质放到了对立的关系,这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二元论的观点,将文质进行强硬机械化分割,有失偏颇。但这一观点使得人们进一步将文质等同视之,有一定现实的积极意义。扬雄进而在《法言》中谈及文与质的关系着眼于辨别真伪,从质出发,这里的质有着质朴、朴素之意。并用虎、豹、狸等例子形象而深刻地说明质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文的道理。而同一时期的其他文论家如董仲舒将“质”与“诗言志”中的“志”联系起来,言诗则说:“诗道志,故长于质”。而对待文质的关系则说:“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文质两备,然后其礼成。先质后文,右志而左物”。把质看作是最必要的东西,而文只是附加在其上的装饰物。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六朝文人对此很自觉,语言形式之美是他们“造文”最主要的审美追求。魏晋时曹丕《典论·论文》中谈及到“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也肯定了文采之美。然而这样的崇尚文采的文风沿袭到齐梁文坛,演变成了一种“文胜质衰”和“繁采寡情”现象,使得儒家诗人刘勰深感文学危机,发出“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的呼声,并希望通过著书立说来改变这一现状。实际上,文质观在《文心雕龙》中其它篇章,如风骨、通变等皆有涉及。但情采篇中文质观更加具体贴切,论述更为完善。刘勰提出以情为经、辞为纬,并提出“文不灭质,博不溺心”的主张,并强调“文附质也”和“质待文也”,“文质附乎性情”中的“文”是文采,“质”是质朴之意。“文”兼有形式和文采之意,质有内容或质朴之意。情采篇作为文质关系的专论,不仅与其他篇章有一脉相承的文质意识,还把文质观切实放到文学本体论的角度来探讨,主张文章应该表达真情实感,反对文采过多淹没情性,强调文学创作作品的艺术风格与整体风貌内外的统一。真正把 “质”提升为一种审美的标志和尺度,表达了作者一定的文学审美要求。这种文质观在刘勰的情采篇中不仅继承并发展了儒家中庸思想,还体现出自然哲理性与传统价值观的统一,对文质概念进行了文学性的根本改造。
二
中国古代文论重体察,善于通过现象举例论证,类比推演得出结论。将自然视为关照对象,传递其哲理意味,从而打破了之前文论家如扬雄、刘向等人的社会价值观下单一文质论,具体表现为更注重自然属性,同时又并不游离于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念,顺时而动,达到了一种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王元化认为“孔子的文质关系是从仁礼关系中推演而来”[3],“仁礼”是孔子“成德之教”的最高范畴。荀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情文俱尽”的文艺标准,第一次涉及了文学的情感因素。此后儒家仁礼关系下的文质因为其特殊历史时期,发生了一定意义上功能性的转移,如《春秋繁露》出现有关政治书写原则方面的文质,王充《论衡》中书写内外之意的文质等。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儒家“把礼法简易、随顺自然称为质,把礼法繁多,注重文化学术称为文”[4]还把文质这一观点用其来代指政治和社会生活,提及 “质文代变”的社会观点,进一步丰富了文质的外延,但与原本文学发展的轨道出现了轻度偏离。
刘勰充分吸收了前人的观点,把文质论再次纳入到文学创作领域中,在文质的基本性质和形式上给予基本的界定。用“情采”来规定文质,“文采所以性情,而辨丽本于情性”,把情视为内在肤质,把采视为外在饰文。认为文章要“为情而造文”“要约而写真”。反对“弄文而失质”,以至于失去了文质语言风格质朴这一体制上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形式上强调了“文”与“质”的必然联系,“文”是“质”的自身本质属性的必然体现,“质”和“文”必须表里相符,融合统一。
刘勰总结了先秦以来文质论中的精辟主张,将零星的观点系统化,情采篇中关于文质的观点不仅有内容和形式之意,第一次也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文质理论,在融汇儒家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在前人观点基础上,刘勰对其文质的本质关系进行进一步哲理化阐释和深度解读。大体上看,刘勰对文风的要求还是文质彬彬、文质并重,但由于时代的不同,他更反对奢靡文风和缺少风骨的文学作品,在《文心雕龙札记》中,黄侃提出刘勰意在反奢而少论质。[5]此外,文心雕龙其他篇章也讲文质的关系,如风骨中以“气质”为体,以骏爽的意气和质素的语言构成了作品的总体风格。而在情采中,“质”与“文”的论述则更丰富和具体,如一方面在文中“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 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以物论及作品内容与形式之意,一方面在“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也。”也暗指语言的华丽与质朴之意。同时将天地人三者归于一体,将外在所见所闻所感归于一心,这种“感物而动”“缘心而发”的人生观影响了情采篇的艺术主张。列举的水、木、虎、豹等自然之物说明“文附质”的重要性,如反对当时“为文造情”的恶习来讲述桃李之实的可贵,颇有《诗经》中比兴意味。
三
情采篇中的文质观不但体现了自然哲理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统一,还继承与发展了儒家思想,对文质的观念进行了文学性的改造和形式上的变更,在文质的传播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后世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刘勰实质上倡导的是文质并重,作为一位有经典意识和现实情怀的文论家,魏晋人的习性和风骨早以融入他的文心和骨髓,而南朝绮靡采丽的文风又不可避免沾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过于推崇文或质的某一方面,而将“文“和“质”放到同一时代的背景下进行填充和分类。他既十分重视对“圣贤书辞”的认真沿袭,又对魏晋以来的文风保留最大限度的吸收。建安时期,应玚和阮瑀分别就文质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文质缺一不可,写作《文质论》。应玚承袭建安文风,列举汉代历史实例,强调重文轻质的文质观。而阮瑀循庄子之道,以器物为喻,认为质胜于文。刘勰在才略篇谈及二者“琳瑀以符擅声”“应玚学优以得文”肯定其创作才华,也是对其不同侧重点文质观以形而上思考之例证。
此外,刘勰主张重“采”,但后又提出“贵乎返本”,回到追求质的真性情上来。这种对文学创作保持初心、追求本真的态度和价值观,与《文心雕龙》的养气篇“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强调成文之标准在于自然,而非牵强附会,矫揉造作之物。这样的文学创作方可“高下在心,进退可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人们对于文质的探讨,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刘勰将道家的“自然”的“本来如此”、“自己如此”等思想引入传统的“文质”论中。一方面从“文”之生成与存在的本体论高度论证了“文”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了“文”与“质”本质上的必然联系,认为“文”是“质”自身本性的必然表现,“文”与“质”必然表里相符、融合统一。“文”的存在既是合理的,又是“质”的必然表现。这极大地丰富了文质的内核,更新了前人的思想。情采篇于刘勰的创作论中的地位,不能以偏概全称为文质之论,但的确是以“衔华佩实”“文质相称”的基本观点为主线,以“为情造文”“剖清析采”为创作主张的优秀篇章。情采中强调的《周易》“贲象穷白”“贵乎反本”也都是为了说明后文的“文不灭质,博不溺心”的重要性。不得不说,刘勰“为情造文”的文质观打破了当时“淫丽烦滥”的魏晋文风,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文学理论成就,为后代研究这一理论观点的人指明了新方向。《梁书》和《南史》中记载:“沈约大重之,为其深得文理。”唐代陆龟蒙说:“刘生吐英辩,上下穷高卑。下臻宋与齐,岂但标八索,殆将包两仪。人谣洞野老,骚怨明湘累。立本以致诘,驱宏来抵隵。清如朔雪严,缓若春烟羸。或欲开户牖,或将饰缨緌。虽非倚天剑,亦是囊中锥。”到了明代,张之象称它为“扬榷古今,品藻得失,持独断以定群嚣,证往哲以觉来彦,盖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也”,而清人纪昀评价刘勰说,“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彥和吃紧为人处。”
刘勰“为情造文”的主张在海德格尔那里成了“物因素”,由“情志”转化成“事类”,再从“事类”谈及到“文辞”,正好对应的是情采篇“文质相称”。如海德格尔在谈及物因素的生成时强调:物是感性之物,即感性中通过感觉可以感知的东西。并指出物本身的多样性就是该物的决定性特征,这一看法在探讨立文本源和艺术先后顺序正与情采篇 “情理定”“后辞采”之原则角度一致。如在谈及诗歌领域的文与质,是以“明道”为中心的强化与深化,唐代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后又说“本之《书》以求其质”。而诗之质,强调的是“意”,言为心声,本乎纯白。《江雪》之诗便颇有返璞归真之质。从容之心以情入文,成文质相衬之作,此乃上品。再如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有“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6]强调立意在先,成文在后。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刘勰的这种“贲象穷白”“贵乎反本”的本色基调文质论也在小说领域得到运用,如曹雪芹《红楼梦》中的偶遇仙人的补天石,下凡摇身一变成了人人赞叹的通灵宝玉,后又化为青埂峰下的大石头。其本质属性是意念的石头,已经脱离了单调草木而上升为带有情感隐喻之物,才能造就“衔华佩实”之遇,生成“为情造文”之作。这正是刘勰情采篇中“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的文质观用意。从具体的历史时代情景中研究到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寻根溯源,雕琢其章,才能成为“圣人书辞,总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