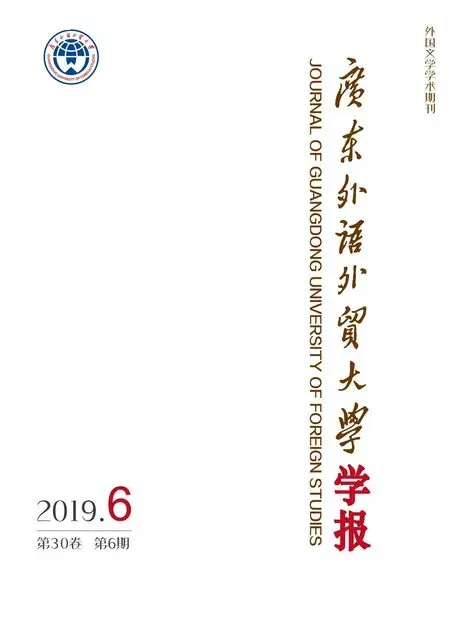基于身体观就医学对晚清、五四文学影响的考察
刘金举 龙开胜
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医卜相,皆方技”,医生并未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尊重。但晚清以降,医学却一步步被提升至与民族存亡、国家盛衰密切相关的“国家事业”这一崇高地位,民国时期,围绕中医存废问题曾多次发生席卷医学界、进而波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大规模论争。医学之争渐次影响到文学领域,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肇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
就该问题,许多学者曾从当时“唯科学”的社会氛围等角度进行过探讨,但对民族存亡危机之际国人的本能举措、该时期医学的被符号化,以及中国传统身体观的影响等问题认识似乎不足,因而影响了对该问题的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而且该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也是日本、韩国等东亚各国的共通现象,就此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东亚各国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政治进程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基于身体视角对医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审视
“拟人说”认为:“人类首先是将世界和社会构想为一个巨大的身体。以此出发,他们从身体的结构组成推衍出了世界、社会”(奥尼尔,1999:17);同时由于社会关系被投射到人的身体结构层面,因此在“作为知识对象或者话语对象”以及“在具体实践和行为中被文化构成的”意义上,个体的身体“是由社会构成的”(康纳顿,2000:127)。尤其在中国,盘古死后身体化成世界的传说形成中国身体观的基础;原始思维的道教认为人身一小天地、天地一大人身,并将身体扩展到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影响更为深远;现代身体理论更是将人的身体分为世界、社会、政治、消费和医学这五种身体。
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语言方面。“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维柯,1989:200),但“拟人说”更重要的作用则体现在比拟社会和政治方面。在西方,自奥古斯丁起就认为国民是按照共同的法律和利益所构成的“身体”。而在信奉“身国同构”(《黄帝内经》)的中国,“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国语·晋语八》),“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高保衡,等,1996:序)思想深入人心。特别是在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一医学价值观、人生观的影响下,知识分子谈医论政蔚然成风。
由于影响深远,身体观成为人类观照万物与自身的基本思维方式,疾病隐喻也自然成为人们理解社会文化生活的基本意象,在西方有后文要介绍的“病夫(sick man)”说,在中国有“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聂夷中《咏田家》)等诗句,“病入膏肓”等成语、俗语更是深入我们的生活。
近代医学成立以来,医学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一方面医学“比其他科学更接近支撑着所有这些科学的人体学框架。由此也导致了它在各种具体生存形式中的威望”(福柯,2001:221);另一方面,由于近代国家需要“确定医学的政治地位,建构国家层次的医学意识”,因而“医生的首要任务具有政治性”(福柯,2001:28,37)。还需引起重视的是,结核杆菌等病原体的发现以及科赫法则的确立,撼动了希波克拉底以来的传统医学,导致“十九世纪的医学更注重正常,而不是健康”。由于“人类科学是作为生命科学的延伸而出现”的,因此“当人们谈论群体或社会的生活、种族的生活、甚至心理生活时,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有机存在物的内部结构,而是医学上的正常与病态两级”(福柯,2001:39-40)。医学因此而上升为指代健康人类与社会的代名词,成为政府重要的政治控制手段,“通过身体的医学化,我们被社会化了”(奥尼尔,1999:123)。其结果是,“在家庭、国家、宗教和党派曾经存在过的地方,取而代之的将是医院和剧院——它们是下一阶段文化中的标准机构”(Rieff,1966:24-25)。因此,面临亡国危机、引进西方政治制度之际,正如“建立西医权威的关键在于出现一个追求现代性的中国国家”(雷祥麟,2003)所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首先引进其医学制度和知识并不奇怪,西医在社会上的权威地位与国家意志密不可分。
二、从身体理论看“东亚病夫”的政治术语性质
“作为一种智慧和评论的源泉”,人类身体“导致了那些大大小小的拟人论秩序的形成——正是这些秩序支撑着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结构体系”,因此“对于人的身体的不可避免的兴趣将有助于我们解决人、自然以及社会机构之间那种复杂关系之中所存在的重大问题”(奥尼尔,1999:2)。在社会发展陷入困境或者面临重大问题时,一个重要的解决途径就是基于身体理论思考政治问题,找到一种象征性语言,营造出作为人们政治生命基本结构的“政治身体”,从而为战胜结构性的社会危机奠定基础。
当时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逐步加深,面临亡国绝种的空前危机。尤其是目睹近邻日本正是由于“明治以降,受到军队和医疗制度等‘新’社会制度的逼压,身体自身被重新制度化”(養老孟司,1997:47-48)而迅速奠定近代国家的基础,通过“脱亚入欧”成为世界强国后,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效法欧美和日本发起启蒙运动。当时最能激发民众、掀起救亡图存高潮的象征性政治语言就是“东亚病夫”。
据考证,十九世纪中期,“病夫”成为西方世界用来形容长期衰败却又无力进行变革的落后国家的政治术语。在中国,学界通常认为,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梁启超翻译刊载于《时务报》的《中国实情》用“病夫”形容中国,批判晚清,呼吁改革的政论中所出现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一语,使西方概念的“病夫”成为中国新闻界鞭挞麻木不仁的国人的警语(杨瑞松,2005)。维新派最初认为中国之病因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革,目的在于推动变法。但经历了“百日维新”后,痛感政治上无力回天的知识分子只能将注意力转向国民,即将个体的身体与国家的命运密切关联起来。在该过程中,严复所引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国家富强之本在于人之素质——强国必先强种这一观念深入人心。自此,中国舆论界尤其是维新派将该政治术语视为救亡图存的利器,如“今之中国……固病夫也”(严复,1962:369)、“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梁启超,1902:6),强大的舆论为戊戌变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但实际上,这里还存在着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哲学与身体观。正如道家的“修炼”、儒家的“静坐”、佛家的“坐禅”所要求的那样,东方哲学是通过“身心一如”来获得真知的。如道教认为身体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其“五脏藏五神”理论认为,作为生理器官的五脏,不仅具有代谢、呼吸等生理功能,还具有魂、魄、神、意等精神性功能,人的生理活动与精神活动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且人的身体存在、感官活动比理论反思更具原初性;身体是其他价值得以实现的起点和场所,强调通过存思身中神而与自然界中相应的诸神沟通,运用大宇宙诸神之力来提升、转化人体,直至在虚无中实现形神、性命、身心混沌不分的状态。
正是有了上述思想基础,在民族危难之际,梁启超等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梁启超,1897-8-11)等主张。一九○三年,他又痛批“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梁启超,1992:163),将原本用来形容衰败国家的“病夫”这一西方政治术语与百姓的身体素质联系在一起。这种新思维和政治操作契合了当时知识分子科学救国、医学维新的思想意识,人为扭曲了西方“中国病夫论”的内涵,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康梁一辈开始,知识分子就以一种舍我其谁的态度,努力于推动各种的身体改造运动,营造一个有关身体‘应然’的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而主政者也为了自身的政权的维系的考量,陆续以新政之名进行这项事业的开展”(黄金麟,2000:23-24)。族力等同于国力,政治改革需要从人的改造做起的新见解便水到渠成,“医学救国论”迅速普及。
三、被符号化的医学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医生和中医并未获得应有的地位。但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兰医”渐渐取代“汉方医”,一八七五年又通过“医师学术考试规则”,在确立西医的合法和主导地位的同时,从法律上将“汉方医”视为民间疗法甚至迷信,并最终予以禁绝。
在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的是:首先,正如“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之大,少闻东洋二三国之事,以中国为冠”,“从中国之书,以其国为中土”(杉田玄白,1976:229、230)所示,日本上述举措是通过攻击“汉方医”的思想内核——儒学而展开的;其次,“在明治的法律制度中,医学制度看似其中的一部分,但在江户时代,被许可的西洋的‘知’只有兰医,还有导致明治维新具备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均来自兰学者……明治时期西洋医学派获得权力,非惟局部,且最具象征意义。相较于其他任何领域,近代医学是‘知’的权利化身”。可以说“从未有任何事物如医学般被如此截然区分为‘知’与‘非知’的代表”(柄谷行人,2004:152)。换言之,“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熊月之,1994:710),即中医和西医分别被视为中华和西方文明的象征而被符号化是一个重要原因(劉金挙,2013)。
在中国,清末民初医学制度的建立和变革深受日本影响。启蒙知识分子借鉴西欧和日本来攻击中医,引进西方医学,并将近代医学推升到最高地位,如梁启超宣扬“凡世界文明之极轨,唯有医学,无有它学”(梁启超,1897-8-11)。针对光绪帝另立医学堂、考究中西医理的变法举措,梁启超大赞:“实为维新之一政也”(中国史学会,1961:80)。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如黄子方在《中国卫生刍议》中所述,认识到“要求国家的生存,要谋民族的自救,非但只在军备上求自卫,还要谋文化上所必需的各种文物建设,科学新医便是这种科学文物的建设之中之最重要者”(杨念群,2006:96)。年轻人纷纷出洋学医,仅以日本为例,一九一一年以前,有名可考的留日医学生就达一百六十三人之多(牛亚华,2003)。五四之后,医学更是被置于东西文化大撞击、大交流的背景下,西医与中医分别被视为“科与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二元对立的象征,西医话语成为五四科学话语的重要部分。进入民国时期,围绕中医存废问题曾多次发生席卷中西医界,进而波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大规模论争。
这种对立和斗争也体现在文艺作品中。如五四作品不厌其烦地描写中西医肺病治疗方案之争。而在现实中,围绕孙中山临终治疗的中西医之争最具代表性。五四知识分子笔下的患者,往往都是在中医救治无望之后再请来西医,而此时则往往由于耽搁已久而早已治愈无望了,如巴金《春》中的海臣和《寒夜》中的汪文宣等的病死。中西医之争,其实质是两种文化、两种哲学观的交锋,其扦格与汇通是两种体制、两种文明纷争与对话的一个侧面,中医治疗方案所导致的死亡寓意着中医的彻底败北。
四、从医治病体到“文学救国”
进入近代以来,医学与文学的关系之所以看似更加紧密,以下原因不可或缺:
(一)小说上升为国家的表象
传统上认为,晚清启蒙知识分子之所以将小说从“小道”迅速提升为“文学之最上乘”,原因就在于:对小说来说,有关乎世道人心的古训和“文以载道”传统思想的影响;同时还因为小说既“能与政体民志息息相通”,又能“开学智,祛弊俗”(邱祎萲,1989:31),故“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榑桑崛起,推波助澜”(商务印书馆主人,1989:51)。但实际上这里忽视了近代小说产生的前提:
(社会上)产生了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以小说为中心的近代“文学”的习惯,借助小说语言的表象,作为思想性概念的近代国民国家得以诞生。同时,国家方面发现:借助文学,近代国民国家作为一个统和体而得以表象,而创作文学的一方也自发地适应该发现所内含的期待(或者命令),由此而产生了这种正可谓“相辅性”的关系(小森陽一,等,1999:28)。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指出,小说是国家想象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方式,即近代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建设国民国家这一需求的结果,这在面临亡国压力的东亚各国尤为明显。正如上文所介绍,现代身体理论认为人体由世界、社会、政治、消费和医学五个层面的身体所构成,这种“相辅性”关系的产生,正是对该理论的最佳例证:近代社会成功塑造了作家的“政治身体”,并进而深刻影响到其日常与创作生活。
在日本,西园寺公望于府邸邀请小说家举办“西园寺总理与国内一流文士的聚会”(1907.6.17-19),平凡社发行“现代大众文学全集”(1913)时,时任总理大臣的若槻礼次郎致推荐词“此乃日本精神所产生的世相与人情美之大殿堂”,将小说与日本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从国家层面对国民语言和文化生活加强了支配,众多作家“应运”创作,最典型的就是其后的“转向文学”“国策文学”等。在中国,基于这种“相辅性”,一八九七年严复创刊《国闻报》,立志印行新小说;梁启超将坪内逍遥所采用的“小说”这一名词转介回中国,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1989:37),发起“小说界”革命,小说被视为政治启蒙、道德教化乃至学校教育的最佳工具,改革社会的热情迅速转变为创造新小说的动力。一九一八年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副题便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掀起建设国语、国语文学的高潮,其目的也在于此。
(二)政治与文学相互关联的“医学性质”思想的影响
“相对于国家而言,自立的‘内面’‘主体’,正是在各项国家制度下才形成的。这个社会已经患病,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治疗这一‘政治’思想也由此而产生。自古以来,‘政治与文学’非但不是相对立的普遍性的问题,更是相互关联的‘医学性质’的思想”(柄谷行人,2004:154),“身体是一个整体社会的隐喻,因此,身体中的疾病也仅仅是社会失范的一个特征象征”(特纳,2003:16)。换言之,“医学身体”开始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
清末民初作家中很多人“医文同飞”,“小说界革命”实际上是改良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折光,梁启超等人对小说作用的过分强调和夸大,其实质是改良主义者为实现救国醒民这一迫切愿望而采取的文化策略。《新中国未来记》(1902)中“黄克强”“李去病”试图用西洋的科学政体去救中国社会之病;《老残游记》(1903)的主人公——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铁英),通过所见所闻揭露清政府的腐朽黑暗、官吏的残暴昏庸、百姓的贫困交迫,目的就在于“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处下手,摇串铃先醒其睡”;随着“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1904)的畅销,作者的笔名“东亚病夫”作为政治词语进入公众舆论圈,疾病隐喻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
启蒙思想家文学救国的思想,极大影响了五四作家,并一脉相承至现代作家,尤其是许多五四作家通过留学亲身感受到国民国家这一政体和国民意识之间的密切关系,“自发地适应该发现所内含的期待(或者命令)”而进行创作。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号召就是知识分子对该“相辅性”深刻认识的结果;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弃医从文,就是对“该发现所内含的期待(或者命令)”的最佳呼应。如鲁迅的人生之路有两次重大转换:一是决意学医。其最初动机就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鲁迅,1981a:304),“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希望借此“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二是弃医从文,完成了从救治肉体到救治国民灵魂的转变。其直接原因便是偶然的“幻灯片”事件:“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鲁迅,1981b:417)。他们的弃医从文实际上是从“救人”到“救国”的转变,体现了当时社会背景下文艺救国、文艺救人的倾向,是功利化的社会民族宏愿的显现。因此,虽然对象发生了改变,但他们拯救和振奋国民精神这一目标并未改变。
总体而言,“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五四’时代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家的社会角色等等的界定,自然很方便地从医学界获得生动形象的借喻”(黄子平,2001:156),从而形成知识分子程度不等地以“医生”的眼光审视人生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他们多以西方的“科学”“文明”为工具,以治病救人的医生自诩,借助治病看病故事情节,积极主动地担当起为社会诊断病象、探究病源、疗治病患的职责,宣传医国救国的思想。五四新文学实践中,有关社会人生病症的揭示屡见不鲜,例如鲁迅小说材料“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1981c:512)。在情节模式上倾向于讲述生病、治病、死亡或生还的故事,如《狂人日记》《明天》等,在该意义上《药》的隐喻意义尤为典型。小说中,革命者夏瑜寻求的是救治病入膏肓的中国的“药”,而华老栓寻找的是为患肺结核的儿子华小栓(患病的中国或者中国国民)救命的“药”(人血馒头),其结果却是启蒙者的鲜血被愚昧的启蒙对象当作救命灵药而吃掉,二者双亡。在这里,鲁迅不可避免地受到父亲为庸医所误这一痛苦经历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鲁迅借“华”“夏”两家的悲剧寓意华夏民族的悲剧,揭示了革命的启蒙与大众的愚昧之间的尖锐对立,希望人们积极探索社会革命的成功之路。这种文学现象不仅深深影响了一代中国人,而且深深影响了当代文学。今天,疾病叙事文学仍是中国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可以说,从晚清试图通过改良文学从而实现改造身体和“新民”,发展到五四时期通过文学革命灌注灵魂从而完成对“国民劣根性”的改造,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强国的一种必然的政治选择。孙中山先生从“医人”发展到“医国”的转变也极大佐证了该观点。
五、结语
由于达尔文社会进化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身体观的影响,晚清以降,面对内忧外患和亡国危机,广大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基于身体理论观照中国社会和政治,探索启蒙和救亡之路。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西方的“病夫”说,促醒国人进行民族主义式的社会变革。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启蒙知识分子将个体的身体打上国家危机的印记,并逐渐将之组织进民族国家的话语,使之成为建构民族国家的工具,治病这一个体行为转化为群体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开启了疾病治疗叙事模式,文学成为强有力的启蒙工具;借助留学经验感受到文学与国民国家表象之间“相辅性”关系的五四作家,自发适应建设国民国家的社会需求,或弃医从文,或借助医学所提供的想象资源,对现实和国家进行以医生为意象的转喻性描写和叙事,并赋予其社会性的讽喻与象征性的美学功能,实现了从“救治肉体”到“救治精神”的转变。中西医与晚清以及近现代文学的复杂关系,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