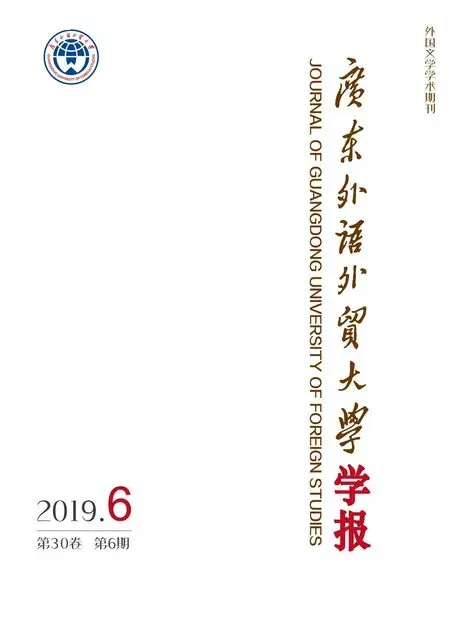高一志《童幼教育》中的友谊观
寒 梅 著 陈彦辉 杨雪樱 译
一、前言
一五八三年,随着罗明坚神父在广东肇庆居住,耶稣会在华传教史正式开始。它迎来了新时代下中西关系的曙光,并为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具有长期影响的西学东渐的革命进程铺平了道路。欧洲科学创新和哲学理念的逐渐传播,不仅从科学的角度推动了现代性,也为中国人提供了新的全球意识和时空观念(黄兴涛,2013)。耶稣会传教士用来进行这场革命的手段就是书面文字。利玛窦(Matteo Ricci)应该是所谓“巨人时代”①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曾说,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是通过书籍而非语言来完成的。在这一直觉的指引下,利玛窦脱去了僧侣的袈裟并逐渐接近儒家文人精英。一六一○年利玛窦逝世后,西学的引入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一新阶段对从欧洲运送过来的科学、哲学和神学文本的翻译,其目的是鼓励建立地方图书馆。作为晚明耶稣会中最多产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1566-1640)在翻译或者说“译写”,“旨在满足中国人(读者)天生的好奇心”的伦理与宗教主题相关书籍方面,以及在山西当地开辟新教区以便更好传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这些伦理著作中,最早的以及最具代表性的教育学论著当属高一志的《童幼教育》。该书于一六三二年在山西绛州出版,但它极有可能是在高一志流亡澳门期间写成的。这本书介绍了欧洲古典和文艺复兴教育传统的核心原则,并巧妙地将它们与宋明教育中最相关的教义相结合。高一志选择撰写与儿童教育相关的作品很有可能是因为以下几点:
1.这个主题还没被他的任何一个同工所涉及,因此《童幼教育》也被认为是“中西方在教育学领域中交流的最早证明”(黄兴涛,2013);
2.高一志正在寻找一个中欧之间的共同话题,使二者的文化能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利玛窦在一五九五年创作《交友论》时,很有可能也受到同一目标的启发(Hosne,2014)。有学者指出,高一志曾计划开办一所学校(Meynard,2014);
3.凭借在意大利耶稣会学院对古典哲学(如西塞罗、塞涅卡、亚里士多德等)和当代哲学(伊拉斯谟、马菲乌斯·维吉乌斯等)的学习,高一志在这个话题上有着广博的认识。在澳门,他还接触到两本非常重要的、被学界认为是《童幼教育》资料来源的两本教育学著作:玻尼法爵的《基督教育》(ChristianiPueriInstitutio,澳门,1588)和托雷斯(Juan de Torres)的 《王子伦理哲学》 (PhilosophiaMoraldePrincipes,布尔戈斯,1596)(Meynard,2014)。
本文旨在阐明高一志在《童幼教育》中论述友谊观的方式,并从文本的维度出发,对该书第二卷第九章《交友》中关于友谊的观点给予特别重视。同时,通过对这一章主要文献来源的交叉核对,本文将确定高一志从中欧古典传统中借鉴的关键概念以及他向中国读者传教的方式。
二、明朝关于友谊的观念
在欧洲哲学中,友谊一直是一个被深入讨论的话题。一些古典作家如西塞罗、塞涅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也参与到这一长期的论争中。同时,这些作家都是耶稣会传统课程学习中的组成部分,他们的言论被广为引用和传播。
然而,中国古典思想对这一话题也有着自己的见解。儒家认为,为了维护社会和谐,人人都需要遵从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等五种人伦关系。其中,朋友之间的关系是孔子“五伦”关系中唯一可以自由选择并且不受等级制度制约的关系(Hosne,2014),这使友谊成为一种独特而又具有潜在危险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友谊的含义历经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也是近期某些研究的主题(Huang,2007:2-34)。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友”这个词在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被用于指代“一个人的男性亲属”(Huang,2007:4),而“友”这种关系后来发展成为伦理道德观念中的友悌之道。在中国古代,友悌之道是规范了几乎所有基本男性关系的根本性原则。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70 - 476年),核心家庭成为基本的社会单位,“友”这个词便失去了它作为“内群体”的词义,并开始指称彼此之间没有亲情关系但有“共同爱好和志向的男性(同志曰友)”(Huang,2007:4)。尽管“友”这个词有着不一样的解释,但它始终被认为是男性的特权,并与男性的社交密切相关。
在这一方面,即使学者们对此给出了不同的诠释,但传统上仍把中国明代看作是男性友谊的“黄金时代”(Huang,2007:9-34)。在社会等级制度下,人们不因阶级差异而受到歧视,使得即便是不同社会背景的个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都受到了鼓舞,而良好的朋友圈则成为每个受过教育男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儒学的复兴使人们重新燃起对友谊在道德与政治层面上意义的兴趣,这些话题都因使用文雅而富有创新性的辞藻而闻名(Hosne,2014)。
利玛窦是耶稣会会士,与高一志在相似的环境中成长。他很快就发现了中国文人之间的这种同窗手足般的情谊;他很快意识到,朋友是中国人取得很多成就的关键:例如(朋友所能提供的)庇护、刊物出版、信仰转变等(Hosne,2014)。
三、从孔子到利玛窦: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友谊观
一五九五年,利玛窦将自己第一部以友谊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交友论》作为礼物赠予南昌建安王朱多节。利玛窦认为,这本书只是一个“纯粹的翻译练习”。但实际上,《交友论》是一部借鉴了欧洲历史中最杰出思想家的格言创作的格言集(Hosne,2014),很可能改编自雷森德的《记言与比喻故事》(Sententiaeetexempla,巴黎,1569年)。出于“文化适应”策略的考虑,利玛窦借用儒家和新儒家哲学中的相关术语,即“耶稣会巧妙地将欧洲传统与中国/儒家传统所共有的友谊观点和观念进行了匹配”(Hosne,2014),从而使非基督徒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他的观点。
尽管在《交友论》之后三十余年才出版,高一志的《童幼教育》依然属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著作(义礼之学之书),并对西方人文思想传入晚明作出了贡献。就像《童幼教育》中其他许多篇章一样,《交友》篇对托雷斯的《王子伦理哲学》多有引用之处,但它并不是对后者的直译。它涵盖了一些政治话题,不能完全服务于高一志的教育目的。
然而在表达友谊观时,高一志又不得不重视第一部由耶稣会会士用中文撰写的关于本话题的著作——利玛窦的《交友论》。在高一志《交友》篇的开始,利玛窦对高一志文学创作的影响就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来。在这一章里,作者首次把友谊的观点介绍为“上帝的旨意”:
宇内无人自足以生自足以事则亦无人不须友以成也。故天主归斯民于同宇,命其结亲交友,彼此相助焉。(高一志,1996:405)
让我们来看看利玛窦用来表达相同观点的话:
各人不能全尽各事,故上帝命之交友,以彼此胥助,若使除其道于世者,人类必散坏也。(Ricci,2009:16)
根据侯安娜(Hosne,2014)的说法,这句话是利玛窦第一次尝试引入“基督教的博爱,被认为是人对上帝的爱,然后转变为对其他人的爱”的概念。利玛窦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这种隐晦的方式,有可能是一个有意识的疏忽(中国读者还没做好接受这个观点的准备)。又或许如侯安娜所言,利玛窦试图找出最恰当的符合基督教教义的汉译形式和适应性措施,因此“在论著中,利玛窦把基督教的友谊当成是博爱。我们不应期望他的这种观点是否精准,而应观察他是如何巧妙地介绍基督教的友谊”。正如上面的引文所言,高一志采取了与他前辈相同的策略,在这一章节中,他只有一次直接提到“天主”一词。这种“定性”而非“定量”地使用上帝一词的策略,在利玛窦的专著中也能看到,他只提到两次“上帝”(格言十六和五十六)(Hosne,2014)。
至于“God”一词的汉译,争论长期存在。我们不会过多地讨论它所带来的影响。这场论战使耶稣会内部产生了观点截然对立的两个派别,它的影响力在十八世纪头十年的中西礼仪之争中仍在持续。高一志就像利玛窦和艾儒略一样,习惯上主张使用“上帝”一词——这个词是从中国古典典籍借用而来的,它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一神论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六页的引文中,高一志把“God”译为“天主”,而“天主”这个词反而受到了修道会总会长龙华民(1559-1654)的支持。这表明,《交友》这一章是在嘉定会议(1627年)之后写的(或校订的),在会上,“天主”这个词成为官方译名。
在其他段落中也能找到利玛窦对高一志的《交友》篇在语言和主题上的影响。例如,根据西塞罗和普鲁塔克关于“真正友谊”的定义,高一志和利玛窦都使用了相似的翻译来表达对待朋友的正确态度:
或问圣人以益友之道,答曰:顺我于理,逆我于非。直言吾恶,简陈吾善。(高一志,1996:409)
正友不常顺友亦不常逆友。 有理者顺之, 无理者逆之。 故直言独为友之真矣。(Ricci,2009:19)
利玛窦将“真理”和“诚实”置于自己论著中的核心位置,并认为谄媚是一种罪。而高一志则强调与“善”和“德”相关的“益”的思想。“德”与“益友之道”这类观念和主张往往被欧洲古典作家忽略,如西塞罗等,但这些观点和主张在儒家传统中却占据重要地位:
或问贤师与何人友可,答曰:于益者而已。 又问其益者云何,曰:善于我者则谓之益。(高一志,1996:413)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篇》)
通过对《交友》篇的仔细分析,也能发现不少从儒家经典,特别是《论语》中借用而来的词。在汉语习得方面,传教士教育的标准程序是从基础语言开始入门,接下来是对“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的学习,然后是对古典文学的学习,最后是断代史。正是通过对明版朱熹《四书集注》的学习,他们开始研究儒家经典。这些文本在耶稣会士的语言和文化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被证明与他们的文学创作相关。耶稣会士们所推崇的儒家哲学,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理解并与儒家文人交往的主要渠道,也为他们提供了将西方哲学与宗教观念融入中国文化环境的功能性词汇。为了向非基督徒读者传递外来概念,高一志和他的许多同行一样,也从儒家的经典文本中借用了许多关键性的术语,以适应自己的交际意图。
四、欧洲经典对《交友》篇的影响
高一志精通中欧经典名言并善于将它们融合在一起,他出众的能力使《童幼教育》成为“中国古代儿童教育论著百花园中的奇葩”(肖朗,2005)。
《交友》篇提到五名学者(普鲁塔克、塞涅卡、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和波伊提乌)以及来自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传统的圣徒约伯,来自儒家和西方经典的名言和谚语。迄今为止,笔者已经确定了五条直接引自托雷斯《王子伦理哲学》中的谚语,这证明了该书对《童幼教育》的重要影响。
再比如,当谈及帮助“善人”和避开“恶人”的重要性时,高一志引用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谚语:
尔自谓与何人交,我亦谓尔将为何人。(高一志,1996:406)
有趣的是,托雷斯的《王子伦理哲学》也有类似的说法,就像“我们每天从长辈那里听到和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东西一样”:
告诉我你和谁在一起,我就会知道你的人品。(Torres,1596:269)
在另一段文字中,高一志描述了不区分社会地位的朋友在人生命中的重要性。在描述过程中,他间接引用西塞罗的一句谚语,这句谚语也曾被托雷斯引用(利玛窦也引用过类似的谚语)(利玛窦,2009):
倘除友于人中,是除日月于天,除水火于地也。(高一志,1996:405)
朋友比火和水更不可或缺。(Torres,1596:264)
一个更直接的拉丁语—汉语的翻译出现在《交友》章第四○八页:在文中,高一志把友无德和“灯无油”做了一个有趣的类比;接下来,他继续间接引用撒路斯提乌斯的一句名言,而这句名言在托雷斯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
西史曰:善者相交谓之友,恶者相交谓之盟。(高一志,1996:408)
好人聚在一起叫友谊,坏人聚在一起叫帮派。(Torres,1596:271)
最后两句话直接引用欧洲特别是基督教文学中的寓言故事,它们被用于描述真正友谊的价值——友谊胜过一切物质的价值。用贤者和圣人传记中的奇闻轶事来传达一个积极向上的信息是中世纪文学的传统,与这一传统相一致,高一志从《王子伦理哲学》中借用有关哲学家薄厄爵和圣人若伯的两段话:
薄厄爵西土大贤也。向闻其友遭患穷困,则慰唁之曰尔室丰业虽亡,信友之众仍在,不必忧也。(高一志,1996:408)
若伯圣人一朝闻广业败毁,子女压死,屋室倾颓,众仆虏亡,乃有三信友者终不离于侧,则圣经所谓金银之重,不可例于信友者,然矣。(Torres,1596:263)
五、结论
本文旨在阐明高一志在《童幼教育》第九章《交友》篇中介绍的友谊观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中欧古典传统。在塑造基督教友谊观的过程中,作者从利玛窦第一次的“文学尝试”——《交友论》中借用了一些关键的词语,并从结构上参考了托雷斯的《王子伦理哲学》,从中引用了相关的名言。
在比较高一志的《交友》和利玛窦的《交友论》时,笔者着重强调“God”(它的两个不同的翻译:“上帝”和“天主”)一词的“定性”用法,这种用法,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童幼教育》等作品的世俗成分的证明(Hosne,2014)。笔者也确定了六条高一志直接或间接从利玛窦的专著中引用的格言,这些格言有时也会使用相同的翻译选择。
综上所述,鉴于高一志的作品对儒家传统的大量参考和引用,那么“中国特色的友谊”这一说法是否恰当?尽管这种说法在目前相当流行,但将它运用到这一具体需求上还需要进一步考量。
利用“异教”的道德哲学作为基督徒的入门教育是文艺复兴时期耶稣会的教育模式。与这模式相一致,利玛窦和他的同工“试图将非基督教的儒家道德哲学作为充实基督徒的知识储备”(Standaert,2003:10)。他们特别注意选择那些可以被分享,以及可以使他们的读者了解的信息。他们忽略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巧妙地介绍”那些与中国人的心理相似程度不大的信息(比如基督教的博爱这个例子)。
使用儒家传统词汇和观点,一方面是一种战略选择,为读者提供一些熟悉的语言坐标,帮助他们找到进入新的文化世界的途径。然而,正如外国人来华旅游一样,这也是耶稣会不得不接受文化适应的必然结果。正如钟鸣旦(Standaert,2003:4)所言,“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能够引起任何回应之前,他们必须与中国人沟通和交流。并且,他们只能通过中国人的语言文字和思维模式进行交流”。因此,在塑造友谊的观点时,利玛窦和高一志都精心挑选了儒家学说中的话题。比如,他们都没有提到友谊是“五伦”关系中的其中一种(Hosne,2014)。不过,这并不足为奇,因为耶稣会会士经常因他们作为寄居异国的未婚男性的身份以及未能促进“五伦”关系的发展而受到批评和指责。另一方面,他们也对这些人伦关系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它们“特别的中国”(Hosne,2014)。高一志认可利玛窦的想法和策略,在传播基督教的友谊观时,看上去也遵循前辈的指导方针来选择主题和论题。耶稣会的使命是宣扬一种新的欧洲文化意识,从而在中国人之间传播基督信仰,因此,他们必须审慎地选择作为传播基督信仰主要方式的书面文字:
我们撰写的书籍并非新作,而是来自我们(欧洲)作品的借用,从中我们摘录那些在我们看来适合中国的材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做出明智的选择。(Bernard,1945:02)
注释:
①这种说法是由邓恩(George Dunne,1962)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它是对中国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卫匡国神父等在道德和文学上的卓越贡献的致敬,也是对他们在发展中西文化关系中所做贡献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