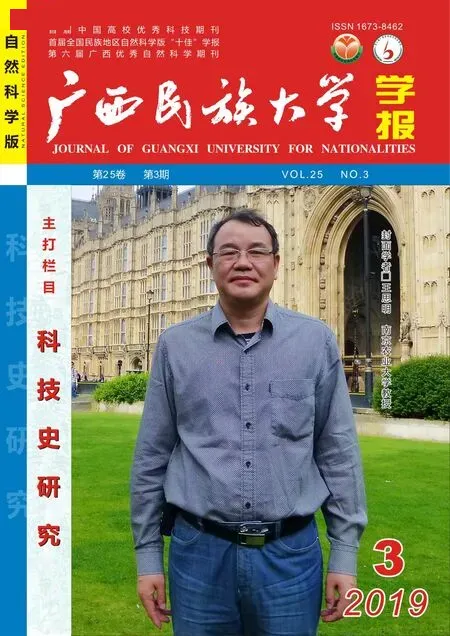科学与政治的互动*
——以女科学家李桓英的麻风病防治事业为例
张会丽
(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0 引言
李桓英,中国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1921年8月21日生于北京,祖籍山西襄垣.1939年,考入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并随校辗转于昆明、重庆与贵阳等地求学.1946年,25岁的李桓英留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师从著名细菌学专家特纳(T.B.Turner)教授.1950-1958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1959年,她在家人都定居美国的同时独自一人回到中国.返回中国后的李桓英在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从事梅毒螺旋体制动和荧光抗体的研究;“文革”期间,她仅用半年时间就认识到了中国麻风病防治的两大弊端,后在苏北农村用土法治疗头癣.改革开放后,李桓英在中国成功实施了世界卫生组织的MDT联合疗法防治麻风病,为麻风病人解除了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枷锁.2001年,李桓英因在麻风病防治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从以上的简介可以看出,李桓英回国后的麻风防治工作几经周折,她在新时期通过适应社会环境并最终在麻风病防治领域做出成绩.这是分析有关科学与政治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文章以李桓英的麻风防治事业为主,分析一位女性科学家是如何在此领域取得成功的,从而揭示科学技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1 新中国麻风病防治概况
1.1 防治麻风病的必要性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共同纲领》中第48条规定“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1]1950年8月7-9日,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基本方针.[2]这三大基本方针的确定为新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提供了政策指导和实施基础.
对于具有政治先进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清除代表旧社会落后的疾病既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优越性的表现.据一份1956年广东省卫生厅举办的“麻风病防治展览会”内容:(1)介绍有关麻风病的症状、传染方式以及防治方法的科学知识;(2)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对麻风病人迫害的情况;(3)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对麻风病人关怀的情况;(4)消灭麻风病规划的介绍.[3]可见,麻风病已经超越了疾病本身所具有的医学范畴,消除疾病代表了新生政府对抗旧政府的成功和社会主义政治的优越性.
从国情方面来讲,这些疾病导致社会劳动力的大量缺失,对当时拥有5亿人口的农业大国来讲,防治疾病也是解放生产力、促进工业发展的必要途径.据1956年1月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28条指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天花、鼠疫、疟疾等.其他疾病,例如:麻疹、赤痢、伤寒等,也应当积极防治……移风易俗,改造国家.”[4]对于麻风病的治疗,更是被视为与农业发展紧密相关的一项任务.20世纪50年代早期,广东有14万多名病人;江苏省约有5万~6万;山东为5万多;福建1.5万名;广西1万;西康1万多.对于麻风病人较多的浙江、云南、贵州等省虽无准确统计数据,但人数尚不在少数.[5]1956年,“初步统计”全国约有38万~39万麻风病患者.由于麻风病的病症之一是致人残疾乃至丧失劳动能力,所以治愈近40万的麻风病患也是增加工农业生产的一项有力措施.
1.2 “大跃进”时期我国的麻风病防治概况
“大跃进”时期,贵州和广西的群众即作两首诗歌颂扬麻风防治工作:
政府办法真周到,隔离治疗实在妙,群众生产无顾虑,病人由死复生了.
麻风害人多少年,昔日刀杀棍棒赶;人民当家做了主,病魔怪蛇都完蛋.太阳出来光万丈,照得旧庄变新庄,照到废人变好人,神仙那比共产党.[6]
诗歌反映了麻风病的治疗与政治先进性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但不免有夸大之嫌.本小节就该时期麻风病的防治情况、防治方法、防治效果等方面进行客观的分析,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考察:新建麻风村与中西医结合治疗.
1957年,在“大跃进”新形势的推动下,各省纷纷提出短时间内消除麻风病的战斗口号,建立麻风村.广东省要求在全省建立麻风病巡回治疗站,防治医生穿隔离衣为病人诊治,使更多的麻风病人能够就近治疗,[7]卫生厅决定在两年内做到全面控制、杜绝传染,而在1956年,广东省麻风病防治机构给出的治疗时限为7年,[8]整整缩短了5年.此外,江苏、江西、陕西等省都根据跃进精神,正在积极开展麻风病防治工作.
麻风隔离点是区、乡、社群众自办的小型隔离组织,以山东莒南县爱国农业社为例,它将传染性麻风病人集中隔离,并对病人的生产和生活做了妥善安排,采取集中隔离治疗与生产自给密切结合的方法;就地隔离治疗措施是一种将麻风病人分散隔离的方法,是在尚未建立麻风村的情况下的过渡阶段,这种方式为数不多,它要求病人单独居住,与家人隔离,由农业社划给病人耕地,医务人员定期检查.[9]麻风村还设置了党、团支部、村委会等组织,村委会下设农副业、文教、保管、财会、保卫等六个股,并划分生产队和自学小组,由农业社赠给耕畜和大型农具,自行种植农作物和饲养牲畜,生产完全自给.[10]
“大跃进”时期,麻风科研工作的目标在于缩短疗程,寻找特效药,中西医必须鼓足干劲,加强钻研,破除迷信,打破陈规.1958年的一篇评论指出:“我们必须在防治麻风病的战线上作促进派”,[11]麻风防治的跃进态势一触即发.药物使用方面,麻风病的防治主要运用氨苯砜单疗和其他土方法治疗,至1959年,全国各地治疗麻风病机构都采用中医中药来治疗,包括愈风膏丸、大枫子油、麻风丸等77种验方,这也是响应中央“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应用实践.[12]以山东省为例,该省使用氨硫脲、氨苯砜、苯丙砜等化学药物和克风露、苦参雄黄丸、小神丸、扫风丸、黄连素等中药的中西医结合疗法.[13]
就“大跃进”时期麻风防治效果而言,可以当时麻风病人数最多的广东省为例.到1959年2月为止,该省已发现的麻风病人95%都已经进行了治疗,几年来共治愈了1357人,其中仅1958年即治愈了709人.[6]19-20这些数字表明,“大跃进”时期有关麻风的防治工作虽积极开展,但因麻风的发现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随着麻风发现率的逐渐上升,麻风患者的治愈数字远远小于整体的麻风病人数.
2 李桓英回国后两次被迫中断的麻风病防治工作
2.1 性病防治与麻风菌的实验室提取
新中国成立后,性病作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已然成为新政府改革社会的顽疾,政府采取了封闭妓院、解放妓女等重大社会改革措施,中央和省、市先后组建了性病防治科研机构,形成了性病防治网络,[14]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以下简称“皮研所”)也应运而生.该所成立于1954年5月,由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院长巴任诺夫和苏联医学专家们按照苏联莫斯科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的模式建所,所址在北京甘水桥原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旧址.建所时共有专家、大夫及其他医务工作人员150余人.所内分设组织指导、实验、职业病调查、皮肤梅毒、泌尿、霉菌、爱克斯光(即X-ray)理疗等主要科室.[15]由时任北京医学院院长胡传揆兼任所长,前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副院长戴正启任副所长,直属中央卫生部领导.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苏联先进的医学科学思想和经验,经过临床实验,来研究矿区的职业性皮肤病、城市内较重要的传染性皮肤病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性病等.[16]1959年3月,刚刚回国的李桓英正式入职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
此时,李桓英即赶上了1960年的“五一献礼”,因其专业所长,她被安排在皮肤梅毒科室搞梅毒螺旋体制动实验(TPI)和荧光抗体的研究.由于当时梅毒螺旋体尚不能体外培养,需要一个适当的培养基,并且得在二氧化碳的条件和无氧的状态下才能够培养,这样就需要花费大量金钱.李桓英曾“带着情绪说”这是“得不偿失”的,她并不赞成这样做,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去做,直至完成“五一献礼”.李桓英对这项实验的态度充分表明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女科学家形象,她认为新中国不应当花费大量金钱来治疗一种很容易治疗的疾病.
1960年以后,李桓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麻风菌的实验室提取,这是她在完成了国家要求的科学研究后自主选择的一次尝试.早在1958年,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各行各业展开,超声波化运动也随即开展.截至1960年5月中旬,北京市共有100万群众参加运动,使用超声波头逾300万个.[17]随着超声波化运动的推进,皮研所顾问马海德提出让李桓英用超声波做麻风抗原的提取工作.此时,虽然李桓英对麻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但她还是从有麻风病患遗体的脾脏内提炼出了抗原——特异性酚醣酯,并在自己身上做实验.
由于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担心麻风病原扩散,就勒令李桓英停止麻风抗原的实验,这是她第一次被迫停止对麻风病的研究.1965年,李桓英转而调查采漆工人和雕漆厂的接触性皮炎和荧光抗体染色,且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2 “文革”期间滨江医院的麻风病防治
李桓英因有在美国学习、工作的经历,在“文革”期间遭到了下放.她对组织的分配不但没有要求,反而自己还贴大字报,要求下放到贫困的农村,解决穷病.此时,李桓英的职业选择与国家大政方针具有“统一性”,公共卫生疾病的治疗需要“群防群治”,这也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方针相契合.
1970年8月,李桓英随研究所从北京迁至江苏省泰州市,后又转至苏北的滨江医院.这是长江北岸的一个很大的麻风病医院,将近一千多人.李桓英在这里第一次切身感受到麻风病对人们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她立志要消除这一病痛.李桓英在查阅国外有关麻风病防治的文章后,了解到早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用氨苯砜治疗麻风病人已经不隔离了,而我国在60年代仍旧隔离.她对这种落后的情况曾说:“国际国内会议都开过,因为氨苯砜治疗已经证明了病人不需要隔离,但我们的翻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怕违反政策就没有翻译.”①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李桓英口述资料:李桓英教授口述访谈1:KS-001-1,20.对于此事,她认为翻译人员只需如实翻译即可,麻风病人隔离与否应交于政府定夺.在下乡期间,李桓英并未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她积极利用仅有的文献材料开展相关研究,这种急于改变国家落后状态的心情正是科学家自我价值的体现.
在滨江医院,李桓英主动和病人握手,不穿隔离衣,检查麻风病人致残的皮肤组织,这种异于其他麻防人员的大胆举止是以她多年的世卫组织工作经验为基础的,也是她学术自信的表现.但是由于“文革”派系斗争,李桓英被要求回到自己的“阵营”(即回到皮肤梅毒科室的“阵营”),加上其他人害怕她这样做会传染,于是,她再一次被迫离开滨江医院的麻风现场.
李桓英曾说:“我愿意在滨江医院待着,待了半年,这就是我的麻风的基地.只待了半年我就知道中国的麻风防治存在什么问题,一是隔离,第二个是长期氨苯砜单一治疗.”②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李桓英口述资料:李桓英教授口述访谈2:KS-001-2,4.疾病本身的特性与政治环境再次改变了她的科学研究轨迹,但李桓英善于在改变中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并展现她的学术价值,她也并不灰心,转而在其他研究领域中从事科研工作.
1972年3月,李桓英离开滨江医院,被派到泰州苏陈公社做巡回医疗,军代表安排她搞头癣.作为主要由西医组成的巡回医疗队队员,她经过调查发现苏陈公社的上百个孩子都患有头癣.年轻的李桓英为了响应中央“把医疗卫生重点放到农村去”①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指出:“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六二六指示”即“把医疗卫生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认为西医教育和诊疗手段不适合农村,随后广大农村出现了大批赤脚医生,将价格低廉的中医药制度引进农村以整合资源.的指示,利用“土法上马”,和同事曹政仁自己培养灰黄霉菌,直接将菌丝体和发酵原料制成水丸,即“灰黄丸”.②“灰黄丸”制作和疗效及注意事项参见:曹正仁、李桓英:《治疗头癣药“灰黄丸”的土法生产介绍》,《赤脚医生杂志》,1976年第12期,第27-28页.该药物不但对头癣有疗效,价格较低,而且还可以在农村自产自用.对于这段工作经历李桓英曾回忆道“那个时候(的工作)是我最得意的工作”.③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李桓英口述资料:李桓英 教授口述访谈1:KS-001-1,27.
2.3 两次被迫中断的麻风防治研究原因分析
如前文所述,1960年之后,李桓英便有机会从事麻风菌的实验室提取工作,这是她主动要求做的科学研究,在将要成功提取麻风菌并应用之际,被皮研所勒令停止研究,理由为:麻风病的传染性.外界的因素迫使李桓英放弃了自己想要做的科学研究.第二次接触麻风病是在“文革”期间,由于在江苏泰州滨江医院的麻风病现场防治经历使她更确切地找出中国麻风病现场防治的弊端:隔离与单一治疗.至于李桓英本人,她虽没有参加政治派别,但仍旧由于政治的影响和麻风这一疾病本身的“特性”(传染性)而被迫离开滨江医院的麻风病院.1959-1976年,只有性病的防治是李桓英主动要求停止的工作,其他均被勒令停止研究.
从李桓英返回中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在皮研所的经历可以看出:国家力量强有力地影响了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这使得李桓英在国家医疗卫生政策主导下从事了不同领域的研究工作,麻风病虽是国家急需解决的难题,但由于社会公众包括国内的医务工作者们对麻风病的认知仍旧停留在隔离治疗上,对其传染性也存在误解,而李桓英根据其在世界卫生组织接受的麻风病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倡导了不隔离和多种治疗的训练,这显然超前于时代,且也没有实现她这一研究计划的条件,这两方面共同导致了李桓英两次被迫停止麻风病研究工作.但是,李桓英仍旧在治疗头癣等方面根据时势、利用环境做出了尽可能的贡献.可见,她并不自怨自艾,而是能够随遇而安、乐观接受并有所作为.
3 新时期麻风病现场防治
3.1 政策变化,项目上马
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世卫组织成立的1946年即为其重要成员国之一;至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此后,新中国也自然成为 WHO控制全球疾病的国家之一.1976年,“文革”结束;此时,世卫组织已在全球开展20年六大热带病防治规划,④即疟疾、血吸虫病、丝虫病、利什曼病、锥虫病和麻风病的防治规划.麻风病作为唯一的细菌性疾病位列其中.而经过了两年的徘徊,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政治压力得到缓解,与世界的交流逐渐加强.社会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变化使得在中国开展麻风防治有了新的契机.
早在1928年12月25日,杭州医院院长洪式闾就写信给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请求拨款扩充热带病研究所,认为我国国民“死于传染病疫者,为数尤众,鼠疫、霍乱、赤痢、白喉等病者,有传染之危险,人尽知之,而以寄生虫及原虫等病原遂致丧失生命者,则似未尝察觉,然其蔓延之广,杀人之众,较之鼠疫、霍乱等殆逾数倍.”[18]但由于经费所限,原计划设立六组二部二馆仅成立了病理学、细菌学及寄生虫动物学三组,并未扩充经费.可见,热带病在中国现代科技史中始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医学问题.
半个世纪后的1979年,李桓英从皮研所调职到刚成立不久的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热研所),该研究所创建于1978年,挂靠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也是我国北方地区唯一的热带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钟惠澜,⑤钟惠澜(1901.8.8-1987.2.6),原籍广东梅州市梅县区雁洋堡 丙村.内科学家、热带病学家和医学寄生虫学家.1922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1934年,他奉派去欧美考察热带病,并在德国汉堡热带医学与卫生学院参加研究工作.1935年底离德返中国协和医院内科及热带病研究室工作,历任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及主治医师.主要开展热带病,特别是寄生虫病的临床与科研工作,建立了热带病形态学、免疫学及分子生物学检查体系,接诊来自北京、全国及世界热带病流行地区归国的热带病患者.
热研所成立后,随即建立了麻风病研究室.李桓英因在皮研所做过麻风菌的实验提取工作,且在1978年作为北京医疗队的成员调查了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公社曼播大队麻风寨的情况,具备一定的现场调查经验.趁着世卫组织的六大热带病规划,她便重新在热研所开展了她的麻风病防治事业.这次机遇始于世界卫生组织热带医学代表团在1979年3月参观了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对该所拟定的麻风研究计划表示赞同,团长卢卡斯(Dr.A.O.Lucas)同意李桓英出国考察美国洛杉矶和亚特兰大两个麻风研究中心,可随后参观并学习伦敦、印度等国的麻风防治经验.①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SG-001-27,李桓英写给北京友谊医院党委的报告,请院党委批准赴美考察学习事宜,1979.4.2.在出国考察前,李桓英与同事张朝秀到广西、云南等地考察选试点,最终选定云南西双版纳州的两个试点,李桓英于1980年3月中旬至江苏泰州皮研所布置两个试点的工作.1980年7月赴美学习和考察.①
在李桓英申请的治疗方案中,她将麻风归纳为多菌型和少菌型两类,利福平、氯苯酚嗪为看服,氨苯砜为自服,具体表现为“正确分型,规则服药,停药后每年进行临床和细菌复查,至少连续5年,最后得出结论”的治疗过程.[19]早在1972年,世卫组织就在马耳他开展联合化疗,②Multidrug Therapy,MDT,即利福平、氯苯酚嗪、氨苯砜规则治疗或至细菌阴转.乔普林(W.H.Jopling)等在1983年对该岛122名病人服用MDT药物后进行了复查,无一例复发.其中,26例平均用药28个月,停药82个月;10例平均用药35个月,停药67个月,但至1984年底仍无复发.[19]73世界其他地区的治疗经验已经表明,三联疗法对于麻风病的治疗是有很大功效的,李桓英之所以将其应用在中国是因为她想探索出一条经济、高效、疗程短的治疗方法.这种理念既与当时中国的国情相关,也与李桓英个人的科研风格和治疗理念相关,即她希望病人能够尽量少吃药达到治愈疾病的效果.
世卫组织在李桓英最初申请MDT现场防治时即给了两公斤的药物,除此之外,还对中国麻风现场防治事业提供了必要的物资和资金资助以及实验室研究帮助.因为李桓英有在农村工作过的经历,她明白基层麻防人员的不易,就向世卫组织申请了15辆汽车;世卫组织不仅支持李桓英个人赴美学习,还对中国省级4个团队学习麻风防治以及统计学和流行病学培训提供资金支持.③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SG-002-30,李桓英写给H.Sansarricq的信,提出送省级4个团队学习麻风防治,1982.05.19.在药品和资金及人员培训等到位之后,李桓英在中国的麻风病现场防治工作终于在1983年云南西双版纳两个试点展开.
3.2 制度保障:基层行政力量的助推
县级专业防治机构的基层防保网是中国麻风病现场防治成功的制度保障,主要表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制度本身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强有力的执行力,同时也与中国逐级负责的行政体制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的麻风病例的发现和治疗主要依靠县级专业防治机构(即县皮肤病防治站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级以下的乡镇卫生院主要承担提供麻风病可疑病例线索和转诊……县级以上综合性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根据条件承担麻风病诊断和转诊工作,并通知患者所在县防治机构,由该防治机构对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20]这仅为县级及县级以下的防治系统.1990年以后,新发现病例,每年由县级防治人员进行详细填写麻风病例个案登记表,每年年底以年报方式向地区、省和国家上报,形成了一套全国麻风病疫情检测系统.
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展麻风防治,其“卫生部有麻风处统管全国,邦及县均有麻风医官;地方也设麻风医官,下辖3~5个非医务督察员;非医务督察员由高年资辅助医务人员受训4个月后充任,下辖4~5个辅助医务人员;后者由2高中毕业学生,受训半年充任,每人负责的地区为:乡村约30个村庄,2万~3万居民;城市1.5万个居民”,[21]如此构成一个垂直的麻风防治系统.但与之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为层级负责制,基层防治人员更有将麻风病的实施情况做到“看服到口”的责任心.印度受中国影响也提出了2000年消灭麻风的计划,但基层保健站作为负责机构却由于麻风防治人员不愿意干,政府也就予以迁就,认为麻风防治计划“交也行,不交就继续干”.中国的防治计划则为必须实现“基本”消灭的目标,这与中央政权的集中管理模式是密切相关的.
基层组织方面,“文化大革命”对李桓英的一个重要影响是让她“能够体验基层人员的心理,工作人员的心理,领导的心理.”④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李桓英口述资料:KS-001-1:李桓英口述访谈1.这段经历使她深知地方官员对实施短程联合化疗的重要带头作用,他们可以使病人由不配合治疗到积极配合.在调查麻风病患者的时候,基层医务人员还遇到过以下事件:
“当时我们去看了以后,我们给每个病人家里粮食,一个像毡子一样的红毯子,我们就说对病人家里面都给一个,当时他们不承认是病人,他们说我们不是麻风病人不吃药,然后我们送去的药,我们刚下那个小竹楼,他就把什么米、毯子摔下来,然后提着刀拿着枪,不让做工作,后来为这个事反映到上面,版纳的领导然后和李大夫一起去,然后开村民大会和大家做工作,要接受这个,既然得了越早治疗越好,最后8个里面有2个没有接受治疗,6个接受了.”⑤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KS-001-8:云南西双版纳州CDC赵志宇访谈.
因防治麻风既关系到地方领导的政绩,也对当地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李桓英便积极利用地方领导的作用,不仅使麻风调查得以顺利进行,而且在后期的MDT联合药物的服用、带头与病人握手、与病人同食等方面促进了麻风现场防治的成功展开.
3.3 人力支持:基层防治人员的辅助
李桓英带领中国基层的麻风防治人员做了有关麻风病在中国分布的详细调查,并制定了实施新疗法的方案和计划,但落实到具体操作时不仅需要药物本身具有显著的疗效,还需要基层麻风病防治人员、患者等各方因素的配合治疗,李桓英作为女性科学家的身份在短期联合化疗现场防治过程中协调各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李桓英的严厉批评与示范带动下,基层麻防人员对待麻风病人的态度由“全副武装”变为愿意与病人亲密接触,并逐渐摆脱了对麻风的恐惧,愿意与病人亲密接触.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麻防科的郭丽珠为例,她于1987年在西双版纳州卫生防疫站从事麻风病防治工作.她曾回忆起当年的麻风病防治情况:
“我到文山州的麻风医院实习的时候,那时候在他们医院,大口罩,大胶鞋,衣领这些都是用胶布,还有包括手袖、手套带,用胶布把它封起来,露的地方就露眼睛,那大胶鞋都是到膝盖的,这是在文山州实习的时候,去麻风医院看病人的时候,老师教我们是这样的.但是我回来第一次参加李教授(的现场防治),除了做病理切片的可以戴口罩,手套,还有做图片的,这几个医生可以戴.其他的全部,教授她本人一样的,她不戴任何(防护服),工作服她也不穿,她做示范.开始我们还是紧张,回到家还是洗手,有时候还是心理作用,会想我们是不是会得麻风病.但随着工作经验和年龄增长,第二次也不怕了,以后也就无所谓了.”①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KS-001-7:云南西双版纳州CDC郭丽珠访谈.
因此,在中国的麻风病现场防治中,李桓英一方面以身作则,带头实施不隔离的疗法,不仅让基层的麻防人员改变以往的做法,还带领他们在“送药到手,看服到口,咽下再走”的口号下,保证每一粒药品都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对待麻风病人,李桓英真正把他们视为需要帮助的人.在云南曼喃醒麻风村,麻风病人对这位北京来的女专家起初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政府治疗了几十年都没有将他们的麻风病治愈,一个女医生怎么就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呢?但李恒英的行动使他们暂时相信了这位女医生,她在治疗过程中耐心疏导和解答麻风病人的疑问,还曾对病人许诺:如果这些药不能治好你们的病,还会拿着新的药物过来,直到治好麻风病为止.
李桓英主持MDT疗法现场防治,果断在麻风患者服药24个月停药,这本身就是早期性格中独立自主、处事果断的表现,同时也是对自己专业能力和药物疗效的准确判断,成为女性科学家鲜明的科研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李桓英的口述访谈中有有关短期停药和基层人员执行力的描述:
“83年正月,春节的时候我才开始治疗.治疗24个月,85年的话正好24个月该下基层去复查,再去做一年复查的时候,做停药复查的时候,说去不了.24个月的时候去不了,最后晚三个月才去,结果他们就治疗了27个月,云南治疗27个月,山东要求治疗27个月.到那个时候你不去的话他们就不停药,我在联合国做报告的时候一说,大家就都笑了.就说麻风这个顽固(疾病),你不来我就不停药.”②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李桓英口述资料:KS-001-1:李桓英口述访谈1,24.
1983-1995年间,中国西南三省试点区共有9307名患者完成短程联合化疗,仅有10人复发,年复发率仅0.03%,远低于世卫组织提出的0.1%的要求.[22]观察结果还表明:每位患者平均节约3-4年的治疗时间;云贵川三省四万余名患者节约与治疗有关的费用5千万元.世卫组织于1994年向全世界推广我国的MDT疗法,李桓英领导的中国麻风病现场防治为世界的麻风病治疗开创了一条快速、高效、经济、实用的新途径,在世界范围内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巨大贡献.世卫组织热带病防治麻风科主任诺丁博士(Dr.S.K.Noordeen)曾对李桓英说:“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4 结语
通过对李桓英回国后开展麻风病防治工作的起承转合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位女性科学家在麻风病防治道路上的起落沉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她的麻风病防治事业既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府号召消灭这一疾病,也由于她的国际热带病防治方法与主流政治力量的主张不一致而中止.改革开放新时期,她调入科研氛围浓厚的热研所,而此时恰值世卫组织在全球开展六大热带病的防治规划,中国即成为其中之一.李桓英善于抓住机遇,利用我国行政制度和地方官员的带头作用,领导基层麻防人员,抓住时代机遇,她的这种不隔离治疗麻风病的方法才在23年后得以全面实施.
可见,当外部环境适宜时,科学家是可以积极运用个人的力量进而推进科技事业发展的.而科技事业的发展既与良好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也与科学工作者在历史洪流中善于积蓄力量、顺应时势、抓住机遇以成就其科学事业有关.人的因素仍旧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科学家个人的科研经历可以揭示科技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